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資深編劇、紀錄片製作人蔡登山,十年前因拍攝張愛玲的電視紀錄片,開始大量閱讀張愛玲的作品及資料,既為她的作品也為她的人生著迷。紀錄片完成後的十年間,他仍多次走訪香港、上海等地,搜尋關於張愛玲的蛛絲馬跡。
本書以張愛玲最掛心的短篇小說〈色,戒〉為主軸,從故事來源,相關史實人物背景,張愛玲如何「偷樑換柱」,何以改寫了二十餘年,又為何拒絕讀者將其「還原」為歷史事件,均有深入的考證和評析。
本書以張愛玲最掛心的短篇小說〈色,戒〉為主軸,從故事來源,相關史實人物背景,張愛玲如何「偷樑換柱」,何以改寫了二十餘年,又為何拒絕讀者將其「還原」為歷史事件,均有深入的考證和評析。
目錄
一、張愛玲的海上舊夢
二、一篇寫了二十多年的小說--〈色,戒〉
三、「七十六號」的兩大魔頭--丁默邨與李士群
四、一山難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
五、一個不尋常的女人--鄭蘋如
六、重尋〈色,戒〉的歷史場景
七、刺丁案的幾種描寫
八、張愛玲的偷樑換柱
九、從〈色,戒〉看張愛玲的愛情投影
十、平心論〈色,戒〉
附錄1、〈色,戒〉故事梗概
附錄2、一篇散佚半世紀的〈鬱金香〉再度飄香
張愛玲未完(後記)
二、一篇寫了二十多年的小說--〈色,戒〉
三、「七十六號」的兩大魔頭--丁默邨與李士群
四、一山難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
五、一個不尋常的女人--鄭蘋如
六、重尋〈色,戒〉的歷史場景
七、刺丁案的幾種描寫
八、張愛玲的偷樑換柱
九、從〈色,戒〉看張愛玲的愛情投影
十、平心論〈色,戒〉
附錄1、〈色,戒〉故事梗概
附錄2、一篇散佚半世紀的〈鬱金香〉再度飄香
張愛玲未完(後記)
試閱
〈色,戒〉故事梗概
抗戰時期,廣州淪陷,嶺南大學遷至香港,借用港大教室上課,女主角王佳芝原是話劇社的當家花旦,在學校演的都是慷慨激昂的愛國歷史劇。男主角易先生隨汪精衛夫婦及陳公博來到香港,王佳芝的同學鄺裕民跟某個副官是小同鄉,無意中得知不少消息。熱血青年們心血來潮,決定定下美人計謀刺易先生,但又不能以學生身份,會讓其有戒心。於是改換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這當然由王佳芝施這位當家花旦擔任了。
王佳芝本質上不過是個小女人,她暗戀鄺裕民,但內斂克制的鄺裕民卻對她無動於衷。「美人計」可是要玩真的,儘管本質上不過是青年們的熱血遊戲。但原本純真的王佳芝為了「色誘」易先生,為了演好這段戲,她不得不提前培養「性經驗」,免得在老奸巨猾的特工易先生的眼中露出破綻,為此她與有過嫖妓經驗的同學梁閏生發生關係,這場「獻身」的戲碼,一切原本都是為了「救國鋤奸」啊,可是到頭來王佳芝卻遭到同學們的竊笑,她因此心懷怨恨,反倒是跟又老又禿的易先生在一起時,才能獲得內心的宣洩與解放,「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沒想到不久之後,易先生突然返回上海,暗殺計畫也跟著流產了。珍珠港事變後,學校又遷回上海,但王佳芝卻獨留在香港,因為她內心惘然,不願再面對過往同學以異樣的眼光來看她。後來,同學們卻再度向她發出召喚,讓她到了上海完成未竟的暗殺行動。
小說的故事一開頭便是王佳芝來到上海後,以「麥太太」的喬裝身份進駐到易太太家並和其「閨中密友」們在牌桌上打牌。牌桌上這些汪偽政府的官太太們大家一身珠光寶氣,每個人似乎都在比手中的鑽戒,唯獨王佳芝沒有鑽戒,只戴了隻翡翠,早知她就不戴了,叫人見笑。易先生進來了,跟三個女客點頭招呼。然後站在易太太背後看牌,牌局中大家又談到鑽戒,易太太抱怨上次易先生捨不的買那隻「火油鑽」給她,易先生白了她說,那隻十幾克拉的「火油鑽」,若戴在她的手上,連牌都打不動了。然後乘在胡牌之際,易先生向王佳芝使了眼色。王佳芝明白了,借機離開牌桌,眾人不放,她費盡唇舌方才脫身。
她回到自己臥室裡,也沒換衣服,匆匆收拾一下,女傭已經來回說車在門口等著。她乘易家的汽車出去,在南京路上的咖啡館等候易先生。她到櫃臺借了電話已暗語告知鄺裕民,要在今晚假借「修耳釘」的名目把易先生騙到暗殺地點:珠寶店,請暗殺小組埋伏好在那裏。在焦慮的等待期間,從前的種種複雜心緒掠上心頭,王佳芝想起與易先生的種種曖昧場面,以及這兩年的經歷,內心五味雜呈、徘徊不定。易先生終於來了,他儘管心狠手辣老謀深算,卻也想不到眼前這個跟自己暗渡陳倉兩年的小情人兒,會是「致命的吸引力」。
兩人曖昧一番,終於來到珠寶店。易先生要買個捨不得買給太太的「火油鑽」給她,而王佳芝著那粉紅鑽戒,紅得有種神秘感,但她心想「可惜不過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這麼一會功夫,使人感到惆悵。」珠寶店外,槍手埋伏。王佳芝內心焦慮,「這時候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怎樣,在這小樓上難免覺得是高坐在火藥桶上,馬上就要給炸飛了,兩條腿都有點虛軟。」。而在易先生低頭為她挑選戒指的一霎那間,王佳芝從他臉上笑容突然感受到這個男人對自己的「愛」,於是在緊要關頭她示意易先生「快走」。易先生臉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來奪門而出,砲彈似的直射出去。只聽見汽車吱的一聲尖叫,彷彿直聳起來,砰!關上車門--還是鎗聲?--橫衝直撞開走了。易先生死裡逃生了,但王佳芝卻渾身疲軟地走出珠寶店,人行道上熙來攘往,車如流水,但只有她一個人心慌意亂地。
未幾,易先生一通電話打去,南京路被封鎖。某個參與暗殺行動的熱血青年被捕,馬上招供。不到晚上十點,除了一條漏網之魚,暗殺團成員全被處決,包括王佳芝。
易先生回到家,太太們還在打麻將,吵吵著要讓他請客吃飯。易先生不動聲色,心裏卻在想著王佳芝。易先生覺得,這個女人真是「愛」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可他必須殺她,「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她也不會愛他。在太太們的喧笑聲中,易先生悄然走了出去。
刺丁案的幾種描寫 蔡登山
張愛玲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間,迅速地走紅於上海,據柯靈回憶說:「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青海晏在印行。」這是文學前輩對她的關心。
其時鄭振鐸也滯留在淪陷的上海,而且由於他在文壇上的高知名度,使他成為敵偽拉攏的對象。據學者陳福康在《鄭振鐸傳》一書中說,「孤島」剛開始時,有一位已「落水」的過去的「朋友」來看他,說什麼日本人很欽佩他,想仰仗他出來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等等,並拿出一張數額巨大的支票,說是一個叫「清水」的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人送給他的。這簡直是瞎了狗眼!他氣得橫眉怒眦,怒髮衝冠,當場把支票撕個粉碎,痛斥了這位「朋友」。此人狼狽不堪地逃走了,他卻氣惱了好幾天,總是念叨著:「士可殺,不可辱!」「豈有此理!真正豈有此理!」。而後來有一次他在中國書店看書,一位伙計悄悄地走過來,用極細微的聲音對他說:「來了一個日本人,叫清水。」他轉身繼續翻他的書。這日本人用流利的漢語說:「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於版本之學的鄭振鐸先生及潘博山先生等,很想認識鄭先生。」一位伙計用眼色來探詢他,他連忙搖搖頭,並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著。伙計們便對清水說:「鄭先生長久不來了,也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等清水走後,他趕緊又到其他各家舊書店,一一叮囑:今後凡日本人或不明身份的人來打聽他,一概回答不知道。
對他利誘不成,敵人便準備下毒手了。據說大約在一九三八年早春的一個早晨,一位重慶方面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曹俊,闖進他家門,要他快走。一問,才知道曹君半夜得到情報,「七十六號」要通過租界工部局「引渡」一批愛國文化人士,其中有鄭振鐸,是作為復社嫌疑份子而列入黑名單的。他及時轉移,躲過追捕。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晚,友人徐蔚南忽然來電話,說「七十六號」要綁架他,經他向一位姓張的朋友詢問,列為黑名單的共有十四人,都是「文藝界救亡協會」的負責人。於是,當夜他就緊急轉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投降了。緊接著好友柯靈、唐弢來找過他,說準備辦一個綜合性的週刊。柯靈原先想取名《自由中國》,後來打算叫《周報》。鄭振鐸也贊成叫《周報》,他更答應為《周報》撰稿。他還告訴他們他正在寫《蟄居散記》,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給《周報》連載。同年九月八日《周報》創刊,馬上成為戰後上海乃至全國新創辦的第一份綜合性週刊。從第一期起,就連載鄭振鐸的《蟄居散記》。那是鄭振鐸在上海淪陷期間所見所聞的回憶錄,第一篇是〈暮影籠罩了一切〉發表於九月十五日的《周報》。第二篇是〈記劉張二先生的被刺〉發表於九月二十二日的《周報》。第三篇是〈「封鎖」線內外〉發表於九月二十九日的《周報》。十月六日則發表〈一個女間諜〉、十月十三日則發表〈鵜鶘與魚〉,一直連載到一九四六年間,前後一共二十五篇,只是後來在一九五一年上海出版公司作為「文藝復興叢書」出版的《蟄居散記》,只收了二十篇,〈一個女間諜〉等五篇並未收錄。
鄭振鐸在〈鵜鶘與魚〉文中,將這些漢奸比喻為鵜鶘,他說「鵜鶘們為漁人所喂養,發揮著他們捕捉魚兒的天性,為漁人幹著這種可怖的殺魚的事業。」「在人間,在淪陷區裡,也正演奏著鵜鶘們的『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把戲。當上海在暮影籠罩下,蝙蝠們開始在亂飛,狐兔們漸漸的由洞穴裡爬了出來時,敵人的特工人員(後來是「七十六號」裡的東西),便像夏天的臭蟲,從板縫裡鑽出來找『血』喝。」至於〈記劉張二先生的被刺〉則是記述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和《大美晚報》記者張似旭的被暗殺。鄭振鐸說「我執著報紙的手因憤激而微微的抖著。友人們李第一個為國犧牲的人;第一個死於自己人的手裡的人!我不能相信:竟會有人替敵人來暗殺愛國之士的!」
在〈一個女間諜〉文中,鄭振鐸這麼描述著:
我國的女間諜們的故事,時時有得聽到,說得是那麼神出鬼沒,然而後來卻證實都是些子虛烏有之談。
我所遇到的卻是一個真實的女間諜,一件真實的悲慘的故事。
有一個青年友人,行為很整飭,但在一個時期,人家傳說他常和一個女友在一處。這女友的行為相當的「浪漫」,時時的出入於歌壇舞榭,且也時時的和敵人及漢奸們相交往。
我曾經勸告過他。他只是笑笑,不否認也不承認。我不便多問什麼。
有一天,在霞飛路上一家咖啡館裡見到了,他和一個女友在一處,談得很起勁。我只和他點頭招呼。他介紹著道:「這位是陳女士。」我們互相微頷了一下。
這位陳女士身材適中,面型豐滿;穿得衣服並不怎樣刺眼,素樸,但顯得華貴;頭髮並不捲燙,朝後梳了一個髻,乾淨俐落。純然是一位少奶奶型的人物,並不向一個「浪漫」的女子。
隔了一個多月,他跑來告訴我道:「你見過的那位陳女士已經殉難死了!」
我嚇得一跳,問道:「為了什麼呢?」
「她是一位女間諜,」他道,「曾經刺探到不少敵人和漢奸們的消息和行動。她的父親是一位法院裡的檢察官,她的母親是一位日本人。她的日本話說得很好。因此,好久就已混入漢奸群中工作著。最近幾個月,她常常警覺到有人跟隨著她,注意或監視著她。她覺得有危險。有一夜,她在一個跳舞的地方,發現她的手提包失蹤了。隔了一會,她舞罷回到座上時,又發現手提包已經放在原處。檢點一下,沒有短少什麼。但她知道這手提包一定曾被嚴密的檢查過。她把這事告訴我,說,也許會有什麼危險吧。但神色很鎮定,一點也沒有退避或躲藏的意思。照常的生活著,照常的刺偵著。」
「後來怎樣的被破獲的呢?」
「我知道她被捕的消息已在她殉難之後。這是另一位做工作的人告訴我的。她計畫著要刺殺丁默邨,那個『七十六號』的主人。在一個清晨,丁伴她到一家百貨公司去購物。壯士們已經埋伏好在那裡。丁富有警覺性,也許,也竟已準備好,一進門,便溜了出來,來不及放一槍。為了到這個地方去的事,只有她一個人知道,因之,她的嫌疑極重。她被捕了,經過了殘酷和刑訊之後,她便從容就義了。」
他說完了話,默默的為這位女英雄誌哀,我也默默的在哀悼著僅見一面的這位愛國的女間諜!
鄭振鐸的〈一個女間諜〉是刺丁案最早被寫成文章的,但偏重於報導性質,並沒有太多的細節得描寫。鄭振鐸藉此來歌頌抗日的愛國行為,多過於小說的經營,況且它還不是以小說的型態出現。文章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在《周報》發表,雖然在當時該報是上海相當暢銷的刊物,主編柯靈又是提拔過張愛玲的,但我們也無任何證據證明張愛玲看過該文章。
相對於鄭振鐸,金雄白因為是出入於汪偽集團的,因此他知道得更仔細,而很多細節他雖沒有親見,但確是親聞的,因此其可信度相當高。胡蘭成在汪偽集團的身份地位,不亞於金雄白,金雄白所知道的事,胡蘭成不可不知。而以胡蘭成的個性,他極可能將這種爆炸性的內幕,炫耀地說給張愛玲聽,因此我們可以假設金雄白所描述的情節,張愛玲是聽過的。
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有「鄭蘋如謀刺丁默邨顛末」一節:
在汪政權中,太多醇酒婦人之輩,而「七十六號」的特工首領丁默邨,尤其是一個色中餓鬼,他雖然支離病骨,弱不禁風,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壯陽藥仍然是他為縱慾而不離身的法寶,他當年與女伶童芷苓的繾綣,早成公開秘密,而鄭蘋如的間諜案,更是遐邇喧傳。海外書報中曾有不少有記述此案的經過,可惜有些是語焉不詳,而有些則與事實相去太遠。
鄭蘋如是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檢察官鄭鉞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國學校讀書,家住法租界法國花園附近的呂班陸萬宜坊。萬宜坊中有著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躍如鄒韜奮,豔麗如鄭蘋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時期住過那裡,每天傍晚,鄭蘋如常常騎了一輛腳踏車由學校返家,必然經過我的門口,一個鵝蛋臉,配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確有動人丰韻。不知她怎樣竟加入了軍統任間諜工作?又不知怎樣竟然會與汪方的特工首領丁默邨發生了曖昧關係?
丁鄭之間的往來,已經有了好幾個月,丁默邨是個特工首領,處於那時的環境中,對事事物物,樣樣提防,而唯獨對於鄭二小姐卻十分放心,數月之間,也從沒有發現她任何可疑之點。一天,默邨在滬西一個朋友家裡吃中飯,臨時打電話邀鄭蘋如來參加。飯後,默邨要到虹口去,鄭蘋如也說要到南京路去,於是,同車而行。從滬西至南京路或虹口,靜安寺路都是必經之道。當車經靜安寺路西伯利亞皮貨店門口時,鄭蘋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亞買一件皮大衣,嬲著默邨同他一起下車幫她挑選。特工人員知道到一個沒有預先約定的地點,而停留不逾半小時,認為決沒有發生危險的可能。默邨以為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種需索的手段而已,於是坦然隨她下車。汽車是停在西伯利亞馬路對面的路側,該店是兩開間的門面,當他們兩人穿過馬路到達店門時,默邨看到有兩個形跡可疑的彪形大漢,腋下各挾有大紙包一個,裡面顯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對。而默邨在此緊要關頭,能持以鎮靜,毫不慌張。仍昂然直入店內,而一轉身即毫不停留,撇開了鄭蘋如,由另一扇門狂奔而出,穿過馬路,躍上自己坐來的保險汽車。兩大漢以為默邨進店,至少要有幾分鐘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過馬路上車,立即拔槍轟擊,但為時已晚,祇車身上中了十幾槍,彈痕斑斑,而默邨則毫髮無損,汽車也急馳而去。
重尋〈色,戒〉的歷史場景 蔡登山
張愛玲的小說〈色,戒〉,雖諸多論者都指向她是以鄭蘋如謀刺丁默邨為原型的,但張愛玲卻始終沒有明確的承認過。儘管如此,小說一開頭就提到曾仲鳴已經在河內被暗殺了,汪精衛從重慶出來,到了香港,再到了上海,這無疑地都合乎史實的。因此它不同於其他張愛玲的小說,你或許不需知道她小說背後的「本事」,但它並不妨礙你對小說的了解;但對於〈色,戒〉而言,追索小說的「本事」,卻有助於對小說的通盤了解,甚至你更可從張愛玲的「改寫」過程中,看到她所謂的「靈魂的偷渡」。因此我們就從小說或是它的「本事」中的幾個歷史場景說起。
(一)從「從金屋藏嬌」到「禍國殃民」的「汪公館」
在上海愚園路上有兩處最有名的花園洋房,其中一處即是現在做為「長寧區少年宮」的「汪公館」。「汪公館」是上海淪陷時期汪精衛的公館,是一幢豪華精美的西班牙式別墅,園內一方平整的綠茵,把小樓映襯得格外雍容。
「汪公館」坐落在現今愚園路1136弄31號(原為愚園路310號)。其實「汪公館」本應稱為「王公館」,因為它的主人是戰前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兼上海大夏大學校長的王伯群。
王伯群,原名文選,字蔭泰,1885年生於貴州省興義縣景家屯,其父王起元以辦團練而聞名鄉里。1905年他得舅父劉顯世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五年後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期間並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王伯群回到家鄉,與其弟王文華、妹夫何應欽,以黔系領導人物折衝於各系軍閥之間。
1924年夏,廈門大學發生學潮,200多名學生失學,部分教授為學生鳴不平辭職來到上海。王伯群時在上海當寓公,便捐款2000元與這些教授辦起了大夏大學。初任校董會主席,兩年後因馬君武辭校長職,王伯群繼任校長。「四一二」清黨後,他因有何應欽為背景,乃於1928年出任交通部長兼招商局監督。
王伯群出任交通部長後,仍兼大夏大學校長一職。在一次學校慶典活動上,時有「校花」之稱的學生保志寧上臺向他獻花,這位早過不惑之年的部長兼校長竟對這朵整整小他26歲的「校花」一見鍾情,從此苦苦追求。保志寧是滿清貴族後裔,家住南通。其父在南京政府供職,其叔保君健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長。保志寧人長得眉清目秀,且善辭令,原就讀滬江大學,以其「才貌雙全,男同學之追求者多而切,不勝其擾,乃轉學大夏大學」。王伯群原有一妻二妾,妻子去世後,一位姨太太先遭遺棄,另一位也在他與保志寧談論婚嫁時亦遭「編遣」。
王伯群與保志寧的婚禮於1935年6月18日在上海徐園舉行,證婚人為「黨國」元老許世英、張群。據說王、保兩人當初議及婚嫁時,保志寧曾提出三個條件:一,贈其嫁妝10萬元;二,婚後供其出洋留學;三,為其購置一幢花園別墅。其中購置花園別墅一項,恰巧當時辛豐記營造廠正在承建南京交通部辦公樓及上海大夏大學的教學樓,於是王伯群便一併交該承建商「代勞」了。他選定愚園路上的屋址後,即於1930年破土動工,歷時四年,於1934年落成。辛豐記老闆為取悅王部長,可謂不惜工本,所用材料中的硬木地板、金山石、馬賽克瓷磚、牛皮石灰等,堪稱高檔。該別墅由協隆洋行(A.J.Yaron)設計,主樓為四層,其中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係鋼筋混凝土結構,坐北朝南,外形為哥德式,但局部立面帶有西班牙式建築風格。建築為對稱佈局,中央有室外大樓梯越過半地下室的底層,直接進入一樓門廳。整幢建築有大、小二廳,房間32間。客廳採用東方傳統藝術裝飾,樑柱平頂飾以彩繪,配以壁畫。地坪採用柚木鑲嵌成蘆蔗紋圖案,踏步欄杆也用柚木製成,室內扶梯花紋則用紫銅仿古鑄造。起居室呈西班牙古典裝飾,書房、臥室則採用不同的摩登風格,還專闢有女主人閨中會客室,用以款待女眷,於豪華中顯示高雅。主樓南側是一片開闊的草地,遍植花木,亭台假山、小橋流水點綴其間,盡顯幽雅。四周圍牆築成城堡式,牆壁塑有梅花圖案,就連門窗拉手也全用紫銅開模,鏤空鑄成松花圖案,其風格與主樓一脈相承。
當時輿論界對這位「老」校長娶「小校花」本有微詞,如今又冒出來這幢美輪美奐的「金屋」,自然是群起而攻之。其中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更是迎頭痛擊。於是就有監察委員提出彈劾案,1935年底王伯群因此被迫辭職。時人戲稱王伯群是「娶了一個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丟了一個官職。」,然因有何應欽做靠山,王伯群仍保留國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委員頭銜。1937年抗戰爆發,王伯群隨大夏大學遷至貴陽,撤離上海後,該建築由保志寧叔父保君健代管。保志寧作為「金屋」的第一任女主人,卻僅住了二年半的時光。
上海淪陷後,該「金屋」被汪精衛作為偽政權駐滬辦公聯絡處,人稱「汪公館」。1939年5月6日,汪精衛和陳璧君在日本特務影佐禎昭的陪同下,乘「北光丸」來到上海。儘管汪精衛在上海的福履理路(今建國西路)570號及愚園路738弄內都有公館,但日寇出於安全考慮,還是讓他暫住在東體育會路7號的「重光堂」,那裏是出名的日本特務「土肥原機關」的所在地。同住的還有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後來汪精衛又搬到西江灣路上的日軍原西尾中將寓所居住,由日本憲兵保護,連汪的貼身衛士都不許隨便出入。日方認為如此一來,汪精衛等人就都成了甕中之鼈,連活動都受到限制,遑論開展「和平運動」。為了便於監控,於是土肥原與影佐禎昭決定將愚園路上的「王公館」撥給汪精衛使用,因為該公館只有愚園路一個出口,便於安全警衛,又因1136弄內另有十幾幢洋房,可以將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陳春圃、羅君強等漢奸也一併遷往那裏居住。安全由「76號」特工負責。於是丁默邨、李士群乃下令,將弄內住戶全部趕走,接著在牆垣上高築電網,四角設置瞭望亭,門窗裝上鐵門、鐵柵。弄堂內外除「76號」特務大隊長張魯率100餘人日夜把守外,日本憲兵也派出一個便衣小隊在弄口盤查行人,出入須持特別通行證。
一切安排停當,汪精衛就在他的寓所裏召集大、小漢奸們開起了偽國民黨「六全一中全會」,自任「主席」。1939年7月9日晚,他還在公館樓前發表〈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廣播講話,日本攝影師為之拍攝新聞紀錄片。直至次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衛才遷往南京頤和路公館居住,但愚園路上的「王公館」仍是他在上海的「行宮」。
(二)汪、日談判地點之一:愚園路1136弄60號
在汪、日談判的過程中,代表日方的是以影佐禎昭為主,因此也稱「影佐機關」或「梅機關」。當時正式的談判從1939年11月1日開始,地點則先在虹口的「六三花園」,後來因為則因為汪精衛等一群人都搬到愚園路住,於是雙方談判的地點也改在愚園路1136弄60號的地點,它距離「汪公館」的1136弄31號,只有幾步之遙。談判中代表汪精衛之一的陶希聖,一度都在此地住過。
(三)殺人不眨眼的「七十六號」魔窟
張愛玲的〈色,戒〉中男主角易先生,被認為是以丁默邨為原型的。而整個情節及發生的場景,脫離不了令人聞風喪膽的所謂「七十六」魔窟。它座落在當年滬西的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也就是現今的萬航度路435號。
極司斐爾路當年屬越界築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強行修築起來的一條馬路,因此路權歸工部局巡捕房管理,路的兩側仍屬華界。「七十六號」就坐落於極司斐爾路中段,它原是陳調元的私宅。陳調元原係北洋軍閥直系將領,曾任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當年,這裏是陳調元做壽、唱堂會的地方。抗戰爆發後,「七十六號」為日軍佔領,經晴氣慶胤少佐的撮合,把它撥給丁默邨、李士群做活動場所。
丁默邨、李士群的漢奸特務組織在與汪精衛集團同流合污前,已經兩易其駐地了。由於特工隊伍人數迅速增加和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他們先從大西路六十七號搬到了憶定盤路九十五弄十號的一座洋房,因對外均由李士群的妻子葉吉卿出面,故稱「葉公館」。但不久,他們又感到這裏並不理想,因為它位處弄堂裏,連一輛汽車都無法掉頭,平時為了安全,只好在弄堂口擺起兩個水果攤,作為望風瞭哨,還派人不時在弄堂裏進進出出地巡視,這既不體面,又不大方便。最後,由晴氣慶胤少佐親自選定,搬進了滬西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這就是後來上海人一提到它,無不談虎色變的汪偽特務魔窟。
為了適宜工作的需要,根據丁默邨的設計,他們首先對「七十六號」內的房屋做了改造,把原先的洋式二道門改為牌樓式,在兩側的牆上開了兩個洞,安裝兩挺輕機槍。二道門內的東邊,南北相對地新蓋了二十多間平房,做為「警衛總隊」的辦公室和審訊室;西邊添造了一幢兩開間的樓房,做為電訊室。花園裏的一個大花棚,改做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樣新穎精緻的三開間平洋房,由日本憲兵佔用,進行現場「指導」和監視。「七十六號」的主要建築物是正中的那座高洋房,樓下是會客室、電話接線室、貯藏室以及餐廳、會議室等,樓上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寢室兼辦公室。三樓有兩個房間,作「犯人優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開間、兩進的石庫門樓房,四周有走馬樓。在走馬樓中間的天井上搭了一個玻璃棚,把樓下的前後兩廂與客堂打通,改做大廳,再搭上一個講臺,算是大禮堂。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就在這裏舉行。
除在「七十六號」大興土木外,丁默邨,李士群又在日本特務機關的許可下,
強行將「七十六號」右側一條名叫「華邨」弄內的住戶統統遷出,佔領了該弄二十餘幢二層樓的小洋房,作為汪偽國民黨中央社會部、肅清委員會與特工總部的高級官員的家屬住宅。為了安全,他們將靠馬路的弄堂口堵死,在「華邨」東首與「七十六號」大門內相隔的牆壁上開了一個便門,所有居住在「華邨」的人,一一發給出入證,,概由「七十六號」大門進出。
抗戰時期,廣州淪陷,嶺南大學遷至香港,借用港大教室上課,女主角王佳芝原是話劇社的當家花旦,在學校演的都是慷慨激昂的愛國歷史劇。男主角易先生隨汪精衛夫婦及陳公博來到香港,王佳芝的同學鄺裕民跟某個副官是小同鄉,無意中得知不少消息。熱血青年們心血來潮,決定定下美人計謀刺易先生,但又不能以學生身份,會讓其有戒心。於是改換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這當然由王佳芝施這位當家花旦擔任了。
王佳芝本質上不過是個小女人,她暗戀鄺裕民,但內斂克制的鄺裕民卻對她無動於衷。「美人計」可是要玩真的,儘管本質上不過是青年們的熱血遊戲。但原本純真的王佳芝為了「色誘」易先生,為了演好這段戲,她不得不提前培養「性經驗」,免得在老奸巨猾的特工易先生的眼中露出破綻,為此她與有過嫖妓經驗的同學梁閏生發生關係,這場「獻身」的戲碼,一切原本都是為了「救國鋤奸」啊,可是到頭來王佳芝卻遭到同學們的竊笑,她因此心懷怨恨,反倒是跟又老又禿的易先生在一起時,才能獲得內心的宣洩與解放,「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沒想到不久之後,易先生突然返回上海,暗殺計畫也跟著流產了。珍珠港事變後,學校又遷回上海,但王佳芝卻獨留在香港,因為她內心惘然,不願再面對過往同學以異樣的眼光來看她。後來,同學們卻再度向她發出召喚,讓她到了上海完成未竟的暗殺行動。
小說的故事一開頭便是王佳芝來到上海後,以「麥太太」的喬裝身份進駐到易太太家並和其「閨中密友」們在牌桌上打牌。牌桌上這些汪偽政府的官太太們大家一身珠光寶氣,每個人似乎都在比手中的鑽戒,唯獨王佳芝沒有鑽戒,只戴了隻翡翠,早知她就不戴了,叫人見笑。易先生進來了,跟三個女客點頭招呼。然後站在易太太背後看牌,牌局中大家又談到鑽戒,易太太抱怨上次易先生捨不的買那隻「火油鑽」給她,易先生白了她說,那隻十幾克拉的「火油鑽」,若戴在她的手上,連牌都打不動了。然後乘在胡牌之際,易先生向王佳芝使了眼色。王佳芝明白了,借機離開牌桌,眾人不放,她費盡唇舌方才脫身。
她回到自己臥室裡,也沒換衣服,匆匆收拾一下,女傭已經來回說車在門口等著。她乘易家的汽車出去,在南京路上的咖啡館等候易先生。她到櫃臺借了電話已暗語告知鄺裕民,要在今晚假借「修耳釘」的名目把易先生騙到暗殺地點:珠寶店,請暗殺小組埋伏好在那裏。在焦慮的等待期間,從前的種種複雜心緒掠上心頭,王佳芝想起與易先生的種種曖昧場面,以及這兩年的經歷,內心五味雜呈、徘徊不定。易先生終於來了,他儘管心狠手辣老謀深算,卻也想不到眼前這個跟自己暗渡陳倉兩年的小情人兒,會是「致命的吸引力」。
兩人曖昧一番,終於來到珠寶店。易先生要買個捨不得買給太太的「火油鑽」給她,而王佳芝著那粉紅鑽戒,紅得有種神秘感,但她心想「可惜不過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這麼一會功夫,使人感到惆悵。」珠寶店外,槍手埋伏。王佳芝內心焦慮,「這時候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怎樣,在這小樓上難免覺得是高坐在火藥桶上,馬上就要給炸飛了,兩條腿都有點虛軟。」。而在易先生低頭為她挑選戒指的一霎那間,王佳芝從他臉上笑容突然感受到這個男人對自己的「愛」,於是在緊要關頭她示意易先生「快走」。易先生臉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來奪門而出,砲彈似的直射出去。只聽見汽車吱的一聲尖叫,彷彿直聳起來,砰!關上車門--還是鎗聲?--橫衝直撞開走了。易先生死裡逃生了,但王佳芝卻渾身疲軟地走出珠寶店,人行道上熙來攘往,車如流水,但只有她一個人心慌意亂地。
未幾,易先生一通電話打去,南京路被封鎖。某個參與暗殺行動的熱血青年被捕,馬上招供。不到晚上十點,除了一條漏網之魚,暗殺團成員全被處決,包括王佳芝。
易先生回到家,太太們還在打麻將,吵吵著要讓他請客吃飯。易先生不動聲色,心裏卻在想著王佳芝。易先生覺得,這個女人真是「愛」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可他必須殺她,「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她也不會愛他。在太太們的喧笑聲中,易先生悄然走了出去。
刺丁案的幾種描寫 蔡登山
張愛玲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間,迅速地走紅於上海,據柯靈回憶說:「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青海晏在印行。」這是文學前輩對她的關心。
其時鄭振鐸也滯留在淪陷的上海,而且由於他在文壇上的高知名度,使他成為敵偽拉攏的對象。據學者陳福康在《鄭振鐸傳》一書中說,「孤島」剛開始時,有一位已「落水」的過去的「朋友」來看他,說什麼日本人很欽佩他,想仰仗他出來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等等,並拿出一張數額巨大的支票,說是一個叫「清水」的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人送給他的。這簡直是瞎了狗眼!他氣得橫眉怒眦,怒髮衝冠,當場把支票撕個粉碎,痛斥了這位「朋友」。此人狼狽不堪地逃走了,他卻氣惱了好幾天,總是念叨著:「士可殺,不可辱!」「豈有此理!真正豈有此理!」。而後來有一次他在中國書店看書,一位伙計悄悄地走過來,用極細微的聲音對他說:「來了一個日本人,叫清水。」他轉身繼續翻他的書。這日本人用流利的漢語說:「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於版本之學的鄭振鐸先生及潘博山先生等,很想認識鄭先生。」一位伙計用眼色來探詢他,他連忙搖搖頭,並站起來在書架上亂翻著。伙計們便對清水說:「鄭先生長久不來了,也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等清水走後,他趕緊又到其他各家舊書店,一一叮囑:今後凡日本人或不明身份的人來打聽他,一概回答不知道。
對他利誘不成,敵人便準備下毒手了。據說大約在一九三八年早春的一個早晨,一位重慶方面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曹俊,闖進他家門,要他快走。一問,才知道曹君半夜得到情報,「七十六號」要通過租界工部局「引渡」一批愛國文化人士,其中有鄭振鐸,是作為復社嫌疑份子而列入黑名單的。他及時轉移,躲過追捕。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晚,友人徐蔚南忽然來電話,說「七十六號」要綁架他,經他向一位姓張的朋友詢問,列為黑名單的共有十四人,都是「文藝界救亡協會」的負責人。於是,當夜他就緊急轉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投降了。緊接著好友柯靈、唐弢來找過他,說準備辦一個綜合性的週刊。柯靈原先想取名《自由中國》,後來打算叫《周報》。鄭振鐸也贊成叫《周報》,他更答應為《周報》撰稿。他還告訴他們他正在寫《蟄居散記》,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給《周報》連載。同年九月八日《周報》創刊,馬上成為戰後上海乃至全國新創辦的第一份綜合性週刊。從第一期起,就連載鄭振鐸的《蟄居散記》。那是鄭振鐸在上海淪陷期間所見所聞的回憶錄,第一篇是〈暮影籠罩了一切〉發表於九月十五日的《周報》。第二篇是〈記劉張二先生的被刺〉發表於九月二十二日的《周報》。第三篇是〈「封鎖」線內外〉發表於九月二十九日的《周報》。十月六日則發表〈一個女間諜〉、十月十三日則發表〈鵜鶘與魚〉,一直連載到一九四六年間,前後一共二十五篇,只是後來在一九五一年上海出版公司作為「文藝復興叢書」出版的《蟄居散記》,只收了二十篇,〈一個女間諜〉等五篇並未收錄。
鄭振鐸在〈鵜鶘與魚〉文中,將這些漢奸比喻為鵜鶘,他說「鵜鶘們為漁人所喂養,發揮著他們捕捉魚兒的天性,為漁人幹著這種可怖的殺魚的事業。」「在人間,在淪陷區裡,也正演奏著鵜鶘們的『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把戲。當上海在暮影籠罩下,蝙蝠們開始在亂飛,狐兔們漸漸的由洞穴裡爬了出來時,敵人的特工人員(後來是「七十六號」裡的東西),便像夏天的臭蟲,從板縫裡鑽出來找『血』喝。」至於〈記劉張二先生的被刺〉則是記述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和《大美晚報》記者張似旭的被暗殺。鄭振鐸說「我執著報紙的手因憤激而微微的抖著。友人們李第一個為國犧牲的人;第一個死於自己人的手裡的人!我不能相信:竟會有人替敵人來暗殺愛國之士的!」
在〈一個女間諜〉文中,鄭振鐸這麼描述著:
我國的女間諜們的故事,時時有得聽到,說得是那麼神出鬼沒,然而後來卻證實都是些子虛烏有之談。
我所遇到的卻是一個真實的女間諜,一件真實的悲慘的故事。
有一個青年友人,行為很整飭,但在一個時期,人家傳說他常和一個女友在一處。這女友的行為相當的「浪漫」,時時的出入於歌壇舞榭,且也時時的和敵人及漢奸們相交往。
我曾經勸告過他。他只是笑笑,不否認也不承認。我不便多問什麼。
有一天,在霞飛路上一家咖啡館裡見到了,他和一個女友在一處,談得很起勁。我只和他點頭招呼。他介紹著道:「這位是陳女士。」我們互相微頷了一下。
這位陳女士身材適中,面型豐滿;穿得衣服並不怎樣刺眼,素樸,但顯得華貴;頭髮並不捲燙,朝後梳了一個髻,乾淨俐落。純然是一位少奶奶型的人物,並不向一個「浪漫」的女子。
隔了一個多月,他跑來告訴我道:「你見過的那位陳女士已經殉難死了!」
我嚇得一跳,問道:「為了什麼呢?」
「她是一位女間諜,」他道,「曾經刺探到不少敵人和漢奸們的消息和行動。她的父親是一位法院裡的檢察官,她的母親是一位日本人。她的日本話說得很好。因此,好久就已混入漢奸群中工作著。最近幾個月,她常常警覺到有人跟隨著她,注意或監視著她。她覺得有危險。有一夜,她在一個跳舞的地方,發現她的手提包失蹤了。隔了一會,她舞罷回到座上時,又發現手提包已經放在原處。檢點一下,沒有短少什麼。但她知道這手提包一定曾被嚴密的檢查過。她把這事告訴我,說,也許會有什麼危險吧。但神色很鎮定,一點也沒有退避或躲藏的意思。照常的生活著,照常的刺偵著。」
「後來怎樣的被破獲的呢?」
「我知道她被捕的消息已在她殉難之後。這是另一位做工作的人告訴我的。她計畫著要刺殺丁默邨,那個『七十六號』的主人。在一個清晨,丁伴她到一家百貨公司去購物。壯士們已經埋伏好在那裡。丁富有警覺性,也許,也竟已準備好,一進門,便溜了出來,來不及放一槍。為了到這個地方去的事,只有她一個人知道,因之,她的嫌疑極重。她被捕了,經過了殘酷和刑訊之後,她便從容就義了。」
他說完了話,默默的為這位女英雄誌哀,我也默默的在哀悼著僅見一面的這位愛國的女間諜!
鄭振鐸的〈一個女間諜〉是刺丁案最早被寫成文章的,但偏重於報導性質,並沒有太多的細節得描寫。鄭振鐸藉此來歌頌抗日的愛國行為,多過於小說的經營,況且它還不是以小說的型態出現。文章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在《周報》發表,雖然在當時該報是上海相當暢銷的刊物,主編柯靈又是提拔過張愛玲的,但我們也無任何證據證明張愛玲看過該文章。
相對於鄭振鐸,金雄白因為是出入於汪偽集團的,因此他知道得更仔細,而很多細節他雖沒有親見,但確是親聞的,因此其可信度相當高。胡蘭成在汪偽集團的身份地位,不亞於金雄白,金雄白所知道的事,胡蘭成不可不知。而以胡蘭成的個性,他極可能將這種爆炸性的內幕,炫耀地說給張愛玲聽,因此我們可以假設金雄白所描述的情節,張愛玲是聽過的。
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有「鄭蘋如謀刺丁默邨顛末」一節:
在汪政權中,太多醇酒婦人之輩,而「七十六號」的特工首領丁默邨,尤其是一個色中餓鬼,他雖然支離病骨,弱不禁風,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壯陽藥仍然是他為縱慾而不離身的法寶,他當年與女伶童芷苓的繾綣,早成公開秘密,而鄭蘋如的間諜案,更是遐邇喧傳。海外書報中曾有不少有記述此案的經過,可惜有些是語焉不詳,而有些則與事實相去太遠。
鄭蘋如是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檢察官鄭鉞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國學校讀書,家住法租界法國花園附近的呂班陸萬宜坊。萬宜坊中有著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躍如鄒韜奮,豔麗如鄭蘋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時期住過那裡,每天傍晚,鄭蘋如常常騎了一輛腳踏車由學校返家,必然經過我的門口,一個鵝蛋臉,配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確有動人丰韻。不知她怎樣竟加入了軍統任間諜工作?又不知怎樣竟然會與汪方的特工首領丁默邨發生了曖昧關係?
丁鄭之間的往來,已經有了好幾個月,丁默邨是個特工首領,處於那時的環境中,對事事物物,樣樣提防,而唯獨對於鄭二小姐卻十分放心,數月之間,也從沒有發現她任何可疑之點。一天,默邨在滬西一個朋友家裡吃中飯,臨時打電話邀鄭蘋如來參加。飯後,默邨要到虹口去,鄭蘋如也說要到南京路去,於是,同車而行。從滬西至南京路或虹口,靜安寺路都是必經之道。當車經靜安寺路西伯利亞皮貨店門口時,鄭蘋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亞買一件皮大衣,嬲著默邨同他一起下車幫她挑選。特工人員知道到一個沒有預先約定的地點,而停留不逾半小時,認為決沒有發生危險的可能。默邨以為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種需索的手段而已,於是坦然隨她下車。汽車是停在西伯利亞馬路對面的路側,該店是兩開間的門面,當他們兩人穿過馬路到達店門時,默邨看到有兩個形跡可疑的彪形大漢,腋下各挾有大紙包一個,裡面顯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對。而默邨在此緊要關頭,能持以鎮靜,毫不慌張。仍昂然直入店內,而一轉身即毫不停留,撇開了鄭蘋如,由另一扇門狂奔而出,穿過馬路,躍上自己坐來的保險汽車。兩大漢以為默邨進店,至少要有幾分鐘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過馬路上車,立即拔槍轟擊,但為時已晚,祇車身上中了十幾槍,彈痕斑斑,而默邨則毫髮無損,汽車也急馳而去。
重尋〈色,戒〉的歷史場景 蔡登山
張愛玲的小說〈色,戒〉,雖諸多論者都指向她是以鄭蘋如謀刺丁默邨為原型的,但張愛玲卻始終沒有明確的承認過。儘管如此,小說一開頭就提到曾仲鳴已經在河內被暗殺了,汪精衛從重慶出來,到了香港,再到了上海,這無疑地都合乎史實的。因此它不同於其他張愛玲的小說,你或許不需知道她小說背後的「本事」,但它並不妨礙你對小說的了解;但對於〈色,戒〉而言,追索小說的「本事」,卻有助於對小說的通盤了解,甚至你更可從張愛玲的「改寫」過程中,看到她所謂的「靈魂的偷渡」。因此我們就從小說或是它的「本事」中的幾個歷史場景說起。
(一)從「從金屋藏嬌」到「禍國殃民」的「汪公館」
在上海愚園路上有兩處最有名的花園洋房,其中一處即是現在做為「長寧區少年宮」的「汪公館」。「汪公館」是上海淪陷時期汪精衛的公館,是一幢豪華精美的西班牙式別墅,園內一方平整的綠茵,把小樓映襯得格外雍容。
「汪公館」坐落在現今愚園路1136弄31號(原為愚園路310號)。其實「汪公館」本應稱為「王公館」,因為它的主人是戰前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兼上海大夏大學校長的王伯群。
王伯群,原名文選,字蔭泰,1885年生於貴州省興義縣景家屯,其父王起元以辦團練而聞名鄉里。1905年他得舅父劉顯世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五年後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期間並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王伯群回到家鄉,與其弟王文華、妹夫何應欽,以黔系領導人物折衝於各系軍閥之間。
1924年夏,廈門大學發生學潮,200多名學生失學,部分教授為學生鳴不平辭職來到上海。王伯群時在上海當寓公,便捐款2000元與這些教授辦起了大夏大學。初任校董會主席,兩年後因馬君武辭校長職,王伯群繼任校長。「四一二」清黨後,他因有何應欽為背景,乃於1928年出任交通部長兼招商局監督。
王伯群出任交通部長後,仍兼大夏大學校長一職。在一次學校慶典活動上,時有「校花」之稱的學生保志寧上臺向他獻花,這位早過不惑之年的部長兼校長竟對這朵整整小他26歲的「校花」一見鍾情,從此苦苦追求。保志寧是滿清貴族後裔,家住南通。其父在南京政府供職,其叔保君健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長。保志寧人長得眉清目秀,且善辭令,原就讀滬江大學,以其「才貌雙全,男同學之追求者多而切,不勝其擾,乃轉學大夏大學」。王伯群原有一妻二妾,妻子去世後,一位姨太太先遭遺棄,另一位也在他與保志寧談論婚嫁時亦遭「編遣」。
王伯群與保志寧的婚禮於1935年6月18日在上海徐園舉行,證婚人為「黨國」元老許世英、張群。據說王、保兩人當初議及婚嫁時,保志寧曾提出三個條件:一,贈其嫁妝10萬元;二,婚後供其出洋留學;三,為其購置一幢花園別墅。其中購置花園別墅一項,恰巧當時辛豐記營造廠正在承建南京交通部辦公樓及上海大夏大學的教學樓,於是王伯群便一併交該承建商「代勞」了。他選定愚園路上的屋址後,即於1930年破土動工,歷時四年,於1934年落成。辛豐記老闆為取悅王部長,可謂不惜工本,所用材料中的硬木地板、金山石、馬賽克瓷磚、牛皮石灰等,堪稱高檔。該別墅由協隆洋行(A.J.Yaron)設計,主樓為四層,其中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係鋼筋混凝土結構,坐北朝南,外形為哥德式,但局部立面帶有西班牙式建築風格。建築為對稱佈局,中央有室外大樓梯越過半地下室的底層,直接進入一樓門廳。整幢建築有大、小二廳,房間32間。客廳採用東方傳統藝術裝飾,樑柱平頂飾以彩繪,配以壁畫。地坪採用柚木鑲嵌成蘆蔗紋圖案,踏步欄杆也用柚木製成,室內扶梯花紋則用紫銅仿古鑄造。起居室呈西班牙古典裝飾,書房、臥室則採用不同的摩登風格,還專闢有女主人閨中會客室,用以款待女眷,於豪華中顯示高雅。主樓南側是一片開闊的草地,遍植花木,亭台假山、小橋流水點綴其間,盡顯幽雅。四周圍牆築成城堡式,牆壁塑有梅花圖案,就連門窗拉手也全用紫銅開模,鏤空鑄成松花圖案,其風格與主樓一脈相承。
當時輿論界對這位「老」校長娶「小校花」本有微詞,如今又冒出來這幢美輪美奐的「金屋」,自然是群起而攻之。其中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更是迎頭痛擊。於是就有監察委員提出彈劾案,1935年底王伯群因此被迫辭職。時人戲稱王伯群是「娶了一個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丟了一個官職。」,然因有何應欽做靠山,王伯群仍保留國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委員頭銜。1937年抗戰爆發,王伯群隨大夏大學遷至貴陽,撤離上海後,該建築由保志寧叔父保君健代管。保志寧作為「金屋」的第一任女主人,卻僅住了二年半的時光。
上海淪陷後,該「金屋」被汪精衛作為偽政權駐滬辦公聯絡處,人稱「汪公館」。1939年5月6日,汪精衛和陳璧君在日本特務影佐禎昭的陪同下,乘「北光丸」來到上海。儘管汪精衛在上海的福履理路(今建國西路)570號及愚園路738弄內都有公館,但日寇出於安全考慮,還是讓他暫住在東體育會路7號的「重光堂」,那裏是出名的日本特務「土肥原機關」的所在地。同住的還有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後來汪精衛又搬到西江灣路上的日軍原西尾中將寓所居住,由日本憲兵保護,連汪的貼身衛士都不許隨便出入。日方認為如此一來,汪精衛等人就都成了甕中之鼈,連活動都受到限制,遑論開展「和平運動」。為了便於監控,於是土肥原與影佐禎昭決定將愚園路上的「王公館」撥給汪精衛使用,因為該公館只有愚園路一個出口,便於安全警衛,又因1136弄內另有十幾幢洋房,可以將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陳春圃、羅君強等漢奸也一併遷往那裏居住。安全由「76號」特工負責。於是丁默邨、李士群乃下令,將弄內住戶全部趕走,接著在牆垣上高築電網,四角設置瞭望亭,門窗裝上鐵門、鐵柵。弄堂內外除「76號」特務大隊長張魯率100餘人日夜把守外,日本憲兵也派出一個便衣小隊在弄口盤查行人,出入須持特別通行證。
一切安排停當,汪精衛就在他的寓所裏召集大、小漢奸們開起了偽國民黨「六全一中全會」,自任「主席」。1939年7月9日晚,他還在公館樓前發表〈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廣播講話,日本攝影師為之拍攝新聞紀錄片。直至次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衛才遷往南京頤和路公館居住,但愚園路上的「王公館」仍是他在上海的「行宮」。
(二)汪、日談判地點之一:愚園路1136弄60號
在汪、日談判的過程中,代表日方的是以影佐禎昭為主,因此也稱「影佐機關」或「梅機關」。當時正式的談判從1939年11月1日開始,地點則先在虹口的「六三花園」,後來因為則因為汪精衛等一群人都搬到愚園路住,於是雙方談判的地點也改在愚園路1136弄60號的地點,它距離「汪公館」的1136弄31號,只有幾步之遙。談判中代表汪精衛之一的陶希聖,一度都在此地住過。
(三)殺人不眨眼的「七十六號」魔窟
張愛玲的〈色,戒〉中男主角易先生,被認為是以丁默邨為原型的。而整個情節及發生的場景,脫離不了令人聞風喪膽的所謂「七十六」魔窟。它座落在當年滬西的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也就是現今的萬航度路435號。
極司斐爾路當年屬越界築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強行修築起來的一條馬路,因此路權歸工部局巡捕房管理,路的兩側仍屬華界。「七十六號」就坐落於極司斐爾路中段,它原是陳調元的私宅。陳調元原係北洋軍閥直系將領,曾任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當年,這裏是陳調元做壽、唱堂會的地方。抗戰爆發後,「七十六號」為日軍佔領,經晴氣慶胤少佐的撮合,把它撥給丁默邨、李士群做活動場所。
丁默邨、李士群的漢奸特務組織在與汪精衛集團同流合污前,已經兩易其駐地了。由於特工隊伍人數迅速增加和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他們先從大西路六十七號搬到了憶定盤路九十五弄十號的一座洋房,因對外均由李士群的妻子葉吉卿出面,故稱「葉公館」。但不久,他們又感到這裏並不理想,因為它位處弄堂裏,連一輛汽車都無法掉頭,平時為了安全,只好在弄堂口擺起兩個水果攤,作為望風瞭哨,還派人不時在弄堂裏進進出出地巡視,這既不體面,又不大方便。最後,由晴氣慶胤少佐親自選定,搬進了滬西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這就是後來上海人一提到它,無不談虎色變的汪偽特務魔窟。
為了適宜工作的需要,根據丁默邨的設計,他們首先對「七十六號」內的房屋做了改造,把原先的洋式二道門改為牌樓式,在兩側的牆上開了兩個洞,安裝兩挺輕機槍。二道門內的東邊,南北相對地新蓋了二十多間平房,做為「警衛總隊」的辦公室和審訊室;西邊添造了一幢兩開間的樓房,做為電訊室。花園裏的一個大花棚,改做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樣新穎精緻的三開間平洋房,由日本憲兵佔用,進行現場「指導」和監視。「七十六號」的主要建築物是正中的那座高洋房,樓下是會客室、電話接線室、貯藏室以及餐廳、會議室等,樓上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寢室兼辦公室。三樓有兩個房間,作「犯人優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開間、兩進的石庫門樓房,四周有走馬樓。在走馬樓中間的天井上搭了一個玻璃棚,把樓下的前後兩廂與客堂打通,改做大廳,再搭上一個講臺,算是大禮堂。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就在這裏舉行。
除在「七十六號」大興土木外,丁默邨,李士群又在日本特務機關的許可下,
強行將「七十六號」右側一條名叫「華邨」弄內的住戶統統遷出,佔領了該弄二十餘幢二層樓的小洋房,作為汪偽國民黨中央社會部、肅清委員會與特工總部的高級官員的家屬住宅。為了安全,他們將靠馬路的弄堂口堵死,在「華邨」東首與「七十六號」大門內相隔的牆壁上開了一個便門,所有居住在「華邨」的人,一一發給出入證,,概由「七十六號」大門進出。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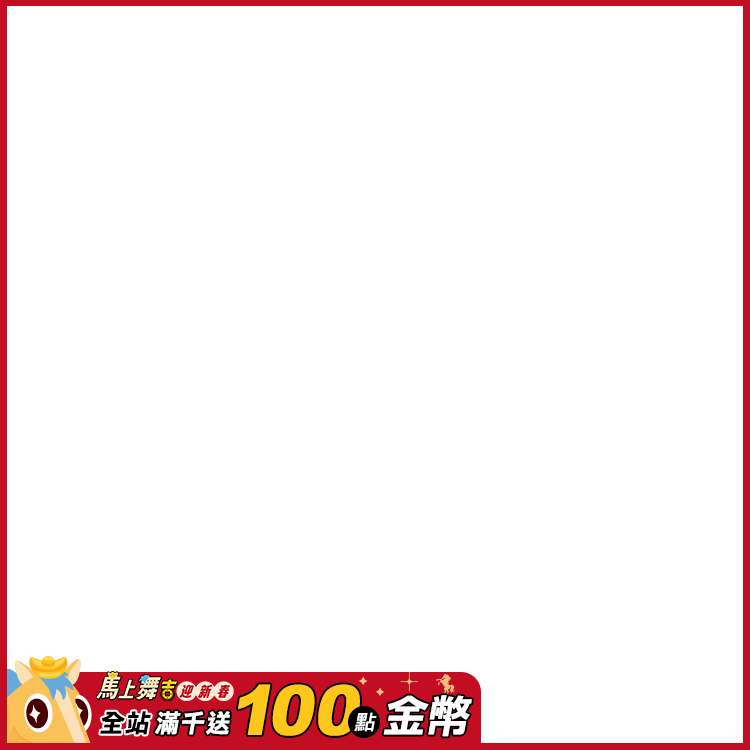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