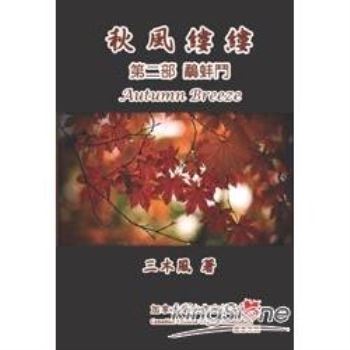第三十四章 魏家驕女興大運
魏琴心中的惆悵和陰影被滿天金燦燦的陽光遮住了。
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青年,更應該有這種無私無畏的寬闊胸懷,個人的情感先放一邊。
魏琴從調到行動組工作以來經歷了很多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參與了剷除二兵團這個小山頭的行動,讓工總司內部得到統一。王司令很高興,行動組的盧頭也非常得意,她也立了汗馬功勞!第二件事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這是新生的政權。百萬人的慶祝大會剛開過,給黨中央的致敬電也剛發出。百萬人,這是多麼宏亮的聲音,這是多偉大的力量!
前些日子,兵團內冒出這個山頭那個山頭,還叫囂什麼“炮打”——全是要摘桃子的傢夥 (搶奪勝利果實)!
這一點也不奇怪,新生的權力機構要誕生,要出世,不經過一場摧腐拉朽的震盪怎麼能成!孕婦分娩還要經過劇烈難忍的陣痛哩。
“炮打張春橋”,那幫傢夥專會造謠中傷!
也不看看他們攻擊的是什麼對象,難道他們沒有聽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那個精采的報告嗎?
報告歷數了文化大革命的發起進程,是中央首長來上海通過張春橋同志指示姚文元秘密寫評海瑞罷官一文,才打響了第一炮;“中央首長”是第一夫人的尊稱。
是春橋同志從飛機下來直奔安亭簽下了工總司的五項要求,從此工總司揚眉吐氣,進而成了全國造反派的楷模,王洪文司令也不愧是響噹噹的工人領袖。
現在,除了在毛主席身邊的中央首長,他們三個人都是上海人民公社的主任副主任,主宰著上海的黨政財文大權。造反派也以“中央首長”稱呼他們。
那些“炮手們”也太不自量力了,他們如果還記得“懷仁堂”事件就應該禁若寒蟬。今年二月,那幫所謂的“元老”和“將帥”在懷仁堂貶摘“文化革命搞糟了……”,結果偉大領袖支持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那幫將帥最終受到撻伐,還背上個“二月逆流”的罪名,現在也都消聲匿跡了!他們怎麼敢怠慢了中央首長!
蚍蜉撼樹,只能落得身敗名裂!
上海人民公社在東方地平線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魏琴沒有參加。如果還是東方紅兵團司令,她就會威風凜凜的率領隊伍向廣場開拔。可她現在是行動組一名接待員,一名看家的勤務員。其他人和頭頭腦腦們都威風去了,慶祝勝利分享勝利果實去了,只留下她和警衛班守著這幢樓房。
盧吉昌說:“留守的任務極其重要,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留守就像坐江山。”魏琴知道他是安慰她送她一頂皇冠戴戴,但她也理解,賴法天這幢樓是誰都可以來搶的。行動組可以調譴兵馬包圍斜橋砸二兵團,二兵團或者什麼其他人也可以來圍殲工總司行動組!
盧吉昌派了一個班保衛行動組。
魏琴忠實地執行了留守任務。慶祝大會的盛大情景都是戰友們傳遞給她的。
“媽,我回來了。”她一進門就輕快地嚷嚷,從手上的拎兜裡往外掏東西。
“那是什麼呀?”黃秀美有點眼花,探頭來看。
“你猜猜。”女兒說著,從紙袋裡抓住一根東西閃電般地塞到母親嘴裡。
黃秀美沒有看見,靠舌頭的味覺辨別口裡的食物,在口腔裡滾了幾個轉,嚼了許久才辨清,笑眯眯的說:
“是雞腸子。”
“媽的舌頭真靈。”魏琴說。
“哪來的?”
“買的。”
“你有票?”
“不要票,興許是快過期了,不賣掉就浪廢了,所以沒有要票。”
“你鈔票用不完了?”
“我有錢。”
“你那幾個錢媽還不知道。”黃秀美不屑一顧,轉過身去。
女兒的零花錢都是黃秀美平時從指縫裡省出來給她的,她在心裡有些責怪女兒浪費,這個家每天支出多少錢她都算的清清楚楚。
“我真的有錢。”魏琴攀著母親的肩失搖晃著,撒嬌道,“勤務員的津貼。我們發津貼了。”
“發的?”黃秀美瞪大了眼睛,驚喜得久久合不攏嘴,“是上面發的?”
“人民公社發的。”魏琴正經八板的說,“凡是勤務員都有。”
黃秀美把女兒摟在懷裡,一支皺巴巴的大手張開五指梳理著女兒的墨發,心裡如灌了半斤蜜糖。
從讀高中起,女兒就開始東跑西顛的總是從家裡拿錢,現在當上勤務員有津貼了,真是新時代新辦法。特別令她興奮的是女兒今天作為人民公社的勤務員拿到了工資。
“這是名正言順的報酬。”魏琴說。
她來當勤務員一月有餘,今天上午,後勤組把報酬送到她手裡。
幹革命是不講報酬的,所以後勤組說是發津貼。在蘇區,在紅軍時代都叫津貼。
人總是要吃飯,為革命而吃飯,津貼就是讓你吃飯的錢。
拿到三十元錢津貼平生還是第一次。她的零用錢都是爸爸通過媽媽的手給的,幾毛錢最多幾塊錢,交個什麼費,買件衣服什麼的,而這可是自己工作得來的,是新生的革命政權發給它的勤務員的津貼,魏琴很興奮, 她口袋裡藏著三十元彈上去發出脆響的有領袖頭像的人民幣,穿街走巷,她要買些吃的和家裡人一起慶祝。經過一個雜貨鋪她給爸爸買了一瓶二鍋頭,但是走了好遠的路也找不到可以買食物的地方。現在物資真缺乏,樣樣都是配給制,想要買額外的可難了,即使有錢也沒有用。
天色已經晚了,商店收攤的收攤打烊的打烊,早就沒有東西賣了。又過了幾條街經過一個街角總算看見有家小店還亮著昏黃的燈,沾滿油漬的玻璃櫃裡竟然還有一小碟一小碟的細片兒肉,魏琴滿懷希望上前一問,也是要憑計畫肉票才可以買的。每個月的計畫肉票媽媽都很小心翼翼地收著輕易不拿出來,那每一小片紙什麼時候可以用都是算計好的。但是魏琴不死心,看著櫥窗不肯走,終於在玻璃櫃的角落裡發現還有兩碟雞雜碎,一問,營業員說不要肉票只要鈔票,太好了,她把兩碟都買了,粗紙包了興奮地徑直往家跑。
“琴兒,那公社當真是我伲人民的?”母親說,老腦筋還在想著市委市政府。
“那還有假。”魏琴說,“主任,常委,一套班子很齊全的。”
黃秀美把紙袋收了,放在灶間的碗櫥裡,快手快腳去煮晚飯。老頭子回來了也不露聲色,繼續做飯。
等兒子魏斌一進門,她就張羅著吃飯,從碗櫥裡拿出雞雜碎擺到桌子上。
然後一手抓了四隻小酒盅,一手抓著一瓶七寶大麯,“今晚高興,大家都喝一口。”
魏真江詫異地盯著老伴,說:“今天拾著金元寶了,有雞又有酒?“
魏斌沉默著,瞅瞅母親又瞧瞧父親,沒開腔。
黃秀美喜盈盈地說:“比拾著金元寶還高興哩。再說拾著的東西要交公的。“
魏琴把垂著的手提上來,笑吟吟的說:“媽,讓爸喝這個。”
魏真江一把奪過酒瓶,一瞧:“呵!二鍋頭。”眉開眼笑。
二鍋頭是北京人常喝的酒,它可比上海人常喝的七寶大麯有名多了。
魏真江十幾年來只喝過三次二鍋頭。一次是出差北京,在小攤頭買了牛什碎,專買了一瓶二鍋頭,和同事在旅社裡喝,那個晚上兩人都喝醉了。第二次是國慶十周年,那天同事邀他上門作客,拿出二鍋頭,那個晚上他也醉了。第三次是糧庫四清運動,宣佈他洗過“熱水澡”,可以“下樓”了 (經過審查沒有問題),那個晚上在家,他一個人喝了一瓶二鍋頭,也醉了。二鍋頭和七寶大麯都是高度白酒,也都是普通勞動者喝得起的酒,可不知道是因為偶然喝外地出產的酒就有“菩薩遠的靈”的感覺還是怎麼地,總覺得它的醇香勝過七寶大麯,順喉而不嗆。
“琴兒今天怎麼專門孝敬老爸了”魏真江喜吟吟地說。
自從女兒去行動組工作,他就不再叫魏琴丫頭了。而且在這個家,真理當真就掌握在她一個人手裡。現在兒子也加入了造反隊,他自己也在人民公社的管轄下任職了。
“這可真是哩。”黃秀美邊斟酒,邊說,“女兒就知道孝敬你,還特地給你買了好酒。”調解委員趁機和解父女的關係。
魏斌覺得有些尷尬。自己工作這麼些年了,只知道領了工資就往媽手裡一交完事,妹妹只一點零花錢還想著給爸買酒,還是妹妹心細。
“讓爸你高興嘛。”魏琴說。
“今天琴兒發津貼了,第一次領工資。”黃秀美甜滋滋地宣佈。
“是嘛?太好了。” 原來這樣,魏斌不禁有些驚訝,很替妹妹高興。
“那當真好啊。太高興了,來,喝酒。”魏真江拿起酒杯仰脖一口幹了。
魏斌喝了半杯就放下杯子,黃秀美和魏琴只沾了沾嘴唇。在這個家,喝酒還是男人的專利。
魏斌又喝了兩口,開始說話。一開口便和這快樂的氣氛不大協調,“這些天外面又有傳單,說上海人民公社寵愛一派排斥 一派,還說要重新組織大聯合的新公社。”
這個傳聞,魏真江也聽到了,他就是不大相信那些傳單能成什麼氣候,而且他也不願意在今晚掃女兒的興。
魏真江喝了口酒,挾了一條雞腸子放到嘴裡咀嚼著:“恐怕是因為人民日報沒有報導公社成立的消息吧。”閱歷多的人好像特敏感,他繼續說:“黑龍江、山東一成立新政權人民日報就報導了,唯獨上海,這麼久了也沒有聽到中央承認的聲音。”
魏斌的話頭也正是從這種分析起頭的。
中央沒有點頭的政權能持久嗎!
魏琴也有這種憂慮,她再也不是未見世面的中學生了,半年多來的闖蕩練就了她抬頭看形勢的眼光。她看到社會上的紛繁複雜,潮流和暗礁,但眼下她相信自己已經抓住了主流,相信新生政權不會輕易動搖。
況且她已經是這個政權的一分子,她必需要有堅定的立場才符合身份。她說:“謠言是有的,但這不能說中央不承認。中央怎麼考慮的誰能知道?說不定哪一天,一句話,人民日報公佈了,謠言也就破產了。”
“鬧啥呀,就這樣太平點。”黃秀美想的是,如今女兒是勤務員,兒子是造反隊,丈夫也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家子太太平平多好。現如今,中學畢業有份工作可不容易,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還在那裡東奔西跑呼口號哩。
魏斌又說:“群眾敢說敢做。”他說了這話頓住,又喝了口酒,瞧瞧妹妹,說:“一派抓另一派的人,用壓是壓不服的。”
魏琴心直口快,反駁哥哥:“擒賊先擒王嘛。頭頭不抓起來哪太平得了?。”赤衛隊頭頭腦腦都被抓了,二兵團的頭頭們沒有被抓,而是被招安了。
魏真江和魏斌都瞪著她——這話顯得她有多稚嫩!
魏真江說:“琴兒,你現在是勤務員,勤務員就要為群眾辦事。你平時也多長兩個心眼。”
黃秀美看到這餐桌上的氣氛有些冷,趕緊調解道:“行了行了。今晚大家該高興,別再說那些事了。喝酒吧。” 她把話題引開,“你表哥有好些日子沒有來了,不知道怎麼樣?” 她瞧著魏琴和魏斌。
魏斌說沒有碰到過。
魏琴也說沒有碰到,不過她倒是有些消息:“聽說還好。開頭兩天被管制不能隨意行動,現在正常上下班了。帶‘長’字頭的大大小小都要靠邊站.,他是個秘書,當然也要享受‘長’字的待遇,總得要寫檢查、揭發什麼的。”
黃秀美問:“能上下班怎不來家裡看看?”
魏真江說:“作道是個有頭腦的明白人,到處瞎跑叫人嫌疑作啥。”
魏斌說:“興許是這個理。”
晚餐,就這樣在切磋之中過去了。
餐桌上母親問起表哥,卻沒有人問到陳吉生,這多半因為表哥到底是親戚,被視作家人,而陳吉生儘管是魏琴串連中的親密朋友,到底還隔得遠了。
這倒好,省得魏琴回答眼下難以回答的問題。
可是,當她洗完臉洗完腳,回到她和哥哥分隔的房間的時候,哥哥卻提出這個問題。
“琴,你知道陳吉生近來的情況嗎?”
魏琴剛在自己簡陋的梳妝兼書桌前坐下,要整理一下她以前串連時用的而如今上下班一直背的那個褪了色的黃布背包,聽到哥哥的問話,心裡一動,停住了手。
“不大知道。”魏琴不想告訴哥哥前不久她專程到真君裡找過陳吉生,也沒有說出陳吉生一 家的境況 。她知道哥哥心裡想的是啥。
陳吉生是她帶到哥哥面前的第一個男性朋友。那天哥哥在食堂招待他們,就有一種把陳吉生看作自己人的態度。
“你不關心這個事?”魏斌是有意激她一激。他不相信純真正直的妹妹對一個串連途中於她有恩有義的人會這麼不聞不問。
“關心的,可關心又能怎樣呢,哥。”魏琴有些激動又有些無耐。“他現在有難處,可我——”
“你還是知道他們家的事的。”魏斌掀開妹妹心中的秘密,“那你還很關心他的是不是?”
魏琴在哥哥面前沉默著。她瞞不過哥哥,也不必瞞著哥哥,哥哥是會保護她幫助她的。
剛才,在餐桌上他隻字不提此事,是怕她尷尬 。“哥。”魏琴惆悵地說,“在井崗山下,在羅婆家裡醒來的時候,我只知道是他把我背離那個死亡之地,沒有他的搭救,我可能就死在那個山溝裡了。當初,我只是很感激,沒有別的想法。”她有些動情。“後來,我們兩個人相伴走南闖北,從對待很多事件的探討切磋中我發現他對待事物的眼光冷靜,遇到突發事件,常常能想出妥當的處理方法,而我卻還沒有想到。慢慢的我就開始對他生起了除了感恩之外的遐想,而且那種感覺來的真快。”她沉吟了一會兒,繼續說,“那時,他沒有問我的家庭,是我奈不住了,很想讓他知道於是主動告訴他的。他聽了我的話,也不主動告訴我關於他父母的事,是我後來問了他才說父親和母親都是幹部,”
魏斌靜靜地聽著妹妹講述心裡的這個秘密
“他沒有說父母都是高幹?”魏斌問道。許多高幹子女都喜歡炫耀自己的家境和光榮歷史,陳吉生卻沒有。
“回上海以後,”魏琴說,“我想看看他的家——真的,我心裡已經很想知道他的家。哥,你別取笑我那麼迫不及待。——我問得緊,他才告訴我地址。有一天,兵團沒有事,我就去了。誰知找到的地址是一幢花園樓房,門前的庭院很寬闊,羅漢松,菊花滿園,比資本家賴法天那吸血魔窟還氣派。”她眼睛睜大盯著哥哥:“哥,你知道我當時心裡怎麼想?我想,難怪他不告訴我,原來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我受了矇騙,憤怒的轉身就走。”
“我走出一段路又想,既然已經來了怎麼也要弄個明白才行。”魏琴繼續說,“於是我又回去。等進了門,才知道陳吉生――他只是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愛炫耀自己的家境。”
魏斌自己還沒有談過戀愛,但他能想像妹妹的感情波瀾。他並沒有要高攀陳吉生這個高幹子弟的想法,只是從妹妹的幾次不多的言談中,瞭解到陳吉生的人品,倘若真能成為妹夫,也未必不是美事。可是現在情況發生了劇變。妹妹把痛苦埋在心底,成天忙忙碌碌嘻嘻哈哈的,作哥哥的不免為她擔憂。
“我們廠的孫師傅遇到過陳吉生。魏斌說。
“孫師傅?哪個孫師傅?他怎麼認識他?”魏琴愕然地發出好幾個問號。她很久沒有陳吉生的情況了。
“他說是在輪船甲板上和陳吉生認識的。”魏斌說。
“輪船甲板上?”魏琴終於回憶起來了,“哦,就是那位孫師傅?陳吉生在甲板上和他熱絡得不得了。他是出差回來和我們同船。”
她腦子裡還浮現在碼頭,在人潮中要分手的時候,陳吉生過去和他握手道別,孫師傅還邀請他到他廠裡去看車床。
她追問:“孫師傅怎麼遇上陳吉生?”
“孫懷勇——哦,我住院時他就在我隔壁床,你見過,那時他的頭裹著繃帶,你看不清。”魏斌說,“他那天騎著自行車正往回走,已經是夜深了,九,十點鐘光景,看到一個人在牆邊看大字報,仔細一看,是陳吉生。他就下車和他在路旁聊了好一陣子。”
孫懷勇從魏斌口中得知陳吉生是高幹子弟,而且他也得知這次奪權中,那個下臺的叫陳槐的局長正是陳吉生的父親。那天在路燈下看見陳吉生,便下了自行車車去和他聊了一會。既是重敘船上的邂逅情誼,也是出於對陳吉生現今境況的憐憫。
陳吉生沒有告訴他自己的家庭變遷,孫懷勇也就不忍掀起這層面紗 “他怎麼說?“魏琴關切地問。她現在很看重旁人怎麼看待陳吉生。
“他說他情緒不高。”魏斌說,“孫師傅是個好心腸的人,他歎口氣說:真是鳳凰落水不如雞呀。”
魏琴眼圈紅了。
“妹妹,你也別難過。”魏斌寬慰道,“落水鳳凰被太陽曬乾了還是很漂亮的,仍然飛得比雞高。”
魏琴被逗笑了。有點心酸的笑
但她很快就覺得脆弱不符合一個紅衛兵領導的性格。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才出去闖蕩造反的嗎?她很快調整了情緒,這下是真笑了,杏眼格外好看。
“哥,你笑話妹妹軟弱嗎?”
她的心事哥哥比父母知道得多知道得徹底。但她不想再說下去,把話題轉了。
問道:“你們廠造反隊是不是有分歧?”
魏斌瞅著妹妹,反問道:“你怎麼曉得?”
魏琴平靜地說:“是不是,你說嘛。”
魏斌透露說:“有。現在不是要建立廠領導班子嗎?廠的黨政領導早就靠邊站了,工作隊也早就撤了。造反隊不需要奪權,就可以發號施令。可是,那個鄭秋光負責人,讓他捏榔頭釘根釘子都是歪的,讓他操縱車床車出來的廢品多於合格品,這樣的人領導一個廠怎麼行!”
魏琴說:“就為這鬧分裂?”
魏斌鄭重地說:“這還不是大事呀!關係幾千人的生活,關係申江廠的生存呢。”
魏琴向哥哥透露了個秘密。她說:“鄭秋光給盧吉昌打電話的時候,我正在旁邊,鄭秋光向盧吉昌求援。我聽盧吉昌說:你放心,申江廠是我一手闖出來的,我不會袖手旁觀的。你們要廢鄭秋光恐怕不易。”
魏斌有些憤懣,他提高聲調:“不是說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嘛。盧吉昌己經高升了,已經去管轄市里的大事情去了,為什麼還抓住申江廠不放。”
魏琴在行動組,到底見的世面廣,經的事兒多,那些老單位不僅是他們發跡的根基,而且是他們一呼百應支持者的所在地。她自己不也時不時要打個電話,或者把蔡萍芳、瞿飛叫來聊聊,問問情況嗎!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出發點和根基。不僅盧吉昌時時關照著他的申江廠,就是王司令位居上海人民公社副主任的高位,也不忘他那個老家廠。”魏琴寓意很深的說。“有了政權就有一切,丟了政權就丟了一切。”
魏斌說:“聰明人就應當讓真正能幹的人去管理建設他的根基。廠搞好了,他自己也光彩。如果讓平庸之輩把持大權,搞砸了,那根基不照樣土崩瓦解,那時候他就沒有什麼好倚靠的了。”
魏琴說:“哥,你說的也有道理。不過,反正這事你當心一點。”
魏斌點點頭,感謝妹妹的提醒,更感謝妹妹透露這個情報。
鄭秋光大概己經預感到自己的腳後跟不穩,腰板子不硬,開始求救于上司了。
這事還得與孫師傅謀劃謀劃,可別吊以輕心了。魏斌心裡想著。
申江機械廠這些日子,看上去很平靜,其實暗潮湧動,大家各有各的心事。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公社核心領導中有盧吉昌的鐵心大哥。
造反隊負責人鄭秋光雄心勃勃:只要管好自已這個廠,就有生存發展、騰達升遷的日子
鄭秋光正和隊委陳菊英談著什麼。
孫懷勇從車間回到隊部,興致勃勃地向鄭秋光彙報說:“機器經過檢修,轉動起來了,如果原材料供得上,生產就可以搞上去。可就是工人太自由了,擅自離開崗位,讓機器空轉的現象太多。”他向鄭秋光求援,“我們得告訴工人以主人翁的態度,抓革命促生產。”
孫懷勇是分工抓生產的隊委,這是前任負責人盧吉昌派定的。孫懷勇論技術,論資歷,還有人緣都是最合適的人選,盧吉昌沒有選錯。
可是,鄭秋光明白,一個工廠,從科室到車間,都是圍著生產轉的,指揮生產者即是指揮工人大眾最實際的指揮者,尤其是當下沒有了黨組織,誰指揮生產誰就是工人大眾最有權威的領導者。而他這個造反隊的負責人除了造反隊開會需要出面,是可有可無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各個部門都在醞釀產生新生的權力機構,醞釀的意見竟然擁護孫懷勇的占了壓倒多數。
到了這節骨眼上,孫懷勇己經對他鄭秋光產生嚴重的威脅,功高震主,鄭秋光不能不膽寒,更令他嫉妒的是孫懷勇日益增長的威信。
鄭秋光對孫懷勇突然闖入打斷他和陳菊英的談話流露出不悅的情緒,他沒好氣地說:“工人不是很聽你的話嗎,你就教育去唄,還來找我做啥。”
孫懷勇是厚道人,沒有深一步辨別鄭秋光話的味道,爽快地答道:“我是想和大夥說說,但是不知道是否符合大方向,來向你請示。如果你也同意,那我們就這樣幹了。”說著起身就要出隊部。
鄭秋光粗聲粗氣地道:“老孫,你可真迫不及待呀。”
孫懷勇轉過身對著鄭秋光和陳菊英發愣,反問道:“你這是怎麼說——”
鄭秋光沉著臉不說話。
陳菊英在旁給鄭秋光的話詮釋,她說:“孫師傅你這是在努力抓出點成績來,給工人群眾有個好印象,這樣選舉建立三結合領導班子就有資本了。”
孫懷勇這下明白了,他氣呼呼地問陳菊英:“你是這樣看的?我抓生產還不是替造反隊效力!如果生產垮了,造反隊能光榮嗎!”他激動地把手一揮,“我這是好心換個驢肝肺,我不幹了。”
陳菊英笑嘻嘻地說:“你要是不幹,也沒人能強迫呀。”
這時,鄭秋光倒和顏悅色地走過夾,拍著孫懷勇的肩膀,撫慰道:“你想撂挑子?!別,別耍小孩兒脾氣。抓革命促生產,這是申江機械廠造反隊的天職。可老孫,我得提醒你一句,或許是一句忠言:抓革命擺在首位。不論怎麼說,抓革命總是比生產重要。我們不能重蹈走資派以抓生產壓制革命的覆轍噢。”他說完這話,很得意很有氣派地坐回椅子上。
孫懷勇氣呼呼地走出造反隊隊部。
西斜的陽光照在樹稍,那光禿禿的枝丫節兒上己經暴出芽,有的己經泛綠,但這些報春的消息沒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辛辛苦苦把工人組織起來,生產恢復起來,反而招來想出風頭的壞名聲。
“孫師傅,從哪裡來啊?”
孫懷勇駐步一看,是魏斌。
他不願提從隊部來,反問道:“你去哪裡?”
魏斌瞧他一臉怒氣,笑呵呵的說:“怎麼,不順心?”
孫懷勇在知心人面前不說假話:“我一心想把生產搞上去,這是黨中央的號召,可有人卻說我是為了撈資本。”
魏斌哈哈笑,笑得這廠區的曠地老遠就能聽到。
他從孫懷勇來的方向就知道他是在隊部受了氣。
“孫師傅,關於廠的領導班子,群眾議論很多。”魏斌把話鋒轉到權力問題上,“你是個很重要的人選哩。你聽到不?”
孫懷勇摸不透魏斌的話中之話,沉默著。
“孫師傅,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魏斌說,“我們這兒沒有宰相,可是,隊委也應當能聽各種意見呀。”
孫懷勇聽到一點風聲但他不放在心上。他說:“那只是大夥尋開心鬧著玩的。”
魏斌正經八板的說:“人家可不是隨便說說的。是鄭重其事的推薦你的。你想,要是那個人獨攬大權,那還行?你不比他強!”
魏斌細細的把群眾意見都告訴了孫懷勇,並說,當不當領導,不是個人的事,是工廠、工人群眾利益的大事。個人辛苦一點,值。
孫懷勇進退兩難:“嗨,這副爛攤子。”他沒有想去攬那碼子事。而且他也覺得自已無法領導一個幾千人的廠。
魏斌說:“你忍心讓幾千弟兄姐妹變成一群烏合之眾?”他給師傅鼓氣道:“只要你腰板直起來,大夥會支持你的。”
魏琴心中的惆悵和陰影被滿天金燦燦的陽光遮住了。
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尤其是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青年,更應該有這種無私無畏的寬闊胸懷,個人的情感先放一邊。
魏琴從調到行動組工作以來經歷了很多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參與了剷除二兵團這個小山頭的行動,讓工總司內部得到統一。王司令很高興,行動組的盧頭也非常得意,她也立了汗馬功勞!第二件事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這是新生的政權。百萬人的慶祝大會剛開過,給黨中央的致敬電也剛發出。百萬人,這是多麼宏亮的聲音,這是多偉大的力量!
前些日子,兵團內冒出這個山頭那個山頭,還叫囂什麼“炮打”——全是要摘桃子的傢夥 (搶奪勝利果實)!
這一點也不奇怪,新生的權力機構要誕生,要出世,不經過一場摧腐拉朽的震盪怎麼能成!孕婦分娩還要經過劇烈難忍的陣痛哩。
“炮打張春橋”,那幫傢夥專會造謠中傷!
也不看看他們攻擊的是什麼對象,難道他們沒有聽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那個精采的報告嗎?
報告歷數了文化大革命的發起進程,是中央首長來上海通過張春橋同志指示姚文元秘密寫評海瑞罷官一文,才打響了第一炮;“中央首長”是第一夫人的尊稱。
是春橋同志從飛機下來直奔安亭簽下了工總司的五項要求,從此工總司揚眉吐氣,進而成了全國造反派的楷模,王洪文司令也不愧是響噹噹的工人領袖。
現在,除了在毛主席身邊的中央首長,他們三個人都是上海人民公社的主任副主任,主宰著上海的黨政財文大權。造反派也以“中央首長”稱呼他們。
那些“炮手們”也太不自量力了,他們如果還記得“懷仁堂”事件就應該禁若寒蟬。今年二月,那幫所謂的“元老”和“將帥”在懷仁堂貶摘“文化革命搞糟了……”,結果偉大領袖支持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那幫將帥最終受到撻伐,還背上個“二月逆流”的罪名,現在也都消聲匿跡了!他們怎麼敢怠慢了中央首長!
蚍蜉撼樹,只能落得身敗名裂!
上海人民公社在東方地平線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魏琴沒有參加。如果還是東方紅兵團司令,她就會威風凜凜的率領隊伍向廣場開拔。可她現在是行動組一名接待員,一名看家的勤務員。其他人和頭頭腦腦們都威風去了,慶祝勝利分享勝利果實去了,只留下她和警衛班守著這幢樓房。
盧吉昌說:“留守的任務極其重要,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留守就像坐江山。”魏琴知道他是安慰她送她一頂皇冠戴戴,但她也理解,賴法天這幢樓是誰都可以來搶的。行動組可以調譴兵馬包圍斜橋砸二兵團,二兵團或者什麼其他人也可以來圍殲工總司行動組!
盧吉昌派了一個班保衛行動組。
魏琴忠實地執行了留守任務。慶祝大會的盛大情景都是戰友們傳遞給她的。
“媽,我回來了。”她一進門就輕快地嚷嚷,從手上的拎兜裡往外掏東西。
“那是什麼呀?”黃秀美有點眼花,探頭來看。
“你猜猜。”女兒說著,從紙袋裡抓住一根東西閃電般地塞到母親嘴裡。
黃秀美沒有看見,靠舌頭的味覺辨別口裡的食物,在口腔裡滾了幾個轉,嚼了許久才辨清,笑眯眯的說:
“是雞腸子。”
“媽的舌頭真靈。”魏琴說。
“哪來的?”
“買的。”
“你有票?”
“不要票,興許是快過期了,不賣掉就浪廢了,所以沒有要票。”
“你鈔票用不完了?”
“我有錢。”
“你那幾個錢媽還不知道。”黃秀美不屑一顧,轉過身去。
女兒的零花錢都是黃秀美平時從指縫裡省出來給她的,她在心裡有些責怪女兒浪費,這個家每天支出多少錢她都算的清清楚楚。
“我真的有錢。”魏琴攀著母親的肩失搖晃著,撒嬌道,“勤務員的津貼。我們發津貼了。”
“發的?”黃秀美瞪大了眼睛,驚喜得久久合不攏嘴,“是上面發的?”
“人民公社發的。”魏琴正經八板的說,“凡是勤務員都有。”
黃秀美把女兒摟在懷裡,一支皺巴巴的大手張開五指梳理著女兒的墨發,心裡如灌了半斤蜜糖。
從讀高中起,女兒就開始東跑西顛的總是從家裡拿錢,現在當上勤務員有津貼了,真是新時代新辦法。特別令她興奮的是女兒今天作為人民公社的勤務員拿到了工資。
“這是名正言順的報酬。”魏琴說。
她來當勤務員一月有餘,今天上午,後勤組把報酬送到她手裡。
幹革命是不講報酬的,所以後勤組說是發津貼。在蘇區,在紅軍時代都叫津貼。
人總是要吃飯,為革命而吃飯,津貼就是讓你吃飯的錢。
拿到三十元錢津貼平生還是第一次。她的零用錢都是爸爸通過媽媽的手給的,幾毛錢最多幾塊錢,交個什麼費,買件衣服什麼的,而這可是自己工作得來的,是新生的革命政權發給它的勤務員的津貼,魏琴很興奮, 她口袋裡藏著三十元彈上去發出脆響的有領袖頭像的人民幣,穿街走巷,她要買些吃的和家裡人一起慶祝。經過一個雜貨鋪她給爸爸買了一瓶二鍋頭,但是走了好遠的路也找不到可以買食物的地方。現在物資真缺乏,樣樣都是配給制,想要買額外的可難了,即使有錢也沒有用。
天色已經晚了,商店收攤的收攤打烊的打烊,早就沒有東西賣了。又過了幾條街經過一個街角總算看見有家小店還亮著昏黃的燈,沾滿油漬的玻璃櫃裡竟然還有一小碟一小碟的細片兒肉,魏琴滿懷希望上前一問,也是要憑計畫肉票才可以買的。每個月的計畫肉票媽媽都很小心翼翼地收著輕易不拿出來,那每一小片紙什麼時候可以用都是算計好的。但是魏琴不死心,看著櫥窗不肯走,終於在玻璃櫃的角落裡發現還有兩碟雞雜碎,一問,營業員說不要肉票只要鈔票,太好了,她把兩碟都買了,粗紙包了興奮地徑直往家跑。
“琴兒,那公社當真是我伲人民的?”母親說,老腦筋還在想著市委市政府。
“那還有假。”魏琴說,“主任,常委,一套班子很齊全的。”
黃秀美把紙袋收了,放在灶間的碗櫥裡,快手快腳去煮晚飯。老頭子回來了也不露聲色,繼續做飯。
等兒子魏斌一進門,她就張羅著吃飯,從碗櫥裡拿出雞雜碎擺到桌子上。
然後一手抓了四隻小酒盅,一手抓著一瓶七寶大麯,“今晚高興,大家都喝一口。”
魏真江詫異地盯著老伴,說:“今天拾著金元寶了,有雞又有酒?“
魏斌沉默著,瞅瞅母親又瞧瞧父親,沒開腔。
黃秀美喜盈盈地說:“比拾著金元寶還高興哩。再說拾著的東西要交公的。“
魏琴把垂著的手提上來,笑吟吟的說:“媽,讓爸喝這個。”
魏真江一把奪過酒瓶,一瞧:“呵!二鍋頭。”眉開眼笑。
二鍋頭是北京人常喝的酒,它可比上海人常喝的七寶大麯有名多了。
魏真江十幾年來只喝過三次二鍋頭。一次是出差北京,在小攤頭買了牛什碎,專買了一瓶二鍋頭,和同事在旅社裡喝,那個晚上兩人都喝醉了。第二次是國慶十周年,那天同事邀他上門作客,拿出二鍋頭,那個晚上他也醉了。第三次是糧庫四清運動,宣佈他洗過“熱水澡”,可以“下樓”了 (經過審查沒有問題),那個晚上在家,他一個人喝了一瓶二鍋頭,也醉了。二鍋頭和七寶大麯都是高度白酒,也都是普通勞動者喝得起的酒,可不知道是因為偶然喝外地出產的酒就有“菩薩遠的靈”的感覺還是怎麼地,總覺得它的醇香勝過七寶大麯,順喉而不嗆。
“琴兒今天怎麼專門孝敬老爸了”魏真江喜吟吟地說。
自從女兒去行動組工作,他就不再叫魏琴丫頭了。而且在這個家,真理當真就掌握在她一個人手裡。現在兒子也加入了造反隊,他自己也在人民公社的管轄下任職了。
“這可真是哩。”黃秀美邊斟酒,邊說,“女兒就知道孝敬你,還特地給你買了好酒。”調解委員趁機和解父女的關係。
魏斌覺得有些尷尬。自己工作這麼些年了,只知道領了工資就往媽手裡一交完事,妹妹只一點零花錢還想著給爸買酒,還是妹妹心細。
“讓爸你高興嘛。”魏琴說。
“今天琴兒發津貼了,第一次領工資。”黃秀美甜滋滋地宣佈。
“是嘛?太好了。” 原來這樣,魏斌不禁有些驚訝,很替妹妹高興。
“那當真好啊。太高興了,來,喝酒。”魏真江拿起酒杯仰脖一口幹了。
魏斌喝了半杯就放下杯子,黃秀美和魏琴只沾了沾嘴唇。在這個家,喝酒還是男人的專利。
魏斌又喝了兩口,開始說話。一開口便和這快樂的氣氛不大協調,“這些天外面又有傳單,說上海人民公社寵愛一派排斥 一派,還說要重新組織大聯合的新公社。”
這個傳聞,魏真江也聽到了,他就是不大相信那些傳單能成什麼氣候,而且他也不願意在今晚掃女兒的興。
魏真江喝了口酒,挾了一條雞腸子放到嘴裡咀嚼著:“恐怕是因為人民日報沒有報導公社成立的消息吧。”閱歷多的人好像特敏感,他繼續說:“黑龍江、山東一成立新政權人民日報就報導了,唯獨上海,這麼久了也沒有聽到中央承認的聲音。”
魏斌的話頭也正是從這種分析起頭的。
中央沒有點頭的政權能持久嗎!
魏琴也有這種憂慮,她再也不是未見世面的中學生了,半年多來的闖蕩練就了她抬頭看形勢的眼光。她看到社會上的紛繁複雜,潮流和暗礁,但眼下她相信自己已經抓住了主流,相信新生政權不會輕易動搖。
況且她已經是這個政權的一分子,她必需要有堅定的立場才符合身份。她說:“謠言是有的,但這不能說中央不承認。中央怎麼考慮的誰能知道?說不定哪一天,一句話,人民日報公佈了,謠言也就破產了。”
“鬧啥呀,就這樣太平點。”黃秀美想的是,如今女兒是勤務員,兒子是造反隊,丈夫也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家子太太平平多好。現如今,中學畢業有份工作可不容易,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還在那裡東奔西跑呼口號哩。
魏斌又說:“群眾敢說敢做。”他說了這話頓住,又喝了口酒,瞧瞧妹妹,說:“一派抓另一派的人,用壓是壓不服的。”
魏琴心直口快,反駁哥哥:“擒賊先擒王嘛。頭頭不抓起來哪太平得了?。”赤衛隊頭頭腦腦都被抓了,二兵團的頭頭們沒有被抓,而是被招安了。
魏真江和魏斌都瞪著她——這話顯得她有多稚嫩!
魏真江說:“琴兒,你現在是勤務員,勤務員就要為群眾辦事。你平時也多長兩個心眼。”
黃秀美看到這餐桌上的氣氛有些冷,趕緊調解道:“行了行了。今晚大家該高興,別再說那些事了。喝酒吧。” 她把話題引開,“你表哥有好些日子沒有來了,不知道怎麼樣?” 她瞧著魏琴和魏斌。
魏斌說沒有碰到過。
魏琴也說沒有碰到,不過她倒是有些消息:“聽說還好。開頭兩天被管制不能隨意行動,現在正常上下班了。帶‘長’字頭的大大小小都要靠邊站.,他是個秘書,當然也要享受‘長’字的待遇,總得要寫檢查、揭發什麼的。”
黃秀美問:“能上下班怎不來家裡看看?”
魏真江說:“作道是個有頭腦的明白人,到處瞎跑叫人嫌疑作啥。”
魏斌說:“興許是這個理。”
晚餐,就這樣在切磋之中過去了。
餐桌上母親問起表哥,卻沒有人問到陳吉生,這多半因為表哥到底是親戚,被視作家人,而陳吉生儘管是魏琴串連中的親密朋友,到底還隔得遠了。
這倒好,省得魏琴回答眼下難以回答的問題。
可是,當她洗完臉洗完腳,回到她和哥哥分隔的房間的時候,哥哥卻提出這個問題。
“琴,你知道陳吉生近來的情況嗎?”
魏琴剛在自己簡陋的梳妝兼書桌前坐下,要整理一下她以前串連時用的而如今上下班一直背的那個褪了色的黃布背包,聽到哥哥的問話,心裡一動,停住了手。
“不大知道。”魏琴不想告訴哥哥前不久她專程到真君裡找過陳吉生,也沒有說出陳吉生一 家的境況 。她知道哥哥心裡想的是啥。
陳吉生是她帶到哥哥面前的第一個男性朋友。那天哥哥在食堂招待他們,就有一種把陳吉生看作自己人的態度。
“你不關心這個事?”魏斌是有意激她一激。他不相信純真正直的妹妹對一個串連途中於她有恩有義的人會這麼不聞不問。
“關心的,可關心又能怎樣呢,哥。”魏琴有些激動又有些無耐。“他現在有難處,可我——”
“你還是知道他們家的事的。”魏斌掀開妹妹心中的秘密,“那你還很關心他的是不是?”
魏琴在哥哥面前沉默著。她瞞不過哥哥,也不必瞞著哥哥,哥哥是會保護她幫助她的。
剛才,在餐桌上他隻字不提此事,是怕她尷尬 。“哥。”魏琴惆悵地說,“在井崗山下,在羅婆家裡醒來的時候,我只知道是他把我背離那個死亡之地,沒有他的搭救,我可能就死在那個山溝裡了。當初,我只是很感激,沒有別的想法。”她有些動情。“後來,我們兩個人相伴走南闖北,從對待很多事件的探討切磋中我發現他對待事物的眼光冷靜,遇到突發事件,常常能想出妥當的處理方法,而我卻還沒有想到。慢慢的我就開始對他生起了除了感恩之外的遐想,而且那種感覺來的真快。”她沉吟了一會兒,繼續說,“那時,他沒有問我的家庭,是我奈不住了,很想讓他知道於是主動告訴他的。他聽了我的話,也不主動告訴我關於他父母的事,是我後來問了他才說父親和母親都是幹部,”
魏斌靜靜地聽著妹妹講述心裡的這個秘密
“他沒有說父母都是高幹?”魏斌問道。許多高幹子女都喜歡炫耀自己的家境和光榮歷史,陳吉生卻沒有。
“回上海以後,”魏琴說,“我想看看他的家——真的,我心裡已經很想知道他的家。哥,你別取笑我那麼迫不及待。——我問得緊,他才告訴我地址。有一天,兵團沒有事,我就去了。誰知找到的地址是一幢花園樓房,門前的庭院很寬闊,羅漢松,菊花滿園,比資本家賴法天那吸血魔窟還氣派。”她眼睛睜大盯著哥哥:“哥,你知道我當時心裡怎麼想?我想,難怪他不告訴我,原來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我受了矇騙,憤怒的轉身就走。”
“我走出一段路又想,既然已經來了怎麼也要弄個明白才行。”魏琴繼續說,“於是我又回去。等進了門,才知道陳吉生――他只是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愛炫耀自己的家境。”
魏斌自己還沒有談過戀愛,但他能想像妹妹的感情波瀾。他並沒有要高攀陳吉生這個高幹子弟的想法,只是從妹妹的幾次不多的言談中,瞭解到陳吉生的人品,倘若真能成為妹夫,也未必不是美事。可是現在情況發生了劇變。妹妹把痛苦埋在心底,成天忙忙碌碌嘻嘻哈哈的,作哥哥的不免為她擔憂。
“我們廠的孫師傅遇到過陳吉生。魏斌說。
“孫師傅?哪個孫師傅?他怎麼認識他?”魏琴愕然地發出好幾個問號。她很久沒有陳吉生的情況了。
“他說是在輪船甲板上和陳吉生認識的。”魏斌說。
“輪船甲板上?”魏琴終於回憶起來了,“哦,就是那位孫師傅?陳吉生在甲板上和他熱絡得不得了。他是出差回來和我們同船。”
她腦子裡還浮現在碼頭,在人潮中要分手的時候,陳吉生過去和他握手道別,孫師傅還邀請他到他廠裡去看車床。
她追問:“孫師傅怎麼遇上陳吉生?”
“孫懷勇——哦,我住院時他就在我隔壁床,你見過,那時他的頭裹著繃帶,你看不清。”魏斌說,“他那天騎著自行車正往回走,已經是夜深了,九,十點鐘光景,看到一個人在牆邊看大字報,仔細一看,是陳吉生。他就下車和他在路旁聊了好一陣子。”
孫懷勇從魏斌口中得知陳吉生是高幹子弟,而且他也得知這次奪權中,那個下臺的叫陳槐的局長正是陳吉生的父親。那天在路燈下看見陳吉生,便下了自行車車去和他聊了一會。既是重敘船上的邂逅情誼,也是出於對陳吉生現今境況的憐憫。
陳吉生沒有告訴他自己的家庭變遷,孫懷勇也就不忍掀起這層面紗 “他怎麼說?“魏琴關切地問。她現在很看重旁人怎麼看待陳吉生。
“他說他情緒不高。”魏斌說,“孫師傅是個好心腸的人,他歎口氣說:真是鳳凰落水不如雞呀。”
魏琴眼圈紅了。
“妹妹,你也別難過。”魏斌寬慰道,“落水鳳凰被太陽曬乾了還是很漂亮的,仍然飛得比雞高。”
魏琴被逗笑了。有點心酸的笑
但她很快就覺得脆弱不符合一個紅衛兵領導的性格。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才出去闖蕩造反的嗎?她很快調整了情緒,這下是真笑了,杏眼格外好看。
“哥,你笑話妹妹軟弱嗎?”
她的心事哥哥比父母知道得多知道得徹底。但她不想再說下去,把話題轉了。
問道:“你們廠造反隊是不是有分歧?”
魏斌瞅著妹妹,反問道:“你怎麼曉得?”
魏琴平靜地說:“是不是,你說嘛。”
魏斌透露說:“有。現在不是要建立廠領導班子嗎?廠的黨政領導早就靠邊站了,工作隊也早就撤了。造反隊不需要奪權,就可以發號施令。可是,那個鄭秋光負責人,讓他捏榔頭釘根釘子都是歪的,讓他操縱車床車出來的廢品多於合格品,這樣的人領導一個廠怎麼行!”
魏琴說:“就為這鬧分裂?”
魏斌鄭重地說:“這還不是大事呀!關係幾千人的生活,關係申江廠的生存呢。”
魏琴向哥哥透露了個秘密。她說:“鄭秋光給盧吉昌打電話的時候,我正在旁邊,鄭秋光向盧吉昌求援。我聽盧吉昌說:你放心,申江廠是我一手闖出來的,我不會袖手旁觀的。你們要廢鄭秋光恐怕不易。”
魏斌有些憤懣,他提高聲調:“不是說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嘛。盧吉昌己經高升了,已經去管轄市里的大事情去了,為什麼還抓住申江廠不放。”
魏琴在行動組,到底見的世面廣,經的事兒多,那些老單位不僅是他們發跡的根基,而且是他們一呼百應支持者的所在地。她自己不也時不時要打個電話,或者把蔡萍芳、瞿飛叫來聊聊,問問情況嗎!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出發點和根基。不僅盧吉昌時時關照著他的申江廠,就是王司令位居上海人民公社副主任的高位,也不忘他那個老家廠。”魏琴寓意很深的說。“有了政權就有一切,丟了政權就丟了一切。”
魏斌說:“聰明人就應當讓真正能幹的人去管理建設他的根基。廠搞好了,他自己也光彩。如果讓平庸之輩把持大權,搞砸了,那根基不照樣土崩瓦解,那時候他就沒有什麼好倚靠的了。”
魏琴說:“哥,你說的也有道理。不過,反正這事你當心一點。”
魏斌點點頭,感謝妹妹的提醒,更感謝妹妹透露這個情報。
鄭秋光大概己經預感到自己的腳後跟不穩,腰板子不硬,開始求救于上司了。
這事還得與孫師傅謀劃謀劃,可別吊以輕心了。魏斌心裡想著。
申江機械廠這些日子,看上去很平靜,其實暗潮湧動,大家各有各的心事。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公社核心領導中有盧吉昌的鐵心大哥。
造反隊負責人鄭秋光雄心勃勃:只要管好自已這個廠,就有生存發展、騰達升遷的日子
鄭秋光正和隊委陳菊英談著什麼。
孫懷勇從車間回到隊部,興致勃勃地向鄭秋光彙報說:“機器經過檢修,轉動起來了,如果原材料供得上,生產就可以搞上去。可就是工人太自由了,擅自離開崗位,讓機器空轉的現象太多。”他向鄭秋光求援,“我們得告訴工人以主人翁的態度,抓革命促生產。”
孫懷勇是分工抓生產的隊委,這是前任負責人盧吉昌派定的。孫懷勇論技術,論資歷,還有人緣都是最合適的人選,盧吉昌沒有選錯。
可是,鄭秋光明白,一個工廠,從科室到車間,都是圍著生產轉的,指揮生產者即是指揮工人大眾最實際的指揮者,尤其是當下沒有了黨組織,誰指揮生產誰就是工人大眾最有權威的領導者。而他這個造反隊的負責人除了造反隊開會需要出面,是可有可無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各個部門都在醞釀產生新生的權力機構,醞釀的意見竟然擁護孫懷勇的占了壓倒多數。
到了這節骨眼上,孫懷勇己經對他鄭秋光產生嚴重的威脅,功高震主,鄭秋光不能不膽寒,更令他嫉妒的是孫懷勇日益增長的威信。
鄭秋光對孫懷勇突然闖入打斷他和陳菊英的談話流露出不悅的情緒,他沒好氣地說:“工人不是很聽你的話嗎,你就教育去唄,還來找我做啥。”
孫懷勇是厚道人,沒有深一步辨別鄭秋光話的味道,爽快地答道:“我是想和大夥說說,但是不知道是否符合大方向,來向你請示。如果你也同意,那我們就這樣幹了。”說著起身就要出隊部。
鄭秋光粗聲粗氣地道:“老孫,你可真迫不及待呀。”
孫懷勇轉過身對著鄭秋光和陳菊英發愣,反問道:“你這是怎麼說——”
鄭秋光沉著臉不說話。
陳菊英在旁給鄭秋光的話詮釋,她說:“孫師傅你這是在努力抓出點成績來,給工人群眾有個好印象,這樣選舉建立三結合領導班子就有資本了。”
孫懷勇這下明白了,他氣呼呼地問陳菊英:“你是這樣看的?我抓生產還不是替造反隊效力!如果生產垮了,造反隊能光榮嗎!”他激動地把手一揮,“我這是好心換個驢肝肺,我不幹了。”
陳菊英笑嘻嘻地說:“你要是不幹,也沒人能強迫呀。”
這時,鄭秋光倒和顏悅色地走過夾,拍著孫懷勇的肩膀,撫慰道:“你想撂挑子?!別,別耍小孩兒脾氣。抓革命促生產,這是申江機械廠造反隊的天職。可老孫,我得提醒你一句,或許是一句忠言:抓革命擺在首位。不論怎麼說,抓革命總是比生產重要。我們不能重蹈走資派以抓生產壓制革命的覆轍噢。”他說完這話,很得意很有氣派地坐回椅子上。
孫懷勇氣呼呼地走出造反隊隊部。
西斜的陽光照在樹稍,那光禿禿的枝丫節兒上己經暴出芽,有的己經泛綠,但這些報春的消息沒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辛辛苦苦把工人組織起來,生產恢復起來,反而招來想出風頭的壞名聲。
“孫師傅,從哪裡來啊?”
孫懷勇駐步一看,是魏斌。
他不願提從隊部來,反問道:“你去哪裡?”
魏斌瞧他一臉怒氣,笑呵呵的說:“怎麼,不順心?”
孫懷勇在知心人面前不說假話:“我一心想把生產搞上去,這是黨中央的號召,可有人卻說我是為了撈資本。”
魏斌哈哈笑,笑得這廠區的曠地老遠就能聽到。
他從孫懷勇來的方向就知道他是在隊部受了氣。
“孫師傅,關於廠的領導班子,群眾議論很多。”魏斌把話鋒轉到權力問題上,“你是個很重要的人選哩。你聽到不?”
孫懷勇摸不透魏斌的話中之話,沉默著。
“孫師傅,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魏斌說,“我們這兒沒有宰相,可是,隊委也應當能聽各種意見呀。”
孫懷勇聽到一點風聲但他不放在心上。他說:“那只是大夥尋開心鬧著玩的。”
魏斌正經八板的說:“人家可不是隨便說說的。是鄭重其事的推薦你的。你想,要是那個人獨攬大權,那還行?你不比他強!”
魏斌細細的把群眾意見都告訴了孫懷勇,並說,當不當領導,不是個人的事,是工廠、工人群眾利益的大事。個人辛苦一點,值。
孫懷勇進退兩難:“嗨,這副爛攤子。”他沒有想去攬那碼子事。而且他也覺得自已無法領導一個幾千人的廠。
魏斌說:“你忍心讓幾千弟兄姐妹變成一群烏合之眾?”他給師傅鼓氣道:“只要你腰板直起來,大夥會支持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