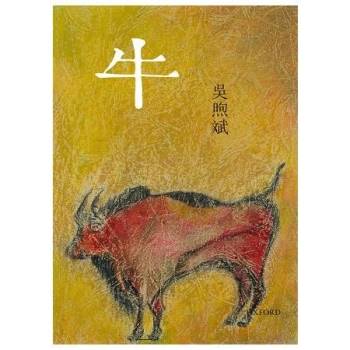佛魚
「來跟着我!我要教你們得人如得魚。」(馬太福音1.19 )
回來的時候已經沒有雨。黑色的山坳只有微弱的綠色閃光。我不知道怎樣向山荑解釋。那天捉的佛魚相信已經死了,我忘記帶一塊石子回家,只有水它準是活不成的。
我慢慢走着。空氣灰森森的瀰漫着霧,固體般的霧隨着我的過處慢慢開啟,然後在背後合攏起來。我跟前常常只有一小塊路,雨過後它已經沒有了顏色,白色的圓形的一小塊路,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把我帶回家裡。
風慢慢從山中吹上來,我感到有點寒冷。出來時我已經知道衣服不夠,但我不敢再在家裡多耽一會。山荑這樣從門後偷偷看我使我害怕。她把臂縮進懷裡,讓袖子空敞出來。我只有匆匆拿了傘跟他走。途中傘子給吹掉了,那天晚上風這樣疾。山間架的橋也塌了下來。木枝凌亂地散落在暗沉的山樹上。但他說沒有關係,我們便繼續走。雨點隨着倒歪的風不住打在我們身上。我們的衣衫都濕透了,沉重地掛下來。後來雨漸漸濃密了,四周一片灰茫茫,我只看見他蒼白的手臂在兩旁掛下來。蒼白的瘦長的手,在風中兀自擺盪。之後我們到了他山上的岩穴。
現在霧慢慢稀朗了,山樹朦朧地蓋着岩石色的日光。我似乎走了許久。回來的路程不知道為甚麼這樣長。身上的薄衣濕了又乾,現在似乎硬了一點,不時輕輕擦着我的頸背。皮膚也繃得緊緊,像新長的一層外皮。幸好家也快到了。
走進白林裡的時候,太陽已經漸漸下山。低黃的天空在枝椏間柔和地展開。地上的積水還沒有乾。枯葉和泥土裡的水在我踩進去時吱咕流過我的腳面。我們的白樹閃着寒冷的亮光。它們也快十尺高了,柔軟的枝椏在空中左右牽纏,月鈴花輕輕從上面掛下來,隨着風發出輕輕的噓聲。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把它掛在衣角,不知道它還會不會隨着行走的腳步唱歌。
風已經停了,空中只有從葉子上掉下來的星散的水滴,搖擺着落到頸子上。我的腿有點發痠,腳完全麻木了。許多天不住給雨水侵蝕,它們已經白得有點透明,青蒼的筋絡蜷曲地在上面爬行然後攀到腳底。我的佛魚也是這樣的顏色,只是它頭上多了一些灰黑的暗暈,一圈圈的疊到背鰭上。我第一次看見牠的時候,牠是躺在河邊一塊蒲團般的圓石子上,石子也是淡青色的。淡青的石子上一條淡青的魚。它盤着底鰭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流水,咀吧一開一合地呼吸,眼睛的下皮受了牽動也在輕輕地抖動。那是一個澄明的早晨,在太陽下牠發出淡淡的青光,給赤灰的四周蓋上一層新的寒蒼。四周一片寂靜,只有流水不時的淙琤聲。這裡沒有樹,所以也沒有葉子在風中的瑟索聲。河兩邊盡是石塊,一直伸展到白林的邊緣。我剛從山上回來,手裡拿着滿瓶子的樹液,看到這景象不覺怔住了。 我靜靜放下瓶子躡足走到牠身旁坐下。相信那時已經是正午,天空很高,無際地架在頭頂上。我也盤起腿獃獃地看着牠,像牠看着水流。我慢慢把手移近它青色的光暈,手上的細毛在青蒼裡微微發出亮光。我感到手背上漸漸加強的寒氣。在大白的太陽之下我竟漸漸顫抖起來了。我屏着氣一動也不敢動,遠處也只有風沙的聲音。但牠突然展開胸鰭穿過靜止的空氣呼啦跳進河裡。我急忙跳下來趕到河邊,但牠已經在白色河床的石子叢中消失了,水面也只有跳躍的白色亮光。之後,我看到他從對岸涉水過來。衣袍在風中蓬飛,太陽在他臉上蓋上一層金黃的日色。
回到家的時候我已經非常疲乏。腿的肌絡在輕輕地抽動。頭也彷彿支持不來。我坐在門跟。風又漸漸強了,從外面帶來一陣陣清淡的濕木氣味。山荑已經睡了。從這裡看來她非常細小。在暗黃的竹床上,她彎着白色的身體向外躺着,一隻手放在臉下,另一隻掛在床緣,頭髮柔柔瀉下來,衣衫的下襬也撩起了一角。我站起來輕輕走近她,相信她已經慟哭了許久。她的眼瞼還有一點紅,手腕給鼻子壓着的地方殘留着一些未乾的淚漬。我輕輕把她的髮撩到肩後。細小的孩子的肩膊。許多個晚上當她以為我睡了的時候,我看見它們在床的角落裡輕輕抽動,然後驚怯地慢慢翻過來看看我有沒有發覺。我的山荑。太陽已經降得很低,外面的白樹可能已經慢慢變成了紅色。我看見有幾根頭髮黏在她的臉上,橫過了小小的下巴,繞到後面去。我輕輕把它們拉出來,給壓着的地方現出了一些淡紅色的淺溝,這也漸漸平伏了。風又吹上來,床上的花瓣有幾片翻飄到床下。顏色已是淡棕色,靜靜躺到地面深褐的花層上,槐樹樁的桌子和小凳邊緣、風壺的耳朵上和樹牆間綴滿的花朵已經垂下了頭。「哎呀,已經沒了。冰箱裡的全用光了。」
「那麼,我去魚政一趟。」
魚政是位於馬路轉角的魚店,從上一代就有交情。
「路上小心。」
二三一面洗米,一面對著一子的背影說道。
時間是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午餐時段結束,店面休息,兩人剛悠閒地吃完員工餐。
晚上配合五點半開店,從四點多開始準備。接下來趁一小時半左右的空檔休息,然後就要一直站到九點。二三上二樓,鑽進暖被桌開始打盹兒。
她們的姓氏寫成「一」,讀作「ninomae」(二之前)。的確,一是二的前面。然而,寫成「二」,卻不讀作「sannomae」(三之前)。日語真難。尤其是人名和地名,甚至有「奇名怪名」這種猜謎節目的單元,實在是一個令人費解的世界。
二十六年前,決定和高結婚時,二三也心想「結婚之後,我就會變成一二三?!」,因而感到困惑。順帶一提的是,二三的舊姓是倉前(kuramae),明明發音和「一」(ninomae)差異不大,但是一旦化為文字,卻是天壤之別。
「有什麼關係,總比一子好多了。」
高彷彿從背後推躊躇不前的二三一把似地說道。
「是啊。哪像我,我是一一子唷。」
一子的這句話令二三消除心中的困惑,邁入了婚姻……
初餐館代代相傳,歷史相當悠久。。六十五年前,曾在銀座的飯店磨鍊的孝藏,和小巷的拉麵店西施—一子結婚,而五十年前,他們獨立門戶,在從小生長的佃這個街區,開了西餐的店。
從此之後,夫妻兩人胼手胝足。這家老街的西餐館生意興隆,但是三十年前,身為一家之主的孝藏心肌梗塞猝死。享年五十八歲。
當時,面臨了關店的危機,但是獨生子—高從任職的一流商社離職,繼承這家店,度過了難關。高的前妻在那前一年死於癌症,而高以看護妻子為由拒絕駐派國外的人事調動命令,遭遇了降職的下場。他從商社員工搖身一變為餐館大叔的背後,也牽扯了這種緣故。二三開始到初餐館用餐,也正好是在此時。她在大學畢業後,任職於大型百貨公司,住在三軒茶屋的公寓單人房,展開獨居生活,二十五歲時,剛搬到佃的廉價公寓。佃距離二三工作地點所在的銀座近,房租相對低廉,對於菜鳥粉領族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一開始愛慕虛榮,吃了苦頭,所以此時,二三也變得務實。縱然是沒有浴室的四疊半單人房、寒酸的廚房裡只有流理台和單口爐,但在佃的生活卻很舒適。她每天會去過了佃小橋即至的日之出湯洗澡,然後在初餐館吃晚餐。
後來,雖然因為奇妙的因緣際會,和高結了婚,但是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二三在百貨公司上班,每天在餐館吃飯,生了女兒—要之後,也繼續身為職業婦女,職位越爬越高。
十年前,高和父親一樣,心肌梗塞猝死……。他比父親去世時的年紀還少五歲,享年五十三歲。
初餐館遇上了第二個,而且是最大的危機。拯救初餐館的是二三的決斷。她決定辭掉百貨公司的工作,和一子一起在餐館工作。她身為服裝的採購員,活躍於職場,在業界亦是屈指可數、名聲響亮的人物,但是她毫不遲疑。這間餐館正是二三唯一的家。
往後十年,她徹底揮別過去能幹職業婦女的身份,如今不管怎麼看,都是一名餐館阿姨。她和化妝、名牌、高跟鞋再也無緣。但不可思議的是,從前被人在背後說成「苛刻」、「嚴厲」的容貌,在這十年內有了改變,最近甚至會被人說成「看起來很溫和的人」。二三切身感受到,餐館的工作意外地適合自己。
一子今年八十二歲,如今仍舊每天站在廚房,身子硬朗地工作。她的腦袋清楚、腰腿強健,無論是外表或內在,都比實際年齡整整年輕十五歲。這一切都是因為她老當益壯地站在第一線工作,而且從前被譽為「佃島的岸惠子」的美貌也仍在。
一子和二三身為婆媳,換作一般人,婆媳之間應該會各懷鬼胎,產生摩擦,但不可思議的是,她們的感情融洽。或許同心協力地一起掌管餐館也是原因之一,她們從以前就莫名投緣,簡單來說,就是合得來。一切應該都是緣份使然。
「阿姨,七草粥還有嗎?」
辰浪康平隔著吧檯,詢問一子。今天是一月七日。每年這一天的中午餐色中,都會有七草粥套餐,晚上偶爾也會有客人在喝酒之後想吃。康平是附近酒店的少東,生性在喝酒之後會想吃飯。
「有啊。你想吃多少?」她衣袍前大口袋中的花也枯了,有一些給壓皺了,尖直的摺角露出口袋外,有些給壓出液汁,把白色的袋子沾上暗紫的漬痕。或者她真的許久沒有到山上唱歌,採我們的花;或者她已經獃在牆角許多天,身子徐徐陷進床心,垂着頭等我回來。我輕輕挨前,握着她的手。
太陽已經沉得非常低,頑艷的擱在橫窗外,整個房間在一種虛幻的紅光中飄浮着,我怔怔的看着她的臉,在浮盪的光裡,她的眼睛慢慢睜開,一霎一霎地亮着。突然她驚跳起來半蹲着退到牆邊,雙手張開按着後面灰棕的樹牆。她憔悴了,臉上也只有太陽的光彩。我沒有做聲,但她已經慢慢平靜。她低下頭咬着咀唇輕輕笑起來,然後提起衣角膝行到床緣,像風中移動的影子,頭髮都溶進太陽裡。現在她的眼中有淚了。她提起手摟着我的脖子,寬闊的衣衫的袖子緩緩滑下來,露出蒼白的手。同樣是蒼白的瘦長的手,同樣的召喚。風又吹起來了。
「我以為你不回來了。」
她把臉貼在我敞開的胸膛上,灼熱的濕潤的臉頰,灼熱的唇,我懷裡劇烈抽動的身體。我感到她短促的呼吸。她顫抖的手輕輕捏着我的肌膚。我在床緣坐下來。她柔軟的纏綣的髮飄到我的耳根。她垂下手慢慢滑下去,伏在我的膝上哭泣。她的身體摺起來,像白色的胚胎。我感到我腿上她輕輕的牙咬,和透過衣衫的濕熱的呼氣。
「我不回來了。」
這裡已經許久沒有下雨,樹牆上新長的雨葉等一會又會掉到床間來,讓海裡來的鳥把它蓋在翅膀的傷口上。但牠也許久沒有來,可能牠已經回到同伴間去了。
山荑這時已經退到牆邊。白色衣衫裡小小的身體在暗紅的光中搖晃不定。她的手伸高抓着橫窗的邊緣。寬闊的衣袖又掉到手肘上。她歪着頭輕輕倚着樹牆,揉亂的髮飄披在淡紅的臉上。她已經沒有哭,剛才的淚也漸漸乾了。外面只有葉子還在乘風兀自翻飛。
可能她已經期待了許久,許多夜裡她靜靜躺在床上看着橫窗外星光的白樹時,她已經想着這樣的事情發生,想着這一切怎樣開始,我的沉默。自從我跑到山後高頂的樹上看天空以來,我便看見她逐漸憔悴。起初,她到河邊打水後會挽着水桶走到高樹對面看着我,靜靜等我下來。她會給我唱歌,唸我們的詩,她的髮上、衣衫上戴滿了奇異的花朵,臉和手在太陽下發出宕盪的金色亮光。有時她只在那裡向我微笑。風中的髮在眼睛裡蓬飛。開始時我總禁不住下來握她的手,跟她一起看灼熱的土地上芒刺的種籽。後來我只是看着她,看着她白色的足踝停止旋轉,她的臉慢慢暗淡下來,看着她在太陽下怔視的眼睛。我想她已經開始了解。最後她只是遠遠站在樹下看着我,寬闊的白色衣袍在她身上拍打,花朵給吹得四散了,恁地在空中飄舞。
後來許久她都沒有唱歌。或許她已經編了許多關於孤獨的故事。只是在等待我告訴她日子已經來臨。我不知道怎麼辦。看見她枯萎下去,我心裡感到絞痛。她曾經是這樣一個雲端的女孩,現在她絕望而美麗。但我不能做甚麼。在我遇到他以後,我甚至沒有明白。
現在一切都簡單了。她不用再害怕。要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最痛苦的在腦子裡懷想了這許久,覆演了這許久,現在已經不帶來傷害。她的臉孔甚至是柔和的。
「跟他一起麼?」
風的說話。風的聲音。
柔軟的白色枝條從橫窗外伸進來,影子落在她白色的衣袍和竹床上,輕輕隨着風吹搖曳。在這黯紅的流動的天光裡,她看來好像在透明的黑樹叢間擺盪,一晃一晃。
「跟他一起。」
「哪裡去?」
「海邊去,有人的地方。」
或者不是這樣。他沒有說。他只是叫我去,我便去了。之後便是不絕的山路和岩石。我們都沒有說話,到岩洞後他便讓我坐在乾地上。麻色的寬闊的岩洞,壁上零星長着灰亮的雙瓣山葉,一片一片,在風中像拍翅的青蟲。他用石竹的根生起火。我們的衣衫都濕透了,髮間的水掉下火裡,升起淡青色的煙。我們的繩鞋都在雨中丟了,落在山窪裡。我們把腳放到柴火旁,讓暖氣慢慢升至腰間。我們都聽到石竹發出輕輕的卵裂聲。之後他告訴我到海邊的路。
「真的不回來麼?」
我也不知道。我能告訴她甚麼呢?我沒有計劃,也忘記了許多事情。我甚至不曉得甚麼會發生。他現在仍在等候我麼?或者我得一個人下去,看海洋上白色的風痕。或者我們會走到人叢裡,我會聽見他對他們說話,他蒼白的手指着日照的天空。或者,許多年後我再會回到這裡看門旁山荑透亮的臉和飄盪的風袍。但我該怎麼說呢?
「不。」「嗯~飯碗七分滿左右。」
「馬上來。」
在花柳界,無論年紀多大,稱呼藝妓為「大姐」是老規矩。同樣地在餐館,無論年紀多大,稱呼工作的女性為「阿姨」,而非「老奶奶」,則是成規。年逾八十仍站在第一線工作的一子,當然是「阿姨」。
「吃粥果然對胃好,對吧?」
康平一面吹涼,一面以湯匙舀粥。一子免費招待了兩顆紀州產的梅乾,令他心情大好。
這一陣子,在超市會賣「七草粥組合」,所以不必特地採購各種材料,初餐館也很省事。
「對了,冬天沒有預定供應冷湯嗎?」
「嗯,那和麵線是夏季限定。季節感很重要。」
二三一面將熱酒端給一般座位的客人,一面應道。
原本在吧檯座位吃著味噌煮鯖魚套餐的客人,頭抖動了一下。
「店裡有賣冷湯嗎?」
「有,從六月賣到十月底。」
客人咕嘟地吞了一口唾沫。他是從去年十一月開始上門的新面孔,幾乎每隔三天就會來報到。總是晚上八點半左右進入店內,不喝酒,只點套餐。年齡將近四十,中等身材,眼睛又細又小、單眼皮,長相不起眼,但是身穿ARMANI的西裝和Ferragamo的皮鞋,手錶更是昂貴到令人眼珠子掉下來的Vacheron Constantin。
二三基於過去的職業病,忍不住對他品頭論足,內心對自己感到羞恥;儘管如此,她仍感到奇怪:為什麼一身高價名牌的男人,一週會有兩天在這種廉價餐館吃晚餐呢?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房子昏沉的溶進陰影裡。我只看見灰牆前她灰白的袍子和蒼白的手。
荒山的風從橫窗外吹進來,帶着雨濕的氣味,可能明天又會下雨了。
一九七二
「來跟着我!我要教你們得人如得魚。」(馬太福音1.19 )
回來的時候已經沒有雨。黑色的山坳只有微弱的綠色閃光。我不知道怎樣向山荑解釋。那天捉的佛魚相信已經死了,我忘記帶一塊石子回家,只有水它準是活不成的。
我慢慢走着。空氣灰森森的瀰漫着霧,固體般的霧隨着我的過處慢慢開啟,然後在背後合攏起來。我跟前常常只有一小塊路,雨過後它已經沒有了顏色,白色的圓形的一小塊路,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把我帶回家裡。
風慢慢從山中吹上來,我感到有點寒冷。出來時我已經知道衣服不夠,但我不敢再在家裡多耽一會。山荑這樣從門後偷偷看我使我害怕。她把臂縮進懷裡,讓袖子空敞出來。我只有匆匆拿了傘跟他走。途中傘子給吹掉了,那天晚上風這樣疾。山間架的橋也塌了下來。木枝凌亂地散落在暗沉的山樹上。但他說沒有關係,我們便繼續走。雨點隨着倒歪的風不住打在我們身上。我們的衣衫都濕透了,沉重地掛下來。後來雨漸漸濃密了,四周一片灰茫茫,我只看見他蒼白的手臂在兩旁掛下來。蒼白的瘦長的手,在風中兀自擺盪。之後我們到了他山上的岩穴。
現在霧慢慢稀朗了,山樹朦朧地蓋着岩石色的日光。我似乎走了許久。回來的路程不知道為甚麼這樣長。身上的薄衣濕了又乾,現在似乎硬了一點,不時輕輕擦着我的頸背。皮膚也繃得緊緊,像新長的一層外皮。幸好家也快到了。
走進白林裡的時候,太陽已經漸漸下山。低黃的天空在枝椏間柔和地展開。地上的積水還沒有乾。枯葉和泥土裡的水在我踩進去時吱咕流過我的腳面。我們的白樹閃着寒冷的亮光。它們也快十尺高了,柔軟的枝椏在空中左右牽纏,月鈴花輕輕從上面掛下來,隨着風發出輕輕的噓聲。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把它掛在衣角,不知道它還會不會隨着行走的腳步唱歌。
風已經停了,空中只有從葉子上掉下來的星散的水滴,搖擺着落到頸子上。我的腿有點發痠,腳完全麻木了。許多天不住給雨水侵蝕,它們已經白得有點透明,青蒼的筋絡蜷曲地在上面爬行然後攀到腳底。我的佛魚也是這樣的顏色,只是它頭上多了一些灰黑的暗暈,一圈圈的疊到背鰭上。我第一次看見牠的時候,牠是躺在河邊一塊蒲團般的圓石子上,石子也是淡青色的。淡青的石子上一條淡青的魚。它盤着底鰭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流水,咀吧一開一合地呼吸,眼睛的下皮受了牽動也在輕輕地抖動。那是一個澄明的早晨,在太陽下牠發出淡淡的青光,給赤灰的四周蓋上一層新的寒蒼。四周一片寂靜,只有流水不時的淙琤聲。這裡沒有樹,所以也沒有葉子在風中的瑟索聲。河兩邊盡是石塊,一直伸展到白林的邊緣。我剛從山上回來,手裡拿着滿瓶子的樹液,看到這景象不覺怔住了。 我靜靜放下瓶子躡足走到牠身旁坐下。相信那時已經是正午,天空很高,無際地架在頭頂上。我也盤起腿獃獃地看着牠,像牠看着水流。我慢慢把手移近它青色的光暈,手上的細毛在青蒼裡微微發出亮光。我感到手背上漸漸加強的寒氣。在大白的太陽之下我竟漸漸顫抖起來了。我屏着氣一動也不敢動,遠處也只有風沙的聲音。但牠突然展開胸鰭穿過靜止的空氣呼啦跳進河裡。我急忙跳下來趕到河邊,但牠已經在白色河床的石子叢中消失了,水面也只有跳躍的白色亮光。之後,我看到他從對岸涉水過來。衣袍在風中蓬飛,太陽在他臉上蓋上一層金黃的日色。
回到家的時候我已經非常疲乏。腿的肌絡在輕輕地抽動。頭也彷彿支持不來。我坐在門跟。風又漸漸強了,從外面帶來一陣陣清淡的濕木氣味。山荑已經睡了。從這裡看來她非常細小。在暗黃的竹床上,她彎着白色的身體向外躺着,一隻手放在臉下,另一隻掛在床緣,頭髮柔柔瀉下來,衣衫的下襬也撩起了一角。我站起來輕輕走近她,相信她已經慟哭了許久。她的眼瞼還有一點紅,手腕給鼻子壓着的地方殘留着一些未乾的淚漬。我輕輕把她的髮撩到肩後。細小的孩子的肩膊。許多個晚上當她以為我睡了的時候,我看見它們在床的角落裡輕輕抽動,然後驚怯地慢慢翻過來看看我有沒有發覺。我的山荑。太陽已經降得很低,外面的白樹可能已經慢慢變成了紅色。我看見有幾根頭髮黏在她的臉上,橫過了小小的下巴,繞到後面去。我輕輕把它們拉出來,給壓着的地方現出了一些淡紅色的淺溝,這也漸漸平伏了。風又吹上來,床上的花瓣有幾片翻飄到床下。顏色已是淡棕色,靜靜躺到地面深褐的花層上,槐樹樁的桌子和小凳邊緣、風壺的耳朵上和樹牆間綴滿的花朵已經垂下了頭。「哎呀,已經沒了。冰箱裡的全用光了。」
「那麼,我去魚政一趟。」
魚政是位於馬路轉角的魚店,從上一代就有交情。
「路上小心。」
二三一面洗米,一面對著一子的背影說道。
時間是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午餐時段結束,店面休息,兩人剛悠閒地吃完員工餐。
晚上配合五點半開店,從四點多開始準備。接下來趁一小時半左右的空檔休息,然後就要一直站到九點。二三上二樓,鑽進暖被桌開始打盹兒。
她們的姓氏寫成「一」,讀作「ninomae」(二之前)。的確,一是二的前面。然而,寫成「二」,卻不讀作「sannomae」(三之前)。日語真難。尤其是人名和地名,甚至有「奇名怪名」這種猜謎節目的單元,實在是一個令人費解的世界。
二十六年前,決定和高結婚時,二三也心想「結婚之後,我就會變成一二三?!」,因而感到困惑。順帶一提的是,二三的舊姓是倉前(kuramae),明明發音和「一」(ninomae)差異不大,但是一旦化為文字,卻是天壤之別。
「有什麼關係,總比一子好多了。」
高彷彿從背後推躊躇不前的二三一把似地說道。
「是啊。哪像我,我是一一子唷。」
一子的這句話令二三消除心中的困惑,邁入了婚姻……
初餐館代代相傳,歷史相當悠久。。六十五年前,曾在銀座的飯店磨鍊的孝藏,和小巷的拉麵店西施—一子結婚,而五十年前,他們獨立門戶,在從小生長的佃這個街區,開了西餐的店。
從此之後,夫妻兩人胼手胝足。這家老街的西餐館生意興隆,但是三十年前,身為一家之主的孝藏心肌梗塞猝死。享年五十八歲。
當時,面臨了關店的危機,但是獨生子—高從任職的一流商社離職,繼承這家店,度過了難關。高的前妻在那前一年死於癌症,而高以看護妻子為由拒絕駐派國外的人事調動命令,遭遇了降職的下場。他從商社員工搖身一變為餐館大叔的背後,也牽扯了這種緣故。二三開始到初餐館用餐,也正好是在此時。她在大學畢業後,任職於大型百貨公司,住在三軒茶屋的公寓單人房,展開獨居生活,二十五歲時,剛搬到佃的廉價公寓。佃距離二三工作地點所在的銀座近,房租相對低廉,對於菜鳥粉領族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一開始愛慕虛榮,吃了苦頭,所以此時,二三也變得務實。縱然是沒有浴室的四疊半單人房、寒酸的廚房裡只有流理台和單口爐,但在佃的生活卻很舒適。她每天會去過了佃小橋即至的日之出湯洗澡,然後在初餐館吃晚餐。
後來,雖然因為奇妙的因緣際會,和高結了婚,但是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二三在百貨公司上班,每天在餐館吃飯,生了女兒—要之後,也繼續身為職業婦女,職位越爬越高。
十年前,高和父親一樣,心肌梗塞猝死……。他比父親去世時的年紀還少五歲,享年五十三歲。
初餐館遇上了第二個,而且是最大的危機。拯救初餐館的是二三的決斷。她決定辭掉百貨公司的工作,和一子一起在餐館工作。她身為服裝的採購員,活躍於職場,在業界亦是屈指可數、名聲響亮的人物,但是她毫不遲疑。這間餐館正是二三唯一的家。
往後十年,她徹底揮別過去能幹職業婦女的身份,如今不管怎麼看,都是一名餐館阿姨。她和化妝、名牌、高跟鞋再也無緣。但不可思議的是,從前被人在背後說成「苛刻」、「嚴厲」的容貌,在這十年內有了改變,最近甚至會被人說成「看起來很溫和的人」。二三切身感受到,餐館的工作意外地適合自己。
一子今年八十二歲,如今仍舊每天站在廚房,身子硬朗地工作。她的腦袋清楚、腰腿強健,無論是外表或內在,都比實際年齡整整年輕十五歲。這一切都是因為她老當益壯地站在第一線工作,而且從前被譽為「佃島的岸惠子」的美貌也仍在。
一子和二三身為婆媳,換作一般人,婆媳之間應該會各懷鬼胎,產生摩擦,但不可思議的是,她們的感情融洽。或許同心協力地一起掌管餐館也是原因之一,她們從以前就莫名投緣,簡單來說,就是合得來。一切應該都是緣份使然。
「阿姨,七草粥還有嗎?」
辰浪康平隔著吧檯,詢問一子。今天是一月七日。每年這一天的中午餐色中,都會有七草粥套餐,晚上偶爾也會有客人在喝酒之後想吃。康平是附近酒店的少東,生性在喝酒之後會想吃飯。
「有啊。你想吃多少?」她衣袍前大口袋中的花也枯了,有一些給壓皺了,尖直的摺角露出口袋外,有些給壓出液汁,把白色的袋子沾上暗紫的漬痕。或者她真的許久沒有到山上唱歌,採我們的花;或者她已經獃在牆角許多天,身子徐徐陷進床心,垂着頭等我回來。我輕輕挨前,握着她的手。
太陽已經沉得非常低,頑艷的擱在橫窗外,整個房間在一種虛幻的紅光中飄浮着,我怔怔的看着她的臉,在浮盪的光裡,她的眼睛慢慢睜開,一霎一霎地亮着。突然她驚跳起來半蹲着退到牆邊,雙手張開按着後面灰棕的樹牆。她憔悴了,臉上也只有太陽的光彩。我沒有做聲,但她已經慢慢平靜。她低下頭咬着咀唇輕輕笑起來,然後提起衣角膝行到床緣,像風中移動的影子,頭髮都溶進太陽裡。現在她的眼中有淚了。她提起手摟着我的脖子,寬闊的衣衫的袖子緩緩滑下來,露出蒼白的手。同樣是蒼白的瘦長的手,同樣的召喚。風又吹起來了。
「我以為你不回來了。」
她把臉貼在我敞開的胸膛上,灼熱的濕潤的臉頰,灼熱的唇,我懷裡劇烈抽動的身體。我感到她短促的呼吸。她顫抖的手輕輕捏着我的肌膚。我在床緣坐下來。她柔軟的纏綣的髮飄到我的耳根。她垂下手慢慢滑下去,伏在我的膝上哭泣。她的身體摺起來,像白色的胚胎。我感到我腿上她輕輕的牙咬,和透過衣衫的濕熱的呼氣。
「我不回來了。」
這裡已經許久沒有下雨,樹牆上新長的雨葉等一會又會掉到床間來,讓海裡來的鳥把它蓋在翅膀的傷口上。但牠也許久沒有來,可能牠已經回到同伴間去了。
山荑這時已經退到牆邊。白色衣衫裡小小的身體在暗紅的光中搖晃不定。她的手伸高抓着橫窗的邊緣。寬闊的衣袖又掉到手肘上。她歪着頭輕輕倚着樹牆,揉亂的髮飄披在淡紅的臉上。她已經沒有哭,剛才的淚也漸漸乾了。外面只有葉子還在乘風兀自翻飛。
可能她已經期待了許久,許多夜裡她靜靜躺在床上看着橫窗外星光的白樹時,她已經想着這樣的事情發生,想着這一切怎樣開始,我的沉默。自從我跑到山後高頂的樹上看天空以來,我便看見她逐漸憔悴。起初,她到河邊打水後會挽着水桶走到高樹對面看着我,靜靜等我下來。她會給我唱歌,唸我們的詩,她的髮上、衣衫上戴滿了奇異的花朵,臉和手在太陽下發出宕盪的金色亮光。有時她只在那裡向我微笑。風中的髮在眼睛裡蓬飛。開始時我總禁不住下來握她的手,跟她一起看灼熱的土地上芒刺的種籽。後來我只是看着她,看着她白色的足踝停止旋轉,她的臉慢慢暗淡下來,看着她在太陽下怔視的眼睛。我想她已經開始了解。最後她只是遠遠站在樹下看着我,寬闊的白色衣袍在她身上拍打,花朵給吹得四散了,恁地在空中飄舞。
後來許久她都沒有唱歌。或許她已經編了許多關於孤獨的故事。只是在等待我告訴她日子已經來臨。我不知道怎麼辦。看見她枯萎下去,我心裡感到絞痛。她曾經是這樣一個雲端的女孩,現在她絕望而美麗。但我不能做甚麼。在我遇到他以後,我甚至沒有明白。
現在一切都簡單了。她不用再害怕。要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最痛苦的在腦子裡懷想了這許久,覆演了這許久,現在已經不帶來傷害。她的臉孔甚至是柔和的。
「跟他一起麼?」
風的說話。風的聲音。
柔軟的白色枝條從橫窗外伸進來,影子落在她白色的衣袍和竹床上,輕輕隨着風吹搖曳。在這黯紅的流動的天光裡,她看來好像在透明的黑樹叢間擺盪,一晃一晃。
「跟他一起。」
「哪裡去?」
「海邊去,有人的地方。」
或者不是這樣。他沒有說。他只是叫我去,我便去了。之後便是不絕的山路和岩石。我們都沒有說話,到岩洞後他便讓我坐在乾地上。麻色的寬闊的岩洞,壁上零星長着灰亮的雙瓣山葉,一片一片,在風中像拍翅的青蟲。他用石竹的根生起火。我們的衣衫都濕透了,髮間的水掉下火裡,升起淡青色的煙。我們的繩鞋都在雨中丟了,落在山窪裡。我們把腳放到柴火旁,讓暖氣慢慢升至腰間。我們都聽到石竹發出輕輕的卵裂聲。之後他告訴我到海邊的路。
「真的不回來麼?」
我也不知道。我能告訴她甚麼呢?我沒有計劃,也忘記了許多事情。我甚至不曉得甚麼會發生。他現在仍在等候我麼?或者我得一個人下去,看海洋上白色的風痕。或者我們會走到人叢裡,我會聽見他對他們說話,他蒼白的手指着日照的天空。或者,許多年後我再會回到這裡看門旁山荑透亮的臉和飄盪的風袍。但我該怎麼說呢?
「不。」「嗯~飯碗七分滿左右。」
「馬上來。」
在花柳界,無論年紀多大,稱呼藝妓為「大姐」是老規矩。同樣地在餐館,無論年紀多大,稱呼工作的女性為「阿姨」,而非「老奶奶」,則是成規。年逾八十仍站在第一線工作的一子,當然是「阿姨」。
「吃粥果然對胃好,對吧?」
康平一面吹涼,一面以湯匙舀粥。一子免費招待了兩顆紀州產的梅乾,令他心情大好。
這一陣子,在超市會賣「七草粥組合」,所以不必特地採購各種材料,初餐館也很省事。
「對了,冬天沒有預定供應冷湯嗎?」
「嗯,那和麵線是夏季限定。季節感很重要。」
二三一面將熱酒端給一般座位的客人,一面應道。
原本在吧檯座位吃著味噌煮鯖魚套餐的客人,頭抖動了一下。
「店裡有賣冷湯嗎?」
「有,從六月賣到十月底。」
客人咕嘟地吞了一口唾沫。他是從去年十一月開始上門的新面孔,幾乎每隔三天就會來報到。總是晚上八點半左右進入店內,不喝酒,只點套餐。年齡將近四十,中等身材,眼睛又細又小、單眼皮,長相不起眼,但是身穿ARMANI的西裝和Ferragamo的皮鞋,手錶更是昂貴到令人眼珠子掉下來的Vacheron Constantin。
二三基於過去的職業病,忍不住對他品頭論足,內心對自己感到羞恥;儘管如此,她仍感到奇怪:為什麼一身高價名牌的男人,一週會有兩天在這種廉價餐館吃晚餐呢?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房子昏沉的溶進陰影裡。我只看見灰牆前她灰白的袍子和蒼白的手。
荒山的風從橫窗外吹進來,帶着雨濕的氣味,可能明天又會下雨了。
一九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