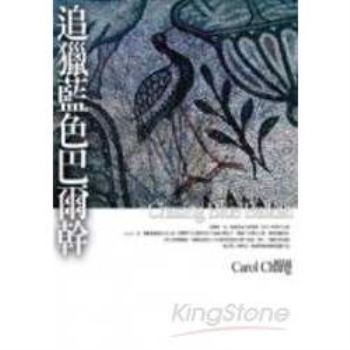奔向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飛機在跑道上滑動,我要離開台灣了。
這一趟,去的是馬其頓。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只有在聖經裡看過「馬其頓的呼喚」,只知道兩千年前,耶穌的門徒保羅去過馬其頓傳道,只知道亞歷山大帝和這個地名有關,如此而已。馬其頓應該是個歷史名詞,怎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有一個國家叫馬其頓? 旅行社的Amy問我:「馬其頓在哪裡啊?非洲還是歐洲?首都叫甚麼名字?」我說:「我也是從外交部打聽到,首都叫Skopje。」
飛機夜裡起飛,衝上天後,與滿天的星星相遇,上機前的混亂全擱在台北。安全帶的警示燈滅了,窗外的月亮離我好近,又圓又大,老朋友了,離開故鄉,就是他了。
在維也納機場等了六小時,下午兩點轉機,直達馬其頓首都Skopje。
候機室裡,除了我和其他四個女生,其他青一色軍人,一個個高頭大馬穿著迷彩軍服,這是國際候機室裡少見的景觀。我開始感覺不一樣了,也有一點不安,看他們的徽章有瑞典、 挪威 、德國 ,都是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問了一下,那四個女生是德國人,穿著T-shirt牛仔褲,到科索沃探老公的。一屋子的軍人,不管他們的表情態度多麼文明,空氣裡還是有股肅殺之氣。才離開台北,還沒踏上巴爾幹,在維也納就先聞到火藥味兒了。
聯合國派部隊到「可能」發生戰爭的地區,免得戰爭爆發後再派就來不及了,這是「維和部隊」的原則和特色。顯然馬其頓目前還沒打仗,但是也顯然有開戰的機率,否則聯合國不會派兵過來。不過中共也已經放話了,他們是安理會的一員,可以否決派兵到任何國家,中共駐馬其頓大使許月荷就曾公開放話──要搞台灣承認是不是?就別怪我們動用否決權。這一切都還在觀察中,馬其頓目前的政府(一九九九)執政不到三個月,非常年輕,總理喬傑夫斯基六0年代出生,才三十幾歲,他們說他離開大學後第一份工作就是總理,少年郎一上來就搞台灣承認,叫初生之犢不怕虎。
飛機在山裡轉來轉去,山頭都披著白雪,日正當中,太陽狠很的照著群山,閃閃發亮,偶爾出現一片紅色瓦房,一白一紅的很是好看。
一個小時後,飛機開始降落,就這麼近,一個小時!難怪巴爾幹有個風吹草動,歐洲大哥們就開始緊張,實在太近了,就在他們的後院。飛機在山堆裡降落,旅客下了飛機,一雙腳直接踩在跑道上,機坪停著兩架飛機,不是我說,這個機場比台中市的水南機場還小。「危險嗎?」我在排隊入境時,問一旁的德國女生。「NO!」也許,危險的是我的旅程,攝影師在哪兒還不知道,衛星上哪兒傳也不知道,一切等到了旅館再說。
前面,一萬個未知在等著。
*火車想開
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日
這輛火車載滿了阿爾巴尼亞難民
早上從科索沃首都佩斯汀納發車
目的地是馬其頓
中午時分 他們到了
警察奉令不讓他們下車
十分鐘後
火車掉頭
一陣尖叫嘶喊聲中
火車又把難民帶回了科索沃
獨立報的老史七早八早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跟他去拍東西,要就馬上到報社搭他便車。
「要!」我說。
「今天中午會有一班火車從佩斯丁納來,」老史一面開車一面說著,「上面會有很多阿爾巴尼亞難民。」佩斯丁納是科索沃的首府,太平時每天有火車與馬其頓對開,北約轟炸塞爾維亞時,改為不定時發車,報社有情報說今天有會有一班車進站。這兩天滿山遍野的難民衝破封鎖線往馬其頓逃,能買到火車票的,想必是有點辦法的。
「希望今天能拍到好東西。」拍到好照片,他就偷偷賣給路透社甚麼的。
「一張可以賣多少錢?」
「一百美金。」對一個月三百美金薪水的人來說,不無小補。
小鎮名叫Vokovo,一個很鄉下的地方,火車比預期的要晚了一個小時,我們才到不久突然聽到嗶嗶的哨子聲,出現了一堆警察,而且是真槍實彈穿著防彈背心衝到記者跟前,把我們都趕到邊上去。「這是怎麼回事啊?」老史對我擠了擠眼睛,要我跟著他過鐵軌到對面去。
火車來了。我聽到火車叫了。
CNN攝影記者從從容容的把機器放上了架,遠遠的站在警察指定的安全區內,等了一個上午,獵物終於要入鏡了。警察和軍人,也在汽笛鳴放後各就各位,不知道他們幹嘛要這麼緊張!車上的人買票進關,又不是通緝犯!
看到了,一部老火車。又黑又重的像才挖出來的煤,又像一隻懷了孕的穿山甲,蹣跚的走出山洞。四節車箱在我眼前停下,幾百隻眼睛惶恐的往外張望,是被眼前的警察給嚇的了!老史咔喳咔喳的按快門,我也本能的拿著傻瓜照像機拍了幾張就拍不下去了!我聽到其他的記者說這批人要「原車遣返!」十分鐘不到,車子緩緩啟動,所有的乘客不許下車,通通回科索沃老家!尖叫聲在啟動的剎那傳出車箱,好絕望的聲音!此起彼落。老史畢竟是專業攝影,他跨越鐵軌衝上車門,不顧警察的哨聲,抓住令人窒息的一刻。我也跟他跑,近距離的看到一張臉,貼著玻璃,與我雙目交視,呆滯的面容,倒沒有半點驚慌,我想他是累了。這些人千山萬水的來了,又要千山萬水的回去……。
十二點十五分,火車想往前開,卻只能往回走,帶著這批倒楣的阿爾巴尼亞難民回科索沃,叫聲傳遍山野,漸漸離去,在歐盟老大哥們不開口收留難民前,馬其頓總理宣部關閉邊界,穿山甲只好回到洞裡,黑暗的命運回歸了黑暗。
收工回家。老史一上車就撥電話:「我要告訴一個阿爾巴尼亞部長,」沒想到他老小子還有點正義感!「部長很生氣說要馬上察!人都出來了怎麼可以往回送!」忽然想到老史是塞爾維亞裔,兩個族群正殺得死去活來。「I am also a human being!」他白了我一眼。
隔幾天又見到老史,笑兮兮的對我說:「賣了一百五十美金。」
*希臘抗暴
2002年七月三十日,我在馬其頓遇上了一件怪事,讓當地人津津樂道,還有人說我是英雄。但我要誠實的說,事情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我的創造,一切與我無關,不過說明生命中有許多的不可知,路上有許多的意外,有悲、有喜罷了。
有一天,正在山上拍禿鷹,突然接到希臘代表處(台灣)友人的電話,無意間得知台灣要來一個球隊,參加第一屆世界杯聾啞籃球賽,台灣贏得東南亞區代表權,我馬上表示要去雅典採訪拍攝。
收到邀請函後,馬上給希臘駐馬其頓辦事處新聞組長打電話,請他協助攝影東尼和司機布切的簽證(我已有申根簽證)。在得知「簽證組說沒問題」後,東尼和布切立刻前往辦理,搞了四個多小時,下午四點多回來了。「怎麼樣?辦好了嗎?」我問。「我從來沒有這麼生氣過,他們把我們的護照扔到地上,叫我們撿起來,說go home! no visa!」
這還了得?我們東尼竟然就乖乖的彎下腰,把兩本護照檢起,不說一句話的回公司。我馬上給希臘新聞組長傳真要他們道歉,「否則後果自行負責!」同事們要我別作夢了,說我這個外國人不懂巴爾幹的文化,不懂「希臘人是不會道歉的!」要我省省力氣。我這就更氣了!「沒有試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說NO!」我把五位同事通通叫過來訓了一頓,對他們這些馬其頓人逆來順受的天性實在覺得不可思議。
第二天一早希臘有反應了。「請問你是Carol小姐嗎?」要我們馬上去辦簽證。辦公室一片歡呼。「我不要簽證,我要那位簽證官道歉。」我相信同事們心裡都在罵我豬頭。「我道歉,」可是你是誰?當地雇員道個什麼歉?「可是我們老闆是不會道歉的。」電話那頭說。「We’ll see!」那我們就等著瞧吧。
二00二年七月五日,我在Holiday Inn開了場致命的記者會,所有主流媒體都到了,我揭露希臘大使館的無恥行為,並宣佈在市中心廣場擺攤,歡迎受過羞辱的全體國民來簽名,他們不道歉我們就不罷休。結果被媒體逼得每天下午兩點在簽名現場舉行記者會,報告「抗議希臘使館粗暴行為運動」最新動態。「大小姐,你知不知道你是捅了麻蜂窩了?」一位友人興奮的說。結果兩禮拜不到,有近兩萬人簽名,這些還是自願出門到廣場簽名的,要是我登門造訪,肯定全國兩百萬的簽名滴水不漏。同事說已經達到組織政黨門檻,我可以組黨啦!
總而言之,反映是出乎意料的瘋狂。老百姓送花、送飲料、送冰淇淋、送自己畫的油畫、送自己打的金墜子,抱著我說「台灣我愛你」。一件應該做的事,一個簡單的動作,勾起了幾代人的憤怒,看著七八十歲的老人,佝僂著腰,兩手顫抖的拿著筆簽下姓名,我知道我做對了一件事。
二00二年七月三十日,希臘外交部副部長到簽名現場道歉,那位簽證官米海羅普洛斯遭調回懲處。這場群眾運動成了我生命中最美麗的一幅畫。
*吉普賽出櫃日
「出櫃甚麼稀奇的?人家吉普賽人幾百年前就出櫃了!」這是我的記者弗拉多對我說的。有一天,上午開會,討論這個禮拜走甚麼題目,弗拉多說想到南部希臘邊界的畢特拉城拍「出櫃」。
「Why are you so surprised? It is a custom here」弗拉多說我大驚小怪。「人家早八百年前就出櫃了,這是他們的風俗!」怎麼可能是風俗?!我在馬其頓住了六年,知道這是一個以百分之六十的東正教徒,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換句話說──相當保守,怎麼可能接受同性相戀的事實?有也是在櫃子裡。「OK,去調查一下吧!」
每年一月十三號,馬其頓南部的一個吉普賽人住的小村子裡,會有一個以上的男孩變裝出來玩 - 在小街上,在巷子裡,在菜市場,在他們住的村子附近鑽來鑽去,告訴族人他們是「同志」,而且還有個小樂隊跟在後面敲鑼打鼓的,很有小小嘉年華的味道。
馬其頓有五萬左右的吉普賽人,總理在二00四年保加利亞舉行的世界吉普賽族大會上,很自豪的說過:「馬其頓是世界上唯一憲法明文規定保護吉普賽民族的國家。」說的不錯,不但有憲法保護,國會裡還有兩個吉普賽議員,還有──兩個吉普賽電視台,很難想像吧?這些基本的權利,在巴爾幹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不過話雖如此,吉普賽人還是蠻苦的,他們卻也樂天知命,很會苦中作樂,喜歡唱歌跳舞。
我們鎖定的採訪對象叫瑞沛特,三十啷噹,職業是油漆工。訪問的時候,鄰居們都說早就知道他是個同性戀,大家都期待這天他能打扮打扮,出來讓他們瞧瞧。我們記者前一天晚上就趕到村子裡,因為天不亮瑞沛特就要開始上裝,我們拿著攝影機跟蹤拍攝,從早錄到晚,換裝打扮的鏡頭是不能漏的。老實講,這個瑞沛特還真醜,一張臉比鏡子還大,兩顆牙齒明顯的不見了,即使不見了牙齒,口紅還是要抹一抹的。房子裡,小朋友跳來跳去,他們一早就來報到,好奇的一會兒看著主角化妝,一會兒圍著攝影機傻笑。「他們都很善良,都是好人,太太們比較擔心,怕老公被拐了,哈哈……。」有個老阿婆對我們說。
一月,是巴爾幹最冷的季節,「女主角」穿著薄如蟬翼的藍色大禮服,我們穿著夾克都嫌冷,也不見他打個哆嗦。我請弗拉多問問街坊為甚麼是一月十三號?幹麻選冬天?應該有個典故吧!
我在倫敦住了將近十年,年年看Pride Day大遊行,成千上萬的同性戀人上街展示他們的意念。英國人以突出的裝扮表達一種概念,反應是愛惡兩極的。再看看我們馬其頓的場面,一個人帶著個小樂隊,單幹戶!驚人的是,觀眾沒有人顯出厭惡的態度,他們走到哪兒跳到哪兒,圍觀的人也跟著跳著,我看到一家店舖的老闆和老闆娘隨著音樂舞起,一高興,塞個紅包給瑞沛特,我也看見許多小朋友跟著跑 - 這是他們的一件快樂的事嘛!
事實上,弗拉多辛苦的拍了一天,就是問不出個所以然,沒人知道這個「風俗」甚麼時候開始的。「很久以前,」有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對我們說。他說他年輕時也出過櫃,他的長輩年輕時也出過櫃……。
「風俗,」老頭兒說。
*蕭瑟的南風
春天的南風是可以很蕭瑟的,如果風中捎來親人離去的訊息。
接到奇偉的電話,他說他很能體會我的感受,兩年前,他的大兒子威威在一場車禍中走了。「我現在走在路上,連看到樹葉子上的陽光都會哭,人家還以為我神經病。」說完乾笑幾聲。
我是幾個禮拜前失去了弟弟。昨天的追思禮拜上,來了不少老友,四、五十歲,幹的都是電視新聞這一行,除了奇偉,還有典婉、玉清他們。這些朋友,在電視新聞或紀錄片工作上水裡來、火裡去,正正派派的幹了幾十年。奇偉去年退休了,典婉早就萌生遠離台灣的意念,玉清也打算到東部找個小漁村,安靜安靜…。我們在禮拜堂裡會面,大家都心情滿滿。就像林語堂書裡說的,這時候的我們,漸漸地遠離了夏的火熱,淡淡的,有了秋的豐滿;然而,我們離冬藏,還是有段路途……。
奇偉去年退休了,曾經是華視新聞部的首席攝影,會拍會寫,拿過好幾座金鐘獎,人生最精華的歲月,給了「華視新聞雜誌」。過去,他不只一次的對我說,他有個心願,希望到大陸去做節目,最好是華視派他到北京,做個Bureau Chief,狠狠的拍些深度報導的新聞節目,「那裡題材真的很多!」他說。這個願望終究是沒能實現。退休後,他也很能享受爬山休閒的日子,可是,他這個年紀,正是美國NBC「六十分鐘」節目記者們的黃金歲月哪!不該冬藏的。
看看典婉,也是一流的新聞戰將,也是能寫能拍,成績有目共睹,是個有感覺的行動派。這兩年,又為什麼離開了電視,做一個招人凌遲的行政專員?甚至想到加拿大去開個茶館甚麼的。還有玉清……。這些台灣電視新聞的「前輩」們,在我看來,都是國家的寶貝,如果不選擇「升官」,難道就只有遠離新聞工作一途嗎?
這次從馬其頓回來,送走了弟弟約翰,他對我說的、最清楚的、最後一句話是:「姊,不要再做電視新聞了啦!」
馬其頓有個叫沙夏的瘸子
我之所以選擇離開住了將近十年的英國,應該不只是採訪報導上的專業考量,而是受到人性的呼喚。簡單的說,馬其頓人像個人。「吃了沒?還沒吃?」馬上到廚房,把剩菜剩飯弄一碗出來「給我吃!」就這麼原始。
我最記得從酒店搬到十二層市民住宅的第二天,一大早匆匆下樓趕個記者會,正打算叫計程車,才發現身上只有美金沒有馬幣,怎麼辦?太早,銀行還沒開門,一個人也不認識,急得要命!突然看到住在隔壁的新鄰居,見他手裡提著菜,迎面走來,他是個瘸子,一拐一拐的,我連他叫甚麼都不知道,就硬著頭皮上前:「我可不可以跟你換一百美金?」他馬上拽著我的手臂,快步,把我拉到雜貨店裡,一面拉一面說:「Macedonia people has no one hundred dollar。」意思是「馬其頓人沒有一百塊美金的」,雜貨店老板不認識我,卻「給」了我一仟馬幣(五百台幣),我要把一百美金壓給老闆,硬是不收!
這種經驗,沒有很久了。
倫敦有看得見的物質文明與看不見的民主制度,倫敦有漂亮的公園,有時髦的精品店,有一流的餐廳,許多東西馬其頓是望塵莫及的。但是,馬其頓有一個叫沙夏的瘸子,是英國打著燈籠也找不著的,要我選擇,答案已不需要言語了,只記得那天早上,這位瘸子先生讓我心情滿滿的出門採訪。
飛機在跑道上滑動,我要離開台灣了。
這一趟,去的是馬其頓。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只有在聖經裡看過「馬其頓的呼喚」,只知道兩千年前,耶穌的門徒保羅去過馬其頓傳道,只知道亞歷山大帝和這個地名有關,如此而已。馬其頓應該是個歷史名詞,怎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有一個國家叫馬其頓? 旅行社的Amy問我:「馬其頓在哪裡啊?非洲還是歐洲?首都叫甚麼名字?」我說:「我也是從外交部打聽到,首都叫Skopje。」
飛機夜裡起飛,衝上天後,與滿天的星星相遇,上機前的混亂全擱在台北。安全帶的警示燈滅了,窗外的月亮離我好近,又圓又大,老朋友了,離開故鄉,就是他了。
在維也納機場等了六小時,下午兩點轉機,直達馬其頓首都Skopje。
候機室裡,除了我和其他四個女生,其他青一色軍人,一個個高頭大馬穿著迷彩軍服,這是國際候機室裡少見的景觀。我開始感覺不一樣了,也有一點不安,看他們的徽章有瑞典、 挪威 、德國 ,都是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問了一下,那四個女生是德國人,穿著T-shirt牛仔褲,到科索沃探老公的。一屋子的軍人,不管他們的表情態度多麼文明,空氣裡還是有股肅殺之氣。才離開台北,還沒踏上巴爾幹,在維也納就先聞到火藥味兒了。
聯合國派部隊到「可能」發生戰爭的地區,免得戰爭爆發後再派就來不及了,這是「維和部隊」的原則和特色。顯然馬其頓目前還沒打仗,但是也顯然有開戰的機率,否則聯合國不會派兵過來。不過中共也已經放話了,他們是安理會的一員,可以否決派兵到任何國家,中共駐馬其頓大使許月荷就曾公開放話──要搞台灣承認是不是?就別怪我們動用否決權。這一切都還在觀察中,馬其頓目前的政府(一九九九)執政不到三個月,非常年輕,總理喬傑夫斯基六0年代出生,才三十幾歲,他們說他離開大學後第一份工作就是總理,少年郎一上來就搞台灣承認,叫初生之犢不怕虎。
飛機在山裡轉來轉去,山頭都披著白雪,日正當中,太陽狠很的照著群山,閃閃發亮,偶爾出現一片紅色瓦房,一白一紅的很是好看。
一個小時後,飛機開始降落,就這麼近,一個小時!難怪巴爾幹有個風吹草動,歐洲大哥們就開始緊張,實在太近了,就在他們的後院。飛機在山堆裡降落,旅客下了飛機,一雙腳直接踩在跑道上,機坪停著兩架飛機,不是我說,這個機場比台中市的水南機場還小。「危險嗎?」我在排隊入境時,問一旁的德國女生。「NO!」也許,危險的是我的旅程,攝影師在哪兒還不知道,衛星上哪兒傳也不知道,一切等到了旅館再說。
前面,一萬個未知在等著。
*火車想開
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日
這輛火車載滿了阿爾巴尼亞難民
早上從科索沃首都佩斯汀納發車
目的地是馬其頓
中午時分 他們到了
警察奉令不讓他們下車
十分鐘後
火車掉頭
一陣尖叫嘶喊聲中
火車又把難民帶回了科索沃
獨立報的老史七早八早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跟他去拍東西,要就馬上到報社搭他便車。
「要!」我說。
「今天中午會有一班火車從佩斯丁納來,」老史一面開車一面說著,「上面會有很多阿爾巴尼亞難民。」佩斯丁納是科索沃的首府,太平時每天有火車與馬其頓對開,北約轟炸塞爾維亞時,改為不定時發車,報社有情報說今天有會有一班車進站。這兩天滿山遍野的難民衝破封鎖線往馬其頓逃,能買到火車票的,想必是有點辦法的。
「希望今天能拍到好東西。」拍到好照片,他就偷偷賣給路透社甚麼的。
「一張可以賣多少錢?」
「一百美金。」對一個月三百美金薪水的人來說,不無小補。
小鎮名叫Vokovo,一個很鄉下的地方,火車比預期的要晚了一個小時,我們才到不久突然聽到嗶嗶的哨子聲,出現了一堆警察,而且是真槍實彈穿著防彈背心衝到記者跟前,把我們都趕到邊上去。「這是怎麼回事啊?」老史對我擠了擠眼睛,要我跟著他過鐵軌到對面去。
火車來了。我聽到火車叫了。
CNN攝影記者從從容容的把機器放上了架,遠遠的站在警察指定的安全區內,等了一個上午,獵物終於要入鏡了。警察和軍人,也在汽笛鳴放後各就各位,不知道他們幹嘛要這麼緊張!車上的人買票進關,又不是通緝犯!
看到了,一部老火車。又黑又重的像才挖出來的煤,又像一隻懷了孕的穿山甲,蹣跚的走出山洞。四節車箱在我眼前停下,幾百隻眼睛惶恐的往外張望,是被眼前的警察給嚇的了!老史咔喳咔喳的按快門,我也本能的拿著傻瓜照像機拍了幾張就拍不下去了!我聽到其他的記者說這批人要「原車遣返!」十分鐘不到,車子緩緩啟動,所有的乘客不許下車,通通回科索沃老家!尖叫聲在啟動的剎那傳出車箱,好絕望的聲音!此起彼落。老史畢竟是專業攝影,他跨越鐵軌衝上車門,不顧警察的哨聲,抓住令人窒息的一刻。我也跟他跑,近距離的看到一張臉,貼著玻璃,與我雙目交視,呆滯的面容,倒沒有半點驚慌,我想他是累了。這些人千山萬水的來了,又要千山萬水的回去……。
十二點十五分,火車想往前開,卻只能往回走,帶著這批倒楣的阿爾巴尼亞難民回科索沃,叫聲傳遍山野,漸漸離去,在歐盟老大哥們不開口收留難民前,馬其頓總理宣部關閉邊界,穿山甲只好回到洞裡,黑暗的命運回歸了黑暗。
收工回家。老史一上車就撥電話:「我要告訴一個阿爾巴尼亞部長,」沒想到他老小子還有點正義感!「部長很生氣說要馬上察!人都出來了怎麼可以往回送!」忽然想到老史是塞爾維亞裔,兩個族群正殺得死去活來。「I am also a human being!」他白了我一眼。
隔幾天又見到老史,笑兮兮的對我說:「賣了一百五十美金。」
*希臘抗暴
2002年七月三十日,我在馬其頓遇上了一件怪事,讓當地人津津樂道,還有人說我是英雄。但我要誠實的說,事情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我的創造,一切與我無關,不過說明生命中有許多的不可知,路上有許多的意外,有悲、有喜罷了。
有一天,正在山上拍禿鷹,突然接到希臘代表處(台灣)友人的電話,無意間得知台灣要來一個球隊,參加第一屆世界杯聾啞籃球賽,台灣贏得東南亞區代表權,我馬上表示要去雅典採訪拍攝。
收到邀請函後,馬上給希臘駐馬其頓辦事處新聞組長打電話,請他協助攝影東尼和司機布切的簽證(我已有申根簽證)。在得知「簽證組說沒問題」後,東尼和布切立刻前往辦理,搞了四個多小時,下午四點多回來了。「怎麼樣?辦好了嗎?」我問。「我從來沒有這麼生氣過,他們把我們的護照扔到地上,叫我們撿起來,說go home! no visa!」
這還了得?我們東尼竟然就乖乖的彎下腰,把兩本護照檢起,不說一句話的回公司。我馬上給希臘新聞組長傳真要他們道歉,「否則後果自行負責!」同事們要我別作夢了,說我這個外國人不懂巴爾幹的文化,不懂「希臘人是不會道歉的!」要我省省力氣。我這就更氣了!「沒有試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說NO!」我把五位同事通通叫過來訓了一頓,對他們這些馬其頓人逆來順受的天性實在覺得不可思議。
第二天一早希臘有反應了。「請問你是Carol小姐嗎?」要我們馬上去辦簽證。辦公室一片歡呼。「我不要簽證,我要那位簽證官道歉。」我相信同事們心裡都在罵我豬頭。「我道歉,」可是你是誰?當地雇員道個什麼歉?「可是我們老闆是不會道歉的。」電話那頭說。「We’ll see!」那我們就等著瞧吧。
二00二年七月五日,我在Holiday Inn開了場致命的記者會,所有主流媒體都到了,我揭露希臘大使館的無恥行為,並宣佈在市中心廣場擺攤,歡迎受過羞辱的全體國民來簽名,他們不道歉我們就不罷休。結果被媒體逼得每天下午兩點在簽名現場舉行記者會,報告「抗議希臘使館粗暴行為運動」最新動態。「大小姐,你知不知道你是捅了麻蜂窩了?」一位友人興奮的說。結果兩禮拜不到,有近兩萬人簽名,這些還是自願出門到廣場簽名的,要是我登門造訪,肯定全國兩百萬的簽名滴水不漏。同事說已經達到組織政黨門檻,我可以組黨啦!
總而言之,反映是出乎意料的瘋狂。老百姓送花、送飲料、送冰淇淋、送自己畫的油畫、送自己打的金墜子,抱著我說「台灣我愛你」。一件應該做的事,一個簡單的動作,勾起了幾代人的憤怒,看著七八十歲的老人,佝僂著腰,兩手顫抖的拿著筆簽下姓名,我知道我做對了一件事。
二00二年七月三十日,希臘外交部副部長到簽名現場道歉,那位簽證官米海羅普洛斯遭調回懲處。這場群眾運動成了我生命中最美麗的一幅畫。
*吉普賽出櫃日
「出櫃甚麼稀奇的?人家吉普賽人幾百年前就出櫃了!」這是我的記者弗拉多對我說的。有一天,上午開會,討論這個禮拜走甚麼題目,弗拉多說想到南部希臘邊界的畢特拉城拍「出櫃」。
「Why are you so surprised? It is a custom here」弗拉多說我大驚小怪。「人家早八百年前就出櫃了,這是他們的風俗!」怎麼可能是風俗?!我在馬其頓住了六年,知道這是一個以百分之六十的東正教徒,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換句話說──相當保守,怎麼可能接受同性相戀的事實?有也是在櫃子裡。「OK,去調查一下吧!」
每年一月十三號,馬其頓南部的一個吉普賽人住的小村子裡,會有一個以上的男孩變裝出來玩 - 在小街上,在巷子裡,在菜市場,在他們住的村子附近鑽來鑽去,告訴族人他們是「同志」,而且還有個小樂隊跟在後面敲鑼打鼓的,很有小小嘉年華的味道。
馬其頓有五萬左右的吉普賽人,總理在二00四年保加利亞舉行的世界吉普賽族大會上,很自豪的說過:「馬其頓是世界上唯一憲法明文規定保護吉普賽民族的國家。」說的不錯,不但有憲法保護,國會裡還有兩個吉普賽議員,還有──兩個吉普賽電視台,很難想像吧?這些基本的權利,在巴爾幹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不過話雖如此,吉普賽人還是蠻苦的,他們卻也樂天知命,很會苦中作樂,喜歡唱歌跳舞。
我們鎖定的採訪對象叫瑞沛特,三十啷噹,職業是油漆工。訪問的時候,鄰居們都說早就知道他是個同性戀,大家都期待這天他能打扮打扮,出來讓他們瞧瞧。我們記者前一天晚上就趕到村子裡,因為天不亮瑞沛特就要開始上裝,我們拿著攝影機跟蹤拍攝,從早錄到晚,換裝打扮的鏡頭是不能漏的。老實講,這個瑞沛特還真醜,一張臉比鏡子還大,兩顆牙齒明顯的不見了,即使不見了牙齒,口紅還是要抹一抹的。房子裡,小朋友跳來跳去,他們一早就來報到,好奇的一會兒看著主角化妝,一會兒圍著攝影機傻笑。「他們都很善良,都是好人,太太們比較擔心,怕老公被拐了,哈哈……。」有個老阿婆對我們說。
一月,是巴爾幹最冷的季節,「女主角」穿著薄如蟬翼的藍色大禮服,我們穿著夾克都嫌冷,也不見他打個哆嗦。我請弗拉多問問街坊為甚麼是一月十三號?幹麻選冬天?應該有個典故吧!
我在倫敦住了將近十年,年年看Pride Day大遊行,成千上萬的同性戀人上街展示他們的意念。英國人以突出的裝扮表達一種概念,反應是愛惡兩極的。再看看我們馬其頓的場面,一個人帶著個小樂隊,單幹戶!驚人的是,觀眾沒有人顯出厭惡的態度,他們走到哪兒跳到哪兒,圍觀的人也跟著跳著,我看到一家店舖的老闆和老闆娘隨著音樂舞起,一高興,塞個紅包給瑞沛特,我也看見許多小朋友跟著跑 - 這是他們的一件快樂的事嘛!
事實上,弗拉多辛苦的拍了一天,就是問不出個所以然,沒人知道這個「風俗」甚麼時候開始的。「很久以前,」有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對我們說。他說他年輕時也出過櫃,他的長輩年輕時也出過櫃……。
「風俗,」老頭兒說。
*蕭瑟的南風
春天的南風是可以很蕭瑟的,如果風中捎來親人離去的訊息。
接到奇偉的電話,他說他很能體會我的感受,兩年前,他的大兒子威威在一場車禍中走了。「我現在走在路上,連看到樹葉子上的陽光都會哭,人家還以為我神經病。」說完乾笑幾聲。
我是幾個禮拜前失去了弟弟。昨天的追思禮拜上,來了不少老友,四、五十歲,幹的都是電視新聞這一行,除了奇偉,還有典婉、玉清他們。這些朋友,在電視新聞或紀錄片工作上水裡來、火裡去,正正派派的幹了幾十年。奇偉去年退休了,典婉早就萌生遠離台灣的意念,玉清也打算到東部找個小漁村,安靜安靜…。我們在禮拜堂裡會面,大家都心情滿滿。就像林語堂書裡說的,這時候的我們,漸漸地遠離了夏的火熱,淡淡的,有了秋的豐滿;然而,我們離冬藏,還是有段路途……。
奇偉去年退休了,曾經是華視新聞部的首席攝影,會拍會寫,拿過好幾座金鐘獎,人生最精華的歲月,給了「華視新聞雜誌」。過去,他不只一次的對我說,他有個心願,希望到大陸去做節目,最好是華視派他到北京,做個Bureau Chief,狠狠的拍些深度報導的新聞節目,「那裡題材真的很多!」他說。這個願望終究是沒能實現。退休後,他也很能享受爬山休閒的日子,可是,他這個年紀,正是美國NBC「六十分鐘」節目記者們的黃金歲月哪!不該冬藏的。
看看典婉,也是一流的新聞戰將,也是能寫能拍,成績有目共睹,是個有感覺的行動派。這兩年,又為什麼離開了電視,做一個招人凌遲的行政專員?甚至想到加拿大去開個茶館甚麼的。還有玉清……。這些台灣電視新聞的「前輩」們,在我看來,都是國家的寶貝,如果不選擇「升官」,難道就只有遠離新聞工作一途嗎?
這次從馬其頓回來,送走了弟弟約翰,他對我說的、最清楚的、最後一句話是:「姊,不要再做電視新聞了啦!」
馬其頓有個叫沙夏的瘸子
我之所以選擇離開住了將近十年的英國,應該不只是採訪報導上的專業考量,而是受到人性的呼喚。簡單的說,馬其頓人像個人。「吃了沒?還沒吃?」馬上到廚房,把剩菜剩飯弄一碗出來「給我吃!」就這麼原始。
我最記得從酒店搬到十二層市民住宅的第二天,一大早匆匆下樓趕個記者會,正打算叫計程車,才發現身上只有美金沒有馬幣,怎麼辦?太早,銀行還沒開門,一個人也不認識,急得要命!突然看到住在隔壁的新鄰居,見他手裡提著菜,迎面走來,他是個瘸子,一拐一拐的,我連他叫甚麼都不知道,就硬著頭皮上前:「我可不可以跟你換一百美金?」他馬上拽著我的手臂,快步,把我拉到雜貨店裡,一面拉一面說:「Macedonia people has no one hundred dollar。」意思是「馬其頓人沒有一百塊美金的」,雜貨店老板不認識我,卻「給」了我一仟馬幣(五百台幣),我要把一百美金壓給老闆,硬是不收!
這種經驗,沒有很久了。
倫敦有看得見的物質文明與看不見的民主制度,倫敦有漂亮的公園,有時髦的精品店,有一流的餐廳,許多東西馬其頓是望塵莫及的。但是,馬其頓有一個叫沙夏的瘸子,是英國打著燈籠也找不著的,要我選擇,答案已不需要言語了,只記得那天早上,這位瘸子先生讓我心情滿滿的出門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