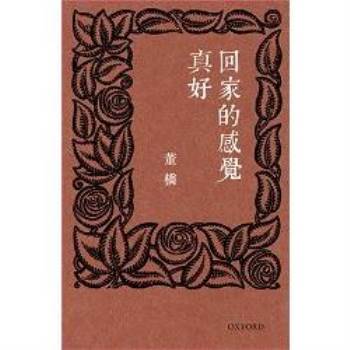佛誕日的一瓣靜念
去年在報上讀翁靈文先生寫姚克和上官雲珠及女兒姚姚的悲劇,心裏非常難過,剪下文章存進檔案櫃子裏。前幾天,熟悉孤島上海文化狀況的內地來客偶然談起著名影劇演員上官雲珠文革受迫害跳樓自殺的往事,說姚克跟上官雲珠離婚南來香港之後,上官雲珠和姚姚好像沒什麼好日子過。
姚克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前輩,中英文都好到絕頂,晚年定居夏威夷。翁先生的文章說,一九七五年九月,姚先生知道在上海的女兒姚姚來香港的單程證手續辦妥,約好翁先生九月二十四號開車陪他去接機。據陳丹燕《紅顏遺事》書上說: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上海下着小雨,姚姚騎單車趕着去跟幾位師友辭行。那天墨西哥體育代表團正好要離滬回國,照文革時期規定,外國人車隊經過的街區都封鎖交通。十點多鐘姚姚經過南京路,交通封了,一輛航運局的載重卡車突然出現,駕駛室門上的鈎子扯住姚姚的雨衣,把她牽倒在卡車輪下,後輪碾過她的胸部和頭部,重傷斃命。
內地來客早年寫過幾篇談佛教談寺廟的長文,雖不信佛,卻愛說緣:「母女倆注定要這樣來、這樣去。早知如此,此生不如吃素唸經,反倒省事」我當年也許看過上官雲珠的戲,沒有印象了。姚克先生的創作著作和譯作我讀得很用心,受用不盡;翁先生說,姚老接到噩耗那天晚飯都沒吃,一個人關起門呆在樓上,我讀了格外難過。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裏有一則故事說:一位巨公四月初八在佛寺禮懺放生,游僧問他為什麼今天要來做好事?他答道:「佛誕日也。」再問:「佛誕日就做好事,餘下的三百五十九天都不必做好事了嗎?我公今日放生,那是眼見的功德;不知道每年家中廚師所殺的雞鴨牛羊夠不夠這次放生的數目?」巨公答不出話。廟裏有個老和尚聽了覺得游僧的話是佛門淨地的獅子一吼,聯想起從前五台出僧人明玉說過的一席話:「心心唸佛,惡意不生,不是日唸數聲就算功德。天天吃素,殺業永除,不是每月戒它幾天就算功德。只限初一十五不吃肉,謂之善人,那貪官污吏每月只限幾天不受錢,可以叫做廉潔的官員嗎?」紀曉嵐轉而引了李杏浦的話說:終身茹素,並不容易;每月守幾天齋,則那幾天也算減少殺生了;越多人那樣做,世間殺生之數也就越少了。人生多苦,宗教信念正是苦中的靜因之道,隨緣之餘,心中常常念記寺廟教堂那一絲祥寧的安瀾,不難換來幾分處世的沉着和氣度。能學王度廬那樣長年吃素,那是澹泊的智慧了。
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
小泉首相不死的愛
日本新任首相小泉純一郎貝多芬的髮型標舉不羈的形象和改革的氣息。《華盛頓郵報》的社評說他離婚是不尋常的處境、慈父是極稀有的品德、一頭飄逸的長髮象徵了清新的反叛精神。社評於是呼籲布殊政府支持小泉的改革措施:「日本的變局吉凶難卜,可是,漠視這次的契機是不對的」。
我倒不覺得這是個契機。畢竟是十足的鷹派,畢竟是狡黠的政客,畢竟是軍國主義的子孫,小泉純一郎其實不但要把自衛隊升格為軍隊,還講明要去參拜靖國神社為皇軍招魂。他的政治改革離不開他那一代日本人冷酷的浪漫軍國情結,砸不破他那一代日本人頑固的政治派系意識。狂熱的愛國情操像黃絲帶那樣永遠繫在靖國神社參天的古樹上。
我七十年代在英國做事的那段時期,有一位日本同事跟我聊起日本老一輩人的愛的觀念。他說,詩人W.H.Auden有一句詩”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後來改成了”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and die”:「日本老一輩人的愛正是這樣,不是沒有愛毋寧死,而是愛要愛到一起死。對老一輩日本人來說,奧登改得太好了!」我不知道小泉的戀愛是不是也愛得想死在一起。我只聽說他見了胖女人就說瘦巴巴的女人沒有魅力:「你現在是最佳狀態,瘦一公斤或胖一公斤都行」。他的政治之愛肯定不會這樣體貼。詩人奧登一九七三年六十六歲去世。他那首詩是一九三九年寫的,我當時翻查過的幾個詩集版本都沒有改:”Hunger allows no choice/To the citizen or the police;/ 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到了一九八九年,我讀到美國科幻小說家Ray Bradbury發表在美國報上的一封信,沉痛抗議奧登一字之易,凶象畢露。他說,活在愛中並不等於從此渾忘周圍的黑暗,反而互為火光,照亮對方。可惜我已經找不到那位日本同事,不能告訴他日本老一輩人的愛的觀念是偏激的。小泉純一郎跟自民黨幹事長古賀誠會談後決定維持三黨聯合政權,決定維持黨的團結。政治利益的牽扯,軍國幽靈的纏繞,小泉注定要扣着腳鐐跳政治圓舞曲。他在議員圈子裏的凝聚力不大,只好以團結的意願作妥協;既講團結,派系自必延續;派系不倒,遑言改革!難怪台灣報上說,小泉純一郎「將來不是摸着石頭過河,便是見風駛舵向現實低頭,不然也許短時期能意氣風發,最後則可能慘淡收場」。
他對軍國主義的愛倒是不會死的。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去年在報上讀翁靈文先生寫姚克和上官雲珠及女兒姚姚的悲劇,心裏非常難過,剪下文章存進檔案櫃子裏。前幾天,熟悉孤島上海文化狀況的內地來客偶然談起著名影劇演員上官雲珠文革受迫害跳樓自殺的往事,說姚克跟上官雲珠離婚南來香港之後,上官雲珠和姚姚好像沒什麼好日子過。
姚克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前輩,中英文都好到絕頂,晚年定居夏威夷。翁先生的文章說,一九七五年九月,姚先生知道在上海的女兒姚姚來香港的單程證手續辦妥,約好翁先生九月二十四號開車陪他去接機。據陳丹燕《紅顏遺事》書上說: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上海下着小雨,姚姚騎單車趕着去跟幾位師友辭行。那天墨西哥體育代表團正好要離滬回國,照文革時期規定,外國人車隊經過的街區都封鎖交通。十點多鐘姚姚經過南京路,交通封了,一輛航運局的載重卡車突然出現,駕駛室門上的鈎子扯住姚姚的雨衣,把她牽倒在卡車輪下,後輪碾過她的胸部和頭部,重傷斃命。
內地來客早年寫過幾篇談佛教談寺廟的長文,雖不信佛,卻愛說緣:「母女倆注定要這樣來、這樣去。早知如此,此生不如吃素唸經,反倒省事」我當年也許看過上官雲珠的戲,沒有印象了。姚克先生的創作著作和譯作我讀得很用心,受用不盡;翁先生說,姚老接到噩耗那天晚飯都沒吃,一個人關起門呆在樓上,我讀了格外難過。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裏有一則故事說:一位巨公四月初八在佛寺禮懺放生,游僧問他為什麼今天要來做好事?他答道:「佛誕日也。」再問:「佛誕日就做好事,餘下的三百五十九天都不必做好事了嗎?我公今日放生,那是眼見的功德;不知道每年家中廚師所殺的雞鴨牛羊夠不夠這次放生的數目?」巨公答不出話。廟裏有個老和尚聽了覺得游僧的話是佛門淨地的獅子一吼,聯想起從前五台出僧人明玉說過的一席話:「心心唸佛,惡意不生,不是日唸數聲就算功德。天天吃素,殺業永除,不是每月戒它幾天就算功德。只限初一十五不吃肉,謂之善人,那貪官污吏每月只限幾天不受錢,可以叫做廉潔的官員嗎?」紀曉嵐轉而引了李杏浦的話說:終身茹素,並不容易;每月守幾天齋,則那幾天也算減少殺生了;越多人那樣做,世間殺生之數也就越少了。人生多苦,宗教信念正是苦中的靜因之道,隨緣之餘,心中常常念記寺廟教堂那一絲祥寧的安瀾,不難換來幾分處世的沉着和氣度。能學王度廬那樣長年吃素,那是澹泊的智慧了。
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
小泉首相不死的愛
日本新任首相小泉純一郎貝多芬的髮型標舉不羈的形象和改革的氣息。《華盛頓郵報》的社評說他離婚是不尋常的處境、慈父是極稀有的品德、一頭飄逸的長髮象徵了清新的反叛精神。社評於是呼籲布殊政府支持小泉的改革措施:「日本的變局吉凶難卜,可是,漠視這次的契機是不對的」。
我倒不覺得這是個契機。畢竟是十足的鷹派,畢竟是狡黠的政客,畢竟是軍國主義的子孫,小泉純一郎其實不但要把自衛隊升格為軍隊,還講明要去參拜靖國神社為皇軍招魂。他的政治改革離不開他那一代日本人冷酷的浪漫軍國情結,砸不破他那一代日本人頑固的政治派系意識。狂熱的愛國情操像黃絲帶那樣永遠繫在靖國神社參天的古樹上。
我七十年代在英國做事的那段時期,有一位日本同事跟我聊起日本老一輩人的愛的觀念。他說,詩人W.H.Auden有一句詩”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後來改成了”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and die”:「日本老一輩人的愛正是這樣,不是沒有愛毋寧死,而是愛要愛到一起死。對老一輩日本人來說,奧登改得太好了!」我不知道小泉的戀愛是不是也愛得想死在一起。我只聽說他見了胖女人就說瘦巴巴的女人沒有魅力:「你現在是最佳狀態,瘦一公斤或胖一公斤都行」。他的政治之愛肯定不會這樣體貼。詩人奧登一九七三年六十六歲去世。他那首詩是一九三九年寫的,我當時翻查過的幾個詩集版本都沒有改:”Hunger allows no choice/To the citizen or the police;/ 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到了一九八九年,我讀到美國科幻小說家Ray Bradbury發表在美國報上的一封信,沉痛抗議奧登一字之易,凶象畢露。他說,活在愛中並不等於從此渾忘周圍的黑暗,反而互為火光,照亮對方。可惜我已經找不到那位日本同事,不能告訴他日本老一輩人的愛的觀念是偏激的。小泉純一郎跟自民黨幹事長古賀誠會談後決定維持三黨聯合政權,決定維持黨的團結。政治利益的牽扯,軍國幽靈的纏繞,小泉注定要扣着腳鐐跳政治圓舞曲。他在議員圈子裏的凝聚力不大,只好以團結的意願作妥協;既講團結,派系自必延續;派系不倒,遑言改革!難怪台灣報上說,小泉純一郎「將來不是摸着石頭過河,便是見風駛舵向現實低頭,不然也許短時期能意氣風發,最後則可能慘淡收場」。
他對軍國主義的愛倒是不會死的。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