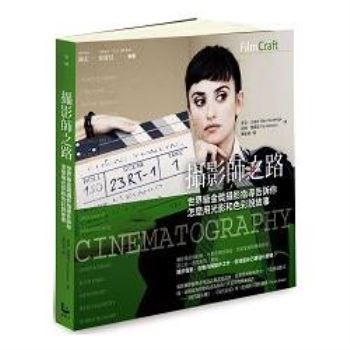維多里歐.史托拉洛Vittorio Storaro
■簡介
維多里歐.史托拉洛於一九四○年出生在羅馬,父親在家鄉的拉克斯電影公司(Lux Film)擔任放映師。十一歲時,在父親的鼓勵下,進入「杜卡德奧斯塔」攝影技術學院(Istituto Tecnico Fotografico “Duca D’Aosta”)就讀,取得名為「攝影師傅」的文憑。十六到十八歲期間,他在義大利電影攝影訓練中心(Italian Cinematographic Training Centre)研習,一九五八年申請獲准進入國立電影學校電影實驗中心(Centro Sperimentale di Cinematagrafia)修習為期兩年的電影攝影課程。二十歲時,他成為電影攝影師亞多.史卡華達(Aldo Scavarda)的助理。二十一歲那年,攝影師馬可.史卡佩利(Marco Scarpelli)讓他晉身義大利最年輕的攝影機操作員。可惜當時義大利電影製作界變得蕭條,耽擱了他的事業生涯,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在貝托魯奇的導演處女作《革命之前》(Before the Revolution, 1964)中擔任攝影助理。
他利用專業生涯早期那一段漫長的空檔研究了各種形式的藝術。一九六九年,他在法朗哥.羅西(Franco Rossi)執導的《青年,青年》(Giovinezza, giovinezza)中,第一次掛名攝影師。同樣在一九六九年,他受雇擔任貝托魯奇執導之《蜘蛛的策略》(The Spider’s Stratagem, 1970)的攝影師,從此展開長期的合作關係,陸續合作了具開創性的《同流者》,以及之後的六部電影:《巴黎最後探戈》、《1900》(1900, 1976)、《迷情逆戀》(La Luna, 1979)、《末代皇帝》、《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1990)和《小活佛》(Little Buddha, 1993)。
史托拉洛也跟其他導演發展出緊密的合作關係,例如跟法蘭西斯.柯波拉合作了影史上的巨作《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1978),以及《舊愛新歡》(One from the Heart, 1982)、《塔克:其人其夢》(Tucker: The Man and His Dream, 1988),以及《大都會傳奇》(New York Stories, 1989)中由柯波拉執導的那段故事。他也跟華倫.比堤合作過三部電影,包括《赤焰烽火萬里情》、《狄克崔西》與《選舉追緝令》(Bulworth, 1998)。
近年來,他和西班牙導演卡洛斯.索拉(Carlos Saura)合作了六部電影,從一九九五的《佛朗明哥》(Flamenco)開始,接著是《計程車》(Taxi, 1996)、《情慾飛舞》(Tango, 1998)、《哥雅的最後歲月》(Goya in Bordeaux, 1999)、《唐喬凡尼》(I, Don Giovanni, 2009),以及《佛朗明哥:傳奇再現》(Flamenco, Flamenco, 2010)。他曾三度贏得奧斯卡獎,得獎作品是《現代啟示錄》、《赤焰烽火萬里情》和《末代皇帝》。
■ INTERVIEW
電影是一種影像的語言,影像始終是透過文字和音樂而成就。
電影是由影像、文字和音樂這「三足」共同撐起的。當別人說我是光影的畫家,我不認同,因為畫家只用單一影像來表達自我,靜照攝影師也是。電影攝影師則必須設計與書寫故事,從開頭就參與其中,一直到電影完成。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的工作是用光影來寫作。電影攝影師需要懂得文學、音樂和繪畫,我不是說你非得成為作家、作曲家、建築師或哲學家,但你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知識,才能更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因為不論是我自己發想或是跟導演討論,當我決定把攝影機架在某個位置,或是用某個特定的方式取景,都是有意義的,我們想向觀眾傳達某種意念。
如果我讓兩個角色並列,一個完全打亮,另一個在陰影中,我其實是在傳達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處於和諧或衝突狀態中。如果你讓演員穿高暖度顏色的服裝,它會散發一股能量,觀眾不光是用他們的雙眼注意到它,而是用他們的渾身上下去感受一種悸動。因此,不用懷疑,如果你會運用光影的字彙,你就能夠用光在膠卷上書寫故事。
坦白說,我剛出道時還沒領悟到這些字彙。我拍的第一部電影是黑白片,當時我主要是意識到光線、陰影,以及濃淡相交處的半影(penumbra),因為那是我當時的字彙。
後來拍攝《同流者》時,我開始構思如何在故事中建立起視覺概念。這個故事第一部分的背景設定在法西斯主義時期,描述主人翁在十二歲時射殺了一個猥褻他的男人,從此感覺自己不再相同。他因為殺人而內疚,卻又隱瞞自己身為同性戀的真實本性,開始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流者。因此,我想到的是:區隔他周遭的光線和陰影,為他營造一種自我衝突的印象。
隨著電影繼續往下走,光和陰影幾乎融合為一了。當男主角去法國時,我把陰影處全部打亮,因為當時對義大利人而言,法國代表自由之地。達文西說過,光線和陰影的結合會創造出色彩,所以我覺得《同流者》中巴黎這一段劇情應該用滿滿的藍色來表現──象徵自由的顏色。
兩年後,我在法國拍攝《巴黎最後探戈》時,迷上了清晨時分那種結合了室內人工照明黃光與冬季大自然冷光的暖色。我採用代表日暮的橘色,暗示馬龍.白蘭度飾演的角色與其人生正步入暮年。當時我已經在用這樣的色彩語言,但其實我還不明白當中的意義,只是覺得應該這樣做。
拍攝《現代啟示錄》時,我能夠用色彩來營造衝突感:一邊是代表越南文化的自然叢林色彩,另一邊是代表美國文化的人工色彩。晚上我會用很強的光線,使它與黃昏時詳和的叢林自然光形成對比,創造出視覺衝突。
等到當我們要拍馬龍.白蘭度的最後幾場戲時,我已經愈來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了。寇茲上校這個角色是一個象徵元素,他在這部片裡不只是一個「人」,也代表從美國文明的無意識中衍生而出的某種真相,跟戰爭的恐怖相關,所以我讓他完全被黑暗包圍。
拍完《現代啟示錄》後,我明白自己必須暫停工作,離開一年去進修,這樣我才能對光和影的運用擁有更有清楚的意識,甚至進一步掌握隱藏在光線中的祕密──然後我發現了色彩的世界。
為了更了解影像中蘊藏的意義,我研究繪畫、文學和建築,也拍了許多靜照。在家鑽研整整一年後,我感覺我準備好了,可以開始將自己的研究成果運用在電影影像的色彩中。《阿嘉莎》是我在那之後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如果你要在這部片裡選出一個代表色,那就是黑色,代表這個女人已陷入危機卻渾然不覺。
事實上,如果要用比喻的方式來形容,我人生旅程的第一章是從黑暗到半影,再到明亮;第二章是從《阿嘉莎》啟程,從黑色到白色,搭配運用整個色譜。
我真正開始使用光譜色的電影是《迷情逆戀》。記得在讀劇本時,我百思不解為何貝納多要把片名取作「La Luna」(月亮),因為這明明是關於一位母親的故事。後來內人告訴我,月亮是母親的象徵,我才明白貝納多是用一種非常象徵性的手法來表達。於是我開始研究佛洛伊德的學說,了解兒童如何用顏色來代表自己眼中所見之父母關係的相關概念。從那時候起,在我看來,色彩就代表了和諧或衝突,而我們每個人都是以很潛意識的方式在看待色彩。於是,從《迷情逆戀》起,我開始運用色彩的象徵意義(symbology of color)。
很幸運的是,我和貝納多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成長的;當他在發掘他自己的表現方式時,我也正經歷同樣的過程。等到拍攝《同流者》時,我們合作起來就很自然了。我知道我必須放手去實現他對攝影的所有感覺和想像,但同時我也在用光和影詮釋他的要的運鏡和構圖,因為它涉及電影的主要概念。
《同流者》中有一場戲是最好的例子:男主角抵達巴黎,去拜訪他過去的老師,而老師跟他說了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貝納多向我解釋,為了了解這個寓言,他得把學生時代的書再拿出來重溫。然後,我發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關掉所有光源,只開一盞燈,來重現這個洞穴的感覺。我們後來恍然大悟,柏拉圖的寓言也是電影的隱喻:囚犯就像觀眾,洞穴外的陽光和火焰就像早期用來放映影像的魔術幻燈(magic lantern),經過洞外時影子投射在洞內牆上的那些人就像電影裡的演員,而洞穴深處那一面牆就像是銀幕。我記得拍攝那場戲時,我們什麼都沒跟對方說,但兩個人都激動不已,因為我們正在一起重現達文西的暗箱研究。
《末代皇帝》的故事是根據溥儀寫的兩本書改編而成。第一次讀那些書時,我很疑惑自己該怎麼呈現這個人的旅程。
這是關於一個孩子的故事。他被遺棄在某種過渡狀態,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再是皇帝了。由於光線代表知識和意識,而光線是由七種顏色組成,於是我想到一個好方法:在他人生的不同階段,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現──這就好比,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程中,而記憶中的某個年紀會讓人聯想到某個特定色彩──遵照牛頓的光譜理論。於是在一開始構思這部電影時,我向貝納多提出這套想法。
我想在人生和光線之間創造一種關連,將不同的色彩比喻為不同的情感。為了讓溥儀可以在自己的記憶中視覺化這段旅程,我在色譜之中展開了一場色彩之旅。所以,當他回憶自己出生在帝王之家,我給他象徵誕生和生命的紅色,也因此我把這場戲設計成夜戲,可以利用火炬來呈現高度的暖色調。第二個顏色是橘色,代表他還住在自己的家裡時,母親和家人環繞他身邊的溫暖。第三個顏色是黃色,代表他當上皇帝時的意識。綠色表示知識,連結教他認識外面的世界的英國家教。這位老師搭著一輛綠色的車子來紫禁城,還送溥儀一台綠色單車等等。
當溥儀終於擺脫紫禁城的禁錮時,我們頭一次看到藍色,那是自由的顏色。當他決定接受日本政府的提議、建立另一個帝國時,他已經不是孩子了,而你會看到靛藍色;這是代表成熟的顏色,是他有機會享受男歡女愛和權力的時刻。最後的顏色是紫蘿蘭色──溥儀在戰犯管理所的審問室裡,體認到自己走過了什麼樣的人生,以及多少人因他的軟弱而死──這是內省的顏色。
當他完成人生教訓,我們用雪景的白色來代表完整,以及旅程的結束。總之,我們在全片使用不同色彩的象徵意義來代表這一整段旅程。
當貝納多接受我的概念,我就把這套色彩配置方案拿給服裝設計詹姆士.艾契森(James Acheson)與美術設計費迪南多.史卡費歐提(Ferdinando Scarfiotti)。詹姆士很驚訝,因為他本來打算在開場戲裡放進各式各樣的顏色。我告訴他不需要用那麼多顏色,只要突顯某些色彩就好。
費迪南多在一開始也有點遲疑,但最後當我們用洋紅、紫蘿蘭和靛藍色調拍完滿洲的皇宮片段時,效果簡直棒極了,一切搭配得天衣無縫。
我人生的第一階段跟貝托魯奇有密切的相連,第二階段是柯波拉,第三階段是華倫.比堤。一九九五年,我認識了卡洛斯.索拉。他提議我們一起拍攝《佛朗明哥》,於是我開始探索西班牙文化和佛朗明哥文化。卡洛斯原本是個攝影師,主要從事黑白攝影。他也拍彩色電影,但還沒意識到色彩的力量。他曾經告訴過我,是我帶領他進入嶄新的色彩世界。
卡洛斯跟貝納多一樣,喜歡親自架攝影機、看觀景窗,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運用空間。我開始把色彩的象徵意義帶入他的影像,他一開始很震驚,後來我發覺根本不必費脣舌向他解釋,而是直接做給他看就好。在彩排一場舞蹈時,他告訴我他想要的運鏡方式,然後我開始打光,甚至沒跟他說我要怎麼做。我們從完全的黑暗開始,搭配我很愛用的燈光控制盤,讓我可以掌握整場戲的光線結構。就在彩排當中,我把我想好的概念直接走一遍給他看,他馬上就愛上了。從那時候起,他開始進入跟我一樣的視野。
在《佛朗明哥》中,我主要使用太陽和月亮的象徵意義。在《情慾飛舞》中,他想藉由探戈呈現自己的人生故事,所以每一支舞都有不同的色彩來代表那段旅程,一步步地走入他自己的潛意識、回到最初,也就是他的孩童時代。在《哥雅的最後歲月》中,我們認為必須用景片的影像來拍這部片,於是跟美術設計達成共識,將室內景的影像印到環繞演員四周的景片上;我們只在他們會坐下的地方放傢俱,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印在壓克力板上的影像。此外,我們從演員的前方或後方用某種色彩來打光,給人一種年代感,營造出角色們生活的時代,或是一種如夢似幻的感覺,因為哥雅是個充滿想像力的不凡畫家──但不光是這樣而已。在卡洛斯編寫的這個故事中,同樣也連結了他的年輕與晚年;有時候,我們會在他年輕和年老時看到相同的影像。我們改變了美術設計的作法,更將古希臘的舞台繪景拆解成一塊塊景片。
我和卡洛斯的合作改變了他的視野,但也同時改變了我的。
@《同流者》THE CONFORMIST, 1970
(圖01)「當我們抵達女演員史蒂芬妮亞.桑德雷利(Stefania Sandrelli)住的公寓時,我心裡想著我要做出區野,將男主角的現實生活和他深埋在內心的那個世界切割開來。
「我想讓光線透過百葉窗射進來,但貝納多說那是白天,應該把百葉窗拉起來才對。我告訴他,百葉窗造成的一條條光束可以在他身上創造出一種視覺上的牢籠,藉此暗示他內心的矛盾。貝納多一聽,馬上愛上這個概念。」
@靈感
(圖01)「我在羅馬的聖王路易堂(San Luigi dei Francese)看到卡拉瓦喬的畫作《聖馬太蒙召喚》(The Calling of St Matthew)時,受到很大的震撼,從此一直把這幅畫的圖像帶在身邊。
「當時我剛拍完我的第一部電影,而這是第一幅讓我下定決心展開由明轉暗(obscurity)這段旅程的畫作。我很納悶,我在學校念攝影和電影攝影念了那麼多年,為什麼他們從沒教過我們繪畫的知識。這幅畫改變了整個視覺藝術史,對電影攝影師而言尤其重要。」
@《赤焰烽火萬里情》REDS, 1981
(圖01-03)史托拉洛為《赤焰烽火萬里情》設計的燈光,是想透過柔和的色調來傳達情感,政治面的事件則以自然主義的方式呈現,全片穿插著寫實無華、跟主人翁約翰.里德(John Reed)和露易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同一時代那些人士的現身說法。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的視覺就像一棵樹。」史托拉洛表示。「樹根代表那些見證者,帶出與里德相關的回憶;樹幹代表里德想成為作家的意志;樹枝和葉子則代表他自由開散的智性和感性,這份感性又進一步連結到情感,於是連結到色彩。因此,當你在《赤焰烽火萬里情》裡看到比較顯著的色彩時,主要是連結到里德與布萊恩特之間的愛情故事。」
@跟華倫.比堤合作
1.跟身兼演員的導演合作遇到的難題
華倫.比堤找來史托拉洛拍攝史詩片《赤焰烽火萬里情》(圖03)。這是華倫.比堤獨立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也是史托拉洛首次跟身兼演員的導演合作。一開始,兩人之間出現不協調的狀況。「我習慣從外部觀點來看一切,也習慣電影製作的語彙。對我來說,攝影機的設定與調整,或是運鏡方式,都跟影像的語言有關。」
2.學習從演員的觀點出發
「但是對他來說,由於他是演員出身,他認為攝影機就該跟著演員移動。剛開拍時,我們會起爭執,因為我想讓他了解攝影機就像是作家的筆一樣。後來我明白他習慣從內部的觀點出發,也就是從角色的觀點,於是我開始去揣摩他的角度,因此也開始理解他,之後我們合作就很順利了。」
@《狄克崔西》
史托拉洛在去舊金山準備柯波拉執導的《塔克:其人其夢》途中,順道跟華倫.比堤碰面討論了《狄克崔西》。他沒看過切斯特.古爾德(Chester Gould)的漫畫,但是在拍攝《塔克:其人其夢》期間,他巧遇一位漫畫收藏家,這個人給他看了幾本古爾德的原作系列。拍完《塔克:其人其夢》後,他回到羅馬,在那些漫畫和德國表現主義畫家奧圖.迪克斯(Otto Dix)的畫作間,發現一種視覺性連結。
「我去書房拿出一本講德國表現主義的書,發覺古爾德受到德國表現主義畫家影響是很合理的事,因為在一九三○年代,不同的藝術形式確實都在互相影響。這些人當中,迪克斯、喬治.葛羅茲(George Grosz)、康拉德.菲力克斯穆勒(Conrad Felixmüller)這些後表現主義藝術家的作品對古爾德影響最大。
「當我去洛衫磯跟華倫.比堤、服裝設計米蕾娜.凱諾尼羅(Milena Canonero),以及美術設計狄恩.塔沃拉里斯(Dean Tavoularis)──他後來因為忙著柯波拉的拍片計畫,改由李察.西爾伯特(Richard Sylbert)接手──開會時,我給他們看那些畫,告訴他們:『我覺得,這部電影應該採納這些畫作的核心概念,一切都必須形成隸屬色譜相對兩端的色彩衝突,於是,有些角色屬於光明、有意識的暖色那一邊,有些角色屬於黑暗的冷色那一邊。狄克的服裝是黃色,代表太陽和天啟的顏色,跟大反派卡普瑞斯的服裝完全相反。甚至,在美術設計和服裝設計的色彩上,我們都應該使用這個色彩規畫。』」
■簡介
維多里歐.史托拉洛於一九四○年出生在羅馬,父親在家鄉的拉克斯電影公司(Lux Film)擔任放映師。十一歲時,在父親的鼓勵下,進入「杜卡德奧斯塔」攝影技術學院(Istituto Tecnico Fotografico “Duca D’Aosta”)就讀,取得名為「攝影師傅」的文憑。十六到十八歲期間,他在義大利電影攝影訓練中心(Italian Cinematographic Training Centre)研習,一九五八年申請獲准進入國立電影學校電影實驗中心(Centro Sperimentale di Cinematagrafia)修習為期兩年的電影攝影課程。二十歲時,他成為電影攝影師亞多.史卡華達(Aldo Scavarda)的助理。二十一歲那年,攝影師馬可.史卡佩利(Marco Scarpelli)讓他晉身義大利最年輕的攝影機操作員。可惜當時義大利電影製作界變得蕭條,耽擱了他的事業生涯,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在貝托魯奇的導演處女作《革命之前》(Before the Revolution, 1964)中擔任攝影助理。
他利用專業生涯早期那一段漫長的空檔研究了各種形式的藝術。一九六九年,他在法朗哥.羅西(Franco Rossi)執導的《青年,青年》(Giovinezza, giovinezza)中,第一次掛名攝影師。同樣在一九六九年,他受雇擔任貝托魯奇執導之《蜘蛛的策略》(The Spider’s Stratagem, 1970)的攝影師,從此展開長期的合作關係,陸續合作了具開創性的《同流者》,以及之後的六部電影:《巴黎最後探戈》、《1900》(1900, 1976)、《迷情逆戀》(La Luna, 1979)、《末代皇帝》、《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1990)和《小活佛》(Little Buddha, 1993)。
史托拉洛也跟其他導演發展出緊密的合作關係,例如跟法蘭西斯.柯波拉合作了影史上的巨作《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1978),以及《舊愛新歡》(One from the Heart, 1982)、《塔克:其人其夢》(Tucker: The Man and His Dream, 1988),以及《大都會傳奇》(New York Stories, 1989)中由柯波拉執導的那段故事。他也跟華倫.比堤合作過三部電影,包括《赤焰烽火萬里情》、《狄克崔西》與《選舉追緝令》(Bulworth, 1998)。
近年來,他和西班牙導演卡洛斯.索拉(Carlos Saura)合作了六部電影,從一九九五的《佛朗明哥》(Flamenco)開始,接著是《計程車》(Taxi, 1996)、《情慾飛舞》(Tango, 1998)、《哥雅的最後歲月》(Goya in Bordeaux, 1999)、《唐喬凡尼》(I, Don Giovanni, 2009),以及《佛朗明哥:傳奇再現》(Flamenco, Flamenco, 2010)。他曾三度贏得奧斯卡獎,得獎作品是《現代啟示錄》、《赤焰烽火萬里情》和《末代皇帝》。
■ INTERVIEW
電影是一種影像的語言,影像始終是透過文字和音樂而成就。
電影是由影像、文字和音樂這「三足」共同撐起的。當別人說我是光影的畫家,我不認同,因為畫家只用單一影像來表達自我,靜照攝影師也是。電影攝影師則必須設計與書寫故事,從開頭就參與其中,一直到電影完成。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的工作是用光影來寫作。電影攝影師需要懂得文學、音樂和繪畫,我不是說你非得成為作家、作曲家、建築師或哲學家,但你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知識,才能更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因為不論是我自己發想或是跟導演討論,當我決定把攝影機架在某個位置,或是用某個特定的方式取景,都是有意義的,我們想向觀眾傳達某種意念。
如果我讓兩個角色並列,一個完全打亮,另一個在陰影中,我其實是在傳達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處於和諧或衝突狀態中。如果你讓演員穿高暖度顏色的服裝,它會散發一股能量,觀眾不光是用他們的雙眼注意到它,而是用他們的渾身上下去感受一種悸動。因此,不用懷疑,如果你會運用光影的字彙,你就能夠用光在膠卷上書寫故事。
坦白說,我剛出道時還沒領悟到這些字彙。我拍的第一部電影是黑白片,當時我主要是意識到光線、陰影,以及濃淡相交處的半影(penumbra),因為那是我當時的字彙。
後來拍攝《同流者》時,我開始構思如何在故事中建立起視覺概念。這個故事第一部分的背景設定在法西斯主義時期,描述主人翁在十二歲時射殺了一個猥褻他的男人,從此感覺自己不再相同。他因為殺人而內疚,卻又隱瞞自己身為同性戀的真實本性,開始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流者。因此,我想到的是:區隔他周遭的光線和陰影,為他營造一種自我衝突的印象。
隨著電影繼續往下走,光和陰影幾乎融合為一了。當男主角去法國時,我把陰影處全部打亮,因為當時對義大利人而言,法國代表自由之地。達文西說過,光線和陰影的結合會創造出色彩,所以我覺得《同流者》中巴黎這一段劇情應該用滿滿的藍色來表現──象徵自由的顏色。
兩年後,我在法國拍攝《巴黎最後探戈》時,迷上了清晨時分那種結合了室內人工照明黃光與冬季大自然冷光的暖色。我採用代表日暮的橘色,暗示馬龍.白蘭度飾演的角色與其人生正步入暮年。當時我已經在用這樣的色彩語言,但其實我還不明白當中的意義,只是覺得應該這樣做。
拍攝《現代啟示錄》時,我能夠用色彩來營造衝突感:一邊是代表越南文化的自然叢林色彩,另一邊是代表美國文化的人工色彩。晚上我會用很強的光線,使它與黃昏時詳和的叢林自然光形成對比,創造出視覺衝突。
等到當我們要拍馬龍.白蘭度的最後幾場戲時,我已經愈來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了。寇茲上校這個角色是一個象徵元素,他在這部片裡不只是一個「人」,也代表從美國文明的無意識中衍生而出的某種真相,跟戰爭的恐怖相關,所以我讓他完全被黑暗包圍。
拍完《現代啟示錄》後,我明白自己必須暫停工作,離開一年去進修,這樣我才能對光和影的運用擁有更有清楚的意識,甚至進一步掌握隱藏在光線中的祕密──然後我發現了色彩的世界。
為了更了解影像中蘊藏的意義,我研究繪畫、文學和建築,也拍了許多靜照。在家鑽研整整一年後,我感覺我準備好了,可以開始將自己的研究成果運用在電影影像的色彩中。《阿嘉莎》是我在那之後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如果你要在這部片裡選出一個代表色,那就是黑色,代表這個女人已陷入危機卻渾然不覺。
事實上,如果要用比喻的方式來形容,我人生旅程的第一章是從黑暗到半影,再到明亮;第二章是從《阿嘉莎》啟程,從黑色到白色,搭配運用整個色譜。
我真正開始使用光譜色的電影是《迷情逆戀》。記得在讀劇本時,我百思不解為何貝納多要把片名取作「La Luna」(月亮),因為這明明是關於一位母親的故事。後來內人告訴我,月亮是母親的象徵,我才明白貝納多是用一種非常象徵性的手法來表達。於是我開始研究佛洛伊德的學說,了解兒童如何用顏色來代表自己眼中所見之父母關係的相關概念。從那時候起,在我看來,色彩就代表了和諧或衝突,而我們每個人都是以很潛意識的方式在看待色彩。於是,從《迷情逆戀》起,我開始運用色彩的象徵意義(symbology of color)。
很幸運的是,我和貝納多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成長的;當他在發掘他自己的表現方式時,我也正經歷同樣的過程。等到拍攝《同流者》時,我們合作起來就很自然了。我知道我必須放手去實現他對攝影的所有感覺和想像,但同時我也在用光和影詮釋他的要的運鏡和構圖,因為它涉及電影的主要概念。
《同流者》中有一場戲是最好的例子:男主角抵達巴黎,去拜訪他過去的老師,而老師跟他說了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貝納多向我解釋,為了了解這個寓言,他得把學生時代的書再拿出來重溫。然後,我發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關掉所有光源,只開一盞燈,來重現這個洞穴的感覺。我們後來恍然大悟,柏拉圖的寓言也是電影的隱喻:囚犯就像觀眾,洞穴外的陽光和火焰就像早期用來放映影像的魔術幻燈(magic lantern),經過洞外時影子投射在洞內牆上的那些人就像電影裡的演員,而洞穴深處那一面牆就像是銀幕。我記得拍攝那場戲時,我們什麼都沒跟對方說,但兩個人都激動不已,因為我們正在一起重現達文西的暗箱研究。
《末代皇帝》的故事是根據溥儀寫的兩本書改編而成。第一次讀那些書時,我很疑惑自己該怎麼呈現這個人的旅程。
這是關於一個孩子的故事。他被遺棄在某種過渡狀態,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再是皇帝了。由於光線代表知識和意識,而光線是由七種顏色組成,於是我想到一個好方法:在他人生的不同階段,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現──這就好比,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程中,而記憶中的某個年紀會讓人聯想到某個特定色彩──遵照牛頓的光譜理論。於是在一開始構思這部電影時,我向貝納多提出這套想法。
我想在人生和光線之間創造一種關連,將不同的色彩比喻為不同的情感。為了讓溥儀可以在自己的記憶中視覺化這段旅程,我在色譜之中展開了一場色彩之旅。所以,當他回憶自己出生在帝王之家,我給他象徵誕生和生命的紅色,也因此我把這場戲設計成夜戲,可以利用火炬來呈現高度的暖色調。第二個顏色是橘色,代表他還住在自己的家裡時,母親和家人環繞他身邊的溫暖。第三個顏色是黃色,代表他當上皇帝時的意識。綠色表示知識,連結教他認識外面的世界的英國家教。這位老師搭著一輛綠色的車子來紫禁城,還送溥儀一台綠色單車等等。
當溥儀終於擺脫紫禁城的禁錮時,我們頭一次看到藍色,那是自由的顏色。當他決定接受日本政府的提議、建立另一個帝國時,他已經不是孩子了,而你會看到靛藍色;這是代表成熟的顏色,是他有機會享受男歡女愛和權力的時刻。最後的顏色是紫蘿蘭色──溥儀在戰犯管理所的審問室裡,體認到自己走過了什麼樣的人生,以及多少人因他的軟弱而死──這是內省的顏色。
當他完成人生教訓,我們用雪景的白色來代表完整,以及旅程的結束。總之,我們在全片使用不同色彩的象徵意義來代表這一整段旅程。
當貝納多接受我的概念,我就把這套色彩配置方案拿給服裝設計詹姆士.艾契森(James Acheson)與美術設計費迪南多.史卡費歐提(Ferdinando Scarfiotti)。詹姆士很驚訝,因為他本來打算在開場戲裡放進各式各樣的顏色。我告訴他不需要用那麼多顏色,只要突顯某些色彩就好。
費迪南多在一開始也有點遲疑,但最後當我們用洋紅、紫蘿蘭和靛藍色調拍完滿洲的皇宮片段時,效果簡直棒極了,一切搭配得天衣無縫。
我人生的第一階段跟貝托魯奇有密切的相連,第二階段是柯波拉,第三階段是華倫.比堤。一九九五年,我認識了卡洛斯.索拉。他提議我們一起拍攝《佛朗明哥》,於是我開始探索西班牙文化和佛朗明哥文化。卡洛斯原本是個攝影師,主要從事黑白攝影。他也拍彩色電影,但還沒意識到色彩的力量。他曾經告訴過我,是我帶領他進入嶄新的色彩世界。
卡洛斯跟貝納多一樣,喜歡親自架攝影機、看觀景窗,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運用空間。我開始把色彩的象徵意義帶入他的影像,他一開始很震驚,後來我發覺根本不必費脣舌向他解釋,而是直接做給他看就好。在彩排一場舞蹈時,他告訴我他想要的運鏡方式,然後我開始打光,甚至沒跟他說我要怎麼做。我們從完全的黑暗開始,搭配我很愛用的燈光控制盤,讓我可以掌握整場戲的光線結構。就在彩排當中,我把我想好的概念直接走一遍給他看,他馬上就愛上了。從那時候起,他開始進入跟我一樣的視野。
在《佛朗明哥》中,我主要使用太陽和月亮的象徵意義。在《情慾飛舞》中,他想藉由探戈呈現自己的人生故事,所以每一支舞都有不同的色彩來代表那段旅程,一步步地走入他自己的潛意識、回到最初,也就是他的孩童時代。在《哥雅的最後歲月》中,我們認為必須用景片的影像來拍這部片,於是跟美術設計達成共識,將室內景的影像印到環繞演員四周的景片上;我們只在他們會坐下的地方放傢俱,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印在壓克力板上的影像。此外,我們從演員的前方或後方用某種色彩來打光,給人一種年代感,營造出角色們生活的時代,或是一種如夢似幻的感覺,因為哥雅是個充滿想像力的不凡畫家──但不光是這樣而已。在卡洛斯編寫的這個故事中,同樣也連結了他的年輕與晚年;有時候,我們會在他年輕和年老時看到相同的影像。我們改變了美術設計的作法,更將古希臘的舞台繪景拆解成一塊塊景片。
我和卡洛斯的合作改變了他的視野,但也同時改變了我的。
@《同流者》THE CONFORMIST, 1970
(圖01)「當我們抵達女演員史蒂芬妮亞.桑德雷利(Stefania Sandrelli)住的公寓時,我心裡想著我要做出區野,將男主角的現實生活和他深埋在內心的那個世界切割開來。
「我想讓光線透過百葉窗射進來,但貝納多說那是白天,應該把百葉窗拉起來才對。我告訴他,百葉窗造成的一條條光束可以在他身上創造出一種視覺上的牢籠,藉此暗示他內心的矛盾。貝納多一聽,馬上愛上這個概念。」
@靈感
(圖01)「我在羅馬的聖王路易堂(San Luigi dei Francese)看到卡拉瓦喬的畫作《聖馬太蒙召喚》(The Calling of St Matthew)時,受到很大的震撼,從此一直把這幅畫的圖像帶在身邊。
「當時我剛拍完我的第一部電影,而這是第一幅讓我下定決心展開由明轉暗(obscurity)這段旅程的畫作。我很納悶,我在學校念攝影和電影攝影念了那麼多年,為什麼他們從沒教過我們繪畫的知識。這幅畫改變了整個視覺藝術史,對電影攝影師而言尤其重要。」
@《赤焰烽火萬里情》REDS, 1981
(圖01-03)史托拉洛為《赤焰烽火萬里情》設計的燈光,是想透過柔和的色調來傳達情感,政治面的事件則以自然主義的方式呈現,全片穿插著寫實無華、跟主人翁約翰.里德(John Reed)和露易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同一時代那些人士的現身說法。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的視覺就像一棵樹。」史托拉洛表示。「樹根代表那些見證者,帶出與里德相關的回憶;樹幹代表里德想成為作家的意志;樹枝和葉子則代表他自由開散的智性和感性,這份感性又進一步連結到情感,於是連結到色彩。因此,當你在《赤焰烽火萬里情》裡看到比較顯著的色彩時,主要是連結到里德與布萊恩特之間的愛情故事。」
@跟華倫.比堤合作
1.跟身兼演員的導演合作遇到的難題
華倫.比堤找來史托拉洛拍攝史詩片《赤焰烽火萬里情》(圖03)。這是華倫.比堤獨立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也是史托拉洛首次跟身兼演員的導演合作。一開始,兩人之間出現不協調的狀況。「我習慣從外部觀點來看一切,也習慣電影製作的語彙。對我來說,攝影機的設定與調整,或是運鏡方式,都跟影像的語言有關。」
2.學習從演員的觀點出發
「但是對他來說,由於他是演員出身,他認為攝影機就該跟著演員移動。剛開拍時,我們會起爭執,因為我想讓他了解攝影機就像是作家的筆一樣。後來我明白他習慣從內部的觀點出發,也就是從角色的觀點,於是我開始去揣摩他的角度,因此也開始理解他,之後我們合作就很順利了。」
@《狄克崔西》
史托拉洛在去舊金山準備柯波拉執導的《塔克:其人其夢》途中,順道跟華倫.比堤碰面討論了《狄克崔西》。他沒看過切斯特.古爾德(Chester Gould)的漫畫,但是在拍攝《塔克:其人其夢》期間,他巧遇一位漫畫收藏家,這個人給他看了幾本古爾德的原作系列。拍完《塔克:其人其夢》後,他回到羅馬,在那些漫畫和德國表現主義畫家奧圖.迪克斯(Otto Dix)的畫作間,發現一種視覺性連結。
「我去書房拿出一本講德國表現主義的書,發覺古爾德受到德國表現主義畫家影響是很合理的事,因為在一九三○年代,不同的藝術形式確實都在互相影響。這些人當中,迪克斯、喬治.葛羅茲(George Grosz)、康拉德.菲力克斯穆勒(Conrad Felixmüller)這些後表現主義藝術家的作品對古爾德影響最大。
「當我去洛衫磯跟華倫.比堤、服裝設計米蕾娜.凱諾尼羅(Milena Canonero),以及美術設計狄恩.塔沃拉里斯(Dean Tavoularis)──他後來因為忙著柯波拉的拍片計畫,改由李察.西爾伯特(Richard Sylbert)接手──開會時,我給他們看那些畫,告訴他們:『我覺得,這部電影應該採納這些畫作的核心概念,一切都必須形成隸屬色譜相對兩端的色彩衝突,於是,有些角色屬於光明、有意識的暖色那一邊,有些角色屬於黑暗的冷色那一邊。狄克的服裝是黃色,代表太陽和天啟的顏色,跟大反派卡普瑞斯的服裝完全相反。甚至,在美術設計和服裝設計的色彩上,我們都應該使用這個色彩規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