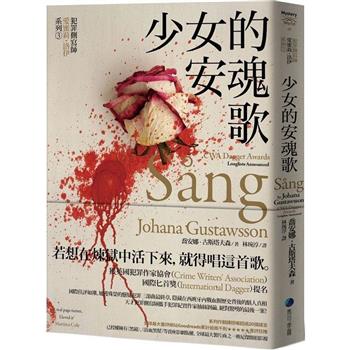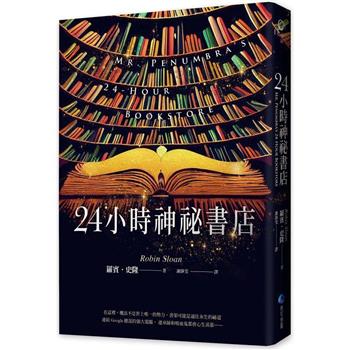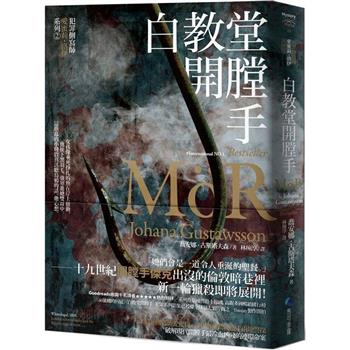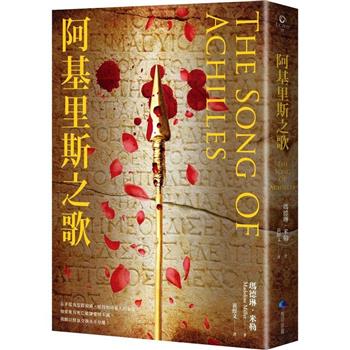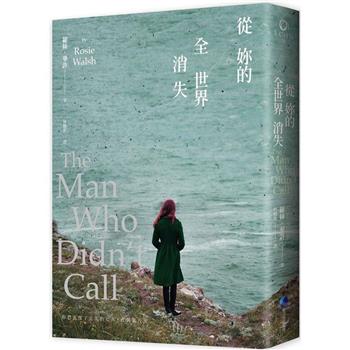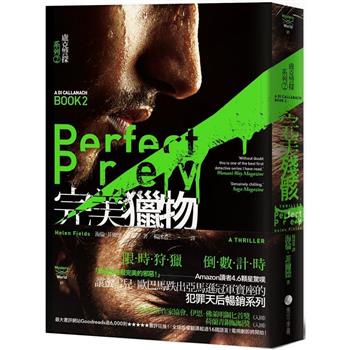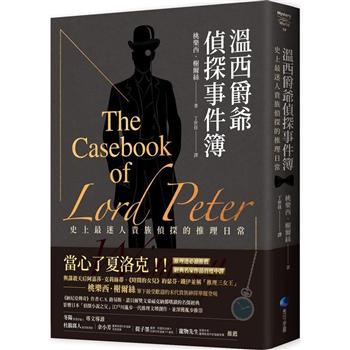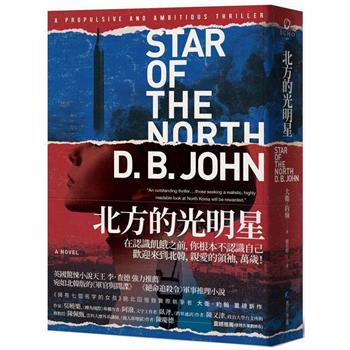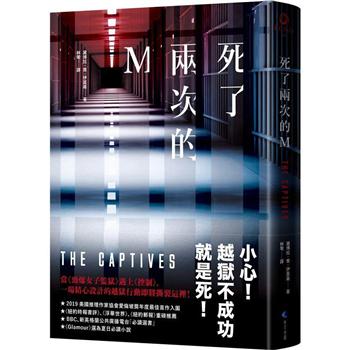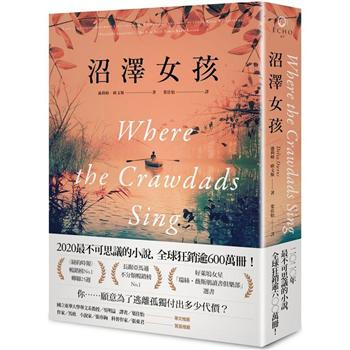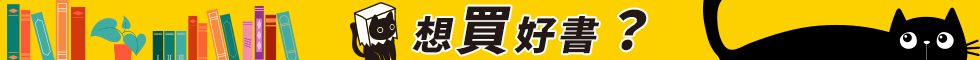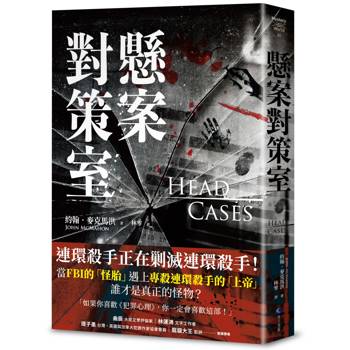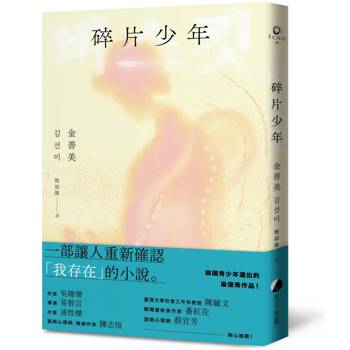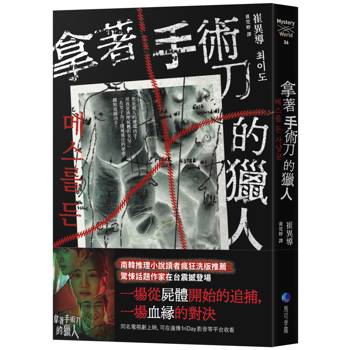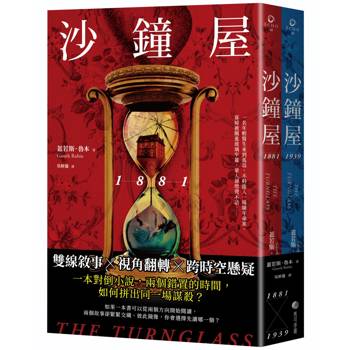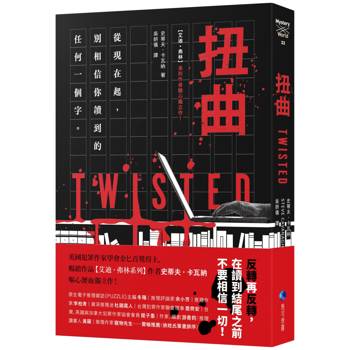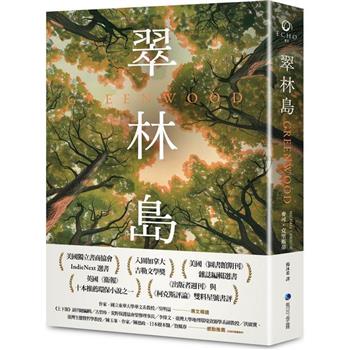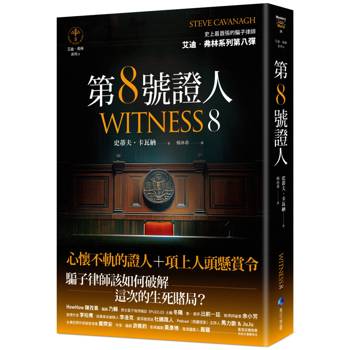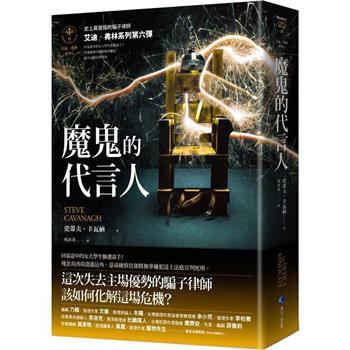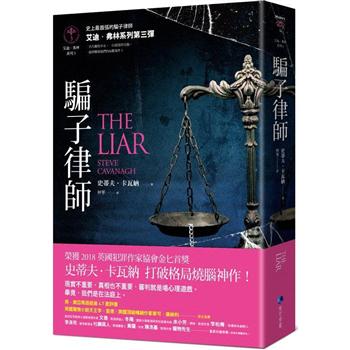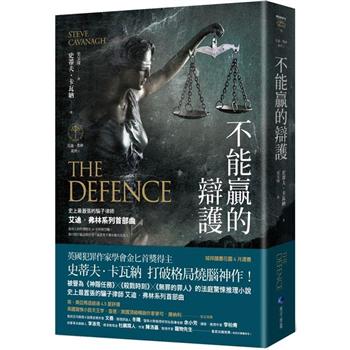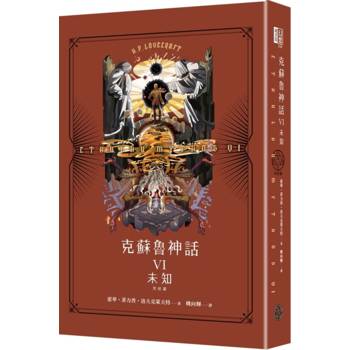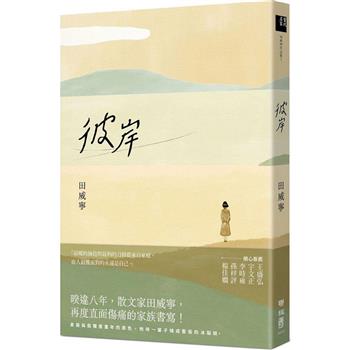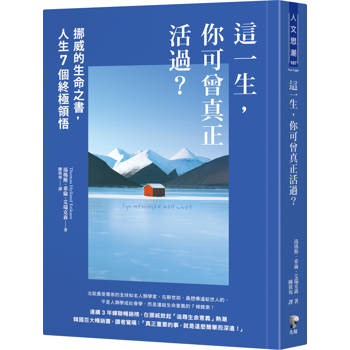02/12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寧視》是「父親之書」,而《彼岸》則是「母親之書」。成長的年月裡,我的家庭始終是離散的,要全家聚在一起,唯有在我的書裡了。
《寧視》出版時,我以為此生也許不會再見到父親,對母親的記憶也將永遠停格在四歲時模糊的畫面,再沒想到我以為完結的故事居然有續篇,還補上前傳。
都說「人生無常」,這四個字是直接刻在我的骨頭上的。
我的文章常被歸類為小說,但我只寫過散文,且對日常生活的質地與人際關係的明暗有著強烈的興趣。我偏愛小津安二郎勝於黑澤明,我偏愛生活中叫不出名字的熟面孔勝於課本裡出現的人名。我知道所有被視為斬釘截鐵的,必定得略去千瘡百孔的襯裡,我也相信最暖的擁抱與最利的刀鋒都來自家庭。而人最難面對的永遠是自己。
我總是在非寫不可的時刻,才將那些放在心裡帶來帶去找不到地方安放的,一股腦地存在文字裡。我的作品沒有華麗的詞藻、精緻的結構或多元的題材,更沒有深邃的哲理思辨與宏偉的社會關懷,有的只是生命中難言的片刻—那些時刻既驚不了天地,亦泣不了鬼神,但都曾觸動我且為我所珍重。
《寧視》收錄的篇章是在剛開始寫作的十年間陸陸續續寫成的,結輯成書後,我驚覺若將父親抽去,那本書將失去所有的意義。我也在那時才正視我不僅沒有母親相伴,居然連記憶都沒有—僅存的一兩個影像都模糊到失真,簡直像經過全身馬賽克與變聲的後製處理。因一個偶然的瞬間有了「萬里尋母」的起心動念,我當下即明白屬於《彼岸》的故事於焉開始。
我的父母皆以不告而別的方式淡出,讓我總覺得故事明明早就結束了,卻缺乏真正的句號。當然在父母離開後日子依舊春去秋來,而季節的遞嬗雖沒有布穀鳥報時,卻依舊晃動了心中始終懸著的擺錘。
我的生命史存在的幾個章節,皆以父親的來去作為分界,而母親的部分曾被我歸類為史前時期—只存在神話與傳說。身為他們的女兒,我沒有必要更沒有機會改變既定的什麼,但我有機會在兩行中間加上另外一行—那恐怕是唯有我才能留下的註記。由我添上的可能出現難堪的、殘破的、多數人藏之唯恐不及的缺口,只是那些遠兜近轉的皆攸關我的人生,我抱著記史的心情,無法迴避,我只求能寫得更接近真實些。
我的父親與母親都是極其平凡的人,有著凡人的追求與執著,也有著凡人的慾望與軟弱,我無法代他們創造力量,也無意將「無私的愛」的聖潔之冠扣在他們頭上—那對他們太沉重,頭會被壓得看不到路。他們是我的父母,但他們理所當然地擁有自己的人生,我從不認為這是矛盾或不應當的。我記下的只是關於他們瑣碎且一再重複的事,是那些事讓我看見舞臺後方的人生的質地。我的父母也是極其勇敢的人,從十幾歲開始,各自在最關鍵的幾個時刻,以一人與全世界對弈,即使曾經一敗塗地,最後也未必全盤皆輸。經歷了人生的起承轉合,他們的性格卻始終如一,而我總認為他們各自活出自己極其精彩而無法被重複的兩輩子。這些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拿自己和父母同齡時的際遇對照,總襯出自己的乏善足述。但我畢竟是他們的女兒,他們的快樂與煩憂、脆弱與堅強理直氣壯地淌在我的血液裡,並將陪我走到人生的盡頭。
父親以自己的步伐行走,走到哪裡,風雨就到哪裡,我在風風雨雨中長途跋涉,走出樹林時,山的那頭和陽光同時出現的彩虹是一路風雨的見證。我將那些與父親共度的時光以文字保存下來,那些片段如碎鑽,在記憶底層閃著光。當我一一收集綴補,卻發現父親早已編織出另一片風景,而那片風景我進不去,也帶不走,僅能遠遠地望著。
我很早就意識到雖為父母子女,但僅能同行一段。人生之路道阻且長,父親總在某個轉彎處消失,而我總是來不及道別。
父親從不說再見。
母親也沒說再見。
母親以自己的步伐行走。因著泥濘不堪的路,踉踉蹌蹌地弄得她走出樹林時鞋也髒了頭髮也亂了;然而,光是看著她的背影,我便清楚意識到她憂煎勞碌的一生絕非徒勞。
我曾認為母親也許是女兒一生最大的資產,或是債務。在女兒的人生字典裡,「母親」二字絕對是以大寫出現。
關於擁抱與被擁抱,我是長大後才習得的能力,至今成績不佳。母親在我未解人事時離開,而我在看過許多無解的母女習題之後,我發現我根本沒出現在應試名單上,也許未必是壞事。沒有與生俱來的財與債,這樣赤手空拳無欠無愧的人生,或許有人願意接手也不一定吧?
都說女兒會從母親身上看到自己未來的模樣,但我根本沒有機會看到題目後面附的參考答案。直到幾年前,我下定決心,無論最後分數如何,我終歸要補修這門關於「人之初」的課。只是,缺乏童年時期無條件的陪伴,我對母親既撒不了嬌,亦撒不了潑,終於比肩而坐,整座太平洋仍在肩膀與肩膀間若隱若現。初次造訪母親的家,我看見母親的護照,一掀開封面我就像被針扎了一下—我一直弄錯母親的名字!從小到大在填寫基本資料卡時,「母親」這欄位從不造成我的困擾,而我當看到母親的名字是「貞」而非「真」的那一刻,我對上命運之神意味深長的眼神。
在全球大疫之前,我已深感命運之不可測,而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連自認最習於變動的我都不時感到「惘惘的威脅」。於是,我開始有意識地想保留一些什麼。我不妄想一手挽住時間的巨輪,但衷心期待留下父親與母親的故事。我的生命、形貌與性格都來自他們,無論到了幾歲,也永遠有著他們的餘震與餘波。近幾年發生許多無法解釋的偶然與巧合,我意識到我人生的下半場於焉開始。於是,我認真地描繪並將那些母女與父女相處的時光定格放大。命運是最有權威的導演,父母是最不會背劇本的演員,記憶是最具創意的剪接師,我則是最入戲的觀眾。黑夜裡那些畫面一幕幕地映在腦海,那些牽動我情緒的片段依舊讓我低迴,讓我出神,甚至令我落淚。
推開記憶深處那扇厚重的鐵門,隨著「吱嘎」聲揚起了漫天的灰塵,陽光終於照進長久曬不到的地方。我在周身溫暖中看到許多珍貴的畫面,心搖神動,於是我寫下來,記下那些可愛又可哀的歲月。
在《寧視》與《彼岸》之間,倏忽已八年。已然步入哀樂中年的我卻仍感到自己時時刻刻被疼愛,諸多美好的人領我走到流著奶與蜜的地方。謝謝姑姑與姊姊永遠無條件的滿滿的愛。謝謝彭自強與陳美桂老師,我的母親在夏威夷,但我在臺北有兩個媽媽,兩個媽媽對我全然的呵護與各種無條件的幫助,我今生無以為報。謝謝寶珠阿姨在夏威夷盡心盡力地幫助我的母親。謝謝鄭秀逸家二十多年來作為我的另一個家。謝謝鄭毓瑜老師與柯裕棻老師成為我的精神導師,我一直一直很努力,只為了能做到老師的千分之一。謝謝我的同事們,我總給大家添麻煩卻總受到各種照顧。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在上班,而是像許多年前一樣,每天開心地來上學。謝謝這些年陪伴我一起成長的少女們,少女們給我的,絕對遠多於她們從我這裡得到的。我每日看見的是最好年齡的澄澈的眼睛與真摯的靈魂,見證以無比認真的神情說著傻話的時刻,分享此生不會再有的悸動。還要謝謝諸多我放在心上,但沒能一一提到的人,我曾收到的溫暖,是不會忘記的。
這本書沒能親手送給尉天驄老師,也沒趕上「愛玲愛玲年」,是我莫大的遺憾,但也正因延宕了這些時日,使我擁有另一些珍貴的緣分。感謝陳逸華與李時雍為此書付出的心力,若沒有時雍的邀約與鼓勵,在夏威夷與母親共處的時光可能不會從一段記憶變成一個專欄,進而成為一本書。感謝董柏廷接手讓此書終於離開母體,安穩地睡在搖籃裡。遇到細心、用心與真心的柏廷,是《彼岸》與我的福氣。最後還要謝謝行銷李邠如,是滿滿專業與母愛的邠如讓《彼岸》能吸引更多艘小船停泊。
父親的日月與母親的歡愁一幕幕投映在夏日光影中,窗外的「知了」「知了」劈頭罩了下來,層層疊疊,有他們走過的路,也有我的人生,我應當是快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