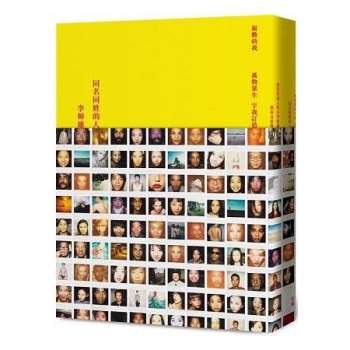我父
我是什麼時候才發現父親其實已不再年輕呢?那天我坐在床上,在新分租的房子裡,時間其實已經不早,我起得晚,不再渾噩的時候正午都過了,但陽光居然還能穿過四周大廈的縫隙照了進來,微塵紛飛,新燙過的窗紗筆直透光,懊悔中竟有一種仍是日初,萬事更新的感覺,彷彿晨光還沒走遠,時間驀地生了寬容,也許我迎頭追趕追趕還來得及開始呢。於是,我便忽然有了努力的衝動,打算好好地利用這剩餘的下午。
然而電話突然響起,鈴聲急促,無先兆地劃破清靜。我拿起一聽,朋友第一句便說剛才想找我,但撥錯了號碼,電話打去了舊居,我父接電話時卻只說我不在,還仔細抄下他的姓名電話,說我回來後會告訴我,好像完全忘了我已經搬出去了似的。我後來回家,不經意向爸提起這事,他揚了揚頭,瞇起眼睛想了想,說:哦,我忘記了,又是當然又是歉意,語氣中竟還有一絲好玩。
父親近年好像沒以前那麼俐落了,好幾次好些簡單的話說到嘴邊也會搞錯,自己卻不自覺。有次我們去飲茶,他興致很好,像我們小時候一樣為我們張羅點心。他隔著兩桌茶客,叫停了推車賣粉果和叉燒包的,問明內容後,高聲說要「粉包」,還轉過來問我和妹妹要多少。賣點心的先是愕然,顯然也有點反應不及,接著便咧嘴笑了出來。我和妹妹都覺得窘,覺得爸爸好像無端被嘲笑,但竟然始終不知道,我們又不忍心說破。後來還是母親開口打發了對方。
然而爸有些事情倒是絕不含糊的。我新搬了地方之後,他堅持要親手為我做幾個書櫃,讓我二十多年來不斷亂買的書可以重見天日,不用再藏身於紙箱之內。他拿了鑰匙,斷斷續續地忙了幾個星期,效率不太高,成果卻一絲不苟:書櫃四個,用寸半厚的木板釘成,櫃邊還做了塑膠的軌道,可以裝上活動的玻璃門。撫著這木櫃,很像握著父親的手,一樣的大而溫厚,堅實而穩重──那是小時候爸爸抓著我的小手,帶我踏著大石階上幼稚園的殘餘的記憶。我好像都以為我忘了,原來還一直記得:天高雲低,陽光朗朗地曬在印有我名字的小小的藍色的塑膠書包上。爸爸走在前面穿著白色長袖襯衫,打著紅領帶,挺著腰,黑髮油亮閃滑,空氣中飛揚著一股爽利的髮乳的氣味,還有清早在路邊叫賣的蒸的白色腸粉的淡淡白米味道。記憶中的父親從來就是這樣的年輕的,似乎也只能是這樣年輕的,就如我在他的心目中也永遠長不大。
以前住一起的時候,他習慣等我們都睡了,半夜會再起來查看我們有沒有鎖好大門。每夜乍醒總看見他坐在廳中,背著神枱燈垂著頭,黑色身影背後是一片紅光,像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全部都坐集一身。那神檯枱的紅燈,退縮在昏暗的一角,清早白天看不見,卻永遠守在那,暗中以血光呼喚黑暗,伺機而行。
搬來這裡之後,下了決心要清理雜物,一時清了幾箱東西,都用大紙箱裝著,準備全部弄完一併丟掉。那夜我很晚才回來,進門看到紙箱上貼著字條,彎腰一看,上面寫著:這箱有待明天拿去丟,因今天太累了。爸──簡單明瞭,不再逞強。我起來的時候失了重心,不意踏了空踩中了紙箱,啪的一聲,彷彿其中有點什麼頹然碎了。
有時我想,中國父子必定是最難相互諒解的。中國男子向來就羞於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心中想的都不好意思直說,成長是一次急促的情感退化。他未嘗不知道男孩最渴望的不是看來遙遠得不知用途的道德訓誨,而是直接單純的關懷,最好是放任得近乎溺愛的自由,然而長大後他便忘記了,又或是慣於抑制了,反過來嚴加管束自己的孩子。然後又過了許多年,他老了,孩童的奢望又復活了,倒又要從他兒子身上找回失落的關切的目光。但兒子呢,可還沒有到老得足夠還童的年紀,仍年輕得不屑兼顧這等婆媽微末之事。
小學作文課,但凡題目叫〈我的爸爸〉的,模範作文的模範父親總是那一類早出晚歸但回家後絕不會身心疲憊反而滿臉笑容耐心指導子女功課還能從不加以打罵兼且和睦鄰里加上言行得人稱羨的。我當時想:父親到底也不過是人呀,然而,為了投其所好,也就倒模仿製了一篇,後來好像還得到了老師在課堂表揚。這事每次想起來就更難過了,覺得親手出賣了父親和自己。
事實上,我印象中總覺得父親對我們過嚴,幼時的歡樂來自他偶爾的寬容。到了不再願意跟父母一起外出的年紀,那時候不怎麼喜歡他在家。我父親中年近視,所以不准我們看電視,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關電視機,於是一下子螢幕上的長劇的悲歡離合便即時灰飛煙滅。我那個時候和哥哥上下鋪睡在客廳,我睡下面。 爸上班前會坐在我的床邊穿襪子。小的時候我會抱他,但中學以後,我會裝睡,默默地不作聲地等他離去。他結婚前晚上去念英文專科學校,英文不成問題,唯獨是他的在工作上有時要面對日本人,每次都不明所以,所以愈發感到外文的重要。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他指定要我去中區的「青年會」學日文,要我每週混在那批三十過外的青年白領之中,呀依烏欸喔,好不尷尬。我一一賭氣陽奉陰違,表面奉行,暗裡反抗。那時我想我還年少,鬥他不過,心裡在等待,等我長大,而我終於長大了,結果中二便要戴眼鏡,讀大學的時候才驚覺日文對研究有莫大的用途,不得已重頭學起。
於是兩代的男人坐在反方向的子彈列車上,彼此重複著對方的路,註定要成為另一個自己,剎那相交,打個照面,想打招呼,但錯過了就錯過了。
我七八歲的時候趴在家中的床上玩槍戰,家裡沒有亮燈,我幻想自己是地球保衛隊唯一生還的隊員,正在獨戰隱形怪獸,目標是怪獸唯一現形的血眼:客廳中的神檯燈。久戰不下,怪獸老是不死,我一時情急,用盡了氣力把塑膠槍丟了過去。燈泡居然沒事,妖魔未除,槍卻從牆壁反彈回地板,碎了一地,壯烈犧牲了。我靠著微弱的紅色燈光小心地把殘骸逐片撿起。頭頂怪獸吊睛紅眼,一搖一擺地眨來眨去,在幸災樂禍。當時我心想,你可別狂傲,我始終是要報復的。
晚上我專心地等爸爸回家,趁他看來還不至於太不愉快的時候拿出盛著槍支碎片的盒子,爸拿在手中一看,我預期他會罵,但更預期著屍體再生。他翻了翻便說:這都修不好了啊。我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爸對我說,乖,別哭,世上有些事,人根本就是無能無力的。我怎樣也不要相信。腦海中的卡通與超人向來都是死而復活的,怎麼早上還完整的好好的神奇死光槍,夜裡就毀了不能復原了呢。
然後是今天,我們一家再次上茶樓。爸坐在窗邊,低著頭要綁鞋帶,陽光正正地曬在我們的脖子上。雖然已經冬至了,但仍有一絲暖意。父親穿上了西裝結了領帶,笑吟吟的,也許是因為星期天,也許是我們兄妹齊集。在父親的意識裡,飲茶應該是占有儀式性的地位的,我大學畢業第一天正式去上班,他要我早點起來,要請我上茶樓。我那天打了領帶,穿了襯衫西褲,扯著領帶跟爸說:好不習慣,這個。
爸說:慢慢就習慣了。生而為我父,我想他總是不快樂的居多,人生付出的是這麼多,回報是那麼的少,而更重要的是年老已漸次自他的腦門把白髮一圈一圈地吃得微禿了。我突然記起老家的浴室,鏡櫃的門一拉開,裡面大半是風溼膏布與小罐的跌打藥酒。看得到的痠痛。他老了,但從沒聽過他問人存在為的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他不說不是他覺得不用說。只是他不知道跟誰說。
他是寂寞的。
自煎
黃昏,他還坐在小巴趕著回家的時候便感到事情的徵兆:喉頭像給什麼卡住了,像蓋住一層薄膜,癢癢的,頭有點熱。他伸手去摸摸鼻孔,手背便沾了光滑的黏液,也黏起早上起床時相同的感覺。原來這徵兆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為什麼當時不察覺,不去做點什麼呢?
他像尾擱淺在陸上的魚,回到家裡把水喝了又喝,卻始終無法溼潤那口腔內最乾涸的地方。那部位確然是小的,然而像土地中一點的沙漠,不用多的,已足以向外擴散,緩緩蠶食其他未變的地方。已不是第一次有這種經驗了,為什麼會忘了呢?
他拿起水杯,想要再喝點水來吞片藥,卻忽然想起他的朋友對他說:有空一同去喝茶啊。他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在這時候記起這一句話,教他往後對他朋友的記憶摻雜了一種藥片的氣息,彷彿附加了一個庸俗的比喻。可是這時他卻真的還能夠感到他的朋友右臂擱在他的背上,嘴巴卻像尾陸上的魚,開開合合,只顧著跟他身旁其他的人說笑話。彷彿不過是今天的事,忽然又像是昨天的,但記得那樣清楚,恐怕又已經說過不止一遍,不是最近的事了。
他們到底有多少次見著面儘在說有空去喝茶呢? 他抬起頭卻只見到滿天的雲,外紅內黑,像冷卻了的炭,無言無語,彷彿碰了一鼻子灰。那次他也只管笑著說:去啊,去啊。朋友說:來啊,來啊,一言為定,笑嘻嘻地答應,任誰也不在意彼此的承諾最終都成了圓不了的謊。來啊來啊,言語間朋友已經和其他人走過去了。
嘴上親切一般無異,但實際上怯生生的,竟然不像老早便認識的人。一撇長長的陰影投了下來,一樣悠長但沒有深度,太陽在他的背後沉了一半,光明西歸,朋友在前頭漸行漸遠,他到頭來踩著的也不過自己的投影。
此刻他手裡的水杯水不揚波,卻沒法映出一個人的完整面容來。他們後來倒真的有喝過茶的,兩杯茶面對面的坐著,銀匙白杯,客客氣氣,各安其位,滿杯的茶彼此都只喝了一半,彷彿滿肚子的話都只露了一半的底。世事難料啊。他以為這是朋友的感慨,但他的友人看著桌上的合約久了,以看著一張人壽保險單的目光看著他,教他幾乎無法相信面前的人就是當年爭喝一瓶酒的人。
有保障比較好。他捧著頭,改了坐姿,移動間腦內沙沙作響,重甸甸的,壓得他喘不過氣。記憶中他們從來不曾有過爭執,根本就沒有問題,不需要做點什麼去阻止,風起沙揚,人情中一點尖刻的石頭便隔出了兩個各自生長的沙丘,流失了親厚的沃土,大地不明不白地龜裂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原。
在未變壞以前,一切彷彿都是好的,病人在發病之前不算是病人,綠洲在被沙漠湮沒前還是綠洲,預兆不是沒有,但都不去理它,心裡想:都還遠著呢,總不會那麼快來到。然而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像由黃昏轉入黑夜,太陽遲遲,過程緩緩,但還是滑過去了,已發生的已無法逆轉,只有無可駁回的一片漆黑。紅日已老,一日已死,永遠無法挽回。
他靜靜地看著那墨黑的夜空,手裡拿著的傷風藥,竟然忘了吃。他只是在想,打從朋友第一次說有空一起喝茶啊他便應該曉得了。正如先前那漫天通紅的晚霞原來是一種警號,怪只怪當初視而不見,教它燒了又煎,空自著急。
我們總是在不對的地方尋找
毫無意外
女廁門口排了長長的人龍
男廁的小便斗卻乏人問津
空張著嘴
愛
張口便像句髒話
忽然之間,右先生
「九二一的時候你在台中嗎?」我問運將大哥。
計程車在開往國美館的路上。
「在呀,怎麼不在。我在醫院,我記得有兩次地震。」
「對,還上下動。」
「嘿呀,第二次,我站在路邊,腳底感到有東西在戳,路面上下在動。」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凌晨兩點零三分,你在哪裡?
你拿起手機,黑暗中沒有電沒有燈沒有訊號,彷彿沒有人類在那一頭。你要打給誰?你在陽台外推的臥房,腳在地板上,卻像是踩在波面之上,你人在手搖杯裡,上下在搖晃,機遇的手舉起又落下,書架快要倒下,書倒下,CD倒下,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也倒下,砰砰砰砰木板閃過某件家具打了下來,有風,氣流颼一聲地掃到你的腳背,書差點砸中你的頭,抽屜被拉開,櫥櫃門被掀開,玻璃杯撞上瓷碗,傾拎哼楞,鍋子沒掛好被拋了出來,摔了一個踉蹌,金屬的回聲在寂靜裡分外清晰地迴盪著,像水波一浪一浪,吊燈在抖,房子還原為真空的框架,你一點一點加進來這個家的東西,被一件一件地扔回去,你是剛從打撈的手那指縫中逃脫的魚,僅以身免,一丁點的顫動都讓你心頭一震,你家剛好在大樓最高的一層,沒有彈力的四面牆被來回拉扯,一搖三晃,最小的容許範圍之內有最大的晃動,你想到腳底下的樓面非常有可能塌下去,你想逃到門外,漆黑中摸索著找到門邊,你多麼慶幸臨睡之前你並沒有如常地關上臥室的門,但搖擺中你無法移動,地球還在嘔吐般前後抽搐,地要往上擠,天要往下壓,木造的門框可能變形斷裂,你的肉身明明白白地告訴你所謂大難臨頭,重點就在臨頭兩個字上。橫梁隨時可以壓頂。多麼地切身。後背發涼。巨變來臨的時候,門是阻礙,牆是陷阱,人身是多麼難得的大目標,每一處都可以受傷。這是餘震,幾秒就是一生一世。
但願這一切沒有發生。
長長的沉默。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凌晨一點四十七分。並不很久。之前。你發現你躺在床上,床板在動,往左右擺,像慣常的台灣地震。你從睡夢裡小塊的黑轉移到張眼後大塊的黑,在完全張眼的瞬間,窗外的街燈分明還亮著,隔了窗戶,窗格子的影子像十字架壓在你的身上,然後,你張開眼,世界在眼前消失。你以為像之前一樣,你翻過身,世界就會平復。但是這次沒有。台灣南北輸電的電纜應聲斷裂。時間如你所願地倒了回去,你趕上了第一次的地震。全黑的世界像無知的心智擴大了一切的感官與恐懼。路上有黑暗,地殼有聲。狗在吠。
接下來是總共一百零二秒的撼動還有歷時很久很久的訊息混亂。之後,你才曉得,這一連兩次的地震會被稱為九二一大地震。規模七.三級。
但願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但南投市武昌宮的柱子折斷,九十度彎腰;魚池鄉日月潭中央的拉魯島面積縮小,月下老人祠崩壞;台中石崗水壩第十六、十七、十八號溢洪閘門斷裂,遠遠看過去像脊椎有三節骨折,水壩潰堤,水是透明的血液;台北東星大樓倒塌,六天後奇蹟地,遭活埋的兄弟在廢墟中被挖出。電力要到了十二天後的十月三日才全面恢復,期間好些地方沒有水,沒有瓦斯。霓虹是菸灰剩餘的紅點,文明被狠狠抖落。震央集集車站的鐵路被嚴重扭曲,這一段路軌後來被移到台中光復國中的校園,那裡的操場被斷層切穿,跑道是剛要捲起就被壓下來的陸地海嘯,永恆凝固了,這地方,兩年後取名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這些,你當時當然都不知道。
如果時間真的可以倒流。
飛散的沙塵可以重新凝聚為磚頭,瓦礫長回水泥牆的身上,梁柱鋼筋不外露,看不到裡面塞的是空的沙拉油罐,跪下的房子重新站起,六樓八樓從一樓的地面爬起來回到原來的位置,被削去頭顱的大樓一棟一棟地依次逐一站好,牆壁顏面都生回來了,龜裂的無縫無垢,土地被撫平,沒有撕裂,骨牌挺回去,救護車警察軍隊倒回去,巨大的崩塌聲響闇啞了,嘶─轟—轟隆─嘩啦—沙—唰—兵砰—豁啷─啪─喔伊—喔伊混合著人們的呼喊聲統統沒入夜晚,復歸於無,年輕的兄弟還在客廳玩大老二撲克牌遊戲,弟弟側耳一聽,還是尋常的半夜,不知哪裡的小嬰兒在哭叫,媽媽低聲地哄著。沒有後來持續很久的惡夢。沒有來不及見的面,沒有等不及的和解,沒有沒說出口的道歉,或愛,沒有生離死別。
但忽然之間,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麼都沒有。歷史沒有如果,命運還是對人丟了石頭。時針停擺,生命像塵埃。二四一五人死,一一三○五人傷,長長的沉默。巨變來臨的時候,你在哪裡,不,他在哪裡?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為什麼我總在非常脆弱的時候,懷念你。那一夜,你存活下來了,歷史定格在某張停擺了的鐘的影像,永遠到不了凌晨兩點,但這一刻,你的時鐘還在走,滴答,滴答,無情地走著,非常響亮。意識回來的時候,你拿起手機,黑暗中沒有電沒有燈沒有訊號。你憑記憶找到室內電話的位置。有訊號,但撥不通。所有的成年人都在打電話嗎?千千萬萬戶迫切地在同一根電話線上擠。你想到了他,卻打給了另外的一個他。到底有沒有所謂對的時間,對的人?還是所有的右先生,右小姐都不過是剛好在你左右可供選擇的先生,或小姐?Right?Now?
(你也會這樣嗎?不只一次想哭嗎?愈努力去解釋,愈被誤解嗎?)
(你真的確定嗎?找到了你的最愛嗎?還是不好意思再拒絕,就說服自己接受他了呢?)
(你真的確定嗎?知道你在做什麼嗎?還是不好意思去承認,就騙騙自己已經很好了?)
台大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的《台灣地區婚姻的變遷與社會衝擊》論文:「一九九八年因該年為虎年且為孤鸞年,初結婚率降至千分之六.六九,然一九九九年隨即提升為千分之七.八七,二○○○年更達到八.一九,這兩年結婚率上升應和千禧龍年有關;之後又下降。」那千分之七.八七和千分之八.一九決定結婚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是因為千禧龍年,多少是因為過了孤鸞年,又有多少是因為那夜裡過不去的一百零二秒?
(你真的知道嗎?真的了解你自己嗎?一直這樣地問,你就會開始動搖嗎?)
(你真的相信嗎?得到了最想要的嗎?還是為了他們的期望,就把那夢想都變小了呢?)
關係可以有很多如果,但現實只有一個結果。放棄是會上癮的。本來要的沒有通,不確切的虛線卻接通了。機會的斷層,葬身著某個名字,你錯過了自己了嗎?
「九二一的時候你在台中嗎?」
時間快速蒸發乾涸,像很喜歡魚池鄉的席德進逝世也快三十三年了。我把別篇文章的開頭移到這一篇。那是二○一一年,那時候我要去看席德進逝世三十年畫展。生命有時,唯有文字的敘述可以無限地開始。
距離九二一快十五個年頭了,然後將會是第十六個夏天第十七個。
九二一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你,現在可能又變回不認識,或是無從認識。
不思量,自難忘。七種靜脈
頸靜脈。Jugular vein。阿婷走出天后地鐵站,抬頭就看見自己在天后廟道與英皇道交界的家。快要午夜的時分,四周有一絲罕見的寧靜,頭頂一個銀白的月亮,沉靜中奇異的光華,壓在自己住的唐樓。左邊一座新蓋的高樓拔地而起,那麼的細長,像陽光不足的瘦弱植物,也益發顯得她的房子矮了一截。她看得脖子也酸了,細細的空置窗戶好像枝莖的纖維毛細管,無人的夜裡靜靜地吸啜著一點什麼。十二月上旬樓宇買賣登記減少五成三。嘉湖山莊成交量跌七成。馬鞍山新樓盤跌百分之八。將軍澳回落百分之三。樓價跌了但樓宇依然屹立高企,像遙不可及的紀念碑。阿婷並不覺得她的生活有什麼改善之處。十五年唐樓供二十年。這就是她引頸以待的生活麼?
肺靜脈。一下子雞雀不分同屬形跡可疑,香港成為了禽流感蔓延下的無掩雞籠,人人自危。威爾斯醫院的護士指責院方沒有隔離要用呼吸機呼吸的女童病人,遇人殺人,遇佛殺佛。禽傳人,不吃雞肉。人傳人,不握手,不擁抱。基絲汀赫然回想有多久沒有擁抱李察了。甚至連碰觸也沒有。
前腔靜脈/後腔靜脈。在香港,阿明困在貨車內卡在早上過海的車龍之中,從老遠望過去,通往銅鑼灣隧道入口的天橋前後包抄,連接城市的上下半身。海港的運輸大動脈凝滯一如瘀血,動彈不得。藍色的集體挫敗感。在台北,要轉往國父紀念館的市民大道上,小馬打開塞在車陣中的車門吐吐悶氣,嘩的一聲吐了一口檳榔汁,落地如血。
渦靜脈。旺角清晨的大廈外面堆滿一袋又一袋黑色塑膠袋的垃圾,像鼓脹的眼球,無辜的。Venacomes。伴隨著動脈的靜脈。光與暗共生。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
第七種靜
脈。Jugular vein,其實並不是頸靜脈。Jugular就是致命弱點的意思。
我是什麼時候才發現父親其實已不再年輕呢?那天我坐在床上,在新分租的房子裡,時間其實已經不早,我起得晚,不再渾噩的時候正午都過了,但陽光居然還能穿過四周大廈的縫隙照了進來,微塵紛飛,新燙過的窗紗筆直透光,懊悔中竟有一種仍是日初,萬事更新的感覺,彷彿晨光還沒走遠,時間驀地生了寬容,也許我迎頭追趕追趕還來得及開始呢。於是,我便忽然有了努力的衝動,打算好好地利用這剩餘的下午。
然而電話突然響起,鈴聲急促,無先兆地劃破清靜。我拿起一聽,朋友第一句便說剛才想找我,但撥錯了號碼,電話打去了舊居,我父接電話時卻只說我不在,還仔細抄下他的姓名電話,說我回來後會告訴我,好像完全忘了我已經搬出去了似的。我後來回家,不經意向爸提起這事,他揚了揚頭,瞇起眼睛想了想,說:哦,我忘記了,又是當然又是歉意,語氣中竟還有一絲好玩。
父親近年好像沒以前那麼俐落了,好幾次好些簡單的話說到嘴邊也會搞錯,自己卻不自覺。有次我們去飲茶,他興致很好,像我們小時候一樣為我們張羅點心。他隔著兩桌茶客,叫停了推車賣粉果和叉燒包的,問明內容後,高聲說要「粉包」,還轉過來問我和妹妹要多少。賣點心的先是愕然,顯然也有點反應不及,接著便咧嘴笑了出來。我和妹妹都覺得窘,覺得爸爸好像無端被嘲笑,但竟然始終不知道,我們又不忍心說破。後來還是母親開口打發了對方。
然而爸有些事情倒是絕不含糊的。我新搬了地方之後,他堅持要親手為我做幾個書櫃,讓我二十多年來不斷亂買的書可以重見天日,不用再藏身於紙箱之內。他拿了鑰匙,斷斷續續地忙了幾個星期,效率不太高,成果卻一絲不苟:書櫃四個,用寸半厚的木板釘成,櫃邊還做了塑膠的軌道,可以裝上活動的玻璃門。撫著這木櫃,很像握著父親的手,一樣的大而溫厚,堅實而穩重──那是小時候爸爸抓著我的小手,帶我踏著大石階上幼稚園的殘餘的記憶。我好像都以為我忘了,原來還一直記得:天高雲低,陽光朗朗地曬在印有我名字的小小的藍色的塑膠書包上。爸爸走在前面穿著白色長袖襯衫,打著紅領帶,挺著腰,黑髮油亮閃滑,空氣中飛揚著一股爽利的髮乳的氣味,還有清早在路邊叫賣的蒸的白色腸粉的淡淡白米味道。記憶中的父親從來就是這樣的年輕的,似乎也只能是這樣年輕的,就如我在他的心目中也永遠長不大。
以前住一起的時候,他習慣等我們都睡了,半夜會再起來查看我們有沒有鎖好大門。每夜乍醒總看見他坐在廳中,背著神枱燈垂著頭,黑色身影背後是一片紅光,像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全部都坐集一身。那神檯枱的紅燈,退縮在昏暗的一角,清早白天看不見,卻永遠守在那,暗中以血光呼喚黑暗,伺機而行。
搬來這裡之後,下了決心要清理雜物,一時清了幾箱東西,都用大紙箱裝著,準備全部弄完一併丟掉。那夜我很晚才回來,進門看到紙箱上貼著字條,彎腰一看,上面寫著:這箱有待明天拿去丟,因今天太累了。爸──簡單明瞭,不再逞強。我起來的時候失了重心,不意踏了空踩中了紙箱,啪的一聲,彷彿其中有點什麼頹然碎了。
有時我想,中國父子必定是最難相互諒解的。中國男子向來就羞於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心中想的都不好意思直說,成長是一次急促的情感退化。他未嘗不知道男孩最渴望的不是看來遙遠得不知用途的道德訓誨,而是直接單純的關懷,最好是放任得近乎溺愛的自由,然而長大後他便忘記了,又或是慣於抑制了,反過來嚴加管束自己的孩子。然後又過了許多年,他老了,孩童的奢望又復活了,倒又要從他兒子身上找回失落的關切的目光。但兒子呢,可還沒有到老得足夠還童的年紀,仍年輕得不屑兼顧這等婆媽微末之事。
小學作文課,但凡題目叫〈我的爸爸〉的,模範作文的模範父親總是那一類早出晚歸但回家後絕不會身心疲憊反而滿臉笑容耐心指導子女功課還能從不加以打罵兼且和睦鄰里加上言行得人稱羨的。我當時想:父親到底也不過是人呀,然而,為了投其所好,也就倒模仿製了一篇,後來好像還得到了老師在課堂表揚。這事每次想起來就更難過了,覺得親手出賣了父親和自己。
事實上,我印象中總覺得父親對我們過嚴,幼時的歡樂來自他偶爾的寬容。到了不再願意跟父母一起外出的年紀,那時候不怎麼喜歡他在家。我父親中年近視,所以不准我們看電視,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關電視機,於是一下子螢幕上的長劇的悲歡離合便即時灰飛煙滅。我那個時候和哥哥上下鋪睡在客廳,我睡下面。 爸上班前會坐在我的床邊穿襪子。小的時候我會抱他,但中學以後,我會裝睡,默默地不作聲地等他離去。他結婚前晚上去念英文專科學校,英文不成問題,唯獨是他的在工作上有時要面對日本人,每次都不明所以,所以愈發感到外文的重要。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他指定要我去中區的「青年會」學日文,要我每週混在那批三十過外的青年白領之中,呀依烏欸喔,好不尷尬。我一一賭氣陽奉陰違,表面奉行,暗裡反抗。那時我想我還年少,鬥他不過,心裡在等待,等我長大,而我終於長大了,結果中二便要戴眼鏡,讀大學的時候才驚覺日文對研究有莫大的用途,不得已重頭學起。
於是兩代的男人坐在反方向的子彈列車上,彼此重複著對方的路,註定要成為另一個自己,剎那相交,打個照面,想打招呼,但錯過了就錯過了。
我七八歲的時候趴在家中的床上玩槍戰,家裡沒有亮燈,我幻想自己是地球保衛隊唯一生還的隊員,正在獨戰隱形怪獸,目標是怪獸唯一現形的血眼:客廳中的神檯燈。久戰不下,怪獸老是不死,我一時情急,用盡了氣力把塑膠槍丟了過去。燈泡居然沒事,妖魔未除,槍卻從牆壁反彈回地板,碎了一地,壯烈犧牲了。我靠著微弱的紅色燈光小心地把殘骸逐片撿起。頭頂怪獸吊睛紅眼,一搖一擺地眨來眨去,在幸災樂禍。當時我心想,你可別狂傲,我始終是要報復的。
晚上我專心地等爸爸回家,趁他看來還不至於太不愉快的時候拿出盛著槍支碎片的盒子,爸拿在手中一看,我預期他會罵,但更預期著屍體再生。他翻了翻便說:這都修不好了啊。我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爸對我說,乖,別哭,世上有些事,人根本就是無能無力的。我怎樣也不要相信。腦海中的卡通與超人向來都是死而復活的,怎麼早上還完整的好好的神奇死光槍,夜裡就毀了不能復原了呢。
然後是今天,我們一家再次上茶樓。爸坐在窗邊,低著頭要綁鞋帶,陽光正正地曬在我們的脖子上。雖然已經冬至了,但仍有一絲暖意。父親穿上了西裝結了領帶,笑吟吟的,也許是因為星期天,也許是我們兄妹齊集。在父親的意識裡,飲茶應該是占有儀式性的地位的,我大學畢業第一天正式去上班,他要我早點起來,要請我上茶樓。我那天打了領帶,穿了襯衫西褲,扯著領帶跟爸說:好不習慣,這個。
爸說:慢慢就習慣了。生而為我父,我想他總是不快樂的居多,人生付出的是這麼多,回報是那麼的少,而更重要的是年老已漸次自他的腦門把白髮一圈一圈地吃得微禿了。我突然記起老家的浴室,鏡櫃的門一拉開,裡面大半是風溼膏布與小罐的跌打藥酒。看得到的痠痛。他老了,但從沒聽過他問人存在為的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他不說不是他覺得不用說。只是他不知道跟誰說。
他是寂寞的。
自煎
黃昏,他還坐在小巴趕著回家的時候便感到事情的徵兆:喉頭像給什麼卡住了,像蓋住一層薄膜,癢癢的,頭有點熱。他伸手去摸摸鼻孔,手背便沾了光滑的黏液,也黏起早上起床時相同的感覺。原來這徵兆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為什麼當時不察覺,不去做點什麼呢?
他像尾擱淺在陸上的魚,回到家裡把水喝了又喝,卻始終無法溼潤那口腔內最乾涸的地方。那部位確然是小的,然而像土地中一點的沙漠,不用多的,已足以向外擴散,緩緩蠶食其他未變的地方。已不是第一次有這種經驗了,為什麼會忘了呢?
他拿起水杯,想要再喝點水來吞片藥,卻忽然想起他的朋友對他說:有空一同去喝茶啊。他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在這時候記起這一句話,教他往後對他朋友的記憶摻雜了一種藥片的氣息,彷彿附加了一個庸俗的比喻。可是這時他卻真的還能夠感到他的朋友右臂擱在他的背上,嘴巴卻像尾陸上的魚,開開合合,只顧著跟他身旁其他的人說笑話。彷彿不過是今天的事,忽然又像是昨天的,但記得那樣清楚,恐怕又已經說過不止一遍,不是最近的事了。
他們到底有多少次見著面儘在說有空去喝茶呢? 他抬起頭卻只見到滿天的雲,外紅內黑,像冷卻了的炭,無言無語,彷彿碰了一鼻子灰。那次他也只管笑著說:去啊,去啊。朋友說:來啊,來啊,一言為定,笑嘻嘻地答應,任誰也不在意彼此的承諾最終都成了圓不了的謊。來啊來啊,言語間朋友已經和其他人走過去了。
嘴上親切一般無異,但實際上怯生生的,竟然不像老早便認識的人。一撇長長的陰影投了下來,一樣悠長但沒有深度,太陽在他的背後沉了一半,光明西歸,朋友在前頭漸行漸遠,他到頭來踩著的也不過自己的投影。
此刻他手裡的水杯水不揚波,卻沒法映出一個人的完整面容來。他們後來倒真的有喝過茶的,兩杯茶面對面的坐著,銀匙白杯,客客氣氣,各安其位,滿杯的茶彼此都只喝了一半,彷彿滿肚子的話都只露了一半的底。世事難料啊。他以為這是朋友的感慨,但他的友人看著桌上的合約久了,以看著一張人壽保險單的目光看著他,教他幾乎無法相信面前的人就是當年爭喝一瓶酒的人。
有保障比較好。他捧著頭,改了坐姿,移動間腦內沙沙作響,重甸甸的,壓得他喘不過氣。記憶中他們從來不曾有過爭執,根本就沒有問題,不需要做點什麼去阻止,風起沙揚,人情中一點尖刻的石頭便隔出了兩個各自生長的沙丘,流失了親厚的沃土,大地不明不白地龜裂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原。
在未變壞以前,一切彷彿都是好的,病人在發病之前不算是病人,綠洲在被沙漠湮沒前還是綠洲,預兆不是沒有,但都不去理它,心裡想:都還遠著呢,總不會那麼快來到。然而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像由黃昏轉入黑夜,太陽遲遲,過程緩緩,但還是滑過去了,已發生的已無法逆轉,只有無可駁回的一片漆黑。紅日已老,一日已死,永遠無法挽回。
他靜靜地看著那墨黑的夜空,手裡拿著的傷風藥,竟然忘了吃。他只是在想,打從朋友第一次說有空一起喝茶啊他便應該曉得了。正如先前那漫天通紅的晚霞原來是一種警號,怪只怪當初視而不見,教它燒了又煎,空自著急。
我們總是在不對的地方尋找
毫無意外
女廁門口排了長長的人龍
男廁的小便斗卻乏人問津
空張著嘴
愛
張口便像句髒話
忽然之間,右先生
「九二一的時候你在台中嗎?」我問運將大哥。
計程車在開往國美館的路上。
「在呀,怎麼不在。我在醫院,我記得有兩次地震。」
「對,還上下動。」
「嘿呀,第二次,我站在路邊,腳底感到有東西在戳,路面上下在動。」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凌晨兩點零三分,你在哪裡?
你拿起手機,黑暗中沒有電沒有燈沒有訊號,彷彿沒有人類在那一頭。你要打給誰?你在陽台外推的臥房,腳在地板上,卻像是踩在波面之上,你人在手搖杯裡,上下在搖晃,機遇的手舉起又落下,書架快要倒下,書倒下,CD倒下,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也倒下,砰砰砰砰木板閃過某件家具打了下來,有風,氣流颼一聲地掃到你的腳背,書差點砸中你的頭,抽屜被拉開,櫥櫃門被掀開,玻璃杯撞上瓷碗,傾拎哼楞,鍋子沒掛好被拋了出來,摔了一個踉蹌,金屬的回聲在寂靜裡分外清晰地迴盪著,像水波一浪一浪,吊燈在抖,房子還原為真空的框架,你一點一點加進來這個家的東西,被一件一件地扔回去,你是剛從打撈的手那指縫中逃脫的魚,僅以身免,一丁點的顫動都讓你心頭一震,你家剛好在大樓最高的一層,沒有彈力的四面牆被來回拉扯,一搖三晃,最小的容許範圍之內有最大的晃動,你想到腳底下的樓面非常有可能塌下去,你想逃到門外,漆黑中摸索著找到門邊,你多麼慶幸臨睡之前你並沒有如常地關上臥室的門,但搖擺中你無法移動,地球還在嘔吐般前後抽搐,地要往上擠,天要往下壓,木造的門框可能變形斷裂,你的肉身明明白白地告訴你所謂大難臨頭,重點就在臨頭兩個字上。橫梁隨時可以壓頂。多麼地切身。後背發涼。巨變來臨的時候,門是阻礙,牆是陷阱,人身是多麼難得的大目標,每一處都可以受傷。這是餘震,幾秒就是一生一世。
但願這一切沒有發生。
長長的沉默。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凌晨一點四十七分。並不很久。之前。你發現你躺在床上,床板在動,往左右擺,像慣常的台灣地震。你從睡夢裡小塊的黑轉移到張眼後大塊的黑,在完全張眼的瞬間,窗外的街燈分明還亮著,隔了窗戶,窗格子的影子像十字架壓在你的身上,然後,你張開眼,世界在眼前消失。你以為像之前一樣,你翻過身,世界就會平復。但是這次沒有。台灣南北輸電的電纜應聲斷裂。時間如你所願地倒了回去,你趕上了第一次的地震。全黑的世界像無知的心智擴大了一切的感官與恐懼。路上有黑暗,地殼有聲。狗在吠。
接下來是總共一百零二秒的撼動還有歷時很久很久的訊息混亂。之後,你才曉得,這一連兩次的地震會被稱為九二一大地震。規模七.三級。
但願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但南投市武昌宮的柱子折斷,九十度彎腰;魚池鄉日月潭中央的拉魯島面積縮小,月下老人祠崩壞;台中石崗水壩第十六、十七、十八號溢洪閘門斷裂,遠遠看過去像脊椎有三節骨折,水壩潰堤,水是透明的血液;台北東星大樓倒塌,六天後奇蹟地,遭活埋的兄弟在廢墟中被挖出。電力要到了十二天後的十月三日才全面恢復,期間好些地方沒有水,沒有瓦斯。霓虹是菸灰剩餘的紅點,文明被狠狠抖落。震央集集車站的鐵路被嚴重扭曲,這一段路軌後來被移到台中光復國中的校園,那裡的操場被斷層切穿,跑道是剛要捲起就被壓下來的陸地海嘯,永恆凝固了,這地方,兩年後取名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這些,你當時當然都不知道。
如果時間真的可以倒流。
飛散的沙塵可以重新凝聚為磚頭,瓦礫長回水泥牆的身上,梁柱鋼筋不外露,看不到裡面塞的是空的沙拉油罐,跪下的房子重新站起,六樓八樓從一樓的地面爬起來回到原來的位置,被削去頭顱的大樓一棟一棟地依次逐一站好,牆壁顏面都生回來了,龜裂的無縫無垢,土地被撫平,沒有撕裂,骨牌挺回去,救護車警察軍隊倒回去,巨大的崩塌聲響闇啞了,嘶─轟—轟隆─嘩啦—沙—唰—兵砰—豁啷─啪─喔伊—喔伊混合著人們的呼喊聲統統沒入夜晚,復歸於無,年輕的兄弟還在客廳玩大老二撲克牌遊戲,弟弟側耳一聽,還是尋常的半夜,不知哪裡的小嬰兒在哭叫,媽媽低聲地哄著。沒有後來持續很久的惡夢。沒有來不及見的面,沒有等不及的和解,沒有沒說出口的道歉,或愛,沒有生離死別。
但忽然之間,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麼都沒有。歷史沒有如果,命運還是對人丟了石頭。時針停擺,生命像塵埃。二四一五人死,一一三○五人傷,長長的沉默。巨變來臨的時候,你在哪裡,不,他在哪裡?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為什麼我總在非常脆弱的時候,懷念你。那一夜,你存活下來了,歷史定格在某張停擺了的鐘的影像,永遠到不了凌晨兩點,但這一刻,你的時鐘還在走,滴答,滴答,無情地走著,非常響亮。意識回來的時候,你拿起手機,黑暗中沒有電沒有燈沒有訊號。你憑記憶找到室內電話的位置。有訊號,但撥不通。所有的成年人都在打電話嗎?千千萬萬戶迫切地在同一根電話線上擠。你想到了他,卻打給了另外的一個他。到底有沒有所謂對的時間,對的人?還是所有的右先生,右小姐都不過是剛好在你左右可供選擇的先生,或小姐?Right?Now?
(你也會這樣嗎?不只一次想哭嗎?愈努力去解釋,愈被誤解嗎?)
(你真的確定嗎?找到了你的最愛嗎?還是不好意思再拒絕,就說服自己接受他了呢?)
(你真的確定嗎?知道你在做什麼嗎?還是不好意思去承認,就騙騙自己已經很好了?)
台大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的《台灣地區婚姻的變遷與社會衝擊》論文:「一九九八年因該年為虎年且為孤鸞年,初結婚率降至千分之六.六九,然一九九九年隨即提升為千分之七.八七,二○○○年更達到八.一九,這兩年結婚率上升應和千禧龍年有關;之後又下降。」那千分之七.八七和千分之八.一九決定結婚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是因為千禧龍年,多少是因為過了孤鸞年,又有多少是因為那夜裡過不去的一百零二秒?
(你真的知道嗎?真的了解你自己嗎?一直這樣地問,你就會開始動搖嗎?)
(你真的相信嗎?得到了最想要的嗎?還是為了他們的期望,就把那夢想都變小了呢?)
關係可以有很多如果,但現實只有一個結果。放棄是會上癮的。本來要的沒有通,不確切的虛線卻接通了。機會的斷層,葬身著某個名字,你錯過了自己了嗎?
「九二一的時候你在台中嗎?」
時間快速蒸發乾涸,像很喜歡魚池鄉的席德進逝世也快三十三年了。我把別篇文章的開頭移到這一篇。那是二○一一年,那時候我要去看席德進逝世三十年畫展。生命有時,唯有文字的敘述可以無限地開始。
距離九二一快十五個年頭了,然後將會是第十六個夏天第十七個。
九二一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你,現在可能又變回不認識,或是無從認識。
不思量,自難忘。七種靜脈
頸靜脈。Jugular vein。阿婷走出天后地鐵站,抬頭就看見自己在天后廟道與英皇道交界的家。快要午夜的時分,四周有一絲罕見的寧靜,頭頂一個銀白的月亮,沉靜中奇異的光華,壓在自己住的唐樓。左邊一座新蓋的高樓拔地而起,那麼的細長,像陽光不足的瘦弱植物,也益發顯得她的房子矮了一截。她看得脖子也酸了,細細的空置窗戶好像枝莖的纖維毛細管,無人的夜裡靜靜地吸啜著一點什麼。十二月上旬樓宇買賣登記減少五成三。嘉湖山莊成交量跌七成。馬鞍山新樓盤跌百分之八。將軍澳回落百分之三。樓價跌了但樓宇依然屹立高企,像遙不可及的紀念碑。阿婷並不覺得她的生活有什麼改善之處。十五年唐樓供二十年。這就是她引頸以待的生活麼?
肺靜脈。一下子雞雀不分同屬形跡可疑,香港成為了禽流感蔓延下的無掩雞籠,人人自危。威爾斯醫院的護士指責院方沒有隔離要用呼吸機呼吸的女童病人,遇人殺人,遇佛殺佛。禽傳人,不吃雞肉。人傳人,不握手,不擁抱。基絲汀赫然回想有多久沒有擁抱李察了。甚至連碰觸也沒有。
前腔靜脈/後腔靜脈。在香港,阿明困在貨車內卡在早上過海的車龍之中,從老遠望過去,通往銅鑼灣隧道入口的天橋前後包抄,連接城市的上下半身。海港的運輸大動脈凝滯一如瘀血,動彈不得。藍色的集體挫敗感。在台北,要轉往國父紀念館的市民大道上,小馬打開塞在車陣中的車門吐吐悶氣,嘩的一聲吐了一口檳榔汁,落地如血。
渦靜脈。旺角清晨的大廈外面堆滿一袋又一袋黑色塑膠袋的垃圾,像鼓脹的眼球,無辜的。Venacomes。伴隨著動脈的靜脈。光與暗共生。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
第七種靜
脈。Jugular vein,其實並不是頸靜脈。Jugular就是致命弱點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