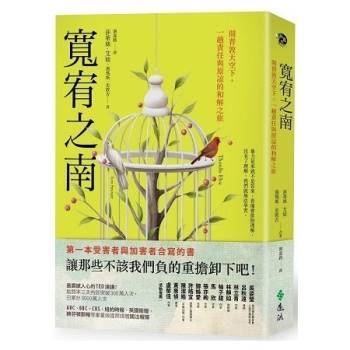第四天 2013年3月30日 (節錄)
等到再度回到忙碌的街道上,整個世界看起來不一樣了。如今我的心胸更為開闊,也發覺風在樹梢吟唱得更響亮,陽光曬在皮膚上的感覺更溫暖。就連胃也感覺不一樣,突然飢腸轆轆起來。有鑑於剛對莫札特咖啡館產生的好感,我建議到那裡吃東西,湯姆也同意。
我們已經坐在咖啡館二樓,由一位滿面笑容的女服務生接待。她推薦我們點裸麥麵包加烤蔬菜和山羊乳酪,我聽從她的建議。
「關於那掛在教堂外的布條,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當女服務生消失在通往廚房的樓梯時,湯姆出聲說話了。
「還有那音樂……」
「……真是動人!」他由衷做出結論。
我再度意識到,我們又選在周遭都是人的環境裡,進行著私密的對話。
我湊近桌子,降低音量:「從絕口不提這話題到不管何時何地都在談這話題,這感覺很怪。」我們先前關於憤怒的對話此時也在心裡閃過,因此我再加了一句:「即便是在雙層巴士多風的車頂上也一樣。」
「沒錯,不過反正那裡也沒人能聽到我們在說什麼。每一個人都戴著耳機。現在想來,那裡反而是進行私密對話最完美的地點。」
「是沒錯,但有些事情我還是不會在那裡說出來。尤其不會在風勢強勁,必須大聲吼叫才能讓你聽見我說話的情況下。」我給他一個心照不宣的表情。
「我想不出你有什麼事情不能說的。」
他的不明所以使我啞口無言。有一會時間,我能做的就是看著他,然後忍不住脫口說出:「所以說我可以在公車上朝你大喊『強暴犯』,你也不在乎囉?」
他哽住了氣,彷彿我剛剛甩了他一巴掌。我也被自己說出的話嚇了一跳,兩隻手摀住了嘴。我的話仍在空中懸盪著。
突然之間,我們放聲大笑到整個身體都抖動起來。我們不由自主地劇烈笑著,直到淚水順著臉龐滑落下來。
「我不敢相信你說了這句話。」他設法在笑聲之間擠出這句話。
「我也不敢相信我們還能大笑出來。」
我們明白哄堂大笑有多不合宜,這反而使得整件事更加戲謔歡樂。即使只是看著彼此,都會忍不住引起一陣痙攣。我最後必須藉口要去洗手間,期望暫時的分開可以抑制這不可控制的情緒迸發。
我回到桌旁時仍在擤鼻子,而湯姆也才剛止住了最後的笑聲。在我們歇斯底里反應背後,是多年來艱困的討論再討論。湯姆與「強暴犯」三個字之間的連結如此極端,使得他長時間以來不敢去尋求幫助、交朋友,或是與他人建立深刻的感情。
「我們都知道,有段時間我就是那三個字。」他告訴我:「那三個字逐步吞噬了自我,還有我的前景。強暴犯的標籤黏著我,彷彿那是我的職業,同時大喇喇地標著我的名字、家鄉以及年紀。我用自己看到的這些基本事實,來定義自己,以及我在這世界扮演的角色。在和朋友聊天時,這個標籤便在我眼前閃現,想著:『這些人絲毫不知道自己和怪物坐在一起。』」
我不快地咬著牙。「為自己犯了錯感到遺憾」和「因為犯了錯為自己感到遺憾」之間的界線是相當細微的。在我看來,我們通信聯絡期間湯姆有幾次跨過了這條線,讓我感受到壓力,自己似乎得為了「他自認是個可怕、不值得同情的失敗者」而感到難過。我總覺得要我去同情湯姆,不僅荒謬而且也不合道理,再則也因為我相信,如果有人深信自己不值得救贖,這想法肯定會阻礙他做出任何有建設性的事情。此外,我也沒興趣去加深他這方面的想法。
我告訴他:「你知道我是怎麼看待這所謂『不值得原諒、友誼、愛情的邪惡強暴犯怪獸』的想法的。」
他淡淡一笑。「對,我知道,記得你有一次對我感到很洩氣,要我結束這場『自怨自艾派對』。你也知道,自責也是另一樣我抓緊不放的護身毯,我後來發現自己對這種情緒模式上癮了,即使跟你在一起也是如此。我會試著透過談論『難處』來博取他人的理解和注意。或是,把自己跟深愛的人隔絕開來,如此一來,當我以堅強、獨立的姿態回來時,就會備受珍惜和仰慕。然而,我卻以此閃避所有責任、情緒和義務。
「等到我終於可以分辨出這模式,進而剷除它的時候,才真正安心下來。就跟戒除藥物一樣,我忍受著所有戒斷症狀。那套『我是個可憐人』,或者說『我是邪惡的強暴犯』的故事在心裡上演了很長一段間,實在是已經厭煩了。」
「我是可以把你想成『強暴犯』,至少是『我的強暴犯』。不過這並不是事實,更別說它和『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幾乎沾不上一丁點邊。就像我曾經喝到爛醉,並不因此就讓我變成了『酒鬼』。我偶爾會說謊,這不表示我是個『騙子』。我被人強暴,這不表示我就是個『受害者』。人在一生之中都會做好事和壞事,我的重點是:我是個人,不是個標籤。我不能把自己簡化成那一晚發生的遭遇,你也不能。」
當食物送上來的時候,我們暫時停止對話。湯姆看起來仍在沉思,我等著他接下來要說的話。
「當我看見生活周遭各種與性剝削有關的事物,不管是年輕女孩在派對上被集體性侵的新聞、男性雜誌上半裸的封面女郎,或是在電視情境喜劇裡談到關於迷姦藥的玩笑,都會讓我湧起一股罪惡感。我知道這就是自怨自艾發展到極致的狀態,也發現自己挺喜歡這感覺。你剛才說,『發生』在你身上的事遠遠不能代表你這個人,我百分之百同意;然而另一方面來看,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當初是有選擇的,但還是做了一件需要隱藏、不讓別人拿來定義我的事情。」
「你發現自己剛做了什麼嗎?」
他詫異地看著我。
「首先,你列出了一大堆『仇視女性』的事情,像是性侵犯、強暴的玩笑,以及對女性的物化等,這也凸顯出這種心理有多普及和正常化。然後,你說『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在你身上。這個嘛,父權制度對你產生了影響,對我們所有人都產生影響。不過你說的對,你那天晚上的確有選擇,沒有人幫你做這決定。
「我不相信性犯罪者生下來就是如此。如果那是男性本能,那麼每一個男人就都是潛在性的強暴犯和猥褻者,我覺得這觀念對男性來說是種侮辱。我拒絕相信我的兒子天生就有性暴力的傾向。我認為他出生時不具備價值觀和信仰,灌輸正確概念是我做為母親最大的任務,但是他也會受到外來影響的形塑。男人為什麼會用武力侵犯女人的答案,在於社會結構,在於我們對待其他人的態度。你曾說過,那一晚感受到自己有這資格那麼做。」
湯姆回答:「你說的對,我在父權體系中成長,它徹底滲入了澳洲人的文化。我們毫不遮掩地物化女性,使得這概念大喇喇地出現在看板上、兒童讀物,也深入到語言當中。我只是不確定利用它來推卸自己的責任是否恰當,畢竟是我自己選擇要侵犯你的。
「不過我也常捫心自問,身邊有那麼多以身作則的好榜樣,教導我尊重、負責平等的同時,我怎麼會做出如此噁心、自私的決定?我唸的都是很棒的男女混校,我來往的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一樣多。過去我根本無法想像有一天會去傷害女性。雖然曾在感情關係裡有出軌過,但這表示我把女性看成是次等人嗎?我不這樣認為。我有物化女性嗎?……我想過去是如此沒錯。我要說的是,受了這麼多教育、感受到這麼多愛,生命裡有許許多多了不起的女性……然而,我還是做出了強暴這種事。」
他搖了搖頭,繼續說:「我寧願選擇你的觀點,莎蒂絲。我也不認為強暴犯是天生的,因為每個人來到這世界時,都是乾淨的白紙。我只是試著去探索內心這不自在的感覺。二分法把我們兩個分隔開來。你絕對不該被單純貼上『受害者』標籤,更何況你一路走來已經遠遠超過這概念了。但就我的部分,我仍然覺得需要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做出性暴力的人,而且這不專指過去那件事。要說『我以前曾經強暴過一個人』似乎……並不完全貼切,我大概還不願意燒掉那張標籤吧。」
我聽進了他的話,決定不再加以探究。畢竟,我沒有權利去定義湯姆對自己的看法。
結完帳之後,我們買了外帶咖啡。我決定要再多享受咖啡因帶來的快感。
「我能問你在教堂時想到些什麼嗎?」湯姆好奇問道。
「大部分就是感激吧。我對自己的健康、家人、這趟旅程……以及這一刻都很感恩,你呢?」
「我想著自己有多高興和感激……」他尋找著正確的字眼:「你很快樂、健康以及被人所愛……」他的嗓音變了。令我驚訝的是,他眼裡充滿了淚水,突然間我明白過來了:儘管他對我做了那件事,他能否原諒自己和我能否找到幸福是密切相關的。
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低聲說:「我是這樣沒錯,我擁有所有你說的東西。」
他擦去臉頰上一滴水,點點頭。笑聲和淚水其實只在一線之間,當心房打開之後,這兩樣情緒甚至可以交融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