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9堂入門課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普立茲獎科學作家 Natalie Angier
一場科學訓練的歡樂巡禮
一本不可或缺的基本讀物
《時人》雜誌形容普立茲獎科學作家昂吉兒擁有罕見的雙重天分:一種對科學的真切熱情,融合了專屬於詩人的第六感。這些天賦具體而微展現在《科學的9堂入門課》之中,其對科學的熱情禮讚讓本書儼然已成某種經典。對所有那些想要了解從幹細胞、禽流感,到演化學及全球暖化等這個時代的偉大議題的任何人而言,《科學的9堂入門課》無疑是一本重要讀物。
這本書也是針對那些曾經因為小孩問起地球如何形成,以及何謂電力而感到些許恐慌的所有父母親所量身訂作。昂吉兒的絕妙文采以及易懂的比喻,讓以往冰冷的科學走入你我的生活,讓我們得以重拾孩童時期發現這個世界的運作原理時的喜悅。《科學的9堂入門課》是一趟針對物理、化學、生物學、地質學以及天文學等主要科學原理的歡樂巡禮。
沿途我們將會得知這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冰淇淋為什麼會融化、咖啡為什麼會變冷、當我們享用奶油煎餅時,肝細胞是怎麼運作的?以及我們人類又是怎麼都由星塵做成的?科學也可以成為日常話題,但同時,我們對科學其實所知甚少,不足以應付日常所需。本書以簡練精粹及基礎入門的方式,提供讀者有趣易懂的內容,讓仍視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為畏途的讀者,可以加入這個世紀最有趣的科學覺醒。
大人們總是把科學當作是小孩子才要學的東西,更多的大人是在他們還小的時候──也就是當初理化被當,之後就再也不碰任何跟科學有關的一切。但是,科學不是一堆事實,科學是一種思考的方式,也是觀看這個世界的方式。如果大多數人不懂科學或科學思考?那會怎麼樣?如果普通人不知道離我們最近的恆星名字(太陽),或是蕃茄有沒有基因(有),或是為什麼手不能穿過桌面(因為兩者的電子會互斥),這有什麼關係呢?就讓專家當專家吧!讓心臟科醫生知道如何修補動脈,生物學家知道如何分析生物滅絕,噴射客機駕駛知道你要起身上廁所的那一刻,馬上點亮「繫好安全帶」的燈號……為什麼我們一般人不能平平靜靜剪折價券或減卡路里就好了呢?實則不然!擁有科學內涵的人,會透過全球暖化、替代能源、胚胎幹細胞、飛彈防禦系統等議題,了解你我還能活多久,以及怎麼樣才能活得更好。而且,擁有科學內涵的理智公民,能夠選出更有智慧的總統或民意代表。有科學常識的大眾,起碼比較不會被迷信、僥倖、謬誤與詐欺所誘騙。你會了解星座背後所持的道理很可笑,也會明白當醫生、助產士,或是計程車司機幫忙接生時,施用的力氣比起太陽、月球,或任何星球在嬰兒誕生那刻所施的引力大上千萬倍。你也可以計算出中樂透的機率,便知道機會小到多麼荒謬可笑,於是決定終生不再買彩券,只是這樣你就不能做公益了……這些就是本書想要說的,也是科學家希望我們所有人都該懂的一切。
一場科學訓練的歡樂巡禮
一本不可或缺的基本讀物
《時人》雜誌形容普立茲獎科學作家昂吉兒擁有罕見的雙重天分:一種對科學的真切熱情,融合了專屬於詩人的第六感。這些天賦具體而微展現在《科學的9堂入門課》之中,其對科學的熱情禮讚讓本書儼然已成某種經典。對所有那些想要了解從幹細胞、禽流感,到演化學及全球暖化等這個時代的偉大議題的任何人而言,《科學的9堂入門課》無疑是一本重要讀物。
這本書也是針對那些曾經因為小孩問起地球如何形成,以及何謂電力而感到些許恐慌的所有父母親所量身訂作。昂吉兒的絕妙文采以及易懂的比喻,讓以往冰冷的科學走入你我的生活,讓我們得以重拾孩童時期發現這個世界的運作原理時的喜悅。《科學的9堂入門課》是一趟針對物理、化學、生物學、地質學以及天文學等主要科學原理的歡樂巡禮。
沿途我們將會得知這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冰淇淋為什麼會融化、咖啡為什麼會變冷、當我們享用奶油煎餅時,肝細胞是怎麼運作的?以及我們人類又是怎麼都由星塵做成的?科學也可以成為日常話題,但同時,我們對科學其實所知甚少,不足以應付日常所需。本書以簡練精粹及基礎入門的方式,提供讀者有趣易懂的內容,讓仍視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為畏途的讀者,可以加入這個世紀最有趣的科學覺醒。
大人們總是把科學當作是小孩子才要學的東西,更多的大人是在他們還小的時候──也就是當初理化被當,之後就再也不碰任何跟科學有關的一切。但是,科學不是一堆事實,科學是一種思考的方式,也是觀看這個世界的方式。如果大多數人不懂科學或科學思考?那會怎麼樣?如果普通人不知道離我們最近的恆星名字(太陽),或是蕃茄有沒有基因(有),或是為什麼手不能穿過桌面(因為兩者的電子會互斥),這有什麼關係呢?就讓專家當專家吧!讓心臟科醫生知道如何修補動脈,生物學家知道如何分析生物滅絕,噴射客機駕駛知道你要起身上廁所的那一刻,馬上點亮「繫好安全帶」的燈號……為什麼我們一般人不能平平靜靜剪折價券或減卡路里就好了呢?實則不然!擁有科學內涵的人,會透過全球暖化、替代能源、胚胎幹細胞、飛彈防禦系統等議題,了解你我還能活多久,以及怎麼樣才能活得更好。而且,擁有科學內涵的理智公民,能夠選出更有智慧的總統或民意代表。有科學常識的大眾,起碼比較不會被迷信、僥倖、謬誤與詐欺所誘騙。你會了解星座背後所持的道理很可笑,也會明白當醫生、助產士,或是計程車司機幫忙接生時,施用的力氣比起太陽、月球,或任何星球在嬰兒誕生那刻所施的引力大上千萬倍。你也可以計算出中樂透的機率,便知道機會小到多麼荒謬可笑,於是決定終生不再買彩券,只是這樣你就不能做公益了……這些就是本書想要說的,也是科學家希望我們所有人都該懂的一切。
名人推薦
中研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生物人類學者王道還
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蝶道》、《迷蝶誌》作者吳明益
臺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高涌泉
臺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孫維新
聯合推薦
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蝶道》、《迷蝶誌》作者吳明益
臺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高涌泉
臺灣大學物理系與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孫維新
聯合推薦
目錄
導論
大力士來唱歌
1.以科學思考
靈魂出竅的體驗
2.機率
鐘形曲線最佳代言
3.校準
把玩尺度
4.物理
真空就已足夠
5.化學
火、冰、間諜和生命
6.演化生物學
萬物理論
7.分子生物學
細胞和口哨
8.地質學
想像世界板塊
9.天文學
天堂的居民
大力士來唱歌
1.以科學思考
靈魂出竅的體驗
2.機率
鐘形曲線最佳代言
3.校準
把玩尺度
4.物理
真空就已足夠
5.化學
火、冰、間諜和生命
6.演化生物學
萬物理論
7.分子生物學
細胞和口哨
8.地質學
想像世界板塊
9.天文學
天堂的居民
試閱
導論
大力士來唱歌
當姐姐的老二也過十三歲時,她說一家人最常流連忘返的科博館與動物園,以後不用再辦會員證了。她解釋那是小孩玩的地方,但是現在兩個小孩的品味比較成熟,喜歡更上乘的娛樂消遣,如美術館、劇院與芭蕾舞等等。這不是很好嗎?孩子的身子拉長了,注意力也隨之增長,可以安靜坐幾個小時欣賞「馬克白」,不會一直偷摸椅子底下有沒有口香糖;不會再將科展台打得乒乒乓乓、用力敲按鈕製造地震,或是使勁搖把手,以便體驗牛頓的運動定律(或其它東東……反正沒有人去看說明,只是常會以為東西弄壞了,急著向媽咪討救兵)。現在,他們不再模仿大猩猩、熱烈討論北極熊的體形架構,或者對駱駝的那一大沱口水好奇得不得了。噢!光陰的步履輕盈飛揚,瞧孩子的靴頭已多麼帥勁挺拔。這種中產階級的成年儀式司空見慣:從白眉猴到莫迪利亞尼(Modigliani),從雷克斯龍(Torex)到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
從分貝大小也可看出這層轉變。動物園與自然科學博物館總是吵吵鬧鬧,喧嘩之聲不絕於耳。劇院與美術館則是輕聲細語,要是觀賞時閣下的手機膽敢響起一丁點貝多芬的來電鈴聲,尤其是還白目到接電話時,其它觀眾早就捲起節目單打人啦。大家總以為,親近科學是留給年紀小小的過動兒,這是當生長激素急速分泌時能稍稍引人駐足的遊戲,等到哪天巴黎的馬蒂斯與畢卡索畫展,比起電影院裡的蜘蛛大戰更具吸引力時,就是大腦處女秀的時候了:來啊!來捉我啊!別忘了帶普魯斯特(Proust)來喔!
我當然利用機會好好唸了姐姐一頓。妳在說什麼啊?只因為小孩長大了,就不用再管科學了嗎?妳覺得學科學到這種程度就足夠了嗎?他們已經知道宇宙、細胞、原子、電磁學、晶簇、三葉蟲、染色體,以及連史帝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說他也搞不懂的傅科擺嗎?那妳怎麼解釋那些詭異的眼睛錯覺,讓人一次只能看見一個花瓶或兩張臉孔,但絕對不會同時看到花瓶與臉孔,不管如何擠眉弄眼、硬要同時看兩邊,不行就是不行!妳的孩子真的準備要將宇宙種種謎團拋在腦後嗎?我兇巴巴地問:真的嗎?
我的聲音拉高了,就像每次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時一樣。早已習慣的姐姐不以為意,她隨口說會員費很貴吶,而且孩子們在學校學的科學夠多了,還有一個想當海洋生物學家呢!至於她自己呢?她說都有公共電視啊,問我何必那麼在意。
因為我腦子清醒啊!我嘀咕著。給我機會,我會證明的。
雖然我氣呼呼,但是不能怪姐姐決定將與科學少有的聯繫切斷。老實說,雖然像奧瑞崗科學工業博物館滿不錯的,但是受到熱列歡迎的「人體奇觀」特展,顯然也是專為年輕孩子的品味所設計的。
小學是人生中大家都要念科學的時期。一旦上中學後開始風雲變色,科學成為少數教士的禁地,鮮有人想越雷池一步;小時候參觀「人體奇觀」的眼界大開與促狹歡樂,長大後反倒變得噁心無比。在美國,喜愛科學的青少年被冠上許多嘲弄的綽號,像怪胎、書呆、蛋頭、傻瓜、瘋子、(白)老鼠,以及新近流行的「自閉兒」,還有很難聽的「匹伯」(peeps-pocket protectors,口袋保護者)、「秀逗」(dogs-duct tape on glasses,用膠帶黏貼眼鏡)或是「俗仔」(losers-last ones selected for every sport,遊戲時最後被挑中的人)。另一方面,不喜歡科學的青少年就是正常人,會特別強調自己是「傢伙」(guys)。他們通常很容易就能分出自己人與科學怪胎,萬一有丁點疑問時,會趕緊宣稱自己是如假包換的「傢伙」。有一次我走在兩名約十六歲少女的背後時,發現了這一點。
A女問B女:妳媽媽做什麼工作呢?
「哦,她在貝塞達的NIH工作,」B女回答:「她是科學家。」(NIH是美國健康研究院。)
「啊哈!」A女說。我等著她加上「哇,了不起!」「好厲害喔!」「超酷的!」,或是再追問這位能幹的媽媽是專長哪門科學。但是隔了一兩秒後,A女吐槽說:「我討厭科學。」
「對啊!妳又不能挑爸媽。」B女邊說邊撥弄灰棕色髮絲:「不管這了,你們傢伙週末要幹嘛?」
長大後,書呆子與一般人的隔閡越來越深,甚至蔓生荊棘,很快就難以跨越。當我的美髮師說他要去波多黎各玩時,因為我前一年夏天正好待在那裡,便推薦他去島上西北邊的阿雷西波無線電望遠鏡。他看著我,好像我叫他去參觀洗衣粉工廠一樣。他問:「我幹嘛去那裡啊?」
我說:「因為那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望遠鏡,好像一塊亮晶晶的水果盤鑲在山谷,而且還對大眾開放呢!」
「啊哈!」他剪掉我的一大塊劉海。
「因為那邊的科博館很棒,讓你更懂宇宙學?」
「你知道我不是熱愛科技的人,」他說。卡嚓、卡嚓、卡嚓、卡嚓、卡嚓。
「因為它出現在茱蒂‧佛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的電影《接觸未來》(Contact)?」我急忙摸著頭。
但那把利剪停不下來。他說:「我不是茱蒂佛斯特的粉絲耶,不過我會列入考慮啦!」
當我回家後,先生掩不住訝異說:「親愛的,妳的頭髮怎麼了?」
說實話,我每次都得處變不驚。不然怎麼辦呢?我是科學作家,一輩子做這行幾十年了,我得承認我愛死科學了。這份迷戀從小開始,我對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是百逛不厭。後來念新水牛城一所迷你中學時稍稍擱置熱情,因為那時學校經費窘迫,一個老師得當幾個人用,所以足球教練還兼任生物、化學、歷史教師。不過,這個累得半死的教練從未失去幽默感,有一天早上我帶著生物作業要繳到他桌上,那是釘有二十幾隻昆蟲的標本,但我發現螳螂、聖甲蟲、天蛾都還沒有完全死掉,而是在釘子下絕望蠕動時,我發出驚叫聲,將整個東西丟到地上。老師睜大眼睛笑嘻嘻看著我,說他等不及看我解剖小豬了。
在大學時,我又重拾昔日對科學的熱情,再度點燃本生燈的藍色火苗。我修了許多堂科學課,雖然我立志當作家,而同好們也很好奇我幹嘛要修什麼勞什子物理、微積分、電腦、天文及古生物學的。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因為我不是天生吃實驗室飯的傢伙。但是我去上課、左敲右打、詛咒發誓、拉扯頭髮,我繼續念下去。
「喂,妳這麼想文武雙全啊?」朋友說:「妳做這些腦力大考驗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說:「我喜歡科學也相信科學,科學讓我很樂觀,讓生命很帶勁。」
他問我為什麼不去當科學家就好了,我告訴他要保持距離才有美感。而且我不會是很好的科學家,我有自知之明。
所以妳會變專業的鑑賞家嘍?他問。
夠接近了,我變成了科學作家。
那麼,如今我已經探到科學的肌理了,還是軟骨、叉骨、表皮或是屁股呢?當科學作家已經有二十五個年頭了,我雖然熱愛科學,但每次總是被迫看清楚科學與人世間多麼疏離隔閡,科學怪胎的形象已深植人心,大人們總把科學當作是小孩子才要學的東西。每當我介紹自己的職業時,總是聽到這句話:「科學作家喔?我從中學當掉化學後,再也沒碰科學了。」(排名第二的回答是「我從中學當掉物理後……」。)加州理工學院的化學系教授芭頓(Jacqueline Barton)對這些話熟到不能再熟,她覺得滑稽的是,發誓自己的化學成績不是「馬馬虎虎」而是「一敗塗地」的人,竟然多到不可勝數!即使經過多年的分數膨脹,也不能去除美國人認為大家的化學成績都是F的印象。
2.機率
鐘形曲線是最佳代言人
每個學期一開始,諾蘭都會教初級統計課的學生一則兩面通的人生基本道理:刻意安排很難搞得像意外,真正的隨機卻很像是作弊。還有什麼比丟硬幣更能證明她的論點呢?
諾蘭將班上約六十五名學生分成兩組,其中一組人從皮包、口袋或向隔壁善心人士借一個硬幣,丟擲一百次,然後將每次的結果記在紙上。另一組學生想像丟硬幣一百次,將自己假想的結果寫下來。接著,學生們在紙上寫下只有自己知道的記號,將紀錄表面朝下交到諾蘭的桌上。
諾蘭離開教室後,學生們開始丟硬幣做紀錄,或是假想後做紀錄。諾蘭回到教室後,看每串一百個正反面的紀錄後,便能指出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想的。她幾乎百發百中,讓學生驚訝萬分。他們認為老師一定作弊,可能是偷看或是有內線。但是諾蘭不用當間諜,因為真正的隨機事件有獨特的印記,在熟悉其模式之前,一般人會覺得隨機一定很亂。諾蘭知道真正的隨機看起來會如何,也懂得如果隨機看起來不夠隨機的話,常常會讓人們覺得不舒服。
若真正丟擲硬幣,會發現出現許多一連串相同的結果,例如連續五次正面或七次反面。若是丟得夠久,會明白這沒什麼大不了,因為丟一、兩百次後都會發生這種事。不過,如果丟幾次便要做決定,例如看誰先選擇度假地點或是誰得處理死老鼠時,老是出現同面可會讓人心生懷疑。連續六個反面?這個硬幣從哪裡拿的?換我試試看。
在想像丟硬幣時,學生天生會提防發生「太多巧合」,於是在正反面之間來來回回做補救。一般若丟出三個相同的結果,學生腦海中便會響起警鈴,讓他們刻意改變結果。諾蘭表示:「當我檢查假想的結果時,連續同面的最高次數實在是少得可以,而且正反面交替的次數也太高了。」大家知道每次丟硬幣時各有一半正面、一半反面的機率,也知道丟一百次時大致上會得到各接近五十次的結果。所以好吧,四十八個反面、五十二個正面,我可以接受。但是連續六次反面呢?
諾蘭指出:「人們想要將五十—五十的原則應用在一段非常短的時間內。他們對機率有扭曲的感覺,認為得到連續正面或反面的機會比實際小了許多。然而連續四個正面或四個反面的可能性是八分之一,因此發生機會還滿高的。」諾蘭用簡單的乘法規則便可導出數字,因為丟硬幣時正反面的機率各為百分之五十,計算得到連續兩個正面的機率時,將兩次相乘即可:0.5×0.5=0.25,也就是丟一分錢時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看到林肯兩次。如果想要看接下來是怎麼回事,只要繼續乘下去。投擲四次要見到四個正面,機率是零點五乘四次,結果是十六分之一的機會。若要計算見到四個正面或四個反面的機率,便要將這兩個事件的發生機率相加,1/16+1/16=1/8。當然,要繼續保持同一面的機率會隨著多丟一次而大減,例如得到連續六個正面或反面的機率只有三十二分之一,大約百分之三。若只是丟六次,機會的確不大,但若丟一百次時,機率便開始加總向上了。
此乘法規則僅適用事件發生順序彼此無關的機率計算,例如投擲硬幣時。但若事件可能影響另一項事件時,則不適用。舉例來說,不能將留鬍子和留髭鬚的個別機率相乘,而計算出一個男人同時擁有鬍子和髭鬚的可能性,因為除了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有鬍子的男人通常也會選擇留髭鬚。
這裡的加法原則需要兩個事件互斥,所以丟擲硬幣可適用,因為手上只有一枚硬幣,不可能同時得到四個正面及四個反面。
我自己試過諾蘭的方法好幾次,每次丟一百次硬幣超過十回合,結果每次都至少出現一次連續六個或七個同面,通常每次都會超過連續六個同面,伴隨多次連續五個與四個同面。我最高紀錄是連續丟九個正面,而且即使已明白箇中道理並決心要騙過老師,但要將這個結果放進幻想的丟擲紀錄表,我想到仍然會不舒服。
直到學生們見識到機率廣大的可能性之前,會把隨機當成是緊張抽筋:對不起、對不起,沒辦法停下來!他們會忍不住將結果翻來翻去,林肯(硬幣頭像)……林肯紀念堂……最後會得到什麼?一個模式。有了模式,再跨一步便是畫地自限,接著可憐的兔子便會自縛手腳。諾蘭解釋:「因為許多人未能掌握隨機的真正意義,對於『偶然』很容易附加意義。如果見到連續正面或反面的次數超過某個長度,便會開始找藉口。」
她說,從這裡可以找到迷信的根基。因為不知道「偶然」發生的機率,我們心裡很好奇機率到底有多高?當然是微乎其微,絕不可能是湊巧!
古斯(Alan Guth)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他舉自己家裡的例子來說明,人們多麼容易將偶然看成是預兆。他有一位獨居的叔叔被發現死在家中,一位警察來通知古斯的母親這項不幸的消息。當警察在那裡時,古斯正在出差的姐姐碰巧打電話給媽媽。古斯說:「我媽媽和姐姐都對這通電話的時間點感到驚異,因為正好與警察上門通知叔叔過世的時間一致,她們覺得這一定是心靈感應。」當古斯聽到母親轉述這則親人心靈相通的「奇蹟」後,忍不住做了一些簡單的計算。他姐姐通常每星期打一次電話給媽媽,通常在早上一起床後打電話,或是趁晚上有空時打電話,那時母親也最可能在家。警察大約在下午五點到他母親家裡,因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討論,所以警察停留的時間可能超過一、兩個小時。
古斯說,綜合各項因素後,他姐姐打電話回家正好碰上警察登門拜訪的機率,和連續得到五個正面或反面是一樣的。他說:「我不認為這是一件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母親幸運能及時得到家人的安慰,但不應該解釋是心電感應。
若對機率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比較不會對巧合大驚小怪。我母親告訴我一個好玩的故事,她和一位舊識在六個月期間,彼此的命運好像被無聊的彼得潘牽連著。巧的是這個人是她以前的數學教授,用在這裡當例子頗合適。事情是這樣的:接連幾個星期,我的父母和這位數學教授不斷在曼哈頓的文化公路地帶相逢,包括外百老匯的一場戲、鋼琴演奏會、柏格曼(Bergman)的電影,以及現代美術博物館的莫內(Monet)「睡蓮」畫展。前幾次,我的母親和教授對兩者品味相近有點尷尬而笑,很快地他們遠隔展覽廳兩端點頭示意。難堪的是幾個月後,那是七月的法國,我父母第一次造訪巴黎,正當他們沿著林蔭大道聖米謝爾閒逛時,沒想到那位教授竟然坐在一間咖啡館前。從他拿報紙遮住臉孔的動作來判斷,我母親知道他已經先看見他們了。
假如我母親很迷信,就會認定老天要告訴她什麼事情(「教授討厭你!」)。不過我知道她超不迷信,而她自己也明白:(a)喜歡莫內的人也喜歡法國藝術;(b)巴黎以一流的法國藝術收藏而聞名天下;(c)「四月在巴黎」聽起來浪漫,但是「美國人逛巴黎」聽起來像七月;(d)戶外咖啡館是度過幾個小時最好的地方,除了喝一杯冷掉的濃縮咖啡、抽著菸灰缸裡還沒熄掉的高盧牌香菸,還有隨便翻翻的《哈洛德論壇報》(Herald-Tribune)。
劍橋大學的利特伍德(John Littlewood)是著名的數學家,他對闖入平凡生活的超自然力提出一種自然法則,稱為「利特伍德的奇蹟法則」。和多數人一樣,他將「奇蹟」定義為:百萬中一次,發生時會引人注目。根據這個法則,每人一生中平均每月發生一次「奇蹟」。利特伍德解釋如下:你每天外出和世界奮戰約八小時,平均每秒鐘可看到或聽到一件事情發生,所以一天總計有三萬次「事件」,每個月大概一百萬次。絕大多數事情你幾乎沒怎麼注意,但是對於驚奇之事經常不會忽視,例如酒吧的鋼琴師彈起你心裡想的一首歌,或是經過當鋪窗前瞥見十八個月前家裡被偷走的傳家戒指。是的,只要不是植物人,而且活得比蜉蝣久一點,生命會充滿大大小小奇蹟的!
因為出生是奇蹟中的奇蹟,所以諾蘭也喜歡用「生日遊戲」,讓學生驚呼連連。她說,我打賭教室裡至少有兩個人的生日是同一天,六十五名學生左看右看,看不出是誰與自己的出生日期很接近,對老師的話抱持懷疑。諾蘭從教室一端開始詢問學生的生日,然後寫在黑板上,接下來換下一位,很快相同的生日出現了。學生很驚訝,如何在三百六十五天(或閏年三百六十六天)中、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選擇裡出現這種事?首先,諾蘭提醒學生,討論的題目不是找出一個特定的生日配對,而是找到任何相同的生日配對。然後,她請學生從另一個方向思考問題:找不到相同生日的機率有多少?結果這個數字很快就讓真相大白了,因為每次新的出生日期列出來後,三百六十五天中可能找不到相同生日的日子又畫掉一天,然而每一次有人要宣布生日時,學生理論上可選擇的範圍都是三百六十五天。換句話說,一方數字一直縮小,另一方數字卻維持一樣。因為這裡的機率計算是比較固定的可能選擇1與縮小的可選擇1(透過乘除),所以在六十五名學生中找不到生日相同的可能性很快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當然,預測只是可能性而非保證,不過抽象又違反直覺的統計學,卻一再在諾蘭的課堂上證明是衡量真實的巧幫手。
大力士來唱歌
當姐姐的老二也過十三歲時,她說一家人最常流連忘返的科博館與動物園,以後不用再辦會員證了。她解釋那是小孩玩的地方,但是現在兩個小孩的品味比較成熟,喜歡更上乘的娛樂消遣,如美術館、劇院與芭蕾舞等等。這不是很好嗎?孩子的身子拉長了,注意力也隨之增長,可以安靜坐幾個小時欣賞「馬克白」,不會一直偷摸椅子底下有沒有口香糖;不會再將科展台打得乒乒乓乓、用力敲按鈕製造地震,或是使勁搖把手,以便體驗牛頓的運動定律(或其它東東……反正沒有人去看說明,只是常會以為東西弄壞了,急著向媽咪討救兵)。現在,他們不再模仿大猩猩、熱烈討論北極熊的體形架構,或者對駱駝的那一大沱口水好奇得不得了。噢!光陰的步履輕盈飛揚,瞧孩子的靴頭已多麼帥勁挺拔。這種中產階級的成年儀式司空見慣:從白眉猴到莫迪利亞尼(Modigliani),從雷克斯龍(Torex)到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
從分貝大小也可看出這層轉變。動物園與自然科學博物館總是吵吵鬧鬧,喧嘩之聲不絕於耳。劇院與美術館則是輕聲細語,要是觀賞時閣下的手機膽敢響起一丁點貝多芬的來電鈴聲,尤其是還白目到接電話時,其它觀眾早就捲起節目單打人啦。大家總以為,親近科學是留給年紀小小的過動兒,這是當生長激素急速分泌時能稍稍引人駐足的遊戲,等到哪天巴黎的馬蒂斯與畢卡索畫展,比起電影院裡的蜘蛛大戰更具吸引力時,就是大腦處女秀的時候了:來啊!來捉我啊!別忘了帶普魯斯特(Proust)來喔!
我當然利用機會好好唸了姐姐一頓。妳在說什麼啊?只因為小孩長大了,就不用再管科學了嗎?妳覺得學科學到這種程度就足夠了嗎?他們已經知道宇宙、細胞、原子、電磁學、晶簇、三葉蟲、染色體,以及連史帝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說他也搞不懂的傅科擺嗎?那妳怎麼解釋那些詭異的眼睛錯覺,讓人一次只能看見一個花瓶或兩張臉孔,但絕對不會同時看到花瓶與臉孔,不管如何擠眉弄眼、硬要同時看兩邊,不行就是不行!妳的孩子真的準備要將宇宙種種謎團拋在腦後嗎?我兇巴巴地問:真的嗎?
我的聲音拉高了,就像每次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時一樣。早已習慣的姐姐不以為意,她隨口說會員費很貴吶,而且孩子們在學校學的科學夠多了,還有一個想當海洋生物學家呢!至於她自己呢?她說都有公共電視啊,問我何必那麼在意。
因為我腦子清醒啊!我嘀咕著。給我機會,我會證明的。
雖然我氣呼呼,但是不能怪姐姐決定將與科學少有的聯繫切斷。老實說,雖然像奧瑞崗科學工業博物館滿不錯的,但是受到熱列歡迎的「人體奇觀」特展,顯然也是專為年輕孩子的品味所設計的。
小學是人生中大家都要念科學的時期。一旦上中學後開始風雲變色,科學成為少數教士的禁地,鮮有人想越雷池一步;小時候參觀「人體奇觀」的眼界大開與促狹歡樂,長大後反倒變得噁心無比。在美國,喜愛科學的青少年被冠上許多嘲弄的綽號,像怪胎、書呆、蛋頭、傻瓜、瘋子、(白)老鼠,以及新近流行的「自閉兒」,還有很難聽的「匹伯」(peeps-pocket protectors,口袋保護者)、「秀逗」(dogs-duct tape on glasses,用膠帶黏貼眼鏡)或是「俗仔」(losers-last ones selected for every sport,遊戲時最後被挑中的人)。另一方面,不喜歡科學的青少年就是正常人,會特別強調自己是「傢伙」(guys)。他們通常很容易就能分出自己人與科學怪胎,萬一有丁點疑問時,會趕緊宣稱自己是如假包換的「傢伙」。有一次我走在兩名約十六歲少女的背後時,發現了這一點。
A女問B女:妳媽媽做什麼工作呢?
「哦,她在貝塞達的NIH工作,」B女回答:「她是科學家。」(NIH是美國健康研究院。)
「啊哈!」A女說。我等著她加上「哇,了不起!」「好厲害喔!」「超酷的!」,或是再追問這位能幹的媽媽是專長哪門科學。但是隔了一兩秒後,A女吐槽說:「我討厭科學。」
「對啊!妳又不能挑爸媽。」B女邊說邊撥弄灰棕色髮絲:「不管這了,你們傢伙週末要幹嘛?」
長大後,書呆子與一般人的隔閡越來越深,甚至蔓生荊棘,很快就難以跨越。當我的美髮師說他要去波多黎各玩時,因為我前一年夏天正好待在那裡,便推薦他去島上西北邊的阿雷西波無線電望遠鏡。他看著我,好像我叫他去參觀洗衣粉工廠一樣。他問:「我幹嘛去那裡啊?」
我說:「因為那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望遠鏡,好像一塊亮晶晶的水果盤鑲在山谷,而且還對大眾開放呢!」
「啊哈!」他剪掉我的一大塊劉海。
「因為那邊的科博館很棒,讓你更懂宇宙學?」
「你知道我不是熱愛科技的人,」他說。卡嚓、卡嚓、卡嚓、卡嚓、卡嚓。
「因為它出現在茱蒂‧佛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的電影《接觸未來》(Contact)?」我急忙摸著頭。
但那把利剪停不下來。他說:「我不是茱蒂佛斯特的粉絲耶,不過我會列入考慮啦!」
當我回家後,先生掩不住訝異說:「親愛的,妳的頭髮怎麼了?」
說實話,我每次都得處變不驚。不然怎麼辦呢?我是科學作家,一輩子做這行幾十年了,我得承認我愛死科學了。這份迷戀從小開始,我對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是百逛不厭。後來念新水牛城一所迷你中學時稍稍擱置熱情,因為那時學校經費窘迫,一個老師得當幾個人用,所以足球教練還兼任生物、化學、歷史教師。不過,這個累得半死的教練從未失去幽默感,有一天早上我帶著生物作業要繳到他桌上,那是釘有二十幾隻昆蟲的標本,但我發現螳螂、聖甲蟲、天蛾都還沒有完全死掉,而是在釘子下絕望蠕動時,我發出驚叫聲,將整個東西丟到地上。老師睜大眼睛笑嘻嘻看著我,說他等不及看我解剖小豬了。
在大學時,我又重拾昔日對科學的熱情,再度點燃本生燈的藍色火苗。我修了許多堂科學課,雖然我立志當作家,而同好們也很好奇我幹嘛要修什麼勞什子物理、微積分、電腦、天文及古生物學的。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因為我不是天生吃實驗室飯的傢伙。但是我去上課、左敲右打、詛咒發誓、拉扯頭髮,我繼續念下去。
「喂,妳這麼想文武雙全啊?」朋友說:「妳做這些腦力大考驗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說:「我喜歡科學也相信科學,科學讓我很樂觀,讓生命很帶勁。」
他問我為什麼不去當科學家就好了,我告訴他要保持距離才有美感。而且我不會是很好的科學家,我有自知之明。
所以妳會變專業的鑑賞家嘍?他問。
夠接近了,我變成了科學作家。
那麼,如今我已經探到科學的肌理了,還是軟骨、叉骨、表皮或是屁股呢?當科學作家已經有二十五個年頭了,我雖然熱愛科學,但每次總是被迫看清楚科學與人世間多麼疏離隔閡,科學怪胎的形象已深植人心,大人們總把科學當作是小孩子才要學的東西。每當我介紹自己的職業時,總是聽到這句話:「科學作家喔?我從中學當掉化學後,再也沒碰科學了。」(排名第二的回答是「我從中學當掉物理後……」。)加州理工學院的化學系教授芭頓(Jacqueline Barton)對這些話熟到不能再熟,她覺得滑稽的是,發誓自己的化學成績不是「馬馬虎虎」而是「一敗塗地」的人,竟然多到不可勝數!即使經過多年的分數膨脹,也不能去除美國人認為大家的化學成績都是F的印象。
2.機率
鐘形曲線是最佳代言人
每個學期一開始,諾蘭都會教初級統計課的學生一則兩面通的人生基本道理:刻意安排很難搞得像意外,真正的隨機卻很像是作弊。還有什麼比丟硬幣更能證明她的論點呢?
諾蘭將班上約六十五名學生分成兩組,其中一組人從皮包、口袋或向隔壁善心人士借一個硬幣,丟擲一百次,然後將每次的結果記在紙上。另一組學生想像丟硬幣一百次,將自己假想的結果寫下來。接著,學生們在紙上寫下只有自己知道的記號,將紀錄表面朝下交到諾蘭的桌上。
諾蘭離開教室後,學生們開始丟硬幣做紀錄,或是假想後做紀錄。諾蘭回到教室後,看每串一百個正反面的紀錄後,便能指出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想的。她幾乎百發百中,讓學生驚訝萬分。他們認為老師一定作弊,可能是偷看或是有內線。但是諾蘭不用當間諜,因為真正的隨機事件有獨特的印記,在熟悉其模式之前,一般人會覺得隨機一定很亂。諾蘭知道真正的隨機看起來會如何,也懂得如果隨機看起來不夠隨機的話,常常會讓人們覺得不舒服。
若真正丟擲硬幣,會發現出現許多一連串相同的結果,例如連續五次正面或七次反面。若是丟得夠久,會明白這沒什麼大不了,因為丟一、兩百次後都會發生這種事。不過,如果丟幾次便要做決定,例如看誰先選擇度假地點或是誰得處理死老鼠時,老是出現同面可會讓人心生懷疑。連續六個反面?這個硬幣從哪裡拿的?換我試試看。
在想像丟硬幣時,學生天生會提防發生「太多巧合」,於是在正反面之間來來回回做補救。一般若丟出三個相同的結果,學生腦海中便會響起警鈴,讓他們刻意改變結果。諾蘭表示:「當我檢查假想的結果時,連續同面的最高次數實在是少得可以,而且正反面交替的次數也太高了。」大家知道每次丟硬幣時各有一半正面、一半反面的機率,也知道丟一百次時大致上會得到各接近五十次的結果。所以好吧,四十八個反面、五十二個正面,我可以接受。但是連續六次反面呢?
諾蘭指出:「人們想要將五十—五十的原則應用在一段非常短的時間內。他們對機率有扭曲的感覺,認為得到連續正面或反面的機會比實際小了許多。然而連續四個正面或四個反面的可能性是八分之一,因此發生機會還滿高的。」諾蘭用簡單的乘法規則便可導出數字,因為丟硬幣時正反面的機率各為百分之五十,計算得到連續兩個正面的機率時,將兩次相乘即可:0.5×0.5=0.25,也就是丟一分錢時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看到林肯兩次。如果想要看接下來是怎麼回事,只要繼續乘下去。投擲四次要見到四個正面,機率是零點五乘四次,結果是十六分之一的機會。若要計算見到四個正面或四個反面的機率,便要將這兩個事件的發生機率相加,1/16+1/16=1/8。當然,要繼續保持同一面的機率會隨著多丟一次而大減,例如得到連續六個正面或反面的機率只有三十二分之一,大約百分之三。若只是丟六次,機會的確不大,但若丟一百次時,機率便開始加總向上了。
此乘法規則僅適用事件發生順序彼此無關的機率計算,例如投擲硬幣時。但若事件可能影響另一項事件時,則不適用。舉例來說,不能將留鬍子和留髭鬚的個別機率相乘,而計算出一個男人同時擁有鬍子和髭鬚的可能性,因為除了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有鬍子的男人通常也會選擇留髭鬚。
這裡的加法原則需要兩個事件互斥,所以丟擲硬幣可適用,因為手上只有一枚硬幣,不可能同時得到四個正面及四個反面。
我自己試過諾蘭的方法好幾次,每次丟一百次硬幣超過十回合,結果每次都至少出現一次連續六個或七個同面,通常每次都會超過連續六個同面,伴隨多次連續五個與四個同面。我最高紀錄是連續丟九個正面,而且即使已明白箇中道理並決心要騙過老師,但要將這個結果放進幻想的丟擲紀錄表,我想到仍然會不舒服。
直到學生們見識到機率廣大的可能性之前,會把隨機當成是緊張抽筋:對不起、對不起,沒辦法停下來!他們會忍不住將結果翻來翻去,林肯(硬幣頭像)……林肯紀念堂……最後會得到什麼?一個模式。有了模式,再跨一步便是畫地自限,接著可憐的兔子便會自縛手腳。諾蘭解釋:「因為許多人未能掌握隨機的真正意義,對於『偶然』很容易附加意義。如果見到連續正面或反面的次數超過某個長度,便會開始找藉口。」
她說,從這裡可以找到迷信的根基。因為不知道「偶然」發生的機率,我們心裡很好奇機率到底有多高?當然是微乎其微,絕不可能是湊巧!
古斯(Alan Guth)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他舉自己家裡的例子來說明,人們多麼容易將偶然看成是預兆。他有一位獨居的叔叔被發現死在家中,一位警察來通知古斯的母親這項不幸的消息。當警察在那裡時,古斯正在出差的姐姐碰巧打電話給媽媽。古斯說:「我媽媽和姐姐都對這通電話的時間點感到驚異,因為正好與警察上門通知叔叔過世的時間一致,她們覺得這一定是心靈感應。」當古斯聽到母親轉述這則親人心靈相通的「奇蹟」後,忍不住做了一些簡單的計算。他姐姐通常每星期打一次電話給媽媽,通常在早上一起床後打電話,或是趁晚上有空時打電話,那時母親也最可能在家。警察大約在下午五點到他母親家裡,因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討論,所以警察停留的時間可能超過一、兩個小時。
古斯說,綜合各項因素後,他姐姐打電話回家正好碰上警察登門拜訪的機率,和連續得到五個正面或反面是一樣的。他說:「我不認為這是一件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母親幸運能及時得到家人的安慰,但不應該解釋是心電感應。
若對機率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比較不會對巧合大驚小怪。我母親告訴我一個好玩的故事,她和一位舊識在六個月期間,彼此的命運好像被無聊的彼得潘牽連著。巧的是這個人是她以前的數學教授,用在這裡當例子頗合適。事情是這樣的:接連幾個星期,我的父母和這位數學教授不斷在曼哈頓的文化公路地帶相逢,包括外百老匯的一場戲、鋼琴演奏會、柏格曼(Bergman)的電影,以及現代美術博物館的莫內(Monet)「睡蓮」畫展。前幾次,我的母親和教授對兩者品味相近有點尷尬而笑,很快地他們遠隔展覽廳兩端點頭示意。難堪的是幾個月後,那是七月的法國,我父母第一次造訪巴黎,正當他們沿著林蔭大道聖米謝爾閒逛時,沒想到那位教授竟然坐在一間咖啡館前。從他拿報紙遮住臉孔的動作來判斷,我母親知道他已經先看見他們了。
假如我母親很迷信,就會認定老天要告訴她什麼事情(「教授討厭你!」)。不過我知道她超不迷信,而她自己也明白:(a)喜歡莫內的人也喜歡法國藝術;(b)巴黎以一流的法國藝術收藏而聞名天下;(c)「四月在巴黎」聽起來浪漫,但是「美國人逛巴黎」聽起來像七月;(d)戶外咖啡館是度過幾個小時最好的地方,除了喝一杯冷掉的濃縮咖啡、抽著菸灰缸裡還沒熄掉的高盧牌香菸,還有隨便翻翻的《哈洛德論壇報》(Herald-Tribune)。
劍橋大學的利特伍德(John Littlewood)是著名的數學家,他對闖入平凡生活的超自然力提出一種自然法則,稱為「利特伍德的奇蹟法則」。和多數人一樣,他將「奇蹟」定義為:百萬中一次,發生時會引人注目。根據這個法則,每人一生中平均每月發生一次「奇蹟」。利特伍德解釋如下:你每天外出和世界奮戰約八小時,平均每秒鐘可看到或聽到一件事情發生,所以一天總計有三萬次「事件」,每個月大概一百萬次。絕大多數事情你幾乎沒怎麼注意,但是對於驚奇之事經常不會忽視,例如酒吧的鋼琴師彈起你心裡想的一首歌,或是經過當鋪窗前瞥見十八個月前家裡被偷走的傳家戒指。是的,只要不是植物人,而且活得比蜉蝣久一點,生命會充滿大大小小奇蹟的!
因為出生是奇蹟中的奇蹟,所以諾蘭也喜歡用「生日遊戲」,讓學生驚呼連連。她說,我打賭教室裡至少有兩個人的生日是同一天,六十五名學生左看右看,看不出是誰與自己的出生日期很接近,對老師的話抱持懷疑。諾蘭從教室一端開始詢問學生的生日,然後寫在黑板上,接下來換下一位,很快相同的生日出現了。學生很驚訝,如何在三百六十五天(或閏年三百六十六天)中、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選擇裡出現這種事?首先,諾蘭提醒學生,討論的題目不是找出一個特定的生日配對,而是找到任何相同的生日配對。然後,她請學生從另一個方向思考問題:找不到相同生日的機率有多少?結果這個數字很快就讓真相大白了,因為每次新的出生日期列出來後,三百六十五天中可能找不到相同生日的日子又畫掉一天,然而每一次有人要宣布生日時,學生理論上可選擇的範圍都是三百六十五天。換句話說,一方數字一直縮小,另一方數字卻維持一樣。因為這裡的機率計算是比較固定的可能選擇1與縮小的可選擇1(透過乘除),所以在六十五名學生中找不到生日相同的可能性很快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當然,預測只是可能性而非保證,不過抽象又違反直覺的統計學,卻一再在諾蘭的課堂上證明是衡量真實的巧幫手。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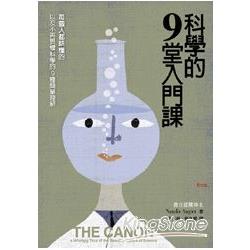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