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2版)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天賦人權」是洛克用來抗衡專制王權與君權神授的概念,充滿了神學的意涵。霍布豪斯等「社會自由主義」理論家,從中加入了社會學、生物學等近代的觀念,來構思一個理想社會的運作方式,他們捍衛「天賦人權」概念,卻不被它帶入「自由放任」與「最小政府」的框架內,可謂是近代社會哲學的一個新典範。
霍布豪斯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一個有機體,不斷地演化,而個人在這個有機體中也持續成長與發展。社會的本質決定個人的幸福,而個人的素質也決定社會的體質。社會需要和諧,個人的精神才能發展,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自由。自由是在具體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上湧現出來的,各類制度如果不能公義平等,則自由將無由著根。這樣的觀念,很不同於將自由視為是「個人不得被侵犯的權利」,在他的自由主義中,權利與義務、個人與社會,是一體的兩面,互相定義。
英國社會理論家霍布豪斯早生了一百年,否則他的思想在今日應是顯學吧!大家把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歸類為「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其實就是「福利國家」政治的先驅。
霍布豪斯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一個有機體,不斷地演化,而個人在這個有機體中也持續成長與發展。社會的本質決定個人的幸福,而個人的素質也決定社會的體質。社會需要和諧,個人的精神才能發展,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自由。自由是在具體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上湧現出來的,各類制度如果不能公義平等,則自由將無由著根。這樣的觀念,很不同於將自由視為是「個人不得被侵犯的權利」,在他的自由主義中,權利與義務、個人與社會,是一體的兩面,互相定義。
英國社會理論家霍布豪斯早生了一百年,否則他的思想在今日應是顯學吧!大家把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歸類為「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其實就是「福利國家」政治的先驅。
目錄
導 讀 有機的社會,理性自律的個人─霍布豪斯的社會自由主義
第一章 在自由主義以前
第二章 自由主義諸要素
第三章 理論的發展
第四章 自由放任主義
第五章 格萊斯頓和彌爾
第六章 自由主義的核心
第七章 國家和個人
第八章 經濟自由主義
第九章 自由主義的未來
第一章 在自由主義以前
第二章 自由主義諸要素
第三章 理論的發展
第四章 自由放任主義
第五章 格萊斯頓和彌爾
第六章 自由主義的核心
第七章 國家和個人
第八章 經濟自由主義
第九章 自由主義的未來
序/導讀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陳思賢
有機的社會,理性自律的個人──霍布豪斯的社會自由主義
英國社會理論家霍布豪斯早生了一百年,否則他的思想在今日應是顯學吧?大家把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歸類為「社會自由主義」(或譯自由社會主義)(Social Liberalism),其實就是「福利國家」政治的先驅。今日我們都已知道,古典自由主義因為立基於原子化的個人與私有財產權至上這兩個原則,其「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哲學與最小政府的治理方式,會造成社會極大的不平等;而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進行試驗的歷史,也證明了國家統制經濟的不可行。因此,約莫從半個多世紀前開始,人類彷彿摸索到了一條中間又務實的道路,那就是打造一個「功能性政府」以適度介入財產重分配與照顧弱勢,這就是「福利國家」。霍布豪斯與和他理念相近的一些前後輩,正是這種制度背後精神之創建者。
近代以降,英國在急遽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的進程中,造就了進步、財富與繁榮,但也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以及社會學的興起),例如勞工處境的艱辛與財富分配的不公。但隨著選舉權的擴散與海外市場的擴大,這些問題又引發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快速變化。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中,從約翰‧彌爾(J. S. Mill)開始,致力修正古典自由主義一切任由「自由市場」來調節、國家不加干預的主張,提倡平等、社會公義與保護弱勢,格林(T. H. Green)繼之而且更加偏向了社會主義的立場,他們兩人都對於霍布豪斯影響很大。於是這三人形成了所謂英國社會自由主義傳統的早期骨幹。在近世政治思想的發展演進歷史上,英國是個奇妙的國家:它不但是自由主義的誕生地,而馬克思的《資本論》泰半也在倫敦完成,現在綜合了前兩者價值關懷的折衷路線──社會自由主義,亦在英國首先醞釀出來;「社會民主」這種現在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東西,就是在英國政治舞台上演化出來的(我們可以想想費邊社的例子),顯然英國是個兼容並蓄的地方。也因為社會民主與福利國家思想的衝擊,英國得以克服若干在快速工業化下產生的社會失調現象,順利地從傳統社會轉型為高度發達工業化國家。
霍布豪斯理想中的自由主義是如何的呢?這就首先要看他是怎樣理解「社會」這個東西。他成長於十九世紀末葉,受到當時開始出現的社會學影響很大;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自由主義思想乃立基於哲學的進路來解釋個人自由在群體社會中的意涵,但他卻採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一個有機體,不斷地演化,而個人在這個有機體中也持續成長與發展。於是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就是緊密而動態的:社會的本質決定個人的幸福,而個人的素質也決定社會的體質。社會需要和諧,個人的精神才能發展,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自由。所以霍布豪斯首先是個自由主義者。但是社會要和諧,「原子化個人式的自由主義立場」是無法使其達成的,這是因為完全的競爭,使得平等不易。霍布豪斯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他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自由,他認為自由是一個「社會性因素」,不是那個完全附著於個人生命的所謂「天賦人權」概念即能包涵之:自由關心的同時是個人、家庭和國家。也就是說,「民主政治不是單單建立在個人的權利或是私人利益上面的……民主政治同樣也建立在個人作為社會一員的職責上。它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共同意志上,同時囑咐每一個聰明的成年人扮演一個角色。」自由是在具體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上湧現出來的,因此跟特定社會的脈絡與肌理息息相關,各類制度如果不能公義平等,則自由將無由著根。
霍布豪斯所謂的制度上的公義,包括了「公民自由」(法治與司法平等),「財政自由」(賦稅合理)、「人身自由」(思想、宗教自由)、「社會自由」(階級流動與性別平等)、「經濟自由」(自由貿易、合理勞資關係與勞動環境)、「家庭自由」(家庭內的平等與兒童的保護)、「地方自由、種族自由和民族自由」(種族平等與民族自決或包容)、「國際自由」(和平主義)與「政治自由和人民主權」(負責任的公民與合理的人民主權行使方式)。
對霍布豪斯來說,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素乃是這樣的信念:社會應該讓個人可以培養出自我管理的能力(不論這稱為「個性」personality、「意志」will或是「自我控制」self-control),自發性地引導自己的生活,以便能自我成長,也可與他人和睦相處。一個真正的社會應當建立在每個人都擁有「自我引導能力」(the self-directing power of personality)這個基礎上,而因為這種能力是如此的重要,無論我們投入多少氣力與花多少代價去建立它,都是值得的。
這種對於自由的看法,來自於對於人類「個性」(personality)的理解。霍布豪斯認為,一個人的「個性」是獨立而不斷成長發展、「鮮活、有生命力」的東西,它可以被禁錮終結掉,卻不能被製造模塑出來。「不能將其打碎了又重新補好,但能置於使其蓬勃發展的條件之下」。「或者,個性如果有病,也可以創造適合條件,使其透過本身的復原力而痊癒」。自由的基礎是「不斷成長」這個觀念!生命是學習,「但是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一個人真正學到的東西是他所吸收的東西,而他所吸收的東西則賴於他本人對周圍環境所花的力量來決定」。一個理想的社會,就是每個人時刻「學習」、「成長」,成為自主而理性的個體。
自由,因此不是指個人的權利,而是建構一個社會所需之要素。它不是指別人對我們的「不侵犯」,而是指別人需對我們可作為一個「理性行為者」的尊重。因此,所謂自由不是獨善其身、無視犯罪或是罔顧錯謬的存在,而是必須要將犯罪者(或是因無知而犯錯者)視為有理性能力可以接受真理、分辨是非者,所以要導引他們改過遷善,而不是加以打擊懲處。因此自由的法則乃是讓每個人都能實現其理性。讓所有人都能訴諸「理性」(reason)、發揮「想像力」(imagination)與凝聚「社會情感」(social feeling),除此以外社會不會進步。
也就是說,社會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在於許多理性自律的個人的連結;若沒有這個基礎,社會將無法穩固和諧,遑論持續發展。讓每個人的理性可以發揚,而成為個人自律的根基,是一個社會須要做的,也因此,社會須要有自由這個東西,使人「自由」地發展個性與理性,以便實現社會道德。這樣的觀念,很不同於將自由視為是「個人不得被侵犯的權利」。二十世紀時英國思想家柏林(Isaiah Berlin)曾將自由區分為「積極」(positive)與「消極」(negative)自由,而這大概就是較為接近積極自由的意涵。
也因為霍布豪斯對自由的看法是如此,所以他在處理個人自由對抗國家權威這個古老問題時,他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自由主義思想昂揚昌盛的時代,把兩者間關係作出「辯證式」的解釋。他認為國家要保護個人在思想、精神、身體、財產方面的自由,但是個人也對這個社會與國家負有維護其文明發展與關注公共事務、提升共同福祉的道德義務。換句話說,國家所保護的個人,就是回過頭來保護國家的人;個人如果在某個社會之內成就了自由與理性的生活,他就必須飲水思源,貢獻其心智與能力於這個社會的公共事務或是福祉,讓這個社會可以持續地、更完善地照顧下一代的個人。在他的自由主義中,權利與義務、個人與社會,是一體的兩面,互相定義。這種辯證的視野,就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偏重於「消極自由」或是「自由放任」(libertarian)的「保護個人」意涵。
當然,他會有這樣的自由觀,一定是受到了人類群體生活之「有機」、「和諧」與「共同福祉」這些觀念的影響。這些觀念的背後,應該有著一個「生物學」的概念,就是社會──與個人一樣──也是「生命體」,社會也會進化或是退化。
雖然他的社會自由主義與達爾文(Charles Darwin)及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同調,但是我們卻可以合理懷疑「發展」與「演化」這些觀念對他的影響。十九世紀末,自然科學與生物學等,對於社會理論的啟發是明顯的(其實到今日亦然,結構功能論、系統理論、控制論等都影響社會理論)。「天賦人權」當初本來是洛克這些理論家用來抗衡專制王權與君權神授的概念,充滿了神學的意涵,也帶出了「財產權神聖」的觀念,因而成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神主牌。霍布豪斯等「社會自由主義」理論家,卻加入了社會學、生物學等這些近代的觀念,來構思一個理想社會的運作方式,他們捍衛「天賦人權」概念,卻不被它帶入「自由放任」與「最小政府」的框架內,這可謂是近代社會哲學的一個新典範。古典自由主義是「天賦人權」概念的合理演繹,順其道而行的「自然」結果;而「社會自由主義」卻圖謀在人文社會的現實環境下實現「天賦人權」的目標,因此將此概念賦予新義──經由對個人與社會之本質重新詮釋。所以說,這個新典範在方法上是「社會的」、「演化的」而非「自然」的,它先天上帶著科際整合的特質與人文化成的氣味。前一代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方法論視野如果算是「平面的」,那他們大概可稱為是「立體的」。霍布豪斯的這種理論創新可能不只歸功於他個人在學理與實踐上都極富於經驗;因他所處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文化氛圍是活躍、創新與追求新知的,所以我們可能也要注意發生在他身上的類似「知識社會學」式的影響。
有機的社會,理性自律的個人──霍布豪斯的社會自由主義
英國社會理論家霍布豪斯早生了一百年,否則他的思想在今日應是顯學吧?大家把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歸類為「社會自由主義」(或譯自由社會主義)(Social Liberalism),其實就是「福利國家」政治的先驅。今日我們都已知道,古典自由主義因為立基於原子化的個人與私有財產權至上這兩個原則,其「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哲學與最小政府的治理方式,會造成社會極大的不平等;而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進行試驗的歷史,也證明了國家統制經濟的不可行。因此,約莫從半個多世紀前開始,人類彷彿摸索到了一條中間又務實的道路,那就是打造一個「功能性政府」以適度介入財產重分配與照顧弱勢,這就是「福利國家」。霍布豪斯與和他理念相近的一些前後輩,正是這種制度背後精神之創建者。
近代以降,英國在急遽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的進程中,造就了進步、財富與繁榮,但也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以及社會學的興起),例如勞工處境的艱辛與財富分配的不公。但隨著選舉權的擴散與海外市場的擴大,這些問題又引發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快速變化。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中,從約翰‧彌爾(J. S. Mill)開始,致力修正古典自由主義一切任由「自由市場」來調節、國家不加干預的主張,提倡平等、社會公義與保護弱勢,格林(T. H. Green)繼之而且更加偏向了社會主義的立場,他們兩人都對於霍布豪斯影響很大。於是這三人形成了所謂英國社會自由主義傳統的早期骨幹。在近世政治思想的發展演進歷史上,英國是個奇妙的國家:它不但是自由主義的誕生地,而馬克思的《資本論》泰半也在倫敦完成,現在綜合了前兩者價值關懷的折衷路線──社會自由主義,亦在英國首先醞釀出來;「社會民主」這種現在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東西,就是在英國政治舞台上演化出來的(我們可以想想費邊社的例子),顯然英國是個兼容並蓄的地方。也因為社會民主與福利國家思想的衝擊,英國得以克服若干在快速工業化下產生的社會失調現象,順利地從傳統社會轉型為高度發達工業化國家。
霍布豪斯理想中的自由主義是如何的呢?這就首先要看他是怎樣理解「社會」這個東西。他成長於十九世紀末葉,受到當時開始出現的社會學影響很大;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自由主義思想乃立基於哲學的進路來解釋個人自由在群體社會中的意涵,但他卻採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一個有機體,不斷地演化,而個人在這個有機體中也持續成長與發展。於是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就是緊密而動態的:社會的本質決定個人的幸福,而個人的素質也決定社會的體質。社會需要和諧,個人的精神才能發展,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自由。所以霍布豪斯首先是個自由主義者。但是社會要和諧,「原子化個人式的自由主義立場」是無法使其達成的,這是因為完全的競爭,使得平等不易。霍布豪斯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他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自由,他認為自由是一個「社會性因素」,不是那個完全附著於個人生命的所謂「天賦人權」概念即能包涵之:自由關心的同時是個人、家庭和國家。也就是說,「民主政治不是單單建立在個人的權利或是私人利益上面的……民主政治同樣也建立在個人作為社會一員的職責上。它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共同意志上,同時囑咐每一個聰明的成年人扮演一個角色。」自由是在具體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上湧現出來的,因此跟特定社會的脈絡與肌理息息相關,各類制度如果不能公義平等,則自由將無由著根。
霍布豪斯所謂的制度上的公義,包括了「公民自由」(法治與司法平等),「財政自由」(賦稅合理)、「人身自由」(思想、宗教自由)、「社會自由」(階級流動與性別平等)、「經濟自由」(自由貿易、合理勞資關係與勞動環境)、「家庭自由」(家庭內的平等與兒童的保護)、「地方自由、種族自由和民族自由」(種族平等與民族自決或包容)、「國際自由」(和平主義)與「政治自由和人民主權」(負責任的公民與合理的人民主權行使方式)。
對霍布豪斯來說,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素乃是這樣的信念:社會應該讓個人可以培養出自我管理的能力(不論這稱為「個性」personality、「意志」will或是「自我控制」self-control),自發性地引導自己的生活,以便能自我成長,也可與他人和睦相處。一個真正的社會應當建立在每個人都擁有「自我引導能力」(the self-directing power of personality)這個基礎上,而因為這種能力是如此的重要,無論我們投入多少氣力與花多少代價去建立它,都是值得的。
這種對於自由的看法,來自於對於人類「個性」(personality)的理解。霍布豪斯認為,一個人的「個性」是獨立而不斷成長發展、「鮮活、有生命力」的東西,它可以被禁錮終結掉,卻不能被製造模塑出來。「不能將其打碎了又重新補好,但能置於使其蓬勃發展的條件之下」。「或者,個性如果有病,也可以創造適合條件,使其透過本身的復原力而痊癒」。自由的基礎是「不斷成長」這個觀念!生命是學習,「但是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一個人真正學到的東西是他所吸收的東西,而他所吸收的東西則賴於他本人對周圍環境所花的力量來決定」。一個理想的社會,就是每個人時刻「學習」、「成長」,成為自主而理性的個體。
自由,因此不是指個人的權利,而是建構一個社會所需之要素。它不是指別人對我們的「不侵犯」,而是指別人需對我們可作為一個「理性行為者」的尊重。因此,所謂自由不是獨善其身、無視犯罪或是罔顧錯謬的存在,而是必須要將犯罪者(或是因無知而犯錯者)視為有理性能力可以接受真理、分辨是非者,所以要導引他們改過遷善,而不是加以打擊懲處。因此自由的法則乃是讓每個人都能實現其理性。讓所有人都能訴諸「理性」(reason)、發揮「想像力」(imagination)與凝聚「社會情感」(social feeling),除此以外社會不會進步。
也就是說,社會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在於許多理性自律的個人的連結;若沒有這個基礎,社會將無法穩固和諧,遑論持續發展。讓每個人的理性可以發揚,而成為個人自律的根基,是一個社會須要做的,也因此,社會須要有自由這個東西,使人「自由」地發展個性與理性,以便實現社會道德。這樣的觀念,很不同於將自由視為是「個人不得被侵犯的權利」。二十世紀時英國思想家柏林(Isaiah Berlin)曾將自由區分為「積極」(positive)與「消極」(negative)自由,而這大概就是較為接近積極自由的意涵。
也因為霍布豪斯對自由的看法是如此,所以他在處理個人自由對抗國家權威這個古老問題時,他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自由主義思想昂揚昌盛的時代,把兩者間關係作出「辯證式」的解釋。他認為國家要保護個人在思想、精神、身體、財產方面的自由,但是個人也對這個社會與國家負有維護其文明發展與關注公共事務、提升共同福祉的道德義務。換句話說,國家所保護的個人,就是回過頭來保護國家的人;個人如果在某個社會之內成就了自由與理性的生活,他就必須飲水思源,貢獻其心智與能力於這個社會的公共事務或是福祉,讓這個社會可以持續地、更完善地照顧下一代的個人。在他的自由主義中,權利與義務、個人與社會,是一體的兩面,互相定義。這種辯證的視野,就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偏重於「消極自由」或是「自由放任」(libertarian)的「保護個人」意涵。
當然,他會有這樣的自由觀,一定是受到了人類群體生活之「有機」、「和諧」與「共同福祉」這些觀念的影響。這些觀念的背後,應該有著一個「生物學」的概念,就是社會──與個人一樣──也是「生命體」,社會也會進化或是退化。
雖然他的社會自由主義與達爾文(Charles Darwin)及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同調,但是我們卻可以合理懷疑「發展」與「演化」這些觀念對他的影響。十九世紀末,自然科學與生物學等,對於社會理論的啟發是明顯的(其實到今日亦然,結構功能論、系統理論、控制論等都影響社會理論)。「天賦人權」當初本來是洛克這些理論家用來抗衡專制王權與君權神授的概念,充滿了神學的意涵,也帶出了「財產權神聖」的觀念,因而成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神主牌。霍布豪斯等「社會自由主義」理論家,卻加入了社會學、生物學等這些近代的觀念,來構思一個理想社會的運作方式,他們捍衛「天賦人權」概念,卻不被它帶入「自由放任」與「最小政府」的框架內,這可謂是近代社會哲學的一個新典範。古典自由主義是「天賦人權」概念的合理演繹,順其道而行的「自然」結果;而「社會自由主義」卻圖謀在人文社會的現實環境下實現「天賦人權」的目標,因此將此概念賦予新義──經由對個人與社會之本質重新詮釋。所以說,這個新典範在方法上是「社會的」、「演化的」而非「自然」的,它先天上帶著科際整合的特質與人文化成的氣味。前一代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方法論視野如果算是「平面的」,那他們大概可稱為是「立體的」。霍布豪斯的這種理論創新可能不只歸功於他個人在學理與實踐上都極富於經驗;因他所處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文化氛圍是活躍、創新與追求新知的,所以我們可能也要注意發生在他身上的類似「知識社會學」式的影響。
試閱
第一章 在自由主義以前
現代國家是一種具獨一無二文化的特殊產物。但是這種產物仍在製造之中,一部分製造過程乃是社會秩序新舊原則之間的鬥爭。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新原則,但是要了解新原則,就必須先對舊原則作一回顧。我們必須了解舊的社會結構是怎樣的,而舊的社會結構,如我將說明的,主要在自由主義思想的鼓舞下,正在緩慢而穩當地被公民國家此一新的組織所取代。舊的結構本身絕對不是原始的。什麼叫真正原始是很難認定的。但是有一點十分清楚。無論什麼時候,人總是生活在社會裡,每一種社會組織都以親屬關係和簡單的鄰居關係為基礎。在最簡單的社會裡,這些關係—可能被宗教或其他信仰所加強和擴展—也許是唯一有重要意義的關係。血統的「經」和通婚的「緯」織成了一張網,從這張網當中產生了許多小而粗糙但卻緊密的團體。但是親屬關係和鄰居關係只在小範圍內才起作用。地方集團、家族或村社往往是朝氣蓬勃的生活中心,較大的部落聚集體卻很難達到真正的社會團結和政治團結,除非以軍事組織為基礎。但是軍事組織既可以把一個部落聯合起來,同樣也可以使其他部落處於屈從地位,從而以原始生活中最寶貴的東西為代價,建立一個更大同時更有秩序的社會。這樣一種秩序一旦建立以後,當然並不以赤裸裸的武力為基礎。統治者們開始擁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這可能因為他們是神或神的後代,也可能因為他們受到全體祭司的祝福和支持。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他們不僅有權掌握人們的肉體,而且有權掌握人們的精神。他們是上帝任命的,因為各種聖職都由他們授派。這樣的政府不一定與百姓水火不容,也不一定對百姓漠不關心。但它主要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就它影響人民生活而言,它按照它自以為明智並對它有利的原則為人民規定義務,例如服兵役、納貢、服從法令乃至新的法律。某一法理學派認為法律是上級對下級發出的命令,並以懲罰制裁為後盾,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但是,儘管這對一般法律來說是不正確的,用來形容那一特定社會階段卻大致是正確的,這個階段我們可以很簡單地稱之為權力主義時期。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以及在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存在著的就只有上面所區分的這兩種社會組織。當然,兩種社會組織本身在細微處可以有許多變異,但是往這些變異的深處看,就只看到這兩種交替出現的類型。一種是小的親屬集團,本身往往非常強勁,但是在採取一致行動方面卻軟弱無力。另一種是較大的社會,其幅員大小和文明程度從一個小的黑人王國到龐大的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各不相同,它們以某種軍事力量和宗教或準宗教信仰的聯合為基礎,我們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權力原則(principle of authority)。在文明較低階段,照例只有用這個方法鎮壓敵對民族的抗爭,在共同的敵人前維護邊界,或建立外部秩序。不實行權力統治,就只能重新回到相對較原始的無政府狀態。
但是古代也出現了另外一種方法。古希臘(Greece)和義大利(Italy)的城邦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它在幾個方面與氏族和村社不同。第一,城邦包含許多氏族和村社,其起源也許在於幾個氏族─不是在征服而是在比較平等的聯盟基礎上合併起來的。雖然城邦與一個古代帝國或一個現代國家相比顯得很小,但是比一個原始的宗族卻大得多。城邦的生活更加複雜多變。它容許個人有更多的自由發揮機會,在它發展的過程中,確實也鎮壓了一些老的氏族組織,並以新的地理的或其他方面的劃分來代替。事實上,城邦不是以親屬關係為基礎,而是以公民權利(civil right)為基礎,就是這一點使它不僅有別於公社,而且也有別於東方的君主國。它所承認並賴以生存的法律不是上級政府對下屬百姓發布的命令。相反地,政府本身也服從法律,法律是城邦的生命,受到全體自由公民的自願支持。此意謂著,城邦是一個自由人的共同體。從集體意義上說,其公民是沒有主人的。他們自己統治自己,只服從一些生活中的規章,這些規章是古時候傳下來的,由於歷代人忠心耿耿地執行而具有力量。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有些最令我們傷腦筋的問題是以一種非常簡單的形式提出的。尤其個人與共同體的關係是緊密、直接和自然的。他們的利益顯然是結合在一起的。除非每個人都盡到自己的義務,否則城邦就很容易被破壞,並使人民遭到奴役。除非城邦為人民著想,否則它就很容易衰亡。更加重要的是,當時沒有教會和國家的對立,沒有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間的分歧,沒有宗教和非宗教之間的分歧,來致使公民無法盡到效忠義務,使內在良心之力反對國家的義務。要把這樣一個共同體形容為人們由於希望生活得好而聯合起來,不必藉助哲學的想像,只要相當簡單和自然地說明事實就行了。我們如今正在致力恢復的理想,在古希臘的生活條件下自然而然地就實現了。
另一方面,這個簡單的聯合有極其嚴重的局限性,最終導致城邦制崩潰。聯合生活的責任特權不是奠基於人類個性的權利,而是奠基於公民身分的權利,而公民身分從來不跟著社會一同擴展。居民中包括奴隸或農奴,在許多城邦中有大批原先被征服的人的後代,他們本身是自由的,但被排斥在統治圈子之外。儘管社會狀況相當單純,城邦卻經常被派系糾紛分裂—一部分也許是老的氏族組織遺留下來的影響,一部分也許是財富的增長和新的階級劃分的結果。派系的弊病因城邦處理各城邦間關係問題失當而變本加厲。希臘城邦堅持其自治權,雖然本來可能解決問題的聯邦原則最終被採用,但是在希臘歷史上為時已晚,挽救不了城邦的命運。
羅馬(Rome)的建設性天才想出了一種不同的方法來應付日益擴大的關係中所包含的政治問題。羅馬公民身分被擴大到包括整個義大利,後來又擴大到包括地中海(Mediterranean)流域的全部自由人。但是這種擴大對於城邦的自治甚至更為致命。義大利人無法在羅馬廣場(Rome Forum)或馬斯平原集會以選舉執政官和通過法律,公民身分擴大得愈廣泛,對政治目的也愈無價值。事實上,羅馬的歷史可以當作一個絕好的例證,它說明,要建立一個大帝國,只能以依靠軍事力量的個人獨裁為基礎,並以有效的官僚機制來維持和平與秩序,除此之外,要在任何其他基礎上建立這個帝國,是何等的困難。在這個巨大的機構中,軍隊是權力的中心,或者不如說,每支駐紮在某個遙遠邊境基地上的軍隊都是一個潛在的權力中心。一個早已公開的「帝國的祕密」是:羅馬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立一個皇帝,雖然當皇帝的人始終有點神聖,法學家也念念不忘皇帝體現人民意志這一理論,事實卻是:皇帝是由一支強大的軍隊選中的,由戰神批准,只要能夠鎮壓任何敵對的覬覦王位者,就能保持權力。帝國在持續的戰爭中迅速解體,這倒不是因為邊境內外都存在著野蠻暴虐。為了恢復秩序,中央和地方權力之間的妥協必不可少,封建主就成了一地之君,效忠於一位遠方的君主,忠誠程度則視情況而定。在這同時,由於秩序普遍混亂,西歐大部分人民失去了自由,一來是由於被征服,二來是由於在亂世必須找到一個保護者。中世紀的社會結構於是便採取了我們稱之為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的等級形式。在這個澈底應用權力原則的過程中,每個人在理論上都有他的主人。農奴聽命於地主,地主聽命於大莊園主,大莊園主聽命於國王,國王聽命於皇帝,皇帝由教皇加冕,教皇聽命於聖彼得(St. Peter)。從宇宙的統治者到最卑微的農奴,門第的鏈子算是完成了。【1】但是在這個體系裡,工商業的興起提出了新的自由中心。人們在城市裡重新學習有關聯合起來進行共同防禦和管理共同利益的課程,這些城市從貴族或國王那裡獲得了權利特許狀,甚至在歐洲大陸成功地建立起完全的獨立。英國(England)從一○六六年被威廉征服後,中央權力最為強大,但即便在英國,城市也由於許多原因變成了自治的共同體。城邦又重新誕生,隨之而來的是活動激增,文藝復興、古代學問重新發現、哲學和科學再生。
中世紀的城邦比古代的城邦優越,主要在於奴隸制度在其生存中不是一個重要因素。相反地,透過歡迎逃亡的農奴,為其自由辯護,大大促成了較溫和的奴役制的滅亡。但是,和古代的城邦一樣,它被內部派系鬥爭嚴重地、永久性地削弱,而且和古代城邦一樣,其成員的特權不是奠基於人類個性的權利,而是以公民的責任為基礎。城市的自由只限於「特許權」,亦即通過特許狀獲得的公司權利以及從國王或封建主那裡爭取到的權利,其中包括行會和同業公會的權利,這些權利只有作為這些集體成員的人們才能享受。但是城邦的真正弱點依然是它的孤立。它僅僅是一代又一代變得愈益強大的封建社會邊界上(實際上是在邊界內)一個相對自由的小島。隨著交通的發達和生活藝術的提高,中央權力﹝尤其在法國(France)和英國﹞開始超過封建主。封建主的反抗和騷亂被鎮壓下去,到十五世紀末,龐大的、統一的國家(現代國家的基礎)已開始存在。它們的出現意味著社會秩序的擴大,在某些方面更意味著社會秩序的改進。在早期階段,它贊成公民自治,鎮壓地方無政府主義和封建特權。但是中央集權的發展最終是和公民獨立的精神不相容的,不利於國王及封建主之間早期的鬥爭為全體人民獲得的政治權利。
於是,我們進入了現代時期,這個時期的社會建立在一個絕對權力主義的基礎上。國王的權力至高無上,並傾向於專制獨裁。在國王以下,從大地主直至幹零活的工人,分成許多社會等級。這個時期較諸早期的社會有一點不同。金字塔的底部是一個至少擁有人身自由的階級。農奴制(Serfdom)在英國實際上已經消失,在法國大部分地方不是消亡了,就是削弱成為土地保有權的某些可憎的財產附帶權。另一方面,英國農民開始脫離土地,為這個國家日後將發生的社會問題奠定了基礎。
現代國家是從一種權力主義制度的基礎開始的,那種制度提出抗議,從宗教、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倫理道德種種方面提出抗議,這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歷史性開端。因此,自由主義最初是作為一種批判出現的,有時甚至作為一種破壞性的、革命性的批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它的主要作用是消極的。它的任務似乎是破壞而不是建設,是去除阻礙人類前進的障礙而不是指出積極的努力方向或製造文明的框架。它發現人類受到壓迫,立志要使其獲得自由。它發現人民在專制統治下呻吟,或國家正受到一個征服者的蹂躪,或工業受到社會特權阻撓或被賦稅摧殘,就提供救濟。它到處消除自上而下的壓力,砸爛桎梏,清除障礙。等破壞完成以後,它是不是也會致力於必要的重建?自由主義的本質到底是建設性的抑或僅僅是破壞性的?它是否具有永久性的意義?它是否表達了社會生活的某些重大真相,抑或只是西歐特殊環境所造成的暫時現象?它的任務是否已經完成,只須心安理得地把火炬交給一個更新的、更有建設性的原理,自己便功成身退,或者偶爾尋找一些更落後的地方來進行傳教工作?這些都在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之列。眼下,我們只須指出自由主義起源的環境,就足以解釋為什麼批判性和破壞性的工作占主要地位,而無須由此推斷出缺少最終的重建力。事實上,無論是藉助自由主義還是透過人類的保守本能,重建工作始終是和破壞工作同時進行的,而且將會一代比一代更加重要。現代國家,如我將要說明的,大大有助於使自由主義諸要素融會貫通,等我們懂得了這些要素,明白它們在何種程度上已獲得實現,我們就能更加地理解自由主義諸要素,並解答其永久性價值的問題。
註解
【1】這當然只是中世紀理論的一個面向,但是這個面向最接近於事實。在中世紀,在古典傳統的影響下,出現了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但是它的主要影響和重要性在於它被當作後來一種思想的起點。關於這整個問題,讀者可參閱吉爾克(Gierke)的《中世紀的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梅特蘭譯。
現代國家是一種具獨一無二文化的特殊產物。但是這種產物仍在製造之中,一部分製造過程乃是社會秩序新舊原則之間的鬥爭。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新原則,但是要了解新原則,就必須先對舊原則作一回顧。我們必須了解舊的社會結構是怎樣的,而舊的社會結構,如我將說明的,主要在自由主義思想的鼓舞下,正在緩慢而穩當地被公民國家此一新的組織所取代。舊的結構本身絕對不是原始的。什麼叫真正原始是很難認定的。但是有一點十分清楚。無論什麼時候,人總是生活在社會裡,每一種社會組織都以親屬關係和簡單的鄰居關係為基礎。在最簡單的社會裡,這些關係—可能被宗教或其他信仰所加強和擴展—也許是唯一有重要意義的關係。血統的「經」和通婚的「緯」織成了一張網,從這張網當中產生了許多小而粗糙但卻緊密的團體。但是親屬關係和鄰居關係只在小範圍內才起作用。地方集團、家族或村社往往是朝氣蓬勃的生活中心,較大的部落聚集體卻很難達到真正的社會團結和政治團結,除非以軍事組織為基礎。但是軍事組織既可以把一個部落聯合起來,同樣也可以使其他部落處於屈從地位,從而以原始生活中最寶貴的東西為代價,建立一個更大同時更有秩序的社會。這樣一種秩序一旦建立以後,當然並不以赤裸裸的武力為基礎。統治者們開始擁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這可能因為他們是神或神的後代,也可能因為他們受到全體祭司的祝福和支持。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他們不僅有權掌握人們的肉體,而且有權掌握人們的精神。他們是上帝任命的,因為各種聖職都由他們授派。這樣的政府不一定與百姓水火不容,也不一定對百姓漠不關心。但它主要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就它影響人民生活而言,它按照它自以為明智並對它有利的原則為人民規定義務,例如服兵役、納貢、服從法令乃至新的法律。某一法理學派認為法律是上級對下級發出的命令,並以懲罰制裁為後盾,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但是,儘管這對一般法律來說是不正確的,用來形容那一特定社會階段卻大致是正確的,這個階段我們可以很簡單地稱之為權力主義時期。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以及在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存在著的就只有上面所區分的這兩種社會組織。當然,兩種社會組織本身在細微處可以有許多變異,但是往這些變異的深處看,就只看到這兩種交替出現的類型。一種是小的親屬集團,本身往往非常強勁,但是在採取一致行動方面卻軟弱無力。另一種是較大的社會,其幅員大小和文明程度從一個小的黑人王國到龐大的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各不相同,它們以某種軍事力量和宗教或準宗教信仰的聯合為基礎,我們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權力原則(principle of authority)。在文明較低階段,照例只有用這個方法鎮壓敵對民族的抗爭,在共同的敵人前維護邊界,或建立外部秩序。不實行權力統治,就只能重新回到相對較原始的無政府狀態。
但是古代也出現了另外一種方法。古希臘(Greece)和義大利(Italy)的城邦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它在幾個方面與氏族和村社不同。第一,城邦包含許多氏族和村社,其起源也許在於幾個氏族─不是在征服而是在比較平等的聯盟基礎上合併起來的。雖然城邦與一個古代帝國或一個現代國家相比顯得很小,但是比一個原始的宗族卻大得多。城邦的生活更加複雜多變。它容許個人有更多的自由發揮機會,在它發展的過程中,確實也鎮壓了一些老的氏族組織,並以新的地理的或其他方面的劃分來代替。事實上,城邦不是以親屬關係為基礎,而是以公民權利(civil right)為基礎,就是這一點使它不僅有別於公社,而且也有別於東方的君主國。它所承認並賴以生存的法律不是上級政府對下屬百姓發布的命令。相反地,政府本身也服從法律,法律是城邦的生命,受到全體自由公民的自願支持。此意謂著,城邦是一個自由人的共同體。從集體意義上說,其公民是沒有主人的。他們自己統治自己,只服從一些生活中的規章,這些規章是古時候傳下來的,由於歷代人忠心耿耿地執行而具有力量。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有些最令我們傷腦筋的問題是以一種非常簡單的形式提出的。尤其個人與共同體的關係是緊密、直接和自然的。他們的利益顯然是結合在一起的。除非每個人都盡到自己的義務,否則城邦就很容易被破壞,並使人民遭到奴役。除非城邦為人民著想,否則它就很容易衰亡。更加重要的是,當時沒有教會和國家的對立,沒有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間的分歧,沒有宗教和非宗教之間的分歧,來致使公民無法盡到效忠義務,使內在良心之力反對國家的義務。要把這樣一個共同體形容為人們由於希望生活得好而聯合起來,不必藉助哲學的想像,只要相當簡單和自然地說明事實就行了。我們如今正在致力恢復的理想,在古希臘的生活條件下自然而然地就實現了。
另一方面,這個簡單的聯合有極其嚴重的局限性,最終導致城邦制崩潰。聯合生活的責任特權不是奠基於人類個性的權利,而是奠基於公民身分的權利,而公民身分從來不跟著社會一同擴展。居民中包括奴隸或農奴,在許多城邦中有大批原先被征服的人的後代,他們本身是自由的,但被排斥在統治圈子之外。儘管社會狀況相當單純,城邦卻經常被派系糾紛分裂—一部分也許是老的氏族組織遺留下來的影響,一部分也許是財富的增長和新的階級劃分的結果。派系的弊病因城邦處理各城邦間關係問題失當而變本加厲。希臘城邦堅持其自治權,雖然本來可能解決問題的聯邦原則最終被採用,但是在希臘歷史上為時已晚,挽救不了城邦的命運。
羅馬(Rome)的建設性天才想出了一種不同的方法來應付日益擴大的關係中所包含的政治問題。羅馬公民身分被擴大到包括整個義大利,後來又擴大到包括地中海(Mediterranean)流域的全部自由人。但是這種擴大對於城邦的自治甚至更為致命。義大利人無法在羅馬廣場(Rome Forum)或馬斯平原集會以選舉執政官和通過法律,公民身分擴大得愈廣泛,對政治目的也愈無價值。事實上,羅馬的歷史可以當作一個絕好的例證,它說明,要建立一個大帝國,只能以依靠軍事力量的個人獨裁為基礎,並以有效的官僚機制來維持和平與秩序,除此之外,要在任何其他基礎上建立這個帝國,是何等的困難。在這個巨大的機構中,軍隊是權力的中心,或者不如說,每支駐紮在某個遙遠邊境基地上的軍隊都是一個潛在的權力中心。一個早已公開的「帝國的祕密」是:羅馬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立一個皇帝,雖然當皇帝的人始終有點神聖,法學家也念念不忘皇帝體現人民意志這一理論,事實卻是:皇帝是由一支強大的軍隊選中的,由戰神批准,只要能夠鎮壓任何敵對的覬覦王位者,就能保持權力。帝國在持續的戰爭中迅速解體,這倒不是因為邊境內外都存在著野蠻暴虐。為了恢復秩序,中央和地方權力之間的妥協必不可少,封建主就成了一地之君,效忠於一位遠方的君主,忠誠程度則視情況而定。在這同時,由於秩序普遍混亂,西歐大部分人民失去了自由,一來是由於被征服,二來是由於在亂世必須找到一個保護者。中世紀的社會結構於是便採取了我們稱之為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的等級形式。在這個澈底應用權力原則的過程中,每個人在理論上都有他的主人。農奴聽命於地主,地主聽命於大莊園主,大莊園主聽命於國王,國王聽命於皇帝,皇帝由教皇加冕,教皇聽命於聖彼得(St. Peter)。從宇宙的統治者到最卑微的農奴,門第的鏈子算是完成了。【1】但是在這個體系裡,工商業的興起提出了新的自由中心。人們在城市裡重新學習有關聯合起來進行共同防禦和管理共同利益的課程,這些城市從貴族或國王那裡獲得了權利特許狀,甚至在歐洲大陸成功地建立起完全的獨立。英國(England)從一○六六年被威廉征服後,中央權力最為強大,但即便在英國,城市也由於許多原因變成了自治的共同體。城邦又重新誕生,隨之而來的是活動激增,文藝復興、古代學問重新發現、哲學和科學再生。
中世紀的城邦比古代的城邦優越,主要在於奴隸制度在其生存中不是一個重要因素。相反地,透過歡迎逃亡的農奴,為其自由辯護,大大促成了較溫和的奴役制的滅亡。但是,和古代的城邦一樣,它被內部派系鬥爭嚴重地、永久性地削弱,而且和古代城邦一樣,其成員的特權不是奠基於人類個性的權利,而是以公民的責任為基礎。城市的自由只限於「特許權」,亦即通過特許狀獲得的公司權利以及從國王或封建主那裡爭取到的權利,其中包括行會和同業公會的權利,這些權利只有作為這些集體成員的人們才能享受。但是城邦的真正弱點依然是它的孤立。它僅僅是一代又一代變得愈益強大的封建社會邊界上(實際上是在邊界內)一個相對自由的小島。隨著交通的發達和生活藝術的提高,中央權力﹝尤其在法國(France)和英國﹞開始超過封建主。封建主的反抗和騷亂被鎮壓下去,到十五世紀末,龐大的、統一的國家(現代國家的基礎)已開始存在。它們的出現意味著社會秩序的擴大,在某些方面更意味著社會秩序的改進。在早期階段,它贊成公民自治,鎮壓地方無政府主義和封建特權。但是中央集權的發展最終是和公民獨立的精神不相容的,不利於國王及封建主之間早期的鬥爭為全體人民獲得的政治權利。
於是,我們進入了現代時期,這個時期的社會建立在一個絕對權力主義的基礎上。國王的權力至高無上,並傾向於專制獨裁。在國王以下,從大地主直至幹零活的工人,分成許多社會等級。這個時期較諸早期的社會有一點不同。金字塔的底部是一個至少擁有人身自由的階級。農奴制(Serfdom)在英國實際上已經消失,在法國大部分地方不是消亡了,就是削弱成為土地保有權的某些可憎的財產附帶權。另一方面,英國農民開始脫離土地,為這個國家日後將發生的社會問題奠定了基礎。
現代國家是從一種權力主義制度的基礎開始的,那種制度提出抗議,從宗教、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倫理道德種種方面提出抗議,這就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歷史性開端。因此,自由主義最初是作為一種批判出現的,有時甚至作為一種破壞性的、革命性的批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它的主要作用是消極的。它的任務似乎是破壞而不是建設,是去除阻礙人類前進的障礙而不是指出積極的努力方向或製造文明的框架。它發現人類受到壓迫,立志要使其獲得自由。它發現人民在專制統治下呻吟,或國家正受到一個征服者的蹂躪,或工業受到社會特權阻撓或被賦稅摧殘,就提供救濟。它到處消除自上而下的壓力,砸爛桎梏,清除障礙。等破壞完成以後,它是不是也會致力於必要的重建?自由主義的本質到底是建設性的抑或僅僅是破壞性的?它是否具有永久性的意義?它是否表達了社會生活的某些重大真相,抑或只是西歐特殊環境所造成的暫時現象?它的任務是否已經完成,只須心安理得地把火炬交給一個更新的、更有建設性的原理,自己便功成身退,或者偶爾尋找一些更落後的地方來進行傳教工作?這些都在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之列。眼下,我們只須指出自由主義起源的環境,就足以解釋為什麼批判性和破壞性的工作占主要地位,而無須由此推斷出缺少最終的重建力。事實上,無論是藉助自由主義還是透過人類的保守本能,重建工作始終是和破壞工作同時進行的,而且將會一代比一代更加重要。現代國家,如我將要說明的,大大有助於使自由主義諸要素融會貫通,等我們懂得了這些要素,明白它們在何種程度上已獲得實現,我們就能更加地理解自由主義諸要素,並解答其永久性價值的問題。
註解
【1】這當然只是中世紀理論的一個面向,但是這個面向最接近於事實。在中世紀,在古典傳統的影響下,出現了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但是它的主要影響和重要性在於它被當作後來一種思想的起點。關於這整個問題,讀者可參閱吉爾克(Gierke)的《中世紀的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梅特蘭譯。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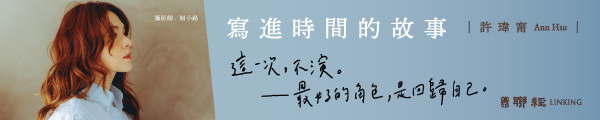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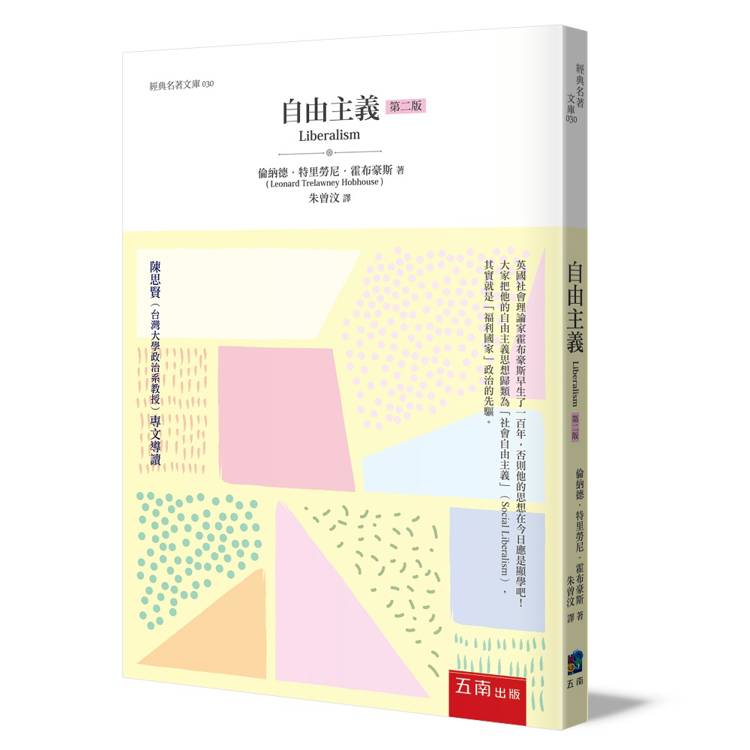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