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者的美學:戰國日本 2
從參謀、軍師、女戰將、佐臣、智將到一方之霸,以月襯日的書寫手法貫穿最詭譎多變的時代!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第一手的史料研究+綜合各家說法的獨到觀察評論
深入淺出的人物故事娓娓道來+百餘幅古圖今照參酌釋義
從參謀、軍師、女戰將、佐臣、智將到一方之霸,
以月襯日的書寫手法貫穿最詭譎多變的時代!
勝者因勝而失去鳥語花香的羊腸小徑
敗者因敗而探得桃紅柳綠的康莊大道
舞台上的歷史是御用劇本家之作,舞台下的歷史則是後世言論家的競技場。
當朝的勝者,不一定能成為歷史的贏家;歷史的敗者,也未必不能流芳百世。
歷史,其實是一場知性推理遊戲!
許多知名事件,交織其中的人物角色、來龍去脈,大家耳熟能詳,卻找不到所謂的「真相」!結果早已凝凍,但其過程、因素卻隱藏著無數種可能性。如何截取善用有限的史料,編織出具說服力的解釋,正是歷史作家的挑戰。
在這場競技中同台角力的不只作家彼此,作者與讀者間也進行較量。知識存檔的版本與數量,決定享用歷史的愉快度;知道越多越是沈迷,正是歷史讀物的魅力。
擅長說故事介紹日本文化歷史的茂呂美耶(Miya),受到戰國史上七組人物驅使,試圖重新解凍,為環繞他們身邊的懸案新下註腳。從世局成敗論,他們都不是風光壓人的勝者;但從大量一手史料挖掘爬梳推敲出有血有肉的立體面貌,卻教人同悲共喜,掩卷深思。
繼暢銷作《戰國日本》之後,Miya此次推出饒富趣味的進階加強版。無論熟悉日本戰國與否,都能從此書中領略到析讀歷史的無上妙趣!
深入淺出的人物故事娓娓道來+百餘幅古圖今照參酌釋義
從參謀、軍師、女戰將、佐臣、智將到一方之霸,
以月襯日的書寫手法貫穿最詭譎多變的時代!
勝者因勝而失去鳥語花香的羊腸小徑
敗者因敗而探得桃紅柳綠的康莊大道
舞台上的歷史是御用劇本家之作,舞台下的歷史則是後世言論家的競技場。
當朝的勝者,不一定能成為歷史的贏家;歷史的敗者,也未必不能流芳百世。
歷史,其實是一場知性推理遊戲!
許多知名事件,交織其中的人物角色、來龍去脈,大家耳熟能詳,卻找不到所謂的「真相」!結果早已凝凍,但其過程、因素卻隱藏著無數種可能性。如何截取善用有限的史料,編織出具說服力的解釋,正是歷史作家的挑戰。
在這場競技中同台角力的不只作家彼此,作者與讀者間也進行較量。知識存檔的版本與數量,決定享用歷史的愉快度;知道越多越是沈迷,正是歷史讀物的魅力。
擅長說故事介紹日本文化歷史的茂呂美耶(Miya),受到戰國史上七組人物驅使,試圖重新解凍,為環繞他們身邊的懸案新下註腳。從世局成敗論,他們都不是風光壓人的勝者;但從大量一手史料挖掘爬梳推敲出有血有肉的立體面貌,卻教人同悲共喜,掩卷深思。
繼暢銷作《戰國日本》之後,Miya此次推出饒富趣味的進階加強版。無論熟悉日本戰國與否,都能從此書中領略到析讀歷史的無上妙趣!
目錄
第1話 獨眼跛腳的燿星參謀
山本勘助
武田信玄身邊不能少的人物
第2話 如夢似幻的越後能臣
宇佐美定滿
上杉謙信的良師兼謀將
第3話 戰國時代的天才軍師
竹中半兵衛、黑田官兵衛
豐臣秀吉的左輔右弼智囊團
第4話 女中豪傑的東國戰華
甲斐姬
不讓鬚眉的關東第一美女
第5話 智勇兼備的義愛賢臣
直江兼續
與上杉景勝共譜最感人的君臣佳話
第6話 奧州軍團的獨眼飛龍
伊達政宗
予生也晚、無緣霸業的雪國戰將
第7話 誓死不二的悲劇智將
石田三成
為豐臣家拋頭顱的忠臣
山本勘助
武田信玄身邊不能少的人物
第2話 如夢似幻的越後能臣
宇佐美定滿
上杉謙信的良師兼謀將
第3話 戰國時代的天才軍師
竹中半兵衛、黑田官兵衛
豐臣秀吉的左輔右弼智囊團
第4話 女中豪傑的東國戰華
甲斐姬
不讓鬚眉的關東第一美女
第5話 智勇兼備的義愛賢臣
直江兼續
與上杉景勝共譜最感人的君臣佳話
第6話 奧州軍團的獨眼飛龍
伊達政宗
予生也晚、無緣霸業的雪國戰將
第7話 誓死不二的悲劇智將
石田三成
為豐臣家拋頭顱的忠臣
序/導讀
前言
歷史是知性推理遊戲
我想,大部分人在學生時代應該都不喜歡歷史課。我也是。想當年為了應付考試,為了死背那些歷史大事年表,真不知摔過幾次歷史課本。
那我到底自何時迷上歷史呢?這和我以前迷上現代推理小說有關。高中時代至三十五歲左右,我讀的小說幾乎全是現代推理小說。而且不限日本推理小說,英、美翻譯推理小說也不放過。
後來不知為何,我對現代推理小說不再感興趣。可能因為讀太多,反倒膩了;也可能因為時代變了,很難再找到「作家提供線索讓讀者解謎」的本格推理小說。不過,奇幻小說、恐怖小說、懸疑小說、時代小說、歷史小說之類的讀物卻始終百看不厭。畢竟上述小說中幾乎都有推理因素存在。
歷史小說中又有個「歷史推理」類別,小說內容主要描述歷史上某一起著名事件或懸案,而且幾乎所有讀者都知道小說中的主角以及事件的來龍去脈。但小說家應用各種現有的真實史料,有時再創造幾個虛構人物,讓真實與虛假混淆,以推理小說方式重新架構歷史事件,並進行考證,繼而展現自己對該歷史事件或懸案的觀點。這種歷史推理小說非常有趣。
倘若讓十位歷史推理小說家動筆寫同一起歷史懸案,真相可能就有十種。小說家從眾多史料中找出他們想要的蛛絲線索,再條條有理地將這些線索聯繫起來,最後演繹歸納出自己的結論。
讀者在事前當然已知道該歷史事件的結果。花錢買歷史推理小說的目的,主要是想看看小說家會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由果以溯因、如何從大眾已知的答案反求該案件的真相。
比如說,一加一等於二;但如果只給你一個答案「二」,讓你去填前面的數學公式,你是不是會興趣大增?畢竟答案是「二」的數學公式並非只有加法。
這大概正是我逐漸遠離現代推理小說,轉而迷上歷史推理小說的主因吧。
正如人死不能復生,歷史事件的結果永遠不變,但該事件的過程和真相卻有無數種可能性。這種遊戲不是很好玩嗎?
舉例來說,日本戰國時代的著名茶人千利休,因得罪了豐臣秀吉,被迫切腹自殺,這是不變的結果。但豐臣秀吉為何命千利休切腹呢?至今仍沒有人知道真正理由,連專家學者也眾說紛紜。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千利休都死了,幹嘛追查他為何切腹自殺的理由。這正是歷史推理迷願意掏腰包買歷史推理小說的原因。甲作家和乙作家從同樣史料中推理得出的真相絕對不一樣,十人十色,非常有趣。
只是,該如何判斷哪位作家對哪一起歷史事件的推理真相最具說服力,則全看讀者具有多少歷史知識存檔。也因此,歷史推理小說亦是小說家和歷史迷讀者之間的一種隱形知性競技遊戲。
追查某歷史事件時,我們不能只鎖定與該事件有關的人物與發生年代。例如有一對情侶在今年分手,我們能說那對情侶在今年某月因某事吵架,所以決定分手嗎?事情有這麼簡單嗎?分手的理由可能還要追溯到過去累積的種種因素,甚至牽涉到彼此的親人和朋友。
千利休被迫切腹的例子也一樣。為何天下人的豐臣秀吉會如此重懲一庶民身分的茶人?
我們若拋開豐臣秀吉和千利休的身分對比,只追索「茶人」這條線索,並仔細翻閱與茶道有關的史料書籍,便可以發現此事件和織田信長死於本能寺的事件有關。
按歷史結果看,率兵襲擊本能寺的當事人是明智光秀。但前一天夜晚,織田信長在本能寺舉辦茶會,接著變成酒會,最後是圍棋對弈。本能寺事件發生時,參與茶會的公卿、富商與茶人均自現場逃脫,並順手牽羊帶走織田信長珍藏的掛軸。
織田信長死於一五八二年,所有人都認為掛軸也在本能寺燒毀。
然而,八、九年後,千利休主辦的茶會中突然出現眾人認為早在本能寺燒毀的掛軸時,秀吉看到後作何感想呢?是不是會心生疑惑,重新暗地調查本能寺之變的幕後陰謀?即便千利休與本能寺之變無關,秀吉是否會懲一儆百,再不為人知地逐一處死相關茶人,順便滅掉當時財界富商和茶人聚集的自治都市?呢?
從「茶人」這條線索追查,會得出與一般說法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真相:
原來織田信長死在當時的財界人手上。
如此換個角度追查下去,歷史是不是就變成非常有趣的知性遊戲呢?
只是,讀者若不知道千利休是何人,亦不清楚織田信長是怎麼死的,這場遊戲就玩不起來。因此我才會說,歷史推理讀物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的隱形知性競技遊戲。
* * *
動筆寫這部書之前,我原本預計依循第一部《戰國日本》的構成,將篇目分為軍師、背叛、友情、親情、暗殺等幾大類,再以人物為主,闡述並推理日本戰國時代的各種懸案。不料,寫著寫著,最後竟變成七個人物。
主編要我寫一篇前言,說明為何選擇這些人物為主角的原因。
坦白說,並非我刻意選擇這些人物,而是寫完一篇後,腦中自然會浮出和上一篇文章有密切關係的人物。除了〈甲斐姬〉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其他人物均是一體關係,沒法分開。
既然以人物為主,我就不能輕描淡寫地只介紹他們的生平,至少要說明事件背景和當時的風俗習慣,並按歷史推理迷的慣例進行考證,最後總結出我的看法。
寫到最後,我才發覺原來我選了這七個人物。但我發誓,這七個人物不是我刻意挑出,而是他們自己跳出來要我寫的。
無奈字數有限,許多細節只能跳過。即便省略不少相關事件,我仍有點擔心對外國讀者來說,內容會不會太深入?畢竟對漢文圈讀者來說,這不是耳熟能詳的中國歷史,而是用中文寫成的外國歷史。
倘若讀者能咀嚼並消化這部書的內容,我便有信心繼續寫《戰國日本Ⅲ》。
請各位多多捧場並鼓勵,讓出版公司持續出版此系列的後續書。
歷史是知性推理遊戲
我想,大部分人在學生時代應該都不喜歡歷史課。我也是。想當年為了應付考試,為了死背那些歷史大事年表,真不知摔過幾次歷史課本。
那我到底自何時迷上歷史呢?這和我以前迷上現代推理小說有關。高中時代至三十五歲左右,我讀的小說幾乎全是現代推理小說。而且不限日本推理小說,英、美翻譯推理小說也不放過。
後來不知為何,我對現代推理小說不再感興趣。可能因為讀太多,反倒膩了;也可能因為時代變了,很難再找到「作家提供線索讓讀者解謎」的本格推理小說。不過,奇幻小說、恐怖小說、懸疑小說、時代小說、歷史小說之類的讀物卻始終百看不厭。畢竟上述小說中幾乎都有推理因素存在。
歷史小說中又有個「歷史推理」類別,小說內容主要描述歷史上某一起著名事件或懸案,而且幾乎所有讀者都知道小說中的主角以及事件的來龍去脈。但小說家應用各種現有的真實史料,有時再創造幾個虛構人物,讓真實與虛假混淆,以推理小說方式重新架構歷史事件,並進行考證,繼而展現自己對該歷史事件或懸案的觀點。這種歷史推理小說非常有趣。
倘若讓十位歷史推理小說家動筆寫同一起歷史懸案,真相可能就有十種。小說家從眾多史料中找出他們想要的蛛絲線索,再條條有理地將這些線索聯繫起來,最後演繹歸納出自己的結論。
讀者在事前當然已知道該歷史事件的結果。花錢買歷史推理小說的目的,主要是想看看小說家會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由果以溯因、如何從大眾已知的答案反求該案件的真相。
比如說,一加一等於二;但如果只給你一個答案「二」,讓你去填前面的數學公式,你是不是會興趣大增?畢竟答案是「二」的數學公式並非只有加法。
這大概正是我逐漸遠離現代推理小說,轉而迷上歷史推理小說的主因吧。
正如人死不能復生,歷史事件的結果永遠不變,但該事件的過程和真相卻有無數種可能性。這種遊戲不是很好玩嗎?
舉例來說,日本戰國時代的著名茶人千利休,因得罪了豐臣秀吉,被迫切腹自殺,這是不變的結果。但豐臣秀吉為何命千利休切腹呢?至今仍沒有人知道真正理由,連專家學者也眾說紛紜。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千利休都死了,幹嘛追查他為何切腹自殺的理由。這正是歷史推理迷願意掏腰包買歷史推理小說的原因。甲作家和乙作家從同樣史料中推理得出的真相絕對不一樣,十人十色,非常有趣。
只是,該如何判斷哪位作家對哪一起歷史事件的推理真相最具說服力,則全看讀者具有多少歷史知識存檔。也因此,歷史推理小說亦是小說家和歷史迷讀者之間的一種隱形知性競技遊戲。
追查某歷史事件時,我們不能只鎖定與該事件有關的人物與發生年代。例如有一對情侶在今年分手,我們能說那對情侶在今年某月因某事吵架,所以決定分手嗎?事情有這麼簡單嗎?分手的理由可能還要追溯到過去累積的種種因素,甚至牽涉到彼此的親人和朋友。
千利休被迫切腹的例子也一樣。為何天下人的豐臣秀吉會如此重懲一庶民身分的茶人?
我們若拋開豐臣秀吉和千利休的身分對比,只追索「茶人」這條線索,並仔細翻閱與茶道有關的史料書籍,便可以發現此事件和織田信長死於本能寺的事件有關。
按歷史結果看,率兵襲擊本能寺的當事人是明智光秀。但前一天夜晚,織田信長在本能寺舉辦茶會,接著變成酒會,最後是圍棋對弈。本能寺事件發生時,參與茶會的公卿、富商與茶人均自現場逃脫,並順手牽羊帶走織田信長珍藏的掛軸。
織田信長死於一五八二年,所有人都認為掛軸也在本能寺燒毀。
然而,八、九年後,千利休主辦的茶會中突然出現眾人認為早在本能寺燒毀的掛軸時,秀吉看到後作何感想呢?是不是會心生疑惑,重新暗地調查本能寺之變的幕後陰謀?即便千利休與本能寺之變無關,秀吉是否會懲一儆百,再不為人知地逐一處死相關茶人,順便滅掉當時財界富商和茶人聚集的自治都市?呢?
從「茶人」這條線索追查,會得出與一般說法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真相:
原來織田信長死在當時的財界人手上。
如此換個角度追查下去,歷史是不是就變成非常有趣的知性遊戲呢?
只是,讀者若不知道千利休是何人,亦不清楚織田信長是怎麼死的,這場遊戲就玩不起來。因此我才會說,歷史推理讀物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的隱形知性競技遊戲。
* * *
動筆寫這部書之前,我原本預計依循第一部《戰國日本》的構成,將篇目分為軍師、背叛、友情、親情、暗殺等幾大類,再以人物為主,闡述並推理日本戰國時代的各種懸案。不料,寫著寫著,最後竟變成七個人物。
主編要我寫一篇前言,說明為何選擇這些人物為主角的原因。
坦白說,並非我刻意選擇這些人物,而是寫完一篇後,腦中自然會浮出和上一篇文章有密切關係的人物。除了〈甲斐姬〉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其他人物均是一體關係,沒法分開。
既然以人物為主,我就不能輕描淡寫地只介紹他們的生平,至少要說明事件背景和當時的風俗習慣,並按歷史推理迷的慣例進行考證,最後總結出我的看法。
寫到最後,我才發覺原來我選了這七個人物。但我發誓,這七個人物不是我刻意挑出,而是他們自己跳出來要我寫的。
無奈字數有限,許多細節只能跳過。即便省略不少相關事件,我仍有點擔心對外國讀者來說,內容會不會太深入?畢竟對漢文圈讀者來說,這不是耳熟能詳的中國歷史,而是用中文寫成的外國歷史。
倘若讀者能咀嚼並消化這部書的內容,我便有信心繼續寫《戰國日本Ⅲ》。
請各位多多捧場並鼓勵,讓出版公司持續出版此系列的後續書。
試閱
第一話 獨眼跛腳的燿星參謀 山本勘助
武田信玄身邊不能少的人物 實實在在的存在
提到日本戰國大名「甲斐之虎」武田信玄,日本人通常眼前會浮現身穿深紅甲冑,高舉「風林火山」軍旗的騎兵隊,同時也會反射性地聯想到山本勘助。
過去有許多日本學者主張山本勘助是虛構人物,但自從一九六九年在北海道發現武田信玄的親筆書信,二○○八年又出現幾份新史料之後,便沒有人再否定山本勘助的存在。然而,學者雖不再為「山本勘助是虛構人物」的問題而口沫橫飛,卻不約而同將矛頭指向「山本勘助是否真是軍師」這點,各執己見爭議得如口吐泡沫的螃蟹。
目前日本專家已承認歷史上確實有山本勘助這個人,但也有人主張他應該是傳送武田信玄書信的使節,而非民間傳說中的軍師。
只是,上述那封出自北海道釧路的武田信玄書信史料,發信年代是一五五七年六月,剛好在第三次「川中島合戰」開戰之前。信中不但提到「川中島合戰」軍事情勢,信末還說明由山本勘助負責口傳詳情。由此可以想見山本勘助不但是傳達書信的使節,亦是武田信玄的親信之一。
再說,以戰國迷的立場來看,武田信玄身邊若少了個山本勘助,這齣戲可就一點都不好玩了。因此,無論山本勘助是武田信玄的軍師或傳送機密書信的重要使節,為了不讓戲班子坐冷板凳,以下有關山本勘助和武田信玄的敘述均根據《甲陽軍鑑》一書。
《甲陽軍鑑》是江戶時代初期的甲州流派著名兵書,大約在戰國時代結束四十年後寫成,全書總計二十卷五十九品。原為武田家老臣高?昌信的口述遺稿,後來由武田家遺臣亦是甲州流派創始人的小幡景憲編撰成書。小幡景憲生於一五七二年,一六六三年去逝。
結束戰國時代的「關原合戰」是發生在一六○○年,德川家康於一六○三年設立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的德川幕府政權,小幡景憲剛好夾在戰國時代與江戶時代的過渡期,不但耳聞目睹戰國時代末期的干戈,也親身經歷到江戶時代初期的混亂,因此《甲陽軍鑑》雖有不少自相矛盾的描述,但總的說來,史料價值仍舊很高。日本歷史小說家在寫戰國時代事跡時,通常會參照《甲陽軍鑑》。「武士道」一詞亦出自《甲陽軍鑑》。
信玄慧眼識獨眼
山本勘助生於三河國(愛知縣)。幼時患天花,臉上全是凹坑痘疤。二十歲時離開故鄉,周遊諸國研習兵法。流浪期間,足跡遍及天下各地,每到一處,必定前往當地古戰場,鑽研古人戰略,並畫下各座古城詳圖,研究城池建構和守城攻城法。此外還探查諸國政治實情及地土風俗,積極造訪各地名將與其討論兵法。
這期間,他拚命尋求願意收容自己的主君,在京都曾找過足利將軍,在中國地方則探訪毛利家和大內家,其他還有九州的大友家、山陰的尼子家、奧羽的南部家、相模的北?家……卻都因其貌不揚又跛腳,全遭拒絕。
窮途潦倒的山本勘助最終回到故鄉,將最後一線希望寄託於駿河太守今川家。此時他已四十出頭,膚色黝黑,原本佈滿凹坑痘疤的臉上又多加幾道傷痕,除了跛腳還失去隻眼,手指也殘疾,可以說滿身瘡痍。
今川義元的家老之一朝比奈兵衛尉(朝比奈信置)和山本勘助是知己,極為欣賞山本勘助的苦學成果。他向主君推薦:
「此人京流劍術高超,精曉佈陣,尤其擅長築城技術,具有守城攻城的非凡才能,是不可多得的大剛者(非常剛強之意)。」
駿河大守今川義元既沒有聽從家老的建議,也不曾實際召喚山本勘助面談,只派人去探聽勘助的風評。得出的結果是:
「這人是殘疾者。矮個子,獨眼跛腳,形貌醜陋,從未出仕任何名將也從未當過城主,連一個提草履的下人都養不起,怎麼可能知悉守城攻城兵法?」
如此,山本勘助在駿河待了九年多,始終不得志。這期間,山本勘助雖然有過幾次劍術功績,但當時流行新當流劍術,不把京流看在眼裡,以致他一直寄居在今川義元的家臣庵原忠胤宅邸,雌伏度日。(待續)古語有云,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連孔子都會以貌取人,王爾德也說「只有膚淺的人才不會以貌取人」,可見以貌取人並沒有錯,這應該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經驗總結。何況「貌」並非單指五官長相,還包括全身散發的氛圍以及彼此對不對盤的問題,毫無準則可言。
今川義元錯在他不信任家老的眼光。試想,家老是大名的重臣,各自統帥各部門的所有家臣,掌管領地的繁瑣事務,是執政核心人物,這種地位的人怎麼可能只憑和對方有交情就隨便向主君推薦人才呢?另一點,今川義元錯在沒有親自和山本勘助面談。即便以貌取人,至少也得和對方交談再下判斷為佳吧。
天文十二年(一五四三)正月三日,武田家眾家老聚集在信玄的根據地躑躅崎館(山梨縣甲府市古府中町,現為武田神社),商討該年的軍備事項。眾人提到國境的築城問題,一致認為築城的首要關鍵是設計和地理位置,只要這兩項不出漏洞,即能以三百守城兵對抗一千攻城兵。信玄問眾人:
「領地內有無築城人才?」
此時,家老總管板垣信方(板垣信形,武田四天王之一)向信玄推舉了三河國的山本勘助。二十三歲的信玄不假思索便說:
「好,給他一百貫俸祿,帶他來見我。」
古時的錢幣中央有洞,用繩子串成一千文便是一貫,換算為稻米至少是一石(十斗);信玄用一百貫俸祿聘請新人,可謂破格高薪。而且信玄很體貼,還命板垣準備馬匹、弓箭、長矛、綢衣、隨侍等,讓勘助在中途換裝,以便他能風風光光前來進謁。
這正是武田信玄和今川義元的相異處。
同年三月,山本勘助果然迢迢趕來謁見武田信玄。不知是勘助談吐不凡,或是信玄獨具慧眼,兩人面談後,信玄當下道:
「勘助是獨眼,因負傷而手腳不靈,膚色又黑得不像話。這麼一個醜男,聲譽竟如此高,應該是極為傑出的武士。這種武士,給一百貫太少了。」
結果,信玄發下一張兩百貫俸祿的朱印狀(蓋有紅色官印的公文)給山本勘助。四、五天後,信玄再度傳喚勘助,訊問今川義元的地盤駿河國(靜岡縣)內情。勘助闡明得有條有理,信玄聽得心服口服,立即讓勘助升任為左右手。
有重臣認為山本勘助還未立功便讓他位居要職,風險太大,而且恐怕也會遭今川家說三道四。信玄回說:
「不是有『謀者近之』這句話嗎?無論今川家說什麼,我只相信勘助說的話。」
信玄是甲斐國歷代守護武田家第十九代家督。父親是統一甲斐國的武田信虎。
《甲陽軍鑑》作者描述武田信虎是個狂人,脾氣極為暴躁。因信虎偏愛次子,長子信玄從小就裝做凡事不如弟弟的豬頭模樣,以免被父親放逐他國。這種例子在戰國時代很常見,尤以日後將繼承國主地位的長子為多。
信玄二十一歲時,信虎的女婿今川義元擔憂岳父將來可能會背叛今川家,又深恐自己的兒子於日後敗在岳父手下,於是決定讓信玄登上國主地位。
今川義元與信玄的家臣聯手,設計引誘信虎離開甲斐,客居今川家,終生不得回國。信玄對趕走父親一事似乎耿耿於懷。
身為守護世家長子身分的信玄,教養極佳,允文允武,精通周詩三百零五篇、《武經七書》等,唯獨不碰《論語》。據說《論語》中有許多孝道典故,會觸痛信玄不為人知的內心隱傷。(待續)地位愈高的人,愈孤獨。
有「戰國第一名將」美譽的武田信玄當然也不例外。
足智多謀的山本勘助,年齡和武田信虎差不多,身分又非譜代家臣,平日沉默寡言,只在關鍵時刻才會提出精確建議。或許信玄的理想父親形象正是這種人。
《甲陽軍鑑》描述,同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信玄出征信州時,全靠勘助的計謀才得以攻下九座城。至於是哪裡的哪座城,書中沒有說明,倒是勘助的俸祿在這時又增至三百貫。
武者守護神「摩利支天」再世
信玄攻滅信濃(長野縣)望族諏訪賴重時,看中諏訪家女兒,想納為側室。這女兒行年十四,是個美女(以現代眼光來看,十四歲仍是初中生,應該是美少女)。但所有重臣都異口同聲反對,認為信玄既然殺了對方的父親,對方很可能懷恨在心,說不定會同諏訪家遺臣和親戚聯手圖謀不軌。
山本勘助勸眾臣說:
「如果納諏訪姬為妾,諏訪的老百姓一定會期望她生下男孩,日後再度振興諏訪家。如此一來,諏訪家的遺臣和老百姓就不會起叛亂之心。」
勘助料得沒錯,諏訪姬於翌年果然生下一男,正是日後的武田勝賴。
信玄本來就預計讓諏訪姬生下的男子繼承諏訪家,為這孩子取名時,沒有讓他承襲武田家嫡子代代相傳的「信」字,特地取了諏訪姬父親名字的「賴」字。
不過信玄的其他兒子不是自盡便是盲目或早夭,剩下的兒子也都過繼給他家,最後只能讓勝賴繼承武田家。
諷刺的是,勝賴雖比父親強大,併合甲州和信州,建立了武田王國,卻也是間接讓武田家走向滅亡的人。
《甲陽軍鑑》作者分析,勝賴因有個被神化的英傑父親,所以無論怎麼拚命都無法令家臣或他國領主心服,只得不斷擴張領地,導致國內民窮兵疲,終於自取絕滅。
說起來勝賴也很可憐,他本是諏訪家家督,地位雖小,卻也是雞口而非牛後。信玄的長子義信過世後,他才臨時晉升為武田家繼承人。但他的出身背景令武田家眾臣視為外人,明明事情做得和父親一樣好,家臣卻在背地裡數落他不如父親。大部分家臣口是心非,不聽命令,連領地老百姓也瞧不起這個「外地來的繼任者」。
對身為第二代的兒子來說,名望過高的父親往往是個重荷,最終大多以悲劇收場。
勝賴的母親諏訪姬在兒子十歲那年過世,由於沒有任何有關她的史料,日本小說家新田次郎在小說《武田信玄》(中譯本遠流出版)中給她取名為「湖衣姬」,井上靖則在《風林火山》(中譯本遠流出版)取名為「由布姬」。但她的墓碑銘有個「梅」字,日本歷史專家推測她的本名應該是「梅」。
諏訪姬委身於信玄後,十年間只生下一個兒子,表示信玄並不寵愛她,讓她終生過著冷宮日子。
看來這對母子確實很苦命,不過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信玄登上國主地位後,以破竹之勢逐漸往西北擴張領地。然而,信玄畢竟還年輕,經驗不足,在攻打信濃北部領主村上義清時,首次吃了敗仗。
村上義清是信州最有勢力的豪族,此時信玄已征服諏訪,再往北就是村上的地盤。村上家和武田家本來是盟友,但和村上結盟的人是信玄的父親信虎,並非信玄本人。信玄登位後即與村上解除盟約,之後又殺死村上的盟友諏訪氏,村上恨信玄恨得要死。
開戰前,村上的家臣曾勸說最好不要以卵擊石,但義清認為信玄只是個未滿三十歲的小毛頭,不足掛齒,何況古來便有「兵多者敗」的例子。
村上義清在前一年因真田幸隆(真田幸村的祖父)的謀略,失去五百將士。他決意在這次戰役中,就算無法親手殺掉信玄,也要砍下真田幸隆的頭顱以湔雪前恥。
勘助五十六歲那年,武田軍與村上軍雙方在上田原(長野縣上田市)隔著河川對陣。(待續)武田軍先鋒正是向信玄推薦山本勘助的板垣信方。
板垣雖然率兵立下先驅之功,砍下一百五十顆敵軍首級,卻忘了「逐奔不踰列」的兵法原則,不但遠離了大本營,還在敵軍很可能反擊的陣前檢閱首級。結果遭村上軍突擊,板垣來不及騎馬逃走便被五、六名士兵以長矛刺死。
之後,村上率七百士兵直搗武田軍大本營,並在馬背上揮刀和信玄單打獨鬥。信玄因此負傷,戰後在甲府市湯村溫泉待了一個月養傷。據說信玄在此次戰役中全靠山本勘助的指揮才得以平安無事逃離戰場。
同年七月,信玄再度敗於村上義清手下,而且敗得很慘。這回的戰場是砥石城(戶石城,長野縣上田市),離村上的根據地葛尾城不遠,算是國境前線守城。信玄只要攻下這座城,村上戰線就不得不往北後退。北方正是上杉謙信的越後國(新潟縣)。
砥石城雖是小城,卻建在絕壁山脊,地理位置險要。況且上田市自古以來便有特殊的「逆霧」氣象。一般山中霧氣是自半山腰升起,逐漸罩住整座山,看上去朦朦朧朧,但上田市的「逆霧」是自山脊稜線降下瀑布般的濃霧雲層,半山腰以上完全被乳白色雲層罩住,形成天然屏障。
絕壁和濃霧令攻城的武田軍束手無策。村上義清又率領主力兵從葛尾城趕來助陣,攻擊武田軍背後。武田軍遭山頂和山下夾攻,損失慘重,前線亂成一團,信玄在大本營發出的軍令完全不起作用。
眼看自己的軍隊可能全線崩潰,信玄決定親自上陣。
此時,山本勘阻止信玄:
「只要引誘敵軍移至南方,這場戰即能轉敗為勝。」
「軍令都無法傳到前方了,怎麼實行佯動作戰?這不是紙上談兵嗎?」信玄問。
「請主君借我五十後備騎兵,這事交給我包辦。」
勘助率領五十騎兵引誘村上主力軍轉移陣地,信玄再趁機重整陣勢,最終扭轉乾坤,武田軍取得勝利。這回的戰役令勘助馳名遠近,武田家上下均稱譽勘助是武者守護神「摩利支天」再世。
勘助的俸祿又升至八百貫,成為足輕(步卒)大將,這時他已經將近六十歲。
大器晚成的勘助喜出望外,向信玄請了幾天假,回故鄉拜訪駿河今川家的家臣庵原氏。表面是道謝過去受照顧的恩情,其實是為了出一口氣而特地衣錦還鄉。
兵法書「一本都沒讀過」?
古時日本所謂的「兵法」專指個人劍術伎倆,並非中國的軍事用兵理論;在日文中,「軍配」才是用兵作戰策略之意。不過為避免讀者看得莫名其妙,在此全統一為中文的「兵法」、「軍師」。
日本戰國時代的大名或有力武將,均有精通陰陽道和易學的軍師。這類軍師和擔任作戰策略的參謀軍師不一樣,他們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占卜並觀測天文氣象,出征之前還得主持出征儀式,戰後檢閱敵方首級時也必須舉行祭祀儀式。
出征儀式和戰後檢閱首級的儀式非常繁雜,宗教色彩極為濃厚。武田家也有幾名這類陰陽道軍師。
其中有個軍師名叫小笠原,擅長幻術,時常在眾人面前表演幻術。例如,夜晚時分,眾人在可以望見山林的房間聊天時,小笠原能依照在座各人的要求讓山林內點起火焰。無論對方要求點燃幾道火焰,他都能操縱自如。
山本勘助對這類幻術、妖術不感興趣,他慣用宮、商、角、徵、羽五音,並觀察城池上空的青、白、赤、黑、黃五雲變化和煙氣,判斷該城能否陷落。此外還觀看烏、鳶、鳩三種軍鳥的飛翔方式以及來去方位推測戰況,兵法樸實,從未玩過幻術妖術。
小笠原自己也說:「幻術只是一種酒席助興把戲,在實際戰場毫無用處。」
可見山本勘助並非主持各類軍事儀式的陰陽道軍師。但此故事正間接說明小笠原的性格可能比較圓滑,勘助則較耿直,不苟言笑。(待續)無論觀雲氣或占禽鳥,中國古代兵書皆有記載,但是勘助的兵法知識似乎並非從古籍中習得。
某天,信玄問勘助:
「你讀過四、五本書嗎?」
「一本都沒讀過。」勘助答。
《甲陽軍鑑》沒有說明信玄為何如此問的理由,所以這段對話很微妙。既可以解釋為信玄驚嘆勘助的軍事策略知識,想問他讀過什麼兵書,也可以解釋為信玄希望勘助多讀一些兵法書。但勘助對信玄說:
「雖然我從未讀過兵法書,但聽說諸葛孔明正是利用《三略》《軍林寶鑑》等兵法書創出八陣圖。望主君也能應用這類兵書創出武田流派兵法。古代唐國有魚鱗、鶴翼、長蛇、偃月、鋒矢、方圓、衡軛、雁行八種陣形,這些陣形雖大有助益,卻不適合我國。主君可以改良這些兵法,讓國內上上下下每個將士都能理解該如何佈陣。」
勘助說的「古代唐國陣形」,是日本平安時代的貴族學者大江維時前往唐國留學時,研習了《三略》《孫子兵法》等兵書,回國後自創陣形名稱並編纂成書。但一般小兵根本無法理解這類高深兵法,勘助的意思是希望信玄深入淺出地改編古代陣形並制定軍法、家法,讓大將小兵於平日銘記在心,如此便能習慣成自然,作戰時不會混亂。
倘若《甲陽軍鑑》記載的是事實,「甲州法度」和「甲州流兵法」就都出自山本勘助的建議了。
勘助雖說他從未讀過任何一本書,但他既然說得出《三略》和《軍林寶鑑》書名,甚至連八陣名稱都能朗朗上口,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他從來不讀書。可能是不願意在信玄面前老王賣瓜,要不然便是在流浪期間以口傳心授方式習得兵法精華,否則就是《甲陽軍鑑》作者加油添醋。
不過,山本勘助確實在武田家留下築城技術功績。《甲陽軍鑑》作者說,武田家的城池建築方式全承襲勘助流。
勘助最擅長設計「馬出」。
城池最重要的戰鬥出入口是「虎口」,在虎口前用土堡圍成一道野戰城郭即為「馬出」,不但守城有利,敵軍也很難攻進。
勘助設計的是弧形「圓馬出」,而且在土堡外圍又挖一道弧形壕溝,名為「三日月堀」。這些都是改建原有的城堡而成,因為甲斐、信濃是山岳地帶,地形複雜,很難建築新城,只能改修原有的舊領主居城。
信玄的居城躑躅崎館沒有城牆,只有一道壕溝,日後才有「人是城,人是石垣,人是壕溝,情是友,仇是敵」這句信玄名言。不過,甲府市教育委員會於二○○七年調查躑躅館遺跡時,挖掘出防禦設施的「圓馬出」痕跡,這應該也是勘助設計的。
躑躅崎館內最有趣的建築,是信玄的專用廁所。房間面積是京都尺寸的「京間」六張榻榻米大,換算為公制大約是十一平方公尺,而且全鋪上在當時算是奢侈品的榻榻米。再從浴室安裝導水管至廁所,類似現代的沖水馬桶。房內設有香爐,由兩名值班人員負責點伽羅香,一天輪換三次。信玄如廁時,另有一名隨從會聽從吩咐送來某國某郡的資料,信玄就在廁所審批文件。
「川中島合戰」之後,信玄每次上廁所都會帶刀,身邊也一定跟著三名佩刀武將,躲在紙門後以防萬一。
如此看來,信玄的廁所相當於現代人的書齋或辦公室。以信玄的身分來說,能夠獨處的時間應該非常少,想靜心處理重大案件或思考戰略時,或許廁所正是最佳場所。
「遺恨十年磨一劍」的死對頭
永祿四年(一五六一)八月十六日,從信濃海津城趕來的信使報告,上杉謙信率領一萬三千軍隊越過犀川和千曲川,在海津城對面的妻女山西條村(長野縣長野市)佈陣,打算攻打海津城(今松代城)。
犀川和千曲川之間的扇形平原地帶,正是川中島。
海津城離甲府約一百五十公里,是武田家唯一新建的城堡,築城者正是山本勘助,守將是《甲陽軍鑑》的作者高?昌信,副將是真田幸隆。
信玄接到報告後,於十八日率兵出陣,二十四日抵達川中島。這期間至少有一星期空檔。過去我一直有個疑問,上杉軍在這期間到底在做什麼呢?
《甲陽軍鑑》沒有說明,於是我就找上杉家史料尋求答案。果然在上杉家於一六六九年向德川幕府提交的上杉家正史《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中找到了。(待續)原來上杉軍在妻女山山腳佈陣後,忙著切斷通往海津城的交通道路,並阻斷自妻女山背面流出的河流,改造成遏止武田軍攻擊的防護河渠。
一五七九年之前寫成的《謙信家記》中,也提到上杉軍為了攻打海津城,在海津城附近村落到處放火。
看來上杉謙信雖打算攻下海津城,但海津城是信玄為了對抗越後國的謙信,特地命勘助新建的城,是集山本勘助築城技術大成的堅城。何況守城副將是鼎鼎大名的真田幸隆,難怪謙信不敢輕舉妄動。
《甲陽軍鑑》描述,武田軍在千曲川渡口的雨宮渡(長野縣千曲市,現在地形都變了)佈陣,堵住上杉軍的退路和補給線。兩軍對峙了五天。
第六天,信玄率軍進入海津城。
九月九日,信玄召喚勘助和武田四名臣之一的馬場信春商討戰略。勘助建議說:
「我們有兩萬兵力,撥出一萬二千攻打妻女山的越後軍,明日卯時(清晨五點左右)開戰。到時候越後軍無論勝敗,必定得渡河撤退,我們再趁此時讓事先埋伏的旗本軍上陣夾攻。」
討論後的結果,信玄這方決定讓奇襲軍分為十隊於卯時攻打上杉軍,旗本軍則組成五隊,其他另有四隊旗本護衛,三隊旗本後援,總計八千。
旗本軍於寅時(清晨三點左右)出發,先渡過千曲川在八幡原等待撤退的上杉軍。戰國時代的旗本軍即本隊,由大名親自指揮。
然而,上杉軍斥候在妻女山上望見海津城炊煙縷縷,下山向謙信報告後,謙信立即識破勘助的策略。
武田軍預計在十日清晨五點向妻女山開戰,謙信卻在九日亥時(夜晚九點左右)早一步率兵渡河移至對岸。
上杉軍的軍律是戰時只在早上做飯,每天早上分配一天份的軍糧給士兵,所以夜晚不用做飯,也就不須燃火。一萬三千士兵就如江戶時代儒學者賴山陽作的漢詩那般,「鞭聲肅肅夜過河」,無聲無息地轉移陣地。信玄率領的旗本軍於半夜抵達八幡原佈好陣勢,等待奇襲軍的捷報。
次日清晨濃霧消失後,信玄才看到眼前突然冒出一萬三千上杉軍,正是賴山陽漢詩的第二句「曉見千兵擁大牙」(大牙是大將立於軍營前的大旗,因竿上以象牙為飾,又稱牙旗)。
《甲陽軍鑑》描述上杉軍本隊的陣勢是「車懸陣」。
「車懸陣」類似中國的「方圓陣」。大將居陣形中央,外圍排成幾層螺旋,機動兵力在最外圈,臨戰時不時往同一個方向旋轉,像個轉動的輪子。這種陣形不但可以避免士兵因疲憊而致使陣形崩潰,且轉到最後會變成雙方的旗本隊直接出馬交戰。
這場仗打得非常激烈,畢竟雙方是「遺恨十年磨一劍」的死對頭,於是刀光劍影殺得「流星光底逸長蛇」。山本勘助正是在這場戰役中戰死。著名的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的「一騎打」(單挑)也是在這場戰役中發生。以上是《甲陽軍鑑》的說法。
我們再來看上杉家史料如何記載這場戰役。
《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描述,九月九日夜晚,武田軍悄悄離開海津城,渡河在川中島佈陣。上杉軍的「夜行者」(忍者)在妻女山上望見此光景,下山向謙信報告此事。謙信和重臣商討後,決定在妻女山留下五隊軍力,當天夜晚十二點親自率領五千兵力,偷偷渡河在川中島佈陣。
次日,天還未亮,上杉軍即高吹戰螺大打戰鼓,攻向武田大本營。武田軍來不及迎戰,退到犀川。這時武田信義率二千軍隊自背面攻擊謙信旗本軍,幸好宇佐美定滿趕來助陣,擊退了武田信義。
另一點很有趣,《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批評《甲陽軍鑑》在第四回川中島合戰中描述的「一騎打」並非事實,那時和謙信單挑的人是信玄的影武者。真正的「一騎打」是在第二回川中島合戰時發生。此外還說上杉謙信在第四回川中島合戰中沒有使用「車懸陣」陣形,上杉家打仗時從來沒有用過「車懸陣」。(待續)江戶時代儒學者賴山陽於一八二六年完成的國史史書《日本外史》卷十一則描述:
上杉軍自妻女山出發時,「全軍啣枚,縛馬舌,?雨宮渡,遇武田斥騎十七人,盡斬之」。信玄軍則為「俟報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 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 以弓銃力拒」。最後,「信玄脫走,謙信追之」。
《日本外史》在第四回川中島合戰中也沒有提到「一騎打」。但在第二回川中島合戰中描述謙信出兵時說:
「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
雙方交戰時,信玄偷渡犀川,「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但宇佐美定滿等人帶兵趕來助陣,信玄與數十騎親信落荒而逃。
此時,「有一騎黃襖騮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自馬背跳下,逃進河中,謙信「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砍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才倖免於難。
這段漢文描述與《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第二回川中島合戰的敘述一致。
如此看來,信玄和謙信的「一騎打」並非只有一次,而是兩次?否則就是《甲陽軍鑑》作者故意把第二回的「一騎打」安排在第四回。若要拍電影或電視劇,我肯定會採用信玄落馬河中與謙信的「一騎打」這段劇情。
總之,第四回川中島合戰時,謙信在妻女山上佈陣(目前已證實在山上無法佈陣,而且現代的妻女山可能也不是史料中記載的「西條山」)、勘助的「啄木鳥戰法」、謙信的「車懸陣」陣形、武田軍的「鶴翼陣」陣形等說法,均出自江戶時代後期的軍記小說《甲越信戰錄》。此書作者不詳,只知是綜合許多當時流行的戰記話本、傳說、戲曲而寫成,類似中國的《三國演義》。
後世的日本歷史作家明明知曉《甲越信戰錄》是史實夾雜虛構的讀物,但正如中國民眾比較愛看《三國演義》一樣,日本民眾也喜歡虛虛實實的故事,因而日本作家才會以此書為小說底本。反正是給大眾看的小說,又非學術論文,三分寫實、七分虛構恰恰好。
說實話,站在讀者的立場,我也會選擇《三國演義》。
即便我知道利用草船借箭的不是諸葛亮,而是孫權,並且孫權只是因輕舟有一側中箭太多,深恐翻船,才調轉船首,讓另一側中箭,最後箭均船平,安全返航。但只要有人提起「草船借箭」,我還是會反射性地聯想到諸葛孔明和赤壁,而且這個諸葛孔明最好是神采飄逸的金城武。
在恩人面前結束自己的一生
話說回來,山本勘助死時,年齡大約六十八歲,這在戰國時代算是相當長壽了。何況他是死在戰場,應該死得無悔無怨。
目前一般說法是勘助因「啄木鳥戰法」失敗,負疚戰死。但我覺得,既然沒有所謂的「啄木鳥戰法」,他根本無須負疚,勘助很可能是因為歲數已大,再加上身有難言的宿疾,自知無法再馳騁戰場,才決意於恩人信玄面前結束自己的一生。
有關第四回川中島合戰,賴山陽除了上述那首著名的「鞭聲肅肅夜過河,曉見千兵擁大牙,遺恨十年磨一劍,流星光底逸長蛇」漢詩外,另有一首〈筑摩河〉:
西條山 筑摩河
越公如虎峽公蛇
汝欲螫 吾已噉
八千騎 夜衝暗
曉霧晴 大旗摯
兩軍搏 山欲裂
快劍斬陣腥風生
虎吼蛇逸河噴雪
傍有毒龍待其蹶
這首詩形容謙信如虎,信玄若蛇。我覺得最後一句很有趣,原來織田信長是毒龍?
武田信玄身邊不能少的人物 實實在在的存在
提到日本戰國大名「甲斐之虎」武田信玄,日本人通常眼前會浮現身穿深紅甲冑,高舉「風林火山」軍旗的騎兵隊,同時也會反射性地聯想到山本勘助。
過去有許多日本學者主張山本勘助是虛構人物,但自從一九六九年在北海道發現武田信玄的親筆書信,二○○八年又出現幾份新史料之後,便沒有人再否定山本勘助的存在。然而,學者雖不再為「山本勘助是虛構人物」的問題而口沫橫飛,卻不約而同將矛頭指向「山本勘助是否真是軍師」這點,各執己見爭議得如口吐泡沫的螃蟹。
目前日本專家已承認歷史上確實有山本勘助這個人,但也有人主張他應該是傳送武田信玄書信的使節,而非民間傳說中的軍師。
只是,上述那封出自北海道釧路的武田信玄書信史料,發信年代是一五五七年六月,剛好在第三次「川中島合戰」開戰之前。信中不但提到「川中島合戰」軍事情勢,信末還說明由山本勘助負責口傳詳情。由此可以想見山本勘助不但是傳達書信的使節,亦是武田信玄的親信之一。
再說,以戰國迷的立場來看,武田信玄身邊若少了個山本勘助,這齣戲可就一點都不好玩了。因此,無論山本勘助是武田信玄的軍師或傳送機密書信的重要使節,為了不讓戲班子坐冷板凳,以下有關山本勘助和武田信玄的敘述均根據《甲陽軍鑑》一書。
《甲陽軍鑑》是江戶時代初期的甲州流派著名兵書,大約在戰國時代結束四十年後寫成,全書總計二十卷五十九品。原為武田家老臣高?昌信的口述遺稿,後來由武田家遺臣亦是甲州流派創始人的小幡景憲編撰成書。小幡景憲生於一五七二年,一六六三年去逝。
結束戰國時代的「關原合戰」是發生在一六○○年,德川家康於一六○三年設立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的德川幕府政權,小幡景憲剛好夾在戰國時代與江戶時代的過渡期,不但耳聞目睹戰國時代末期的干戈,也親身經歷到江戶時代初期的混亂,因此《甲陽軍鑑》雖有不少自相矛盾的描述,但總的說來,史料價值仍舊很高。日本歷史小說家在寫戰國時代事跡時,通常會參照《甲陽軍鑑》。「武士道」一詞亦出自《甲陽軍鑑》。
信玄慧眼識獨眼
山本勘助生於三河國(愛知縣)。幼時患天花,臉上全是凹坑痘疤。二十歲時離開故鄉,周遊諸國研習兵法。流浪期間,足跡遍及天下各地,每到一處,必定前往當地古戰場,鑽研古人戰略,並畫下各座古城詳圖,研究城池建構和守城攻城法。此外還探查諸國政治實情及地土風俗,積極造訪各地名將與其討論兵法。
這期間,他拚命尋求願意收容自己的主君,在京都曾找過足利將軍,在中國地方則探訪毛利家和大內家,其他還有九州的大友家、山陰的尼子家、奧羽的南部家、相模的北?家……卻都因其貌不揚又跛腳,全遭拒絕。
窮途潦倒的山本勘助最終回到故鄉,將最後一線希望寄託於駿河太守今川家。此時他已四十出頭,膚色黝黑,原本佈滿凹坑痘疤的臉上又多加幾道傷痕,除了跛腳還失去隻眼,手指也殘疾,可以說滿身瘡痍。
今川義元的家老之一朝比奈兵衛尉(朝比奈信置)和山本勘助是知己,極為欣賞山本勘助的苦學成果。他向主君推薦:
「此人京流劍術高超,精曉佈陣,尤其擅長築城技術,具有守城攻城的非凡才能,是不可多得的大剛者(非常剛強之意)。」
駿河大守今川義元既沒有聽從家老的建議,也不曾實際召喚山本勘助面談,只派人去探聽勘助的風評。得出的結果是:
「這人是殘疾者。矮個子,獨眼跛腳,形貌醜陋,從未出仕任何名將也從未當過城主,連一個提草履的下人都養不起,怎麼可能知悉守城攻城兵法?」
如此,山本勘助在駿河待了九年多,始終不得志。這期間,山本勘助雖然有過幾次劍術功績,但當時流行新當流劍術,不把京流看在眼裡,以致他一直寄居在今川義元的家臣庵原忠胤宅邸,雌伏度日。(待續)古語有云,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連孔子都會以貌取人,王爾德也說「只有膚淺的人才不會以貌取人」,可見以貌取人並沒有錯,這應該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經驗總結。何況「貌」並非單指五官長相,還包括全身散發的氛圍以及彼此對不對盤的問題,毫無準則可言。
今川義元錯在他不信任家老的眼光。試想,家老是大名的重臣,各自統帥各部門的所有家臣,掌管領地的繁瑣事務,是執政核心人物,這種地位的人怎麼可能只憑和對方有交情就隨便向主君推薦人才呢?另一點,今川義元錯在沒有親自和山本勘助面談。即便以貌取人,至少也得和對方交談再下判斷為佳吧。
天文十二年(一五四三)正月三日,武田家眾家老聚集在信玄的根據地躑躅崎館(山梨縣甲府市古府中町,現為武田神社),商討該年的軍備事項。眾人提到國境的築城問題,一致認為築城的首要關鍵是設計和地理位置,只要這兩項不出漏洞,即能以三百守城兵對抗一千攻城兵。信玄問眾人:
「領地內有無築城人才?」
此時,家老總管板垣信方(板垣信形,武田四天王之一)向信玄推舉了三河國的山本勘助。二十三歲的信玄不假思索便說:
「好,給他一百貫俸祿,帶他來見我。」
古時的錢幣中央有洞,用繩子串成一千文便是一貫,換算為稻米至少是一石(十斗);信玄用一百貫俸祿聘請新人,可謂破格高薪。而且信玄很體貼,還命板垣準備馬匹、弓箭、長矛、綢衣、隨侍等,讓勘助在中途換裝,以便他能風風光光前來進謁。
這正是武田信玄和今川義元的相異處。
同年三月,山本勘助果然迢迢趕來謁見武田信玄。不知是勘助談吐不凡,或是信玄獨具慧眼,兩人面談後,信玄當下道:
「勘助是獨眼,因負傷而手腳不靈,膚色又黑得不像話。這麼一個醜男,聲譽竟如此高,應該是極為傑出的武士。這種武士,給一百貫太少了。」
結果,信玄發下一張兩百貫俸祿的朱印狀(蓋有紅色官印的公文)給山本勘助。四、五天後,信玄再度傳喚勘助,訊問今川義元的地盤駿河國(靜岡縣)內情。勘助闡明得有條有理,信玄聽得心服口服,立即讓勘助升任為左右手。
有重臣認為山本勘助還未立功便讓他位居要職,風險太大,而且恐怕也會遭今川家說三道四。信玄回說:
「不是有『謀者近之』這句話嗎?無論今川家說什麼,我只相信勘助說的話。」
信玄是甲斐國歷代守護武田家第十九代家督。父親是統一甲斐國的武田信虎。
《甲陽軍鑑》作者描述武田信虎是個狂人,脾氣極為暴躁。因信虎偏愛次子,長子信玄從小就裝做凡事不如弟弟的豬頭模樣,以免被父親放逐他國。這種例子在戰國時代很常見,尤以日後將繼承國主地位的長子為多。
信玄二十一歲時,信虎的女婿今川義元擔憂岳父將來可能會背叛今川家,又深恐自己的兒子於日後敗在岳父手下,於是決定讓信玄登上國主地位。
今川義元與信玄的家臣聯手,設計引誘信虎離開甲斐,客居今川家,終生不得回國。信玄對趕走父親一事似乎耿耿於懷。
身為守護世家長子身分的信玄,教養極佳,允文允武,精通周詩三百零五篇、《武經七書》等,唯獨不碰《論語》。據說《論語》中有許多孝道典故,會觸痛信玄不為人知的內心隱傷。(待續)地位愈高的人,愈孤獨。
有「戰國第一名將」美譽的武田信玄當然也不例外。
足智多謀的山本勘助,年齡和武田信虎差不多,身分又非譜代家臣,平日沉默寡言,只在關鍵時刻才會提出精確建議。或許信玄的理想父親形象正是這種人。
《甲陽軍鑑》描述,同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信玄出征信州時,全靠勘助的計謀才得以攻下九座城。至於是哪裡的哪座城,書中沒有說明,倒是勘助的俸祿在這時又增至三百貫。
武者守護神「摩利支天」再世
信玄攻滅信濃(長野縣)望族諏訪賴重時,看中諏訪家女兒,想納為側室。這女兒行年十四,是個美女(以現代眼光來看,十四歲仍是初中生,應該是美少女)。但所有重臣都異口同聲反對,認為信玄既然殺了對方的父親,對方很可能懷恨在心,說不定會同諏訪家遺臣和親戚聯手圖謀不軌。
山本勘助勸眾臣說:
「如果納諏訪姬為妾,諏訪的老百姓一定會期望她生下男孩,日後再度振興諏訪家。如此一來,諏訪家的遺臣和老百姓就不會起叛亂之心。」
勘助料得沒錯,諏訪姬於翌年果然生下一男,正是日後的武田勝賴。
信玄本來就預計讓諏訪姬生下的男子繼承諏訪家,為這孩子取名時,沒有讓他承襲武田家嫡子代代相傳的「信」字,特地取了諏訪姬父親名字的「賴」字。
不過信玄的其他兒子不是自盡便是盲目或早夭,剩下的兒子也都過繼給他家,最後只能讓勝賴繼承武田家。
諷刺的是,勝賴雖比父親強大,併合甲州和信州,建立了武田王國,卻也是間接讓武田家走向滅亡的人。
《甲陽軍鑑》作者分析,勝賴因有個被神化的英傑父親,所以無論怎麼拚命都無法令家臣或他國領主心服,只得不斷擴張領地,導致國內民窮兵疲,終於自取絕滅。
說起來勝賴也很可憐,他本是諏訪家家督,地位雖小,卻也是雞口而非牛後。信玄的長子義信過世後,他才臨時晉升為武田家繼承人。但他的出身背景令武田家眾臣視為外人,明明事情做得和父親一樣好,家臣卻在背地裡數落他不如父親。大部分家臣口是心非,不聽命令,連領地老百姓也瞧不起這個「外地來的繼任者」。
對身為第二代的兒子來說,名望過高的父親往往是個重荷,最終大多以悲劇收場。
勝賴的母親諏訪姬在兒子十歲那年過世,由於沒有任何有關她的史料,日本小說家新田次郎在小說《武田信玄》(中譯本遠流出版)中給她取名為「湖衣姬」,井上靖則在《風林火山》(中譯本遠流出版)取名為「由布姬」。但她的墓碑銘有個「梅」字,日本歷史專家推測她的本名應該是「梅」。
諏訪姬委身於信玄後,十年間只生下一個兒子,表示信玄並不寵愛她,讓她終生過著冷宮日子。
看來這對母子確實很苦命,不過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信玄登上國主地位後,以破竹之勢逐漸往西北擴張領地。然而,信玄畢竟還年輕,經驗不足,在攻打信濃北部領主村上義清時,首次吃了敗仗。
村上義清是信州最有勢力的豪族,此時信玄已征服諏訪,再往北就是村上的地盤。村上家和武田家本來是盟友,但和村上結盟的人是信玄的父親信虎,並非信玄本人。信玄登位後即與村上解除盟約,之後又殺死村上的盟友諏訪氏,村上恨信玄恨得要死。
開戰前,村上的家臣曾勸說最好不要以卵擊石,但義清認為信玄只是個未滿三十歲的小毛頭,不足掛齒,何況古來便有「兵多者敗」的例子。
村上義清在前一年因真田幸隆(真田幸村的祖父)的謀略,失去五百將士。他決意在這次戰役中,就算無法親手殺掉信玄,也要砍下真田幸隆的頭顱以湔雪前恥。
勘助五十六歲那年,武田軍與村上軍雙方在上田原(長野縣上田市)隔著河川對陣。(待續)武田軍先鋒正是向信玄推薦山本勘助的板垣信方。
板垣雖然率兵立下先驅之功,砍下一百五十顆敵軍首級,卻忘了「逐奔不踰列」的兵法原則,不但遠離了大本營,還在敵軍很可能反擊的陣前檢閱首級。結果遭村上軍突擊,板垣來不及騎馬逃走便被五、六名士兵以長矛刺死。
之後,村上率七百士兵直搗武田軍大本營,並在馬背上揮刀和信玄單打獨鬥。信玄因此負傷,戰後在甲府市湯村溫泉待了一個月養傷。據說信玄在此次戰役中全靠山本勘助的指揮才得以平安無事逃離戰場。
同年七月,信玄再度敗於村上義清手下,而且敗得很慘。這回的戰場是砥石城(戶石城,長野縣上田市),離村上的根據地葛尾城不遠,算是國境前線守城。信玄只要攻下這座城,村上戰線就不得不往北後退。北方正是上杉謙信的越後國(新潟縣)。
砥石城雖是小城,卻建在絕壁山脊,地理位置險要。況且上田市自古以來便有特殊的「逆霧」氣象。一般山中霧氣是自半山腰升起,逐漸罩住整座山,看上去朦朦朧朧,但上田市的「逆霧」是自山脊稜線降下瀑布般的濃霧雲層,半山腰以上完全被乳白色雲層罩住,形成天然屏障。
絕壁和濃霧令攻城的武田軍束手無策。村上義清又率領主力兵從葛尾城趕來助陣,攻擊武田軍背後。武田軍遭山頂和山下夾攻,損失慘重,前線亂成一團,信玄在大本營發出的軍令完全不起作用。
眼看自己的軍隊可能全線崩潰,信玄決定親自上陣。
此時,山本勘阻止信玄:
「只要引誘敵軍移至南方,這場戰即能轉敗為勝。」
「軍令都無法傳到前方了,怎麼實行佯動作戰?這不是紙上談兵嗎?」信玄問。
「請主君借我五十後備騎兵,這事交給我包辦。」
勘助率領五十騎兵引誘村上主力軍轉移陣地,信玄再趁機重整陣勢,最終扭轉乾坤,武田軍取得勝利。這回的戰役令勘助馳名遠近,武田家上下均稱譽勘助是武者守護神「摩利支天」再世。
勘助的俸祿又升至八百貫,成為足輕(步卒)大將,這時他已經將近六十歲。
大器晚成的勘助喜出望外,向信玄請了幾天假,回故鄉拜訪駿河今川家的家臣庵原氏。表面是道謝過去受照顧的恩情,其實是為了出一口氣而特地衣錦還鄉。
兵法書「一本都沒讀過」?
古時日本所謂的「兵法」專指個人劍術伎倆,並非中國的軍事用兵理論;在日文中,「軍配」才是用兵作戰策略之意。不過為避免讀者看得莫名其妙,在此全統一為中文的「兵法」、「軍師」。
日本戰國時代的大名或有力武將,均有精通陰陽道和易學的軍師。這類軍師和擔任作戰策略的參謀軍師不一樣,他們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占卜並觀測天文氣象,出征之前還得主持出征儀式,戰後檢閱敵方首級時也必須舉行祭祀儀式。
出征儀式和戰後檢閱首級的儀式非常繁雜,宗教色彩極為濃厚。武田家也有幾名這類陰陽道軍師。
其中有個軍師名叫小笠原,擅長幻術,時常在眾人面前表演幻術。例如,夜晚時分,眾人在可以望見山林的房間聊天時,小笠原能依照在座各人的要求讓山林內點起火焰。無論對方要求點燃幾道火焰,他都能操縱自如。
山本勘助對這類幻術、妖術不感興趣,他慣用宮、商、角、徵、羽五音,並觀察城池上空的青、白、赤、黑、黃五雲變化和煙氣,判斷該城能否陷落。此外還觀看烏、鳶、鳩三種軍鳥的飛翔方式以及來去方位推測戰況,兵法樸實,從未玩過幻術妖術。
小笠原自己也說:「幻術只是一種酒席助興把戲,在實際戰場毫無用處。」
可見山本勘助並非主持各類軍事儀式的陰陽道軍師。但此故事正間接說明小笠原的性格可能比較圓滑,勘助則較耿直,不苟言笑。(待續)無論觀雲氣或占禽鳥,中國古代兵書皆有記載,但是勘助的兵法知識似乎並非從古籍中習得。
某天,信玄問勘助:
「你讀過四、五本書嗎?」
「一本都沒讀過。」勘助答。
《甲陽軍鑑》沒有說明信玄為何如此問的理由,所以這段對話很微妙。既可以解釋為信玄驚嘆勘助的軍事策略知識,想問他讀過什麼兵書,也可以解釋為信玄希望勘助多讀一些兵法書。但勘助對信玄說:
「雖然我從未讀過兵法書,但聽說諸葛孔明正是利用《三略》《軍林寶鑑》等兵法書創出八陣圖。望主君也能應用這類兵書創出武田流派兵法。古代唐國有魚鱗、鶴翼、長蛇、偃月、鋒矢、方圓、衡軛、雁行八種陣形,這些陣形雖大有助益,卻不適合我國。主君可以改良這些兵法,讓國內上上下下每個將士都能理解該如何佈陣。」
勘助說的「古代唐國陣形」,是日本平安時代的貴族學者大江維時前往唐國留學時,研習了《三略》《孫子兵法》等兵書,回國後自創陣形名稱並編纂成書。但一般小兵根本無法理解這類高深兵法,勘助的意思是希望信玄深入淺出地改編古代陣形並制定軍法、家法,讓大將小兵於平日銘記在心,如此便能習慣成自然,作戰時不會混亂。
倘若《甲陽軍鑑》記載的是事實,「甲州法度」和「甲州流兵法」就都出自山本勘助的建議了。
勘助雖說他從未讀過任何一本書,但他既然說得出《三略》和《軍林寶鑑》書名,甚至連八陣名稱都能朗朗上口,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他從來不讀書。可能是不願意在信玄面前老王賣瓜,要不然便是在流浪期間以口傳心授方式習得兵法精華,否則就是《甲陽軍鑑》作者加油添醋。
不過,山本勘助確實在武田家留下築城技術功績。《甲陽軍鑑》作者說,武田家的城池建築方式全承襲勘助流。
勘助最擅長設計「馬出」。
城池最重要的戰鬥出入口是「虎口」,在虎口前用土堡圍成一道野戰城郭即為「馬出」,不但守城有利,敵軍也很難攻進。
勘助設計的是弧形「圓馬出」,而且在土堡外圍又挖一道弧形壕溝,名為「三日月堀」。這些都是改建原有的城堡而成,因為甲斐、信濃是山岳地帶,地形複雜,很難建築新城,只能改修原有的舊領主居城。
信玄的居城躑躅崎館沒有城牆,只有一道壕溝,日後才有「人是城,人是石垣,人是壕溝,情是友,仇是敵」這句信玄名言。不過,甲府市教育委員會於二○○七年調查躑躅館遺跡時,挖掘出防禦設施的「圓馬出」痕跡,這應該也是勘助設計的。
躑躅崎館內最有趣的建築,是信玄的專用廁所。房間面積是京都尺寸的「京間」六張榻榻米大,換算為公制大約是十一平方公尺,而且全鋪上在當時算是奢侈品的榻榻米。再從浴室安裝導水管至廁所,類似現代的沖水馬桶。房內設有香爐,由兩名值班人員負責點伽羅香,一天輪換三次。信玄如廁時,另有一名隨從會聽從吩咐送來某國某郡的資料,信玄就在廁所審批文件。
「川中島合戰」之後,信玄每次上廁所都會帶刀,身邊也一定跟著三名佩刀武將,躲在紙門後以防萬一。
如此看來,信玄的廁所相當於現代人的書齋或辦公室。以信玄的身分來說,能夠獨處的時間應該非常少,想靜心處理重大案件或思考戰略時,或許廁所正是最佳場所。
「遺恨十年磨一劍」的死對頭
永祿四年(一五六一)八月十六日,從信濃海津城趕來的信使報告,上杉謙信率領一萬三千軍隊越過犀川和千曲川,在海津城對面的妻女山西條村(長野縣長野市)佈陣,打算攻打海津城(今松代城)。
犀川和千曲川之間的扇形平原地帶,正是川中島。
海津城離甲府約一百五十公里,是武田家唯一新建的城堡,築城者正是山本勘助,守將是《甲陽軍鑑》的作者高?昌信,副將是真田幸隆。
信玄接到報告後,於十八日率兵出陣,二十四日抵達川中島。這期間至少有一星期空檔。過去我一直有個疑問,上杉軍在這期間到底在做什麼呢?
《甲陽軍鑑》沒有說明,於是我就找上杉家史料尋求答案。果然在上杉家於一六六九年向德川幕府提交的上杉家正史《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中找到了。(待續)原來上杉軍在妻女山山腳佈陣後,忙著切斷通往海津城的交通道路,並阻斷自妻女山背面流出的河流,改造成遏止武田軍攻擊的防護河渠。
一五七九年之前寫成的《謙信家記》中,也提到上杉軍為了攻打海津城,在海津城附近村落到處放火。
看來上杉謙信雖打算攻下海津城,但海津城是信玄為了對抗越後國的謙信,特地命勘助新建的城,是集山本勘助築城技術大成的堅城。何況守城副將是鼎鼎大名的真田幸隆,難怪謙信不敢輕舉妄動。
《甲陽軍鑑》描述,武田軍在千曲川渡口的雨宮渡(長野縣千曲市,現在地形都變了)佈陣,堵住上杉軍的退路和補給線。兩軍對峙了五天。
第六天,信玄率軍進入海津城。
九月九日,信玄召喚勘助和武田四名臣之一的馬場信春商討戰略。勘助建議說:
「我們有兩萬兵力,撥出一萬二千攻打妻女山的越後軍,明日卯時(清晨五點左右)開戰。到時候越後軍無論勝敗,必定得渡河撤退,我們再趁此時讓事先埋伏的旗本軍上陣夾攻。」
討論後的結果,信玄這方決定讓奇襲軍分為十隊於卯時攻打上杉軍,旗本軍則組成五隊,其他另有四隊旗本護衛,三隊旗本後援,總計八千。
旗本軍於寅時(清晨三點左右)出發,先渡過千曲川在八幡原等待撤退的上杉軍。戰國時代的旗本軍即本隊,由大名親自指揮。
然而,上杉軍斥候在妻女山上望見海津城炊煙縷縷,下山向謙信報告後,謙信立即識破勘助的策略。
武田軍預計在十日清晨五點向妻女山開戰,謙信卻在九日亥時(夜晚九點左右)早一步率兵渡河移至對岸。
上杉軍的軍律是戰時只在早上做飯,每天早上分配一天份的軍糧給士兵,所以夜晚不用做飯,也就不須燃火。一萬三千士兵就如江戶時代儒學者賴山陽作的漢詩那般,「鞭聲肅肅夜過河」,無聲無息地轉移陣地。信玄率領的旗本軍於半夜抵達八幡原佈好陣勢,等待奇襲軍的捷報。
次日清晨濃霧消失後,信玄才看到眼前突然冒出一萬三千上杉軍,正是賴山陽漢詩的第二句「曉見千兵擁大牙」(大牙是大將立於軍營前的大旗,因竿上以象牙為飾,又稱牙旗)。
《甲陽軍鑑》描述上杉軍本隊的陣勢是「車懸陣」。
「車懸陣」類似中國的「方圓陣」。大將居陣形中央,外圍排成幾層螺旋,機動兵力在最外圈,臨戰時不時往同一個方向旋轉,像個轉動的輪子。這種陣形不但可以避免士兵因疲憊而致使陣形崩潰,且轉到最後會變成雙方的旗本隊直接出馬交戰。
這場仗打得非常激烈,畢竟雙方是「遺恨十年磨一劍」的死對頭,於是刀光劍影殺得「流星光底逸長蛇」。山本勘助正是在這場戰役中戰死。著名的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的「一騎打」(單挑)也是在這場戰役中發生。以上是《甲陽軍鑑》的說法。
我們再來看上杉家史料如何記載這場戰役。
《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描述,九月九日夜晚,武田軍悄悄離開海津城,渡河在川中島佈陣。上杉軍的「夜行者」(忍者)在妻女山上望見此光景,下山向謙信報告此事。謙信和重臣商討後,決定在妻女山留下五隊軍力,當天夜晚十二點親自率領五千兵力,偷偷渡河在川中島佈陣。
次日,天還未亮,上杉軍即高吹戰螺大打戰鼓,攻向武田大本營。武田軍來不及迎戰,退到犀川。這時武田信義率二千軍隊自背面攻擊謙信旗本軍,幸好宇佐美定滿趕來助陣,擊退了武田信義。
另一點很有趣,《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批評《甲陽軍鑑》在第四回川中島合戰中描述的「一騎打」並非事實,那時和謙信單挑的人是信玄的影武者。真正的「一騎打」是在第二回川中島合戰時發生。此外還說上杉謙信在第四回川中島合戰中沒有使用「車懸陣」陣形,上杉家打仗時從來沒有用過「車懸陣」。(待續)江戶時代儒學者賴山陽於一八二六年完成的國史史書《日本外史》卷十一則描述:
上杉軍自妻女山出發時,「全軍啣枚,縛馬舌,?雨宮渡,遇武田斥騎十七人,盡斬之」。信玄軍則為「俟報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 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 以弓銃力拒」。最後,「信玄脫走,謙信追之」。
《日本外史》在第四回川中島合戰中也沒有提到「一騎打」。但在第二回川中島合戰中描述謙信出兵時說:
「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
雙方交戰時,信玄偷渡犀川,「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但宇佐美定滿等人帶兵趕來助陣,信玄與數十騎親信落荒而逃。
此時,「有一騎黃襖騮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自馬背跳下,逃進河中,謙信「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砍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才倖免於難。
這段漢文描述與《河中島五箇度合戰記》第二回川中島合戰的敘述一致。
如此看來,信玄和謙信的「一騎打」並非只有一次,而是兩次?否則就是《甲陽軍鑑》作者故意把第二回的「一騎打」安排在第四回。若要拍電影或電視劇,我肯定會採用信玄落馬河中與謙信的「一騎打」這段劇情。
總之,第四回川中島合戰時,謙信在妻女山上佈陣(目前已證實在山上無法佈陣,而且現代的妻女山可能也不是史料中記載的「西條山」)、勘助的「啄木鳥戰法」、謙信的「車懸陣」陣形、武田軍的「鶴翼陣」陣形等說法,均出自江戶時代後期的軍記小說《甲越信戰錄》。此書作者不詳,只知是綜合許多當時流行的戰記話本、傳說、戲曲而寫成,類似中國的《三國演義》。
後世的日本歷史作家明明知曉《甲越信戰錄》是史實夾雜虛構的讀物,但正如中國民眾比較愛看《三國演義》一樣,日本民眾也喜歡虛虛實實的故事,因而日本作家才會以此書為小說底本。反正是給大眾看的小說,又非學術論文,三分寫實、七分虛構恰恰好。
說實話,站在讀者的立場,我也會選擇《三國演義》。
即便我知道利用草船借箭的不是諸葛亮,而是孫權,並且孫權只是因輕舟有一側中箭太多,深恐翻船,才調轉船首,讓另一側中箭,最後箭均船平,安全返航。但只要有人提起「草船借箭」,我還是會反射性地聯想到諸葛孔明和赤壁,而且這個諸葛孔明最好是神采飄逸的金城武。
在恩人面前結束自己的一生
話說回來,山本勘助死時,年齡大約六十八歲,這在戰國時代算是相當長壽了。何況他是死在戰場,應該死得無悔無怨。
目前一般說法是勘助因「啄木鳥戰法」失敗,負疚戰死。但我覺得,既然沒有所謂的「啄木鳥戰法」,他根本無須負疚,勘助很可能是因為歲數已大,再加上身有難言的宿疾,自知無法再馳騁戰場,才決意於恩人信玄面前結束自己的一生。
有關第四回川中島合戰,賴山陽除了上述那首著名的「鞭聲肅肅夜過河,曉見千兵擁大牙,遺恨十年磨一劍,流星光底逸長蛇」漢詩外,另有一首〈筑摩河〉:
西條山 筑摩河
越公如虎峽公蛇
汝欲螫 吾已噉
八千騎 夜衝暗
曉霧晴 大旗摯
兩軍搏 山欲裂
快劍斬陣腥風生
虎吼蛇逸河噴雪
傍有毒龍待其蹶
這首詩形容謙信如虎,信玄若蛇。我覺得最後一句很有趣,原來織田信長是毒龍?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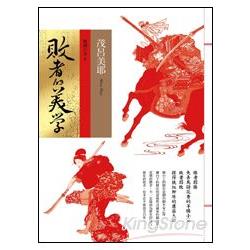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