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他本是老上海社會底層的一個小人物,卻因仰慕文化,仰慕出版,仰慕三聯書店,不斷努力,幾經周折,終於進入出版業。他就是大陸著名出版人、前三聯書店總經理「沈公」沈昌文。
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經歷過「文革」,經歷過「改革開放」,風雲變幻,波譎雲詭。「出版」因其特殊地位,其生存和發展狀況更是充滿曲折和故事。沈公既是大陸六十年出版事業的親歷者,更曾擔任大陸著名出版單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總經理十年,主持《讀書》雜誌編務十餘年,並將三聯和《讀書》發揚光大,其間種種,可謂深味甘苦。本書作為沈公的個人傳記,不單紀錄了他個人的成長歷史,也以一位從業者的身份娓娓道出大陸六十年出版歷程的波瀾和轉折,其間心路歷程、面對危機的應對閃避,非深入其中者不能道出。由此,我們也得以透過沈公的描述來瞭解大陸出版事業的詭譎境況。
試閱
第五章
五朵金花
《讀書》初創,即已聲名鵲起。主持人都是名流,前面已一一表過。然而,奇怪的是,主持人以下,卻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後來很多也都文明昭著,但當年畢竟是小人物。
說這些小人物文化程度不高,不確。準確地說,應是學歷不高。這是那個年頭的特色。在「偉大領袖」指示的光輝照耀下,眾多青年無法上學,初中畢業即已上山下鄉。所以在改革開放剛起步的那些年頭要招員工,要招有高學歷的青年實在很難。
三聯書店特別是《讀書》雜誌的這些激進青年,後來名聲大噪,人稱「五朵金花」。她們都是女性,因謂。
「五朵金花」中的第一朵自然是董秀玉。她不是「知青」,情況與上述有所不同。她是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從上海找來的校對員。她初中畢業後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任那時的蘇聯展覽解說員,展覽結束後,其中不少解說員來北京工作,董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但是此人從小出手不凡,在當年的出版部門中,她最能幹,而且大有當今所說的「女強人」的風範。所謂「女強人」也者,即不甘低男士一頭,凡事必須勝過那些屁男人。我寫過小文表彰過她在某年一起勞動時,男士挑擔一百斤,已稱英雄(我這男士只能挑六七十斤),她忿然而起,挑一百二十斤健步而行,於是眾人拜服,其中自然少不了鄙人這一「小男人」。
董秀玉調《讀書》,我曾出過力,但也只是向范公誇讚其人而已。以後在《讀書》,我想她文化水平不夠,不料她十分勝任。尤其是聯絡作者。比如錢鍾書、楊絳夫婦,對「三聯」始終只信她一人。個中奧妙,我亦不知,在旁盛讚而已。
另一朵「金花」吳彬,吳祖光老先生外甥女(外傳「姪女」,誤。吳彬從母姓,所以姓吳。)。吳祖光先生是范用好友,介紹來此。她是典型的「知青」,初中畢業即去雲南插隊,以後在北京當油漆工人。她從小在文人圈子中長大,出去組稿,凡屬北京文化圈子中的老人,她往往稱叔叔、阿姨,因為都是舊識。僅只如此,還以為她只是靠人際關係才在《讀書》生根發芽的。非也!我曾為一事驚嘆她讀書之多。我多年在北京閒逛,往往見到一些著名的舊宅,上面寫著「某某公府」,知是清代名人的府第。以後見面問吳彬,這某公是誰,她必定立即滔滔不絕地告我這位清代大官姓名為何,官居何職,有何功過大事,根本不用回去查書,即可倒背如流,如數家珍,令我嘆服!
至於另一位「金花」趙麗雅,更是奇人。她開過卡車,做過小販,後來考入《讀書》雜誌。其人身材矮小,訥於言談,初識之時,必定漠然對之。時間越長,發現其人深度越甚。我至今奇怪,一個如此小女子,自學出身,竟然學得如此深入。究竟如何深入,以我淺學,表達也難,大家只要翻讀她以筆名「揚之水」發表的眾多學術論著即知。一個人靠自學而得如此成就,大概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奇蹟。由此不能不說,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其實一點沒有扼殺中國文化,反而大大有助於如揚之水之類文壇明珠的迅速成長。
奇怪的是,趙麗雅在《讀書》編輯部不出聲色。能為人所不及的,只是她善於與某些位學有素養的學人打交道,為人所不及。因為她在學術上易為人瞭解,善於相處。最瞭解她的是張中行先生。他為此寫了專文,推介趙女士,我看後大驚失色,因為從來沒想到,旁邊這一開卡車出身的自學青年,竟有如此功力。
還有兩朵「金花」是楊麗華、賈寶蘭。這兩位有高學歷,楊女士可能還是碩士。她們來得較晚,而且因學有專長,關注面較狹,瞭解她們的人不多。但她們也都為《讀書》作了不少貢獻,稱之為「金花」而無愧。
說起《讀書》,大家都太注意女性的成就,其實除了「金花」外,還可注意一下「鋼球」。我指的是王焱。王君也是自學出身,當過巴士的售票員。他自己報名投考而來。進入《讀書》未久,即以學術見長。所以,沒過多少年,我即申報他為《讀書》編輯部主任。他凡事均可從學理上申說,實在高我一等。他與趙麗雅,後來都因學術成就顯赫,由自學青年而成學術教授了。
除了上述各位,來過《讀書》的「知青」尚多,恕不一一細說。知青政策的因禍得福
回憶及此,覺得不妨再說說當年偉大領袖的「知青」政策。上面說過,從《讀書》當年的情況看,知青上山下鄉倒也並非壞事。因為他們經過這一番歷練,知道求知之艱難,學術之可貴,於是工作起來,對學問讀書之道倍感興趣,對工作更加熱愛。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同作家的交往。如我認識金克木先生久矣,但即使交往很多,金老不會贊佩我的學識。而我推介趙麗雅去見金克木先生,金老立即嘆為奇才,一次交來稿件五篇。
那麼「知青」的學識是否全是來自艱難環境下的自學呢?自然,這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我仔細觀察,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是「家教」。知青當年不論如何生活艱苦,所以孜孜不倦者,幼小的家教是個重要因素。有了「書香門第」的家教,以後生活再艱苦,他們自然離不開書本和學問。一旦環境轉變,自然刻苦向學,而且學起來比常人快且易於收效。因為只有嘗過多年的「窩窩頭」,方知大米飯及饅頭之香也。
因是之故,我在「三聯」以後的年月中,十分注意吸收家中有良好的知識環境的知青。以後,翻譯編輯室的迮衛、倪樂等人,就都返鄉進入「三聯」。迮衛的祖輩和父母輩是外交官員,自幼研習外語。倪樂是「同仁堂」後裔,在「文革」中淪為售貨員,以後出洋讀書,遂成英語專家。
我不知道以後的發展情況會如何,在當年,所謂「知青」政策倒促使三聯書店在人事政策上取得了成功。因為,「真金不怕火來煉」是也!
辦公室裡的紅燒肉
在這種氛圍下,我這個頭頭如何辦呢?
我從來不懂學術,說實話,也對這一點沒有興趣。我一直奇怪,如趙麗雅,過去比我文化程度還低,何以現在對《詩經》之類誦之不倦。她過去寫的著作,我還翻讀一下。現在寫的專著,不僅買不起,而且實在讀不動,所以簡直不買。其實她現在講的,我理應大感興趣。例如談古代人的飾物。我是從小為女士們製作飾物出身的,但是對趙女士深研春秋戰國以來仕女的飾物歷史,我卻只有嘆服,絕不細研她的學術大著。可惜不是出身於學術世家,對於讀書明理,從來只認為是一個人生求飽的出路,而不是學術嚮往。幾十年來,我都是功利觀念來看自己所面對的種種,求其應對之道,而沒有耐心求學的意願。對我這小上海人來說,功利主義的侵蝕實在太厲害了。
因此,我之團結文人,籠絡部下,所用之道,不是學術感染,而是功利。功利也者,範圍何其廣泛,而我手中所恃極為有限。無奈之下,我還是常想到自己在做學徒時的缺食少吃之苦,所以常有一些廉價食物來籠絡同儕乃至文人。
我發現,當時市面上有一新產品名「高壓鍋」,插上電後可以立即產生高溫,持續很久。於是我購置一具,放在辦公室,上班後即在其中放入豬肉、醬油、黃酒、白糖之類,不久肉香四溢。中午開鍋邀友大嚼,加上啤酒、燒餅,遂成佳餚。這一味,有時還加上別的菜,打動不了那些“金花”,但是如丁聰老人之流,自然會聞味而來,因為他們都是肥肉之同好。
舉紅燒肉只是舉例子。事實上,我不斷採取此類「大嚼」政策,賴以團結作者、同僚。後來當然發展為去飯館大嚼。我於是編出了周邊飯館的清單,大家瀏覽,隨便點名前去。這名為大嚼,實際上是一種團結文士的手腕。領導文化而到了這地步,惜哉!朱楓的故事
講到我如何賞識台灣的文化,還可再敘一敘朱楓的故事。
上面說過,我多年來十分賞識這位女士。這不僅因為她是三聯書店的前輩,而且由於,我同朱女士的家屬,有較多的關係。
朱楓出身鎮海,這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我說過,我學徒時,老闆即我的師傅就是鎮海人。於是,他們把我的戶口本上的籍貫填為「鎮海」。這是我這個當年的小廝覺得很光榮,於是我拼命學鎮海土話,瞭解鎮海情況(可是直到現在我沒去過鎮海一次)。
朱楓的先生,一九四九以後是北京國際書店的頭頭,我聞名未久。不過他是高幹,當年我這是一個辦事級的小幹部,無緣結識,只是聞名而已。但是朱楓的一位姑表姐妹,卻當過人民出版社資料室負責人,算是認識。更重要的是,這位女士的兒子朱輝,卻多年同我在一個部門工作,至今還有交往,而且住在一個樓群裡面。
我最近特別關心此事,還因為上海遠東出版社在二00七年出版了一本書,馮亦同著:《鎮海的女兒——朱楓傳》。此書出版未久即被禁,不解何故。但因被禁,引起我的巨大興趣,千方百計覓得一本,細讀一過。我由此書得知作者很多材料得諸馮修蕙女士。啊哟,哟!馮女士是我在人民出版社的老領導,極其熟悉。原來,馮女士的丈夫萬經光先生即是引導朱女士去台灣做勸降工作的這裡的官員。萬先生我也見過。但我從來沒聽馮女士講過這類故事,這想必是當年「黨的紀律」之故。現在一切知悉,自然快何如之。
這本《朱楓傳》我一讀再讀,並且盡力在三聯書店同事中宣傳。現在三聯書店也極其重視其事。最近蒙台灣同胞努力,將朱女士遺骨遷至鎮海,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三聯書店的領導親自蒞臨。從這裡看,三聯書店同台灣同胞有了血肉之緣。據說,三聯書店現掌門還要去台灣開分店。這些使我這個兩岸交往迷大為高興,為之暗暗興奮不已。
五朵金花
《讀書》初創,即已聲名鵲起。主持人都是名流,前面已一一表過。然而,奇怪的是,主持人以下,卻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後來很多也都文明昭著,但當年畢竟是小人物。
說這些小人物文化程度不高,不確。準確地說,應是學歷不高。這是那個年頭的特色。在「偉大領袖」指示的光輝照耀下,眾多青年無法上學,初中畢業即已上山下鄉。所以在改革開放剛起步的那些年頭要招員工,要招有高學歷的青年實在很難。
三聯書店特別是《讀書》雜誌的這些激進青年,後來名聲大噪,人稱「五朵金花」。她們都是女性,因謂。
「五朵金花」中的第一朵自然是董秀玉。她不是「知青」,情況與上述有所不同。她是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從上海找來的校對員。她初中畢業後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任那時的蘇聯展覽解說員,展覽結束後,其中不少解說員來北京工作,董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但是此人從小出手不凡,在當年的出版部門中,她最能幹,而且大有當今所說的「女強人」的風範。所謂「女強人」也者,即不甘低男士一頭,凡事必須勝過那些屁男人。我寫過小文表彰過她在某年一起勞動時,男士挑擔一百斤,已稱英雄(我這男士只能挑六七十斤),她忿然而起,挑一百二十斤健步而行,於是眾人拜服,其中自然少不了鄙人這一「小男人」。
董秀玉調《讀書》,我曾出過力,但也只是向范公誇讚其人而已。以後在《讀書》,我想她文化水平不夠,不料她十分勝任。尤其是聯絡作者。比如錢鍾書、楊絳夫婦,對「三聯」始終只信她一人。個中奧妙,我亦不知,在旁盛讚而已。
另一朵「金花」吳彬,吳祖光老先生外甥女(外傳「姪女」,誤。吳彬從母姓,所以姓吳。)。吳祖光先生是范用好友,介紹來此。她是典型的「知青」,初中畢業即去雲南插隊,以後在北京當油漆工人。她從小在文人圈子中長大,出去組稿,凡屬北京文化圈子中的老人,她往往稱叔叔、阿姨,因為都是舊識。僅只如此,還以為她只是靠人際關係才在《讀書》生根發芽的。非也!我曾為一事驚嘆她讀書之多。我多年在北京閒逛,往往見到一些著名的舊宅,上面寫著「某某公府」,知是清代名人的府第。以後見面問吳彬,這某公是誰,她必定立即滔滔不絕地告我這位清代大官姓名為何,官居何職,有何功過大事,根本不用回去查書,即可倒背如流,如數家珍,令我嘆服!
至於另一位「金花」趙麗雅,更是奇人。她開過卡車,做過小販,後來考入《讀書》雜誌。其人身材矮小,訥於言談,初識之時,必定漠然對之。時間越長,發現其人深度越甚。我至今奇怪,一個如此小女子,自學出身,竟然學得如此深入。究竟如何深入,以我淺學,表達也難,大家只要翻讀她以筆名「揚之水」發表的眾多學術論著即知。一個人靠自學而得如此成就,大概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奇蹟。由此不能不說,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其實一點沒有扼殺中國文化,反而大大有助於如揚之水之類文壇明珠的迅速成長。
奇怪的是,趙麗雅在《讀書》編輯部不出聲色。能為人所不及的,只是她善於與某些位學有素養的學人打交道,為人所不及。因為她在學術上易為人瞭解,善於相處。最瞭解她的是張中行先生。他為此寫了專文,推介趙女士,我看後大驚失色,因為從來沒想到,旁邊這一開卡車出身的自學青年,竟有如此功力。
還有兩朵「金花」是楊麗華、賈寶蘭。這兩位有高學歷,楊女士可能還是碩士。她們來得較晚,而且因學有專長,關注面較狹,瞭解她們的人不多。但她們也都為《讀書》作了不少貢獻,稱之為「金花」而無愧。
說起《讀書》,大家都太注意女性的成就,其實除了「金花」外,還可注意一下「鋼球」。我指的是王焱。王君也是自學出身,當過巴士的售票員。他自己報名投考而來。進入《讀書》未久,即以學術見長。所以,沒過多少年,我即申報他為《讀書》編輯部主任。他凡事均可從學理上申說,實在高我一等。他與趙麗雅,後來都因學術成就顯赫,由自學青年而成學術教授了。
除了上述各位,來過《讀書》的「知青」尚多,恕不一一細說。知青政策的因禍得福
回憶及此,覺得不妨再說說當年偉大領袖的「知青」政策。上面說過,從《讀書》當年的情況看,知青上山下鄉倒也並非壞事。因為他們經過這一番歷練,知道求知之艱難,學術之可貴,於是工作起來,對學問讀書之道倍感興趣,對工作更加熱愛。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同作家的交往。如我認識金克木先生久矣,但即使交往很多,金老不會贊佩我的學識。而我推介趙麗雅去見金克木先生,金老立即嘆為奇才,一次交來稿件五篇。
那麼「知青」的學識是否全是來自艱難環境下的自學呢?自然,這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我仔細觀察,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是「家教」。知青當年不論如何生活艱苦,所以孜孜不倦者,幼小的家教是個重要因素。有了「書香門第」的家教,以後生活再艱苦,他們自然離不開書本和學問。一旦環境轉變,自然刻苦向學,而且學起來比常人快且易於收效。因為只有嘗過多年的「窩窩頭」,方知大米飯及饅頭之香也。
因是之故,我在「三聯」以後的年月中,十分注意吸收家中有良好的知識環境的知青。以後,翻譯編輯室的迮衛、倪樂等人,就都返鄉進入「三聯」。迮衛的祖輩和父母輩是外交官員,自幼研習外語。倪樂是「同仁堂」後裔,在「文革」中淪為售貨員,以後出洋讀書,遂成英語專家。
我不知道以後的發展情況會如何,在當年,所謂「知青」政策倒促使三聯書店在人事政策上取得了成功。因為,「真金不怕火來煉」是也!
辦公室裡的紅燒肉
在這種氛圍下,我這個頭頭如何辦呢?
我從來不懂學術,說實話,也對這一點沒有興趣。我一直奇怪,如趙麗雅,過去比我文化程度還低,何以現在對《詩經》之類誦之不倦。她過去寫的著作,我還翻讀一下。現在寫的專著,不僅買不起,而且實在讀不動,所以簡直不買。其實她現在講的,我理應大感興趣。例如談古代人的飾物。我是從小為女士們製作飾物出身的,但是對趙女士深研春秋戰國以來仕女的飾物歷史,我卻只有嘆服,絕不細研她的學術大著。可惜不是出身於學術世家,對於讀書明理,從來只認為是一個人生求飽的出路,而不是學術嚮往。幾十年來,我都是功利觀念來看自己所面對的種種,求其應對之道,而沒有耐心求學的意願。對我這小上海人來說,功利主義的侵蝕實在太厲害了。
因此,我之團結文人,籠絡部下,所用之道,不是學術感染,而是功利。功利也者,範圍何其廣泛,而我手中所恃極為有限。無奈之下,我還是常想到自己在做學徒時的缺食少吃之苦,所以常有一些廉價食物來籠絡同儕乃至文人。
我發現,當時市面上有一新產品名「高壓鍋」,插上電後可以立即產生高溫,持續很久。於是我購置一具,放在辦公室,上班後即在其中放入豬肉、醬油、黃酒、白糖之類,不久肉香四溢。中午開鍋邀友大嚼,加上啤酒、燒餅,遂成佳餚。這一味,有時還加上別的菜,打動不了那些“金花”,但是如丁聰老人之流,自然會聞味而來,因為他們都是肥肉之同好。
舉紅燒肉只是舉例子。事實上,我不斷採取此類「大嚼」政策,賴以團結作者、同僚。後來當然發展為去飯館大嚼。我於是編出了周邊飯館的清單,大家瀏覽,隨便點名前去。這名為大嚼,實際上是一種團結文士的手腕。領導文化而到了這地步,惜哉!朱楓的故事
講到我如何賞識台灣的文化,還可再敘一敘朱楓的故事。
上面說過,我多年來十分賞識這位女士。這不僅因為她是三聯書店的前輩,而且由於,我同朱女士的家屬,有較多的關係。
朱楓出身鎮海,這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我說過,我學徒時,老闆即我的師傅就是鎮海人。於是,他們把我的戶口本上的籍貫填為「鎮海」。這是我這個當年的小廝覺得很光榮,於是我拼命學鎮海土話,瞭解鎮海情況(可是直到現在我沒去過鎮海一次)。
朱楓的先生,一九四九以後是北京國際書店的頭頭,我聞名未久。不過他是高幹,當年我這是一個辦事級的小幹部,無緣結識,只是聞名而已。但是朱楓的一位姑表姐妹,卻當過人民出版社資料室負責人,算是認識。更重要的是,這位女士的兒子朱輝,卻多年同我在一個部門工作,至今還有交往,而且住在一個樓群裡面。
我最近特別關心此事,還因為上海遠東出版社在二00七年出版了一本書,馮亦同著:《鎮海的女兒——朱楓傳》。此書出版未久即被禁,不解何故。但因被禁,引起我的巨大興趣,千方百計覓得一本,細讀一過。我由此書得知作者很多材料得諸馮修蕙女士。啊哟,哟!馮女士是我在人民出版社的老領導,極其熟悉。原來,馮女士的丈夫萬經光先生即是引導朱女士去台灣做勸降工作的這裡的官員。萬先生我也見過。但我從來沒聽馮女士講過這類故事,這想必是當年「黨的紀律」之故。現在一切知悉,自然快何如之。
這本《朱楓傳》我一讀再讀,並且盡力在三聯書店同事中宣傳。現在三聯書店也極其重視其事。最近蒙台灣同胞努力,將朱女士遺骨遷至鎮海,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三聯書店的領導親自蒞臨。從這裡看,三聯書店同台灣同胞有了血肉之緣。據說,三聯書店現掌門還要去台灣開分店。這些使我這個兩岸交往迷大為高興,為之暗暗興奮不已。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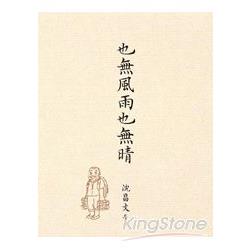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