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E691-1~3孔薏《藥妻甜夫》全3冊
依親的表小姐進王府當天就碰上表哥趙澈墜馬昏迷,
事主徐靜書都想哭了,因為從風俗上來說就是她帶衰啊……
為了留在這最後的庇護所,她不顧自己瘦弱的小身板,
低調貢獻出擁有解毒療效的血,救命之恩讓她一躍成為座上賓,
表哥還將象徵身分的玉佩給了她,
不過歸他罩也不是簡單的事,得三不五時做個甜點賄賂他,甜他的嘴,
一樁失蹤案勾起了她的噩夢,幸好這回有他挺身護她,
明白她的憂心和抱負,他不僅為她延請夫子,
得知朝中有急缺,立刻動用人脈安排她先行面試,
新任殿前糾察御史的她不僅在聖上面前和老臣廷辯,
還以一打二駁得他們無話可說,成為儲君推行新政的大幫手,
不過破除陋習這件事也砍到了姑父信王身上,
為了讓府中眾人免受牽連,他逼著姑父讓出爵位,前提是他得成親……
(熱銷再現,精製封面二版)
依親的表小姐進王府當天就碰上表哥趙澈墜馬昏迷,
事主徐靜書都想哭了,因為從風俗上來說就是她帶衰啊……
為了留在這最後的庇護所,她不顧自己瘦弱的小身板,
低調貢獻出擁有解毒療效的血,救命之恩讓她一躍成為座上賓,
表哥還將象徵身分的玉佩給了她,
不過歸他罩也不是簡單的事,得三不五時做個甜點賄賂他,甜他的嘴,
一樁失蹤案勾起了她的噩夢,幸好這回有他挺身護她,
明白她的憂心和抱負,他不僅為她延請夫子,
得知朝中有急缺,立刻動用人脈安排她先行面試,
新任殿前糾察御史的她不僅在聖上面前和老臣廷辯,
還以一打二駁得他們無話可說,成為儲君推行新政的大幫手,
不過破除陋習這件事也砍到了姑父信王身上,
為了讓府中眾人免受牽連,他逼著姑父讓出爵位,前提是他得成親……
(熱銷再現,精製封面二版)
試閱
第一章 謊報生辰救表哥 大周武德元年七月廿三夜,戌時近尾。 長信郡王府內,夜露凝枝,月色氤氳著秋意,客廂庭前,徐靜書立在孤植的朱砂丹桂下,雙手攏於寬袖,瘦小身軀融進暗夜樹影。 時值初秋,枝頭有初綻的桂子悄悄遞散著馥鬱,她接連深吸氣,不斷將那甜津津的蜜香納入肺腑。 「表小姐怎地站在風口?」從外頭回來的侍女念荷匆匆迎上,溫聲勸說:「入秋夜風撲人,表小姐身子弱,又有傷,當心著涼。」 念荷是長信郡王府侍女,進府不到半年,之前只做粗使活計,三日前,前來投親的表小姐徐靜書被安置在此住下,念荷托她的福,被總管臨時升等,撥來照應飲食起居。 徐靜書身形較同齡人瘦小許多,投親路上又逢波折磨難,身上帶了些傷,慘白小臉不見血色,病懨懨叫人生憐。 「多謝念荷姊姊關懷。」徐靜書彎了笑眼,細聲訥訥,「我睡不著,透透氣。」 她是長信郡王妃的侄女,雖是五服之外的旁支遠親,那也是實打實的血脈親緣,府中誰都得恭敬稱她表小姐,念荷哪敢當她這聲姊姊。 「表小姐喚我念荷就好,」念荷挪了步子,以身替她擋風,「我瞧您每頓都吃得少,可是餓了才睡不著?」 徐靜書猛地挺直小腰板,認真道:「不餓的!我本就吃得很少,每頓只一點點就夠。」 她使勁眨眨眼,話頭一轉,「念荷姊……念荷,妳是去含光院了嗎?大公子可醒了?」 含光院是郡王府大公子趙澈的居所。 念荷搖頭道:「含光院這幾日不許旁人近前,我只找了白日在裏頭當值的小姊妹打聽,據說大公子還是沒醒。」 這消息讓徐靜書笑容發僵,兩耳嗡嗡響,連幾時被念荷送進寢房都不知道。 三日前的黃昏,長信郡王府大公子趙澈與友人在鎬京東郊遊獵,不慎墜馬傷及頭部,當場昏迷,郡王府立刻就炸了鍋。 長信郡王趙誠銳立刻進內城請了聖諭,帶回幾名太醫替趙澈診治,三天兩夜過去,趙澈絲毫沒有醒轉跡象,太醫們也束手無策。 郡王府內一時人心惶惶,眾人各懷心思,卻都不約而同關切著含光院的動靜。 雖然還沒與那位表哥見過面,可徐靜書發自肺腑祈望他安度難關、儘快甦醒。 她是在趙澈出事當天早上前來投親的,按鄉間忌諱,有客登門時若家裏人出了事,這客無論如何都不能留。 徐靜書不清楚郡王府內會不會也有這講究,若有,那她真不知自己還能去哪裏。 欽州堂庭山鄉下雖有她的母親,可母親有了新的夫婿和新的兒女,對那個家來說,徐靜書只是個浪費米糧的累贅,好不容易才送走,誰會樂意她再回去? 長信郡王妃徐蟬是徐靜書出了五服的遠房姑母,她千里迢迢上鎬京來投親,說來有點厚臉皮,可除了這位八竿子才能打著的遠房姑母,她再無可投靠的去處。 想到這些,徐靜書扁著嘴蹲在牆角,於黑暗中抱頭縮成一團,像隻倉皇落單的幼獸。 她今年十一,沒有家,沒有可供撒嬌耍賴、予她庇護的親人,沒有一技之長,甚至沒有足以養活自己的強健身軀,好不容易有個遠房姑母肯收留她,卻又遇到這樣的事…… 或許明日就要被趕走了吧?到底要怎麼做她才能活下去? 亥時,院外響起嘈雜人聲,徐靜書忙收好落寞思緒站起來。 她起得太急,眼前霎時一片白茫茫,兩腿又因蹲太久而發麻打晃,幸虧及時伸手扣住窗櫺才沒摔倒。 細瘦右腕裹著傷布,死命扣住窗櫺時太過用力,將癒未癒的傷口再度繃開,新鮮血跡迅速滲出,她未覺疼痛,左手按住狂跳的心口,小心將窗戶拉開一道縫,屏息凝神向外張望。 難道是等不及天亮,這就要將她趕走了? 念荷匆匆披衣出來應門,客院門外的陣仗讓她發懵,呆立半晌才想起要行禮,「孫總管夜安……」 「虛禮就免了,急著呢。」總管孫廣語速匆匆,「我記得妳是陽年陽月出生的,那妳出生時辰是?」 念荷不明白總管特地來問她生辰是要做什麼,卻又不敢亂問,老實應道:「癸卯時。孫總管大約是記差了,我生在乙丑年……」 「不是陽年啊……也不是陽時……」孫廣失望歎氣,急得想跺腳。 「孫總管可是要尋陽年陽月陽時出生的人?」從寢房奔出的徐靜書單手按在腰間,站在念荷身側喘聲急問。 門口高懸的燈籠灑下昏黃光暈,照著瘦小蒼白的臉龐,也照亮她眼中的熱切。 「表小姐夜安。」孫廣得體執禮,「正是。事情急,一時沒法去府外找人,驚擾表小姐歇息了。」 「無妨。」徐靜書垂下顫抖的睫毛,使勁嚥了口水潤著乾澀喉嚨,唇角揚起笑弧,「我是,我是純陽生辰。」 早年外頭戰亂不歇,偏僻鄉間沒處求醫問藥,能墾些荒山野地養家活口就算天可憐見,若不幸遭逢病痛,只能靠口口相傳的土方尋些草藥,至於服下後能否好轉,全靠各人的緣分各人的命。 如此一來,不少人便將活命的希望寄託於鬼神、巫祝,越是窮鄉僻壤、深山蠻荒,對方術、巫醫之道越習以為常。 長在山間村落的徐靜書對方士、巫醫慣用的法子自不陌生,當她隱約聽到總管孫廣在問念荷的生辰,又念叨「陽年陽月陽時」之類,就大致猜到所為何事。 趙澈昏迷三天兩夜,連太醫們都沒法子,想來長信郡王夫婦是偷偷尋了方士或巫醫,這八成是需要純陽生辰的血替趙澈解厄消災。 徐靜書立刻就想到,若自己對這府中能有點用處,想必就不會被趕走了,為避免流落街頭,她得賭這把。 到了含光院,瞧見郡王夫婦跟前那灰白道袍的遊方女術士,徐靜書心中巨石稍落半寸。 見孫廣竟領來投靠自己才沒幾日的遠房侄女,郡王妃徐蟬眉心蹙緊,轉頭看向自家夫婿。 長信郡王趙誠銳是今上的異母弟弟,是個不擔朝職的富貴閒王,為著昏迷不醒的長子,他已三天兩夜未曾合眼,此刻雙目佈滿血絲,焦躁又憔悴,哪有心思留意旁的。 孫廣解釋道:「宵禁將啟,不便出外另尋他人。查遍府中,實在只表小姐一個純陽生辰的姑娘……」 趙誠銳揉揉眉心,舉目看向瘦小的徐靜書,「為救妳表哥,也是沒旁的法子才如此,需取妳三滴血,再勞煩妳在他跟前守一夜,不會傷妳性命。只要妳表哥能醒轉,姑父姑母今後絕不虧待妳,妳可願意?」 沙啞疲憊的嗓音裏滿是誠摯懇求,貴為郡王,又是長輩,這姿態著實算放得很低了。 徐靜書怯怯垂著臉不敢直視,只輕輕點頭,「願意。」 遊方女術士說,欲使趙澈醒轉,除了要徐靜書三滴「純陽血」化入符水給他喝下,還需借助她的「純陽氣」。 女術士將寢房內的侍者全數遣出,點了清香符紙在裏頭淨了一遍,便出來與長信郡王夫婦一道等在外頭,只讓徐靜書單獨入內。 徐靜書小心翼翼地捧著那碗化了三滴血的符水,繞過屏風慢慢走向內間。 床榻上躺著位長身少年,雙目緊閉,面無血色,昏迷三天兩夜水米不進,他的唇瓣呈虛弱淡粉,乾燥發皺,翹著點白色的皮,可即便如此,他仍是個好看到不像話的矜貴公子。 徐靜書將符水放在床頭小櫃上,站在床畔垂眸打量這位初次見面的表哥,心中沒來由地篤定道:他的眼睛必定也極漂亮。 出神片刻,她捏著小拳頭揉揉酸澀的眼眶,告密似的軟糯低喃道:「符水是騙人的。」五歲那年,她眼睜睜看著爹喝下符水,可隔天就沒了。 「純陽生辰也是假的。」她和那女術士沒兩樣,都是騙子,「就這一回,往後我一定做個誠實正直的好人。我不會一直賴在你家,等長高些,能尋到差事糊口就走。」 她想了想,小聲補充,「將來做工掙錢了,我每月送一半工錢回來。我在你家也不吃白食,能幫忙做許多事,我雖然力氣小,不能挑水劈柴,但我會洗衣做飯,會照顧小孩子,會做好吃的糕點。我脾氣也好,往後你若不高興,我哄著你、讓著你,我還很聰明……」 她頓了頓,望著床榻上氣息微弱的少年,兀自點頭強調,「是真的,我爹說的。」 昏迷中的少年聽不見也看不著,自無任何回應。 「我不知是不是當真可以救你,但我必須試試,不然我就沒處去了,」徐靜書鄭重對床榻上鞠了一躬,「總之,求你一定要醒,拜託了。」 單方面談好條件後,她以舌尖潤著自己乾澀的唇,四下梭巡一番,最終將目光落在枕畔。 枕下露出匕首外鞘的尾端一截,鎏金雕花嵌著紅色寶石,在長燭燈火下爍著幽光。 徐靜書艱難嚥下喉頭哽阻,慢慢朝那匕首探出手去,指尖不住輕顫…… 雖說徐靜書年紀小,沒多大見識,但有父親的前車之鑒,她是打心底不信方術、巫醫能救人性命的,既然方術、巫醫不能信,那碗懸浮著紙灰碎屑的符水就更不能信了。 她緊攥著從趙澈枕下摸來的匕首,端著符水躡手躡腳走到窗畔花几前,將符水全數倒進花盆,這才走到圓桌旁,揭開桌上的瓷壺蓋子,定睛一看,裏頭是半壺早已涼透的白開水。 她放下心,去外間角落的紅泥小爐上倒了滾燙開水,將空碗刷乾淨,再回來時,她又忐忑地瞧了一眼床榻上的少年,最終咬牙在圓桌旁坐下,慢慢捲起衣袖,神情悲壯。 進京投親的路上遭遇頗多波折,她從老家帶出來的小行李早不知落到何處了,到長信郡王府那日沒有換洗衣衫,徐蟬便命人去郡王府二姑娘那裏拿了幾套舊衣裙給她先將就著。 據說那位二姑娘比她小半歲,可人家的衣衫在她身上足足大了兩圈,衣袖又空又長,將她的手遮得只能瞧見五個指尖。 徐靜書扁扁嘴,將過於寬大的衣袖捲至手肘,露出乾瘦細腕上沁血的傷布。 她閉眼深吸一口氣,屏除腦中雜念,將傷布一圈圈解開,吹吹已繃裂的舊傷,彷彿這樣能止疼。 將瓷壺中倒出的那碗涼開水喝去小半,沁涼白水猛地入喉,直落胃袋,驚得她一個激靈,腦中霎時清明。 要涼水承接,這樣才不會很快凝固。 照之前的實例,若從右腕取血,致死的機率小些。 對,沿著這裏劃開,刀口切莫偏了。待血湧出後數到十,迅速扎緊傷口上方脈跳處。 她握緊匕首,極力回想那些人取她活血時的畫面與言詞,照著記憶中的痛楚紋路,一絲不差地劃拉開去。 不怕的,她很聰明,不會記錯。 七月廿四寅時,日夜交替之際,整個鎬京都在昏昏殘夢中將醒未醒。 隨著寢房門慢慢打開,廊下候了一夜的長信郡王夫婦倏地從椅子上站起,一旁的侍從們也繃直腰背,全都屏息凝神緊望著徐靜書。 清冷晨風拂過衣襬,越發顯得她身軀瘦小孱弱,慘白的小臉上隱隱透點青,雙眼發直,恍兮惚兮,半晌找不著落點,這副模樣叫人看不懂事情端倪。 徐蟬被驚得兩腿發軟,在侍女的攙扶下顫顫迎上去,「靜書,妳表哥……」 聽到徐蟬的聲音,徐靜書勉強定住渙散的目光,抬頭怔怔衝她揚了唇,「他疼,在哼哼。」 據太醫們的診斷,趙澈墜馬觸地時傷及頭部造成昏迷,連日來是五感盡失,若已能哼哼喊疼,也就是說——他醒了! 之後含光院又發生了什麼,徐靜書全不知情,她在念荷的攙扶下回到客廂,恍恍惚惚嘀咕了句「我先睡會兒」,便兀自和衣而臥,軟綿綿地蜷進被中,彷彿周身精力全被抽乾,整個人像具忘了填塞中空的皮偶。 睡一覺就會好。以往每次有病有傷,都是睡一覺就好的,她不怕。 徐家祖上在淮南是小有名聲的書香之家,但徐靜書生不逢時,沒趕上家裏風光的年月,實在不是個身嬌體貴的命。 她父母成婚不久,異族鐵蹄就侵門踏戶,前朝亡國,短短數月之內,江左三州呈流血漂鹵、十室九空的慘狀,僥倖活下來的年輕夫婦倉皇逃到江右,狼狽輾轉數年,終於回到徐家先祖最初的來處——欽州堂庭山間的破落村莊。 夫婦倆在人煙稀少的山間小村結廬而居,墾點荒地勉強度日。 她父親原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母親更是碧玉嬌嬌的大小姐,兩人年少時都十指不沾陽春水,突然要靠耕種活口,艱難潦倒可想而知。 到徐靜書五歲時,父親積勞成疾,不到三十就撒手人寰,母親獨自帶著她,日子過得越發艱難,苦撐三年後,她母親應了同村胡姓莊稼漢的求親,母女倆總算能一日吃上兩頓飯。 如此身世的徐靜書自不會是溫室嬌蘭,看著身板瘦小、性子怯軟,卻禁得起風雪,耐得住摧折,絕不會輕易倒下。 從卯時睡到未時,足足五個時辰後,徐靜書被餓醒了。 扶牆出了寢房,發覺不知何時下起了雨,雖說雨不大,到底「一陣秋雨一層涼」,她又才從暖呼呼的被窩裏出來,當即被撲面涼意激得縮了脖子。 吃飯時,念荷見她冷得唇色發白,愁眉不展地道:「早前從二姑娘那裏取來的幾套衣衫都不大厚實,這……」 當初借二姑娘的衣衫只是事急從權,郡王妃原打算過後再請人來替徐靜書量身裁製新衣,哪知跟著趙澈就出了事,再沒顧得上她這邊。 徐靜書乖巧地笑了笑,「我也沒旁的事,待會兒還回床上裹著被子吧,雨停了就不冷了。」 口中說著話,她的目光卻始終黏在碗底最後一點雞茸粥上,就剩一丁點兒了,用甜白小匙刮了半晌也舀不起來,這讓她有些焦灼。 掀起眼簾偷覷了念荷一眼,見她正皺眉打量著外頭的雨勢,徐靜書飛快端起碗湊到小臉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碗底那點粥舔得乾乾淨淨。 念荷回頭時她已將空碗放到桌上,假作鎮定地將雙手置於兩腿,「我吃好了。」雖明知念荷並未瞧見她方才的舉動,可她還是覺得赧然,雙頰隱隱燙紅。 「我再去廚房拿一碗吧?」念荷見她吃得乾淨,尋思是沒吃飽的。 徐靜書堅定搖頭道:「已經飽了。」才怪。 到長信郡王府這些日子,她始終有寄人籬下的自覺,不好意思多耗姑母家米糧。 怕念荷還要勸,她趕忙另起話頭,「含光院那頭如何了?」 「我方才去大廚房取粥時,聽人說大公子已醒了,送去的雞茸粥都吃下半盅呢。」 徐靜書一口長氣還沒吁完,就聽念荷又道:「可大公子的眼睛似乎瞧不見了。」 啊?徐靜書猛地抬頭,才有點血色的小臉又轉白,聲氣虛弱,「怎麼會呢……」難道她的血有問題?不應該啊。 念荷將自己零碎聽來的消息轉述一遍,「太醫們說,大公子墜馬觸地時磕著頭,腦中有血瘀,需長久服藥慢慢化開才能復明。」 聽完這話,徐靜書才慢慢鬆了肩,她雖半懂不懂,卻對太醫們的診斷深信不疑,太醫可是在內城給皇帝陛下看診的大夫,不會騙人的。 重新回到寢房裹進被子裏,徐靜書卻睡不著了,她後知後覺地想起,趙澈乍然失了目力,心裏不知有多難受。 「太醫說的長久服藥,到底是多久?」她使勁撓了撓頭,煩躁地嘀咕著,若他的眼睛很久都不好,那她算是救了他,還是沒救他?到底會不會被趕走啊? 念荷見徐靜書沒有再睡的意思,便端了熱水,又拿了新的傷布與藥膏進來。 「早上表小姐回來就睡沉了,我怕吵著您,沒敢換藥。」 徐靜書裹著被子坐在床上,低垂眼睫道:「我可以自己來。」 「那哪兒成?」念荷端了凳子坐在床前,擰巾子先替她擦了手臉。 她身上有傷口,這幾日念荷都只能替她擦擦,不敢讓她沐浴。 「呀,傷口怎麼又繃開了。」念荷小心替她吹著,解著舊傷布的動作越發輕柔。 徐靜書頓了頓,抬起臉笑彎了眼睛,「大公子躺著嚥不下東西,我扶他起來時繃開的。」 這解釋在念荷聽來順理成章,倒也沒多想,另拿了乾淨濕棉布,一點點將傷口周邊的血汙拭淨。 徐靜書脊背繃緊,卻不喊疼,只不停嚥口水。 念荷正準備替她重新上藥時,房門被推開,一位粉色衣裙的漂亮小姑娘大搖大擺走了進來,見著來人,念荷立刻起身請安,「二姑娘安好。」 來的是長信郡王府二姑娘趙蕎,趙澈的異母妹妹。 「在上藥啊?忙妳們的。」趙蕎擺了擺手道:「我母親說下雨了,天冷,讓我給……」她盯著徐靜書的小瘦臉稍作猶豫,片刻後繼續道:「給表妹送幾套衣衫過來應急。」 念荷忍笑,小聲提醒,「表小姐比二姑娘大半歲,該是表姊。」 「她小小一隻,怎麼是我表姊?」趙蕎將手中那疊衣衫放在床尾,撇撇嘴,「就是表妹,不許強嘴。」 「那、那就表妹吧。」徐靜書衝她笑,「多謝二姑娘的衣衫,給妳添麻煩了。」 「嘖,妳怎麼跟著叫二姑娘?」趙蕎皺起鼻子衝她做怪相,「叫表姊。」 徐靜書與長信郡王府這門遠親,順的是郡王妃徐蟬母家血脈,論起來已是八竿子才能打著的關係,而這位二小姐趙蕎的母親,是長信郡王的側妃孟貞,她與徐靜書之間可真是八竿子都打不著。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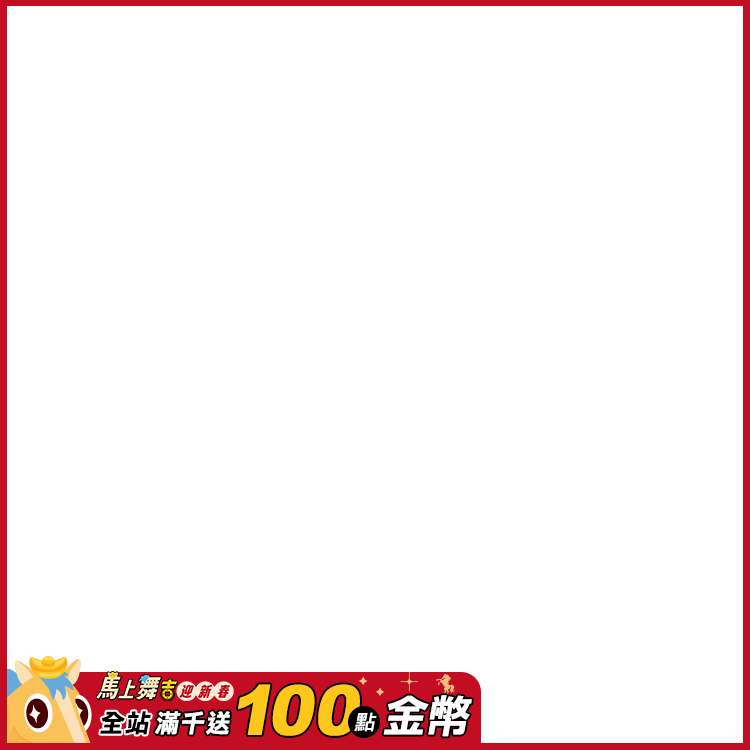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