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環:論語與雞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透過一個讀私塾(書房)的學生的眼睛,觀看村民們為了砍伐竹子引發衝突,斬雞頭發誓清白的行徑,刻畫教授「論語」的夫子,如何斯文掃地的搶先撿回被砍頭而丟棄的死雞。寫出了少年幻滅的悲哀,及臺灣傳統書房教育式微的種種樣貌。
作者那無可奈何的心情、淡淡的諷刺、追憶懷舊的情緒,就像「論語」與「雞」不合諧的放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盡在不言之中。
延伸閱讀:日據時代的教育制度、私塾
作者那無可奈何的心情、淡淡的諷刺、追憶懷舊的情緒,就像「論語」與「雞」不合諧的放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盡在不言之中。
延伸閱讀:日據時代的教育制度、私塾
序/導讀
張文環有不少小說反映了嘉義梅山山村的生活經驗,他有意把梅山的山村世界,當作臺灣社會的縮影來看待,這篇小說雖然沒有明顯指出時空,但大致可推估是作者熟悉的20年代的山村,一個日本文明已經吹進山村,而山村的價值觀也在改變之中。
小說透過一個讀私塾(書房)的學生阿源的眼睛,來觀看村民們為了砍伐竹子引發衝突,斬雞頭發誓清白的行徑,刻畫教授「論語」的夫子,如何斯文掃地的搶先撿回被砍頭而丟棄的死雞。寫出了少年阿源幻滅的悲哀,及臺灣傳統書房教育式微的種種樣貌。作者花了不少筆墨,描寫傳統私塾教育的細節,家長希望孩子上書房,又擔心先生光收束脩卻偷懶怠惰的矛盾心態。尤其下雨天先生不在,未盡督課責任,任由孩童嬉鬧,一片混亂,家長終於決定領回孩子。過去借功名以求宦途顯達的傳統教育已日漸不受重視,更重要的是「現在連這樣的山裡的小村子,也在高喊日本文明。」在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下,就讀書房的學童,最大的願望竟是「戴上制帽,操一口流利國語(指日語),好好地嚇唬一下這裡的鄉巴佬們。」雖然是小孩的玩笑話,但隨著日本統治帶來的強勢語言的現象,真是很明顯了,會講國語(日語)即代表高人一等的想法,已經使天真孩童傾向接受、模仿日本文化。這種種的描寫,都有意無意的指出:新時代的自由空氣已經吹進了山村,書房教育好像寒風中的殘燭。
作者被認為是臺灣風俗民情作家的能手,在故事一開始就出現村人為了慶典拜拜,夜間排練陣頭、舞獅的祭典;老人聚在雜貨店前賭錢吃酒,聽學堂先生講三國故事;遇到紛爭,訴諸良心及神明的制裁,似乎一切仍保存原來的傳統漢族社會,村人們的步調生活想法並未因統治者變了而有改變。風俗題材的應用,有的呈現野蠻殘酷,有的體現地方、民族特點的各種傳統生活和生活習慣,張文環的小說風格即屬於第二類,為作品增色不少,尤其本篇小說最引人入勝的情節,在於描寫中元時節,村民們為了偷砍竹子引發言語衝突,爭執不休,最後決定到有應公斬雞頭發誓清白,細節寫得很細膩,書房先生做公證,一大群學生自行尾隨做旁證,陳砍雞一刀,雞頭未斷,鄭再砍一刀,將雞丟下崖下竹林,見證的先生竟跳下崖去撿半死的雞。為了撿雞,先生忘了斥回一群溜出學堂的學生,為了忙拔雞毛,撒下學生不管,那一身奮力追雞的窘態,對照前頭經營的道學先生形象,阿源能不因之「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這些活潑潑的山村民俗風的描繪,將書房沒落、新文明入侵、成人世界的虛偽、道學先生的失責、貪婪齷齪,以及少年學子對學堂新式教育多樣課程的期待等等,在回溯中從容不迫的帶出來。
小說對小孩子心理、動作的掌握很傳神,如做錯事怕被處罰而撒嬌的情態,先生不在而恣意撒尿的行為、想脫離父親的掌握以享有自由行動的想法等等。起初阿源對先生有種嚴肅的感覺,只有先生不在時他才能暫時解脫束縛,享受那肆意撒野的快感,這正是阿源想脫離權威的潛在慾望,直到搶雞一事發生,他才脫離權威的壓抑,從原有懦弱性格領悟成長,敢在與父親、叔叔的對話中,說出他心中的不屑。這樣的一個轉變過程,很像青少年成長蛻變的歷程。小說透露的訊息,解讀的角度本來就可以有多面性,這篇小說中被嘲弄的小丑式人物書房先生,其被嘲弄的緣由,應該是他那猥瑣、貪吃的性格吧。為了臭豆腐和酒,老師也溜課,放著學生不管,為了飽食一頓雞肉餐,一般人都不願撿食的被咒誓的死雞,他毫不顧形象,跳落崖下爭取。書房先生對食物的態度,呈現了他的怪異,只要與吃有關的事物,他已經無法顧及做為老師應該有的自律自尊。當然,對處於戰爭末期、物資缺乏的臺灣人民來說,(尤其是子曰店沒落,收入拮据的先生)要以自然的態度應付食物、生活也有些困難,作者的這一絲絲嘲諷,並非用以譏笑人物的卑微,背後裡實有著無限的惋嘆同情。
小說發表的時間雖是1941年,但並未呈現臺灣籠罩在戰爭陰影之下的氛圍,反而省思了臺灣傳統書房教育日漸式微的實相,是當時真實的歷史寫照。日據初期負有延續斯文於一線的傳統書房,至統治末期真是搖搖欲墜了,作者那無可奈何的心情、淡淡的諷刺、追憶懷舊的情緒,就像「論語」與「雞」不合諧的放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盡在不言之中。
小說透過一個讀私塾(書房)的學生阿源的眼睛,來觀看村民們為了砍伐竹子引發衝突,斬雞頭發誓清白的行徑,刻畫教授「論語」的夫子,如何斯文掃地的搶先撿回被砍頭而丟棄的死雞。寫出了少年阿源幻滅的悲哀,及臺灣傳統書房教育式微的種種樣貌。作者花了不少筆墨,描寫傳統私塾教育的細節,家長希望孩子上書房,又擔心先生光收束脩卻偷懶怠惰的矛盾心態。尤其下雨天先生不在,未盡督課責任,任由孩童嬉鬧,一片混亂,家長終於決定領回孩子。過去借功名以求宦途顯達的傳統教育已日漸不受重視,更重要的是「現在連這樣的山裡的小村子,也在高喊日本文明。」在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下,就讀書房的學童,最大的願望竟是「戴上制帽,操一口流利國語(指日語),好好地嚇唬一下這裡的鄉巴佬們。」雖然是小孩的玩笑話,但隨著日本統治帶來的強勢語言的現象,真是很明顯了,會講國語(日語)即代表高人一等的想法,已經使天真孩童傾向接受、模仿日本文化。這種種的描寫,都有意無意的指出:新時代的自由空氣已經吹進了山村,書房教育好像寒風中的殘燭。
作者被認為是臺灣風俗民情作家的能手,在故事一開始就出現村人為了慶典拜拜,夜間排練陣頭、舞獅的祭典;老人聚在雜貨店前賭錢吃酒,聽學堂先生講三國故事;遇到紛爭,訴諸良心及神明的制裁,似乎一切仍保存原來的傳統漢族社會,村人們的步調生活想法並未因統治者變了而有改變。風俗題材的應用,有的呈現野蠻殘酷,有的體現地方、民族特點的各種傳統生活和生活習慣,張文環的小說風格即屬於第二類,為作品增色不少,尤其本篇小說最引人入勝的情節,在於描寫中元時節,村民們為了偷砍竹子引發言語衝突,爭執不休,最後決定到有應公斬雞頭發誓清白,細節寫得很細膩,書房先生做公證,一大群學生自行尾隨做旁證,陳砍雞一刀,雞頭未斷,鄭再砍一刀,將雞丟下崖下竹林,見證的先生竟跳下崖去撿半死的雞。為了撿雞,先生忘了斥回一群溜出學堂的學生,為了忙拔雞毛,撒下學生不管,那一身奮力追雞的窘態,對照前頭經營的道學先生形象,阿源能不因之「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這些活潑潑的山村民俗風的描繪,將書房沒落、新文明入侵、成人世界的虛偽、道學先生的失責、貪婪齷齪,以及少年學子對學堂新式教育多樣課程的期待等等,在回溯中從容不迫的帶出來。
小說對小孩子心理、動作的掌握很傳神,如做錯事怕被處罰而撒嬌的情態,先生不在而恣意撒尿的行為、想脫離父親的掌握以享有自由行動的想法等等。起初阿源對先生有種嚴肅的感覺,只有先生不在時他才能暫時解脫束縛,享受那肆意撒野的快感,這正是阿源想脫離權威的潛在慾望,直到搶雞一事發生,他才脫離權威的壓抑,從原有懦弱性格領悟成長,敢在與父親、叔叔的對話中,說出他心中的不屑。這樣的一個轉變過程,很像青少年成長蛻變的歷程。小說透露的訊息,解讀的角度本來就可以有多面性,這篇小說中被嘲弄的小丑式人物書房先生,其被嘲弄的緣由,應該是他那猥瑣、貪吃的性格吧。為了臭豆腐和酒,老師也溜課,放著學生不管,為了飽食一頓雞肉餐,一般人都不願撿食的被咒誓的死雞,他毫不顧形象,跳落崖下爭取。書房先生對食物的態度,呈現了他的怪異,只要與吃有關的事物,他已經無法顧及做為老師應該有的自律自尊。當然,對處於戰爭末期、物資缺乏的臺灣人民來說,(尤其是子曰店沒落,收入拮据的先生)要以自然的態度應付食物、生活也有些困難,作者的這一絲絲嘲諷,並非用以譏笑人物的卑微,背後裡實有著無限的惋嘆同情。
小說發表的時間雖是1941年,但並未呈現臺灣籠罩在戰爭陰影之下的氛圍,反而省思了臺灣傳統書房教育日漸式微的實相,是當時真實的歷史寫照。日據初期負有延續斯文於一線的傳統書房,至統治末期真是搖搖欲墜了,作者那無可奈何的心情、淡淡的諷刺、追憶懷舊的情緒,就像「論語」與「雞」不合諧的放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盡在不言之中。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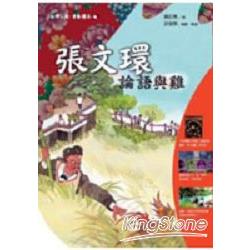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