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樂巨人馬勒:我的時代已經來臨
本書是第一本以中文寫成的馬勒傳記,遍覽所有的馬勒傳記、研究資料,融匯了各家敘述,收入了最新發現...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生於1860年的馬勒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交響曲作曲家。在他手中,交響曲「像這個世界,無所不包」,不僅兼蓄西方古典音樂數百年來發展出的傳統,人聲器樂交相爭輝,各種新奇的樂器也被馬勒納入其中,令當時的聽眾手足無措。
百年之後,馬勒的交響曲已經成為音樂會的常演曲目,指揮與樂團爭取演出馬勒作品的機會不遺餘力。當年令聽眾困惑的跨界拼貼手法,如今卻是這個世界的日常景象。馬勒也因而成為傳記作家的最愛。
本書是第一本以中文寫成的馬勒傳記,作者林衡哲醫師是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催生者,也是馬勒作曲的重度樂迷。在過去的三十年來,他不錯過每一場能欣賞到的馬勒音樂會,他更花了三年時間,遍覽所有的馬勒傳記、研究資料,融匯了各家敘述,收入了最新發現,寫成這本以編年方式寫成的傳記。
百年之後,馬勒的交響曲已經成為音樂會的常演曲目,指揮與樂團爭取演出馬勒作品的機會不遺餘力。當年令聽眾困惑的跨界拼貼手法,如今卻是這個世界的日常景象。馬勒也因而成為傳記作家的最愛。
本書是第一本以中文寫成的馬勒傳記,作者林衡哲醫師是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催生者,也是馬勒作曲的重度樂迷。在過去的三十年來,他不錯過每一場能欣賞到的馬勒音樂會,他更花了三年時間,遍覽所有的馬勒傳記、研究資料,融匯了各家敘述,收入了最新發現,寫成這本以編年方式寫成的傳記。
名人推薦
「對馬勒的生平、經歷有詳盡的記載和生動的描述。讀者像是隨著主人翁一起經歷他五十年生命的每一階段……,對其猶太人的原罪、思想、藝術個性、交往人物至情史也多有著墨。讀者如身處世紀末的維也納,看著藝術史中的重要人物一個個以馬勒為中心,在舞台婆娑演出。而林醫師對馬勒赤子般的熱愛,在字裡行間處處可見。個人對作者描述馬勒死前一段時間之文字,包括許多專業的醫療細節,印象特別深刻,讀後像是親身目睹巨人的殞落,感慨良久。」──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呂紹嘉
「我們同是投入音樂很深的醫師,彼此相知相惜。本書是林衡哲醫師嘔心瀝血的創作,也為馬勒音樂在世界、在台灣留下很好的見證。」──輔仁大學醫務副校長 江漢聲
欽佩林醫師為了心儀的藝術家願意付的代價、願意下的功夫。這樣的代價同功夫,汗顏地講很多所謂職業音樂家都不見得願意擺上。──樂興之時管絃樂團、音樂理想國創辦人/藝術總監 江靖波
「我們同是投入音樂很深的醫師,彼此相知相惜。本書是林衡哲醫師嘔心瀝血的創作,也為馬勒音樂在世界、在台灣留下很好的見證。」──輔仁大學醫務副校長 江漢聲
欽佩林醫師為了心儀的藝術家願意付的代價、願意下的功夫。這樣的代價同功夫,汗顏地講很多所謂職業音樂家都不見得願意擺上。──樂興之時管絃樂團、音樂理想國創辦人/藝術總監 江靖波
序/導讀
自序
一位馬勒迷的心路歷程
我的音樂啟蒙甚晚,或許因為是因為我不是出身音樂家庭的緣故。我大約是在宜蘭中學初三畢業那年暑假,宜蘭大專校友會在故鄉舉行「古典音樂欣賞會」,才初聆貝多芬第四號交響曲。我一聽就入迷了,在內心呼喚著:「這就是我想聽的音樂。」
在台北唸建中的時候,因為讀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以貝多芬為藍本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就成了「貝多芬迷」,還寫過一篇〈貝多芬為什麼偉大〉,得到作文比賽首獎。我在建中隔壁的美國新聞處看到庫塞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在譚格林(Tanglewood)演出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便在內心默默發誓,將來一定要到譚格林聽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
想不到在唸東海大學外文系那一年,我不必出國,就有機會在台灣親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那天是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地點是在台北中山堂。我坐七小時的車子,冒雨前往台北,最後買到了台幣七十元(原價二十元)的黃牛票。但是能夠聽到指揮大師孟治(Charles Munch, 1891-1968)演出貝多芬第三號《英雄》號交響曲,我覺得連靈魂都飛上了天,那是畢生難忘的精神享受。聽過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世紀之音,我此後成為忠實的古典樂迷,當天晚上還寫了生平第一篇樂評〈波士頓交一位馬勒迷的心路歷程響樂團聆賞記〉,想不到平常打分數很嚴格的魯實先教授,給我這篇樂評九十分的高分,使我成為業餘樂評家的信心。
*為了音樂會而重考醫科
當時台中是音樂文化的沙漠,好的音樂會都在台北,我便在一九六○年參加聯考,考上台大醫科。在醫科七年中,我依然是貝多芬迷,兼了不少家教,為的是領到錢之後,可以買貝多芬的原版唱片,或到「田園咖啡」欣賞貝多芬的號交響曲。如果有貝多芬號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的音樂會,就算是碰到考試,我也絕不錯過。大學室友受我的感染,也有不少迷上貝多芬的音樂。不管功課有多忙,我也抽空在《功學月刊》和《愛樂》投稿,除了樂評文章之外,也介紹了不少西方音樂家如文藝復興時代的帕勒斯特利納(Giovanni Palestrina, 1525-1594)、義大利歌劇巨擘貝利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貝多芬音樂的鋼琴權威許納貝爾(Artur Schnabel, 1882-1951),以及南美洲阿根廷的作曲大師琴那斯特拉(Alberto Ginastera, 1916-1983)等給台灣的樂迷。
當時的台灣正處於反共抗俄的年代,國防費用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社會窮困,世界知名的音樂家來台灣的很少。多虧了吳心柳主持的遠東音樂社,我在台大醫學院七年期間,聽了黑人世紀女高音安德遜(Marian Anderson, 1902-1993)、大提琴泰斗皮亞悌哥斯基(Gregor Piatigorsky, 1903-1976)、鋼琴大師塞金(Rudolf Serkin, 1903-1991)以及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要聽這些名家,通常一大早就要去排隊等候。那時我對西方浪漫派音樂家的故事都很熟悉,也看了不少他們的傳記。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主編的「傳記文學精選集」(列入新潮文庫一一○號,一九七四年初版)中,就選了兩篇音樂家的傳記〈怪人華格納〉(狄姆斯‧泰勒著)和〈終生獨身的音樂家────布拉姆斯〉(紐曼著)。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十九世紀末維也納樂壇兩大陣營的對手,也不知道馬勒跟他們兩人的關係。
我在大一日記裡曾列了六十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當時馬勒還是榜上無名。到了大四,我又在日記中列了一百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馬勒才入榜,但我只知道他是一八六○年生在捷克,一九一一年死於維也納,其他事情還不是很了解。總之,我在一九六八年出國之前,從未聽過馬勒作品的現場演出,也沒有讀過他的任何傳記;正如出國之前,我是台灣文化的文盲,蔣渭水、賴和、韓石泉雖是台大醫科前輩,但我對他們的貢獻完全不了解。當時我是馬勒的「樂盲」,崇拜的人物是羅素、史懷哲、卡薩爾斯和愛因斯坦等人,作曲家則是貝多芬,我還在日記中寫道,「史懷哲的音樂情人是巴赫,而我的音樂情人是貝多芬。」
其實,在我唸醫科的一九六○年代,馬勒的音樂已經在歐美復活了。伯恩斯坦的青少年音樂會,台灣也有轉播,那時我也迷伯恩斯坦的指揮風采,他指揮的音樂會我聽過三十多場,但沒有一場是馬勒的音樂。他介紹馬勒的青少年音樂會(包括「誰是古斯塔夫‧馬勒」)的節目,我也都錯過了。
大學時代,我深受蕭孟能《文星》雜誌的影響。《文星》曾經以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和指揮家托斯卡尼尼做過封面人物,音樂雜誌也有不少介紹他們的文章。我在出國前主編《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時,作曲家選史特拉汶斯基,指揮家選托斯卡尼尼,但沒有馬勒。
到了一九八七年,李哲洋才在他主編的《音樂文摘》中,用兩期有系統地介紹馬勒的人與音樂,但那時我已經在美國加州了。二十世紀指揮大師克倫普勒(Otto Klemperer)曾親自受教於馬勒和托斯卡尼尼,他說:「他們兩位都是偉大的指揮家,但就詮釋的深度而言,馬勒比托斯卡尼尼更偉大。因為托斯卡尼尼永遠是托斯卡尼尼,而馬勒指揮莫札特的歌劇,就變成莫札特的化身;他演出華格納時,又變成華格納的分身。」大學時代的我,顯然是有眼不識泰山。
出國之後,在紐約十年(1968-1978)期間,雖然當時透過華爾特與伯恩斯坦在紐約的努力,以及蕭提在芝加哥的不斷演出,馬勒的時代已在美國來臨,但我個人的馬勒時代仍未降臨。我在紐約十年聽了四、五百場音樂會,但有馬勒作品的音樂會,可能不會超過三場。印象較深刻的一場是海汀克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演出馬勒第九。那天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我與台大醫科學長張南雄一同去欣賞,我在日記寫道:「馬勒第九的結尾與一般的號交響曲相反,在平靜的尾聲中結束。」
我在紐約的時候還不是馬勒迷,西貝流士和蕭士塔高維奇的交響曲還聽的比較多;最大的缺憾是沒有聽過伯恩斯坦、蕭提和庫貝利克這三位馬勒大師指揮的馬勒。
*小澤征爾使我變成馬勒迷
一九七八年搬到南加州之後,我已經年近不惑。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聽慕提(Riccardo Muti)指揮費城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一號《巨人》交響曲之後,我在日記寫道:「慕提的指揮充滿活力與流動感,馬勒音樂的高潮如排山倒海而來。有名的費城之音並不因奧曼第(Eugene Ormandy, 1899-1985)的離開而失色,慕提注入了簇新的生命力。」接著一九八六年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南加州的Cerrito演藝中心,演出了馬勒第二號《復活》號交響曲,讓我生平第二次有靈魂飛上天的感覺。不久又接連聆賞拉圖(Simon Rattle)和沙洛南(Esa-Pekka Salonen)指揮洛杉磯愛樂演出馬勒第二號,令人印象深刻,我這才逐漸變成馬勒迷,馬勒的時代才終於在我身上降臨了。義大利指揮大師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擔任洛杉磯愛樂的指揮(1973-1976)之後,也常演出馬勒的經典作品,因此馬勒的時代也終於降臨了南加州的洛杉磯。
一九九七年,維也納愛樂來南加州演出馬勒,我因為買不到票而錯過了。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排隊時認識了一位長堤交響樂團的小提琴家,她發現我是馬勒迷,立刻送我兩張貴賓券去聽女指揮家芙麗塔(JoAnn Falleta)指揮長堤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七號交響曲。雖然這首曲子,印度指揮祖賓梅塔說是他一生碰到最難演的交響曲,但因演出前她做了一場精彩且平易近人的樂曲解說,加上演出非常感人, 贏得全場起立鼓掌。因此我在一週之內,寫出生平第一篇介紹馬勒的生平與作品的文章,登在《太平洋時報》,約五千字,這是海外華文報紙第一次比較詳細介紹馬勒的文章。從此以後,我很少錯過馬勒音樂在南加州的演出。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返台擔任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那時我最擔心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在台灣東部再也聽不到馬勒的音樂了。在黃勝雄院長大力支持下,我催生的門諾醫院系列音樂會聞名花東。當時慈濟醫學院院長李明亮不但是馬勒迷,也是蕭泰然迷,他可說是門諾音樂會最忠實的聽眾;而我在東華大學與慈濟醫學院教「醫學與人文」時,也教學生欣賞馬勒的美好樂章。
一九九九年初,與馬勒迷的老友侯平文聯絡上,他是「紐約馬勒協會」的創會會友,也是資深馬勒迷。他告訴我這年9月柏林有精彩的馬勒音樂節,我設法買到該音樂節馬勒第八號《千人》的票。那年我為了到歐洲聆賞馬勒,並探訪我心目中的平凡偉人蘭大弼,特別向門諾請假一個月,踏著馬勒的足跡,先到布拉格、布達佩斯和維也納。我在馬勒工作十年、並使他發光發熱的維也納歌劇院,發現馬勒的畫像、羅丹的馬勒雕像以及他用過的私人鋼琴。
*《千人》引起心靈震撼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發生大地震的那天晚上,我終於在柏林愛樂廳聽到了馬勒的第八號《千人》交響曲,由荷蘭指揮大師海汀克(Bernard Haitink)指揮柏林愛樂做了一場震撼心靈的演出。柏林愛樂不管是樂團的表現或音樂廳的水準,都是世界一流的,而海汀克對馬勒的詮釋也非常有深度。德國文豪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親聆馬勒第八號交響曲的世界首演後告訴太太:「今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偉人。」我聽完這場演出之後,也告訴我太太:「這是我生平聽過感覺上最偉大的一場音樂會。」
二○○二年,我離開花蓮的行醫事業,應許添財市長之邀,不務正業做了一年台南市文化局長。期間曾序1:
映照馬勒的完整面貌
賴德和(作曲家,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得主)
馬勒有作曲家的心靈,兼有指揮家的耳朵,因此數十年來我對馬勒的交響曲始終鍾情。從四十年前第四號交響曲入門,其後曾有多年先後愛上第一、第五。目前的最愛是第八號和《大地之歌》。無論聆聽或研讀總譜,都是受惠無窮。表面上,馬勒的交響曲幾乎完全以調性氛圍寫成,不免被批評過份保守。可是這些交響曲意象繽紛,經常從莊嚴與俚俗,龐雜與單純之間快速換軌,造成多重情境令人悲喜莫名,或許這樣的表現更切合現代人的心靈感受。
早年讀了不少林衡哲先生主編的《新潮文庫》,只是心儀但無緣得識。十幾年前,在花蓮一場紀念郭子究先生的音樂會上,初識林衡哲先生,當時他是門諾醫院的醫生。不但是近乎癡狂的愛樂者,同時也是熱情的音樂贊助者。之後的交往只是偶而音樂會場相遇打招呼聊上兩句,正是君子之交淡若水。直到三年前,他開始較密集地打電話談音樂,話題主要圍繞著馬勒的交響曲。
隨著林醫師的生花妙筆和熾熱的愛心,一口氣讀完《西方音樂巨人馬勒──我的時代已經來臨》全書,這是一次愉快的閱讀經驗,它補足了我原來對馬勒的零碎印象,也以更全面的人文觀點映照我純從聲音和樂譜所認識的馬勒。
序2:
馬勒研究的精彩入門書
呂紹嘉(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從小透過「新潮文庫」知道林衡哲醫師大名。十年前第一次見面,就對這位長者推動文化的「唐吉訶德」式的堅強信念印象深刻;近年來更知道他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馬勒痴,僕僕風塵於世界各地,聆賞一流的馬勒演奏,尋訪他的足跡,鑽研其文獻,終至成就這本心血結晶。
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是個不論從音樂、人、時代來切入研究都極為精彩的「現象」。他的長篇交響曲內容包羅萬象,寓意繁複,生前並不廣被接受,百年至今卻已是全世界許多樂迷的最愛,也是各大樂團及指揮的「必修課」。他的音樂世界植基於德奧傳統,卻又明顯叛逆而指向未來,訴說人性、自然,有著參透宇宙真理的智慧及偉大的神性,但也處處瀰漫著不可捉摸、詭譎多變、甚至導向大災難的魔性。總而言之,馬勒的音樂就是維也納世紀末藝術世界一個活生生的縮影。
而馬勒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宏觀而前瞻性的視野、大破大立的魄力與毫不妥協的個性,樹立了一個真正藝術領導者的典範,也儼然成為二十世紀新音樂的精神導師。他有許多振臂高呼的名言,今日聽來仍一樣響亮,如「傳統不是對灰燼的膜拜,而是火炬的傳承」。正因如此,我覺得在馬勒去世一百周年紀念的難得時機,在台灣能藉由音樂、文字深度探討這個「現象」是很有意義的事。
我閱讀這本馬勒傳記,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對馬勒的生平、經歷有詳盡的記載和生動的描述。讀者像是隨著主人翁一起經歷他五十年生命的每一階段,從困苦的童年、展露才華的求學時代、職業指揮生涯的每一站(包括詳細的曲目),到生涯最高點的維也納歌劇院總監,之後到美國,乃至走向生命的終點都有細述;對其猶太人的原罪、思想、藝術個性、交往人物至情史,也多有著墨。讀者如身處世紀末的維也納,看著藝術史中的重要人物一個個以馬勒為中心,在舞台婆娑演出。也因此,此書可讀性高。而林醫師對馬勒赤子般的熱愛,在字裡行間處處可見。個人對作者描述馬勒死前一段時間之文字,包括許多專業的醫療細節,印象特別深刻,讀後像是親身目睹巨人的殞落,感慨良久。
跟許多同一代的台灣人一樣,我自《徬徨少年時》起,就不自覺的吸收「新潮文庫」的滋養,今天得以在林醫師又撒下一粒文化種子之際,就近「觀禮」並說幾句話,深覺榮幸及不敢當。衷心希望此書能引導台灣更多愛樂者進入馬勒的音樂世界,並祈願更多文化種子繼續深植本土,開花結果,庇蔭滋養美麗寶島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心靈。
序3:
一本書,一個世界
江靖波(樂興之時管絃樂團、音樂理想國創辦人/藝術總監)
依然冷峭的初春,我在義大利多羅米特山區,馬勒寫第九號、《大地之歌》,以及未完成的第十號的小木屋裡。一百五十步之遙,一九○八、○九年那兩個夏天他同艾瑪1及三架鋼琴旅居的客棧仍在,只是如今已然美輪美奐,改名叫做Gustav Mahler Stube。我有點爆炸,心裡同時想著這複雜的、謎樣的、巨大的小個頭的一生、以及那一年因流產而憂鬱的艾瑪去到Toblebad散心卻邂逅了葛羅佩斯,乃至後者還因此來訪同馬勒攤牌的情境、以及第九的開頭。眼前的綠野緩坡,周遭是疏松林,背後不遠處是悚然千壑的多羅米特山脈,想像五十歲的馬勒接見年輕發亮的葛羅佩斯,聽這不速之客這般熱切地傾訴其之於艾瑪的渴求同契合,然後他安靜地送客,默默地回到木屋繼續寫作,心裡只剩對生命及美的無盡眷戀。
馬勒曾說,「一首交響曲,一個世界。」(Ein Sinfonie, ein Welt)何況他的生命如斯豐富,他的心靈如斯剝離卻又層層相疊?我從稚時不識他,及長卻每每透過音樂深刻感覺與其相知,或許關鍵特別在於他那marginal man──邊緣人── 的自我感受。從他小時候醉心閱讀乃至可以完全活在想像世界中的避世傾向,到他撂下的那句感慨,「在奧地利我被看作波希米亞人,在德國我被看作奧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猶太人;各處都勉強收留我,但都不歡迎我。」到第九號第三樂章的Burlesque那撕裂人的、虎頭鍘喀嚓喀嚓清脆爽利地響的外在世界,我想他這同世界脫軌、或被視之為陌生、或自覺被排斥、或害怕反被潑冷水的感受是根結的。但是請不要遽下斷語,以為他搞不好得了被迫害妄想。仔細聽他譬如說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這首歌,聽他如何娓娓訴說:「我同世界失了聯繫,它或許以為我已經不在了,但它若這麼想倒也沒錯……我獨自安息在我的天國裡,我的愛裡,我的歌裡……。」你便明白他的孤獨是選擇,裡頭沒有自憐;你也就看見當一個藝術家將對於「美」的執拗在工作及生活中都不自覺地無限上了綱後可能出現的生命光景。
承蒙林醫師邀序,我覺得很不敢當。欽佩林醫師為了心儀的藝術家願意付的代價,願意下的功夫。這樣的代價同功夫,說來汗顏,很多所謂職業音樂家都不見得願意擺上。期盼這本書的流傳能夠讓更多的人更認識馬勒,更親近他的心,更明白他那個時代。忽然覺得《大地之歌》中王維的詩亦十分貼近林醫師的瀟灑,不如摘來送他: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中華民國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序4:
馬勒的現代知己 林衡哲的音樂人生
林采韻(資深樂評人,《旺報》文化副刊組副主任)
每次接到林衡哲醫師打來的電話,不外乎關於兩件事,「望春風出版社」或「馬勒」,去年(二○一○年)九月,電話那端又傳來林醫師的聲音,這次他顯得相當興奮,因為他以三年時間寫作的馬勒傳記終於完成了。
林衡哲先生的正職是小兒科醫生,但是他對音樂的熱情,讓我在與他對話的過程中,往往覺得,音樂才是他的正職,小兒科只是他安居的副業。他之所以成為醫生,甚至遠到美國行醫,都是因為他的人生選擇跟著音樂走。
就讀建國中學三年級時,作文比賽同學寫保家衛國,他拿下第一名的題目是《貝多芬為什麼偉大?》;大學保送東海大學外文系,他讀完一年決定重考,因為重要的音樂會大多在台北他不想錯過,沒想到這一重考成績考得太好,誤打誤撞進入台大醫學院;醫學院畢業後,他決定前往美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想親炙鋼琴大師魯賓斯坦的現場演出。
靠著這股對古典音樂只增溫不降火的熱情,林衡哲以一生的時間追尋這份他生活中的美好,而且從不吝嗇與他人分享,只要他人在台北,只要有馬勒的音樂會,他馬上扮演最忠實的推銷員,通知所有親朋好友,只怕他們錯失被馬勒感動的機會。
林醫師記憶極佳,不論音樂會年代的遠近,他可以精確的覆誦每場音樂會的時間、地點、曲目和演奏家;他意志堅定,只要想聽的音樂會,想親耳見證的大師,絕對讓自己美夢成真,這樣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為馬勒寫傳的決心上。
林醫師說他不是音樂專家,只是業餘的音樂愛好者,這部馬勒傳不是寫給專家看,而是寫給廣大的古典音樂愛好者,為他們建立一座進入馬勒音樂世界的橋樑,發現屬於自己的生命感動。因此在這本傳記中,沒有艱澀難懂的音樂理論,或是失去溫度的學術文字,在林醫師數十萬的文字中,他就像是一位傳道士,竭盡所能的介紹他心中的馬勒,以真誠書寫馬勒生命的價值所在,同時分享他在追尋馬勒過程中的所見所聞。
過去三年每逢暑假,林醫師都閉關在南加州克萊蒙學院圖書館寫書,閱畢十多本馬勒相關外文書籍後,才敢下手。他說馬勒曾以「被世界遺忘的感覺」形容暑假期間在作曲小屋埋頭寫曲的時光,如今在他的寫作過程中,終於體會到馬勒的感受。馬勒曾說「我的時代終將來臨」,我想在馬勒迎向他時代的路途上,林醫師已如實扮演了知己的角色。
一位馬勒迷的心路歷程
我的音樂啟蒙甚晚,或許因為是因為我不是出身音樂家庭的緣故。我大約是在宜蘭中學初三畢業那年暑假,宜蘭大專校友會在故鄉舉行「古典音樂欣賞會」,才初聆貝多芬第四號交響曲。我一聽就入迷了,在內心呼喚著:「這就是我想聽的音樂。」
在台北唸建中的時候,因為讀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以貝多芬為藍本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就成了「貝多芬迷」,還寫過一篇〈貝多芬為什麼偉大〉,得到作文比賽首獎。我在建中隔壁的美國新聞處看到庫塞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在譚格林(Tanglewood)演出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便在內心默默發誓,將來一定要到譚格林聽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
想不到在唸東海大學外文系那一年,我不必出國,就有機會在台灣親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那天是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地點是在台北中山堂。我坐七小時的車子,冒雨前往台北,最後買到了台幣七十元(原價二十元)的黃牛票。但是能夠聽到指揮大師孟治(Charles Munch, 1891-1968)演出貝多芬第三號《英雄》號交響曲,我覺得連靈魂都飛上了天,那是畢生難忘的精神享受。聽過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世紀之音,我此後成為忠實的古典樂迷,當天晚上還寫了生平第一篇樂評〈波士頓交一位馬勒迷的心路歷程響樂團聆賞記〉,想不到平常打分數很嚴格的魯實先教授,給我這篇樂評九十分的高分,使我成為業餘樂評家的信心。
*為了音樂會而重考醫科
當時台中是音樂文化的沙漠,好的音樂會都在台北,我便在一九六○年參加聯考,考上台大醫科。在醫科七年中,我依然是貝多芬迷,兼了不少家教,為的是領到錢之後,可以買貝多芬的原版唱片,或到「田園咖啡」欣賞貝多芬的號交響曲。如果有貝多芬號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的音樂會,就算是碰到考試,我也絕不錯過。大學室友受我的感染,也有不少迷上貝多芬的音樂。不管功課有多忙,我也抽空在《功學月刊》和《愛樂》投稿,除了樂評文章之外,也介紹了不少西方音樂家如文藝復興時代的帕勒斯特利納(Giovanni Palestrina, 1525-1594)、義大利歌劇巨擘貝利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貝多芬音樂的鋼琴權威許納貝爾(Artur Schnabel, 1882-1951),以及南美洲阿根廷的作曲大師琴那斯特拉(Alberto Ginastera, 1916-1983)等給台灣的樂迷。
當時的台灣正處於反共抗俄的年代,國防費用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社會窮困,世界知名的音樂家來台灣的很少。多虧了吳心柳主持的遠東音樂社,我在台大醫學院七年期間,聽了黑人世紀女高音安德遜(Marian Anderson, 1902-1993)、大提琴泰斗皮亞悌哥斯基(Gregor Piatigorsky, 1903-1976)、鋼琴大師塞金(Rudolf Serkin, 1903-1991)以及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要聽這些名家,通常一大早就要去排隊等候。那時我對西方浪漫派音樂家的故事都很熟悉,也看了不少他們的傳記。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主編的「傳記文學精選集」(列入新潮文庫一一○號,一九七四年初版)中,就選了兩篇音樂家的傳記〈怪人華格納〉(狄姆斯‧泰勒著)和〈終生獨身的音樂家────布拉姆斯〉(紐曼著)。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十九世紀末維也納樂壇兩大陣營的對手,也不知道馬勒跟他們兩人的關係。
我在大一日記裡曾列了六十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當時馬勒還是榜上無名。到了大四,我又在日記中列了一百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馬勒才入榜,但我只知道他是一八六○年生在捷克,一九一一年死於維也納,其他事情還不是很了解。總之,我在一九六八年出國之前,從未聽過馬勒作品的現場演出,也沒有讀過他的任何傳記;正如出國之前,我是台灣文化的文盲,蔣渭水、賴和、韓石泉雖是台大醫科前輩,但我對他們的貢獻完全不了解。當時我是馬勒的「樂盲」,崇拜的人物是羅素、史懷哲、卡薩爾斯和愛因斯坦等人,作曲家則是貝多芬,我還在日記中寫道,「史懷哲的音樂情人是巴赫,而我的音樂情人是貝多芬。」
其實,在我唸醫科的一九六○年代,馬勒的音樂已經在歐美復活了。伯恩斯坦的青少年音樂會,台灣也有轉播,那時我也迷伯恩斯坦的指揮風采,他指揮的音樂會我聽過三十多場,但沒有一場是馬勒的音樂。他介紹馬勒的青少年音樂會(包括「誰是古斯塔夫‧馬勒」)的節目,我也都錯過了。
大學時代,我深受蕭孟能《文星》雜誌的影響。《文星》曾經以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和指揮家托斯卡尼尼做過封面人物,音樂雜誌也有不少介紹他們的文章。我在出國前主編《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時,作曲家選史特拉汶斯基,指揮家選托斯卡尼尼,但沒有馬勒。
到了一九八七年,李哲洋才在他主編的《音樂文摘》中,用兩期有系統地介紹馬勒的人與音樂,但那時我已經在美國加州了。二十世紀指揮大師克倫普勒(Otto Klemperer)曾親自受教於馬勒和托斯卡尼尼,他說:「他們兩位都是偉大的指揮家,但就詮釋的深度而言,馬勒比托斯卡尼尼更偉大。因為托斯卡尼尼永遠是托斯卡尼尼,而馬勒指揮莫札特的歌劇,就變成莫札特的化身;他演出華格納時,又變成華格納的分身。」大學時代的我,顯然是有眼不識泰山。
出國之後,在紐約十年(1968-1978)期間,雖然當時透過華爾特與伯恩斯坦在紐約的努力,以及蕭提在芝加哥的不斷演出,馬勒的時代已在美國來臨,但我個人的馬勒時代仍未降臨。我在紐約十年聽了四、五百場音樂會,但有馬勒作品的音樂會,可能不會超過三場。印象較深刻的一場是海汀克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演出馬勒第九。那天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我與台大醫科學長張南雄一同去欣賞,我在日記寫道:「馬勒第九的結尾與一般的號交響曲相反,在平靜的尾聲中結束。」
我在紐約的時候還不是馬勒迷,西貝流士和蕭士塔高維奇的交響曲還聽的比較多;最大的缺憾是沒有聽過伯恩斯坦、蕭提和庫貝利克這三位馬勒大師指揮的馬勒。
*小澤征爾使我變成馬勒迷
一九七八年搬到南加州之後,我已經年近不惑。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聽慕提(Riccardo Muti)指揮費城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一號《巨人》交響曲之後,我在日記寫道:「慕提的指揮充滿活力與流動感,馬勒音樂的高潮如排山倒海而來。有名的費城之音並不因奧曼第(Eugene Ormandy, 1899-1985)的離開而失色,慕提注入了簇新的生命力。」接著一九八六年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南加州的Cerrito演藝中心,演出了馬勒第二號《復活》號交響曲,讓我生平第二次有靈魂飛上天的感覺。不久又接連聆賞拉圖(Simon Rattle)和沙洛南(Esa-Pekka Salonen)指揮洛杉磯愛樂演出馬勒第二號,令人印象深刻,我這才逐漸變成馬勒迷,馬勒的時代才終於在我身上降臨了。義大利指揮大師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擔任洛杉磯愛樂的指揮(1973-1976)之後,也常演出馬勒的經典作品,因此馬勒的時代也終於降臨了南加州的洛杉磯。
一九九七年,維也納愛樂來南加州演出馬勒,我因為買不到票而錯過了。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排隊時認識了一位長堤交響樂團的小提琴家,她發現我是馬勒迷,立刻送我兩張貴賓券去聽女指揮家芙麗塔(JoAnn Falleta)指揮長堤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七號交響曲。雖然這首曲子,印度指揮祖賓梅塔說是他一生碰到最難演的交響曲,但因演出前她做了一場精彩且平易近人的樂曲解說,加上演出非常感人, 贏得全場起立鼓掌。因此我在一週之內,寫出生平第一篇介紹馬勒的生平與作品的文章,登在《太平洋時報》,約五千字,這是海外華文報紙第一次比較詳細介紹馬勒的文章。從此以後,我很少錯過馬勒音樂在南加州的演出。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返台擔任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那時我最擔心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在台灣東部再也聽不到馬勒的音樂了。在黃勝雄院長大力支持下,我催生的門諾醫院系列音樂會聞名花東。當時慈濟醫學院院長李明亮不但是馬勒迷,也是蕭泰然迷,他可說是門諾音樂會最忠實的聽眾;而我在東華大學與慈濟醫學院教「醫學與人文」時,也教學生欣賞馬勒的美好樂章。
一九九九年初,與馬勒迷的老友侯平文聯絡上,他是「紐約馬勒協會」的創會會友,也是資深馬勒迷。他告訴我這年9月柏林有精彩的馬勒音樂節,我設法買到該音樂節馬勒第八號《千人》的票。那年我為了到歐洲聆賞馬勒,並探訪我心目中的平凡偉人蘭大弼,特別向門諾請假一個月,踏著馬勒的足跡,先到布拉格、布達佩斯和維也納。我在馬勒工作十年、並使他發光發熱的維也納歌劇院,發現馬勒的畫像、羅丹的馬勒雕像以及他用過的私人鋼琴。
*《千人》引起心靈震撼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發生大地震的那天晚上,我終於在柏林愛樂廳聽到了馬勒的第八號《千人》交響曲,由荷蘭指揮大師海汀克(Bernard Haitink)指揮柏林愛樂做了一場震撼心靈的演出。柏林愛樂不管是樂團的表現或音樂廳的水準,都是世界一流的,而海汀克對馬勒的詮釋也非常有深度。德國文豪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親聆馬勒第八號交響曲的世界首演後告訴太太:「今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偉人。」我聽完這場演出之後,也告訴我太太:「這是我生平聽過感覺上最偉大的一場音樂會。」
二○○二年,我離開花蓮的行醫事業,應許添財市長之邀,不務正業做了一年台南市文化局長。期間曾序1:
映照馬勒的完整面貌
賴德和(作曲家,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得主)
馬勒有作曲家的心靈,兼有指揮家的耳朵,因此數十年來我對馬勒的交響曲始終鍾情。從四十年前第四號交響曲入門,其後曾有多年先後愛上第一、第五。目前的最愛是第八號和《大地之歌》。無論聆聽或研讀總譜,都是受惠無窮。表面上,馬勒的交響曲幾乎完全以調性氛圍寫成,不免被批評過份保守。可是這些交響曲意象繽紛,經常從莊嚴與俚俗,龐雜與單純之間快速換軌,造成多重情境令人悲喜莫名,或許這樣的表現更切合現代人的心靈感受。
早年讀了不少林衡哲先生主編的《新潮文庫》,只是心儀但無緣得識。十幾年前,在花蓮一場紀念郭子究先生的音樂會上,初識林衡哲先生,當時他是門諾醫院的醫生。不但是近乎癡狂的愛樂者,同時也是熱情的音樂贊助者。之後的交往只是偶而音樂會場相遇打招呼聊上兩句,正是君子之交淡若水。直到三年前,他開始較密集地打電話談音樂,話題主要圍繞著馬勒的交響曲。
隨著林醫師的生花妙筆和熾熱的愛心,一口氣讀完《西方音樂巨人馬勒──我的時代已經來臨》全書,這是一次愉快的閱讀經驗,它補足了我原來對馬勒的零碎印象,也以更全面的人文觀點映照我純從聲音和樂譜所認識的馬勒。
序2:
馬勒研究的精彩入門書
呂紹嘉(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從小透過「新潮文庫」知道林衡哲醫師大名。十年前第一次見面,就對這位長者推動文化的「唐吉訶德」式的堅強信念印象深刻;近年來更知道他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馬勒痴,僕僕風塵於世界各地,聆賞一流的馬勒演奏,尋訪他的足跡,鑽研其文獻,終至成就這本心血結晶。
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是個不論從音樂、人、時代來切入研究都極為精彩的「現象」。他的長篇交響曲內容包羅萬象,寓意繁複,生前並不廣被接受,百年至今卻已是全世界許多樂迷的最愛,也是各大樂團及指揮的「必修課」。他的音樂世界植基於德奧傳統,卻又明顯叛逆而指向未來,訴說人性、自然,有著參透宇宙真理的智慧及偉大的神性,但也處處瀰漫著不可捉摸、詭譎多變、甚至導向大災難的魔性。總而言之,馬勒的音樂就是維也納世紀末藝術世界一個活生生的縮影。
而馬勒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宏觀而前瞻性的視野、大破大立的魄力與毫不妥協的個性,樹立了一個真正藝術領導者的典範,也儼然成為二十世紀新音樂的精神導師。他有許多振臂高呼的名言,今日聽來仍一樣響亮,如「傳統不是對灰燼的膜拜,而是火炬的傳承」。正因如此,我覺得在馬勒去世一百周年紀念的難得時機,在台灣能藉由音樂、文字深度探討這個「現象」是很有意義的事。
我閱讀這本馬勒傳記,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對馬勒的生平、經歷有詳盡的記載和生動的描述。讀者像是隨著主人翁一起經歷他五十年生命的每一階段,從困苦的童年、展露才華的求學時代、職業指揮生涯的每一站(包括詳細的曲目),到生涯最高點的維也納歌劇院總監,之後到美國,乃至走向生命的終點都有細述;對其猶太人的原罪、思想、藝術個性、交往人物至情史,也多有著墨。讀者如身處世紀末的維也納,看著藝術史中的重要人物一個個以馬勒為中心,在舞台婆娑演出。也因此,此書可讀性高。而林醫師對馬勒赤子般的熱愛,在字裡行間處處可見。個人對作者描述馬勒死前一段時間之文字,包括許多專業的醫療細節,印象特別深刻,讀後像是親身目睹巨人的殞落,感慨良久。
跟許多同一代的台灣人一樣,我自《徬徨少年時》起,就不自覺的吸收「新潮文庫」的滋養,今天得以在林醫師又撒下一粒文化種子之際,就近「觀禮」並說幾句話,深覺榮幸及不敢當。衷心希望此書能引導台灣更多愛樂者進入馬勒的音樂世界,並祈願更多文化種子繼續深植本土,開花結果,庇蔭滋養美麗寶島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心靈。
序3:
一本書,一個世界
江靖波(樂興之時管絃樂團、音樂理想國創辦人/藝術總監)
依然冷峭的初春,我在義大利多羅米特山區,馬勒寫第九號、《大地之歌》,以及未完成的第十號的小木屋裡。一百五十步之遙,一九○八、○九年那兩個夏天他同艾瑪1及三架鋼琴旅居的客棧仍在,只是如今已然美輪美奐,改名叫做Gustav Mahler Stube。我有點爆炸,心裡同時想著這複雜的、謎樣的、巨大的小個頭的一生、以及那一年因流產而憂鬱的艾瑪去到Toblebad散心卻邂逅了葛羅佩斯,乃至後者還因此來訪同馬勒攤牌的情境、以及第九的開頭。眼前的綠野緩坡,周遭是疏松林,背後不遠處是悚然千壑的多羅米特山脈,想像五十歲的馬勒接見年輕發亮的葛羅佩斯,聽這不速之客這般熱切地傾訴其之於艾瑪的渴求同契合,然後他安靜地送客,默默地回到木屋繼續寫作,心裡只剩對生命及美的無盡眷戀。
馬勒曾說,「一首交響曲,一個世界。」(Ein Sinfonie, ein Welt)何況他的生命如斯豐富,他的心靈如斯剝離卻又層層相疊?我從稚時不識他,及長卻每每透過音樂深刻感覺與其相知,或許關鍵特別在於他那marginal man──邊緣人── 的自我感受。從他小時候醉心閱讀乃至可以完全活在想像世界中的避世傾向,到他撂下的那句感慨,「在奧地利我被看作波希米亞人,在德國我被看作奧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猶太人;各處都勉強收留我,但都不歡迎我。」到第九號第三樂章的Burlesque那撕裂人的、虎頭鍘喀嚓喀嚓清脆爽利地響的外在世界,我想他這同世界脫軌、或被視之為陌生、或自覺被排斥、或害怕反被潑冷水的感受是根結的。但是請不要遽下斷語,以為他搞不好得了被迫害妄想。仔細聽他譬如說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這首歌,聽他如何娓娓訴說:「我同世界失了聯繫,它或許以為我已經不在了,但它若這麼想倒也沒錯……我獨自安息在我的天國裡,我的愛裡,我的歌裡……。」你便明白他的孤獨是選擇,裡頭沒有自憐;你也就看見當一個藝術家將對於「美」的執拗在工作及生活中都不自覺地無限上了綱後可能出現的生命光景。
承蒙林醫師邀序,我覺得很不敢當。欽佩林醫師為了心儀的藝術家願意付的代價,願意下的功夫。這樣的代價同功夫,說來汗顏,很多所謂職業音樂家都不見得願意擺上。期盼這本書的流傳能夠讓更多的人更認識馬勒,更親近他的心,更明白他那個時代。忽然覺得《大地之歌》中王維的詩亦十分貼近林醫師的瀟灑,不如摘來送他: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中華民國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序4:
馬勒的現代知己 林衡哲的音樂人生
林采韻(資深樂評人,《旺報》文化副刊組副主任)
每次接到林衡哲醫師打來的電話,不外乎關於兩件事,「望春風出版社」或「馬勒」,去年(二○一○年)九月,電話那端又傳來林醫師的聲音,這次他顯得相當興奮,因為他以三年時間寫作的馬勒傳記終於完成了。
林衡哲先生的正職是小兒科醫生,但是他對音樂的熱情,讓我在與他對話的過程中,往往覺得,音樂才是他的正職,小兒科只是他安居的副業。他之所以成為醫生,甚至遠到美國行醫,都是因為他的人生選擇跟著音樂走。
就讀建國中學三年級時,作文比賽同學寫保家衛國,他拿下第一名的題目是《貝多芬為什麼偉大?》;大學保送東海大學外文系,他讀完一年決定重考,因為重要的音樂會大多在台北他不想錯過,沒想到這一重考成績考得太好,誤打誤撞進入台大醫學院;醫學院畢業後,他決定前往美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想親炙鋼琴大師魯賓斯坦的現場演出。
靠著這股對古典音樂只增溫不降火的熱情,林衡哲以一生的時間追尋這份他生活中的美好,而且從不吝嗇與他人分享,只要他人在台北,只要有馬勒的音樂會,他馬上扮演最忠實的推銷員,通知所有親朋好友,只怕他們錯失被馬勒感動的機會。
林醫師記憶極佳,不論音樂會年代的遠近,他可以精確的覆誦每場音樂會的時間、地點、曲目和演奏家;他意志堅定,只要想聽的音樂會,想親耳見證的大師,絕對讓自己美夢成真,這樣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為馬勒寫傳的決心上。
林醫師說他不是音樂專家,只是業餘的音樂愛好者,這部馬勒傳不是寫給專家看,而是寫給廣大的古典音樂愛好者,為他們建立一座進入馬勒音樂世界的橋樑,發現屬於自己的生命感動。因此在這本傳記中,沒有艱澀難懂的音樂理論,或是失去溫度的學術文字,在林醫師數十萬的文字中,他就像是一位傳道士,竭盡所能的介紹他心中的馬勒,以真誠書寫馬勒生命的價值所在,同時分享他在追尋馬勒過程中的所見所聞。
過去三年每逢暑假,林醫師都閉關在南加州克萊蒙學院圖書館寫書,閱畢十多本馬勒相關外文書籍後,才敢下手。他說馬勒曾以「被世界遺忘的感覺」形容暑假期間在作曲小屋埋頭寫曲的時光,如今在他的寫作過程中,終於體會到馬勒的感受。馬勒曾說「我的時代終將來臨」,我想在馬勒迎向他時代的路途上,林醫師已如實扮演了知己的角色。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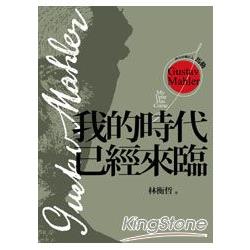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