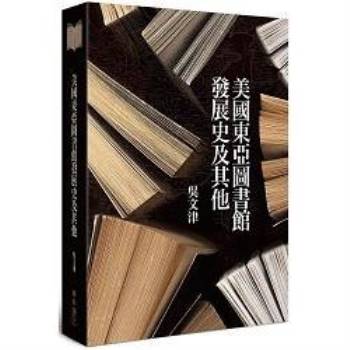第一章 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
美國東亞圖書館蒐藏中國典籍之緣起與現況
這次能到淡江來和大家見面,分享我這幾十年來在圖書館工作上的一些感受與觀察,感到非常榮幸。以前我到淡江來參觀過好幾次,在朱立民教授擔任副校長的時候我也來過。我和朱教授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在重慶中央大學是同班同學,也同時參加青年軍服役,一起派去作翻譯官。我們在昆明服役的時間最長。他在昆明參謀作戰學校任翻譯官隊長,後來調到緬甸,我接他的職位。後來一直沒有見面。直到戰後才知道他在台灣,於是又和他聯絡上了。之後我們來往很密切,不論他在美國念書,或我到台灣,我們都會相聚。所以我覺得因為他,我和淡江也沾上了一些間接的關係。而這次我被邀請到此地來擔任講座,我覺得跟淡江的關係就更密切了。
這次我來演講的三個題目,是在淡江指定的範圍內由我選擇決定的。今天要講的是〈美國東亞圖書館蒐藏中國典籍之緣起與現況〉,明天講〈哈佛燕京圖書館簡史及其中國典籍收藏概況〉,後天講〈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資料問題〉。我希望能在這三個主題之下和大家交換意見,還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批評指教。我並且希望每一次講完後大家可以提出問題來,我知道的可以立刻答覆,我不知道的回去以後再作書面答覆。
美國現在有六十幾個東亞圖書館在收集中文資料,這次我選當中11個最重要的作一個報告。這11個當中有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的東亞圖書館,和加州大學圖書館。因為有這許多圖書館,所以我只能為每一個做些簡單扼要的介紹。但是國會圖書館的中文部和胡佛研究院東亞圖書館這兩處我會講得多一些,因為國會圖書館是美國第一個收集中文資料的圖書館,也是現在西方最大的收集中文資料的圖書館;胡佛研究院的東亞圖書館則是因為我在那裡工作了14年,所以我知道比較多,也稍微多講一些。明天則專門講哈佛燕京圖書館,因為像剛剛黃院長所說,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服務了32年,所以知道的也比較清楚。
圖書館的發展跟教學及研究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關於東亞方面的教學及研究雖然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萌芽,但是其真正的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事。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有少數大學開設了一些有關東亞的課程,但是並未受到很大的重視。教授和學生的人數很少,課程也只限於歷史與語文方面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原本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教育政策有了基本的轉變,從比較窄礙的西方唯尊的觀點轉變為世界多元文化的觀點。在歐美以外的地區因而受到重視,特別是東亞。主要的原因是從1940年代到1950年代這短短十幾年當中,美國在東亞地區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若干歷史上有轉捩性的重大事件,諸如太平洋戰爭,占領日本,協調中國內戰失敗,朝鮮半島分割為南韓、北韓,旋又參加韓戰抵制北韓和中共等。這一連串的事件提高了美國政府和民間對東亞地區的重視,同時也感覺到需要進一步了解東亞各國歷史與文化的迫切性。
於是美國各大學在私人基金會與聯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陸續擴張或開創了整體性的──包括所有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有關東亞各國教學的課程和研究的項目。在50年後的今天,在這種有系統和加快步伐的發展下,美國在這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在西方世界是範圍最廣、內容最豐富的。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為支援教學與研究的需要,美國圖書館在東亞圖書方面也跟著有顯著的發展。美國有些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開始收集中、日文的書籍,其中並有非常珍貴的,一直到現在還是研究漢學不可或缺的典籍文獻。但是全面性的、普遍的、迅速的發展,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二次大戰後的一二十年間,除早期已經成立的圖書館外,另外有些後來成為重要的東亞圖書館也在這個時期先後成立,諸如密西根大學的亞洲圖書館、胡佛研究院的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東亞圖書館等都是在1940年代末期建立的。其他如伊利諾、印第安那與威斯康辛大學的東亞館在1960年代才開始運作。所以說美國東亞圖書館的全面和迅速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不是誇大其詞的。
美國圖書館中收集中文資料最早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它是在1869年(清朝同治八年)就開始收藏中文典籍,後來耶魯大學在1878年(清光緒四年),哈佛大學在1879年(清光緒五年〉,加州大學在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也都開始收集。在20世紀上半紀,哥倫比亞大學在1902年開始、康乃爾大學1918年、普林斯頓大學1926年、芝加哥大學1936年也相繼開始收集。今天所要介紹的就是上述這幾個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除外,那是明天的講題)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成立的胡佛研究院東亞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收集中文資料的起源、現況及其特徵作一個簡單扼要的敘述。
國會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美國收藏中文典籍的第一個圖書館,始於1869年。關於這件事,前芝加哥大學錢存訓教授曾於1965年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23卷撰文,有詳盡的敘述。文名“First Chinese-American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後譯名為〈中美書緣:紀念中美文化交換百周年〉收錄在台灣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錢先生所著的《中美書緣》中。另外一份資料也可供參考。就是現任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撰寫的一篇文章〈簡介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收藏〉(“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 Brief Introduction”),後來由國家圖書館吳碧娟女士譯成中文,發表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2期(1983年12月)。前些時候,王冀先生又略微修改了他的原稿,將中英文合刊,用其原來名字印成一部小冊,私人發行。除了這兩種資料外,關於國會圖書館中文部發展講述得最詳細的一部書,是從前台大教授胡述兆先生的專著《國會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建設》(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79)。這三種資料是國會圖書館中文資料建設的前後過程最有權威性的著作。現在我就根據它們作一個簡要的敘述。
美國國會在1867年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美國政府的出版物每一種需保留50份,由史密森學院(Smithonian Institution)負責與各國交換。諮會各國後,中國清朝政府並沒有回應。第二年,美國農業部派了一位駐華代表,負責收集有關中國農業的資料。這位農業代表到中國的時候,帶了五穀、蔬菜、豆類的種子,和有關美國農業、機械、礦業、地圖,和測量美國太平洋鐵路的報告書若干種,贈送給清廷,並且希望能夠得到同等的回禮作為交換。但是當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是當時清朝的外交部,沒有予以答覆。
過了一年,1869年(清同治八年)美國國務院應美國聯邦政府土地局的要求,令其駐華公使館向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戶口的資料。美國公使也藉此機會,再向總理衙門提出圖書交換的要求。於是總理衙門才做出了決定,以相當數量的書籍和穀類種子作為交換。這些東西在1869年6月7日(清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由總理衙門送到美國使館。國務院把其中的10種書籍交給史密森學院處理,史密森學院再轉存國會圖書館,於是完成了第一次中美圖書交換的工作。國會圖書館因而也成為美國收藏中文典籍的第一個圖書館,這次首次交換給美國的書籍,一共有下列10種,共130函:《皇清經解》道光九年(1829),廣東粵雅堂刊本,360冊,80函、《五禮通考》乾隆十九年(1754),江蘇陽湖刊本,120冊12函、《欽定三禮》乾隆十四年(1749),殿本,136冊18函、《醫宗今鑑》乾隆五年(1740),北京刊本,90冊12函、《本草綱目》順治十二年(1655),北京刊本,48冊4函、《農政全書》道光十七年(1837),貴州刊本,24冊4函、《駢字類編》雍正五年(1727),北京刊本,120冊20函、《針灸大全》道光十九年(1834),江西刊本,10冊2函、《梅氏叢書》康熙四十六年(1707),北京刊本,10冊2函、《性理大全》明永樂十四年(1416),內府刊本,16冊2函。
在這次交換之後到19世紀末,除了在1879年購得前美國駐華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所收集的滿漢書籍237種約2,500餘冊(其中有太平天國的官書、清刻的多種地方志)以外,國會圖書館沒有添增其他的中國典籍。
到了20世紀初葉,在1901到1902年之間,另一位前駐華公使羅克義(William W. Rockhill)將其收藏的漢、滿、蒙文書籍約6,000冊,全數捐贈國會圖書館。1904年中國政府把運到美國參加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展出的198種中國善本典籍也捐贈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後在1908年,中國政府為了表示感謝美國政府退還給中國還沒有動用的庚子賠款1,200多萬美金,特派唐紹儀作為專使到美國致謝,同時贈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一部非常有價值的雍正六年(1728)在北京以銅活字印行的《古今圖書集成》全套,共5,020冊。
美國東亞圖書館蒐藏中國典籍之緣起與現況
這次能到淡江來和大家見面,分享我這幾十年來在圖書館工作上的一些感受與觀察,感到非常榮幸。以前我到淡江來參觀過好幾次,在朱立民教授擔任副校長的時候我也來過。我和朱教授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在重慶中央大學是同班同學,也同時參加青年軍服役,一起派去作翻譯官。我們在昆明服役的時間最長。他在昆明參謀作戰學校任翻譯官隊長,後來調到緬甸,我接他的職位。後來一直沒有見面。直到戰後才知道他在台灣,於是又和他聯絡上了。之後我們來往很密切,不論他在美國念書,或我到台灣,我們都會相聚。所以我覺得因為他,我和淡江也沾上了一些間接的關係。而這次我被邀請到此地來擔任講座,我覺得跟淡江的關係就更密切了。
這次我來演講的三個題目,是在淡江指定的範圍內由我選擇決定的。今天要講的是〈美國東亞圖書館蒐藏中國典籍之緣起與現況〉,明天講〈哈佛燕京圖書館簡史及其中國典籍收藏概況〉,後天講〈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資料問題〉。我希望能在這三個主題之下和大家交換意見,還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批評指教。我並且希望每一次講完後大家可以提出問題來,我知道的可以立刻答覆,我不知道的回去以後再作書面答覆。
美國現在有六十幾個東亞圖書館在收集中文資料,這次我選當中11個最重要的作一個報告。這11個當中有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的東亞圖書館,和加州大學圖書館。因為有這許多圖書館,所以我只能為每一個做些簡單扼要的介紹。但是國會圖書館的中文部和胡佛研究院東亞圖書館這兩處我會講得多一些,因為國會圖書館是美國第一個收集中文資料的圖書館,也是現在西方最大的收集中文資料的圖書館;胡佛研究院的東亞圖書館則是因為我在那裡工作了14年,所以我知道比較多,也稍微多講一些。明天則專門講哈佛燕京圖書館,因為像剛剛黃院長所說,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服務了32年,所以知道的也比較清楚。
圖書館的發展跟教學及研究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關於東亞方面的教學及研究雖然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萌芽,但是其真正的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事。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有少數大學開設了一些有關東亞的課程,但是並未受到很大的重視。教授和學生的人數很少,課程也只限於歷史與語文方面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原本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教育政策有了基本的轉變,從比較窄礙的西方唯尊的觀點轉變為世界多元文化的觀點。在歐美以外的地區因而受到重視,特別是東亞。主要的原因是從1940年代到1950年代這短短十幾年當中,美國在東亞地區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若干歷史上有轉捩性的重大事件,諸如太平洋戰爭,占領日本,協調中國內戰失敗,朝鮮半島分割為南韓、北韓,旋又參加韓戰抵制北韓和中共等。這一連串的事件提高了美國政府和民間對東亞地區的重視,同時也感覺到需要進一步了解東亞各國歷史與文化的迫切性。
於是美國各大學在私人基金會與聯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陸續擴張或開創了整體性的──包括所有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有關東亞各國教學的課程和研究的項目。在50年後的今天,在這種有系統和加快步伐的發展下,美國在這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在西方世界是範圍最廣、內容最豐富的。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為支援教學與研究的需要,美國圖書館在東亞圖書方面也跟著有顯著的發展。美國有些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開始收集中、日文的書籍,其中並有非常珍貴的,一直到現在還是研究漢學不可或缺的典籍文獻。但是全面性的、普遍的、迅速的發展,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二次大戰後的一二十年間,除早期已經成立的圖書館外,另外有些後來成為重要的東亞圖書館也在這個時期先後成立,諸如密西根大學的亞洲圖書館、胡佛研究院的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東亞圖書館等都是在1940年代末期建立的。其他如伊利諾、印第安那與威斯康辛大學的東亞館在1960年代才開始運作。所以說美國東亞圖書館的全面和迅速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不是誇大其詞的。
美國圖書館中收集中文資料最早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它是在1869年(清朝同治八年)就開始收藏中文典籍,後來耶魯大學在1878年(清光緒四年),哈佛大學在1879年(清光緒五年〉,加州大學在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也都開始收集。在20世紀上半紀,哥倫比亞大學在1902年開始、康乃爾大學1918年、普林斯頓大學1926年、芝加哥大學1936年也相繼開始收集。今天所要介紹的就是上述這幾個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除外,那是明天的講題)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成立的胡佛研究院東亞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收集中文資料的起源、現況及其特徵作一個簡單扼要的敘述。
國會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美國收藏中文典籍的第一個圖書館,始於1869年。關於這件事,前芝加哥大學錢存訓教授曾於1965年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23卷撰文,有詳盡的敘述。文名“First Chinese-American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後譯名為〈中美書緣:紀念中美文化交換百周年〉收錄在台灣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錢先生所著的《中美書緣》中。另外一份資料也可供參考。就是現任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撰寫的一篇文章〈簡介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收藏〉(“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 Brief Introduction”),後來由國家圖書館吳碧娟女士譯成中文,發表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2期(1983年12月)。前些時候,王冀先生又略微修改了他的原稿,將中英文合刊,用其原來名字印成一部小冊,私人發行。除了這兩種資料外,關於國會圖書館中文部發展講述得最詳細的一部書,是從前台大教授胡述兆先生的專著《國會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建設》(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79)。這三種資料是國會圖書館中文資料建設的前後過程最有權威性的著作。現在我就根據它們作一個簡要的敘述。
美國國會在1867年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美國政府的出版物每一種需保留50份,由史密森學院(Smithonian Institution)負責與各國交換。諮會各國後,中國清朝政府並沒有回應。第二年,美國農業部派了一位駐華代表,負責收集有關中國農業的資料。這位農業代表到中國的時候,帶了五穀、蔬菜、豆類的種子,和有關美國農業、機械、礦業、地圖,和測量美國太平洋鐵路的報告書若干種,贈送給清廷,並且希望能夠得到同等的回禮作為交換。但是當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是當時清朝的外交部,沒有予以答覆。
過了一年,1869年(清同治八年)美國國務院應美國聯邦政府土地局的要求,令其駐華公使館向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戶口的資料。美國公使也藉此機會,再向總理衙門提出圖書交換的要求。於是總理衙門才做出了決定,以相當數量的書籍和穀類種子作為交換。這些東西在1869年6月7日(清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由總理衙門送到美國使館。國務院把其中的10種書籍交給史密森學院處理,史密森學院再轉存國會圖書館,於是完成了第一次中美圖書交換的工作。國會圖書館因而也成為美國收藏中文典籍的第一個圖書館,這次首次交換給美國的書籍,一共有下列10種,共130函:《皇清經解》道光九年(1829),廣東粵雅堂刊本,360冊,80函、《五禮通考》乾隆十九年(1754),江蘇陽湖刊本,120冊12函、《欽定三禮》乾隆十四年(1749),殿本,136冊18函、《醫宗今鑑》乾隆五年(1740),北京刊本,90冊12函、《本草綱目》順治十二年(1655),北京刊本,48冊4函、《農政全書》道光十七年(1837),貴州刊本,24冊4函、《駢字類編》雍正五年(1727),北京刊本,120冊20函、《針灸大全》道光十九年(1834),江西刊本,10冊2函、《梅氏叢書》康熙四十六年(1707),北京刊本,10冊2函、《性理大全》明永樂十四年(1416),內府刊本,16冊2函。
在這次交換之後到19世紀末,除了在1879年購得前美國駐華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所收集的滿漢書籍237種約2,500餘冊(其中有太平天國的官書、清刻的多種地方志)以外,國會圖書館沒有添增其他的中國典籍。
到了20世紀初葉,在1901到1902年之間,另一位前駐華公使羅克義(William W. Rockhill)將其收藏的漢、滿、蒙文書籍約6,000冊,全數捐贈國會圖書館。1904年中國政府把運到美國參加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展出的198種中國善本典籍也捐贈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後在1908年,中國政府為了表示感謝美國政府退還給中國還沒有動用的庚子賠款1,200多萬美金,特派唐紹儀作為專使到美國致謝,同時贈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一部非常有價值的雍正六年(1728)在北京以銅活字印行的《古今圖書集成》全套,共5,020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