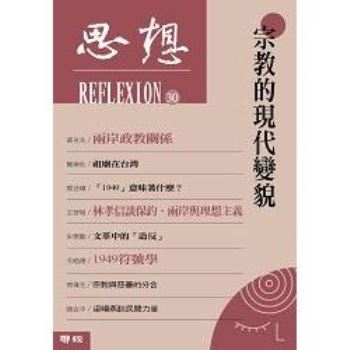一個失控的成長團體︰日月明功個案初探(丁仁傑)
一、前言
2013年底,台灣彰化縣爆發了震驚社會的日月明功高中生被拘禁致死案。詹姓婦女在日月明功團體內部,以管教與戒毒的名義,和其他信徒一起將自己的小孩詹生毆打和拘禁致死。此案引起媒體廣泛報導並引發社會大眾關注。2014年12月9日彰化地方法院宣判,八名被告,依傷害與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領導人陳巧明被判處13年,詹母判4年6個月,其他六名參與者也被判處6個月到4年等不等的刑罰。2015年8月27日台灣高等法院二審改判,罪名均改為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陳巧明與詹母刑期不變,其他被告則有加重者也有減輕者。
2013年底,當事件發生時,媒體界,甚至是報章上學者意見的表達,採取了一面倒式地報導與討論,一般認為︰日月明功是一個神祕性的宗教團體,信徒心智受到教主綁架而喪失判斷能力,教團內則有嚴密檢查與洗腦的措施,讓一些高社經地位者與世隔絕而陷於狂熱性的修行活動中,並將這種控制強施於第二代年輕學員身上。
如同2013年12月21日彭懷真教授在中國時報投書中所出現的話語︰
涉嫌虐死高中生詹淳寓的共犯,有3位老師。檢警專案小組訊問她們時,忍不住質問:「身為師長,怎麼會如此殘忍害死學生?」尤其涉案老師具有輔導或護理背景,在校教的是生涯輔導、生命教育及健康與護理等課程。這怎麼解釋?……
我曾經在監所擔任心理輔導老師,接觸上千個案例,還沒遇到這樣的「加害人」。……
這3位老師顯然沒有用「對的方法」去關心詹淳寓,她們對神祕力量順服,寧可做幫凶也執迷不悟。……
媒體上的報導和一些學者的想像,固然也可能確實捕捉到了部分事實,但整體上看來,其實多半是一種未經分析與查證的想像,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言語上的驅魔」(verbal exorcism),它是一種當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受到了和此不同的另一種世界的直接挑戰和侵犯時,所引發的刺激人們想要起而捍衛與維護既有生活世界的舉動。但事實上,台灣社會目前充斥許多如同日月明功這類中小型的修行或宗教團體,它們一方面有著追求自我成長的目標(或許我們可以稱其為「成長團體」〔growth group〕),卻又創造出了領導人獨特的權威,並與周遭地景或居住脈絡處於一種相對隔絕性的狀態,其內部運作邏輯和特殊發展歷程應該被有所正視,而不能僅被以驅魔的方式來加以想像,這是激發我開始進行日月明功個案研究的原因。
不過,因為該團體已經解散,無法加以觀察,相關研究只能是回溯性的。目前的本文是這個回溯性研究的一個相當初步的分析,主要根據的一手資料為一審起訴書,一審和二審的判決書和法院新聞稿,兩位詹生家屬和五位學員的訪談記錄(男性兩位、女性三位),約兩年間的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旁聽筆記(共約近二十次),和多次我被受訪者拒絕接受訪談但仍在電話中所獲得的珍貴訊息等。
由於該案目前仍處在最高法院審理的階段,任何學術討論和訪談資料,都有可能成為法官自由心證上的參考依據。也因為這個原因,本人現階段對於日月明功的研究和論述,的確具有某種程度倫理上的爭議性。在無可避免的爭議性下,底下的討論,除了領導人陳巧明、詹生、詹母外,將不會出現任何其他人名。
二、心靈控制與團體的「高付出需求」
全控機構
前述媒體中常見的說法(日月明功信徒受到洗腦與嚴格的心靈控制),同樣也反映在法官判決背後的法律見解中。彰化地院一審判決書中對於默園,有一個鮮明的描述︰
默園裡面雖然沒有任何工具(例如上鎖)可以限制被害人的行動,但在這樣的團體迷思下,拘束人身自由的方式,並非直接持續施加物理力,而是「心理」的限制。
簡言之,雖然判決書中沒有提到這個名詞,但根據判決書中的描述,我們看到︰一個心理上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這樣的名詞似乎可以說明日月明功中成員受到無形綑綁與限制的情況。
「全控機構」的概念,在Erving Goffman的著作《精神病院》一書中有很好的說明︰有一類機構,將一群人予以科層體系式的管理,而這群人的生活跟一般人的日常活動區隔開來,其控制方式是將睡眠、工作、與休閒活動完全限定在一個機構內。Goffman在「全控機構」的概念中,分析了被收容人與監督人的生活形式,並強調,出於管理人的意圖,其中會產生不可避免的科層體制的區隔和操弄。他也分析了受收容者在機構中所產生的非正式地下生活文化與對抗性作為。Goffman提出這個概念,一方面在微觀性地觀察這類區隔性的機構中的特殊互動模式,尤其是互動歷程中自我形象的建構與調整;一方面也是在了解先進工業社會中這種社會控制過程的運作機制。描述性地來看︰
全控機構:這是一個讓處境類似的一大群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們在那裡與更寬闊的社會隔開好一段時間,共同過著封閉、受到正式管理的生活。
有些﹝機構﹞涵蓋的程度比其他機構還要大上許多。這種涵蓋性或全面性起因於它們和外界的阻絕。它們經常具有實體的阻絕物,像是深鎖的大門、高牆、電柵、崖壁、水流、森林甚至是荒野。
全控機構為被收容者安排了整天的行程,意思就是說,被收容者的一切基本需求都必須事先加以規劃。
但是,Goffman「全控機構」的概念,在某些情況中,忽略了一些事實,也就是,有時候,嚴密控制的本身,不全然是外加的強迫性措施,而是參與者也參與在其中的集體群聚,也就是一種出於集體性的共謀所造成;更且,「全控」的出現,往往有一個漫長的發展性過程在其中,一個自發性群聚的組織,有時會發展成為「全控機構」,但這是一連串因素所造成,而非一開始就是以嚴密監控為目的。
高付出需求機構
在Goffman「全控機構」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去想像另一個社會學的概念︰「高付出需求機構」(Greedy Institution)。
德裔美籍社會學家Lewis Coser,或許是出於對Goffman「全控機構」概念不太滿意,而在1974年提出了另一個概念「高付出需求機構」,用來指稱那種對成員有極高的要求,而且是完全占有性的,團體要求成員對團體要有不可分割性的忠誠。
在「高付出需求機構」中,組織對成員並不是以強制為手段,而是機構會涵蓋整個人格需求,而得以來獲得成員無條件的順服與參與。他們要求成員對團體有高度的認同,而希望完全占有成員,並削弱成員與其他團體之間的關係。和 Goffman所說的「全控機構」相比,「高付出需求機構」並不使用物理性的暴力,而主要是經由心理壓力和社會神聖化的效果來規訓成員。對「高付出需求機構」背後更大的歷史脈絡,Coser說:
在相對未分化的社會,對個人忠誠度的要求比較少,不過即使如此,對於成員歸屬要求之衝突,仍然是一個常態而不是例外。Max Gluckman及其他人都曾指出,在原初社會,例如說在地域性跟親屬團體之間,總是存在有競爭性的要求。在中世紀,分化程度較高(對於此,就一般所讚揚的所謂「中世紀的整合」這件事,我們對其存在具有高度的懷疑),存在於聖壇和王權之間對於人們忠誠度的爭奪是不可忽視的。不過,和早期的社會結構相比,在高度分化的社會裡,因在歸屬和忠誠度等層面上的要求而所產生的衝突,可能會愈來愈為明顯。
雖然Coser對社會分化與「高付出需求機構」之間的關係並未深入討論,我們大致仍可以發現,二者之間,不是一種直線性的關係,而是在內外環境變化中會產生某種辯證性的發展。
在社會低度分化時,看起來團體對個人的壟斷性較高,也就是團體對個人的忠誠度的要求較高,但其實不然,因為當組織專門化的程度較低,對成員刻意的占有性並不高;等到社會分化成多類團體,譬如說有親屬團體、地域團體、宗教團體等的區別,這時團體間會彼此競爭有限成員的資源與情感歸屬,「高付出需求機構」的型態也就出現了,我認為,這時的「高付出需求性」,它更多的可能是來自對於成員情感歸屬的占有,而不是來自於團體專門化的內在需要;等到社會高度分化,各類團體愈趨於專門化,個人在其中的表現被要求達到極致化,個人對團體的參與不能散漫而前後不一致,這在內在邏輯上,對於個人的忠誠度與付出,有了一種更明確的「高付出需求」(greediness)傾向,但弔詭的是,當社會高度分化,除一些初級團體外,更多了各類工作團體、政治團體、志願參與團體等等,多類團體分割了個人的生活空間,社會上反而醞釀出某種要求,或者是有法律依據(如工時的限制)、或者是有不成文規範,不能允許單一團體對個人自主性的生活空間有太大的獨占性,於是當內外不同力量間產生相生相剋般的辯證性的結合,這又會形成一種相當矛盾而時有緊張性發生的情況。除了現代組織內在一致性的要求以外,對於為什麼在分化社會之公共規範要求團體不能對個人有所獨占性時,社會上還是會出現各種「高付出需求機構」,Coser書中並未詳加說明,而僅在一個段落中指出,這可能是因為某些團體有著烏托邦式的訴求,仍想要對抗外在世俗性的主流價值,而想要刻意維持一種團體內外間的界線,以讓成員不為外在環境所混淆或迷惑,而產生出這種與社會主流規範所相反的「高付出需求機構」。
「高付出需求機構」對成員有一個總體性的要求,要將成員日常生活圈中的人格展現予以完全占有,團體要求著成員完全且不可分割的忠誠,它通常不會以外部性的強制來與外界區隔,相反地,它傾向於經過自願性服從和忠誠,並以成員主動投入的形式來運作。以上這種特徵,我們已由日月明功愈來愈強的教主權威與愈來愈維嚴格的管教模式中,看到了「高付出需求機構」的樣貌,而在這種「高付出需求」中,我們看到,雖然多位成員在法院證詞中都表達出了當時參與的壓力與緊張,但他們並不會否認其曾自願且認真投入於內部學習與互動的事實。
現代高分化社會裡仍然出現各式各樣的「高付出需求機構」,其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以及對團體與社會產生緊張性的模式為何?參與者在這類團體中的身心狀態又是如何呢?透過「高付出需求機構」這個概念,相對於「全控機構」這個概念,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情況中,一個團體由外在看起來是嚴密的社會控制,但是在團體的結構性成因以及成員參與的過程來看,成員常常是出於自願,並且常是懷抱著特殊的情感狀態或目的而來參與。不過,一旦某個團體在冒犯了法律的界線或是觸犯了外在的集體共識時,在內在外,或者被內部成員重新看待,或者被外界仔細檢視,這個團體往往會被理解為是一種強迫性控制的「全控機構」,而且是出於洗腦與規訓而所形成的團體的藩籬。兩種觀點間的微妙差異,會影響我們對於某個團體內在本質和動態表現形式的理解。
以下,我將會以「高付出需求機構」,作為理解日月明功的一個主要核心概念;「全控機構」則作為一個輔助性的概念,以助於描述這個團體的運作型態和發展過程。
一、前言
2013年底,台灣彰化縣爆發了震驚社會的日月明功高中生被拘禁致死案。詹姓婦女在日月明功團體內部,以管教與戒毒的名義,和其他信徒一起將自己的小孩詹生毆打和拘禁致死。此案引起媒體廣泛報導並引發社會大眾關注。2014年12月9日彰化地方法院宣判,八名被告,依傷害與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領導人陳巧明被判處13年,詹母判4年6個月,其他六名參與者也被判處6個月到4年等不等的刑罰。2015年8月27日台灣高等法院二審改判,罪名均改為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陳巧明與詹母刑期不變,其他被告則有加重者也有減輕者。
2013年底,當事件發生時,媒體界,甚至是報章上學者意見的表達,採取了一面倒式地報導與討論,一般認為︰日月明功是一個神祕性的宗教團體,信徒心智受到教主綁架而喪失判斷能力,教團內則有嚴密檢查與洗腦的措施,讓一些高社經地位者與世隔絕而陷於狂熱性的修行活動中,並將這種控制強施於第二代年輕學員身上。
如同2013年12月21日彭懷真教授在中國時報投書中所出現的話語︰
涉嫌虐死高中生詹淳寓的共犯,有3位老師。檢警專案小組訊問她們時,忍不住質問:「身為師長,怎麼會如此殘忍害死學生?」尤其涉案老師具有輔導或護理背景,在校教的是生涯輔導、生命教育及健康與護理等課程。這怎麼解釋?……
我曾經在監所擔任心理輔導老師,接觸上千個案例,還沒遇到這樣的「加害人」。……
這3位老師顯然沒有用「對的方法」去關心詹淳寓,她們對神祕力量順服,寧可做幫凶也執迷不悟。……
媒體上的報導和一些學者的想像,固然也可能確實捕捉到了部分事實,但整體上看來,其實多半是一種未經分析與查證的想像,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言語上的驅魔」(verbal exorcism),它是一種當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受到了和此不同的另一種世界的直接挑戰和侵犯時,所引發的刺激人們想要起而捍衛與維護既有生活世界的舉動。但事實上,台灣社會目前充斥許多如同日月明功這類中小型的修行或宗教團體,它們一方面有著追求自我成長的目標(或許我們可以稱其為「成長團體」〔growth group〕),卻又創造出了領導人獨特的權威,並與周遭地景或居住脈絡處於一種相對隔絕性的狀態,其內部運作邏輯和特殊發展歷程應該被有所正視,而不能僅被以驅魔的方式來加以想像,這是激發我開始進行日月明功個案研究的原因。
不過,因為該團體已經解散,無法加以觀察,相關研究只能是回溯性的。目前的本文是這個回溯性研究的一個相當初步的分析,主要根據的一手資料為一審起訴書,一審和二審的判決書和法院新聞稿,兩位詹生家屬和五位學員的訪談記錄(男性兩位、女性三位),約兩年間的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旁聽筆記(共約近二十次),和多次我被受訪者拒絕接受訪談但仍在電話中所獲得的珍貴訊息等。
由於該案目前仍處在最高法院審理的階段,任何學術討論和訪談資料,都有可能成為法官自由心證上的參考依據。也因為這個原因,本人現階段對於日月明功的研究和論述,的確具有某種程度倫理上的爭議性。在無可避免的爭議性下,底下的討論,除了領導人陳巧明、詹生、詹母外,將不會出現任何其他人名。
二、心靈控制與團體的「高付出需求」
全控機構
前述媒體中常見的說法(日月明功信徒受到洗腦與嚴格的心靈控制),同樣也反映在法官判決背後的法律見解中。彰化地院一審判決書中對於默園,有一個鮮明的描述︰
默園裡面雖然沒有任何工具(例如上鎖)可以限制被害人的行動,但在這樣的團體迷思下,拘束人身自由的方式,並非直接持續施加物理力,而是「心理」的限制。
簡言之,雖然判決書中沒有提到這個名詞,但根據判決書中的描述,我們看到︰一個心理上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這樣的名詞似乎可以說明日月明功中成員受到無形綑綁與限制的情況。
「全控機構」的概念,在Erving Goffman的著作《精神病院》一書中有很好的說明︰有一類機構,將一群人予以科層體系式的管理,而這群人的生活跟一般人的日常活動區隔開來,其控制方式是將睡眠、工作、與休閒活動完全限定在一個機構內。Goffman在「全控機構」的概念中,分析了被收容人與監督人的生活形式,並強調,出於管理人的意圖,其中會產生不可避免的科層體制的區隔和操弄。他也分析了受收容者在機構中所產生的非正式地下生活文化與對抗性作為。Goffman提出這個概念,一方面在微觀性地觀察這類區隔性的機構中的特殊互動模式,尤其是互動歷程中自我形象的建構與調整;一方面也是在了解先進工業社會中這種社會控制過程的運作機制。描述性地來看︰
全控機構:這是一個讓處境類似的一大群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們在那裡與更寬闊的社會隔開好一段時間,共同過著封閉、受到正式管理的生活。
有些﹝機構﹞涵蓋的程度比其他機構還要大上許多。這種涵蓋性或全面性起因於它們和外界的阻絕。它們經常具有實體的阻絕物,像是深鎖的大門、高牆、電柵、崖壁、水流、森林甚至是荒野。
全控機構為被收容者安排了整天的行程,意思就是說,被收容者的一切基本需求都必須事先加以規劃。
但是,Goffman「全控機構」的概念,在某些情況中,忽略了一些事實,也就是,有時候,嚴密控制的本身,不全然是外加的強迫性措施,而是參與者也參與在其中的集體群聚,也就是一種出於集體性的共謀所造成;更且,「全控」的出現,往往有一個漫長的發展性過程在其中,一個自發性群聚的組織,有時會發展成為「全控機構」,但這是一連串因素所造成,而非一開始就是以嚴密監控為目的。
高付出需求機構
在Goffman「全控機構」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去想像另一個社會學的概念︰「高付出需求機構」(Greedy Institution)。
德裔美籍社會學家Lewis Coser,或許是出於對Goffman「全控機構」概念不太滿意,而在1974年提出了另一個概念「高付出需求機構」,用來指稱那種對成員有極高的要求,而且是完全占有性的,團體要求成員對團體要有不可分割性的忠誠。
在「高付出需求機構」中,組織對成員並不是以強制為手段,而是機構會涵蓋整個人格需求,而得以來獲得成員無條件的順服與參與。他們要求成員對團體有高度的認同,而希望完全占有成員,並削弱成員與其他團體之間的關係。和 Goffman所說的「全控機構」相比,「高付出需求機構」並不使用物理性的暴力,而主要是經由心理壓力和社會神聖化的效果來規訓成員。對「高付出需求機構」背後更大的歷史脈絡,Coser說:
在相對未分化的社會,對個人忠誠度的要求比較少,不過即使如此,對於成員歸屬要求之衝突,仍然是一個常態而不是例外。Max Gluckman及其他人都曾指出,在原初社會,例如說在地域性跟親屬團體之間,總是存在有競爭性的要求。在中世紀,分化程度較高(對於此,就一般所讚揚的所謂「中世紀的整合」這件事,我們對其存在具有高度的懷疑),存在於聖壇和王權之間對於人們忠誠度的爭奪是不可忽視的。不過,和早期的社會結構相比,在高度分化的社會裡,因在歸屬和忠誠度等層面上的要求而所產生的衝突,可能會愈來愈為明顯。
雖然Coser對社會分化與「高付出需求機構」之間的關係並未深入討論,我們大致仍可以發現,二者之間,不是一種直線性的關係,而是在內外環境變化中會產生某種辯證性的發展。
在社會低度分化時,看起來團體對個人的壟斷性較高,也就是團體對個人的忠誠度的要求較高,但其實不然,因為當組織專門化的程度較低,對成員刻意的占有性並不高;等到社會分化成多類團體,譬如說有親屬團體、地域團體、宗教團體等的區別,這時團體間會彼此競爭有限成員的資源與情感歸屬,「高付出需求機構」的型態也就出現了,我認為,這時的「高付出需求性」,它更多的可能是來自對於成員情感歸屬的占有,而不是來自於團體專門化的內在需要;等到社會高度分化,各類團體愈趨於專門化,個人在其中的表現被要求達到極致化,個人對團體的參與不能散漫而前後不一致,這在內在邏輯上,對於個人的忠誠度與付出,有了一種更明確的「高付出需求」(greediness)傾向,但弔詭的是,當社會高度分化,除一些初級團體外,更多了各類工作團體、政治團體、志願參與團體等等,多類團體分割了個人的生活空間,社會上反而醞釀出某種要求,或者是有法律依據(如工時的限制)、或者是有不成文規範,不能允許單一團體對個人自主性的生活空間有太大的獨占性,於是當內外不同力量間產生相生相剋般的辯證性的結合,這又會形成一種相當矛盾而時有緊張性發生的情況。除了現代組織內在一致性的要求以外,對於為什麼在分化社會之公共規範要求團體不能對個人有所獨占性時,社會上還是會出現各種「高付出需求機構」,Coser書中並未詳加說明,而僅在一個段落中指出,這可能是因為某些團體有著烏托邦式的訴求,仍想要對抗外在世俗性的主流價值,而想要刻意維持一種團體內外間的界線,以讓成員不為外在環境所混淆或迷惑,而產生出這種與社會主流規範所相反的「高付出需求機構」。
「高付出需求機構」對成員有一個總體性的要求,要將成員日常生活圈中的人格展現予以完全占有,團體要求著成員完全且不可分割的忠誠,它通常不會以外部性的強制來與外界區隔,相反地,它傾向於經過自願性服從和忠誠,並以成員主動投入的形式來運作。以上這種特徵,我們已由日月明功愈來愈強的教主權威與愈來愈維嚴格的管教模式中,看到了「高付出需求機構」的樣貌,而在這種「高付出需求」中,我們看到,雖然多位成員在法院證詞中都表達出了當時參與的壓力與緊張,但他們並不會否認其曾自願且認真投入於內部學習與互動的事實。
現代高分化社會裡仍然出現各式各樣的「高付出需求機構」,其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以及對團體與社會產生緊張性的模式為何?參與者在這類團體中的身心狀態又是如何呢?透過「高付出需求機構」這個概念,相對於「全控機構」這個概念,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情況中,一個團體由外在看起來是嚴密的社會控制,但是在團體的結構性成因以及成員參與的過程來看,成員常常是出於自願,並且常是懷抱著特殊的情感狀態或目的而來參與。不過,一旦某個團體在冒犯了法律的界線或是觸犯了外在的集體共識時,在內在外,或者被內部成員重新看待,或者被外界仔細檢視,這個團體往往會被理解為是一種強迫性控制的「全控機構」,而且是出於洗腦與規訓而所形成的團體的藩籬。兩種觀點間的微妙差異,會影響我們對於某個團體內在本質和動態表現形式的理解。
以下,我將會以「高付出需求機構」,作為理解日月明功的一個主要核心概念;「全控機構」則作為一個輔助性的概念,以助於描述這個團體的運作型態和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