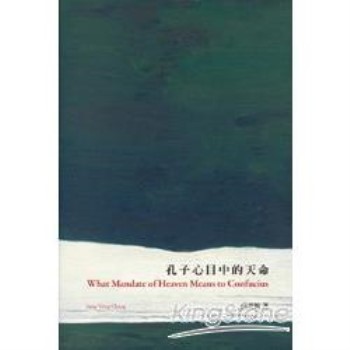第一章 「天命」的興起與式微
〔本章提要〕
「天命」觀是周人的發明。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起源於武王滅商之後,周公相成王討伐三監、淮夷之前(代表文獻是〈周書.大誥〉),而在平定武庚之亂後,進一步形成「三代」史觀(參見〈周書.召誥〉、〈多士〉),目的在於合法化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革命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就理論的建構而言,周人的「天命」觀由於增補了「敬德」原則(見於〈周書.康誥〉、〈酒誥〉以下諸篇)終於形成完整的「天命」論述。在這套「天命」論述中,周人不僅為新取得的政權建立了來自於「天」的超越根據(「天命」),而且也為這個超越性的合法根據提出了合理性的實踐準則(「敬德」)。
「天命」論述原本代表周初對於政權合法性(來自於「天」)和治權合理性(「德」治)的政治理想,然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看,卻存在著無從解決的缺陷和困難。理論上,「天命」歸屬的問題,最終難免等同於「成王敗寇」的結果論;而在現實政治中,一旦基於血統論的君位世襲制度確立,「天命」論述就完全被架空,只成了「家天下」的某個神聖家族的傳說。
一、「天命」觀的興起:文獻的考察
「天」(「帝」)和「命」概念的出現和使用,淵源久遠,在《書》、《詩》中已經各自擁有豐富的意義內涵。同樣也是在《書》、《詩》中,作為複合概念的「天命」一詞也多次出現(有時候也並不直接使用複合概念「天命」,而使用「天……命……」的語句形式,甚至只是以「命」一字來加以統括),表達了當時對於「政權合法性來自於天」的政治論述。「天命」觀的要點在於,政權合法性的充分條件取決於一個超越人世的最高主宰或人格神(「帝」或「天」)的授權,這種「超越性的授權」既指對新統治者的認可,同時也是對舊統治者權力的否定和剝奪。前者(即對新統治者的認可)可以從以下《書》、《詩》中的引句 得到明證:
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周書.金縢〉)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周書.大誥〉)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頌.清廟之什.昊天有成命〉)
後者(即對舊統治者權力的剝奪)則有如:
天既訖我殷命。(〈商書.西伯戡黎〉)
天降喪于殷……今惟殷墜厥命。(〈周書.酒誥〉)
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周書.君奭〉)
然而實際上,以上兩者的具體指涉又常常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說,在新舊政權的轉移過程中,「天」既褫奪了對舊統治者的原有授權,也同時賦與了新統治者的最新授權。這樣的表述在《書》中也不少見: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周書.康誥〉)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周書.召誥〉)
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殷命終于帝。(〈周書.多士〉)
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周書.君奭〉)
上引各例句中的「命」字大都具有實質的指涉,或者是指被剝奪的統治權力,或者是指被授予的統治權力,而不論是被剝奪還是被授予,先後的權力轉移顯然都帶有一種權威性的印記,這當然是因為這種授權(「命」)是來自於「天」的緣故。「天命」原本就具有超出個人或集團力量的超越性、絕對性與終極性。不過,這種實質指涉的「命」字卻並非是《書》、《詩》中「命」字的本義。
「命」字是從「令」字演化而來,而「『令』字之本式,像一人屈身跽于一三角形之下」,「令」字上部的那個三角形,「蓋本為屋宇或帳幕之原始象形」,因為「古者發號施令恆於宮廟行之,凡受命者引領待於其下,是以『令』字如此作。」 因此,「命」字的本義當作「命令」或「指使」(不管是作為動詞或者動詞的名詞化),一如《說文》所說:「命,使也,從口、令」;「令,發號也。」
就《書》而言,作「命令」解的「命」字 出現最早、次數也最多,但這樣的「命」字還不具備特殊的理論內涵,而是要到了從君王的命令蛻變為「天」的命令之後,一個關於政權合法性授權的「天命」觀才終於浮現。在〈虞夏書〉和〈商書〉中已經可見「(天)命」的說法:
有扈氏……天用勦絕其命。(〈虞夏書.甘誓〉)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書.湯誓〉)
天既訖我殷命。(〈商書.西伯戡黎〉)
不過這三處引文中「天……命……」或「天命」的用法和意義在〈虞夏書〉和〈商書〉中只算是特例,它們所表達的「天命」觀既沒有同時代其它文本的佐證 ,也完全沒有形成一套普遍的論述 。相較之下,作為複合概念的「天命」大量湧現於周初文獻的事實,則讓人印象深刻 ,而且還是作為異常突出的政治觀點被擴大操作。
散布在《周書》 諸篇中的「天命」觀,是周人有意識地自覺創造出來的政治論述,這個論述的根本意義在於,周人為自己從商人手中以武力取得的新政權提出了合法性的說明。從時間上來看,「天命」觀的定型化似乎不能早過武王克商之役,因為在〈牧誓〉 篇中,周人還沒有高舉「天命」的大纛作為「翦商」(〈詩.魯頌.駉之什.閟宮〉)的號召,而只是略數了商紂的不義 ,然後說「今予發(按,即武王),惟恭行天之罰」。本來,「天罰」也在「天命」的含義之內,意指「上天(對舊統治者)的懲罰」,但既然在殷商政權轉移的那個歷史性的黎明時分所宣告的〈牧誓〉中並沒有標明「天命」一詞,這似乎強烈暗示了,至少在武王伐紂之前,周人還沒有建構完成他們的「天命」觀。
從傳世文獻來看,周人最早的「天命」觀,應該出現在武王滅商後兩年(代表作是〈周書.金縢〉)與周公相成王討伐三監 、淮夷之前(代表作是〈周書.大誥〉)的一段相對短暫的年代之間。〈金縢〉描述了周公因為武王重病而向先王祈求,希望以自己替代武王的生命(「以旦代某之身」),在該篇內史官的祝禱詞中,周公第一次提到了「無墜天之降寶命」 。〈大誥〉則是周公東征「三監」前對臣民所作的告諭。就當時情勢來看,周王朝的諸侯和朝臣對於征伐「三監」似乎不甚用心,同時也顯得信心不足,周公面對內憂外患一齊俱來,處境十分孤立。周公後來訴諸於占卜和「天命」以重建周王朝臣民的信心,再加上策略性地分化殷人,得到殷貴族們的擁護,才逐漸扭轉了劣勢。〈大誥〉就是周公率軍「將黜殷」(〈書序〉)之前的精神講話。
〈大誥〉率先提出了「格知天命」、「前人受命」之說,然後對反對出兵的諸侯國君、百官和王室近臣曉諭勸導,表白了成王不敢不遵循「上帝命」,因為「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文王繼承了「天命」在前,他自己現在也要實現「寧王大命」。文中最後再一次提出「上帝命」,又反覆陳說周邦的「天命不易」、「天命不僭」,因為「天惟喪殷」。
在〈大誥〉中,周人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命」觀 ,並且還是藉著文王而呈現,這和《詩》中對於文王「受命」的事後追述有異曲同工之妙。《詩》〈大雅〉和〈周頌〉中許多詩篇集中表達了對文王「受命」的讚頌(有時兼及武王),甚至把文王和「上帝」聯結起來,幾乎視文王為「上帝」的代理人 :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大雅.文王之什.大明〉)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頌.清廟之什.昊天有成〉)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時周之命,於繹思!(〈周頌.閔予小子之什.賚〉)
周人的「天命」觀還不僅用以合法化文王、武王革命流血的軍事行動,他們甚至也把這個觀點多次回溯套用在商人(湯)從夏人(桀)手中奪取政權的歷史: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周書.召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按,指夏、商),其正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召誥〉的時代背景是周公平定了武庚之亂,準備營建洛邑作為東都,好將殷遺民集中在洛邑以方便統一管理。〈書序〉說:「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史記.周本紀〉也記載了這件事:「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這是周公還政於成王時候的事。除了〈召誥〉,商革夏命的論述邏輯同樣見於《周書》以下各篇: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多士〉)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多方〉)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立政〉)
如此一來,「天命」觀甚至成了一種「三代」史觀。根據這種三代「天命」史觀,周人自己的代殷「受命」和前代的以殷代夏,都獲得了當時人們心目中的最高主宰者(「天」或「帝」) 的授意和授權。授意是指人們理解並接受上天或隱或顯的指示,而授權則是說人們根據前項指示以取得並保有新的、也是合法的政權。
周人的「天命」觀一方面從歷史的縱深中尋求支點(三代史觀),另一方面也在周初政權還不穩定的時空背景下積極營造有利於自己的政治環境。後者尤其表現在新王朝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內、對外推廣「天命」觀,周人在這方面的努力以〈康誥〉和〈多士〉兩篇最為典型。〈康誥〉是冊封康叔於衛國的誥辭,是一篇標準的對內宣傳的官方文書: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康誥〉)
〈多士〉則是遷殷遺民於洛邑之後,周公對「商王士」(或作「殷遺多士」,即商遺民中的貴族)的諭示,因為性質上是對外的,對象是昔日的敵人,周公更是不厭其煩地反覆致意:
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有夏不適逸……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于帝。(〈多士〉)
在〈多士〉中,周公多次憑藉「天命」之說來勸導、壓制殷商的舊貴族。也許因為聽眾中也有同情或參與叛周行動的各族人員,所以周公的用語則顯得嚴厲,但不忘恩威並重。周公對這些人說,將他們遷居洛邑是因為「天命」,而對那些在武庚之亂後有意為新王朝服務的人(這似乎是沿用舊例,因為殷革夏命之後也任用了夏朝遺臣為官),周公說他是用人唯德,如果有德,就會被拔擢任官。周公告誡眾人,所有這一切的是是非非,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時惟天命」,他並且多次以「天罰」作為威脅。
〔本章提要〕
「天命」觀是周人的發明。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起源於武王滅商之後,周公相成王討伐三監、淮夷之前(代表文獻是〈周書.大誥〉),而在平定武庚之亂後,進一步形成「三代」史觀(參見〈周書.召誥〉、〈多士〉),目的在於合法化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革命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就理論的建構而言,周人的「天命」觀由於增補了「敬德」原則(見於〈周書.康誥〉、〈酒誥〉以下諸篇)終於形成完整的「天命」論述。在這套「天命」論述中,周人不僅為新取得的政權建立了來自於「天」的超越根據(「天命」),而且也為這個超越性的合法根據提出了合理性的實踐準則(「敬德」)。
「天命」論述原本代表周初對於政權合法性(來自於「天」)和治權合理性(「德」治)的政治理想,然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看,卻存在著無從解決的缺陷和困難。理論上,「天命」歸屬的問題,最終難免等同於「成王敗寇」的結果論;而在現實政治中,一旦基於血統論的君位世襲制度確立,「天命」論述就完全被架空,只成了「家天下」的某個神聖家族的傳說。
一、「天命」觀的興起:文獻的考察
「天」(「帝」)和「命」概念的出現和使用,淵源久遠,在《書》、《詩》中已經各自擁有豐富的意義內涵。同樣也是在《書》、《詩》中,作為複合概念的「天命」一詞也多次出現(有時候也並不直接使用複合概念「天命」,而使用「天……命……」的語句形式,甚至只是以「命」一字來加以統括),表達了當時對於「政權合法性來自於天」的政治論述。「天命」觀的要點在於,政權合法性的充分條件取決於一個超越人世的最高主宰或人格神(「帝」或「天」)的授權,這種「超越性的授權」既指對新統治者的認可,同時也是對舊統治者權力的否定和剝奪。前者(即對新統治者的認可)可以從以下《書》、《詩》中的引句 得到明證:
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周書.金縢〉)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周書.大誥〉)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頌.清廟之什.昊天有成命〉)
後者(即對舊統治者權力的剝奪)則有如:
天既訖我殷命。(〈商書.西伯戡黎〉)
天降喪于殷……今惟殷墜厥命。(〈周書.酒誥〉)
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周書.君奭〉)
然而實際上,以上兩者的具體指涉又常常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說,在新舊政權的轉移過程中,「天」既褫奪了對舊統治者的原有授權,也同時賦與了新統治者的最新授權。這樣的表述在《書》中也不少見: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周書.康誥〉)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周書.召誥〉)
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殷命終于帝。(〈周書.多士〉)
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周書.君奭〉)
上引各例句中的「命」字大都具有實質的指涉,或者是指被剝奪的統治權力,或者是指被授予的統治權力,而不論是被剝奪還是被授予,先後的權力轉移顯然都帶有一種權威性的印記,這當然是因為這種授權(「命」)是來自於「天」的緣故。「天命」原本就具有超出個人或集團力量的超越性、絕對性與終極性。不過,這種實質指涉的「命」字卻並非是《書》、《詩》中「命」字的本義。
「命」字是從「令」字演化而來,而「『令』字之本式,像一人屈身跽于一三角形之下」,「令」字上部的那個三角形,「蓋本為屋宇或帳幕之原始象形」,因為「古者發號施令恆於宮廟行之,凡受命者引領待於其下,是以『令』字如此作。」 因此,「命」字的本義當作「命令」或「指使」(不管是作為動詞或者動詞的名詞化),一如《說文》所說:「命,使也,從口、令」;「令,發號也。」
就《書》而言,作「命令」解的「命」字 出現最早、次數也最多,但這樣的「命」字還不具備特殊的理論內涵,而是要到了從君王的命令蛻變為「天」的命令之後,一個關於政權合法性授權的「天命」觀才終於浮現。在〈虞夏書〉和〈商書〉中已經可見「(天)命」的說法:
有扈氏……天用勦絕其命。(〈虞夏書.甘誓〉)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書.湯誓〉)
天既訖我殷命。(〈商書.西伯戡黎〉)
不過這三處引文中「天……命……」或「天命」的用法和意義在〈虞夏書〉和〈商書〉中只算是特例,它們所表達的「天命」觀既沒有同時代其它文本的佐證 ,也完全沒有形成一套普遍的論述 。相較之下,作為複合概念的「天命」大量湧現於周初文獻的事實,則讓人印象深刻 ,而且還是作為異常突出的政治觀點被擴大操作。
散布在《周書》 諸篇中的「天命」觀,是周人有意識地自覺創造出來的政治論述,這個論述的根本意義在於,周人為自己從商人手中以武力取得的新政權提出了合法性的說明。從時間上來看,「天命」觀的定型化似乎不能早過武王克商之役,因為在〈牧誓〉 篇中,周人還沒有高舉「天命」的大纛作為「翦商」(〈詩.魯頌.駉之什.閟宮〉)的號召,而只是略數了商紂的不義 ,然後說「今予發(按,即武王),惟恭行天之罰」。本來,「天罰」也在「天命」的含義之內,意指「上天(對舊統治者)的懲罰」,但既然在殷商政權轉移的那個歷史性的黎明時分所宣告的〈牧誓〉中並沒有標明「天命」一詞,這似乎強烈暗示了,至少在武王伐紂之前,周人還沒有建構完成他們的「天命」觀。
從傳世文獻來看,周人最早的「天命」觀,應該出現在武王滅商後兩年(代表作是〈周書.金縢〉)與周公相成王討伐三監 、淮夷之前(代表作是〈周書.大誥〉)的一段相對短暫的年代之間。〈金縢〉描述了周公因為武王重病而向先王祈求,希望以自己替代武王的生命(「以旦代某之身」),在該篇內史官的祝禱詞中,周公第一次提到了「無墜天之降寶命」 。〈大誥〉則是周公東征「三監」前對臣民所作的告諭。就當時情勢來看,周王朝的諸侯和朝臣對於征伐「三監」似乎不甚用心,同時也顯得信心不足,周公面對內憂外患一齊俱來,處境十分孤立。周公後來訴諸於占卜和「天命」以重建周王朝臣民的信心,再加上策略性地分化殷人,得到殷貴族們的擁護,才逐漸扭轉了劣勢。〈大誥〉就是周公率軍「將黜殷」(〈書序〉)之前的精神講話。
〈大誥〉率先提出了「格知天命」、「前人受命」之說,然後對反對出兵的諸侯國君、百官和王室近臣曉諭勸導,表白了成王不敢不遵循「上帝命」,因為「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文王繼承了「天命」在前,他自己現在也要實現「寧王大命」。文中最後再一次提出「上帝命」,又反覆陳說周邦的「天命不易」、「天命不僭」,因為「天惟喪殷」。
在〈大誥〉中,周人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命」觀 ,並且還是藉著文王而呈現,這和《詩》中對於文王「受命」的事後追述有異曲同工之妙。《詩》〈大雅〉和〈周頌〉中許多詩篇集中表達了對文王「受命」的讚頌(有時兼及武王),甚至把文王和「上帝」聯結起來,幾乎視文王為「上帝」的代理人 :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大雅.文王之什.大明〉)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頌.清廟之什.昊天有成〉)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時周之命,於繹思!(〈周頌.閔予小子之什.賚〉)
周人的「天命」觀還不僅用以合法化文王、武王革命流血的軍事行動,他們甚至也把這個觀點多次回溯套用在商人(湯)從夏人(桀)手中奪取政權的歷史: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周書.召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按,指夏、商),其正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召誥〉的時代背景是周公平定了武庚之亂,準備營建洛邑作為東都,好將殷遺民集中在洛邑以方便統一管理。〈書序〉說:「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史記.周本紀〉也記載了這件事:「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這是周公還政於成王時候的事。除了〈召誥〉,商革夏命的論述邏輯同樣見於《周書》以下各篇: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多士〉)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多方〉)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立政〉)
如此一來,「天命」觀甚至成了一種「三代」史觀。根據這種三代「天命」史觀,周人自己的代殷「受命」和前代的以殷代夏,都獲得了當時人們心目中的最高主宰者(「天」或「帝」) 的授意和授權。授意是指人們理解並接受上天或隱或顯的指示,而授權則是說人們根據前項指示以取得並保有新的、也是合法的政權。
周人的「天命」觀一方面從歷史的縱深中尋求支點(三代史觀),另一方面也在周初政權還不穩定的時空背景下積極營造有利於自己的政治環境。後者尤其表現在新王朝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內、對外推廣「天命」觀,周人在這方面的努力以〈康誥〉和〈多士〉兩篇最為典型。〈康誥〉是冊封康叔於衛國的誥辭,是一篇標準的對內宣傳的官方文書: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康誥〉)
〈多士〉則是遷殷遺民於洛邑之後,周公對「商王士」(或作「殷遺多士」,即商遺民中的貴族)的諭示,因為性質上是對外的,對象是昔日的敵人,周公更是不厭其煩地反覆致意:
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有夏不適逸……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于帝。(〈多士〉)
在〈多士〉中,周公多次憑藉「天命」之說來勸導、壓制殷商的舊貴族。也許因為聽眾中也有同情或參與叛周行動的各族人員,所以周公的用語則顯得嚴厲,但不忘恩威並重。周公對這些人說,將他們遷居洛邑是因為「天命」,而對那些在武庚之亂後有意為新王朝服務的人(這似乎是沿用舊例,因為殷革夏命之後也任用了夏朝遺臣為官),周公說他是用人唯德,如果有德,就會被拔擢任官。周公告誡眾人,所有這一切的是是非非,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時惟天命」,他並且多次以「天罰」作為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