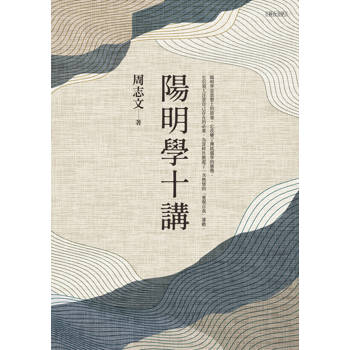一、為何講陽明學?
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講題是「陽明學十講」,陽明是誰,我想大家都知道。陽明就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陽明,明代有很多思想家,為什麼要講他?還有,如果要講思想家,中國自孔子以來,有成百上千的思想家,不講別的,只講王陽明,是什麼緣故?
當然,中國兩三千年來有許多了不起的思想與思想家,都有人研究,也都會有人講的,我只能講我比較熟悉的部分。我認真的讀過不少有關王陽明的書,對他的想法與作為,有點體會,有點看法。簡單說,我自己覺得對王陽明的了解比對別的思想家多一些,所以在介紹中國思想家裡面,我選擇了王陽明,這是個人的緣故。
其次是歷史的原因,陽明在歷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研究明代思想的人都必定會讀《明儒學案》這本書,《明儒學案》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黃宗羲寫的。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是浙江餘姚人,算起來他是王陽明的小同鄉。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重要的學者,他除了《明儒學案》之外還有《宋元學案》,這兩部書是後代研究宋、元、明學術思想史不可缺的材料(《宋元學案》他沒寫完,是由他後學全祖望等人續成)。他還有《明夷待訪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由他領軍,在他學生後輩如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同鄉後代全祖望(1705-1755)等人努力之下,在清代學術史上開啟了「浙東史學」一派,對後世史學與學術史的研究有很大的開拓作用與影響。
提到黃宗羲也不由得令人想起「清初三大儒」這名詞,依晚清後的學人看,這「清初三大儒」指的是黃宗羲、顧炎武(亭林,1613-1682)、王夫之(船山,1619-1692)三人,但顧與王在清初的時候名尚未顯,知道他們的人不多,而且顧、王的學術,是偏向反王學一方。當時也有「三大儒」之稱,不過所指的是黃宗羲、孫奇逢(夏峰,1584-1675)與李顒(二曲,1627-1705)三人。孫奇逢是河北人,李顒是陜西人,這兩人都都是北方人,加上黃宗羲,三人同是以王學為宗,但對王學也都有修正,可見明末的學術,仍是王學的天下。不論清末認定的或清初既有的「三大儒」,都把黃宗羲包括在內,因此他在清代學術界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要想知道黃宗羲的學術貢獻,全祖望在《鮚埼亭集》中有篇〈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面說: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首3次3)
雖然是推崇之語,但大體上也說得很恰當,可見黃宗羲明清之際學術上的重要。本文不是談黃宗羲的,我們得回歸談陽明學術的主要線條上。談起陽明必須先從黃宗羲的著作談起,而談起黃宗羲,又必須從黃的老師談起。黃梨洲的老師叫劉宗周(蕺山,1578-1645),是浙江山陰人。山陰就是今天的紹興,春秋時叫作會稽,是當時越國的首都,這地方出了許多歷史的名人,晉代的書法家王羲之(303-361)自少年便遷居到此處,有名的〈蘭亭集序〉就寫在此,蘭亭就在紹興,王陽明雖是餘姚人,但少年時就隨父王華遷居紹興,以後在此長住,在此講學,所以山陰也算陽明的故鄉,餘姚反而很少回去,山陰、餘姚兩地其實不遠,陽明死後也葬在山陰。
劉宗周算是一個奇人,他與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白安,1584-1626)一樣,都是與明末有名的「東林書院」有關的人物。東林在今江蘇無錫,原是宋朝大儒楊時(龜山,1053-1135)歸隱講學之處,到明朝成了個有名的書院。東林書院的人物講學,十分注重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也就是後世說的「學問為濟世之本」,是主張求學問是要用來服務社會的,東林書院的學者都比較主張用學術干預實際政治,學問不是空談心性就夠了,說穿了,就是傳統儒家講的「內聖外王」之學,所謂內聖外王,講的就是自己修養好了,要去解救世人,君子是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的,必求兼善天下。《明儒學案》形容東林師友的特色,說:「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冷風指社會的反應不見得好,熱血指自己仍不死心,雖經挫折,仍充滿了拯救時代的願力。黃宗羲又稱道東林的作用,說:「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流風于韻也。」可見東林在晚明的作用及重要性。
東林派學者基本上都是陽明學派,但他們對晚明有一派的陽明學者很不滿,認為他們太猖狂又不學無術,所以他們都比較重視讀書,又主張讀書要能變化氣質,還有他們認為讀書的目的不在講玄虛的道理,更不在媚俗,而在立身,立身的目的是要積極服務社會,當時不叫服務社會,而是叫「經世」。今天我們到無錫的東林書院,還看得到那副有名的對聯高懸在大廳,對聯寫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書院領導人顧憲成(涇陽1550-1612)寫的,可見他們東林學者的胸襟。
劉宗周治學嚴謹,一生標舉「慎獨」兩字,要求學生哪怕一個人獨處,也得小心謹慎,絲毫不茍。劉宗周無疑是明代陽明學的殿軍,他承襲了陽明的良知學說裡面最嚴謹的部分,他對良知說所達的幽微處境也深有所契,而他對當時陽明學的「末流」也嚴詞批判。到了劉宗周,明朝就亡國了。有一點非常值得說的是,劉宗周雖也科舉出身,但在明亡時並未擔任要職,他聽到明思宗自縊煤山的消息後悲痛不已,後來眼看清兵南下,杭州即將淪陷,竟然採絕食的方式殉國了。絕食是很辛苦的事,要靠極堅強的意志力才能做到的,劉的絕食而死,對當時影響很大,他的學生王毓蓍(-1645)與祝淵(1614-1645)也都先後自殺,還有一些學生如陳確(乾初,1604-1677)與黃宗羲等雖未死,卻以氣節自勵,終生不肯降清,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很大。
今天要研究明代思想,一定要依據、參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們來看《明儒學案》這本書,王陽明與他後學所形成的學派佔有多少篇幅?《明儒學案》從第一卷〈崇仁學案〉開始到第六十二卷〈蕺山學案〉為止,一共六十二卷,卷九之前是陽明前的諸儒學案,包括〈崇仁學案〉四卷,〈白沙學案〉二卷,〈河東學案〉二卷,〈三原學案〉一卷,從第十卷〈姚江學案〉(就是寫陽明本身的那一部分)之後,其中在〈泰州學案〉之前有〈止修學案〉一卷,〈泰州學案〉有〈甘泉學案〉佔有六卷,之後〈諸儒學案〉共分上中下共十五卷,〈諸儒學案〉之後就是〈東林學案〉與〈蕺山學案〉了,這兩學案中的人物對陽明學雖有批判,但也算是陽明學的一支,所以我們統計全書,寫陽明與陽明後學的共有三十一卷,以卷數言,正好占了《明儒學案》的一半,就內容言,當然更不只於此,因為陽明後的「諸儒」,就算其學宗旨不標榜陽明學,但所討論的,也絕大多是與陽明學有關的事。
我認為陽明學的重要,在於它改變了傳統儒學的態勢,也就是說陽明學比較注意自己存在的必要,這是以往所有儒學家比較忽視的問題。
傳統的儒家比較注意禮,比較講道德,禮是一種行為的約束,而道德又是社會生活下的產物,因此儒家講學問,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這套學問講到極致,往往忽略了自己,忽略了個人,陽明之學比較注意個人良知的呈現,主張一個人內心最初的判斷往往最為準確,這種說法,有點否定傳統知識的說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的爭議與回響,是十分特殊的。當然在陽明之前,在北宋的時候與朱子(名熹,字晦庵,1130-1200)同時的陸象山(號九淵,1139-1193)之學,已經有了這種「態勢」了。陸學與朱學最大的不同在朱學比較講學問,也就是歷史上稱的「道問學」,比較強調學問知識的重要,而陸九淵比較注意的是「尊德性」,所謂尊德性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在涵養,換句話說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心,比較講究一個人內心所達的道德境界,陸學也被稱為是「發明本心」。
陸九淵這派學說比較注意內在,不求外表,在乎心之所得,不在乎自己讀過了多少書、掌握了多少知識。但在宋朝,陸學的勢力始終不敵朱學,原因是客觀知識比變化莫測的內心更好把握一些,朱學比較有途徑可尋,而陸學的境界對一般人而言,反而難以達成。
但到了明朝,這種態勢就大大改變了,這是因為朱學已盛了幾百年,本身已露出了疲態,再加上明代社會已去南宋的時代太遠,很多事已變得十分不同了。王陽明的學說比較接近象山一派,陸、王之學都有一種「發明本心」的傾向,陽明之學自興起後,得到的社會呼應極大,在明代,王學的起來有點像掀起了一種遍及社會各層的「發現自我」運動。
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講題是「陽明學十講」,陽明是誰,我想大家都知道。陽明就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陽明,明代有很多思想家,為什麼要講他?還有,如果要講思想家,中國自孔子以來,有成百上千的思想家,不講別的,只講王陽明,是什麼緣故?
當然,中國兩三千年來有許多了不起的思想與思想家,都有人研究,也都會有人講的,我只能講我比較熟悉的部分。我認真的讀過不少有關王陽明的書,對他的想法與作為,有點體會,有點看法。簡單說,我自己覺得對王陽明的了解比對別的思想家多一些,所以在介紹中國思想家裡面,我選擇了王陽明,這是個人的緣故。
其次是歷史的原因,陽明在歷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研究明代思想的人都必定會讀《明儒學案》這本書,《明儒學案》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黃宗羲寫的。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是浙江餘姚人,算起來他是王陽明的小同鄉。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重要的學者,他除了《明儒學案》之外還有《宋元學案》,這兩部書是後代研究宋、元、明學術思想史不可缺的材料(《宋元學案》他沒寫完,是由他後學全祖望等人續成)。他還有《明夷待訪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由他領軍,在他學生後輩如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同鄉後代全祖望(1705-1755)等人努力之下,在清代學術史上開啟了「浙東史學」一派,對後世史學與學術史的研究有很大的開拓作用與影響。
提到黃宗羲也不由得令人想起「清初三大儒」這名詞,依晚清後的學人看,這「清初三大儒」指的是黃宗羲、顧炎武(亭林,1613-1682)、王夫之(船山,1619-1692)三人,但顧與王在清初的時候名尚未顯,知道他們的人不多,而且顧、王的學術,是偏向反王學一方。當時也有「三大儒」之稱,不過所指的是黃宗羲、孫奇逢(夏峰,1584-1675)與李顒(二曲,1627-1705)三人。孫奇逢是河北人,李顒是陜西人,這兩人都都是北方人,加上黃宗羲,三人同是以王學為宗,但對王學也都有修正,可見明末的學術,仍是王學的天下。不論清末認定的或清初既有的「三大儒」,都把黃宗羲包括在內,因此他在清代學術界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要想知道黃宗羲的學術貢獻,全祖望在《鮚埼亭集》中有篇〈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面說: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首3次3)
雖然是推崇之語,但大體上也說得很恰當,可見黃宗羲明清之際學術上的重要。本文不是談黃宗羲的,我們得回歸談陽明學術的主要線條上。談起陽明必須先從黃宗羲的著作談起,而談起黃宗羲,又必須從黃的老師談起。黃梨洲的老師叫劉宗周(蕺山,1578-1645),是浙江山陰人。山陰就是今天的紹興,春秋時叫作會稽,是當時越國的首都,這地方出了許多歷史的名人,晉代的書法家王羲之(303-361)自少年便遷居到此處,有名的〈蘭亭集序〉就寫在此,蘭亭就在紹興,王陽明雖是餘姚人,但少年時就隨父王華遷居紹興,以後在此長住,在此講學,所以山陰也算陽明的故鄉,餘姚反而很少回去,山陰、餘姚兩地其實不遠,陽明死後也葬在山陰。
劉宗周算是一個奇人,他與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白安,1584-1626)一樣,都是與明末有名的「東林書院」有關的人物。東林在今江蘇無錫,原是宋朝大儒楊時(龜山,1053-1135)歸隱講學之處,到明朝成了個有名的書院。東林書院的人物講學,十分注重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也就是後世說的「學問為濟世之本」,是主張求學問是要用來服務社會的,東林書院的學者都比較主張用學術干預實際政治,學問不是空談心性就夠了,說穿了,就是傳統儒家講的「內聖外王」之學,所謂內聖外王,講的就是自己修養好了,要去解救世人,君子是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的,必求兼善天下。《明儒學案》形容東林師友的特色,說:「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冷風指社會的反應不見得好,熱血指自己仍不死心,雖經挫折,仍充滿了拯救時代的願力。黃宗羲又稱道東林的作用,說:「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流風于韻也。」可見東林在晚明的作用及重要性。
東林派學者基本上都是陽明學派,但他們對晚明有一派的陽明學者很不滿,認為他們太猖狂又不學無術,所以他們都比較重視讀書,又主張讀書要能變化氣質,還有他們認為讀書的目的不在講玄虛的道理,更不在媚俗,而在立身,立身的目的是要積極服務社會,當時不叫服務社會,而是叫「經世」。今天我們到無錫的東林書院,還看得到那副有名的對聯高懸在大廳,對聯寫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書院領導人顧憲成(涇陽1550-1612)寫的,可見他們東林學者的胸襟。
劉宗周治學嚴謹,一生標舉「慎獨」兩字,要求學生哪怕一個人獨處,也得小心謹慎,絲毫不茍。劉宗周無疑是明代陽明學的殿軍,他承襲了陽明的良知學說裡面最嚴謹的部分,他對良知說所達的幽微處境也深有所契,而他對當時陽明學的「末流」也嚴詞批判。到了劉宗周,明朝就亡國了。有一點非常值得說的是,劉宗周雖也科舉出身,但在明亡時並未擔任要職,他聽到明思宗自縊煤山的消息後悲痛不已,後來眼看清兵南下,杭州即將淪陷,竟然採絕食的方式殉國了。絕食是很辛苦的事,要靠極堅強的意志力才能做到的,劉的絕食而死,對當時影響很大,他的學生王毓蓍(-1645)與祝淵(1614-1645)也都先後自殺,還有一些學生如陳確(乾初,1604-1677)與黃宗羲等雖未死,卻以氣節自勵,終生不肯降清,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很大。
今天要研究明代思想,一定要依據、參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們來看《明儒學案》這本書,王陽明與他後學所形成的學派佔有多少篇幅?《明儒學案》從第一卷〈崇仁學案〉開始到第六十二卷〈蕺山學案〉為止,一共六十二卷,卷九之前是陽明前的諸儒學案,包括〈崇仁學案〉四卷,〈白沙學案〉二卷,〈河東學案〉二卷,〈三原學案〉一卷,從第十卷〈姚江學案〉(就是寫陽明本身的那一部分)之後,其中在〈泰州學案〉之前有〈止修學案〉一卷,〈泰州學案〉有〈甘泉學案〉佔有六卷,之後〈諸儒學案〉共分上中下共十五卷,〈諸儒學案〉之後就是〈東林學案〉與〈蕺山學案〉了,這兩學案中的人物對陽明學雖有批判,但也算是陽明學的一支,所以我們統計全書,寫陽明與陽明後學的共有三十一卷,以卷數言,正好占了《明儒學案》的一半,就內容言,當然更不只於此,因為陽明後的「諸儒」,就算其學宗旨不標榜陽明學,但所討論的,也絕大多是與陽明學有關的事。
我認為陽明學的重要,在於它改變了傳統儒學的態勢,也就是說陽明學比較注意自己存在的必要,這是以往所有儒學家比較忽視的問題。
傳統的儒家比較注意禮,比較講道德,禮是一種行為的約束,而道德又是社會生活下的產物,因此儒家講學問,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這套學問講到極致,往往忽略了自己,忽略了個人,陽明之學比較注意個人良知的呈現,主張一個人內心最初的判斷往往最為準確,這種說法,有點否定傳統知識的說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的爭議與回響,是十分特殊的。當然在陽明之前,在北宋的時候與朱子(名熹,字晦庵,1130-1200)同時的陸象山(號九淵,1139-1193)之學,已經有了這種「態勢」了。陸學與朱學最大的不同在朱學比較講學問,也就是歷史上稱的「道問學」,比較強調學問知識的重要,而陸九淵比較注意的是「尊德性」,所謂尊德性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在涵養,換句話說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心,比較講究一個人內心所達的道德境界,陸學也被稱為是「發明本心」。
陸九淵這派學說比較注意內在,不求外表,在乎心之所得,不在乎自己讀過了多少書、掌握了多少知識。但在宋朝,陸學的勢力始終不敵朱學,原因是客觀知識比變化莫測的內心更好把握一些,朱學比較有途徑可尋,而陸學的境界對一般人而言,反而難以達成。
但到了明朝,這種態勢就大大改變了,這是因為朱學已盛了幾百年,本身已露出了疲態,再加上明代社會已去南宋的時代太遠,很多事已變得十分不同了。王陽明的學說比較接近象山一派,陸、王之學都有一種「發明本心」的傾向,陽明之學自興起後,得到的社會呼應極大,在明代,王學的起來有點像掀起了一種遍及社會各層的「發現自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