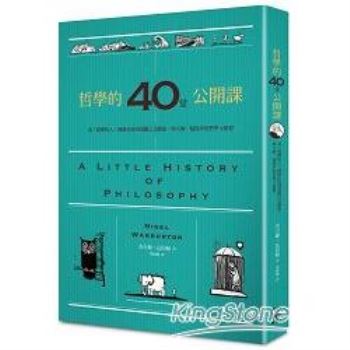你可能在做夢嗎?-笛卡兒
你聽到鬧鈴響了,把鬧鐘關掉,爬下床去著裝,吃了早餐,準備好面對今天。但接著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你醒了過來,發現那只是一場夢。你在夢中是醒的,過著生活,但現實中你還蜷縮在鴨絨被底下熟睡。如果你有過這種經驗,就會知道我的意思。這種夢通常叫做「假清醒」,顯得很逼真。法國哲學家笛卡兒做過一次這種夢,而這個夢讓他開始思考。他怎麼能夠確定他不是在做夢?
笛卡兒認為值得在人生中試一次,去弄清楚他能夠確知的是什麼(如果真有的話)。為了這麼做,他發展出一個方法,稱作「笛卡兒的懷疑方法」。這個方法相當直接:如果一件事有一絲可能是假的,就別當成真的。試想有一大袋蘋果,你知道袋子裡有些蘋果發霉了,不過你不確定是哪幾顆。你想要擁有一整袋好蘋果、沒有任何發霉蘋果。要怎麼樣達到這個結果呢?一種辦法是把蘋果全部倒在地板上,然後一次檢查一顆,只把你完全確定沒問題的蘋果擺回袋子裡去。在過程中你或許丟掉幾顆好蘋果,因為乍看之下它們可能裡頭發霉,不過最後絕對只有好蘋果進得了你的袋子。笛卡兒的懷疑方法大致上就是這樣。你拿出一個信念加以檢驗,像是「我現在正醒著讀這本書」,只有在你確定這個信念不可能出錯或造成誤導的狀況下才接受。只要有一丁點懷疑的空間,就不接受。笛卡兒逐一檢查過他相信的幾件事,質疑他是否完全確定這些事就如同表面看來那樣。世界真的就是他眼中的那個樣子嗎?他確定他沒在做夢嗎?
笛卡兒追求確定性的出發點是思考來自感官的證據:視覺、觸覺、嗅覺、味覺跟聽覺。我們可以信任我們的感官嗎?他的結論是其實不能。感官有時候會欺騙我們。我們會犯錯。想想你看到的事物:你的視覺在每件事物上都很可靠嗎?你應該總是相信你的眼睛嗎?
如果你從側面看一根放進水中的筆直棍子,它看起來是彎的。一個方形高塔從遠處看可能是圓的。我們全都偶爾會看錯。而且笛卡兒指出,信任一個以前欺騙過你的東西是不明智的,所以他拒絕把感官當成確定性的可能來源。他永遠不能確定他的感官沒騙他;大部分時候可能沒有,但感官會騙人的那點微薄可能性,就表示他不能完全信賴它們。這讓他落入什麼狀況呢?
「我現在正醒著讀這本書」這個信念在你看來可能相當肯定。你醒著(我希望如此),而且你正在閱讀。你怎麼可能去懷疑這一點?但我們已經提過,你在夢中會認為自己是清醒的。你怎麼知道你現在沒在做夢?或許你認為你的經驗太有真實感、太細膩,不會是夢,但許多人都會做非常真實的夢,你確定你現在不是在做這種夢嗎?你怎麼知道?或許你已經捏了自己一把,看看你是不是在睡覺。如果你還沒這麼做,試試看。那證明了什麼?什麼也沒證明。你可能是夢到你在捏自己。所以你可能在做夢。我知道感覺上不像,而且這也非常不可能,但你到底是不是醒著,肯定還是有微小的懷疑空間。所以,應用笛卡兒的懷疑方法,你必須拒絕「我現在正醒著讀這本書」的想法,因為它不是完全確定的。
他論證的下一步導出了哲學中數一數二著名的句子,不過知道這句話的人比真正理解的人多上許多。只要他還有個思緒在,他,笛卡兒,就一定存在。如果他不存在,惡魔就不可能讓他相信他存在。那是因為不存在的東西不可能思考。「我思故我在」(拉丁文是cogito ergo sum)就是笛卡兒的結論。我在思考,所以我一定存在。你也試著想想看。只要你有什麼思緒或感覺,就不可能懷疑你的存在。你是什麼則是另一個問題——你可以懷疑你是否有身體,或者懷疑你看得見、摸得到的那個身體。不過你不能懷疑你以某種思考之物的形式存在,那樣的懷疑會自相矛盾。一旦你開始懷疑自己的存在,這個懷疑的舉動正好證明你是身為思考之物而存在。
透過無知達成公平-羅爾斯
或許你很有錢。或許你超級有錢。但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是,有些人還非常貧窮,短促的人生中大半時間都挨餓生病。這似乎不對也不公平,的確如此。如果世界上有真正的正義,就不會有任何一個小孩挨餓、富人卻錢多到不知怎麼花。每個生病的人都有管道得到良好的醫療;非洲的貧民處境不會比美國與英國的窮人糟糕這麼多;西方國家的富人不會比那些沒有過錯卻生來居於劣勢的人富有好幾千倍。正義就是公平對待人。我們周遭有些人的生活充滿了美好事物,另一些人雖然自己沒有過錯,生存方式卻沒多少選擇:無法選擇工作,甚至不能選擇居住的城鎮。有些人想到這些不平等的時候,只會說:「哎,好啦,人生就是不公平。」然後聳聳肩了事。他們通常就是特別幸運的那些人。但也有人會花時間思考怎麼組織一個更好的社會,或許還試著要改造社會,讓它變得更公平。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一個謙遜文靜的哈佛學者,他的一本著作改變了人類思索這類事情的方式。這本書是《正義論》(西元一九七一年出版),他苦思將近二十年的結晶。這實際上是一位教授寫給其他教授讀的書,書寫方式是相當枯燥的學術風格。然而跟大部分這類的書不同,《正義論》並沒有躺在圖書館裡積灰塵;不僅沒有,它更變成了暢銷書。從某些方面來說,這本書有如此多讀者很讓人訝異,但它的關鍵論點實在太有意思,所以很快就有人宣稱它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書籍之一,哲學家、律師、政治家以及許多人都在讀,羅爾斯自己做夢都沒想過會這樣。
羅爾斯曾在二次大戰時參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空投到廣島時,他人在太平洋上。他的戰時經驗影響他很深,他相信使用核武是錯誤的。就像許多曾經活過那時代的人,他想要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更好的社會。但他帶來改變的方式是透過思考與寫作,而不是加入政治運動與集會。他執筆寫作《正義論》的時候,越戰方酣,橫跨全美的大規模反戰示威正在進行,這些示威不完全是和平的。羅爾斯選擇以寫作討論抽象的一般正義問題,而不是困在當時的議題之中。他的研究核心是:我們必須想清楚我們要怎麼共同生活,還有國家影響我們生活的種種方式。要讓我們的存在堪可忍受,我們就必須合作。但要怎麼合作呢?
請想像你必須設計出一個更美好的嶄新社會。你可能會問的一個問題是:「誰得到什麼?」如果你住在一棟有室內游泳池與僕人的漂亮大宅裡,還有一輛私人噴射機隨時能迅速送你去一座熱帶小島,那麼你很可能會想出一個有些人非常富裕——或許是最努力工作的那些人——其他人則窮得多的世界。如果你現在過著赤貧的生活,那麼你可能會設計出一個不許任何人超級有錢的世界,每個人都得到一份更平等的可用資源:不准有私人噴射機,而不幸的人會有更好的機會。人性就像這樣:人在描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時,往往會想到自己的處境,無論他們自己有沒有察覺到這一點。這些成見與偏好會扭曲政治思維。
羅爾斯的神來之筆是想到一個思想實驗,他稱之為「原初境況」,淡化了我們全都有的一些自私偏見。他的主要概念非常簡單:設計一個更好的社會,而且你設計時不知道自己會處於什麼樣的社會地位。你不知道你會有錢還是貧窮、身體有障礙還是外表好看、是男還是女、醜不醜、聰不聰明、別有天賦或欠缺長才、是同性戀、雙性戀或異性戀。他認為在這個想像的「無知之幕」後面,你會選擇比較公平的原則,因為你不知道你最後可能會是什麼狀態、可能會是哪種人。透過這個在不知道自身地位狀況下做選擇的簡單設計,羅爾斯發展出了他的正義論。正義論奠基於他認為所有理性的人都會接受的兩個原則,也就是自由與平等。
羅爾斯已經啟發了現在寫作的新一代哲學家,包括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湯瑪斯・博格(Thomas Pogge)、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等人,他們全都相信哲學應該處理我們能夠如何共同生活、應該如何共同生活的深刻難題。不像上一代的某些哲學家,他們並不怕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不怕去刺激社會改變。他們相信哲學應該實際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而不只是改變我們如何討論生活的方式。
你聽到鬧鈴響了,把鬧鐘關掉,爬下床去著裝,吃了早餐,準備好面對今天。但接著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你醒了過來,發現那只是一場夢。你在夢中是醒的,過著生活,但現實中你還蜷縮在鴨絨被底下熟睡。如果你有過這種經驗,就會知道我的意思。這種夢通常叫做「假清醒」,顯得很逼真。法國哲學家笛卡兒做過一次這種夢,而這個夢讓他開始思考。他怎麼能夠確定他不是在做夢?
笛卡兒認為值得在人生中試一次,去弄清楚他能夠確知的是什麼(如果真有的話)。為了這麼做,他發展出一個方法,稱作「笛卡兒的懷疑方法」。這個方法相當直接:如果一件事有一絲可能是假的,就別當成真的。試想有一大袋蘋果,你知道袋子裡有些蘋果發霉了,不過你不確定是哪幾顆。你想要擁有一整袋好蘋果、沒有任何發霉蘋果。要怎麼樣達到這個結果呢?一種辦法是把蘋果全部倒在地板上,然後一次檢查一顆,只把你完全確定沒問題的蘋果擺回袋子裡去。在過程中你或許丟掉幾顆好蘋果,因為乍看之下它們可能裡頭發霉,不過最後絕對只有好蘋果進得了你的袋子。笛卡兒的懷疑方法大致上就是這樣。你拿出一個信念加以檢驗,像是「我現在正醒著讀這本書」,只有在你確定這個信念不可能出錯或造成誤導的狀況下才接受。只要有一丁點懷疑的空間,就不接受。笛卡兒逐一檢查過他相信的幾件事,質疑他是否完全確定這些事就如同表面看來那樣。世界真的就是他眼中的那個樣子嗎?他確定他沒在做夢嗎?
笛卡兒追求確定性的出發點是思考來自感官的證據:視覺、觸覺、嗅覺、味覺跟聽覺。我們可以信任我們的感官嗎?他的結論是其實不能。感官有時候會欺騙我們。我們會犯錯。想想你看到的事物:你的視覺在每件事物上都很可靠嗎?你應該總是相信你的眼睛嗎?
如果你從側面看一根放進水中的筆直棍子,它看起來是彎的。一個方形高塔從遠處看可能是圓的。我們全都偶爾會看錯。而且笛卡兒指出,信任一個以前欺騙過你的東西是不明智的,所以他拒絕把感官當成確定性的可能來源。他永遠不能確定他的感官沒騙他;大部分時候可能沒有,但感官會騙人的那點微薄可能性,就表示他不能完全信賴它們。這讓他落入什麼狀況呢?
「我現在正醒著讀這本書」這個信念在你看來可能相當肯定。你醒著(我希望如此),而且你正在閱讀。你怎麼可能去懷疑這一點?但我們已經提過,你在夢中會認為自己是清醒的。你怎麼知道你現在沒在做夢?或許你認為你的經驗太有真實感、太細膩,不會是夢,但許多人都會做非常真實的夢,你確定你現在不是在做這種夢嗎?你怎麼知道?或許你已經捏了自己一把,看看你是不是在睡覺。如果你還沒這麼做,試試看。那證明了什麼?什麼也沒證明。你可能是夢到你在捏自己。所以你可能在做夢。我知道感覺上不像,而且這也非常不可能,但你到底是不是醒著,肯定還是有微小的懷疑空間。所以,應用笛卡兒的懷疑方法,你必須拒絕「我現在正醒著讀這本書」的想法,因為它不是完全確定的。
他論證的下一步導出了哲學中數一數二著名的句子,不過知道這句話的人比真正理解的人多上許多。只要他還有個思緒在,他,笛卡兒,就一定存在。如果他不存在,惡魔就不可能讓他相信他存在。那是因為不存在的東西不可能思考。「我思故我在」(拉丁文是cogito ergo sum)就是笛卡兒的結論。我在思考,所以我一定存在。你也試著想想看。只要你有什麼思緒或感覺,就不可能懷疑你的存在。你是什麼則是另一個問題——你可以懷疑你是否有身體,或者懷疑你看得見、摸得到的那個身體。不過你不能懷疑你以某種思考之物的形式存在,那樣的懷疑會自相矛盾。一旦你開始懷疑自己的存在,這個懷疑的舉動正好證明你是身為思考之物而存在。
透過無知達成公平-羅爾斯
或許你很有錢。或許你超級有錢。但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是,有些人還非常貧窮,短促的人生中大半時間都挨餓生病。這似乎不對也不公平,的確如此。如果世界上有真正的正義,就不會有任何一個小孩挨餓、富人卻錢多到不知怎麼花。每個生病的人都有管道得到良好的醫療;非洲的貧民處境不會比美國與英國的窮人糟糕這麼多;西方國家的富人不會比那些沒有過錯卻生來居於劣勢的人富有好幾千倍。正義就是公平對待人。我們周遭有些人的生活充滿了美好事物,另一些人雖然自己沒有過錯,生存方式卻沒多少選擇:無法選擇工作,甚至不能選擇居住的城鎮。有些人想到這些不平等的時候,只會說:「哎,好啦,人生就是不公平。」然後聳聳肩了事。他們通常就是特別幸運的那些人。但也有人會花時間思考怎麼組織一個更好的社會,或許還試著要改造社會,讓它變得更公平。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一個謙遜文靜的哈佛學者,他的一本著作改變了人類思索這類事情的方式。這本書是《正義論》(西元一九七一年出版),他苦思將近二十年的結晶。這實際上是一位教授寫給其他教授讀的書,書寫方式是相當枯燥的學術風格。然而跟大部分這類的書不同,《正義論》並沒有躺在圖書館裡積灰塵;不僅沒有,它更變成了暢銷書。從某些方面來說,這本書有如此多讀者很讓人訝異,但它的關鍵論點實在太有意思,所以很快就有人宣稱它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書籍之一,哲學家、律師、政治家以及許多人都在讀,羅爾斯自己做夢都沒想過會這樣。
羅爾斯曾在二次大戰時參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空投到廣島時,他人在太平洋上。他的戰時經驗影響他很深,他相信使用核武是錯誤的。就像許多曾經活過那時代的人,他想要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更好的社會。但他帶來改變的方式是透過思考與寫作,而不是加入政治運動與集會。他執筆寫作《正義論》的時候,越戰方酣,橫跨全美的大規模反戰示威正在進行,這些示威不完全是和平的。羅爾斯選擇以寫作討論抽象的一般正義問題,而不是困在當時的議題之中。他的研究核心是:我們必須想清楚我們要怎麼共同生活,還有國家影響我們生活的種種方式。要讓我們的存在堪可忍受,我們就必須合作。但要怎麼合作呢?
請想像你必須設計出一個更美好的嶄新社會。你可能會問的一個問題是:「誰得到什麼?」如果你住在一棟有室內游泳池與僕人的漂亮大宅裡,還有一輛私人噴射機隨時能迅速送你去一座熱帶小島,那麼你很可能會想出一個有些人非常富裕——或許是最努力工作的那些人——其他人則窮得多的世界。如果你現在過著赤貧的生活,那麼你可能會設計出一個不許任何人超級有錢的世界,每個人都得到一份更平等的可用資源:不准有私人噴射機,而不幸的人會有更好的機會。人性就像這樣:人在描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時,往往會想到自己的處境,無論他們自己有沒有察覺到這一點。這些成見與偏好會扭曲政治思維。
羅爾斯的神來之筆是想到一個思想實驗,他稱之為「原初境況」,淡化了我們全都有的一些自私偏見。他的主要概念非常簡單:設計一個更好的社會,而且你設計時不知道自己會處於什麼樣的社會地位。你不知道你會有錢還是貧窮、身體有障礙還是外表好看、是男還是女、醜不醜、聰不聰明、別有天賦或欠缺長才、是同性戀、雙性戀或異性戀。他認為在這個想像的「無知之幕」後面,你會選擇比較公平的原則,因為你不知道你最後可能會是什麼狀態、可能會是哪種人。透過這個在不知道自身地位狀況下做選擇的簡單設計,羅爾斯發展出了他的正義論。正義論奠基於他認為所有理性的人都會接受的兩個原則,也就是自由與平等。
羅爾斯已經啟發了現在寫作的新一代哲學家,包括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湯瑪斯・博格(Thomas Pogge)、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等人,他們全都相信哲學應該處理我們能夠如何共同生活、應該如何共同生活的深刻難題。不像上一代的某些哲學家,他們並不怕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不怕去刺激社會改變。他們相信哲學應該實際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而不只是改變我們如何討論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