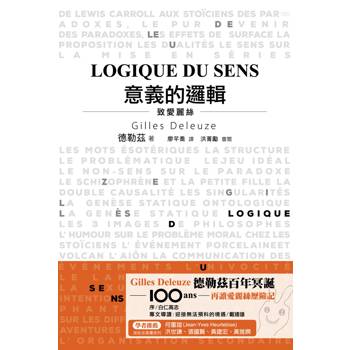第十八系列:諸哲學家的三種形象(18e série, des 3 images de philosophes)
哲學家的形象,無論是通俗的還是科學的,似乎已被柏拉圖主義所固定:一個走出洞穴的上升存有,因為他的上升而更加提升和淨化自己。在這本《上升的心理現象》[ 譯注:法國物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艾蒂安.克萊因(Étienne Klein)的著作。](Psychisme ascensionnel)書中,道德與哲學、苦行理想與思想理念連結成非常密切的關係。雲裡的哲學家的通俗形象取決於此,科學形象也取決於此,哲學家的天空根據該科學形象,是一個可理解的天空,這樣的天空較少替我們抽出它包含在內的大地法則。不過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切都發生在高度(即使是道德法則的天空中個人的高度)。當人們問道「思想中的指向是什麼?」,看來思想本身預先假設了方針和方向並以此依據而發展,在具有一段歷史之前思想擁有一種地理學,在構建系統之前它勾勒出諸多維度。高度是柏拉圖專有的太陽東升的方向。哲學家的運作因而被確定為提升、換位,也就是說,轉向他前進的高處原則之運動,並借助於這樣的轉動決定自己、充實自己和自我認識。人們將不會將哲學和疾病進行比較,可是卻有諸多哲學特有的疾病。唯心論是柏拉圖哲學的先天性疾病,隨著其一連串的上升和下降,哲學本身也是狂躁—抑鬱的形式。狂躁(mania)啟發並引導柏拉圖。辯證法是諸理念的飛逝,即思緒奔馳(l’Ideenflucht);正如柏拉圖談及理念,「它飛逝或消失⋯」。而且,甚至蘇格拉底之死,也有一種抑鬱性自殺的某種東西。
尼采對於這種自高度取其定位表示懷疑,並自問,若非呈現哲學的實現,這定位是否就不是以蘇格拉底開始的衰退和迷途。尼采以這種方式對於思想定位的全部問題重新提出質疑:思想行為在思想中醞釀而成,和思想者在生命中孕育出來,難道這不是根據其他維度嗎?尼采具備一個他發明的方法:不應該滿足於傳記或參考書目,必須達到神秘點,在此生命軼事和思想格言皆是同一件事。這就像意義一樣,一方面歸因於生命狀態,另一方面則在思想的命題中堅持著。這裡有維度、時間和地點,一些從未緩和的冰川區域或熱帶,整個異國地理有一種思維模式的特徵,也有一種生活型式的特徵。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ène Laërce),在他絕美的篇章中大概曾有這種方法的預想:找到攸關生命的格言,同樣是思想軼事—哲學家的姿態。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與埃特納火山(l’Etna),就是一件哲學軼事。等同蘇格拉底之死,不過這恰恰在另一維度上運作。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不從洞穴裡走出來,他反而認為,人們還不夠深入洞穴中,還不到被吞沒的地步。他拒絕的是忒修斯手中的那條線:「您的向上之路、您那通往外面、往幸福和道德的線與我們何干⋯您想藉助這條線的輔助來拯救我們嗎?而我們,懇求您:用這條線自縊!」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已在洞穴中放置思想,在深處安置生命。他們已探測水和火。他們用錘子敲打來研究哲學,如恩培多克勒打破雕像一樣,以地質學家、洞穴學家的鐵鎚。在水與火的氾濫中,火山從恩培多克勒身上只噴吐出一樣東西,那就是他的銅製涼鞋。柏拉圖靈魂的翅膀與恩培多克勒的涼鞋相對立,後者證明他屬於大地、在大地之下,且是原住民。柏拉圖的羽翼拍擊,與前蘇格拉底的錘子敲擊相對立。柏拉圖的換位,與前蘇格拉底的顛覆相對立。環環相扣的深度似乎對於尼采來說是哲學的真正方向,是在未來哲學中以一種同作為思想的生命,或者以一種同作為身體語言的所有力量,再次採用前蘇格拉底的發現。「任何洞穴背後都有另一個更深處,一定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地方,在表面下有一個更廣闊、最陌生、最豐富的世界,在任何深底之下,在任何地基之外,都有一處深淵」[ 奇怪的是,力圖描繪尼采的想像力特點的巴舍拉(Bachelard),卻將其呈現為一種「上升的心理現象」(L'Air et les songes, ch. V)。巴什拉不僅將尼采的大地和表面作用最小化,他也將尼采的「垂直性」(verticalité)解釋為處於任何高度和登高之前。儘管如此,它是相當地深和下墜。猛禽不會飛升,除非發生意外:牠懸垂且「猛襲」。甚至應當說,尼采使用深度來譴責高度的理念和上升的理想;高度只是一種故弄玄虛,一種表面效應,其騙不了深度之眼,也無法擺脫它的凝視。參考自,關於米歇爾.傅柯的評論,〈尼采,佛洛伊德,馬克思〉,載於《尼采》(in Nietzsche, Cahiers de Royaumont, éd. de Minuit, 1967, pp. 186-187)。]。首先,思覺失調症:前蘇格拉底主義是哲學特有的思覺失調症,在身體和思想中被挖掘的絕對深度,這意味著荷爾德林(Hölderlin)在尼采之前就知道要找到恩培多克勒。在恩培多克勒著名的交替中,在恨和愛的互補中,我們一方面遇到了恨的身體,漏勺和被分割的身體,「無頸之首,無肩之臂,無顏額之眼」,另一方面遇到了享天福且無器官的聖身,「整體式形式」,無四肢、無聲也無性徵。同樣地,戴奧尼索斯(Dionysos)以他的兩張臉面向我們,伸出他開放且撕裂的身體、他漠然且無器官的頭,被割下四肢的戴奧尼索斯,也是不可參透的戴奧尼索斯。
與深度的這次重逢,尼采只能透過征服諸表面才再次相遇。但他卻不停留在表面上;表面在他看來,必須從深度之眼所更新的觀點來判斷。尼采對柏拉圖之後發生的事不感興趣,認為這必然接下來是一段長時間的墮落期。然而,按照方法本身,我們卻感覺到,哲學家們的第三種形象正在出現。這是尼采對他們尤其適用的用語:這些希臘人由於不斷地接近淺表是多麼地有深度呀![ 《尼采反華格納》(Nietzsche contre Wagner, épilogue, § 2)。] 這些第三種希臘人,甚至完全不再是希臘人。救贖,他們不再從地球或本土深處,更不是從天堂和理念中等待它,而是從事件、從東方,在旁等待它 —在那,正如卡羅所說,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會出現。與麥加拉學派、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開始出現一種新哲學家和一種新類型的軼事。讓我們再讀第歐根尼.拉爾修最絕妙的篇章,其關於錫諾普的第歐根尼(Diogène le Cynique)、關於斯多噶學派的克律西波斯(Chrysippe le Stoïcien )。我們看到了一種挑釁的好奇求知系統的發展。一方面,哲學家吃得極其狼吞虎嚥,他吃得過飽;他在公共場合自慰,遺憾的是我們無法飢餓而思淫慾;他不譴責與母親、姊妹或女兒的亂倫;他容忍同類相食和嗜食人肉習性──當然,他也保持著最崇高程度的樸實和端正。另一方面,當有人向他提問時,他卻保持沉默,或者給您一記悶棍,或者是當您問他一個抽象又很困難的問題時,他以指出一樣食物,或甚至給您一盒食物隨後當著您的面打破食物盒來回應您,總是用棍子來擊破它——而且儘管如此,他還掌握新創的演說、由新哲學悖論、價值和涵義賦予活力的嶄新邏各斯。我們明確地感覺到這些軼事不再是柏拉圖式的,也非前蘇格拉底式的。
這是整體思想以及意味著思考意義的重新定位:既不再有深度亦不再有高度。反柏拉圖的犬儒式和斯多噶式的嘲諷不計其數:始終關乎撤銷理念,和表明無形體不在高度上,而在表面上,表明它不是最高的因,而是卓越的淺表效應,其非本質,而是事件。另一面,人們將表明深度是一種消化幻象,它補全了理想的光幻視。其實,這種狼吞虎嚥、這種對亂倫的辯護、這種對同類相食的辯解意味著什麼?這道最後的主題是克律西波斯和錫諾普的第歐根尼所共有的,拉爾修對於克律西波斯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可是他為錫諾普的第歐根尼提出了一個特別令人信服的解釋:「他不認為食人肉像人們對待外國人那樣如此可憎,他說,一切都合理地存於一切之中且無處不在。麵包裡有肉,草本植物裡有麵包;這些身體和許多其他身體透過隱密的管道進入所有身體,然後一起蒸發,如他在《提耶斯忒斯》(Thyeste)的戲劇中所表示的,萬一有人將悲劇歸咎於他,卻是屬於他自己的⋯。」這個論題,一樣適用於亂倫,確立了在身體深處,一切皆為混合的;人們寧可去稱一種混合是劣質的,而不是去指另一種混合,然而卻沒有任何可根據的規則。與柏拉圖所認為的相反,對於混合來說沒有一種高度測量、一些可以去定義好壞混合的理念組合。與前蘇格拉底學派相反的是,更沒有任何能夠在自然(Phusis)深度裡,去固定一項混合的順序和進展之內在度量;任何混合等於與相互滲透的身體和共存的諸部分之等價者。混合的世界怎麼不是自一切都被允許的黑暗深處的世界呢?
克律西波斯區分出兩種混合,不完美混合使身體變質,和完美混合使身體完好無損和使身體共存於它們的所有部分裡。諸原因之間物質因的統一大概定義了一種完美且流體的混合,於此,一切正好在宇宙當下。但是,身體投進其有限現在時的特性裡,不直接隨著其因果順序而相遇,因果關係僅適用於整體,考慮到所有同時的組合。這就是為什麼任何混合可被說是好的或壞的:在全(le tout)的順序中是好的,可是在局部發生的相遇順序中是不完美的、劣的甚至是糟糕的。激情本身就屬滲透到其他身體的身體,和特殊意志是一種根本的惡,在此領域中怎麼去譴責亂倫和嗜食人肉者呢?讓我們以塞內卡(Sénèque)的非凡悲劇為例。我們自問斯多噶思想,與這種首次將致力於惡的存有搬上舞台,如此精確地預示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之悲劇思想,他們的統一性是什麼。不是幾個斯多噶化的諧合就能做出統一性。真正的斯多噶學派,在此是對身體—激情的發現,以及激情所組織或經受的地獄般混合之發現,如熱情的毒素,戀童筵席。提耶斯忒斯的悲劇性宴席不僅僅是第歐根尼已失傳的主題,也是幸運地被保存下來的塞內卡的主題。有毒的膜從灼傷皮膚開始,燒光表面;然後它們到達最深處,沿著一條從被蝕穿的身體到成塊的身體(membra discerpta)的路徑。身體深處到處都冒出有毒的混合物,轉化成可憎的招魂術、亂倫和食物。讓我們尋找解藥或反證:塞內卡的悲劇英雄和斯多噶整體思想中的英雄,是海克力斯(Hercule)。然而,海克力斯總是身處於與三界有關之地:地獄深淵、上天和地球表面。在深處,他只發現了可怕的混合物;於空中,他只感受到虛空,甚至還有比地獄魔多一倍的天獸。而他卻是地球的調解者和土地丈量者,他甚至在水面上行走。他用盡所有方法再次上下表面;他把地獄犬和天狗、地獄的九頭蛇妖和天空的巨蛇帶回表面。不再是底部的戴奧尼索斯,也不再是上面的阿波羅,而是表面的海克力斯,在他與深度和高度的雙重鬥爭中:整個被再—定位的思想、嶄新的地理。
斯多噶主義有時被描述為在柏拉圖之外,操作一種前蘇格拉底主義的回返,例如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之回返。這就是關乎對前蘇格拉底世界的全面重新評價:通過深度混合的物理學來解釋它,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使其部分地陷入所有局部的無秩序中,這些局部無秩序只能與巨大混合取得協調,也就是說,與諸原因之間它們的統一性一致。這是一個充滿恐怖和殘酷、亂倫和嗜食人肉的世界。大概還有另一部分:從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中,可以上升至表面並將獲得一個全新的地位者—即事件在其本質上與身體—原因的差異,永恆(l’Aiôn)在其本質上與消耗的克諾時間(le Chronos)之差異。同時,柏拉圖主義也經歷過類似的全面再—定位:聲稱還更勝於前蘇格拉底的世界,還把它往後推得更遠,在高度的重壓下將它壓碎,卻感覺自己被剝奪了自己的高度,以及理念再度掉落在如無形體的唯一效應一樣的表面。這是斯多噶學派的偉大發現,反對前蘇格拉底學派也同時反對柏拉圖:(P. 158)表面的自主性,獨立於高度和深度之外,反對高度和深度;無形體事件的發現,無論是意義或效應,皆無法還原為具深度的身體和崇高的理念。所發生的一切,和所說的一切,皆在表面上發生和被說出來。這有不少是必須探究,有不少是未知的,還有可能比非—意義的深度和高度還要多。因為主要的邊界已位移。它不再於共相和個別之間向上移動。它不再於實體和偶性之間深入。也許這在於安提斯泰尼(Antisthène)的思想,應該為這條另闢蹊徑給予榮耀:在事物和命題本身之間。介於由命題所指稱的,如存在的事物,和不存於命題之外的被表達者之間(實體只是事物的次要規定性,而共相只是被表達者的次要規定性)。
表面、窗簾、地毯、外套,這是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的安身之處,和他們周圍的東西。表面的雙重意義,背面和正面的連續性,接替了高度和深度。窗簾後面什麼也沒有,除了說不出名稱的混合物。地毯上面什麼也沒有,除了空蕩蕩的天空。意義在表面上出現並發揮作用,至少假如有人知道如何適當地敲打表面,為了讓它可排列出粉末的字母,或者像是可以讓手指在玻璃窗書寫的蒸汽一樣。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中用棍棒敲擊的哲學接替了用錘子敲打的哲學。哲學家不再是洞穴裡的存有,也不再是柏拉圖的靈魂或禽鳥,而是表面的扁平動物,壁蝨、蝨子。哲學的象徵不再是柏拉圖的翅膀,也不再是恩培多克勒的銅製涼鞋,而是安提斯泰尼和第歐根尼的雙層披風。手杖和披風,就像海克力斯拿著狼牙棒和獅皮披肩一樣。如何命名哲學的新操作,作為它既反對柏拉圖的換位,也反對前蘇格拉底的顛覆?如果反常確實意味著一種表面的奇特藝術的話,那麼也許用「反常」這個詞,至少符合哲學家這種新型態的挑釁系統。
第十九系列:幽默(19e série, de l’humour)
首先,語言似乎無法在自我表達者的狀態中,也無法在指定的感性事物中找到充分的基礎,而只能在賦予語言一種真實和錯誤的可能性之理念中找到。儘管如此,我們很難看出命題透過什麼樣的奇蹟,以一種比說話的身體或我們談論的身體更可靠的方法參與理念,除非理念本身就是「名稱自身」。而身體,在另一極,能否更好地奠定語言?當聲音在身體上被閉合且成為混合體的行動和激情時,它們只會帶來淒厲的非—意義。我們相繼譴責柏拉圖語言和前蘇格拉底語言、唯心主義語言和物理語言、躁狂語言和思覺失調語言的不可能性。我們強加無結局的二擇一:要麼什麼都沒說,要麼吸收、吃進我們所說的。正如克律西波斯(Chrysippe)所說,「如果你說貨車這個詞,一輛貨車就會經由你的嘴裡駛出」,而這並不是最佳或最合適的說法,如果這是貨車的理念的話。
唯心主義語言是由實體化的涵義所組成的。但是,每一次我們被問到關於這樣的詞義時 —「何謂美、正義等等,何謂人?」—我們都以指定一個身體、以展示一個可模仿的或甚至可食用的客體來回應,有必要透過用棍棒一擊,棍棒被視為任何可能指稱的工具。犬儒派第歐根尼(Diogène le cynique)拋出一隻被㷟去羽毛的公雞來回應,柏拉圖的說法「無毛的兩足動物」作為人類的詞義。而對於詢問「何謂哲學?」的提問者,第歐根尼用細繩末端上的鯡魚回應之:魚,是最具口腔的動物,其提出啞、可食用性、顎化元素中的輔音問題,即語言的問題。柏拉圖嘲笑那些僅限於舉例、展示、指定而不觸及本質的人:我不問你(他說)誰是公正的,而是問正義是什麼,等等。然而,輕易地又順著柏拉圖聲稱引導我們攀登的道路而爬。每次我們被問到一個涵義時,我們都會以純粹的一項指定、一個說明來回應。為了說服觀眾這非關一個簡單的「例子」,而是柏拉圖的問題提得不好,人們將模仿自己指稱的東西,人們將以動作和表情模擬它,或者人們將吃掉它,將打破自己所展現的東西。重要的是動作要迅速:立即找到某事物來指定、食用或打破,取代了促使您去尋找的涵義(理念)。因為沒有,也不應該在我們呈現的和我們被問到的之間有任何相似之處,所以越快越好:只有一種不穩定的關係,其拒絕了本質—例子柏拉圖錯誤的二元性。對於這項用指稱、說明、食用性和純粹破壞來取代涵義的練習來說,需要一種怪誕的靈感,必須會「下降」—幽默,去反對蘇格拉底的反諷或上升的技巧。
可是這樣的下降會使我們落入何處呢?直到身體深處和其混合的無—底;正是因為任何指稱都以消耗、研碎和破壞中延展,如果不停止這種運動的話,猶如棍棒打碎了它所展示的一切,我們清楚地看到,語言無法以涵義為基礎更甚於以指稱為基礎。涵義使我們陷入取而代之且廢黜涵義的純粹指稱之中,這是作為無涵義的荒謬。但是,這些指稱反過來使我們陷入破壞性和消化性的深處,這是作為意義下(Sous-sens)或感官下(Untersinn)的深度之非—意義。那麼有何種脫身辦法呢?語言甚至從運動中高處落下,然後沉沒,我們必須被帶回表面,在那裡不再有任何必須指定、必須賦予涵義的東西,反而產生了純粹的意義:其與第三元素的主要關係中,這一次產出表面的非—意義。而且,再者,重要的是要做得快,這就是速度。
智者從表面發現了什麼?純粹事件於其永恆的真理中被沿用,也就是說,在實體中,將事件獨立於它們以時空在事物狀態的落實之外,來作為推論基礎。或者,回返至相同者,純粹的特異性,特異性於其隨機元素裡的輻射,獨立於體現或落實特異性的個體和個人之外。這趟幽默的歷險,這種有利於表面的高度和深度的雙重罷黜,這首先是斯多噶學派智者的歷險。但是,後來和在另一個背景下,也是禪宗(Zen)的歷險 —反對婆羅門教的深度和佛教的高度。著名的試題、問答、公案(koan),顯露涵義的荒謬,展示指稱的非—意義。棍棒是萬能工具,問題大師,啞劇和消耗就是答案。回到表面上,智者發現了事件—客體,所有這些都在構成其實體的空白中進行交流,它們在永恆中具體化和在從未填滿它的狀況下發展[ 斯多噶學派已經設計出一套非常完美的空白理論,同時作為超—存有(extra-être)和堅決要求(insistance)。如果無形體事件是存有或身體的邏輯屬性,那麼空白就像是這些屬性的實體,它本質上與有形的實體不同,以至於我們甚至不能說世界「在」空白之中。參考自,布列赫(É. Bréhier),《古斯多噶主義的無形體理論》(La Théorie des incorporels dans l’ancien stoïcisme, ch. III)。]。事件,是形式與空白的同一性。事件不是作為被指稱的客體,而是作為被表達或可表達的客體,從未在場,但總是已經過去並且尚待到來,如在馬拉美作品中,因其自身的缺席或廢除而有價值,因為這種廢除(拒絕:abdicatio)恰恰是作為純粹事件(奉獻:dedicatio)在空白中的位置。「禪宗說:如果你有一根棍棒,我再給你一根,如果你沒有,我從你身上拿走它」(或者,正如克律西波斯所說:「如果您沒有丟失一物,您就擁有它了;然而,您沒有失去任何犄角,因此您就有角了)。否定詞不再表達任何負面否定,而只是釋放純粹的可表達性與其兩個不對稱的半邊,其一總是在另一缺席,既然它通過其自身的缺少而超出,冒著通過其過剩而缺乏之風險,對於物 = x 而言,詞 = x 。我們確實在禪的藝術中看到這一點,不僅是書畫藝術,懸空的手腕操縱畫筆使得形式與空白佈局平衡,且將純粹事件的特異性分佈在偶然的輕彈和「細線」的系列中,也是園藝、插花和茶藝,以及射箭術、劍術,「鐵充分的發展」從絕妙的虛空中湧現。透過廢除涵義和失去指稱,空白是意義或事件的所在地,意義和事件由其自身的非—意義組成,在那種情況下僅有空白處發生。空白本身就是悖論元素,表面的非—意義,一直移位的隨機點,事件而從中以意義突然顯現。「沒有生死輪迴,而應該逃脫這迴圈,也沒有可觸及的至高無上的知識」:空白的天空拒絕精神的最高思想,也拒絕本性的深度循環。關於將現時性「立即」被保留下來的這個地方被決定為無法觸及的地方,並不少於關乎觸及現時性的問題:產生空白的表面,以及與之相關的任何事件,邊界作為一把劍的利刃或弓的細線。因此,無描繪而畫,非思想,無擊之射擊術,無言語而言:根本不是在高度或深度上的不可言喻,而是這條邊界、使語言有可能的這個表面,並且成為可能性,只激發出一種即刻靜默的交流,因為語言僅在復活所有被廢止的間接涵義和指稱的情況下才能被使用。
根據使語言有可能者,我們要問是誰在說話。對於相同的問題,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答案。我們將決定個體者作為說話者的回答稱為「古典」答案。他所說的恰恰被確定為一種說話特色,而中間項,即語言本身,被確定為約定俗成的一般性。那麼這是在一種變位的三重操作中,關乎得出的個體的普遍形式(實在性),同時我們從所論及的之中提取一個純粹的理念(必然性),並且我們以一個被假設為原始的、自然的或完全有理的理想原型來比對語言(可能性)。正是這種觀念使蘇格拉底的反諷如昇華般活躍,並派給它任務,將個體從其現時的存在中分離出來,同時也朝向理念超越感性的特點和建立語言符合原型的規則。這就是有記憶和說話的主體性之「辯證」總體。然而,要使這操作完整,個體不僅必須是起點和跳板,而且也必須重返終點,而理念的一般概念也必須作為兩者之間的交換手段。反諷的結束、這種迴路在柏拉圖那裡仍然缺乏,或只在喜劇和嘲笑的種類下出現,如蘇格拉底—阿爾西比亞德(Socrate-Alcibiade)的往來。當古典反諷有時不只將實在性的全部也將可能性的總體確定為先天的最高個體化時,它反而獲得了這種完美狀態。我們所見,康德希望將再現的古典世界服膺於理性批判,以準確地描述它開始:「任何可能性總體的理念被純化,直到形成一個先驗地完全確定的概念,因此從而成為單數存有的概念」[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論先驗理想〉(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 De l’idéal transcendantal »)。]。古典反諷以確保存有與個體於再現世界中同外延性的堅決要求而起作用。因此,不僅是理念的一般概念,也是就最初的可能性而言,有理的純粹語言之原型,都成為了具高度個體化的上帝和祂所創造的衍生個體之間本性的交流手段;正是這位上帝使個體有可能上升至普遍形式。
不過,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之後,出現了第三種反諷的修辭格:浪漫的反諷將說話者認定為個人,而不再作為個體。這反諷是基於個人的有限綜合的統一體,而不再建立於個體的分析同一性。反諷經由我(le Je)和再現自身的同外延性被定義。這裡不僅僅有詞語變化(為了將其確定為整個重點,有必要評估如蒙田的《隨筆集》(Essais),這些文集已經納入古典世界之中,作為探索個體化最多樣的修辭格,和盧梭的《懺悔錄》(Confessions)之間的差異,後者宣告浪漫主義,作為其為一個人或一個我(Je)的首要表現)。不僅是普遍理念和感性的特點,也是個體化的兩極,以及與個體相符的世界,現下都成了個人自己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繼續被分為起源和衍生,而起源卻只代表個人對於所有可能世界的恆定謂詞(範疇),而衍生,代表個體的多變,個人在這些不同世界中被體現。產生一種深層的轉變,是理念的一般概念、主體性的形式、作為語言的可能性作用的原型之轉變。個人的位置作為無窮的級別,卻只有一位成員(我),這位置就是浪漫的反諷。在笛卡兒的我思(le cogito)中,尤其在萊布尼茲的個人中,大概已有先驅元素;而這些元素仍然服從於個體化的要求,然而諸元素在康德之後的浪漫主義中,透過顛覆從屬關係自我釋放並且以其自身被表達出來。「這種具無窮詩意的著名自由以積極的方式被表達為,個體在可能性的形式下已貫穿一整個不同確定性的系列,和在它陷入虛無之前給予確定性如詩一般的存在。致力於反諷的靈魂與畢達哥拉斯(Pythagore)學說中貫穿世界的靈魂相似:靈魂總是在旅途中,卻不再需要一段如此長久的持續時間⋯。如孩子們走向有利可圖的人一樣,諷刺詩人屈指一算:白馬王子或行乞者等。所有的這些化身在他眼中除了純粹可能性的價值之外沒有別的了,他可以和孩子一樣,在遊戲中快速破關。相反地,對於諷刺詩人來說則需要時間,他按照自己的幻想所確信的詩意角色精心裝扮自己⋯對諷刺詩人來說,如果給定的實在性因此失去其價值,那並不是由於實在性是一種過時的現實,而應該讓位給另一個更真實的現實,而是因為諷刺詩人體現了基本的我(le Je),對此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現實」[ 齊克果,〈反諷的概念〉(《齊克果,其生活、其作品》(Pierre Ménard, Kierkegaard, sa vie, son œuvre, pp. 57-59))。]。
所有反諷的修辭格的共同點在於,將特異性包圍在個體或個人的範圍內。所以反諷只是表面上飄移。然而,尤其是為什麼所有的這些修辭格都受到一個從內部將它們成形的內在敵人之威脅:無區分之底,我們先前談到的無—底,它再現了悲劇性思想,反諷以悲劇文體維持最為矛盾的情緒關係。這是蘇格拉底下的戴奧尼索斯,這也是惡魔,他將鏡子遞向上帝和祂的創造物,普遍的個體性於鏡中解體,還是摧毀個人的混沌。個體持有古典演說,個人則持有浪漫演說。不過,在這兩種演說之下,和以各種方式推翻它們的,正是現下以轟轟聲說話的無顏面之底。我們已見,這種底層語言、與身體深度混在一起的語言,具有雙重力量,即分散的語音音素之力量、難以發音的重音值的力量。這正是前者從內部去威脅並且推翻古典言說,而後者推翻的則是浪漫言說。因此,我們必須在每一情況下,針對每一類型的言說,區分出三種語言。首先,一種實在的語言,對應於說話者(個體,或者個人⋯)完全慣常的指定。然後是一種理想語言,根據語言持有者的形式來再現言說的原型(例如,對於蘇格拉底主體性而言,《克拉底魯篇》(Cratyle)的神聖原型、對於古典個體性而言,萊布尼茲的有理原型、對於浪漫的個人而言,進化論原型)。最後是難以理解的語言,在每一情況下,透過深底,呈現出對理想語言的顛覆和對持有實在語言者的拆解。此外,理想模式與其難懂的顛倒之間,和反諷與悲劇深底之間,每一次都存在著內在關係,以至於我們根本不知道哪一邊才是最大化的反諷。這就是為什麼替所有難以理解的語言尋求獨一的公式、獨一的概念皆是徒勞:如為了關閉古典世界的庫爾.德.哥柏林(Court de Gébelin)的語音、文字和音節的重要綜合,以及結束浪漫主義的讓—皮耶.布里塞(Jean-Pierre Brisset)的可演化重音的重要綜合(我們同樣見到了,不與組合詞一致)。
誰在說話?我們有時以個體、有時由個人來回應,有時以溶解兩者的深底來回答這個問題。「抒情詩人的自我從存有的深淵深處提高嗓門,他的主體性是純粹的想像」[ 尼采,《悲劇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tragédie, § 5)。]。卻仍採納最後一個答案:它既否認個體和個人形式,也否認未區分的初始深底,以及同時拒絕它們的矛盾和它們的互補性。非也,特異性並沒有被囚禁在個體和個人之中;當我們打亂個體和個人時,我們更不會陷入未區分的深底、無底之深度。非人稱和前—個體的,就是自由和遊牧的特異性。比任何深底更深層的,就是表面、是皮膚。在此形成了難以理解的語言的一種新類型,對於其自身是它自己的原型和實在性。當瘋狂—生成變異(le devenir-fou)上升至表面時,在永恆的直線上、永久性上改變其形貌;同樣地,分解的自我、裂開的我、丟失的身份,當它們不再下沉時,反而會釋放出表面的特異性。非—意義和意義打破了它們動態對立的關係,而進入與靜態生成同在,如表面的非—意義和在表面上掠過的意義。悲劇和反諷讓位給一項新價值,即幽默。因為如果反諷是存有和個體,或我和再現同外延性,而幽默則是意義與非—意義的同外延性;幽默是表面和襯裡、遊牧的特異性和一直位移的隨機點之技巧,是靜態生成的技巧、純粹事件的訣竅或「單數的第四人稱」(la quatr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任何涵義、指稱和表現被懸置,任何深度和高度被廢除。
哲學家的形象,無論是通俗的還是科學的,似乎已被柏拉圖主義所固定:一個走出洞穴的上升存有,因為他的上升而更加提升和淨化自己。在這本《上升的心理現象》[ 譯注:法國物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艾蒂安.克萊因(Étienne Klein)的著作。](Psychisme ascensionnel)書中,道德與哲學、苦行理想與思想理念連結成非常密切的關係。雲裡的哲學家的通俗形象取決於此,科學形象也取決於此,哲學家的天空根據該科學形象,是一個可理解的天空,這樣的天空較少替我們抽出它包含在內的大地法則。不過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切都發生在高度(即使是道德法則的天空中個人的高度)。當人們問道「思想中的指向是什麼?」,看來思想本身預先假設了方針和方向並以此依據而發展,在具有一段歷史之前思想擁有一種地理學,在構建系統之前它勾勒出諸多維度。高度是柏拉圖專有的太陽東升的方向。哲學家的運作因而被確定為提升、換位,也就是說,轉向他前進的高處原則之運動,並借助於這樣的轉動決定自己、充實自己和自我認識。人們將不會將哲學和疾病進行比較,可是卻有諸多哲學特有的疾病。唯心論是柏拉圖哲學的先天性疾病,隨著其一連串的上升和下降,哲學本身也是狂躁—抑鬱的形式。狂躁(mania)啟發並引導柏拉圖。辯證法是諸理念的飛逝,即思緒奔馳(l’Ideenflucht);正如柏拉圖談及理念,「它飛逝或消失⋯」。而且,甚至蘇格拉底之死,也有一種抑鬱性自殺的某種東西。
尼采對於這種自高度取其定位表示懷疑,並自問,若非呈現哲學的實現,這定位是否就不是以蘇格拉底開始的衰退和迷途。尼采以這種方式對於思想定位的全部問題重新提出質疑:思想行為在思想中醞釀而成,和思想者在生命中孕育出來,難道這不是根據其他維度嗎?尼采具備一個他發明的方法:不應該滿足於傳記或參考書目,必須達到神秘點,在此生命軼事和思想格言皆是同一件事。這就像意義一樣,一方面歸因於生命狀態,另一方面則在思想的命題中堅持著。這裡有維度、時間和地點,一些從未緩和的冰川區域或熱帶,整個異國地理有一種思維模式的特徵,也有一種生活型式的特徵。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ène Laërce),在他絕美的篇章中大概曾有這種方法的預想:找到攸關生命的格言,同樣是思想軼事—哲學家的姿態。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與埃特納火山(l’Etna),就是一件哲學軼事。等同蘇格拉底之死,不過這恰恰在另一維度上運作。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不從洞穴裡走出來,他反而認為,人們還不夠深入洞穴中,還不到被吞沒的地步。他拒絕的是忒修斯手中的那條線:「您的向上之路、您那通往外面、往幸福和道德的線與我們何干⋯您想藉助這條線的輔助來拯救我們嗎?而我們,懇求您:用這條線自縊!」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已在洞穴中放置思想,在深處安置生命。他們已探測水和火。他們用錘子敲打來研究哲學,如恩培多克勒打破雕像一樣,以地質學家、洞穴學家的鐵鎚。在水與火的氾濫中,火山從恩培多克勒身上只噴吐出一樣東西,那就是他的銅製涼鞋。柏拉圖靈魂的翅膀與恩培多克勒的涼鞋相對立,後者證明他屬於大地、在大地之下,且是原住民。柏拉圖的羽翼拍擊,與前蘇格拉底的錘子敲擊相對立。柏拉圖的換位,與前蘇格拉底的顛覆相對立。環環相扣的深度似乎對於尼采來說是哲學的真正方向,是在未來哲學中以一種同作為思想的生命,或者以一種同作為身體語言的所有力量,再次採用前蘇格拉底的發現。「任何洞穴背後都有另一個更深處,一定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地方,在表面下有一個更廣闊、最陌生、最豐富的世界,在任何深底之下,在任何地基之外,都有一處深淵」[ 奇怪的是,力圖描繪尼采的想像力特點的巴舍拉(Bachelard),卻將其呈現為一種「上升的心理現象」(L'Air et les songes, ch. V)。巴什拉不僅將尼采的大地和表面作用最小化,他也將尼采的「垂直性」(verticalité)解釋為處於任何高度和登高之前。儘管如此,它是相當地深和下墜。猛禽不會飛升,除非發生意外:牠懸垂且「猛襲」。甚至應當說,尼采使用深度來譴責高度的理念和上升的理想;高度只是一種故弄玄虛,一種表面效應,其騙不了深度之眼,也無法擺脫它的凝視。參考自,關於米歇爾.傅柯的評論,〈尼采,佛洛伊德,馬克思〉,載於《尼采》(in Nietzsche, Cahiers de Royaumont, éd. de Minuit, 1967, pp. 186-187)。]。首先,思覺失調症:前蘇格拉底主義是哲學特有的思覺失調症,在身體和思想中被挖掘的絕對深度,這意味著荷爾德林(Hölderlin)在尼采之前就知道要找到恩培多克勒。在恩培多克勒著名的交替中,在恨和愛的互補中,我們一方面遇到了恨的身體,漏勺和被分割的身體,「無頸之首,無肩之臂,無顏額之眼」,另一方面遇到了享天福且無器官的聖身,「整體式形式」,無四肢、無聲也無性徵。同樣地,戴奧尼索斯(Dionysos)以他的兩張臉面向我們,伸出他開放且撕裂的身體、他漠然且無器官的頭,被割下四肢的戴奧尼索斯,也是不可參透的戴奧尼索斯。
與深度的這次重逢,尼采只能透過征服諸表面才再次相遇。但他卻不停留在表面上;表面在他看來,必須從深度之眼所更新的觀點來判斷。尼采對柏拉圖之後發生的事不感興趣,認為這必然接下來是一段長時間的墮落期。然而,按照方法本身,我們卻感覺到,哲學家們的第三種形象正在出現。這是尼采對他們尤其適用的用語:這些希臘人由於不斷地接近淺表是多麼地有深度呀![ 《尼采反華格納》(Nietzsche contre Wagner, épilogue, § 2)。] 這些第三種希臘人,甚至完全不再是希臘人。救贖,他們不再從地球或本土深處,更不是從天堂和理念中等待它,而是從事件、從東方,在旁等待它 —在那,正如卡羅所說,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會出現。與麥加拉學派、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開始出現一種新哲學家和一種新類型的軼事。讓我們再讀第歐根尼.拉爾修最絕妙的篇章,其關於錫諾普的第歐根尼(Diogène le Cynique)、關於斯多噶學派的克律西波斯(Chrysippe le Stoïcien )。我們看到了一種挑釁的好奇求知系統的發展。一方面,哲學家吃得極其狼吞虎嚥,他吃得過飽;他在公共場合自慰,遺憾的是我們無法飢餓而思淫慾;他不譴責與母親、姊妹或女兒的亂倫;他容忍同類相食和嗜食人肉習性──當然,他也保持著最崇高程度的樸實和端正。另一方面,當有人向他提問時,他卻保持沉默,或者給您一記悶棍,或者是當您問他一個抽象又很困難的問題時,他以指出一樣食物,或甚至給您一盒食物隨後當著您的面打破食物盒來回應您,總是用棍子來擊破它——而且儘管如此,他還掌握新創的演說、由新哲學悖論、價值和涵義賦予活力的嶄新邏各斯。我們明確地感覺到這些軼事不再是柏拉圖式的,也非前蘇格拉底式的。
這是整體思想以及意味著思考意義的重新定位:既不再有深度亦不再有高度。反柏拉圖的犬儒式和斯多噶式的嘲諷不計其數:始終關乎撤銷理念,和表明無形體不在高度上,而在表面上,表明它不是最高的因,而是卓越的淺表效應,其非本質,而是事件。另一面,人們將表明深度是一種消化幻象,它補全了理想的光幻視。其實,這種狼吞虎嚥、這種對亂倫的辯護、這種對同類相食的辯解意味著什麼?這道最後的主題是克律西波斯和錫諾普的第歐根尼所共有的,拉爾修對於克律西波斯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可是他為錫諾普的第歐根尼提出了一個特別令人信服的解釋:「他不認為食人肉像人們對待外國人那樣如此可憎,他說,一切都合理地存於一切之中且無處不在。麵包裡有肉,草本植物裡有麵包;這些身體和許多其他身體透過隱密的管道進入所有身體,然後一起蒸發,如他在《提耶斯忒斯》(Thyeste)的戲劇中所表示的,萬一有人將悲劇歸咎於他,卻是屬於他自己的⋯。」這個論題,一樣適用於亂倫,確立了在身體深處,一切皆為混合的;人們寧可去稱一種混合是劣質的,而不是去指另一種混合,然而卻沒有任何可根據的規則。與柏拉圖所認為的相反,對於混合來說沒有一種高度測量、一些可以去定義好壞混合的理念組合。與前蘇格拉底學派相反的是,更沒有任何能夠在自然(Phusis)深度裡,去固定一項混合的順序和進展之內在度量;任何混合等於與相互滲透的身體和共存的諸部分之等價者。混合的世界怎麼不是自一切都被允許的黑暗深處的世界呢?
克律西波斯區分出兩種混合,不完美混合使身體變質,和完美混合使身體完好無損和使身體共存於它們的所有部分裡。諸原因之間物質因的統一大概定義了一種完美且流體的混合,於此,一切正好在宇宙當下。但是,身體投進其有限現在時的特性裡,不直接隨著其因果順序而相遇,因果關係僅適用於整體,考慮到所有同時的組合。這就是為什麼任何混合可被說是好的或壞的:在全(le tout)的順序中是好的,可是在局部發生的相遇順序中是不完美的、劣的甚至是糟糕的。激情本身就屬滲透到其他身體的身體,和特殊意志是一種根本的惡,在此領域中怎麼去譴責亂倫和嗜食人肉者呢?讓我們以塞內卡(Sénèque)的非凡悲劇為例。我們自問斯多噶思想,與這種首次將致力於惡的存有搬上舞台,如此精確地預示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之悲劇思想,他們的統一性是什麼。不是幾個斯多噶化的諧合就能做出統一性。真正的斯多噶學派,在此是對身體—激情的發現,以及激情所組織或經受的地獄般混合之發現,如熱情的毒素,戀童筵席。提耶斯忒斯的悲劇性宴席不僅僅是第歐根尼已失傳的主題,也是幸運地被保存下來的塞內卡的主題。有毒的膜從灼傷皮膚開始,燒光表面;然後它們到達最深處,沿著一條從被蝕穿的身體到成塊的身體(membra discerpta)的路徑。身體深處到處都冒出有毒的混合物,轉化成可憎的招魂術、亂倫和食物。讓我們尋找解藥或反證:塞內卡的悲劇英雄和斯多噶整體思想中的英雄,是海克力斯(Hercule)。然而,海克力斯總是身處於與三界有關之地:地獄深淵、上天和地球表面。在深處,他只發現了可怕的混合物;於空中,他只感受到虛空,甚至還有比地獄魔多一倍的天獸。而他卻是地球的調解者和土地丈量者,他甚至在水面上行走。他用盡所有方法再次上下表面;他把地獄犬和天狗、地獄的九頭蛇妖和天空的巨蛇帶回表面。不再是底部的戴奧尼索斯,也不再是上面的阿波羅,而是表面的海克力斯,在他與深度和高度的雙重鬥爭中:整個被再—定位的思想、嶄新的地理。
斯多噶主義有時被描述為在柏拉圖之外,操作一種前蘇格拉底主義的回返,例如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之回返。這就是關乎對前蘇格拉底世界的全面重新評價:通過深度混合的物理學來解釋它,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使其部分地陷入所有局部的無秩序中,這些局部無秩序只能與巨大混合取得協調,也就是說,與諸原因之間它們的統一性一致。這是一個充滿恐怖和殘酷、亂倫和嗜食人肉的世界。大概還有另一部分:從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中,可以上升至表面並將獲得一個全新的地位者—即事件在其本質上與身體—原因的差異,永恆(l’Aiôn)在其本質上與消耗的克諾時間(le Chronos)之差異。同時,柏拉圖主義也經歷過類似的全面再—定位:聲稱還更勝於前蘇格拉底的世界,還把它往後推得更遠,在高度的重壓下將它壓碎,卻感覺自己被剝奪了自己的高度,以及理念再度掉落在如無形體的唯一效應一樣的表面。這是斯多噶學派的偉大發現,反對前蘇格拉底學派也同時反對柏拉圖:(P. 158)表面的自主性,獨立於高度和深度之外,反對高度和深度;無形體事件的發現,無論是意義或效應,皆無法還原為具深度的身體和崇高的理念。所發生的一切,和所說的一切,皆在表面上發生和被說出來。這有不少是必須探究,有不少是未知的,還有可能比非—意義的深度和高度還要多。因為主要的邊界已位移。它不再於共相和個別之間向上移動。它不再於實體和偶性之間深入。也許這在於安提斯泰尼(Antisthène)的思想,應該為這條另闢蹊徑給予榮耀:在事物和命題本身之間。介於由命題所指稱的,如存在的事物,和不存於命題之外的被表達者之間(實體只是事物的次要規定性,而共相只是被表達者的次要規定性)。
表面、窗簾、地毯、外套,這是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的安身之處,和他們周圍的東西。表面的雙重意義,背面和正面的連續性,接替了高度和深度。窗簾後面什麼也沒有,除了說不出名稱的混合物。地毯上面什麼也沒有,除了空蕩蕩的天空。意義在表面上出現並發揮作用,至少假如有人知道如何適當地敲打表面,為了讓它可排列出粉末的字母,或者像是可以讓手指在玻璃窗書寫的蒸汽一樣。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中用棍棒敲擊的哲學接替了用錘子敲打的哲學。哲學家不再是洞穴裡的存有,也不再是柏拉圖的靈魂或禽鳥,而是表面的扁平動物,壁蝨、蝨子。哲學的象徵不再是柏拉圖的翅膀,也不再是恩培多克勒的銅製涼鞋,而是安提斯泰尼和第歐根尼的雙層披風。手杖和披風,就像海克力斯拿著狼牙棒和獅皮披肩一樣。如何命名哲學的新操作,作為它既反對柏拉圖的換位,也反對前蘇格拉底的顛覆?如果反常確實意味著一種表面的奇特藝術的話,那麼也許用「反常」這個詞,至少符合哲學家這種新型態的挑釁系統。
第十九系列:幽默(19e série, de l’humour)
首先,語言似乎無法在自我表達者的狀態中,也無法在指定的感性事物中找到充分的基礎,而只能在賦予語言一種真實和錯誤的可能性之理念中找到。儘管如此,我們很難看出命題透過什麼樣的奇蹟,以一種比說話的身體或我們談論的身體更可靠的方法參與理念,除非理念本身就是「名稱自身」。而身體,在另一極,能否更好地奠定語言?當聲音在身體上被閉合且成為混合體的行動和激情時,它們只會帶來淒厲的非—意義。我們相繼譴責柏拉圖語言和前蘇格拉底語言、唯心主義語言和物理語言、躁狂語言和思覺失調語言的不可能性。我們強加無結局的二擇一:要麼什麼都沒說,要麼吸收、吃進我們所說的。正如克律西波斯(Chrysippe)所說,「如果你說貨車這個詞,一輛貨車就會經由你的嘴裡駛出」,而這並不是最佳或最合適的說法,如果這是貨車的理念的話。
唯心主義語言是由實體化的涵義所組成的。但是,每一次我們被問到關於這樣的詞義時 —「何謂美、正義等等,何謂人?」—我們都以指定一個身體、以展示一個可模仿的或甚至可食用的客體來回應,有必要透過用棍棒一擊,棍棒被視為任何可能指稱的工具。犬儒派第歐根尼(Diogène le cynique)拋出一隻被㷟去羽毛的公雞來回應,柏拉圖的說法「無毛的兩足動物」作為人類的詞義。而對於詢問「何謂哲學?」的提問者,第歐根尼用細繩末端上的鯡魚回應之:魚,是最具口腔的動物,其提出啞、可食用性、顎化元素中的輔音問題,即語言的問題。柏拉圖嘲笑那些僅限於舉例、展示、指定而不觸及本質的人:我不問你(他說)誰是公正的,而是問正義是什麼,等等。然而,輕易地又順著柏拉圖聲稱引導我們攀登的道路而爬。每次我們被問到一個涵義時,我們都會以純粹的一項指定、一個說明來回應。為了說服觀眾這非關一個簡單的「例子」,而是柏拉圖的問題提得不好,人們將模仿自己指稱的東西,人們將以動作和表情模擬它,或者人們將吃掉它,將打破自己所展現的東西。重要的是動作要迅速:立即找到某事物來指定、食用或打破,取代了促使您去尋找的涵義(理念)。因為沒有,也不應該在我們呈現的和我們被問到的之間有任何相似之處,所以越快越好:只有一種不穩定的關係,其拒絕了本質—例子柏拉圖錯誤的二元性。對於這項用指稱、說明、食用性和純粹破壞來取代涵義的練習來說,需要一種怪誕的靈感,必須會「下降」—幽默,去反對蘇格拉底的反諷或上升的技巧。
可是這樣的下降會使我們落入何處呢?直到身體深處和其混合的無—底;正是因為任何指稱都以消耗、研碎和破壞中延展,如果不停止這種運動的話,猶如棍棒打碎了它所展示的一切,我們清楚地看到,語言無法以涵義為基礎更甚於以指稱為基礎。涵義使我們陷入取而代之且廢黜涵義的純粹指稱之中,這是作為無涵義的荒謬。但是,這些指稱反過來使我們陷入破壞性和消化性的深處,這是作為意義下(Sous-sens)或感官下(Untersinn)的深度之非—意義。那麼有何種脫身辦法呢?語言甚至從運動中高處落下,然後沉沒,我們必須被帶回表面,在那裡不再有任何必須指定、必須賦予涵義的東西,反而產生了純粹的意義:其與第三元素的主要關係中,這一次產出表面的非—意義。而且,再者,重要的是要做得快,這就是速度。
智者從表面發現了什麼?純粹事件於其永恆的真理中被沿用,也就是說,在實體中,將事件獨立於它們以時空在事物狀態的落實之外,來作為推論基礎。或者,回返至相同者,純粹的特異性,特異性於其隨機元素裡的輻射,獨立於體現或落實特異性的個體和個人之外。這趟幽默的歷險,這種有利於表面的高度和深度的雙重罷黜,這首先是斯多噶學派智者的歷險。但是,後來和在另一個背景下,也是禪宗(Zen)的歷險 —反對婆羅門教的深度和佛教的高度。著名的試題、問答、公案(koan),顯露涵義的荒謬,展示指稱的非—意義。棍棒是萬能工具,問題大師,啞劇和消耗就是答案。回到表面上,智者發現了事件—客體,所有這些都在構成其實體的空白中進行交流,它們在永恆中具體化和在從未填滿它的狀況下發展[ 斯多噶學派已經設計出一套非常完美的空白理論,同時作為超—存有(extra-être)和堅決要求(insistance)。如果無形體事件是存有或身體的邏輯屬性,那麼空白就像是這些屬性的實體,它本質上與有形的實體不同,以至於我們甚至不能說世界「在」空白之中。參考自,布列赫(É. Bréhier),《古斯多噶主義的無形體理論》(La Théorie des incorporels dans l’ancien stoïcisme, ch. III)。]。事件,是形式與空白的同一性。事件不是作為被指稱的客體,而是作為被表達或可表達的客體,從未在場,但總是已經過去並且尚待到來,如在馬拉美作品中,因其自身的缺席或廢除而有價值,因為這種廢除(拒絕:abdicatio)恰恰是作為純粹事件(奉獻:dedicatio)在空白中的位置。「禪宗說:如果你有一根棍棒,我再給你一根,如果你沒有,我從你身上拿走它」(或者,正如克律西波斯所說:「如果您沒有丟失一物,您就擁有它了;然而,您沒有失去任何犄角,因此您就有角了)。否定詞不再表達任何負面否定,而只是釋放純粹的可表達性與其兩個不對稱的半邊,其一總是在另一缺席,既然它通過其自身的缺少而超出,冒著通過其過剩而缺乏之風險,對於物 = x 而言,詞 = x 。我們確實在禪的藝術中看到這一點,不僅是書畫藝術,懸空的手腕操縱畫筆使得形式與空白佈局平衡,且將純粹事件的特異性分佈在偶然的輕彈和「細線」的系列中,也是園藝、插花和茶藝,以及射箭術、劍術,「鐵充分的發展」從絕妙的虛空中湧現。透過廢除涵義和失去指稱,空白是意義或事件的所在地,意義和事件由其自身的非—意義組成,在那種情況下僅有空白處發生。空白本身就是悖論元素,表面的非—意義,一直移位的隨機點,事件而從中以意義突然顯現。「沒有生死輪迴,而應該逃脫這迴圈,也沒有可觸及的至高無上的知識」:空白的天空拒絕精神的最高思想,也拒絕本性的深度循環。關於將現時性「立即」被保留下來的這個地方被決定為無法觸及的地方,並不少於關乎觸及現時性的問題:產生空白的表面,以及與之相關的任何事件,邊界作為一把劍的利刃或弓的細線。因此,無描繪而畫,非思想,無擊之射擊術,無言語而言:根本不是在高度或深度上的不可言喻,而是這條邊界、使語言有可能的這個表面,並且成為可能性,只激發出一種即刻靜默的交流,因為語言僅在復活所有被廢止的間接涵義和指稱的情況下才能被使用。
根據使語言有可能者,我們要問是誰在說話。對於相同的問題,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答案。我們將決定個體者作為說話者的回答稱為「古典」答案。他所說的恰恰被確定為一種說話特色,而中間項,即語言本身,被確定為約定俗成的一般性。那麼這是在一種變位的三重操作中,關乎得出的個體的普遍形式(實在性),同時我們從所論及的之中提取一個純粹的理念(必然性),並且我們以一個被假設為原始的、自然的或完全有理的理想原型來比對語言(可能性)。正是這種觀念使蘇格拉底的反諷如昇華般活躍,並派給它任務,將個體從其現時的存在中分離出來,同時也朝向理念超越感性的特點和建立語言符合原型的規則。這就是有記憶和說話的主體性之「辯證」總體。然而,要使這操作完整,個體不僅必須是起點和跳板,而且也必須重返終點,而理念的一般概念也必須作為兩者之間的交換手段。反諷的結束、這種迴路在柏拉圖那裡仍然缺乏,或只在喜劇和嘲笑的種類下出現,如蘇格拉底—阿爾西比亞德(Socrate-Alcibiade)的往來。當古典反諷有時不只將實在性的全部也將可能性的總體確定為先天的最高個體化時,它反而獲得了這種完美狀態。我們所見,康德希望將再現的古典世界服膺於理性批判,以準確地描述它開始:「任何可能性總體的理念被純化,直到形成一個先驗地完全確定的概念,因此從而成為單數存有的概念」[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論先驗理想〉(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 De l’idéal transcendantal »)。]。古典反諷以確保存有與個體於再現世界中同外延性的堅決要求而起作用。因此,不僅是理念的一般概念,也是就最初的可能性而言,有理的純粹語言之原型,都成為了具高度個體化的上帝和祂所創造的衍生個體之間本性的交流手段;正是這位上帝使個體有可能上升至普遍形式。
不過,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之後,出現了第三種反諷的修辭格:浪漫的反諷將說話者認定為個人,而不再作為個體。這反諷是基於個人的有限綜合的統一體,而不再建立於個體的分析同一性。反諷經由我(le Je)和再現自身的同外延性被定義。這裡不僅僅有詞語變化(為了將其確定為整個重點,有必要評估如蒙田的《隨筆集》(Essais),這些文集已經納入古典世界之中,作為探索個體化最多樣的修辭格,和盧梭的《懺悔錄》(Confessions)之間的差異,後者宣告浪漫主義,作為其為一個人或一個我(Je)的首要表現)。不僅是普遍理念和感性的特點,也是個體化的兩極,以及與個體相符的世界,現下都成了個人自己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繼續被分為起源和衍生,而起源卻只代表個人對於所有可能世界的恆定謂詞(範疇),而衍生,代表個體的多變,個人在這些不同世界中被體現。產生一種深層的轉變,是理念的一般概念、主體性的形式、作為語言的可能性作用的原型之轉變。個人的位置作為無窮的級別,卻只有一位成員(我),這位置就是浪漫的反諷。在笛卡兒的我思(le cogito)中,尤其在萊布尼茲的個人中,大概已有先驅元素;而這些元素仍然服從於個體化的要求,然而諸元素在康德之後的浪漫主義中,透過顛覆從屬關係自我釋放並且以其自身被表達出來。「這種具無窮詩意的著名自由以積極的方式被表達為,個體在可能性的形式下已貫穿一整個不同確定性的系列,和在它陷入虛無之前給予確定性如詩一般的存在。致力於反諷的靈魂與畢達哥拉斯(Pythagore)學說中貫穿世界的靈魂相似:靈魂總是在旅途中,卻不再需要一段如此長久的持續時間⋯。如孩子們走向有利可圖的人一樣,諷刺詩人屈指一算:白馬王子或行乞者等。所有的這些化身在他眼中除了純粹可能性的價值之外沒有別的了,他可以和孩子一樣,在遊戲中快速破關。相反地,對於諷刺詩人來說則需要時間,他按照自己的幻想所確信的詩意角色精心裝扮自己⋯對諷刺詩人來說,如果給定的實在性因此失去其價值,那並不是由於實在性是一種過時的現實,而應該讓位給另一個更真實的現實,而是因為諷刺詩人體現了基本的我(le Je),對此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現實」[ 齊克果,〈反諷的概念〉(《齊克果,其生活、其作品》(Pierre Ménard, Kierkegaard, sa vie, son œuvre, pp. 57-59))。]。
所有反諷的修辭格的共同點在於,將特異性包圍在個體或個人的範圍內。所以反諷只是表面上飄移。然而,尤其是為什麼所有的這些修辭格都受到一個從內部將它們成形的內在敵人之威脅:無區分之底,我們先前談到的無—底,它再現了悲劇性思想,反諷以悲劇文體維持最為矛盾的情緒關係。這是蘇格拉底下的戴奧尼索斯,這也是惡魔,他將鏡子遞向上帝和祂的創造物,普遍的個體性於鏡中解體,還是摧毀個人的混沌。個體持有古典演說,個人則持有浪漫演說。不過,在這兩種演說之下,和以各種方式推翻它們的,正是現下以轟轟聲說話的無顏面之底。我們已見,這種底層語言、與身體深度混在一起的語言,具有雙重力量,即分散的語音音素之力量、難以發音的重音值的力量。這正是前者從內部去威脅並且推翻古典言說,而後者推翻的則是浪漫言說。因此,我們必須在每一情況下,針對每一類型的言說,區分出三種語言。首先,一種實在的語言,對應於說話者(個體,或者個人⋯)完全慣常的指定。然後是一種理想語言,根據語言持有者的形式來再現言說的原型(例如,對於蘇格拉底主體性而言,《克拉底魯篇》(Cratyle)的神聖原型、對於古典個體性而言,萊布尼茲的有理原型、對於浪漫的個人而言,進化論原型)。最後是難以理解的語言,在每一情況下,透過深底,呈現出對理想語言的顛覆和對持有實在語言者的拆解。此外,理想模式與其難懂的顛倒之間,和反諷與悲劇深底之間,每一次都存在著內在關係,以至於我們根本不知道哪一邊才是最大化的反諷。這就是為什麼替所有難以理解的語言尋求獨一的公式、獨一的概念皆是徒勞:如為了關閉古典世界的庫爾.德.哥柏林(Court de Gébelin)的語音、文字和音節的重要綜合,以及結束浪漫主義的讓—皮耶.布里塞(Jean-Pierre Brisset)的可演化重音的重要綜合(我們同樣見到了,不與組合詞一致)。
誰在說話?我們有時以個體、有時由個人來回應,有時以溶解兩者的深底來回答這個問題。「抒情詩人的自我從存有的深淵深處提高嗓門,他的主體性是純粹的想像」[ 尼采,《悲劇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tragédie, § 5)。]。卻仍採納最後一個答案:它既否認個體和個人形式,也否認未區分的初始深底,以及同時拒絕它們的矛盾和它們的互補性。非也,特異性並沒有被囚禁在個體和個人之中;當我們打亂個體和個人時,我們更不會陷入未區分的深底、無底之深度。非人稱和前—個體的,就是自由和遊牧的特異性。比任何深底更深層的,就是表面、是皮膚。在此形成了難以理解的語言的一種新類型,對於其自身是它自己的原型和實在性。當瘋狂—生成變異(le devenir-fou)上升至表面時,在永恆的直線上、永久性上改變其形貌;同樣地,分解的自我、裂開的我、丟失的身份,當它們不再下沉時,反而會釋放出表面的特異性。非—意義和意義打破了它們動態對立的關係,而進入與靜態生成同在,如表面的非—意義和在表面上掠過的意義。悲劇和反諷讓位給一項新價值,即幽默。因為如果反諷是存有和個體,或我和再現同外延性,而幽默則是意義與非—意義的同外延性;幽默是表面和襯裡、遊牧的特異性和一直位移的隨機點之技巧,是靜態生成的技巧、純粹事件的訣竅或「單數的第四人稱」(la quatr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任何涵義、指稱和表現被懸置,任何深度和高度被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