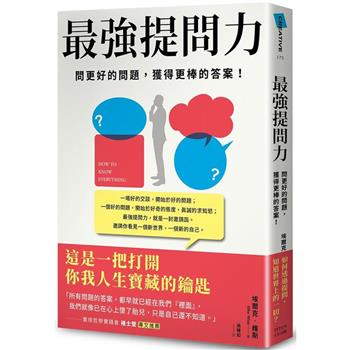【前言】被對話的框架框住了?
我們的判斷從何而來?
「快啊,問吧。」蘇格拉底在我耳邊說。「就問吧,沒什麼好不問的。」
我眨了眨眼。「蘇格拉底,你聽我說,」我解釋道,「我知道你是從兩千五百年前來的,所以可能有點糊塗了,但是這種事情在現代不是可以就這樣開口問的……」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我報名了一堂「實用哲學」的課程,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因為想要進行有哲理的對話還有澄清我的思緒,所以希望能學一點相關的理論和可以實際運用的知識。身為舞台劇作家又是導演,我也希望能夠在創作的過程中更清楚地掌握腦海裡的思緒。也許更明確的說法應該是,我希望能在問演員問題的時候能更精準地遣詞達意。所以就這樣,我當時就在那裡想要接觸哲學的實際面。
課程的第一天,午餐休息時間的時候,五位同學與我同桌用餐,分別是四女一男。沒多久,餐桌上的對話就開始討論起孩子了。大家按照座位順序輪流發言。你有小孩嗎?有,一個兒子。那你呢?兩個女兒,快顧不來了!大家都問了幾個後續的問題:孩子幾歲啊?上學了嗎?你給小孩iPad了嗎?都是我很熟悉的閒聊內容。當時的我二十多歲快三十歲,這個話題已經遇過不知道多少次。只要一有人說「沒吔,我沒有小孩」,現場若不是一陣怪異的沉默,就是馬上把一問一答的流程轉移到下一個人身上。毫不意外,有小孩的人很愛聊有小孩的事,但是感覺上更像是大家不想聽沒有小孩的人的故事。然而即便如此,我以前還是會這樣想,等一下,大家都有故事可以說啊。我們怎麼可以因為某人的行為就決定一個問題也不問、就判定他們的故事沒人想聽?
對話很快就輪到我身上了,我老實地說自己沒有小孩。我吸了口氣,準備好要多介紹一點自己。當時的我在學校教戲劇課,多的是跟孩子相關的故事好說,多的是我樂意分享的故事。
除此之外,我也很想聽聽其他人的經驗分享,想知道他們生活中的動力來源是什麼。我想跟他們分享我對於生小孩這件事的猶豫心情,像是,你怎麼知道你是真的想要小孩?感覺是個非常大的突破,是決定性的時刻,是一件你必須認真思考的事吧。你怎麼做出這樣重大的決定?但是我還沒來得及開口,已經有人匆匆將「那你呢?」三個字對著下一個成員說了出口。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我身邊的女子身上,她也很快就開始熱切地訴說起七歲小孩的事情。每個人都刻意避開了我的目光:顯然我的故事在這裡沒有立足之地。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畢竟,我們年紀都差不多,加上大家都來報名了這堂課,所以看起來至少有一個共同興趣才對。現場顯然很適合聊一些更有深度的話題吧,可以不用被標準的對話框架局限才對。
我心裡冒出一種不悅的感覺。為何要開始講小孩的話題,且只讓一部分人參與?為何暗自判定誰的故事可以說,誰的應該被跳過?為什麼不讓每個人自己決定他們有沒有東西要分享?
我身邊的女子把所有跟她家小女孩有關的事情都說完了以後,問題輪到了下一個人身上—一名年約四十出頭的女性,一頭俏麗棕色鬈髮。「不,」她說,「我沒有小孩。」一說完,小團體立刻就準備好換下一個人。
你為什麼沒有勇氣問?
就是這時候,我感覺到時間暫停了下來,我聽見身後傳來一個聲音說,「快啊,問吧。」蘇格拉底對我露出鼓勵的微笑。他看著我坐立難安的模樣,眼神趣味盎然。「就問吧!沒什麼好不問的。」
我看著他,解釋給他聽,在我們這個年代,事情不是這樣運作的。「我不能突然問那種問題……」蘇格拉底挑眉。「你們的問題就在這裡。你們想出了這套行為守則,把某些問題貼上不舒服、不恰當的標籤,其他問題則被分類為正面的、允許提問。只因為你們覺得要顧及他人的感受—問題本身必須有禮,一定要避開真實、甚至是痛苦的問題,忽視了問題之所以重要,其實就是因為那些因素這點。」
「對,可是……」
「你想問的問題是事實對吧?」「呃,對……」
「一個事實問題,怎麼會不恰當?」「我……呃……我不知道。」
「就是啊。『是你決定不要生小孩的嗎?』這個問題跟『是你決定不慶生的嗎?是你選擇不決定求學的嗎?是你決定不接受升職的嗎?』這些問題的差異並不大,你自己要在特定主題上面附加痛苦情緒,使得避開這些題目變成一種潛規則,這跟問題本體一點關係都沒有。這也難怪你們這些人總是想要到處找更有深度的人生。你們把對話變成了地雷區!因為太害怕會引爆炸彈,所以決定盡可能地讓所有東西都維持在安全範圍內。然而一旦這麼做,對話就會變得很膚淺,而且索然無味。」
我張嘴想要辯解,可是蘇格拉底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就繼續接著說下去了。「而且如果你覺得沒小孩的人也有資格分享自己的故事,卻一直什麼都不說,那你就是這問題的一部分。你跟那些一直維護潛規則的人一樣有罪。」
我再次眨眨眼,覺得有點茫然。那現在要怎麼樣?
「問問題啊!」蘇格拉底嘆了口氣,朝著那個有一頭俏麗鬈髮的女生點點頭,然後往椅背一靠。
你為什麼有權利問?
於是我忘卻了問問題的藝術,本著一點善意和希望自己能有所成長的心態,加上蘇格拉底的鼓勵,我決定要放手一試。革命就此開始,我心想。我要在所有小組討論中當沒有子女的女性的代表,更不用說還能為眼前這場討論增加一點深度。我鼓起勇氣,深呼吸後,看著俏麗鬈髮女的雙眼,打破了小組間短暫的沉默。「那,是妳決定不要生小孩的嗎?」緊接而來的是另一陣沉默,這次緊繃又尷尬。我感覺到小組中其他人都屏息以待。女子瞪視著我,像是凍結了一樣,然後咬牙切齒地說,「不。不是我決定的,不是。」其他人簡直可說是透過全體一起努力,把自己變成了透明人。以擠在一張小桌邊的六個人來說,這可不是容易的事,不過他們豁出去了。
我感覺到自己的神經瞬間斷光。「還真是個好建議啊,老兄!」我對蘇格拉底低聲怒道。「感謝你一點忙都沒幫到。」我的腦海裡警鈴大響。我到底該怎麼解救眼前的情況?
午餐時間已經結束了,我們一群人一起走回教室。我刻意配合俏麗鬈髮女的腳步,一邊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有的沒的,還有「我不是故意要讓妳難過,我只是覺得像這樣的討論,沒有小孩的人常常都會被跳過,真的太不公平了,而且我其實都會想要多聽一點大家的故事,而且因為我是真的對妳的經歷有興趣,所以想說就直接問妳……因為,嗯,大家的故事都應該要有人聽,加上畢竟我們來是要學實用哲學和如何提出更好的問題,還有……」
在我自己佈下的地雷場步履闌珊地前進的我,看來是沒有整理出一個有連貫性的想法。我那懦弱又羞愧的道歉,就這樣懸在空氣中。她冷冷地點點頭,意思是我可以不要再想了,然後惡狠狠地用氣聲說,「妳知道嗎,有人覺得自己有權利問這種問題,我覺得很奇怪。」她大步走向教室,留我一個人走在她的身後,舉步維艱。
那次的午餐互動、那場對話和那個問題在我腦海裡如此清晰,是因為其帶來的感受強烈無比—對被問問題的那個女子以及對問問題的我來說都是。
我覺得很羞愧,充滿罪惡感,但是我沒辦法確切說出原因。我的動機很單純:我想要與對方建立連結,創造更開放、更有意義的交談,讓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想超越膚淺的閒聊,像是「你做什麼工作啊?」「你住哪邊?」還有「你有幾個小孩?」。我本來是希望能夠讓每個人的故事都有一個位置,希望可以質疑那些在我眼中顯得不公平的潛規則。宛若現代蘇格拉底,我本來是希望能夠用好的問題、有價值的答案和更優質的對話來征服世界。
我真希望在那次命定的午餐休息時光裡的我已經知道了我現在知道的東西。希望我已經知道要問那樣的問題有其他辦法,不必把所有人都拖進壞情緒的泥沼裡。希望我已經知道要建立環境和條件,讓對話超越閒聊的程度,產生更深的共鳴是有可能的。希望我已經知道你可以問一些能夠建立連結的問題、能夠真的傳達真正想說的話的問題,即便有時候會帶來一些疼痛也一樣。
希望我已經知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問題,找到可以問問題又不會引發對方做出防禦回應的方法。希望我已經知道好的問題會引導出有利的答案,值得你全心的對待。
希望我已經知道對話一定有辦法平等地進行,重要的想法和信念都可以被看見,能讓對話深入主題的核心,分辨重要的內容和廢話—這方法讓大家能夠對自己的情緒和敏感負起責任。這個方法讓問題維持單純的身分:用來邀請大家深入一點。你可以自由決定拒絕或接受這個邀請。不需要令人如坐針氈的沉默、受傷的靈魂,也不必在一張小到沒有空間躲藏的午餐桌邊瘋狂祈禱自己變隱形。
從此你的名字可以叫「思考者」
如果當時的我就知道這些我現在知道的東西,我一定還是會問那個問題。但我會換個方式問。我會比照蘇格拉底的習慣,先取得對方的同意。我會改說,「我有興趣多聽一點,妳介意我繼續問嗎?」
但當時的我並不知道我現在知道的這些。當時的我盡可能地運用了手邊僅有的工具,最後換來了慘痛的經驗,一個從那之後便常常讓我深思與糾結的經驗。那次短暫經歷對我接下來幾年的人格成長、教育,甚至是這本書,都產生了顯著的貢獻。從那之後我便開始學習更多關於實用哲學的知識、問問題的藝術,以及進行有哲理、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我在荷蘭以及海外進修,並成立了一間公司,名為「思考者」,提供蘇格拉底式論述、批判性思考和提問的訓練課程和研習。那之後的每一天都是學習的過程。學習哪些東西可行,哪些不行。哪些條件能構成好的問題。學習能做什麼事情來增加討論的深度,讓大家開始動腦,一起用哲學思考,建立彼此間的連結。我也認識了蘇格拉底,現在的我把他當作英雄看待。他是我哲學世界裡的碧昂絲,而我絕對是忠實歌迷。
在培訓課程、哲學諮商和報告中,我親眼見過、感受過用不同的動機帶領談話所能造成的衝擊,以及如果能刻意培養蘇格拉底式的態度、努力調整問問題的方法,人與人之間的交談能夠改善多少。我目睹過在聽人交談、與人交談的時候,若能提防那些針對人性存在的陷阱,並且找到方法避免落入其中,對話與交談可以變得多有重量、有意義。
我體驗過把這個知識分享給其他人、幫助他們領悟這件事、取得技巧之後的快樂。隨著時間過去,我發現自己想要寫一本書,來幫助所有一心渴望能與人進行更有品質的交談卻苦無方法的人。讓我帶你踏上這條旅程吧。有了蘇格拉底當我們的嚮導,就可以來好好探索問問題的藝術。這樣一來,在所有場合、任何情況下,你都有辦法為交談內容帶來深度,也會知道如何透過問出該問的問題,就可以多了解身邊環境—對所有東西都了解更深一點。
Part1:為什麼我們都這麼拙於問出好問題?
「我一天到晚在問問題,是有什麼好學的?」
我熱愛我的工作。每次在派對上,或是在一些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場合,只要有人問我從事什麼職業,我都會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利用哲學方法,幫助別人問出更好的問題。我舉辦研習、課程、擔任個人教練,讓人了解自己的思緒過程,以及—」通常講到這裡,就會有人打斷。「你教人問問題?問問題有什麼難的?我整天都在問問題啊,要問問題為什麼還要上課?」
我心裡有一小部分想要賣弄一下,想要指出眼前這情況有多諷刺:一個認為問問題這件事並不需要他人協助的人,正巧就問出了一連串有引導性、花稍虛無且完全與開放性和好奇心大相逕庭的問題,都是難以視為真誠提問的問題。可是我沒有這麼做,而是將這樣的情況拿來提醒自己,講到如何提出真正的好問題這件事,還有多少人需要幫助,我們還有多少學習空間。
當然,這位派對上的朋友沒有錯。我們的確是整天都在問問題,或者說,至少我們認為如此。
就算你深信自己整天都在問問題,且應該也很擅長此事,然而事實通常有極大落差。實際上,你每次提問大概都只是在傳達一個帶問號的句子罷了。要做到這件事,的確不需要上課。另一件我們整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呼吸,但是好幾項研究都顯示其實人並不太擅長此事:大多數人的呼吸都太急促而淺短。問問題也是類似的狀況,我們潛意識的習慣會讓自己走偏。
我們的社會整體來說,並沒有將問問題這件事掌握得很好。一般人太常想到什麼就問什麼,這些問題往往不完整、帶有暗示性、花稍虛無、不合時宜,或者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你不覺得湯姆最近很易怒嗎?」「我怎麼會想換方法做啊?」「你這次又有什麼藉口?」「你不覺得麥可變胖了嗎?」「你覺得安娜不來是不是因為她會怕?還是她在生氣,還是說她……?」
每當有人拿問題或困境找上門來,我們通常不是先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而是立刻跳進解決問題的模式。「你有跟她談過嗎?」「我的諮商師很有用,對你一定也會有幫助的!」不然就是用建議把對方淹沒。「你知道你該怎麼做嗎?你應該……」「你現在應該要聯絡這些人。」或者是會用自己的經驗來蓋過對方的事件。「我也遇過一樣的事!不過我那次比較……」
我們通常會寧可讓對方相信我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而不是仔細檢視對方的觀點。一聽到他們的故事,馬上就先跟自己的生活建立連結,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對方想要告訴我們的事件上。我們的思緒早已往前衝,思考等對方說完後,自己要回答什麼話:「對,但是這情況我有完全不同的見解……」其實我們大可把時間花在好好地聆聽。
好消息是:「問出正確的問題」是一項可以習得的能力。問問題的能力也許是天生具備,但也是一個可以熟能生巧的技能。其實跟跳高有點像:理論上這是幾乎所有人類小時候都能做到的事,不過要是有認真思考方法,鍛鍊這個天生的能力,就能表現得更好。
「問題」就像是工具。用得對,就能讓你進入深度思考的討論之中,探索對方的觀點。你可以是一把細小的鑷子,或是粗重的鑽頭;可以低調如砂紙,或跟撬棍一樣直截了當。就跟使用工具的時候一樣,結果會隨著用法改變。我可以用鑿子在大石頭上一點一點雕刻出藝術品,但是如果我做過頭,在錯誤的方向施力過度,可能就會不小心把雕像的頭鑿斷。我也可以拿砂紙把整個表面都打磨光滑,但是如果我的施壓力道不夠,就看不出什麼改變。問問題也是這樣:透過技巧、有了目的,就能更有效益。
從純然的好奇心之中產生的問題,就是往對方踏出去的第一步。透過問出那樣的問題,你就像是在說:我希望能夠更接近一點、更了解你一點。這麼做必然會有風險,也會造成一點壓力。畢竟,對方很可能會直接叫你滾。這也是為何人會對於問出好問題這件事這麼猶豫的原因之一。
到底什麼是「問題」?
大家應該要花點時間想想何謂問題,更重要的是去想想,什麼東西不是問題?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假定大家都知道「問題」的意思,但是仔細想想,許多人問的問題其實根本都不是問題。而是假裝成問題的聲明、預想或假設。「你不覺得艾莉絲說得對嗎?」「你是想暗示……嗎?」「班說的有道理,不是嗎?」這些其實更像是打包在問題裡的意見,或者是一些需要被快速確認一下的假說。白紙黑字呈現的時候,也許就很清楚了。「哎,那當然不是真的問題啊!大家都看得出來!」但是從現在開始,仔細去聽,你會開始發現我們每天問的這些問題,其中有多少其實跟真誠的提問完全相反。
牛津英文字典對「問題」的定義是「語句的用詞或傳達的意思能從一個人身上引導出資訊」。雖然這個定義完全可以拿來解釋何謂問題—我可沒打算跟牛津英文字典作對啊!—卻沒有進一步提及這樣的語句可以怎樣操弄、語句背後的目的或對他人會產生的效果。從實用哲學的背景以及我們的重點,也就是如何問好問題這點來看,我做出了以下定義:
一個問題,就是一封邀請函。邀請對方思考、解釋、去蕪存菁、深入鑽研、提供資訊、調查、建立連結。
◎一個好的問題的建構會很清楚,具備開放、好奇的態度。
◎一個好的問題會把焦點留在對方和他們訴說的故事上頭。
◎一個好的問題會讓人開始思考。
◎一個好的問題會為接收的那一方消除干擾、帶來新的領悟或新視角。
◎一個好的問題,目的不是要給出建議、檢視假說、強加觀點、分享意見、提出建議或讓對方感覺到被批評或受困。
最後一點尤為重要。雖然這之中的差異似乎非常顯而易見,我們每天問的問題卻多落在這些範圍之外。我們都太常無意間、甚至在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問出以自我為中心點的問題。從自己的恐懼、感覺、想法、偏見和需求去問。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問題投射這些東西到其他人的故事之上。換句話說,我們問問題都只是要讓自己安心,而不是真的進一步詢問對方說話的內容。
就好像你跟摯友說自己和另一半大吵一架的事之後,他卻問你:「你想要離開他嗎?」或者像同事聽完你說去托斯卡尼的度假經驗後回你:「連續一個禮拜都是義大利麵和披薩,你不膩嗎?」還有聽完你說擔心母親健康每況愈下的事情之後,那個朋友回答你,「所以你去照顧她了嗎?會很辛苦喔。我自己這樣做過一段日子……」
所謂的爛問題並不存在?
你可能常聽到有人說爛問題不存在,概括來看,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全盤錯誤。通常這種問題會讓人毫無保留地高談闊論,這當然是好事,問題本來就不該憋在心裡。然而,很多立意良善的問題卻被用乏善可陳的言語架構而成。即便問題背後的意圖很實際,問問題的人的動機也無可挑剔,問題本身卻可能會完全錯過重點。王爾德曾寫下這樣的文字,「書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只有寫得好或寫得差的分別。」問問題也是這樣。世上沒有天生的好問題或爛問題,但是絕對有組織得好的問題跟組織得不好的問題,還有用得好或用得不好的問題。
我在這本書裡說到的「好的問題」,意思一定都是指誠懇、真摯,能夠鼓勵他人思考的問題。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目的都不是想要出力影響或改變事物的方向。沒有想要修復問題點或強加自己思考方式的意圖。一個好的問題一看就知道在問的情境中能夠產生作用,並符合其目的。
在這裡如果舉出確切的例子就失焦了:在某一個情境中能夠擊中目標的問題,在另一個情境中可能完全偏離核心。這次適合的做法,下次可能就行不通。在這場對話中的意圖與另一場對話的意圖各不相同,這也會決定問題的效益。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應證我自己下的定義:一個問題,就是一封邀請函。
有深度的對話是由什麼東西構成的?
在這本書裡面,我會跟各位談談有深度的對話:有真的內涵的對話,能夠觸及核心的對話。花點時間去思考一場好的、有深度的對話要包含什麼東西是值得的。一場好的對話不會乏善可陳,也不是只有一邊不斷訴說而已。好的對話不僅是兩個人各自把自己的意見列出來、交換奇聞軼事、閒聊,不是兩段獨白的重疊,或同時喋喋不休。
有深度的對話包含去探索另一人的經驗,進一步檢視想法、概念,和其中可以探討的問題,尤其是關於人性的觀念。把焦點放在另一人的經驗上這件事說易行難,若沒有刻意為之,我們很可能會變成太過熱情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經驗或觀點,忘了應該要先去深入了解另一人。一段有深度的談話應該是一種能夠激勵人且能共同進行的過程,讓兩人合力追求智慧。
雖然是一片好意,但我親愛的老奶奶聽到我扭傷腳的消息後說的話就沒有及格。「噢,小可憐,太慘了吧。格雷塔的姪女去年也是這樣。三個禮拜的時間直接作廢,沒辦法開車,沒辦法走路—完全一無是處。糟透了!真的是糟糕透頂!」
為什麼好的問題得來不易?
要改善問問題的能力,先明白自己為何不太擅長此事很重要。如果我想要當一個優秀的辯論家,我最好勤加練習。但是光只是練習並不能讓我達成目標,我還需要認識辯論中的陷阱,並且透過學會如何進行辯論以及建立強而有力的論點來掌握理論的內容。要成為一名更優秀的廚師,我得在廚房裡好好練習,了解如何結合不同的風味、氣味、質地和材料,並且研究為什麼使用某些組合、工具和技巧,得到的效果特別好。曾經親眼目睹自己做的巧克力舒芙蕾在烤箱裡烤到塌陷的人就會知道,認識陷阱、摸清可能會導致失敗的元素,有時候是最好的起點。
所以說,在我們開始練習「如何」問出好問題之前,要先停下來思考一下,為什麼好問題這麼難出現。一旦理解了為什麼大家常常在這個地方失敗,你就會發現自己也經常做出這些經典錯誤提問。光是認知到這點,就能讓你對於自己問問題的能力更加留心,也能幫助你閃避陷阱。不僅如此,很快地,你也會開始可以更注意身邊的日常對話與媒體傳播的內容,進而辨識許多在你要問出好問題的時候,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
我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蒐集了許多意見回饋,進行採訪,問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最重要的兩點分別為「是什麼東西讓你不願意問問題?」以及「你覺得一般人為什麼會不想問問題?」。透過我自己的研究、經驗、發現和結論,我把答案統整起來,整理出人無法問出好問題的六大原因:
1.人類天性:談論自己的感覺比問問題好多了。
2.害怕提問:提問有的時候是一種很恐怖的處境。
3.得分點:發表意見比提出問題更能令人印象深刻。
4.缺乏客觀性:我們的客觀的推理能力日漸衰退。
5.沒有耐性:我們認為問好問題只是在浪費時間。
6.缺乏能力:沒有人教過我們怎麼做。
我們的判斷從何而來?
「快啊,問吧。」蘇格拉底在我耳邊說。「就問吧,沒什麼好不問的。」
我眨了眨眼。「蘇格拉底,你聽我說,」我解釋道,「我知道你是從兩千五百年前來的,所以可能有點糊塗了,但是這種事情在現代不是可以就這樣開口問的……」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我報名了一堂「實用哲學」的課程,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因為想要進行有哲理的對話還有澄清我的思緒,所以希望能學一點相關的理論和可以實際運用的知識。身為舞台劇作家又是導演,我也希望能夠在創作的過程中更清楚地掌握腦海裡的思緒。也許更明確的說法應該是,我希望能在問演員問題的時候能更精準地遣詞達意。所以就這樣,我當時就在那裡想要接觸哲學的實際面。
課程的第一天,午餐休息時間的時候,五位同學與我同桌用餐,分別是四女一男。沒多久,餐桌上的對話就開始討論起孩子了。大家按照座位順序輪流發言。你有小孩嗎?有,一個兒子。那你呢?兩個女兒,快顧不來了!大家都問了幾個後續的問題:孩子幾歲啊?上學了嗎?你給小孩iPad了嗎?都是我很熟悉的閒聊內容。當時的我二十多歲快三十歲,這個話題已經遇過不知道多少次。只要一有人說「沒吔,我沒有小孩」,現場若不是一陣怪異的沉默,就是馬上把一問一答的流程轉移到下一個人身上。毫不意外,有小孩的人很愛聊有小孩的事,但是感覺上更像是大家不想聽沒有小孩的人的故事。然而即便如此,我以前還是會這樣想,等一下,大家都有故事可以說啊。我們怎麼可以因為某人的行為就決定一個問題也不問、就判定他們的故事沒人想聽?
對話很快就輪到我身上了,我老實地說自己沒有小孩。我吸了口氣,準備好要多介紹一點自己。當時的我在學校教戲劇課,多的是跟孩子相關的故事好說,多的是我樂意分享的故事。
除此之外,我也很想聽聽其他人的經驗分享,想知道他們生活中的動力來源是什麼。我想跟他們分享我對於生小孩這件事的猶豫心情,像是,你怎麼知道你是真的想要小孩?感覺是個非常大的突破,是決定性的時刻,是一件你必須認真思考的事吧。你怎麼做出這樣重大的決定?但是我還沒來得及開口,已經有人匆匆將「那你呢?」三個字對著下一個成員說了出口。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我身邊的女子身上,她也很快就開始熱切地訴說起七歲小孩的事情。每個人都刻意避開了我的目光:顯然我的故事在這裡沒有立足之地。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畢竟,我們年紀都差不多,加上大家都來報名了這堂課,所以看起來至少有一個共同興趣才對。現場顯然很適合聊一些更有深度的話題吧,可以不用被標準的對話框架局限才對。
我心裡冒出一種不悅的感覺。為何要開始講小孩的話題,且只讓一部分人參與?為何暗自判定誰的故事可以說,誰的應該被跳過?為什麼不讓每個人自己決定他們有沒有東西要分享?
我身邊的女子把所有跟她家小女孩有關的事情都說完了以後,問題輪到了下一個人身上—一名年約四十出頭的女性,一頭俏麗棕色鬈髮。「不,」她說,「我沒有小孩。」一說完,小團體立刻就準備好換下一個人。
你為什麼沒有勇氣問?
就是這時候,我感覺到時間暫停了下來,我聽見身後傳來一個聲音說,「快啊,問吧。」蘇格拉底對我露出鼓勵的微笑。他看著我坐立難安的模樣,眼神趣味盎然。「就問吧!沒什麼好不問的。」
我看著他,解釋給他聽,在我們這個年代,事情不是這樣運作的。「我不能突然問那種問題……」蘇格拉底挑眉。「你們的問題就在這裡。你們想出了這套行為守則,把某些問題貼上不舒服、不恰當的標籤,其他問題則被分類為正面的、允許提問。只因為你們覺得要顧及他人的感受—問題本身必須有禮,一定要避開真實、甚至是痛苦的問題,忽視了問題之所以重要,其實就是因為那些因素這點。」
「對,可是……」
「你想問的問題是事實對吧?」「呃,對……」
「一個事實問題,怎麼會不恰當?」「我……呃……我不知道。」
「就是啊。『是你決定不要生小孩的嗎?』這個問題跟『是你決定不慶生的嗎?是你選擇不決定求學的嗎?是你決定不接受升職的嗎?』這些問題的差異並不大,你自己要在特定主題上面附加痛苦情緒,使得避開這些題目變成一種潛規則,這跟問題本體一點關係都沒有。這也難怪你們這些人總是想要到處找更有深度的人生。你們把對話變成了地雷區!因為太害怕會引爆炸彈,所以決定盡可能地讓所有東西都維持在安全範圍內。然而一旦這麼做,對話就會變得很膚淺,而且索然無味。」
我張嘴想要辯解,可是蘇格拉底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就繼續接著說下去了。「而且如果你覺得沒小孩的人也有資格分享自己的故事,卻一直什麼都不說,那你就是這問題的一部分。你跟那些一直維護潛規則的人一樣有罪。」
我再次眨眨眼,覺得有點茫然。那現在要怎麼樣?
「問問題啊!」蘇格拉底嘆了口氣,朝著那個有一頭俏麗鬈髮的女生點點頭,然後往椅背一靠。
你為什麼有權利問?
於是我忘卻了問問題的藝術,本著一點善意和希望自己能有所成長的心態,加上蘇格拉底的鼓勵,我決定要放手一試。革命就此開始,我心想。我要在所有小組討論中當沒有子女的女性的代表,更不用說還能為眼前這場討論增加一點深度。我鼓起勇氣,深呼吸後,看著俏麗鬈髮女的雙眼,打破了小組間短暫的沉默。「那,是妳決定不要生小孩的嗎?」緊接而來的是另一陣沉默,這次緊繃又尷尬。我感覺到小組中其他人都屏息以待。女子瞪視著我,像是凍結了一樣,然後咬牙切齒地說,「不。不是我決定的,不是。」其他人簡直可說是透過全體一起努力,把自己變成了透明人。以擠在一張小桌邊的六個人來說,這可不是容易的事,不過他們豁出去了。
我感覺到自己的神經瞬間斷光。「還真是個好建議啊,老兄!」我對蘇格拉底低聲怒道。「感謝你一點忙都沒幫到。」我的腦海裡警鈴大響。我到底該怎麼解救眼前的情況?
午餐時間已經結束了,我們一群人一起走回教室。我刻意配合俏麗鬈髮女的腳步,一邊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有的沒的,還有「我不是故意要讓妳難過,我只是覺得像這樣的討論,沒有小孩的人常常都會被跳過,真的太不公平了,而且我其實都會想要多聽一點大家的故事,而且因為我是真的對妳的經歷有興趣,所以想說就直接問妳……因為,嗯,大家的故事都應該要有人聽,加上畢竟我們來是要學實用哲學和如何提出更好的問題,還有……」
在我自己佈下的地雷場步履闌珊地前進的我,看來是沒有整理出一個有連貫性的想法。我那懦弱又羞愧的道歉,就這樣懸在空氣中。她冷冷地點點頭,意思是我可以不要再想了,然後惡狠狠地用氣聲說,「妳知道嗎,有人覺得自己有權利問這種問題,我覺得很奇怪。」她大步走向教室,留我一個人走在她的身後,舉步維艱。
那次的午餐互動、那場對話和那個問題在我腦海裡如此清晰,是因為其帶來的感受強烈無比—對被問問題的那個女子以及對問問題的我來說都是。
我覺得很羞愧,充滿罪惡感,但是我沒辦法確切說出原因。我的動機很單純:我想要與對方建立連結,創造更開放、更有意義的交談,讓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想超越膚淺的閒聊,像是「你做什麼工作啊?」「你住哪邊?」還有「你有幾個小孩?」。我本來是希望能夠讓每個人的故事都有一個位置,希望可以質疑那些在我眼中顯得不公平的潛規則。宛若現代蘇格拉底,我本來是希望能夠用好的問題、有價值的答案和更優質的對話來征服世界。
我真希望在那次命定的午餐休息時光裡的我已經知道了我現在知道的東西。希望我已經知道要問那樣的問題有其他辦法,不必把所有人都拖進壞情緒的泥沼裡。希望我已經知道要建立環境和條件,讓對話超越閒聊的程度,產生更深的共鳴是有可能的。希望我已經知道你可以問一些能夠建立連結的問題、能夠真的傳達真正想說的話的問題,即便有時候會帶來一些疼痛也一樣。
希望我已經知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問題,找到可以問問題又不會引發對方做出防禦回應的方法。希望我已經知道好的問題會引導出有利的答案,值得你全心的對待。
希望我已經知道對話一定有辦法平等地進行,重要的想法和信念都可以被看見,能讓對話深入主題的核心,分辨重要的內容和廢話—這方法讓大家能夠對自己的情緒和敏感負起責任。這個方法讓問題維持單純的身分:用來邀請大家深入一點。你可以自由決定拒絕或接受這個邀請。不需要令人如坐針氈的沉默、受傷的靈魂,也不必在一張小到沒有空間躲藏的午餐桌邊瘋狂祈禱自己變隱形。
從此你的名字可以叫「思考者」
如果當時的我就知道這些我現在知道的東西,我一定還是會問那個問題。但我會換個方式問。我會比照蘇格拉底的習慣,先取得對方的同意。我會改說,「我有興趣多聽一點,妳介意我繼續問嗎?」
但當時的我並不知道我現在知道的這些。當時的我盡可能地運用了手邊僅有的工具,最後換來了慘痛的經驗,一個從那之後便常常讓我深思與糾結的經驗。那次短暫經歷對我接下來幾年的人格成長、教育,甚至是這本書,都產生了顯著的貢獻。從那之後我便開始學習更多關於實用哲學的知識、問問題的藝術,以及進行有哲理、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我在荷蘭以及海外進修,並成立了一間公司,名為「思考者」,提供蘇格拉底式論述、批判性思考和提問的訓練課程和研習。那之後的每一天都是學習的過程。學習哪些東西可行,哪些不行。哪些條件能構成好的問題。學習能做什麼事情來增加討論的深度,讓大家開始動腦,一起用哲學思考,建立彼此間的連結。我也認識了蘇格拉底,現在的我把他當作英雄看待。他是我哲學世界裡的碧昂絲,而我絕對是忠實歌迷。
在培訓課程、哲學諮商和報告中,我親眼見過、感受過用不同的動機帶領談話所能造成的衝擊,以及如果能刻意培養蘇格拉底式的態度、努力調整問問題的方法,人與人之間的交談能夠改善多少。我目睹過在聽人交談、與人交談的時候,若能提防那些針對人性存在的陷阱,並且找到方法避免落入其中,對話與交談可以變得多有重量、有意義。
我體驗過把這個知識分享給其他人、幫助他們領悟這件事、取得技巧之後的快樂。隨著時間過去,我發現自己想要寫一本書,來幫助所有一心渴望能與人進行更有品質的交談卻苦無方法的人。讓我帶你踏上這條旅程吧。有了蘇格拉底當我們的嚮導,就可以來好好探索問問題的藝術。這樣一來,在所有場合、任何情況下,你都有辦法為交談內容帶來深度,也會知道如何透過問出該問的問題,就可以多了解身邊環境—對所有東西都了解更深一點。
Part1:為什麼我們都這麼拙於問出好問題?
「我一天到晚在問問題,是有什麼好學的?」
我熱愛我的工作。每次在派對上,或是在一些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場合,只要有人問我從事什麼職業,我都會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利用哲學方法,幫助別人問出更好的問題。我舉辦研習、課程、擔任個人教練,讓人了解自己的思緒過程,以及—」通常講到這裡,就會有人打斷。「你教人問問題?問問題有什麼難的?我整天都在問問題啊,要問問題為什麼還要上課?」
我心裡有一小部分想要賣弄一下,想要指出眼前這情況有多諷刺:一個認為問問題這件事並不需要他人協助的人,正巧就問出了一連串有引導性、花稍虛無且完全與開放性和好奇心大相逕庭的問題,都是難以視為真誠提問的問題。可是我沒有這麼做,而是將這樣的情況拿來提醒自己,講到如何提出真正的好問題這件事,還有多少人需要幫助,我們還有多少學習空間。
當然,這位派對上的朋友沒有錯。我們的確是整天都在問問題,或者說,至少我們認為如此。
就算你深信自己整天都在問問題,且應該也很擅長此事,然而事實通常有極大落差。實際上,你每次提問大概都只是在傳達一個帶問號的句子罷了。要做到這件事,的確不需要上課。另一件我們整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呼吸,但是好幾項研究都顯示其實人並不太擅長此事:大多數人的呼吸都太急促而淺短。問問題也是類似的狀況,我們潛意識的習慣會讓自己走偏。
我們的社會整體來說,並沒有將問問題這件事掌握得很好。一般人太常想到什麼就問什麼,這些問題往往不完整、帶有暗示性、花稍虛無、不合時宜,或者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你不覺得湯姆最近很易怒嗎?」「我怎麼會想換方法做啊?」「你這次又有什麼藉口?」「你不覺得麥可變胖了嗎?」「你覺得安娜不來是不是因為她會怕?還是她在生氣,還是說她……?」
每當有人拿問題或困境找上門來,我們通常不是先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而是立刻跳進解決問題的模式。「你有跟她談過嗎?」「我的諮商師很有用,對你一定也會有幫助的!」不然就是用建議把對方淹沒。「你知道你該怎麼做嗎?你應該……」「你現在應該要聯絡這些人。」或者是會用自己的經驗來蓋過對方的事件。「我也遇過一樣的事!不過我那次比較……」
我們通常會寧可讓對方相信我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而不是仔細檢視對方的觀點。一聽到他們的故事,馬上就先跟自己的生活建立連結,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對方想要告訴我們的事件上。我們的思緒早已往前衝,思考等對方說完後,自己要回答什麼話:「對,但是這情況我有完全不同的見解……」其實我們大可把時間花在好好地聆聽。
好消息是:「問出正確的問題」是一項可以習得的能力。問問題的能力也許是天生具備,但也是一個可以熟能生巧的技能。其實跟跳高有點像:理論上這是幾乎所有人類小時候都能做到的事,不過要是有認真思考方法,鍛鍊這個天生的能力,就能表現得更好。
「問題」就像是工具。用得對,就能讓你進入深度思考的討論之中,探索對方的觀點。你可以是一把細小的鑷子,或是粗重的鑽頭;可以低調如砂紙,或跟撬棍一樣直截了當。就跟使用工具的時候一樣,結果會隨著用法改變。我可以用鑿子在大石頭上一點一點雕刻出藝術品,但是如果我做過頭,在錯誤的方向施力過度,可能就會不小心把雕像的頭鑿斷。我也可以拿砂紙把整個表面都打磨光滑,但是如果我的施壓力道不夠,就看不出什麼改變。問問題也是這樣:透過技巧、有了目的,就能更有效益。
從純然的好奇心之中產生的問題,就是往對方踏出去的第一步。透過問出那樣的問題,你就像是在說:我希望能夠更接近一點、更了解你一點。這麼做必然會有風險,也會造成一點壓力。畢竟,對方很可能會直接叫你滾。這也是為何人會對於問出好問題這件事這麼猶豫的原因之一。
到底什麼是「問題」?
大家應該要花點時間想想何謂問題,更重要的是去想想,什麼東西不是問題?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假定大家都知道「問題」的意思,但是仔細想想,許多人問的問題其實根本都不是問題。而是假裝成問題的聲明、預想或假設。「你不覺得艾莉絲說得對嗎?」「你是想暗示……嗎?」「班說的有道理,不是嗎?」這些其實更像是打包在問題裡的意見,或者是一些需要被快速確認一下的假說。白紙黑字呈現的時候,也許就很清楚了。「哎,那當然不是真的問題啊!大家都看得出來!」但是從現在開始,仔細去聽,你會開始發現我們每天問的這些問題,其中有多少其實跟真誠的提問完全相反。
牛津英文字典對「問題」的定義是「語句的用詞或傳達的意思能從一個人身上引導出資訊」。雖然這個定義完全可以拿來解釋何謂問題—我可沒打算跟牛津英文字典作對啊!—卻沒有進一步提及這樣的語句可以怎樣操弄、語句背後的目的或對他人會產生的效果。從實用哲學的背景以及我們的重點,也就是如何問好問題這點來看,我做出了以下定義:
一個問題,就是一封邀請函。邀請對方思考、解釋、去蕪存菁、深入鑽研、提供資訊、調查、建立連結。
◎一個好的問題的建構會很清楚,具備開放、好奇的態度。
◎一個好的問題會把焦點留在對方和他們訴說的故事上頭。
◎一個好的問題會讓人開始思考。
◎一個好的問題會為接收的那一方消除干擾、帶來新的領悟或新視角。
◎一個好的問題,目的不是要給出建議、檢視假說、強加觀點、分享意見、提出建議或讓對方感覺到被批評或受困。
最後一點尤為重要。雖然這之中的差異似乎非常顯而易見,我們每天問的問題卻多落在這些範圍之外。我們都太常無意間、甚至在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問出以自我為中心點的問題。從自己的恐懼、感覺、想法、偏見和需求去問。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問題投射這些東西到其他人的故事之上。換句話說,我們問問題都只是要讓自己安心,而不是真的進一步詢問對方說話的內容。
就好像你跟摯友說自己和另一半大吵一架的事之後,他卻問你:「你想要離開他嗎?」或者像同事聽完你說去托斯卡尼的度假經驗後回你:「連續一個禮拜都是義大利麵和披薩,你不膩嗎?」還有聽完你說擔心母親健康每況愈下的事情之後,那個朋友回答你,「所以你去照顧她了嗎?會很辛苦喔。我自己這樣做過一段日子……」
所謂的爛問題並不存在?
你可能常聽到有人說爛問題不存在,概括來看,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全盤錯誤。通常這種問題會讓人毫無保留地高談闊論,這當然是好事,問題本來就不該憋在心裡。然而,很多立意良善的問題卻被用乏善可陳的言語架構而成。即便問題背後的意圖很實際,問問題的人的動機也無可挑剔,問題本身卻可能會完全錯過重點。王爾德曾寫下這樣的文字,「書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只有寫得好或寫得差的分別。」問問題也是這樣。世上沒有天生的好問題或爛問題,但是絕對有組織得好的問題跟組織得不好的問題,還有用得好或用得不好的問題。
我在這本書裡說到的「好的問題」,意思一定都是指誠懇、真摯,能夠鼓勵他人思考的問題。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目的都不是想要出力影響或改變事物的方向。沒有想要修復問題點或強加自己思考方式的意圖。一個好的問題一看就知道在問的情境中能夠產生作用,並符合其目的。
在這裡如果舉出確切的例子就失焦了:在某一個情境中能夠擊中目標的問題,在另一個情境中可能完全偏離核心。這次適合的做法,下次可能就行不通。在這場對話中的意圖與另一場對話的意圖各不相同,這也會決定問題的效益。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應證我自己下的定義:一個問題,就是一封邀請函。
有深度的對話是由什麼東西構成的?
在這本書裡面,我會跟各位談談有深度的對話:有真的內涵的對話,能夠觸及核心的對話。花點時間去思考一場好的、有深度的對話要包含什麼東西是值得的。一場好的對話不會乏善可陳,也不是只有一邊不斷訴說而已。好的對話不僅是兩個人各自把自己的意見列出來、交換奇聞軼事、閒聊,不是兩段獨白的重疊,或同時喋喋不休。
有深度的對話包含去探索另一人的經驗,進一步檢視想法、概念,和其中可以探討的問題,尤其是關於人性的觀念。把焦點放在另一人的經驗上這件事說易行難,若沒有刻意為之,我們很可能會變成太過熱情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經驗或觀點,忘了應該要先去深入了解另一人。一段有深度的談話應該是一種能夠激勵人且能共同進行的過程,讓兩人合力追求智慧。
雖然是一片好意,但我親愛的老奶奶聽到我扭傷腳的消息後說的話就沒有及格。「噢,小可憐,太慘了吧。格雷塔的姪女去年也是這樣。三個禮拜的時間直接作廢,沒辦法開車,沒辦法走路—完全一無是處。糟透了!真的是糟糕透頂!」
為什麼好的問題得來不易?
要改善問問題的能力,先明白自己為何不太擅長此事很重要。如果我想要當一個優秀的辯論家,我最好勤加練習。但是光只是練習並不能讓我達成目標,我還需要認識辯論中的陷阱,並且透過學會如何進行辯論以及建立強而有力的論點來掌握理論的內容。要成為一名更優秀的廚師,我得在廚房裡好好練習,了解如何結合不同的風味、氣味、質地和材料,並且研究為什麼使用某些組合、工具和技巧,得到的效果特別好。曾經親眼目睹自己做的巧克力舒芙蕾在烤箱裡烤到塌陷的人就會知道,認識陷阱、摸清可能會導致失敗的元素,有時候是最好的起點。
所以說,在我們開始練習「如何」問出好問題之前,要先停下來思考一下,為什麼好問題這麼難出現。一旦理解了為什麼大家常常在這個地方失敗,你就會發現自己也經常做出這些經典錯誤提問。光是認知到這點,就能讓你對於自己問問題的能力更加留心,也能幫助你閃避陷阱。不僅如此,很快地,你也會開始可以更注意身邊的日常對話與媒體傳播的內容,進而辨識許多在你要問出好問題的時候,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
我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蒐集了許多意見回饋,進行採訪,問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最重要的兩點分別為「是什麼東西讓你不願意問問題?」以及「你覺得一般人為什麼會不想問問題?」。透過我自己的研究、經驗、發現和結論,我把答案統整起來,整理出人無法問出好問題的六大原因:
1.人類天性:談論自己的感覺比問問題好多了。
2.害怕提問:提問有的時候是一種很恐怖的處境。
3.得分點:發表意見比提出問題更能令人印象深刻。
4.缺乏客觀性:我們的客觀的推理能力日漸衰退。
5.沒有耐性:我們認為問好問題只是在浪費時間。
6.缺乏能力:沒有人教過我們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