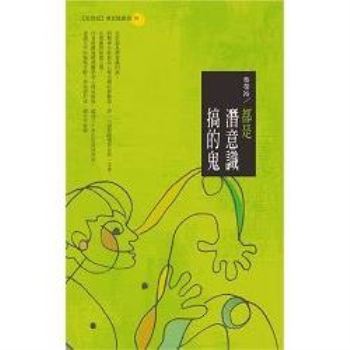<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經驗談>
第一章 開始治療也開始困擾?
幾個困擾很久的問題,怎麼開頭呢?
要怎麼開口呢?有人出現相同問題嗎?如果只是我自己的問題,那怎麼辦?這是令人多麼困擾的開始啊,有問題已經很困擾了,但是想要怎麼對別人說,又加重了一層麻煩和不安。
算了,算了吧,這太辛苦了。光想到治療就已經夠麻煩了,何必自己找麻煩呢。
如果這是一般被叫做個案的人,對於「有問題」時常出現的困擾,你也常這種感覺嗎?
然後,有一位被叫做精神科醫師的人,看過你後(或你看過醫師後),給你一個精神科診斷,除了開一些精神藥物給你,又善意地說,你需要心理治療。也許你會覺得明明有了一個藥袋的藥丸,就已經夠困擾你了,怎麼醫師又奉送一個叫做心理治療的東西,那是什麼啊?
「我真的需要心理治療嗎?這是什麼東西啊?」也許,這是你心中的疑惑。
你可能覺得被硬塞了禮物,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禮物(或多多少少知道內容是什麼),但是,這是精神科醫師的待客之道嗎?或者,你突然納悶加上一點點害怕,心想你的問題有那麼嚴重嗎?為什麼需要心理治療?有那麼嚴重嗎?
難道,精神科醫師認為你是裝病?不然,怎麼會建議你要做心理治療呢?你可能帶著這些還不敢開口,或不知如何開口的疑惑,跟著藥袋一起回家。回到家後,看著藥袋,開始想像精神科醫師可能不(或不夠)了解你,因此,你也對那袋藥物開始懷疑了起來。
「這些藥物真能解決我的問題嗎?」
常常,當這些疑問出現腦海時,就表示可能已經是肯定句了。以疑問句的方式出現,其實只是為了要保護精神科醫師,總不能連醫師也懷疑啊。雖然你可能覺得,自己是需要藥物,但是為什麼精神科醫師還說,需要心理治療呢?顯然的,精神科醫師看錯你的問題了,醫師開的藥物,真的有對症下藥嗎?
在這些看診後所出現的困擾裡,加上生活上原來就存在的困擾,在門診後你反而變成雙重困擾。你可能開始後悔,幹嘛看精神科?覺得看錯了精神科醫師。你覺得,你的問題是真的問題,不是心理問題,你覺得自己並沒有假裝有病,顯然地,你可能將精神科醫師說的「心理問題」,理解成是那是假裝出來的問題。這些情況當然不會是你來求診時的全部狀況,我只是試著想像,或者是從某些個案的說法,來描述這些可能的狀況。我只是先著重,來看門診後可能帶來的困擾。
說完你的困擾,我打算談談我的困擾,希望這不會增加你的困擾,畢竟此刻你是安靜地在自己的地方閱讀著這本書,而不是在精神科醫師的診療室裡。
如何談論我自己的經驗呢?又如何從這些經驗裡學到一些東西呢?
開始前,我卻必須先交待,何以要先談我的困擾,我到底想了多少,是否有足夠理由,從我自己的經驗與觀點,開始本書的第一章嗎?第一章是這麼重要的章節,談你的困擾後,我迫不及待要談我自己的困擾,是否會變成我將自己的主觀與困擾,強加在原本需要客觀討論的課題上?
何況探討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時,總是先從歷史上相關理念出發,或者先做個精神科診斷,將你放進一個(或幾個)診斷裡,好像需要這樣子,才能好好談以後要怎麼做的事情。
畢竟,這套專業已有很多很多理論可以著手,再舉出個案的例子來做補充,好像這麼做比較保險穩當些,比較可以避免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就科學來說,難免期待談論個案時要避免主觀的影響。
這些想法與顧慮,就變成了我著手第一章時的困難,讓我思考了至少一個禮拜(其實更久更久),是否直接切進主題,談論精神分析與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嗎?這意味著好像有一個很獨立客觀的東西,就在那裡等著我去寫。也許這種想法並沒有錯,但我卻覺得少了些什麼?
也許我就像你,要找精神科醫師(或心理治療師,或精神分析師)談談困擾,起初,好像有一個清楚明確的問題要處理,但是開始開口說話時,卻發現不知如何說起?可以說的事情太多了,要選擇哪個主題做為開始呢?
你要談大家認為客觀發生的事,或者從你主觀經驗出發呢?例如,你的父親如何拋棄你與母親,你卻始終覺得那是媽媽的過錯,周遭的人卻都不允許你這麼想,更不能這麼說。
後來,有我自己的決定。
我這個決定是很久以來,反覆思索後所做的決定,雖然最後決定是在瞬間發生。偏偏我無法一下子就很清楚地列出,一定是什麼因素,讓我下了決定。我的決定是,也將我的自身經驗同時做為這本書的主題。這個方法將遭遇的挑戰是,是否因此太過於個人化了,這是否違反了精神分析現有的一套客觀資料與理論呢?這的確讓我困擾,雖然我做了決定,但是做決定後,並不意味著心中猶豫和困擾就不見了。
我也假設你看過精神科醫師,談了一些自己的心事,出了診療室後卻更感到困擾的經驗,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首先,以我做為主詞開始談,就容易陷在被批評的自我中心裡,好像「我」這個主詞就代表了一切。因此我先就這個可能的批評,先做一些防衛,讓我可以比較安全地開始說話舖陳,我想要探索的主題,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是什麼?
這也是我的困擾,我思索這本書要寫給誰看?讀者是否會誤解我的說法?但是我試著冒險使用這種方式,來說我所經歷的故事,那是心中的故事,也是心理的故事,對我來說,心理故事是主觀的,但真實無比,比一隻鉛筆的存在還要真實。
例如,有人可能因為一隻硬梆梆的鉛筆而死掉,絕對有更多的人可能因為「沒有希望了」(沒有人摸得到它)的心理故事而軟扒扒地死掉。
第二章 你的問題很特殊嗎?
在第一章裡,我描述了一些可能困擾的問題。其實,決定以「我」這個主詞,來描述診療室裡所發生的事,也可能是源於第一章開頭所描述,你來求助診療時,所可能遭遇的複雜內在和外在的困境,包括,你如何談自己的問題,以及你說了後,精神科醫師或心理治療師會如何聽,是不是會批評你呢?
這涉及有個主詞的說話者--你,以及有個聽你說話的人--我。不論你要帶來的原來問題是什麼,好像都是這樣子開始的互動關係。你開始談你的問題,並期待你的心聲可以被聽到。
說話能被別人聽到是很重要的事,但你如何確定你的聲音有被聽到呢?而且真的有聽進去了?問題是,什麼才是:聆聽的人有聽進你的話呢?
你也許知道這很難定義?但是這麼多問題,哪有時間與心力,來想清楚這個定義呢?沒有時間與力氣來定義正潛在發生的一些想像,並不表示那些因素就不會有影響力。遺憾的是,這個了解還是以後的事,現在仍陷在一堆困惑裡。
雖然處在這些困惑裡,你仍努力地聚焦在被你視為症狀的內容裡,好像有一種隱隱的假設存在,你只要說清楚自己認定的症狀問題,並被精神科醫師或心理治療師確認後,那樣子,你的困惑就會不見了。果真會這樣順利發展嗎?你一點把握也沒有,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這是多難熬的時刻啊。
現在,在我的文字裡羅列這些困擾,可能還是隔著遙遠距離,在談論一件深層心理覺得受干擾與不安的事情。畢竟,你可能覺得自己的「問題」 (或你覺得是「症狀」,或精神科醫師也同意是「症狀」的東西。),被談出來後好像就開始變形了。
這是很可怕的感覺。通常無法用「困擾」這兩個字,就足以形容這種可怕。你不了解為什麼,說出自己的問題後,卻好像變得更模糊了,更令你不安。起初,你可能想要有更清楚具體的問題,可以馬上著手處理,因此不自主地逼迫自己,一定要儘快找出具體問題,不然,如果任由問題愈來愈模糊,你擔心那只會增加原本已有的困擾。
你可能覺得開始看精神科醫師門診後,這些困擾才開始出現。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感冒後如果早點去看醫師,拿了感冒藥回家,吃了藥,隔天,仍有可能出現前一天還沒來得及出現的症狀,如流鼻水或咳嗽。你不會認為,那是吃了感冒藥後,才出現的副作用,因為你充份知道那是感冒症狀的一部分。
但是,現在來精神科門診後你的經驗是,問題被自己說出來後,那些問題就好像長了腳,自己在外頭走動,偶爾還回頭來干擾你。你還差點要關起門(或者心門),想要將那些問題關在外頭,好像那些根本不是你的問題。
真的很奇怪,看了精神科醫師,談了些問題,有了診斷,也有了藥物,帶了這堆東西回家後,可能出現的一些後續想像與干擾,卻不像感冒症狀那般明確。因為一些「莫名的」感覺,可能隨時跑出來做怪,你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問題?
這些情況可能讓你覺得不安、痛苦,甚至說不清楚那是什麼?你的想像和擔心可能已被啟動而無法終止下來,雖然你希望趕緊忘記這些事情。但是,新愁加上舊愁,將你決定要看精神科前的所有想像,都被打破了(或者因為你的客氣,你只感覺有一點點解體了。)
你甚至開始後悔,幹嘛去看精神科,還被莫名建議要做心理治療?至於我,可能還在沈思著,你到底怎麼回事?你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來談自己的問題?我不是毫無經驗,但是我不能只仗著已有的經驗,過早對你的問題下結論。更讓我覺得困難的是,你可能還會想進一步追問,要多久你可以得到我的結論?我也想著,我可以對你的問題有所結論嗎,在這樣短暫的照面裡?
什麼是人生的結論?我有可能知道別人的人生的結論嗎?你可能會想,如果我不知道這些答案,那我配當個心理治療師嗎?
也許你的問題在別人身上出現過類似情況,我也聽過不少個案,談過相同或類似的問題。但是我的經驗,已經讓我無法認為你的問題跟別人都一樣,例如,都是憂鬱,這是一個多麼好的說詞,表面上好像可以解釋很多問題,而且迎合當代人對於很多周遭問題的解釋方式。
如果堅持因為你是你,他們是他們,因此你的問題不會跟別人完全一樣,因此針對你,我假設要有不同的想法,想要多了解屬於你個人特有的問題,或你說問題的特有方式是否有什麼個別意義?這些假設可能都跟你從小生長的環境有關。雖然,你也隱微地表示,希望我會用最不一樣的角度,看你這些很個人、很特別且與別人不同的問題。
但是愈想把你當做是與別人不同的人,不是和他人有相同症狀的一群「症狀人」,被如此看待的經驗所帶來的也常不是愉快的。這裡所謂的不愉快感受,是指何以無法很快地找出一個自己相信的說法,並且能夠馬上以這種說法做為結論?
畢竟,這種有很多可能原因的想像,所帶來的不確定感覺,就是一種不愉快的感受。你跟我可能都會沈陷在,希望趕緊有個答案的急切心情,而這種急切心情將會影響我的判斷,例如,可能為了盡快有答案,藉此得到方向感和確定感,卻忽略了問題的複雜度。
結果,你跟我好像都很努力,急切地想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以便可以有更快的介入方式,但卻可能為了求快而忽略潛在的一些重要問題。所謂潛在問題,是指不容易被發現的問題,我卻不知道你有多少耐心,可以忍受「有某種潛在問題因素影響著你」的說法?就在這些想法裡,繞來繞去,加上當我愈堅持(這需要堅持才做得到):將你當做是特殊的人,與別人不同的人。這個想法也同時困擾我。我的堅持,只是替自己帶來麻煩。如果我輕易假設,你就跟別人一樣啊,別人的解決方式也可以輕易地搬到你身上,這樣子,問題好像就「容易」些了吧,我的困擾也就減少很多了。
雖然這種「容易」,可能沒有真正了解你,但是,有部分的我卻多麼希望,就把你當做像其他人那樣,給你一般制式的說法或建議。這樣子,我會覺得好過些?難道,我堅持你有所不同的特殊性,只是為了找自己或找你麻煩嗎?
< 隨筆>
靜物:黃玫瑰
其實,它談不上是絕美的風景。
而且現在,我還不知道,當時,如果與探頭出來向外看的女主人,打個招呼,事情會變得什麼樣。甚至,記不起來,女主人的臉色怎麼樣?微笑,或者傳言中的,英國人拘謹內斂?三月的倫敦,依然冷意追隨著風,加上一些些毛毛雨。
這並不是說,我已經說服自己,當時應該要與那女主人打招呼。或者,停下來和她聊聊倫敦的天氣。畢竟,我覺得這種結局,卻是更貼近我的倫敦。我不在意,倫敦有多真實,我更在意,倫敦在我心中的真實。我始終帶著不確定的謎團,等待下一次的謎樣,那種淡淡透光些微的黃。倫敦已不再如當年,傳說多霧,但迷霧般透著光的路旁草皮,仍有歷史耳語漫遊,傳遞著埋在草地裡的球莖,已經就要出頭了。
這就是我看見的倫敦,心中的第二故鄉,卻總是近鄉情怯。尤其是冬天時,穿著土耳其黃的羊毛長大衣,包裹著身體,走在隨處可見神木般的楓樹,就在觸手可摸到的道路旁,逃回到自己的溫暖。如果有人問我,倫敦是怎麼樣的城市?我一定會想很久,而且每次答案不同,此刻,我的回答會是:我的膽怯加上溫暖,還有黃玫瑰。
我相信,很難有人了解這句話,因此,我需要很多的字句,來舖陳倫敦,讓古早時候,馬車走的道路,適於我的腳步。因此,我不會修改我的回答,而是持續增添一些些黃,或者加上些許的透光。我覺得,好像在偷取些什麼。是的,我必須承認,我一直在走路與搜尋,心想,得帶些什麼回到台灣。儘管,只是拿著相機,最簡單結構的機器,捕捉花瓶裡的黃玫瑰花,以及千年來複雜的心思。靜物畫般的黃玫瑰,當有人從房門裡,探頭出來,她的一眼,卻讓我變成盗取風景的人。如果,普羅米修斯從天庭盗取火種,傳播到人間之前,途中曾被宙斯撞見,是否他仍會這麼做?
後續的十幾天,每當我路過相同地方時,仍是先準備好相機,待走過那面窗戶時,我隨即按下兩張相片。然後,若無其事地,我往地鐵站的方向走。那是每天必經的路,為了避免心情過於沈重,照完相後,我即不再回頭。
為了避免看見那女主人的眼神,撞見我忍不住想照相,守住她家窗戶的風景。
其實,就只是深藍色並有白色點的花瓶,裝有一束黃色的玫瑰花。印象裡,第一天是粉紅玫瑰。我以為印象錯誤,後來搜尋隨意照的相片,確定前一天是粉紅色的玫瑰花。花瓶擺在窗台上,白色薄紗窗簾,刻意地從底下兩邊往旁拉,讓窗簾形成八字型,讓花瓶與花,就在八字型裡。窗戶是在地下室,經過路旁時,只要稍低頭即可看見它。有著主人經心刻意的佈置,也有著路人經心刻意的長歌。
後來,我在相片裡,比對不同天的花朵,是否曾有凋萎,也同時找尋再一次的別離,是否讓我死心了。只因為我相信,在我死心之前,我會一直問自己:「是誰還在徬徨呢?滿街已張貼了春天的花朵。」
回到台北後,數度到建國花市,尋找黃玫瑰。終於找到了,卻怎麼擺都覺得不太對味。我是應該困惑,絕沒有理由相信,能夠找回那種感受,只是,某種叫做不死心的心情,讓我來來回回倫敦,也來回替那窗台上的黃玫瑰照相。
我重複地從二十二張相片裡,探勘人類學家的視野,依照些微不同的角度,讚嘆或者靜默,並與鏡頭的倍數接近程度,接近或疏遠,數數共有多少朵黃玫瑰?應該有十六朵花吧。我保有了相片,但我確信,仍然不了解倫敦,也不了解自己。我已不勉強多了解自己了,這花了我很多年了吧,只想要在散步的時候,捕捉我的城市想像,尤其是走過有泥土的地方。我想在倫敦找自己,遺失的部分卻在台北街頭。
但我確定,那是我的黃玫瑰,淡淡的黃有著透光的性格,卻不是梵谷的向日葵。我提醒自己,不要過於急切,臣服於早熟的風向;不要過於相信,那些宣稱已經找到自己的人;不要過於認定,流浪是種浪漫。
我知道,那一天,我會回頭,再度描寫那束黃玫瑰。因為我已經決定,自私的,不採用它的意見,也不讓它凋零。我還想再問自己:「是誰還在徬徨呢?不死心容易凋謝,或者,認命容易凋敝?」
第一章 開始治療也開始困擾?
幾個困擾很久的問題,怎麼開頭呢?
要怎麼開口呢?有人出現相同問題嗎?如果只是我自己的問題,那怎麼辦?這是令人多麼困擾的開始啊,有問題已經很困擾了,但是想要怎麼對別人說,又加重了一層麻煩和不安。
算了,算了吧,這太辛苦了。光想到治療就已經夠麻煩了,何必自己找麻煩呢。
如果這是一般被叫做個案的人,對於「有問題」時常出現的困擾,你也常這種感覺嗎?
然後,有一位被叫做精神科醫師的人,看過你後(或你看過醫師後),給你一個精神科診斷,除了開一些精神藥物給你,又善意地說,你需要心理治療。也許你會覺得明明有了一個藥袋的藥丸,就已經夠困擾你了,怎麼醫師又奉送一個叫做心理治療的東西,那是什麼啊?
「我真的需要心理治療嗎?這是什麼東西啊?」也許,這是你心中的疑惑。
你可能覺得被硬塞了禮物,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禮物(或多多少少知道內容是什麼),但是,這是精神科醫師的待客之道嗎?或者,你突然納悶加上一點點害怕,心想你的問題有那麼嚴重嗎?為什麼需要心理治療?有那麼嚴重嗎?
難道,精神科醫師認為你是裝病?不然,怎麼會建議你要做心理治療呢?你可能帶著這些還不敢開口,或不知如何開口的疑惑,跟著藥袋一起回家。回到家後,看著藥袋,開始想像精神科醫師可能不(或不夠)了解你,因此,你也對那袋藥物開始懷疑了起來。
「這些藥物真能解決我的問題嗎?」
常常,當這些疑問出現腦海時,就表示可能已經是肯定句了。以疑問句的方式出現,其實只是為了要保護精神科醫師,總不能連醫師也懷疑啊。雖然你可能覺得,自己是需要藥物,但是為什麼精神科醫師還說,需要心理治療呢?顯然的,精神科醫師看錯你的問題了,醫師開的藥物,真的有對症下藥嗎?
在這些看診後所出現的困擾裡,加上生活上原來就存在的困擾,在門診後你反而變成雙重困擾。你可能開始後悔,幹嘛看精神科?覺得看錯了精神科醫師。你覺得,你的問題是真的問題,不是心理問題,你覺得自己並沒有假裝有病,顯然地,你可能將精神科醫師說的「心理問題」,理解成是那是假裝出來的問題。這些情況當然不會是你來求診時的全部狀況,我只是試著想像,或者是從某些個案的說法,來描述這些可能的狀況。我只是先著重,來看門診後可能帶來的困擾。
說完你的困擾,我打算談談我的困擾,希望這不會增加你的困擾,畢竟此刻你是安靜地在自己的地方閱讀著這本書,而不是在精神科醫師的診療室裡。
如何談論我自己的經驗呢?又如何從這些經驗裡學到一些東西呢?
開始前,我卻必須先交待,何以要先談我的困擾,我到底想了多少,是否有足夠理由,從我自己的經驗與觀點,開始本書的第一章嗎?第一章是這麼重要的章節,談你的困擾後,我迫不及待要談我自己的困擾,是否會變成我將自己的主觀與困擾,強加在原本需要客觀討論的課題上?
何況探討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時,總是先從歷史上相關理念出發,或者先做個精神科診斷,將你放進一個(或幾個)診斷裡,好像需要這樣子,才能好好談以後要怎麼做的事情。
畢竟,這套專業已有很多很多理論可以著手,再舉出個案的例子來做補充,好像這麼做比較保險穩當些,比較可以避免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就科學來說,難免期待談論個案時要避免主觀的影響。
這些想法與顧慮,就變成了我著手第一章時的困難,讓我思考了至少一個禮拜(其實更久更久),是否直接切進主題,談論精神分析與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嗎?這意味著好像有一個很獨立客觀的東西,就在那裡等著我去寫。也許這種想法並沒有錯,但我卻覺得少了些什麼?
也許我就像你,要找精神科醫師(或心理治療師,或精神分析師)談談困擾,起初,好像有一個清楚明確的問題要處理,但是開始開口說話時,卻發現不知如何說起?可以說的事情太多了,要選擇哪個主題做為開始呢?
你要談大家認為客觀發生的事,或者從你主觀經驗出發呢?例如,你的父親如何拋棄你與母親,你卻始終覺得那是媽媽的過錯,周遭的人卻都不允許你這麼想,更不能這麼說。
後來,有我自己的決定。
我這個決定是很久以來,反覆思索後所做的決定,雖然最後決定是在瞬間發生。偏偏我無法一下子就很清楚地列出,一定是什麼因素,讓我下了決定。我的決定是,也將我的自身經驗同時做為這本書的主題。這個方法將遭遇的挑戰是,是否因此太過於個人化了,這是否違反了精神分析現有的一套客觀資料與理論呢?這的確讓我困擾,雖然我做了決定,但是做決定後,並不意味著心中猶豫和困擾就不見了。
我也假設你看過精神科醫師,談了一些自己的心事,出了診療室後卻更感到困擾的經驗,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首先,以我做為主詞開始談,就容易陷在被批評的自我中心裡,好像「我」這個主詞就代表了一切。因此我先就這個可能的批評,先做一些防衛,讓我可以比較安全地開始說話舖陳,我想要探索的主題,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是什麼?
這也是我的困擾,我思索這本書要寫給誰看?讀者是否會誤解我的說法?但是我試著冒險使用這種方式,來說我所經歷的故事,那是心中的故事,也是心理的故事,對我來說,心理故事是主觀的,但真實無比,比一隻鉛筆的存在還要真實。
例如,有人可能因為一隻硬梆梆的鉛筆而死掉,絕對有更多的人可能因為「沒有希望了」(沒有人摸得到它)的心理故事而軟扒扒地死掉。
第二章 你的問題很特殊嗎?
在第一章裡,我描述了一些可能困擾的問題。其實,決定以「我」這個主詞,來描述診療室裡所發生的事,也可能是源於第一章開頭所描述,你來求助診療時,所可能遭遇的複雜內在和外在的困境,包括,你如何談自己的問題,以及你說了後,精神科醫師或心理治療師會如何聽,是不是會批評你呢?
這涉及有個主詞的說話者--你,以及有個聽你說話的人--我。不論你要帶來的原來問題是什麼,好像都是這樣子開始的互動關係。你開始談你的問題,並期待你的心聲可以被聽到。
說話能被別人聽到是很重要的事,但你如何確定你的聲音有被聽到呢?而且真的有聽進去了?問題是,什麼才是:聆聽的人有聽進你的話呢?
你也許知道這很難定義?但是這麼多問題,哪有時間與心力,來想清楚這個定義呢?沒有時間與力氣來定義正潛在發生的一些想像,並不表示那些因素就不會有影響力。遺憾的是,這個了解還是以後的事,現在仍陷在一堆困惑裡。
雖然處在這些困惑裡,你仍努力地聚焦在被你視為症狀的內容裡,好像有一種隱隱的假設存在,你只要說清楚自己認定的症狀問題,並被精神科醫師或心理治療師確認後,那樣子,你的困惑就會不見了。果真會這樣順利發展嗎?你一點把握也沒有,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這是多難熬的時刻啊。
現在,在我的文字裡羅列這些困擾,可能還是隔著遙遠距離,在談論一件深層心理覺得受干擾與不安的事情。畢竟,你可能覺得自己的「問題」 (或你覺得是「症狀」,或精神科醫師也同意是「症狀」的東西。),被談出來後好像就開始變形了。
這是很可怕的感覺。通常無法用「困擾」這兩個字,就足以形容這種可怕。你不了解為什麼,說出自己的問題後,卻好像變得更模糊了,更令你不安。起初,你可能想要有更清楚具體的問題,可以馬上著手處理,因此不自主地逼迫自己,一定要儘快找出具體問題,不然,如果任由問題愈來愈模糊,你擔心那只會增加原本已有的困擾。
你可能覺得開始看精神科醫師門診後,這些困擾才開始出現。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感冒後如果早點去看醫師,拿了感冒藥回家,吃了藥,隔天,仍有可能出現前一天還沒來得及出現的症狀,如流鼻水或咳嗽。你不會認為,那是吃了感冒藥後,才出現的副作用,因為你充份知道那是感冒症狀的一部分。
但是,現在來精神科門診後你的經驗是,問題被自己說出來後,那些問題就好像長了腳,自己在外頭走動,偶爾還回頭來干擾你。你還差點要關起門(或者心門),想要將那些問題關在外頭,好像那些根本不是你的問題。
真的很奇怪,看了精神科醫師,談了些問題,有了診斷,也有了藥物,帶了這堆東西回家後,可能出現的一些後續想像與干擾,卻不像感冒症狀那般明確。因為一些「莫名的」感覺,可能隨時跑出來做怪,你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問題?
這些情況可能讓你覺得不安、痛苦,甚至說不清楚那是什麼?你的想像和擔心可能已被啟動而無法終止下來,雖然你希望趕緊忘記這些事情。但是,新愁加上舊愁,將你決定要看精神科前的所有想像,都被打破了(或者因為你的客氣,你只感覺有一點點解體了。)
你甚至開始後悔,幹嘛去看精神科,還被莫名建議要做心理治療?至於我,可能還在沈思著,你到底怎麼回事?你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來談自己的問題?我不是毫無經驗,但是我不能只仗著已有的經驗,過早對你的問題下結論。更讓我覺得困難的是,你可能還會想進一步追問,要多久你可以得到我的結論?我也想著,我可以對你的問題有所結論嗎,在這樣短暫的照面裡?
什麼是人生的結論?我有可能知道別人的人生的結論嗎?你可能會想,如果我不知道這些答案,那我配當個心理治療師嗎?
也許你的問題在別人身上出現過類似情況,我也聽過不少個案,談過相同或類似的問題。但是我的經驗,已經讓我無法認為你的問題跟別人都一樣,例如,都是憂鬱,這是一個多麼好的說詞,表面上好像可以解釋很多問題,而且迎合當代人對於很多周遭問題的解釋方式。
如果堅持因為你是你,他們是他們,因此你的問題不會跟別人完全一樣,因此針對你,我假設要有不同的想法,想要多了解屬於你個人特有的問題,或你說問題的特有方式是否有什麼個別意義?這些假設可能都跟你從小生長的環境有關。雖然,你也隱微地表示,希望我會用最不一樣的角度,看你這些很個人、很特別且與別人不同的問題。
但是愈想把你當做是與別人不同的人,不是和他人有相同症狀的一群「症狀人」,被如此看待的經驗所帶來的也常不是愉快的。這裡所謂的不愉快感受,是指何以無法很快地找出一個自己相信的說法,並且能夠馬上以這種說法做為結論?
畢竟,這種有很多可能原因的想像,所帶來的不確定感覺,就是一種不愉快的感受。你跟我可能都會沈陷在,希望趕緊有個答案的急切心情,而這種急切心情將會影響我的判斷,例如,可能為了盡快有答案,藉此得到方向感和確定感,卻忽略了問題的複雜度。
結果,你跟我好像都很努力,急切地想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以便可以有更快的介入方式,但卻可能為了求快而忽略潛在的一些重要問題。所謂潛在問題,是指不容易被發現的問題,我卻不知道你有多少耐心,可以忍受「有某種潛在問題因素影響著你」的說法?就在這些想法裡,繞來繞去,加上當我愈堅持(這需要堅持才做得到):將你當做是特殊的人,與別人不同的人。這個想法也同時困擾我。我的堅持,只是替自己帶來麻煩。如果我輕易假設,你就跟別人一樣啊,別人的解決方式也可以輕易地搬到你身上,這樣子,問題好像就「容易」些了吧,我的困擾也就減少很多了。
雖然這種「容易」,可能沒有真正了解你,但是,有部分的我卻多麼希望,就把你當做像其他人那樣,給你一般制式的說法或建議。這樣子,我會覺得好過些?難道,我堅持你有所不同的特殊性,只是為了找自己或找你麻煩嗎?
< 隨筆>
靜物:黃玫瑰
其實,它談不上是絕美的風景。
而且現在,我還不知道,當時,如果與探頭出來向外看的女主人,打個招呼,事情會變得什麼樣。甚至,記不起來,女主人的臉色怎麼樣?微笑,或者傳言中的,英國人拘謹內斂?三月的倫敦,依然冷意追隨著風,加上一些些毛毛雨。
這並不是說,我已經說服自己,當時應該要與那女主人打招呼。或者,停下來和她聊聊倫敦的天氣。畢竟,我覺得這種結局,卻是更貼近我的倫敦。我不在意,倫敦有多真實,我更在意,倫敦在我心中的真實。我始終帶著不確定的謎團,等待下一次的謎樣,那種淡淡透光些微的黃。倫敦已不再如當年,傳說多霧,但迷霧般透著光的路旁草皮,仍有歷史耳語漫遊,傳遞著埋在草地裡的球莖,已經就要出頭了。
這就是我看見的倫敦,心中的第二故鄉,卻總是近鄉情怯。尤其是冬天時,穿著土耳其黃的羊毛長大衣,包裹著身體,走在隨處可見神木般的楓樹,就在觸手可摸到的道路旁,逃回到自己的溫暖。如果有人問我,倫敦是怎麼樣的城市?我一定會想很久,而且每次答案不同,此刻,我的回答會是:我的膽怯加上溫暖,還有黃玫瑰。
我相信,很難有人了解這句話,因此,我需要很多的字句,來舖陳倫敦,讓古早時候,馬車走的道路,適於我的腳步。因此,我不會修改我的回答,而是持續增添一些些黃,或者加上些許的透光。我覺得,好像在偷取些什麼。是的,我必須承認,我一直在走路與搜尋,心想,得帶些什麼回到台灣。儘管,只是拿著相機,最簡單結構的機器,捕捉花瓶裡的黃玫瑰花,以及千年來複雜的心思。靜物畫般的黃玫瑰,當有人從房門裡,探頭出來,她的一眼,卻讓我變成盗取風景的人。如果,普羅米修斯從天庭盗取火種,傳播到人間之前,途中曾被宙斯撞見,是否他仍會這麼做?
後續的十幾天,每當我路過相同地方時,仍是先準備好相機,待走過那面窗戶時,我隨即按下兩張相片。然後,若無其事地,我往地鐵站的方向走。那是每天必經的路,為了避免心情過於沈重,照完相後,我即不再回頭。
為了避免看見那女主人的眼神,撞見我忍不住想照相,守住她家窗戶的風景。
其實,就只是深藍色並有白色點的花瓶,裝有一束黃色的玫瑰花。印象裡,第一天是粉紅玫瑰。我以為印象錯誤,後來搜尋隨意照的相片,確定前一天是粉紅色的玫瑰花。花瓶擺在窗台上,白色薄紗窗簾,刻意地從底下兩邊往旁拉,讓窗簾形成八字型,讓花瓶與花,就在八字型裡。窗戶是在地下室,經過路旁時,只要稍低頭即可看見它。有著主人經心刻意的佈置,也有著路人經心刻意的長歌。
後來,我在相片裡,比對不同天的花朵,是否曾有凋萎,也同時找尋再一次的別離,是否讓我死心了。只因為我相信,在我死心之前,我會一直問自己:「是誰還在徬徨呢?滿街已張貼了春天的花朵。」
回到台北後,數度到建國花市,尋找黃玫瑰。終於找到了,卻怎麼擺都覺得不太對味。我是應該困惑,絕沒有理由相信,能夠找回那種感受,只是,某種叫做不死心的心情,讓我來來回回倫敦,也來回替那窗台上的黃玫瑰照相。
我重複地從二十二張相片裡,探勘人類學家的視野,依照些微不同的角度,讚嘆或者靜默,並與鏡頭的倍數接近程度,接近或疏遠,數數共有多少朵黃玫瑰?應該有十六朵花吧。我保有了相片,但我確信,仍然不了解倫敦,也不了解自己。我已不勉強多了解自己了,這花了我很多年了吧,只想要在散步的時候,捕捉我的城市想像,尤其是走過有泥土的地方。我想在倫敦找自己,遺失的部分卻在台北街頭。
但我確定,那是我的黃玫瑰,淡淡的黃有著透光的性格,卻不是梵谷的向日葵。我提醒自己,不要過於急切,臣服於早熟的風向;不要過於相信,那些宣稱已經找到自己的人;不要過於認定,流浪是種浪漫。
我知道,那一天,我會回頭,再度描寫那束黃玫瑰。因為我已經決定,自私的,不採用它的意見,也不讓它凋零。我還想再問自己:「是誰還在徬徨呢?不死心容易凋謝,或者,認命容易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