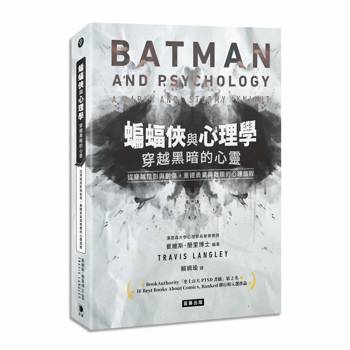第1章 蒙面頭罩之下:蝙蝠俠是誰?
扮演第一代蝙蝠俠的亞當.威斯特曾經問我,是否認為蝙蝠俠很瘋狂。《蝙蝠俠與心理學:穿越黑暗的心靈》是我的答案。
自1939年《偵探漫畫》(Detective Comics)第27期首度登場以來,蝙蝠俠隨時間透過眾多媒體讓全球數十億人感到興奮激動。世界上最著名的三位漫畫英雄——蝙蝠、蜘蛛和來自另一星球的人,組成孤兒三重奏。而他,是那個夜間工作、需要一輛車載他入城、最致命的人。他是沒有超能力的超級英雄,我們最容易相信他可能棲居在我們的世界。他的秘密身分是三人之中最奇妙的,一個迷人英俊的億萬富翁住在一個巨大洞穴上方的豪宅裡,而其他兩人是平庸的報社職員,然而,巨富有助於我們接受他的蒙面身分,感覺更為真實。那些很棒的玩具,總要有人買單。現實世界中,人們知道的超級富豪比超能力者多。蝙蝠俠是成年人也能想像存在現實生活的英雄,較不令人懷疑。儘管布魯斯.韋恩擁有極少人享有的機會,但他來自一座城市,而非神話中的島嶼或遙遠世界,他透過訓練和努力將自己打造為英雄——不需要輻射、秘密配方或魔法戒指。他的出身悲慘,而且故事殘酷可信。它觸及了我們童年時期最原始的恐懼:一場家庭郊遊,一名搶劫犯在他眼前槍殺了他的父母,結果釀成悲劇。
他的電影列名歷史上最高票房電影之中,這個角色出演的動畫、真人版電影與電視影集比任何其他漫畫英雄都多。為什麼這名一身沉鬱的自發義警、飽受折磨的靈魂,出沒街頭找麻煩、穿著像吸血鬼,卻讓我們如此著迷?他的故事充滿了敵人與他自身的雙重性(duality)和強迫意念(obsession)。他的敵人反映且扭曲了他自己的各個方面。他自鳴得意,他詭秘狡猾,他是如此令人懼怕,以至於當他進入一個房間,儘管裡頭滿是會飛、會讀心術、會施咒或跑步比光快的人,還是這些人被他嚇倒——這就是我們愛的部分。他強而有力,聰明機警,不受財務限制或其他任何人的規則束縛,將我們深切的願望化為現實。我們想要嚇退所有生命中的霸凌者,而蝙蝠俠正是這個部分。
在創作明亮耀眼的超人時,傑瑞 .西格爾(Jerry Siegel)和喬 .舒斯特(Joe Shuster)靈光一閃。一個不眠之夜,傑瑞構思出「類似《聖經》中大力士參孫(Samson)、希臘神話英雄海克力斯(Hercules)的角色,把我聽說過的所有強者的形象合而為一,仍有過之而無不及。」傑瑞和他的繪師朋友喬從古往今來的神聖英雄中汲取靈感,創作出不僅僅是超人本人,正好還有變裝超級英雄的概念。他們製作迷因。他們開創現代神話。超人立即引起轟動。首位披風英雄成功之後,出版商們爭先恐後地炮製更多英雄。年輕漫畫家鮑勃.凱恩為超人的出版商打造了下一個變裝社會改革家。搶在所有即將推出的超人模仿作品之前,凱恩與合作者比爾.芬格不是從啟發傑瑞和喬的超人形象中汲取靈感,而是從無聲電影和低俗小說的暗黑神秘人物中汲取靈感,最著名的是蒙面俠蘇洛(Zorro)和魅影奇俠( the Shadow),儘管他們卓爾不凡,但仍是人。超人從地球的太陽汲取力量,而蝙蝠俠則在城市的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力量。*傑瑞和喬考量的是明亮與不可能;鮑勃和比爾則是藉由添加另一面向——黑暗與難以置信的可能——來擴展迷因。
今天,所有人在讀第一個蝙蝠俠故事時,都已知道那個撲朔迷離的自發治安維持者,最終落在一名百無聊賴的富家子弟手裡,直到漫畫的最後一格,他把時間全花在作為戈登局長(Commissioner Gordon)的陪襯角色,成為戈登能夠表達想法的參謀對象——就像我們會對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經典小說《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摸不著頭腦,因為搞不清楚舉止溫文的傑寇爾醫生(Dr. Jekyll)與缺乏教養的海德先生(Mr. Hyde)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面具後面那個人的名字和面孔,但是什麼潛藏在面孔的後面?比起蝙蝠俠的蒙面頭罩、布魯斯.韋恩的外表或他選用的任何名字,「蝙蝠俠是誰?」(Who is Batman?)這個問題更深刻。一個「誰」(who)的問題包含許多「為何」(why):為何他要打擊犯罪?為何以自發義警的身分?為何面具、蝙蝠和未成年夥伴?為何與他應當關押起來的「壞女孩」發展出最親密的關係?為何他不殺掉那個殺人如麻的綠髮小丑?
蝙蝠俠精神失常嗎?(譯註:英文原文have bats in his belfry[他的鐘塔內有蝙蝠]是一種暗喻。用語中的belfry是教堂頂部的鐘塔,常為蝙蝠棲息的地方,蝙蝠受鐘聲影響,會到處亂飛,以belfry比喻人的腦袋,have bats in his belfry意即他的行為乖張、精神失常。)
第2章 哪個蝙蝠俠?
「我有點擔心。我曾在2016、2012、2008、2005、1997、1995、1992、1989年看過你經歷類似的階段,還有1966年那個詭異的階段。你想談一談嗎?」
——《樂高蝙蝠俠電影》(2017年電影)中的阿福(Alfred,由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配音)
我們在分析角色之前,必須先界定變數。在探討「誰」(who)及所有其「為何」(why)的問題之前,首先必須考量指的是「哪個」(which)蝙蝠俠。
儘管蝙蝠俠源於漫畫人物且一直存在,但我們大多數人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電視上。從我還是個蹣跚學步的幼童時,亞當.威斯特便是活生生的蝙蝠俠。我也在週六早上看披風戰士的卡通,讓蝙蝠俠和羅賓的玩具與開著綠色塑膠廂型車的小丑鬥著玩,同時穿著毛巾披風、戴著黑色手套,把自己扮成蝙蝠俠。週六早上,由歐蘭.索爾(Olan Soule)配音、一個較嚴肅(但仍然積極樂觀)的蝙蝠俠與超人、神力女超人和水行俠(Aquaman)組成一個小型的正義聯盟,即最早的《超級英雄》(Super Friends)。在我終於有空細讀漫畫書較黑暗的故事時,這些電視版本曾經帶給我一些大驚奇。
下一世代,我的兒子主要透過《蝙蝠俠:動畫影集》認識蝙蝠俠。大兒子第一次看這節目是在八歲,他原已從其他媒體知道蝙蝠俠,但記憶是個有趣的東西,這部卡通透過時間將記憶回調,讓卡通追溯起來像是最先進入記憶。卡通成為他記憶中最早的蝙蝠俠,儘管他知道應該並非如此。小兒子發現蝙蝠俠的過程比較像我,身為學齡前兒童,他不為蝙蝠俠並非真正存在的事實所困擾,這可能是為何在兩個男孩中,他更迷蝙蝠俠。一開始,他著迷的是蝙蝠俠玩具。不過,在他小腦袋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對他來說的蝙蝠俠最初記憶,則是電視剪輯版《蝙蝠俠大顯神威》(Batman Returns)的蝙蝠車,能夠分解部分車身而迅速穿梭狹窄巷弄。他先前對玩具車的熱情就鎖定在那部車上。蝙蝠俠讓他感到驚奇,蝙蝠俠的玩具也是。
銀幕╱螢幕史
1940年代電影系列
蝙蝠俠的銀幕史始於哥倫比亞影業(Columbia Pictures)的影集《蝙蝠俠》(Batman,1943),由路易斯.威爾森(Lewis Wilson)和道格拉斯.克羅夫特(Douglas Croft)主演,他們是第一次真人版出演的蝙蝠俠和羅賓,該角色首度出現於漫畫書是四年前。在那個年代,對許多人來說,一個典型的週六意味著坐在地方戲院的座位上共享群體經驗,看一部完整的劇情長片、新聞短片、卡通、由「三個臭皮匠」(Three Stooges)或「小搗蛋」(Our Gang)主演的喜劇短片,以及電影系列的至少一集,《蝙蝠俠》是新事物,並非他們生平全都知道。歷經十五週一連串的高潮迭起,他們看到活力雙雄(Dynamic Duo)大戰美國惡棍、日本特工提托.達卡博士(Dr. Tito Daka)以及遭達卡控制心智的「喪屍」(zombie)奴隸。
恐懼是蝙蝠俠故事中反覆出現的元素,但有一種恐懼特別形塑了這部電影系列的創作——仇外心理(xenophobia),即對外國人或陌生人的過度恐懼。二戰期間,反亞裔情緒對美國來說並不陌生,這部電影系列中對日本人的刻畫與描述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該電影系列的旁白告訴我們:「自從明智的政府圍捕賊眉鼠眼的日本人後1,城市小東京區的建築物已經空置。這指涉的是一九四二年日本襲擊珍珠港後,美國政府將逾十萬名日裔美國公民和居民重新安置與收容至戰時再安置營(War Relocation Camp)。這樣的再安置未曾發生在任何德裔或義裔人士身上,只有對祖先來自軸心國聯盟(Axis alliance)亞洲成員的人才如此。
間諜達卡體現的是許多感到害怕的日本外僑仍然潛伏在美國,且以某種方式避免遭到圍捕——這一點在蝙蝠俠如此告訴達卡時已清楚傳達:「自從你殺死了那兩名被指派驅逐你的特工以來,我們一直在找你。」
儘管如此,該電影系列還是為蝙蝠俠神話做出貢獻。正如《超人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Superman)廣播節目將吉米.奧爾森(Jimmy Olsen)、派瑞.懷特(Perry White)和致命的氪星石(Kryptonite)添加到超人鋼鐵英雄(Man of Steel)的生活中一樣,蝙蝠俠電影系列也給了黑暗騎士蝙蝠洞、穿越古董落地鐘的入口,以及有時會在現場協助英雄們的高瘦管家阿福。一九四九年的《蝙蝠俠與羅賓》(Batman and Robin)是一部寫得較好、但演得較差的續集,裡頭沒有鼓吹種族主義。這兩部電影系列都取得票房佳績,但在1950年代,銀幕上未出現新的蝙蝠俠,或許這是因為弗雷德里克.沃瑟姆(Fredric Wertham)1954年著書《純真的誘惑》(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 之類的嚴厲批評激起對漫畫書的強烈抵制。1965年,《蝙蝠俠》電影系列重新在劇院上映,電影系列每集半小時,馬拉松式的放映一次呈現全部十五集,事實證明它非常成功,足以為新蝙蝠俠的驚險故事鋪路,而這次是在電視上。
《蝙蝠俠》(Batman,1966至1968年電視影集,1966年電影)
「有些日子,你就是無法擺脫炸彈。」
——蝙蝠俠(由亞當.威斯特飾演),「蝙蝠俠:電影」
二十二年前的《蝙蝠俠》電影系列重新上映,觀眾們很享受其中不經意的滑稽浮誇,所以後來激發出故意營造的坎普風格(camp,極盡荒謬滑稽、華麗浮誇或妖豔庸俗,使觀者感到「有意思」的表現手法)。當時執行製作人威廉.多茲爾(William Dozier)和編劇小羅倫佐.山普(Lorenzo Semple Jr.)為美國廣播公司(ABC)帶來一部簡易通俗的喜劇電視影集,足以讓大人放聲大笑、讓孩子們欣賞英雄行為。電視對《超人》(Superman)、《獨行俠》(The Lone Ranger)和《泰山》(Tarzan)的描繪絲毫不遜於其原始素材。在超級英雄節目中,「蝙蝠俠」是新的東西。事實證明,演員能夠一本正經地演繹出最愚蠢台詞,對影集的成功至關重要。多茲爾向演員亞當.威斯特說明:「必須演得像是我們正在廣島投下一顆炸彈,帶著那樣的極度嚴肅。」在他們的形塑下,威斯特成為古板拘謹又不講情面的蝙蝠俠。大人明白笑點,小孩很興奮看到英雄打壞人,結果如預期進行。
影集很少涉及任何明顯的心理議題。「我們很膚淺,」威斯特評論道:「我們知道什麼?」即使涉及,刻意的滑稽鬧劇也沒有精確描述精神疾病或其治療的空間。精神控制曾經突然出現在數集中,與任何現實世界中的催眠或洗腦技術完全不同。其中一集,「海妖賽蓮」(Siren)的聲音迫使布魯斯.韋恩將財產轉讓給她,然後跳樓;另一集中,「睡魔」(the Sandman)讓羅賓啟動機器,如果披風戰士沒有逃過當週的驚險情節,機器就會殺死蝙蝠俠。
作為揭露小丑偽造行為的計畫一環,布魯斯.韋恩讓小丑坐上高譚國家銀行副行長一職,戈登局長認為這位百萬富翁花花公子已經失去理智而讓他就範。身穿緊束衣的布魯斯逃脫,從反瘋子小隊(Anti-Lunatic Squad)的廂型車後面滾下去。故事的結尾是一名醫生給布魯斯一份健康證明,宣稱他從廂型車上摔下來使他恢復一些知覺,從而恢復理智。醫生測試精神健全程度的方法,甚至讓幼時的我感到困惑:他用反射錘敲布魯斯的膝蓋。
儘管蝙蝠俠的敵人做出各種滑稽古怪的舉動,但他們無一被貼上犯罪型精神病人的標籤。這些浮誇的重罪犯是從高譚州立監獄脫逃,而非阿卡漢療養院。就長期的人物塑造而言,與心理最相關的故事元素是圖坦王的古怪情況(參見案例2–1:圖坦王)。
《蝙蝠俠》(Batman,1989年電影)
「很多人認為你和小丑一樣危險。」
——維琪.維爾(Vicki Vale,由金.貝辛格[Kim Basinger]飾演)
蝙蝠角色在漫畫書中首次亮相五十年後,導演提姆.波頓帶給我們一個在陰影中運作的電影蝙蝠俠。執行製片人麥可.烏斯蘭希望波頓以蝙蝠俠的《偵探漫畫》故事(前羅賓)第一年,以及後來由丹尼斯.奧尼爾和史蒂夫.恩格爾哈特分別撰寫的冒險故事為基礎來刻畫蝙蝠俠。法蘭克.米勒的四部圖像小說《黑暗騎士歸來》在當時大受歡迎的程度,顯示粉絲們可能已經準備好迎接更黑暗的蝙蝠俠故事。波頓添入自己的鬼才:第一次,我們看到一個神經質的蝙蝠俠和笨拙的布魯斯.韋恩。儘管這部電影確實有一些奇怪的坎普風格(記得那些邋遢的新聞主播嗎?),但最怪異的幽默來自小丑,這也頗符合他的本性。
劇本採用黑色手法,以黑色城市圍繞著蝙蝠俠,讓他更可信。波頓的高譚市赫然聳現,依山姆.哈姆的劇本描述:「彷彿地獄突然穿透路面而出,並且繼續不斷」。波頓解釋,波頓與製作設計師(production designer,又名美術指導)安東.佛斯特(Anton Furst)望看紐約,「決定將所有東西變暗,垂直建造,將東西塞在一起,然後以更卡通的手法推進,這有歌劇的感覺和幾乎永恆的質感。」。「蝙蝠俠:動畫系列」的創作者同樣採用這些原則。「這座新表現主義的德式城市」及其哥德式建築,提供我們一個需要蝙蝠俠的環境。他與他的城市並肩而行。一個幫助我們相信另一個。
波頓電影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聲音。演員米高.基頓在扮演蝙蝠俠時壓低嗓音,讓聲音更低沉、更粗啞,幫助我們接受人們不會認出蝙蝠俠就是布魯斯.韋恩——在這點上,懷疑的懸念是必要的。「布魯斯.韋恩是花花公子、知名人士,人們都認得他的聲音,所以我想到壓低嗓音的靈感,」基頓解釋道:「蝙蝠俠來自較低層的東西,他必須降貴紆尊,直到成為準義警的存在。」現在,漫畫書的故事本身告訴讀者蝙蝠俠在變裝時的聲音變得粗啞。
依波頓之見,布魯斯.韋恩成日睡眠不足,他的笨拙不是裝的。波頓並未遵循蝙蝠俠為體格與社交皆極其出色的傳統形象,而是選擇讓布魯斯.韋恩變得軟弱,使他更人性化。在為這個角色試鏡一個又一個肌肉男時,波頓發現自己無法想像一個看起來已經像是動作冒險英雄的人決定打扮得像蝙蝠。當他想像一個弱者為徹底改變自己而穿上這套服裝時,概念隨之產生。「我們單從心理上來說,『這傢伙看起來不像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他為什麼這樣做?』他不是試圖為自己塑造形象,而是想成為一個不像他的人。」波頓的蝙蝠俠以身著的服裝作為甲冑、作為防彈外骨骼,賦予他原本缺乏的權力和力量。「他這麼做,因為他需要,因為他不是如此身材魁梧的大男人。這一切都與徹底改變有關。」
波頓的布魯斯.韋恩在蝙蝠俠與布魯斯之間來回轉換,而精神病態的傑克.納皮爾(Jack Napier)則發生不可逆的轉變,從一個出於實際原因殺人的兇狠冷酷黑幫,變成一個為了黑色幽默而殺人、頂著小丑臉格格笑的犯罪大師。*
《蝙蝠俠大顯神威》(Batman Returns,1992年電影)
「狂人從未嚇到我,至少他們執著。」
——瑟琳娜.凱爾(Selina Kyle,由蜜雪兒.菲佛[Michelle Pfeiffer]飾演)
在續集中,波頓想引進貓女——對他來說,繼小丑之後,蝙蝠俠最有趣的對手是貓女。然而,製片廠高層堅持用企鵝人(Penguin),他們認為企鵝人是蝙蝠俠的第二號敵人,所以這部電影最終融入兩者。波頓在談到塑造企鵝人奧斯華.科波特(Oswald Cobblepot)的挑戰時說道:「你可以發現蝙蝠俠、貓女、小丑的心理剖繪,但企鵝人只是一個叼著香菸、戴大禮帽的傢伙。」直到波頓給了這個角色另一層次,將他與電影主題:雙重性聯繫起來,角色形象才成型。
在這部續集中,蝙蝠俠和貓女都有雙重身分:光明面和黑暗面。布魯斯和瑟琳娜是兩個不自在、不確定、不快樂的人,他們在白天走路時保守低調,但到了晚上就變得相反,堅定自信而果敢。當所有其他派對嘉賓變裝且戴著面具,在化裝舞會上聊天、跳舞、兜來轉去,布魯斯和瑟琳娜兩人穿著正裝到場,一人穿晚宴服、一人著長禮服,外表文雅有禮,沒有戴任何面具。「瑟琳娜,你不懂嗎?」電影快結束時,布魯斯在撕下面具之前向她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是一樣的,由中間分裂為二。」
《蝙蝠俠大顯神威》中,黑暗面是動物本性:蝙蝠、貓,和冷冰冰的小鳥。布魯斯.韋恩和瑟琳娜.凱爾穿動物裝,科波特與他們不同,天生是長蹼足而非手的「怪胎」。他們決定化身為夜行動物,而企鵝人則努力成為一個能夠步入光明的人,只是他試圖這樣做,用的方法卻是欺騙,且未放棄他的獸性。
在波頓的兩部蝙蝠電影中,布魯斯.韋恩很冷漠,反派搶盡風頭,而戀人們牢牢抓住我們的注意力。在每段故事的過程中,維琪.維爾和瑟琳娜.凱爾給予我們關注的面向。儘管提姆.波頓意識到有人抱怨小丑搶了第一部電影的風頭,而第二部電影出現蝙蝠俠的部分太少,但他認為這些批評「沒有抓住角色重點……這個傢伙想盡可能隱藏在陰影中,盡可能不暴露自己,所以他不會用這些大型演講和在蝙蝠洞周圍跳舞來佔用螢幕時間。」無論波頓的推論有多合理,這些批評反映出漫畫有一潛在優勢,就是相對於電影,漫畫的文本(text)可以思想氣球(thought balloon)和旁白(narration)的形式,讓我們進入角色的腦袋裡。
《蝙蝠俠3》(Batman Forever,1995年電影)
「我帶上葡萄酒,你帶上你傷痕累累的心靈。」
——馬慈絲博士(Dr. Chase Meridian,由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飾演)
提姆.波頓決定協助製作但不執導下一部電影時,接手的導演喬伊.舒馬克(Joel Schumacher)預想著一部更輕鬆、更光明、充滿壯觀和閃耀場面的偉大蝙蝠俠電影,儘管它確實有其優勢。比起之前的電影,這部電影更詳細地探討了蝙蝠俠的起源。據編劇艾基瓦.高茲曼(Akiva Goldsman)表示,「蝙蝠俠3」部分是「以一種試圖更近距離檢視布魯斯.韋恩的心理以及他如何變老的方式來重述故事起源」。目睹迪克.格雷森(Dick Grayson,即第一任羅賓)的雜技演員世家遭謀殺,讓布魯斯反思自己的源始。
布魯斯(由方.基墨[Val Kilmer]飾演):和我父母一樣。悲劇再次上演。一個怪物從黑夜中走出,一聲尖叫,兩聲槍響。我殺了他們。
阿福(由麥可.高福[Michael Gough]飾演):你說什麼?
布魯斯:他殺了他們。雙面人,他殺了那個男孩的父母。
阿福:不。不,你剛剛說「我」。「我殺了他們。」
布魯斯與犯罪心理學家馬慈絲商討有關神秘跟踪者在韋恩莊園(Wayne Manor)留下謎語一事後,布魯斯告訴她,自己對父母死亡的相關事件都不太記得,有的記憶大部分來自夢中。然而,自從格雷森一家遭遇類似的死亡事件後,這些記憶開始在他醒著時縈繞腦海之中:在父母的守靈夜後,少年布魯斯找到父親的日記,同時他意識到那個令人心碎的事實,就是他的父親再也寫不了日記。馬慈絲說,他正在描述被壓抑的記憶(repressed memory):「被遺忘的痛苦意象正在試圖浮現。」佛洛伊德(Freud)認為潛抑(repression)是最重要的防衛機制,儘管現代實證目前顯示這種情形極少發生,無意識心靈(unconscious mind)會封鎖意識自我(conscious ego)無法承受的感受、慾望和經驗。為何布魯斯壓抑這麼簡單的事?為何記憶的恢復如此重要?高茲曼後來解釋:
在劇本和我們拍攝的電影中,電影核心有一點非常不同,就是他打開日記,最後一句是「瑪莎[布魯斯的母親]和我今晚都想待在家裡,但布魯斯堅持要去看電影」。[布魯斯]壓抑自己的想像,想像這都是他的錯,如果當晚沒有讓他們去看電影,他們就絕不會出門,也絕不會被殺。所以整部電影其實是圍繞著這樣的心理算計展開的。這就是為何戀人是心理學家。
儘管這部電影刪除了布魯斯在能夠接受迪克.格雷森為打擊犯罪夥伴之前需要解決的壓抑內疚感,但保留了大部分蝙蝠俠故事中的重要議題:雙重性和強迫意念。電影中的二號反派「雙面人」兼具兩者。他名副其實,顏面從中分開,右側帥氣、左側為硫酸傷疤,這位前地方檢察官哈維.丹特(Harvey Dent)強迫性地拋擲硬幣,讓命運來做決定。馬慈絲和蝙蝠俠稱他擁有「多重人格」,然而,除了他以複數自稱,影片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有這種情況。這位雙面人不曾在是非之間掙扎。他總是想做錯事。拋擲硬幣來做決定只是免除自身行為的責任。當拋擲的結果與意願相反時,他會表現其失望,甚至反覆拋擲,直到能讓他做想做的事。儘管半張臉毀容的創傷突顯出他的陰暗面,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他在自我之間轉換,也沒有跡象顯示好哈維與壞哈維之間有任何記憶落差。
愛德華.尼格瑪(Edward Nygma)是片中的主要反派——謎語人(Riddler,又名謎天大聖),他似乎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症(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這是一種不穩定、不完整的認同,特徵為思想、情緒、行為和自我概念混亂,「無論在生活上或治療上,都是最令人沮喪的精神疾病之一」。愛德華的具體症狀包括分裂(splitting),將人分為正負極端,在理想化和妖魔化同一人之間乍然切換,正如他面對布魯斯.韋恩的搖擺觀點所示。「你是我的偶像。」第一次見面時,他這樣告訴布魯斯。最初,愛德華的創意靈感給布魯斯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卻因為追得太緊,錯失了獲得千萬富翁資助研究的機會。英雄崇拜轉化為危險的強迫意念。愛德華跟蹤布魯斯,匿名留給他帶有不祥暗示的謎語。馬慈絲警告布魯斯:「他對你有執念,唯一的擺脫辦法可能是清除固著(fixation,使個人心理滯留在某一階段而不繼續向前發展的強迫性驅力)」,即他有「潛在的殺人傾向」。
心理學家馬慈絲和邊緣人愛德華在電影中皆以不同的方式被布魯斯.韋恩所吸引,試圖進入蝙蝠俠的內心——在愛德華的例子中,確實如此。馬慈絲想和布魯斯在一起,愛德華想成為像他一樣的人。馬慈絲與布魯斯一起參加宴會;主人愛德華貼上一顆假痣,模仿布魯斯(由方.基墨飾演)臉上的痣。馬慈絲建立一個研究蝙蝠俠的檔案;愛德華建造腦波操控器來竊取人們腦中的資訊,包括布魯斯.韋恩的秘密。隨著愛德華愈來愈需要與更全能的人往來,他從崇拜和模仿布魯斯,到從所有連接尼格瑪科技(Nygmatech)3D魔盒至電視上的人汲取少量資訊和智商,融入他自己身上。該機器導致愛德華的大腦超載,讓他在阿卡漢療養院裡行為脫節與陷入困惑,誤以為自己就是蝙蝠俠。
在波頓至舒馬克的所有蝙蝠俠電影中,沒有其他電影讓布魯斯.韋恩如此頻繁地出場,也沒有其他電影如此徹底地將他描繪成意義重大的角色。這位布魯斯穿任何衣服都更勇敢、更大膽、更自在。沒時間變裝的布魯斯,猶如身穿黑色晚禮服的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毫不猶豫就出手攻擊「雙面人」方的暴徒們,同時發狂似地試圖阻止一顆滴答作響的炸彈,避免馬戲團中數百人遭到殺害。他並未化身蝙蝠俠。他是蝙蝠俠。
布魯斯:你喜歡蝙蝠嗎?
馬慈絲:哦,韋恩先生,那是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一團墨跡而已。人們只看見內心所想。我想問題會是:你喜歡蝙蝠嗎?
這部電影的坎普風格時段使人分散對其心理學廣度的關注,以及忽視它與舒馬克下一部蝙蝠電影的關聯,一部可謂三十多年來最具坎普風格的電影。
《蝙蝠俠4:急凍人》(Batman & Robin,1997年電影)
「這就是超人總是一個人行動的原因。」
——蝙蝠俠(由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飾演)
由於電影《蝙蝠俠4:急凍人》對蝙蝠俠本人的刻劃並不深入,*若要深度觀察蝙蝠俠的角色發展,觀眾必須退後一步,細細思量他縱貫四部電影的個人故事情節:在波頓的電影中,》蝙蝠俠》裡的布魯斯.韋恩一開始是個無聊乏味的人物,但至少嘗試社交,以及維持某種生活假象。到了「蝙蝠俠大顯神威」,他不再費心假裝。他在前部電影一開始所舉辦的派對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他在家中,獨自坐在黑暗裡,直到蝙蝠信號燈(Bat-Signal)啟動蝙蝠俠身分轉換,他的理想我(ideal self)瞬間活躍起來。瑟琳娜必須進入他的生活,他才考慮重訪高譚市的社交現場。這位反英雄(antihero)以貓女的身分挑戰蝙蝠俠、以瑟琳娜的身分與布魯斯約會,她以維琪.維爾不曾做到的方式喚醒他的人性,即透過吸引與匹配雙方面——蝙蝠和人。到電影結尾,他發現自己確實想要另外有人存在他的生活中。接著,舒馬克的電影顯示他日漸舒展。在《蝙蝠俠3》中,他向心理學家敞開心扉,還勉強找了一個搭檔,隨後在電影《蝙蝠俠4:急凍人》中,他毫不猶豫就欣然接受蝙蝠女孩(Batgirl)和整個蝙蝠家族的概念。
扮演第一代蝙蝠俠的亞當.威斯特曾經問我,是否認為蝙蝠俠很瘋狂。《蝙蝠俠與心理學:穿越黑暗的心靈》是我的答案。
自1939年《偵探漫畫》(Detective Comics)第27期首度登場以來,蝙蝠俠隨時間透過眾多媒體讓全球數十億人感到興奮激動。世界上最著名的三位漫畫英雄——蝙蝠、蜘蛛和來自另一星球的人,組成孤兒三重奏。而他,是那個夜間工作、需要一輛車載他入城、最致命的人。他是沒有超能力的超級英雄,我們最容易相信他可能棲居在我們的世界。他的秘密身分是三人之中最奇妙的,一個迷人英俊的億萬富翁住在一個巨大洞穴上方的豪宅裡,而其他兩人是平庸的報社職員,然而,巨富有助於我們接受他的蒙面身分,感覺更為真實。那些很棒的玩具,總要有人買單。現實世界中,人們知道的超級富豪比超能力者多。蝙蝠俠是成年人也能想像存在現實生活的英雄,較不令人懷疑。儘管布魯斯.韋恩擁有極少人享有的機會,但他來自一座城市,而非神話中的島嶼或遙遠世界,他透過訓練和努力將自己打造為英雄——不需要輻射、秘密配方或魔法戒指。他的出身悲慘,而且故事殘酷可信。它觸及了我們童年時期最原始的恐懼:一場家庭郊遊,一名搶劫犯在他眼前槍殺了他的父母,結果釀成悲劇。
他的電影列名歷史上最高票房電影之中,這個角色出演的動畫、真人版電影與電視影集比任何其他漫畫英雄都多。為什麼這名一身沉鬱的自發義警、飽受折磨的靈魂,出沒街頭找麻煩、穿著像吸血鬼,卻讓我們如此著迷?他的故事充滿了敵人與他自身的雙重性(duality)和強迫意念(obsession)。他的敵人反映且扭曲了他自己的各個方面。他自鳴得意,他詭秘狡猾,他是如此令人懼怕,以至於當他進入一個房間,儘管裡頭滿是會飛、會讀心術、會施咒或跑步比光快的人,還是這些人被他嚇倒——這就是我們愛的部分。他強而有力,聰明機警,不受財務限制或其他任何人的規則束縛,將我們深切的願望化為現實。我們想要嚇退所有生命中的霸凌者,而蝙蝠俠正是這個部分。
在創作明亮耀眼的超人時,傑瑞 .西格爾(Jerry Siegel)和喬 .舒斯特(Joe Shuster)靈光一閃。一個不眠之夜,傑瑞構思出「類似《聖經》中大力士參孫(Samson)、希臘神話英雄海克力斯(Hercules)的角色,把我聽說過的所有強者的形象合而為一,仍有過之而無不及。」傑瑞和他的繪師朋友喬從古往今來的神聖英雄中汲取靈感,創作出不僅僅是超人本人,正好還有變裝超級英雄的概念。他們製作迷因。他們開創現代神話。超人立即引起轟動。首位披風英雄成功之後,出版商們爭先恐後地炮製更多英雄。年輕漫畫家鮑勃.凱恩為超人的出版商打造了下一個變裝社會改革家。搶在所有即將推出的超人模仿作品之前,凱恩與合作者比爾.芬格不是從啟發傑瑞和喬的超人形象中汲取靈感,而是從無聲電影和低俗小說的暗黑神秘人物中汲取靈感,最著名的是蒙面俠蘇洛(Zorro)和魅影奇俠( the Shadow),儘管他們卓爾不凡,但仍是人。超人從地球的太陽汲取力量,而蝙蝠俠則在城市的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力量。*傑瑞和喬考量的是明亮與不可能;鮑勃和比爾則是藉由添加另一面向——黑暗與難以置信的可能——來擴展迷因。
今天,所有人在讀第一個蝙蝠俠故事時,都已知道那個撲朔迷離的自發治安維持者,最終落在一名百無聊賴的富家子弟手裡,直到漫畫的最後一格,他把時間全花在作為戈登局長(Commissioner Gordon)的陪襯角色,成為戈登能夠表達想法的參謀對象——就像我們會對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經典小說《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摸不著頭腦,因為搞不清楚舉止溫文的傑寇爾醫生(Dr. Jekyll)與缺乏教養的海德先生(Mr. Hyde)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面具後面那個人的名字和面孔,但是什麼潛藏在面孔的後面?比起蝙蝠俠的蒙面頭罩、布魯斯.韋恩的外表或他選用的任何名字,「蝙蝠俠是誰?」(Who is Batman?)這個問題更深刻。一個「誰」(who)的問題包含許多「為何」(why):為何他要打擊犯罪?為何以自發義警的身分?為何面具、蝙蝠和未成年夥伴?為何與他應當關押起來的「壞女孩」發展出最親密的關係?為何他不殺掉那個殺人如麻的綠髮小丑?
蝙蝠俠精神失常嗎?(譯註:英文原文have bats in his belfry[他的鐘塔內有蝙蝠]是一種暗喻。用語中的belfry是教堂頂部的鐘塔,常為蝙蝠棲息的地方,蝙蝠受鐘聲影響,會到處亂飛,以belfry比喻人的腦袋,have bats in his belfry意即他的行為乖張、精神失常。)
第2章 哪個蝙蝠俠?
「我有點擔心。我曾在2016、2012、2008、2005、1997、1995、1992、1989年看過你經歷類似的階段,還有1966年那個詭異的階段。你想談一談嗎?」
——《樂高蝙蝠俠電影》(2017年電影)中的阿福(Alfred,由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配音)
我們在分析角色之前,必須先界定變數。在探討「誰」(who)及所有其「為何」(why)的問題之前,首先必須考量指的是「哪個」(which)蝙蝠俠。
儘管蝙蝠俠源於漫畫人物且一直存在,但我們大多數人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電視上。從我還是個蹣跚學步的幼童時,亞當.威斯特便是活生生的蝙蝠俠。我也在週六早上看披風戰士的卡通,讓蝙蝠俠和羅賓的玩具與開著綠色塑膠廂型車的小丑鬥著玩,同時穿著毛巾披風、戴著黑色手套,把自己扮成蝙蝠俠。週六早上,由歐蘭.索爾(Olan Soule)配音、一個較嚴肅(但仍然積極樂觀)的蝙蝠俠與超人、神力女超人和水行俠(Aquaman)組成一個小型的正義聯盟,即最早的《超級英雄》(Super Friends)。在我終於有空細讀漫畫書較黑暗的故事時,這些電視版本曾經帶給我一些大驚奇。
下一世代,我的兒子主要透過《蝙蝠俠:動畫影集》認識蝙蝠俠。大兒子第一次看這節目是在八歲,他原已從其他媒體知道蝙蝠俠,但記憶是個有趣的東西,這部卡通透過時間將記憶回調,讓卡通追溯起來像是最先進入記憶。卡通成為他記憶中最早的蝙蝠俠,儘管他知道應該並非如此。小兒子發現蝙蝠俠的過程比較像我,身為學齡前兒童,他不為蝙蝠俠並非真正存在的事實所困擾,這可能是為何在兩個男孩中,他更迷蝙蝠俠。一開始,他著迷的是蝙蝠俠玩具。不過,在他小腦袋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對他來說的蝙蝠俠最初記憶,則是電視剪輯版《蝙蝠俠大顯神威》(Batman Returns)的蝙蝠車,能夠分解部分車身而迅速穿梭狹窄巷弄。他先前對玩具車的熱情就鎖定在那部車上。蝙蝠俠讓他感到驚奇,蝙蝠俠的玩具也是。
銀幕╱螢幕史
1940年代電影系列
蝙蝠俠的銀幕史始於哥倫比亞影業(Columbia Pictures)的影集《蝙蝠俠》(Batman,1943),由路易斯.威爾森(Lewis Wilson)和道格拉斯.克羅夫特(Douglas Croft)主演,他們是第一次真人版出演的蝙蝠俠和羅賓,該角色首度出現於漫畫書是四年前。在那個年代,對許多人來說,一個典型的週六意味著坐在地方戲院的座位上共享群體經驗,看一部完整的劇情長片、新聞短片、卡通、由「三個臭皮匠」(Three Stooges)或「小搗蛋」(Our Gang)主演的喜劇短片,以及電影系列的至少一集,《蝙蝠俠》是新事物,並非他們生平全都知道。歷經十五週一連串的高潮迭起,他們看到活力雙雄(Dynamic Duo)大戰美國惡棍、日本特工提托.達卡博士(Dr. Tito Daka)以及遭達卡控制心智的「喪屍」(zombie)奴隸。
恐懼是蝙蝠俠故事中反覆出現的元素,但有一種恐懼特別形塑了這部電影系列的創作——仇外心理(xenophobia),即對外國人或陌生人的過度恐懼。二戰期間,反亞裔情緒對美國來說並不陌生,這部電影系列中對日本人的刻畫與描述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該電影系列的旁白告訴我們:「自從明智的政府圍捕賊眉鼠眼的日本人後1,城市小東京區的建築物已經空置。這指涉的是一九四二年日本襲擊珍珠港後,美國政府將逾十萬名日裔美國公民和居民重新安置與收容至戰時再安置營(War Relocation Camp)。這樣的再安置未曾發生在任何德裔或義裔人士身上,只有對祖先來自軸心國聯盟(Axis alliance)亞洲成員的人才如此。
間諜達卡體現的是許多感到害怕的日本外僑仍然潛伏在美國,且以某種方式避免遭到圍捕——這一點在蝙蝠俠如此告訴達卡時已清楚傳達:「自從你殺死了那兩名被指派驅逐你的特工以來,我們一直在找你。」
儘管如此,該電影系列還是為蝙蝠俠神話做出貢獻。正如《超人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Superman)廣播節目將吉米.奧爾森(Jimmy Olsen)、派瑞.懷特(Perry White)和致命的氪星石(Kryptonite)添加到超人鋼鐵英雄(Man of Steel)的生活中一樣,蝙蝠俠電影系列也給了黑暗騎士蝙蝠洞、穿越古董落地鐘的入口,以及有時會在現場協助英雄們的高瘦管家阿福。一九四九年的《蝙蝠俠與羅賓》(Batman and Robin)是一部寫得較好、但演得較差的續集,裡頭沒有鼓吹種族主義。這兩部電影系列都取得票房佳績,但在1950年代,銀幕上未出現新的蝙蝠俠,或許這是因為弗雷德里克.沃瑟姆(Fredric Wertham)1954年著書《純真的誘惑》(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 之類的嚴厲批評激起對漫畫書的強烈抵制。1965年,《蝙蝠俠》電影系列重新在劇院上映,電影系列每集半小時,馬拉松式的放映一次呈現全部十五集,事實證明它非常成功,足以為新蝙蝠俠的驚險故事鋪路,而這次是在電視上。
《蝙蝠俠》(Batman,1966至1968年電視影集,1966年電影)
「有些日子,你就是無法擺脫炸彈。」
——蝙蝠俠(由亞當.威斯特飾演),「蝙蝠俠:電影」
二十二年前的《蝙蝠俠》電影系列重新上映,觀眾們很享受其中不經意的滑稽浮誇,所以後來激發出故意營造的坎普風格(camp,極盡荒謬滑稽、華麗浮誇或妖豔庸俗,使觀者感到「有意思」的表現手法)。當時執行製作人威廉.多茲爾(William Dozier)和編劇小羅倫佐.山普(Lorenzo Semple Jr.)為美國廣播公司(ABC)帶來一部簡易通俗的喜劇電視影集,足以讓大人放聲大笑、讓孩子們欣賞英雄行為。電視對《超人》(Superman)、《獨行俠》(The Lone Ranger)和《泰山》(Tarzan)的描繪絲毫不遜於其原始素材。在超級英雄節目中,「蝙蝠俠」是新的東西。事實證明,演員能夠一本正經地演繹出最愚蠢台詞,對影集的成功至關重要。多茲爾向演員亞當.威斯特說明:「必須演得像是我們正在廣島投下一顆炸彈,帶著那樣的極度嚴肅。」在他們的形塑下,威斯特成為古板拘謹又不講情面的蝙蝠俠。大人明白笑點,小孩很興奮看到英雄打壞人,結果如預期進行。
影集很少涉及任何明顯的心理議題。「我們很膚淺,」威斯特評論道:「我們知道什麼?」即使涉及,刻意的滑稽鬧劇也沒有精確描述精神疾病或其治療的空間。精神控制曾經突然出現在數集中,與任何現實世界中的催眠或洗腦技術完全不同。其中一集,「海妖賽蓮」(Siren)的聲音迫使布魯斯.韋恩將財產轉讓給她,然後跳樓;另一集中,「睡魔」(the Sandman)讓羅賓啟動機器,如果披風戰士沒有逃過當週的驚險情節,機器就會殺死蝙蝠俠。
作為揭露小丑偽造行為的計畫一環,布魯斯.韋恩讓小丑坐上高譚國家銀行副行長一職,戈登局長認為這位百萬富翁花花公子已經失去理智而讓他就範。身穿緊束衣的布魯斯逃脫,從反瘋子小隊(Anti-Lunatic Squad)的廂型車後面滾下去。故事的結尾是一名醫生給布魯斯一份健康證明,宣稱他從廂型車上摔下來使他恢復一些知覺,從而恢復理智。醫生測試精神健全程度的方法,甚至讓幼時的我感到困惑:他用反射錘敲布魯斯的膝蓋。
儘管蝙蝠俠的敵人做出各種滑稽古怪的舉動,但他們無一被貼上犯罪型精神病人的標籤。這些浮誇的重罪犯是從高譚州立監獄脫逃,而非阿卡漢療養院。就長期的人物塑造而言,與心理最相關的故事元素是圖坦王的古怪情況(參見案例2–1:圖坦王)。
《蝙蝠俠》(Batman,1989年電影)
「很多人認為你和小丑一樣危險。」
——維琪.維爾(Vicki Vale,由金.貝辛格[Kim Basinger]飾演)
蝙蝠角色在漫畫書中首次亮相五十年後,導演提姆.波頓帶給我們一個在陰影中運作的電影蝙蝠俠。執行製片人麥可.烏斯蘭希望波頓以蝙蝠俠的《偵探漫畫》故事(前羅賓)第一年,以及後來由丹尼斯.奧尼爾和史蒂夫.恩格爾哈特分別撰寫的冒險故事為基礎來刻畫蝙蝠俠。法蘭克.米勒的四部圖像小說《黑暗騎士歸來》在當時大受歡迎的程度,顯示粉絲們可能已經準備好迎接更黑暗的蝙蝠俠故事。波頓添入自己的鬼才:第一次,我們看到一個神經質的蝙蝠俠和笨拙的布魯斯.韋恩。儘管這部電影確實有一些奇怪的坎普風格(記得那些邋遢的新聞主播嗎?),但最怪異的幽默來自小丑,這也頗符合他的本性。
劇本採用黑色手法,以黑色城市圍繞著蝙蝠俠,讓他更可信。波頓的高譚市赫然聳現,依山姆.哈姆的劇本描述:「彷彿地獄突然穿透路面而出,並且繼續不斷」。波頓解釋,波頓與製作設計師(production designer,又名美術指導)安東.佛斯特(Anton Furst)望看紐約,「決定將所有東西變暗,垂直建造,將東西塞在一起,然後以更卡通的手法推進,這有歌劇的感覺和幾乎永恆的質感。」。「蝙蝠俠:動畫系列」的創作者同樣採用這些原則。「這座新表現主義的德式城市」及其哥德式建築,提供我們一個需要蝙蝠俠的環境。他與他的城市並肩而行。一個幫助我們相信另一個。
波頓電影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聲音。演員米高.基頓在扮演蝙蝠俠時壓低嗓音,讓聲音更低沉、更粗啞,幫助我們接受人們不會認出蝙蝠俠就是布魯斯.韋恩——在這點上,懷疑的懸念是必要的。「布魯斯.韋恩是花花公子、知名人士,人們都認得他的聲音,所以我想到壓低嗓音的靈感,」基頓解釋道:「蝙蝠俠來自較低層的東西,他必須降貴紆尊,直到成為準義警的存在。」現在,漫畫書的故事本身告訴讀者蝙蝠俠在變裝時的聲音變得粗啞。
依波頓之見,布魯斯.韋恩成日睡眠不足,他的笨拙不是裝的。波頓並未遵循蝙蝠俠為體格與社交皆極其出色的傳統形象,而是選擇讓布魯斯.韋恩變得軟弱,使他更人性化。在為這個角色試鏡一個又一個肌肉男時,波頓發現自己無法想像一個看起來已經像是動作冒險英雄的人決定打扮得像蝙蝠。當他想像一個弱者為徹底改變自己而穿上這套服裝時,概念隨之產生。「我們單從心理上來說,『這傢伙看起來不像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他為什麼這樣做?』他不是試圖為自己塑造形象,而是想成為一個不像他的人。」波頓的蝙蝠俠以身著的服裝作為甲冑、作為防彈外骨骼,賦予他原本缺乏的權力和力量。「他這麼做,因為他需要,因為他不是如此身材魁梧的大男人。這一切都與徹底改變有關。」
波頓的布魯斯.韋恩在蝙蝠俠與布魯斯之間來回轉換,而精神病態的傑克.納皮爾(Jack Napier)則發生不可逆的轉變,從一個出於實際原因殺人的兇狠冷酷黑幫,變成一個為了黑色幽默而殺人、頂著小丑臉格格笑的犯罪大師。*
《蝙蝠俠大顯神威》(Batman Returns,1992年電影)
「狂人從未嚇到我,至少他們執著。」
——瑟琳娜.凱爾(Selina Kyle,由蜜雪兒.菲佛[Michelle Pfeiffer]飾演)
在續集中,波頓想引進貓女——對他來說,繼小丑之後,蝙蝠俠最有趣的對手是貓女。然而,製片廠高層堅持用企鵝人(Penguin),他們認為企鵝人是蝙蝠俠的第二號敵人,所以這部電影最終融入兩者。波頓在談到塑造企鵝人奧斯華.科波特(Oswald Cobblepot)的挑戰時說道:「你可以發現蝙蝠俠、貓女、小丑的心理剖繪,但企鵝人只是一個叼著香菸、戴大禮帽的傢伙。」直到波頓給了這個角色另一層次,將他與電影主題:雙重性聯繫起來,角色形象才成型。
在這部續集中,蝙蝠俠和貓女都有雙重身分:光明面和黑暗面。布魯斯和瑟琳娜是兩個不自在、不確定、不快樂的人,他們在白天走路時保守低調,但到了晚上就變得相反,堅定自信而果敢。當所有其他派對嘉賓變裝且戴著面具,在化裝舞會上聊天、跳舞、兜來轉去,布魯斯和瑟琳娜兩人穿著正裝到場,一人穿晚宴服、一人著長禮服,外表文雅有禮,沒有戴任何面具。「瑟琳娜,你不懂嗎?」電影快結束時,布魯斯在撕下面具之前向她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是一樣的,由中間分裂為二。」
《蝙蝠俠大顯神威》中,黑暗面是動物本性:蝙蝠、貓,和冷冰冰的小鳥。布魯斯.韋恩和瑟琳娜.凱爾穿動物裝,科波特與他們不同,天生是長蹼足而非手的「怪胎」。他們決定化身為夜行動物,而企鵝人則努力成為一個能夠步入光明的人,只是他試圖這樣做,用的方法卻是欺騙,且未放棄他的獸性。
在波頓的兩部蝙蝠電影中,布魯斯.韋恩很冷漠,反派搶盡風頭,而戀人們牢牢抓住我們的注意力。在每段故事的過程中,維琪.維爾和瑟琳娜.凱爾給予我們關注的面向。儘管提姆.波頓意識到有人抱怨小丑搶了第一部電影的風頭,而第二部電影出現蝙蝠俠的部分太少,但他認為這些批評「沒有抓住角色重點……這個傢伙想盡可能隱藏在陰影中,盡可能不暴露自己,所以他不會用這些大型演講和在蝙蝠洞周圍跳舞來佔用螢幕時間。」無論波頓的推論有多合理,這些批評反映出漫畫有一潛在優勢,就是相對於電影,漫畫的文本(text)可以思想氣球(thought balloon)和旁白(narration)的形式,讓我們進入角色的腦袋裡。
《蝙蝠俠3》(Batman Forever,1995年電影)
「我帶上葡萄酒,你帶上你傷痕累累的心靈。」
——馬慈絲博士(Dr. Chase Meridian,由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飾演)
提姆.波頓決定協助製作但不執導下一部電影時,接手的導演喬伊.舒馬克(Joel Schumacher)預想著一部更輕鬆、更光明、充滿壯觀和閃耀場面的偉大蝙蝠俠電影,儘管它確實有其優勢。比起之前的電影,這部電影更詳細地探討了蝙蝠俠的起源。據編劇艾基瓦.高茲曼(Akiva Goldsman)表示,「蝙蝠俠3」部分是「以一種試圖更近距離檢視布魯斯.韋恩的心理以及他如何變老的方式來重述故事起源」。目睹迪克.格雷森(Dick Grayson,即第一任羅賓)的雜技演員世家遭謀殺,讓布魯斯反思自己的源始。
布魯斯(由方.基墨[Val Kilmer]飾演):和我父母一樣。悲劇再次上演。一個怪物從黑夜中走出,一聲尖叫,兩聲槍響。我殺了他們。
阿福(由麥可.高福[Michael Gough]飾演):你說什麼?
布魯斯:他殺了他們。雙面人,他殺了那個男孩的父母。
阿福:不。不,你剛剛說「我」。「我殺了他們。」
布魯斯與犯罪心理學家馬慈絲商討有關神秘跟踪者在韋恩莊園(Wayne Manor)留下謎語一事後,布魯斯告訴她,自己對父母死亡的相關事件都不太記得,有的記憶大部分來自夢中。然而,自從格雷森一家遭遇類似的死亡事件後,這些記憶開始在他醒著時縈繞腦海之中:在父母的守靈夜後,少年布魯斯找到父親的日記,同時他意識到那個令人心碎的事實,就是他的父親再也寫不了日記。馬慈絲說,他正在描述被壓抑的記憶(repressed memory):「被遺忘的痛苦意象正在試圖浮現。」佛洛伊德(Freud)認為潛抑(repression)是最重要的防衛機制,儘管現代實證目前顯示這種情形極少發生,無意識心靈(unconscious mind)會封鎖意識自我(conscious ego)無法承受的感受、慾望和經驗。為何布魯斯壓抑這麼簡單的事?為何記憶的恢復如此重要?高茲曼後來解釋:
在劇本和我們拍攝的電影中,電影核心有一點非常不同,就是他打開日記,最後一句是「瑪莎[布魯斯的母親]和我今晚都想待在家裡,但布魯斯堅持要去看電影」。[布魯斯]壓抑自己的想像,想像這都是他的錯,如果當晚沒有讓他們去看電影,他們就絕不會出門,也絕不會被殺。所以整部電影其實是圍繞著這樣的心理算計展開的。這就是為何戀人是心理學家。
儘管這部電影刪除了布魯斯在能夠接受迪克.格雷森為打擊犯罪夥伴之前需要解決的壓抑內疚感,但保留了大部分蝙蝠俠故事中的重要議題:雙重性和強迫意念。電影中的二號反派「雙面人」兼具兩者。他名副其實,顏面從中分開,右側帥氣、左側為硫酸傷疤,這位前地方檢察官哈維.丹特(Harvey Dent)強迫性地拋擲硬幣,讓命運來做決定。馬慈絲和蝙蝠俠稱他擁有「多重人格」,然而,除了他以複數自稱,影片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有這種情況。這位雙面人不曾在是非之間掙扎。他總是想做錯事。拋擲硬幣來做決定只是免除自身行為的責任。當拋擲的結果與意願相反時,他會表現其失望,甚至反覆拋擲,直到能讓他做想做的事。儘管半張臉毀容的創傷突顯出他的陰暗面,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他在自我之間轉換,也沒有跡象顯示好哈維與壞哈維之間有任何記憶落差。
愛德華.尼格瑪(Edward Nygma)是片中的主要反派——謎語人(Riddler,又名謎天大聖),他似乎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症(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這是一種不穩定、不完整的認同,特徵為思想、情緒、行為和自我概念混亂,「無論在生活上或治療上,都是最令人沮喪的精神疾病之一」。愛德華的具體症狀包括分裂(splitting),將人分為正負極端,在理想化和妖魔化同一人之間乍然切換,正如他面對布魯斯.韋恩的搖擺觀點所示。「你是我的偶像。」第一次見面時,他這樣告訴布魯斯。最初,愛德華的創意靈感給布魯斯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卻因為追得太緊,錯失了獲得千萬富翁資助研究的機會。英雄崇拜轉化為危險的強迫意念。愛德華跟蹤布魯斯,匿名留給他帶有不祥暗示的謎語。馬慈絲警告布魯斯:「他對你有執念,唯一的擺脫辦法可能是清除固著(fixation,使個人心理滯留在某一階段而不繼續向前發展的強迫性驅力)」,即他有「潛在的殺人傾向」。
心理學家馬慈絲和邊緣人愛德華在電影中皆以不同的方式被布魯斯.韋恩所吸引,試圖進入蝙蝠俠的內心——在愛德華的例子中,確實如此。馬慈絲想和布魯斯在一起,愛德華想成為像他一樣的人。馬慈絲與布魯斯一起參加宴會;主人愛德華貼上一顆假痣,模仿布魯斯(由方.基墨飾演)臉上的痣。馬慈絲建立一個研究蝙蝠俠的檔案;愛德華建造腦波操控器來竊取人們腦中的資訊,包括布魯斯.韋恩的秘密。隨著愛德華愈來愈需要與更全能的人往來,他從崇拜和模仿布魯斯,到從所有連接尼格瑪科技(Nygmatech)3D魔盒至電視上的人汲取少量資訊和智商,融入他自己身上。該機器導致愛德華的大腦超載,讓他在阿卡漢療養院裡行為脫節與陷入困惑,誤以為自己就是蝙蝠俠。
在波頓至舒馬克的所有蝙蝠俠電影中,沒有其他電影讓布魯斯.韋恩如此頻繁地出場,也沒有其他電影如此徹底地將他描繪成意義重大的角色。這位布魯斯穿任何衣服都更勇敢、更大膽、更自在。沒時間變裝的布魯斯,猶如身穿黑色晚禮服的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毫不猶豫就出手攻擊「雙面人」方的暴徒們,同時發狂似地試圖阻止一顆滴答作響的炸彈,避免馬戲團中數百人遭到殺害。他並未化身蝙蝠俠。他是蝙蝠俠。
布魯斯:你喜歡蝙蝠嗎?
馬慈絲:哦,韋恩先生,那是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一團墨跡而已。人們只看見內心所想。我想問題會是:你喜歡蝙蝠嗎?
這部電影的坎普風格時段使人分散對其心理學廣度的關注,以及忽視它與舒馬克下一部蝙蝠電影的關聯,一部可謂三十多年來最具坎普風格的電影。
《蝙蝠俠4:急凍人》(Batman & Robin,1997年電影)
「這就是超人總是一個人行動的原因。」
——蝙蝠俠(由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飾演)
由於電影《蝙蝠俠4:急凍人》對蝙蝠俠本人的刻劃並不深入,*若要深度觀察蝙蝠俠的角色發展,觀眾必須退後一步,細細思量他縱貫四部電影的個人故事情節:在波頓的電影中,》蝙蝠俠》裡的布魯斯.韋恩一開始是個無聊乏味的人物,但至少嘗試社交,以及維持某種生活假象。到了「蝙蝠俠大顯神威」,他不再費心假裝。他在前部電影一開始所舉辦的派對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他在家中,獨自坐在黑暗裡,直到蝙蝠信號燈(Bat-Signal)啟動蝙蝠俠身分轉換,他的理想我(ideal self)瞬間活躍起來。瑟琳娜必須進入他的生活,他才考慮重訪高譚市的社交現場。這位反英雄(antihero)以貓女的身分挑戰蝙蝠俠、以瑟琳娜的身分與布魯斯約會,她以維琪.維爾不曾做到的方式喚醒他的人性,即透過吸引與匹配雙方面——蝙蝠和人。到電影結尾,他發現自己確實想要另外有人存在他的生活中。接著,舒馬克的電影顯示他日漸舒展。在《蝙蝠俠3》中,他向心理學家敞開心扉,還勉強找了一個搭檔,隨後在電影《蝙蝠俠4:急凍人》中,他毫不猶豫就欣然接受蝙蝠女孩(Batgirl)和整個蝙蝠家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