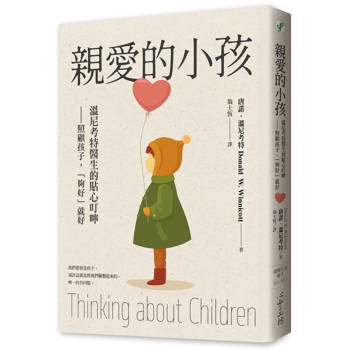第1章 對人類本質的客觀探究
今天我受邀與各位分享關於心理學的背景、假設與其帶來的發現。這是一個範圍極廣的主題,而我必須誠實地承認,我能呈現的,只是我個人視野中一小部分的體會。這就像站在一片森林前,我僅能描繪我曾穿行的那一條小徑。
我也明白,坐在這裡的每一位,都會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來聆聽我說的話。有些人習慣實驗與證據、有些人偏好歷史與事實的軌跡、有些人則深信直覺,喜歡以主觀的方式接觸新知。既然我無法一次回應所有視角,那麼今天我選擇誠實地,向大家呈現我自己的方法與眼光。
我想先提出一個核心觀點:「心理學」其實是一門關於人類本質的探究,就如同物理、生理或生物學一般,是科學的一支。這是我一貫的信念,也是我今日所要分享的起點。這篇講稿原初的雛形在我一位親愛的同事馬蘇可汗(Masud Khan)的建議下改進許多。對我來說,這樣的視角不是偶然,而是一生投入的方向。我想讓各位知道,我的身分不只是醫師,同時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師,而這樣的身份深深影響我理解「人是什麼」的方式。
直到近年來,精神分析才開始被視為一門可以嚴肅對待的學問。它逐漸成為我們社會中談論心理的共通語言,不過使用這些詞語時,日常與專業之間仍存在著深刻的差異。如果你問一位醫師,精神分析如今在醫學或人性研究中有什麼價值,可能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畢竟,從醫療角度審視個案背後的心理脈絡,仍是一種尚在發展的新觀念,尚未被廣泛實踐。
在座的各位當中,也許有些人未來會成為醫師,少數人甚至可能投身於深入心靈工作的領域。除了醫學知識,這條路也需要心理與精神分析的訓練。但就算你只想成為一位能照顧病患全人經驗的家庭醫師,這樣的理解與培養,也都將為你帶來莫大的幫助。
心理學若想真正成為探究人類本質的學問,就必須走上一條科學的道路。當然,我們也能透過感受與直覺來理解像莎士比亞這樣的藝術家——他的作品本身就是對人性深刻的感知。但如果我們願意讓心理學成為一門可驗證、可傳承的知識體系,那麼每一步的科學進展,都會讓我們在閱讀莎士比亞時看得更深,也更少落入空泛的論調。我們必須持續談論人類的本質,而當心理學的語言能帶出真正的內容、能經得起檢驗,那麼它也就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其實,這並不是說在精神分析進入醫療領域以前,心理上的療癒就不存在。一直以來,一位好的醫師同時也需要是一位有同理心的心理觀察者——他要能理解病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也能觸碰病人內在的掙扎與感受。但即使如此,當醫師試圖談論人類本質時,仍可能說出許多不著邊際的話。直覺雖然在日常中偶有洞見,但在面對複雜的人性議題時卻不總是可靠的。它或許能幫助一位醫師理解一名偷竊病人的苦衷,卻無法作為建立「偷竊行為心理學」的基礎。在需要下判斷與做決策的情境中,比如少年法庭,我們更需要能被討論、被驗證的知識,而不是憑感覺說出的意見。
醫學生會經歷長年艱苦的訓練,但這條路並不一定能培養他們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反而可能阻礙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從十八歲開始,一路忙碌到二十五歲,有時回過頭來,已走進中年的門檻。為了在職涯上趕上同行,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於臨床實務中,往往無暇過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與此同時,曾經一起長大的朋友們,或許早已在二十五歲時就展開了屬於自己的人生風景。
也許你已經開始看見,探索人類本質的科學旅程正穩步前行。我們透過觀察尋找線索,建立理論,再用新發現來修正舊有的理解。這是一條不斷接近真理的道路。然而你是否也察覺,科學與直覺之間,根本上的差異?真正的直覺有時能如閃電般指向核心,也有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通向錯誤。與此相比,科學從不聲稱自己掌握「全部的真理」;它所做的,是誠實地建構出一條通往真理的橋樑。這就是為什麼科學訓練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如此重要——它教我們如何腳踏實地地站在當下,並回頭看我們所立足的這片土地。我們的感受與想像可能會跌跤,也可能引我們偏離方向。然而這些時刻,也允許我們夢想與飛翔,即便下一瞬間是失落與墜落。那麼,我們不斷掉落——直到醒來,直到我們回到那個可檢驗、可接納我們的世界:一個名為科學的現實空間。
你曾經這樣想像過「科學」嗎?一門學問若發現某些尚未解釋的現象,如果我們對此一片空白,那麼就記錄它,將它作為未來研究的起點。對於依賴直覺的人,這些尚未串連起來的空白是未知的鴻溝,也許令人恐慌;但物理學家可能會說,那只是一種尚未被發現的元素。不必驚慌,因為總有一天,它會自然嵌入世界的秩序中。像「M&B」這類藥物的療效,初被發現時,科學家或許尚不理解其原理,但他們不會輕易將之視為奇蹟。他們只是繼續研究,慢慢找出答案。即使,至今依然無法掌握世上所有的知識,也沒關係。
心理學的知識與經驗之間,存在著更巨大的落差。但如果我們願意以科學的態度來面對,那麼即使那些直覺派的人說:「我們早就知道了!」我們也可以坦然面對,因為他們並沒有指出那些同時存在的混亂與偏差。真正的科學精神,讓我們得以自在地說「我們還不知道」,而不用發明華麗卻空洞的理論,來填補那些還未看清的部分。
當我們還是嬰兒——甚至剛出生——的時候,我們就像小小的科學家一樣,用身體、感官與心靈去探索這個世界。若我們在那個階段擁有了「夠好」的照顧,一切就不會變得混亂難解。我們靠著想像力先構築了自己的世界,然後慢慢讓真實的世界走進來、與我們相遇。那是一種由外而內的轉化:我們依賴外在事物,因為我們可以用它們來成為「我們自己」。這些事物,即便有時會讓我們生氣,比如餓了還得等待,它們的存在依然是無比珍貴的。因為那真實的外在世界幫助我們忍受那種「一切皆有可能」的魔幻想像。那時,我們的經驗還很原始,夢境也沒有什麼內容,只有一些感受在我們體內浮動。
這些早期的感受,有些是驚奇,有些則帶著警告般的力量。而我們也從臨床經驗中明白:若一個人在這個階段無法好好整理這些感受,他後來的世界可能就會變得混亂,甚至失序。我們中有許多人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用科學的方式探索萬物,卻也同時排除了對內在感受、直覺與主觀經驗的重視。從某個角度來看,西方文化似乎傾向於用「思考」來取代「感受」;而在某些東方傳統中,則相反地忽視了科學所帶來的可靠方法。
不過,西方文化仍有其珍貴之處——我們努力以科學接近現實,也沒有完全遺棄音樂、繪畫、詩歌這些直觸人心的語言。在信仰與藝術之中,我們保留下來那種創造力的直覺,那些來自生命深處的原始感受。它們總是突然出現、無法被計算,卻能深刻表達一個人內在的真實狀態。
那麼,如果我們能同意心理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為什麼不讓它穩穩地立足,並延續著如科學那樣的知識傳統呢?在我看來,為什麼心理學會在所有科學的最後才出現?它緊接著生物學,而生物學在某種意義上,又接續於物理學。(當然,如今這些學科應當是並肩同行的。)顯而易見地,當一門科學與生命越靠近,它的語言與方法也就越難完全貼合科學的方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學生時代的我第一次讀到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時,內心激動不已,幾乎一氣呵成地讀完。那時我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就像濟慈在他的詩〈初讀查普曼譯荷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中所描寫的:
我彷彿是站在蒼穹之下的人,
凝望著一顆新行星劃過天際;
又或像武勇的科特茲⋯⋯
當時的我其實還不完全明白,為什麼這樣的閱讀會引起那麼大的激動。(譯按:那是一種「看見」的震撼,一種突如其來的、整體性的理解,就在你眼前綻放。)但後來我慢慢懂了,這份悸動來自於一種發現:原來「生命本身」,也能被放進科學的框架中去理解。
這樣的理解帶來了解放,它讓我不再對知識與理解之間的差距感到緊張,也讓我重新找回了那份能工作、能遊戲的自由能量。我相信,如果我今天還是學生,一定也能在某些書中找到那種讓人熱血沸騰的感覺,並願意在心中的知識地圖上,為心理學畫下一個屬於它的位置。不過,至今我還沒找到一本心理學的著作,能像《物種起源》那般具有標誌性。當然,《物種起源》今天也因包含過時的理論與錯誤而受到批評,但若真要談被批判的強度,心理學的經典著作往往面臨更激烈的質疑。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就是一例。
自從佛洛伊德寫下這本充滿遠見的著作以來,心理學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而其中許多里程碑仍可追溯到他本人。不過,即使是今天,一位精神分析師在推薦這本書時,仍會抱持謹慎態度,因為唯有在與他人共同討論、細讀並理解佛洛伊德所開啟的思想框架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本書的深度。若我們能夠按照時間軸閱讀他的著作,就會逐步看見他的思想如何一步步拓展出一個全新的領域。他不只是點燃一種新的方法,更親身承擔了這場探索的長程旅途。而如今,這份任務由他的後繼者們繼續承擔下來,也會在新的時代中,延伸出各自的方向。
現在,我想談談心理學作為科學所面臨的一個根本困難。我曾說過,科學訓練的重要性,在於它讓我們能夠穩穩地站在當下的立足點,看清我們所處的位置。然而,心理學所要站穩的那塊土地,並不只是觀察他人,而同時也必須回望自己。正因如此,它和其他科學截然不同,也永遠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我們不只是用儀器觀察對象——我們是用我們的心,去靠近另一顆心;我們是用我們的感覺,去體會另一個人的感受。
這就像在測試一台顯微鏡,而那台顯微鏡正是我們自己。(譯按:我們的觀察從來無法完全客觀,因為我們就是這場觀察的一部分。)這也難怪心理學會是科學的最後一門學科。也因此,有些人因此堅持:心理學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科學。事實上,學術心理學長期以來,都卡在這個問題上難以前進。但佛洛伊德選擇不退縮,以堅持不懈的精神,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而我們當中許多人也開始相信——在二十世紀初,他已經成功地為心理學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在佛洛伊德的經典著作《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正面面對那些被認為無法跨越的障礙。他用一種既大膽又嚴謹的方式,告訴我們:心理學也可以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他的做法非常特別,將其轉換為推進科學研究的助力。如果他要求病人記錄夢境的每個細節、相信其中意義,那他自己也必須願意這樣做——他必須有能力,也願意深入分析自己心中所生出的夢,並將它們誠實地攤開在學術討論的場域中。佛洛伊德對夢的探討是一種創新的思考模式。而他的許多見解,也確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佛洛伊德的另一本重要作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更進一步嘗試將心理學以科學的方式介紹給大眾。(譯按:他說明了我們日常中的錯誤、遺忘、口誤,都不是偶然,而可能隱藏著深層的心理動力。)他就像一位不斷向前的思想探險家,一邊書寫,一邊開拓。而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甚至還不知道這些書早已出版。我也懷疑,當時的我是否真的準備好,去理解那些如此深刻的作品。
如今,我更能理解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究竟面對著多大的挑戰,而佛洛伊德其實已經為我們踏出了第一步。在這裡,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概念:「無意識」。在一般語言裡,這個詞可能讓人聯想到暈倒或昏迷,但在心理學中,它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它指的是:在任何當下,我們其實都無法「完全覺察」我們能夠知道的一切。就像一位畫家在創作時,可能會感受到一種尚未顯影的圖像,那是一種從他生命深處浮現出來的感受,一種尚無語言可以描述的預感。這導致我們很難說「畫家能完全掌握自己的畫作」。(譯按:這些無法被完全意識到的經驗,不代表它們不存在;它們只是靜靜地待在我們內在的陰影裡,等待被看見、等待被理解。)
儘管在當時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佛洛伊德仍勇敢地踏進人類心靈最幽微深邃的角落。他用科學的方式,揭示了一個嶄新的觀念:「潛抑的無意識」。在這裡,無意識不只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是那些我們一度知道,但後來因為太痛苦、太難承受而被封鎖起來的真相。(譯按:它們之所以被遺忘,並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它們太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動用極大的心理能量來壓抑它們。然而,這股壓抑的力量會耗損我們原本可以用來熱愛生命、參與關係、創造未來的能量。也正是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療才會產生改變:當一個人不再需要那麼多力氣來「壓住痛苦」,他就能把這些力量用來過日子,用來愛人、感受、行動。
佛洛伊德發明了一種方法——它既是一種治療,也是一種對人類本質的深入研究工具。他讓精神分析不只是問診與對話,而是一種穩定、自由的空間,讓人的心可以真正開始「動起來」。在這個空間裡,來接受治療的人會慢慢地觸碰到自己最難面對的部分。而在與分析師的關係中,這些他無法單憑自己去觸及的事件與情感經驗,種種痛苦都逐漸浮現。如此一來,被阻礙的成長便得以展開。
讓我試著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描述: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一個人若想修正他過去經歷的某段傷痛——不管那是真實發生的,還是內在深處某種想像的記憶——,就要重訪那段過程。(譯按:而不是重演。)在一個安全、有節制的情感空間裡,那些原本太痛而無法面對的情緒,開始慢慢浮現出來。而分析師不急於處理或解釋,僅僅「在場」——陪著他一點一點去說、去感覺。這樣一種「簡化的場景」讓人得以重新經歷那段經驗。(譯按:但這次不再只有孤單與崩潰,有人能接得住他。)雖然相較起來,實際的臨床工作往往更複雜得多,但我相信這樣的描述可以幫助你抓到核心的意思。
在精神分析的關係中,分析師與來談的人,是並肩坐在同一張長椅上的兩個人,他們不是上對下的關係,也不是誰掌控誰的進程。這也正是精神分析在某些人心目中特別有力量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曾在權威關係中受過傷、不願再被控制的人。即使催眠或其他技術方法可以更快速地消除症狀,但它無法真正接觸到那個人與痛苦之間的真實關係。
佛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不只是為了治療,它更是一條更靠近科學真理的道路。它讓人開始相信:我們所經歷的情緒現象,其實可以以科學的方式去理解與研究;而我們對自我理解中的巨大空白,也不再是失敗與恐懼的來源。我們不再被焦慮驅使著,建構出各種錯誤的理論與人生信念。
你可以清楚地看見,精神分析帶來的一個重要改變,重新喚醒了邏輯的生命。曾幾何時,邏輯曾是思考的榮耀起點,但也快速地淪為冰冷無用的工具。人們曾希望透過「正確的思考方式」來控制人類的行為,期望以此建立更穩固的社會秩序。但這些企圖,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我們不是只有意識,我們還有無意識。那些不合理的行為、看似荒謬的信念,有時並不是邏輯錯了,而是這個人正在努力對抗一些他無法承受的內在真相。我們現在明白了:如果不考慮無意識的力量,任何「合理化」的努力都可能只是表面的假象。
透過精神分析,我們獲得了一種特別的理解方式:一種從混亂與不健康中長出來的頓悟(insight)。同時,因為精神分析,我們也開始理解:人有潛力將自己最原始的衝動——那些來自本能的能量——轉化為創造力、想像力,甚至是利他的行為。這樣的轉化不是壓抑,而是一種成熟的妥協:我們既保留了內在的火,也尊重了外在的邊界。這讓人可以活出更整合、更自由的自己,而不必犧牲與社會的連結。
當我們深入研究那些患有神經官能症的個案時,幾乎總能發現一個共通點:他們在童年早期的情緒發展歷程中,曾遭遇重大的阻礙。尤其二歲、三歲、四歲這個階段的孩子,正經歷最初的人際關係、學習信任與分離的時期——如果此時發生強烈的不安或情緒衝突,很容易種下深遠的焦慮種子。為了生存,孩子會發展出一套防衛機制,而這些防衛,有時日後就會以神經性症狀或角色混淆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個年紀的孩子,其人格還在慢慢形成。他們的「自我」正在學習如何整合來自本能的驅力、環境的要求,以及逐漸內化的「超我」——那是一種從重要他人身上學來的價值感與內在規則。
此時此刻,一個穩定而溫暖的環境至關重要。因為孩子會拿周圍的大人作為心理建構的藍圖,並在過程中逐步形成「超我」——去想像什麼是「允許」、什麼是「禁止」、什麼是「被愛」的條件。(在我的述說中常使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但日常中,它們其實沒有使用上的必要,只是建構理論時與討論時的符號。)而在更嚴重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一些被標記為「精神病」的症狀,其根源甚至不只是早期童年,而是更早、更原始的嬰兒階段。在那個時期,孩子的人格尚未整合,他還無法分清什麼是內在的幻想、什麼是外在的現實,他與世界的溝通還非常脆弱。(譯按:孩子依賴外界的回應是否一致、可預測、溫柔。如果那時的環境是混亂、忽冷忽熱或情感斷裂的,那麼孩子可能連最基本的「我在這裡、我是誰」的感覺都尚未建立。這種早期的失落,後來會以更深層的方式出現,讓一個人難以與現實建立穩定的關係。)
因此,精神分析發展出一種精緻、嶄新的方法,讓我們得以研究人類自己,也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是一種工具——深刻、複雜,但仍然只是工具。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信仰。佛洛伊德本人就曾明白地說過:精神分析不能代替信仰,也不能替人生困難找出所有答案。對於初次接觸這門學問的人來說,這是重要的提醒。
人們常常問我:接受精神分析,真的能讓生活變得輕鬆嗎?但我要說,如果有誰聲稱做了什麼就可以保證輕鬆,那恐怕我們也該對這樣的承諾多些懷疑。精神分析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痛苦的過程,它不能改變生活艱難的事實;它帶來的最好結果,也許是:一個人不再覺得自己被命運拖著走,而是逐漸能夠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回應人生的困難與矛盾。於是,他開始成長,變得成熟,並在過程中建立起更穩定的自我,也更能與這個社會產生真實的連結。
第6章 兒童的拒絕入睡
在漢諾克(Edouard Henoch, 1820-1910)關於兒童疾病的演講中,他的觀察相當值得注意。他並未將「無法入睡」(sleeplessness)列入症狀索引中,而是將這一現象歸類於「夜驚」(pavor nocturnus)的一部分。他對於我們今日所稱為「小兒科」這整個領域的觀察具體而微,極具啟發性。我們只能設想,在他所處的年代(大約是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五年間),在他診所接觸的七千八百一十五位兩歲以下兒童中,有五千三百六十八名死亡(約佔百分之七十);而兩歲以上的六千一百六十五位兒童中,則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人死亡(約佔百分之二十三)。在那個時代,兒童死亡率之高,使得生理因素無疑成為首要的關注焦點。相較之下,孩子無法入睡的問題或許顯得微不足道。然而,正如我們今日所了解的,兒童的睡眠困難,很可能使得父母與孩子本身都無比困擾。
如今我們能夠自由地觀察那些身心健康,但情緒上受困的孩子,也能觀察他們所表現出的種種異常狀況,因此,我們其實有機會深入探究睡眠困擾所隱含的意義,與可能的「益處」。例如,在那些拒絕入睡的案例中,孩子似乎是「故意」維持清醒狀態的。在這裡,我們面對的問題,與其說是單純的睡眠障礙,不如說更接近於「拒學症」的情境,這當中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期待與主動性。當然,每一個案例都牽涉到無意識的動機:這些動機是潛抑的成分,隱藏在孩子與父母的內心深處,卻共同構成並決定了這些異常現象的互動性質。
睡眠困擾這個主題本身十分龐大,但在此我們可以將焦點縮限在「拒絕入睡」的現象上。如此一來,我們也許能指出其中一兩項重要的特徵,而無需對「人性」這深奧的課題提出太過顛覆性的見解。
睡眠障礙的核心在於焦慮。有時,孩子在睡眠中經歷了難以忍受的惡夢,而在驚醒後才得以解除那份恐懼;若無法解除,他就會開始害怕入睡,因為夢境對他來說,已然成為威脅現實生活的因素。另一方面,有些困難則發生在孩子從清醒進入夢境的過渡狀態之中,這段時間介於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常常伴隨著極大的不安感。
然而,這些過渡的危險時刻所感到的不安,往往來自於過往經驗的身體記憶,或許可以追溯到嬰兒時期,因此孩子可能會有吸吮拇指或其他的衍生行為。這些手段能夠幫助孩子穿越那段充滿幻覺與錯亂感的短暫時光,使他回到可被掌控與信任的內在世界中。這一切現象,都屬於人性的本質,屬於每個個體在人生成長過程中,透過情緒的逐漸發展而完成的任務。這樣的成長由遺傳的整合力量所支撐,也受到內在促進成熟與發展的方向性所引導。而這些發展都需要依賴一個「夠好環境」(a good-enough environment)才有可能實現。
這些因素交織極為複雜,並在不同理論體系中被賦予了各異的名稱與定義。對於這些現象,各領域的工作者(包括治療師與學者)已在許多層面上達到相當一致的理解,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本能驅力所帶來的興奮,並且都認為:無論這種興奮是全身性的還是局部性的,都可能引發睡眠障礙中那種突如其來、急性而劇烈的特質,例如我們所熟知的惡夢。
「拒絕入睡」(sleep refusal)這個說法,或許正好提醒我們注意某種特定型態的睡眠困擾。例如,孩子不願入睡,或甚至不想「嘗試去睡覺」;或者他只能在家庭生活的嘈雜背景中入眠;必須有母親陪伴才睡得著;又或者一旦父母離開去上床睡覺,他便會立刻驚醒。在這類型的睡眠困難中,我們必須特別留意「母親」的角色,或更廣泛地說,其實父母都參與其中,成為這場睡眠障礙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所有這類案例中,父母的介入常常提供了重要線索;甚至可以說,至少其部分地揭示了這一障礙的成因。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有時候,造成這些睡眠困擾的,反而是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訊息,它們或許不具備明確意義,卻蘊含於父母態度中的無意識元素。例如,孩子到姨媽家暫住幾天時,睡眠情況可能就完全正常、沒有任何問題。無論如何,在這些例子中,真正的困難往往不在孩子本身,而是父母在撫育歷程中的某種挫敗。這些挫敗來自於更深層、更複雜的家庭情境,也就是孩子是否真實地處於一個「夠好」的促發性環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之中。這樣的「夠好環境」能夠結合出一種有彈性的調適與情緒的承載方式,既符合孩子的發展需求,也讓孩子能夠安然地生活於白日與黑夜之間。也就是說,在這個促發性的環境中,人類能夠如其所是地活著:擁有自己的生活與情感,也會有疲憊與惱怒,有個人的脆弱面,但仍然維持一致的態度,並且能夠思考這些生命條件所構成的主要趨勢與細微差異。
父母有著他們自身的困境,他們在自我防衛的心理組織中,壓抑了某些情感素材。在此,不妨讓我們稍微發揮一些想像力:設想有一對夫婦,已有兩個或三個孩子。他們並不希望再有更多小孩,因此,性生活的協調與滿意度逐漸降低,對於避孕的討論也更加難以啟齒。然而,在這樣的情境下,夫妻其中一方可能依然非常容易受到本能的興奮所激發。也正因如此,在缺乏充足時間與空間進行心理整合與反思的情況下,意外往往就此發生。
而當父母在一起時,某個孩子剛好「需要被特別關注」,這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再方便不過的安排了!如果這一點沒有被覺察,那麼孩子便很容易適應這樣一個被指派的角色,成為那個讓父母得以「避孕」的存在。
對孩子而言,這其實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因為這樣的安排往往伴隨著父母之間的疏離,而孩子也可能發現,自己無法真正享受那個「家中的掌控者」,甚至「整個世界的控制者」的角色。久而久之,甚至會對這種掌控感產生一種厭煩與疲憊。這樣的情緒狀態,往往也會延伸到夜晚,導致孩子無法入睡;接著,在白天表現出易怒、煩躁,並衍生出一系列次發性的心理或行為症狀。
由此看來,對這樣的孩子使用安眠藥來解決問題,幾乎註定徒勞無功,甚至可以說,一開始就不應該這麼做。同樣地,若醫師以強勢的方式介入,無論是以隱喻的形式,還是更直接的方式,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命運。這是因為孩子根本不知道,他們此刻的行為,其實是在替父母的生活困境提供一種「解方」;甚至連父母自己,也未必清楚這一點,或頂多只能稍稍有所覺察。
在這種情況下,最殘忍的事之一,莫過於去批評或嚴厲教訓父母。即使是給予建議,也可能是不智之舉。那麼,身為臨床工作者究竟該說些什麼呢?除了「改變你的狀態」、「試著了解你其實還不認識你自己」、「只需要好好思考你自己」這類話之外,又還能說什麼?醫生又清楚他必須考量眾多其他因素,例如對每個孩子需求的調適,還得遵守無數的社會規範與期待。同時,我們也千萬別忘了——醫生自己,也可能正深陷於和病人一樣的困境之中。
或許,最好的方式,是什麼都不去做,而是學著去「容忍」這樣混亂、困頓的狀況。(譯按:讓它被經歷、被承受,直到它有機會可以自行從生活褪去。)然而,也有人會這麼說:我們仍需要「個案工作」,也就是由一位具有結構性與專業知能的社工師進行介入,並且持續一段時間,使彼此之間能夠建立信任,進而讓洞察的回饋得以自然地發展。
透過自身的想像與經驗,一個人不僅能建構出一個複雜的困難處境,也可能逐步發展出一種自我:這個「自我」,透過思緒的日益清晰,並從父母部分的覺察與放手中獲得自由。如此,個體便能在生活中尋找一種能夠整合各種需求的「管理技術」。也許,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臨床工作者總是渴望「治癒」他的病人;但在這類工作中,他必須學會等待:等待個體自身,以及整個社會的演化與轉化。
今天我受邀與各位分享關於心理學的背景、假設與其帶來的發現。這是一個範圍極廣的主題,而我必須誠實地承認,我能呈現的,只是我個人視野中一小部分的體會。這就像站在一片森林前,我僅能描繪我曾穿行的那一條小徑。
我也明白,坐在這裡的每一位,都會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來聆聽我說的話。有些人習慣實驗與證據、有些人偏好歷史與事實的軌跡、有些人則深信直覺,喜歡以主觀的方式接觸新知。既然我無法一次回應所有視角,那麼今天我選擇誠實地,向大家呈現我自己的方法與眼光。
我想先提出一個核心觀點:「心理學」其實是一門關於人類本質的探究,就如同物理、生理或生物學一般,是科學的一支。這是我一貫的信念,也是我今日所要分享的起點。這篇講稿原初的雛形在我一位親愛的同事馬蘇可汗(Masud Khan)的建議下改進許多。對我來說,這樣的視角不是偶然,而是一生投入的方向。我想讓各位知道,我的身分不只是醫師,同時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師,而這樣的身份深深影響我理解「人是什麼」的方式。
直到近年來,精神分析才開始被視為一門可以嚴肅對待的學問。它逐漸成為我們社會中談論心理的共通語言,不過使用這些詞語時,日常與專業之間仍存在著深刻的差異。如果你問一位醫師,精神分析如今在醫學或人性研究中有什麼價值,可能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畢竟,從醫療角度審視個案背後的心理脈絡,仍是一種尚在發展的新觀念,尚未被廣泛實踐。
在座的各位當中,也許有些人未來會成為醫師,少數人甚至可能投身於深入心靈工作的領域。除了醫學知識,這條路也需要心理與精神分析的訓練。但就算你只想成為一位能照顧病患全人經驗的家庭醫師,這樣的理解與培養,也都將為你帶來莫大的幫助。
心理學若想真正成為探究人類本質的學問,就必須走上一條科學的道路。當然,我們也能透過感受與直覺來理解像莎士比亞這樣的藝術家——他的作品本身就是對人性深刻的感知。但如果我們願意讓心理學成為一門可驗證、可傳承的知識體系,那麼每一步的科學進展,都會讓我們在閱讀莎士比亞時看得更深,也更少落入空泛的論調。我們必須持續談論人類的本質,而當心理學的語言能帶出真正的內容、能經得起檢驗,那麼它也就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其實,這並不是說在精神分析進入醫療領域以前,心理上的療癒就不存在。一直以來,一位好的醫師同時也需要是一位有同理心的心理觀察者——他要能理解病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也能觸碰病人內在的掙扎與感受。但即使如此,當醫師試圖談論人類本質時,仍可能說出許多不著邊際的話。直覺雖然在日常中偶有洞見,但在面對複雜的人性議題時卻不總是可靠的。它或許能幫助一位醫師理解一名偷竊病人的苦衷,卻無法作為建立「偷竊行為心理學」的基礎。在需要下判斷與做決策的情境中,比如少年法庭,我們更需要能被討論、被驗證的知識,而不是憑感覺說出的意見。
醫學生會經歷長年艱苦的訓練,但這條路並不一定能培養他們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反而可能阻礙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從十八歲開始,一路忙碌到二十五歲,有時回過頭來,已走進中年的門檻。為了在職涯上趕上同行,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於臨床實務中,往往無暇過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與此同時,曾經一起長大的朋友們,或許早已在二十五歲時就展開了屬於自己的人生風景。
也許你已經開始看見,探索人類本質的科學旅程正穩步前行。我們透過觀察尋找線索,建立理論,再用新發現來修正舊有的理解。這是一條不斷接近真理的道路。然而你是否也察覺,科學與直覺之間,根本上的差異?真正的直覺有時能如閃電般指向核心,也有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通向錯誤。與此相比,科學從不聲稱自己掌握「全部的真理」;它所做的,是誠實地建構出一條通往真理的橋樑。這就是為什麼科學訓練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如此重要——它教我們如何腳踏實地地站在當下,並回頭看我們所立足的這片土地。我們的感受與想像可能會跌跤,也可能引我們偏離方向。然而這些時刻,也允許我們夢想與飛翔,即便下一瞬間是失落與墜落。那麼,我們不斷掉落——直到醒來,直到我們回到那個可檢驗、可接納我們的世界:一個名為科學的現實空間。
你曾經這樣想像過「科學」嗎?一門學問若發現某些尚未解釋的現象,如果我們對此一片空白,那麼就記錄它,將它作為未來研究的起點。對於依賴直覺的人,這些尚未串連起來的空白是未知的鴻溝,也許令人恐慌;但物理學家可能會說,那只是一種尚未被發現的元素。不必驚慌,因為總有一天,它會自然嵌入世界的秩序中。像「M&B」這類藥物的療效,初被發現時,科學家或許尚不理解其原理,但他們不會輕易將之視為奇蹟。他們只是繼續研究,慢慢找出答案。即使,至今依然無法掌握世上所有的知識,也沒關係。
心理學的知識與經驗之間,存在著更巨大的落差。但如果我們願意以科學的態度來面對,那麼即使那些直覺派的人說:「我們早就知道了!」我們也可以坦然面對,因為他們並沒有指出那些同時存在的混亂與偏差。真正的科學精神,讓我們得以自在地說「我們還不知道」,而不用發明華麗卻空洞的理論,來填補那些還未看清的部分。
當我們還是嬰兒——甚至剛出生——的時候,我們就像小小的科學家一樣,用身體、感官與心靈去探索這個世界。若我們在那個階段擁有了「夠好」的照顧,一切就不會變得混亂難解。我們靠著想像力先構築了自己的世界,然後慢慢讓真實的世界走進來、與我們相遇。那是一種由外而內的轉化:我們依賴外在事物,因為我們可以用它們來成為「我們自己」。這些事物,即便有時會讓我們生氣,比如餓了還得等待,它們的存在依然是無比珍貴的。因為那真實的外在世界幫助我們忍受那種「一切皆有可能」的魔幻想像。那時,我們的經驗還很原始,夢境也沒有什麼內容,只有一些感受在我們體內浮動。
這些早期的感受,有些是驚奇,有些則帶著警告般的力量。而我們也從臨床經驗中明白:若一個人在這個階段無法好好整理這些感受,他後來的世界可能就會變得混亂,甚至失序。我們中有許多人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用科學的方式探索萬物,卻也同時排除了對內在感受、直覺與主觀經驗的重視。從某個角度來看,西方文化似乎傾向於用「思考」來取代「感受」;而在某些東方傳統中,則相反地忽視了科學所帶來的可靠方法。
不過,西方文化仍有其珍貴之處——我們努力以科學接近現實,也沒有完全遺棄音樂、繪畫、詩歌這些直觸人心的語言。在信仰與藝術之中,我們保留下來那種創造力的直覺,那些來自生命深處的原始感受。它們總是突然出現、無法被計算,卻能深刻表達一個人內在的真實狀態。
那麼,如果我們能同意心理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為什麼不讓它穩穩地立足,並延續著如科學那樣的知識傳統呢?在我看來,為什麼心理學會在所有科學的最後才出現?它緊接著生物學,而生物學在某種意義上,又接續於物理學。(當然,如今這些學科應當是並肩同行的。)顯而易見地,當一門科學與生命越靠近,它的語言與方法也就越難完全貼合科學的方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學生時代的我第一次讀到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時,內心激動不已,幾乎一氣呵成地讀完。那時我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就像濟慈在他的詩〈初讀查普曼譯荷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中所描寫的:
我彷彿是站在蒼穹之下的人,
凝望著一顆新行星劃過天際;
又或像武勇的科特茲⋯⋯
當時的我其實還不完全明白,為什麼這樣的閱讀會引起那麼大的激動。(譯按:那是一種「看見」的震撼,一種突如其來的、整體性的理解,就在你眼前綻放。)但後來我慢慢懂了,這份悸動來自於一種發現:原來「生命本身」,也能被放進科學的框架中去理解。
這樣的理解帶來了解放,它讓我不再對知識與理解之間的差距感到緊張,也讓我重新找回了那份能工作、能遊戲的自由能量。我相信,如果我今天還是學生,一定也能在某些書中找到那種讓人熱血沸騰的感覺,並願意在心中的知識地圖上,為心理學畫下一個屬於它的位置。不過,至今我還沒找到一本心理學的著作,能像《物種起源》那般具有標誌性。當然,《物種起源》今天也因包含過時的理論與錯誤而受到批評,但若真要談被批判的強度,心理學的經典著作往往面臨更激烈的質疑。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就是一例。
自從佛洛伊德寫下這本充滿遠見的著作以來,心理學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而其中許多里程碑仍可追溯到他本人。不過,即使是今天,一位精神分析師在推薦這本書時,仍會抱持謹慎態度,因為唯有在與他人共同討論、細讀並理解佛洛伊德所開啟的思想框架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本書的深度。若我們能夠按照時間軸閱讀他的著作,就會逐步看見他的思想如何一步步拓展出一個全新的領域。他不只是點燃一種新的方法,更親身承擔了這場探索的長程旅途。而如今,這份任務由他的後繼者們繼續承擔下來,也會在新的時代中,延伸出各自的方向。
現在,我想談談心理學作為科學所面臨的一個根本困難。我曾說過,科學訓練的重要性,在於它讓我們能夠穩穩地站在當下的立足點,看清我們所處的位置。然而,心理學所要站穩的那塊土地,並不只是觀察他人,而同時也必須回望自己。正因如此,它和其他科學截然不同,也永遠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我們不只是用儀器觀察對象——我們是用我們的心,去靠近另一顆心;我們是用我們的感覺,去體會另一個人的感受。
這就像在測試一台顯微鏡,而那台顯微鏡正是我們自己。(譯按:我們的觀察從來無法完全客觀,因為我們就是這場觀察的一部分。)這也難怪心理學會是科學的最後一門學科。也因此,有些人因此堅持:心理學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科學。事實上,學術心理學長期以來,都卡在這個問題上難以前進。但佛洛伊德選擇不退縮,以堅持不懈的精神,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而我們當中許多人也開始相信——在二十世紀初,他已經成功地為心理學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在佛洛伊德的經典著作《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正面面對那些被認為無法跨越的障礙。他用一種既大膽又嚴謹的方式,告訴我們:心理學也可以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他的做法非常特別,將其轉換為推進科學研究的助力。如果他要求病人記錄夢境的每個細節、相信其中意義,那他自己也必須願意這樣做——他必須有能力,也願意深入分析自己心中所生出的夢,並將它們誠實地攤開在學術討論的場域中。佛洛伊德對夢的探討是一種創新的思考模式。而他的許多見解,也確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佛洛伊德的另一本重要作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更進一步嘗試將心理學以科學的方式介紹給大眾。(譯按:他說明了我們日常中的錯誤、遺忘、口誤,都不是偶然,而可能隱藏著深層的心理動力。)他就像一位不斷向前的思想探險家,一邊書寫,一邊開拓。而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甚至還不知道這些書早已出版。我也懷疑,當時的我是否真的準備好,去理解那些如此深刻的作品。
如今,我更能理解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究竟面對著多大的挑戰,而佛洛伊德其實已經為我們踏出了第一步。在這裡,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概念:「無意識」。在一般語言裡,這個詞可能讓人聯想到暈倒或昏迷,但在心理學中,它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它指的是:在任何當下,我們其實都無法「完全覺察」我們能夠知道的一切。就像一位畫家在創作時,可能會感受到一種尚未顯影的圖像,那是一種從他生命深處浮現出來的感受,一種尚無語言可以描述的預感。這導致我們很難說「畫家能完全掌握自己的畫作」。(譯按:這些無法被完全意識到的經驗,不代表它們不存在;它們只是靜靜地待在我們內在的陰影裡,等待被看見、等待被理解。)
儘管在當時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佛洛伊德仍勇敢地踏進人類心靈最幽微深邃的角落。他用科學的方式,揭示了一個嶄新的觀念:「潛抑的無意識」。在這裡,無意識不只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是那些我們一度知道,但後來因為太痛苦、太難承受而被封鎖起來的真相。(譯按:它們之所以被遺忘,並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它們太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動用極大的心理能量來壓抑它們。然而,這股壓抑的力量會耗損我們原本可以用來熱愛生命、參與關係、創造未來的能量。也正是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療才會產生改變:當一個人不再需要那麼多力氣來「壓住痛苦」,他就能把這些力量用來過日子,用來愛人、感受、行動。
佛洛伊德發明了一種方法——它既是一種治療,也是一種對人類本質的深入研究工具。他讓精神分析不只是問診與對話,而是一種穩定、自由的空間,讓人的心可以真正開始「動起來」。在這個空間裡,來接受治療的人會慢慢地觸碰到自己最難面對的部分。而在與分析師的關係中,這些他無法單憑自己去觸及的事件與情感經驗,種種痛苦都逐漸浮現。如此一來,被阻礙的成長便得以展開。
讓我試著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描述: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一個人若想修正他過去經歷的某段傷痛——不管那是真實發生的,還是內在深處某種想像的記憶——,就要重訪那段過程。(譯按:而不是重演。)在一個安全、有節制的情感空間裡,那些原本太痛而無法面對的情緒,開始慢慢浮現出來。而分析師不急於處理或解釋,僅僅「在場」——陪著他一點一點去說、去感覺。這樣一種「簡化的場景」讓人得以重新經歷那段經驗。(譯按:但這次不再只有孤單與崩潰,有人能接得住他。)雖然相較起來,實際的臨床工作往往更複雜得多,但我相信這樣的描述可以幫助你抓到核心的意思。
在精神分析的關係中,分析師與來談的人,是並肩坐在同一張長椅上的兩個人,他們不是上對下的關係,也不是誰掌控誰的進程。這也正是精神分析在某些人心目中特別有力量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曾在權威關係中受過傷、不願再被控制的人。即使催眠或其他技術方法可以更快速地消除症狀,但它無法真正接觸到那個人與痛苦之間的真實關係。
佛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不只是為了治療,它更是一條更靠近科學真理的道路。它讓人開始相信:我們所經歷的情緒現象,其實可以以科學的方式去理解與研究;而我們對自我理解中的巨大空白,也不再是失敗與恐懼的來源。我們不再被焦慮驅使著,建構出各種錯誤的理論與人生信念。
你可以清楚地看見,精神分析帶來的一個重要改變,重新喚醒了邏輯的生命。曾幾何時,邏輯曾是思考的榮耀起點,但也快速地淪為冰冷無用的工具。人們曾希望透過「正確的思考方式」來控制人類的行為,期望以此建立更穩固的社會秩序。但這些企圖,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我們不是只有意識,我們還有無意識。那些不合理的行為、看似荒謬的信念,有時並不是邏輯錯了,而是這個人正在努力對抗一些他無法承受的內在真相。我們現在明白了:如果不考慮無意識的力量,任何「合理化」的努力都可能只是表面的假象。
透過精神分析,我們獲得了一種特別的理解方式:一種從混亂與不健康中長出來的頓悟(insight)。同時,因為精神分析,我們也開始理解:人有潛力將自己最原始的衝動——那些來自本能的能量——轉化為創造力、想像力,甚至是利他的行為。這樣的轉化不是壓抑,而是一種成熟的妥協:我們既保留了內在的火,也尊重了外在的邊界。這讓人可以活出更整合、更自由的自己,而不必犧牲與社會的連結。
當我們深入研究那些患有神經官能症的個案時,幾乎總能發現一個共通點:他們在童年早期的情緒發展歷程中,曾遭遇重大的阻礙。尤其二歲、三歲、四歲這個階段的孩子,正經歷最初的人際關係、學習信任與分離的時期——如果此時發生強烈的不安或情緒衝突,很容易種下深遠的焦慮種子。為了生存,孩子會發展出一套防衛機制,而這些防衛,有時日後就會以神經性症狀或角色混淆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個年紀的孩子,其人格還在慢慢形成。他們的「自我」正在學習如何整合來自本能的驅力、環境的要求,以及逐漸內化的「超我」——那是一種從重要他人身上學來的價值感與內在規則。
此時此刻,一個穩定而溫暖的環境至關重要。因為孩子會拿周圍的大人作為心理建構的藍圖,並在過程中逐步形成「超我」——去想像什麼是「允許」、什麼是「禁止」、什麼是「被愛」的條件。(在我的述說中常使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但日常中,它們其實沒有使用上的必要,只是建構理論時與討論時的符號。)而在更嚴重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一些被標記為「精神病」的症狀,其根源甚至不只是早期童年,而是更早、更原始的嬰兒階段。在那個時期,孩子的人格尚未整合,他還無法分清什麼是內在的幻想、什麼是外在的現實,他與世界的溝通還非常脆弱。(譯按:孩子依賴外界的回應是否一致、可預測、溫柔。如果那時的環境是混亂、忽冷忽熱或情感斷裂的,那麼孩子可能連最基本的「我在這裡、我是誰」的感覺都尚未建立。這種早期的失落,後來會以更深層的方式出現,讓一個人難以與現實建立穩定的關係。)
因此,精神分析發展出一種精緻、嶄新的方法,讓我們得以研究人類自己,也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是一種工具——深刻、複雜,但仍然只是工具。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信仰。佛洛伊德本人就曾明白地說過:精神分析不能代替信仰,也不能替人生困難找出所有答案。對於初次接觸這門學問的人來說,這是重要的提醒。
人們常常問我:接受精神分析,真的能讓生活變得輕鬆嗎?但我要說,如果有誰聲稱做了什麼就可以保證輕鬆,那恐怕我們也該對這樣的承諾多些懷疑。精神分析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痛苦的過程,它不能改變生活艱難的事實;它帶來的最好結果,也許是:一個人不再覺得自己被命運拖著走,而是逐漸能夠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回應人生的困難與矛盾。於是,他開始成長,變得成熟,並在過程中建立起更穩定的自我,也更能與這個社會產生真實的連結。
第6章 兒童的拒絕入睡
在漢諾克(Edouard Henoch, 1820-1910)關於兒童疾病的演講中,他的觀察相當值得注意。他並未將「無法入睡」(sleeplessness)列入症狀索引中,而是將這一現象歸類於「夜驚」(pavor nocturnus)的一部分。他對於我們今日所稱為「小兒科」這整個領域的觀察具體而微,極具啟發性。我們只能設想,在他所處的年代(大約是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五年間),在他診所接觸的七千八百一十五位兩歲以下兒童中,有五千三百六十八名死亡(約佔百分之七十);而兩歲以上的六千一百六十五位兒童中,則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人死亡(約佔百分之二十三)。在那個時代,兒童死亡率之高,使得生理因素無疑成為首要的關注焦點。相較之下,孩子無法入睡的問題或許顯得微不足道。然而,正如我們今日所了解的,兒童的睡眠困難,很可能使得父母與孩子本身都無比困擾。
如今我們能夠自由地觀察那些身心健康,但情緒上受困的孩子,也能觀察他們所表現出的種種異常狀況,因此,我們其實有機會深入探究睡眠困擾所隱含的意義,與可能的「益處」。例如,在那些拒絕入睡的案例中,孩子似乎是「故意」維持清醒狀態的。在這裡,我們面對的問題,與其說是單純的睡眠障礙,不如說更接近於「拒學症」的情境,這當中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期待與主動性。當然,每一個案例都牽涉到無意識的動機:這些動機是潛抑的成分,隱藏在孩子與父母的內心深處,卻共同構成並決定了這些異常現象的互動性質。
睡眠困擾這個主題本身十分龐大,但在此我們可以將焦點縮限在「拒絕入睡」的現象上。如此一來,我們也許能指出其中一兩項重要的特徵,而無需對「人性」這深奧的課題提出太過顛覆性的見解。
睡眠障礙的核心在於焦慮。有時,孩子在睡眠中經歷了難以忍受的惡夢,而在驚醒後才得以解除那份恐懼;若無法解除,他就會開始害怕入睡,因為夢境對他來說,已然成為威脅現實生活的因素。另一方面,有些困難則發生在孩子從清醒進入夢境的過渡狀態之中,這段時間介於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常常伴隨著極大的不安感。
然而,這些過渡的危險時刻所感到的不安,往往來自於過往經驗的身體記憶,或許可以追溯到嬰兒時期,因此孩子可能會有吸吮拇指或其他的衍生行為。這些手段能夠幫助孩子穿越那段充滿幻覺與錯亂感的短暫時光,使他回到可被掌控與信任的內在世界中。這一切現象,都屬於人性的本質,屬於每個個體在人生成長過程中,透過情緒的逐漸發展而完成的任務。這樣的成長由遺傳的整合力量所支撐,也受到內在促進成熟與發展的方向性所引導。而這些發展都需要依賴一個「夠好環境」(a good-enough environment)才有可能實現。
這些因素交織極為複雜,並在不同理論體系中被賦予了各異的名稱與定義。對於這些現象,各領域的工作者(包括治療師與學者)已在許多層面上達到相當一致的理解,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本能驅力所帶來的興奮,並且都認為:無論這種興奮是全身性的還是局部性的,都可能引發睡眠障礙中那種突如其來、急性而劇烈的特質,例如我們所熟知的惡夢。
「拒絕入睡」(sleep refusal)這個說法,或許正好提醒我們注意某種特定型態的睡眠困擾。例如,孩子不願入睡,或甚至不想「嘗試去睡覺」;或者他只能在家庭生活的嘈雜背景中入眠;必須有母親陪伴才睡得著;又或者一旦父母離開去上床睡覺,他便會立刻驚醒。在這類型的睡眠困難中,我們必須特別留意「母親」的角色,或更廣泛地說,其實父母都參與其中,成為這場睡眠障礙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所有這類案例中,父母的介入常常提供了重要線索;甚至可以說,至少其部分地揭示了這一障礙的成因。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有時候,造成這些睡眠困擾的,反而是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訊息,它們或許不具備明確意義,卻蘊含於父母態度中的無意識元素。例如,孩子到姨媽家暫住幾天時,睡眠情況可能就完全正常、沒有任何問題。無論如何,在這些例子中,真正的困難往往不在孩子本身,而是父母在撫育歷程中的某種挫敗。這些挫敗來自於更深層、更複雜的家庭情境,也就是孩子是否真實地處於一個「夠好」的促發性環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之中。這樣的「夠好環境」能夠結合出一種有彈性的調適與情緒的承載方式,既符合孩子的發展需求,也讓孩子能夠安然地生活於白日與黑夜之間。也就是說,在這個促發性的環境中,人類能夠如其所是地活著:擁有自己的生活與情感,也會有疲憊與惱怒,有個人的脆弱面,但仍然維持一致的態度,並且能夠思考這些生命條件所構成的主要趨勢與細微差異。
父母有著他們自身的困境,他們在自我防衛的心理組織中,壓抑了某些情感素材。在此,不妨讓我們稍微發揮一些想像力:設想有一對夫婦,已有兩個或三個孩子。他們並不希望再有更多小孩,因此,性生活的協調與滿意度逐漸降低,對於避孕的討論也更加難以啟齒。然而,在這樣的情境下,夫妻其中一方可能依然非常容易受到本能的興奮所激發。也正因如此,在缺乏充足時間與空間進行心理整合與反思的情況下,意外往往就此發生。
而當父母在一起時,某個孩子剛好「需要被特別關注」,這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再方便不過的安排了!如果這一點沒有被覺察,那麼孩子便很容易適應這樣一個被指派的角色,成為那個讓父母得以「避孕」的存在。
對孩子而言,這其實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因為這樣的安排往往伴隨著父母之間的疏離,而孩子也可能發現,自己無法真正享受那個「家中的掌控者」,甚至「整個世界的控制者」的角色。久而久之,甚至會對這種掌控感產生一種厭煩與疲憊。這樣的情緒狀態,往往也會延伸到夜晚,導致孩子無法入睡;接著,在白天表現出易怒、煩躁,並衍生出一系列次發性的心理或行為症狀。
由此看來,對這樣的孩子使用安眠藥來解決問題,幾乎註定徒勞無功,甚至可以說,一開始就不應該這麼做。同樣地,若醫師以強勢的方式介入,無論是以隱喻的形式,還是更直接的方式,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命運。這是因為孩子根本不知道,他們此刻的行為,其實是在替父母的生活困境提供一種「解方」;甚至連父母自己,也未必清楚這一點,或頂多只能稍稍有所覺察。
在這種情況下,最殘忍的事之一,莫過於去批評或嚴厲教訓父母。即使是給予建議,也可能是不智之舉。那麼,身為臨床工作者究竟該說些什麼呢?除了「改變你的狀態」、「試著了解你其實還不認識你自己」、「只需要好好思考你自己」這類話之外,又還能說什麼?醫生又清楚他必須考量眾多其他因素,例如對每個孩子需求的調適,還得遵守無數的社會規範與期待。同時,我們也千萬別忘了——醫生自己,也可能正深陷於和病人一樣的困境之中。
或許,最好的方式,是什麼都不去做,而是學著去「容忍」這樣混亂、困頓的狀況。(譯按:讓它被經歷、被承受,直到它有機會可以自行從生活褪去。)然而,也有人會這麼說:我們仍需要「個案工作」,也就是由一位具有結構性與專業知能的社工師進行介入,並且持續一段時間,使彼此之間能夠建立信任,進而讓洞察的回饋得以自然地發展。
透過自身的想像與經驗,一個人不僅能建構出一個複雜的困難處境,也可能逐步發展出一種自我:這個「自我」,透過思緒的日益清晰,並從父母部分的覺察與放手中獲得自由。如此,個體便能在生活中尋找一種能夠整合各種需求的「管理技術」。也許,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臨床工作者總是渴望「治癒」他的病人;但在這類工作中,他必須學會等待:等待個體自身,以及整個社會的演化與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