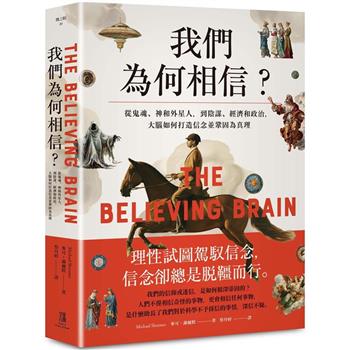第二章 柯林斯博士的轉變
你現在可能在想,「拜託!這跟我有什麼關係?這個達皮諾是砌磚工人欸,我的信念是基於合理的分析和受過教育的考量。我從來沒有聽過什麼聲音,也沒有想去見總統。我的大腦和信念都好得很,謝了。」
這就是為什麼在繼達皮諾的故事之後,我要介紹法蘭西斯‧柯林斯博士(Francis Collins)。他是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醫生,曾任人類基因組計畫負責人、現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榮獲總統自由勳章,也是地位崇高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羅馬教皇科學院院士,而這些不過是他的部分成就。柯林斯博士也經歷過一次改變人生的頓悟,同樣也是在清晨,促使他成為一名熱於分享的重生福音派基督徒,還寫了一本暢銷書,講述他從鐵桿無神論者轉變為熱忱信徒的經歷和旅程。你可能會認為自己能對砌磚匠故事中所展現的信念力量免疫,但我相信本書的讀者,應該沒有幾個人敢說自己擁有柯林斯的智力或科學資歷,畢竟他是當代最聰明的人之一。如果這種事能發生在他身上,那麼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事實上,正如我在本書中所論證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信念的力量,只是強度不一,還有出現在生命中的階段和時期不同。柯林斯博士的信仰之路,細節之處與達皮諾的截然不同,但信念如何形成以及鞏固的過程,才是我主要想要研究的內容。
柯林斯在他2006年的暢銷書《上帝的語言:科學家為信仰提供證據》(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中,1敍述了他從無神論者到一神論者的心路歷程。一開始,柯林斯經歷一段停滯不前的腦內風暴,腦中充滿科學家在研究新想法時經常出現的自我辯論(「我猶豫了,害怕後果,並受到懷疑的困擾」)。他閱讀有關上帝存在和基督神性的書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牛津學者兼小說家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作品。路易斯的通俗非小說作品已成為基督教辨惑學的經典,他的兒童讀物《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系列,故事中充滿幾乎不加掩飾的聖經寓言,正陸續拍成好萊塢電影。當年我在佩珀代因大學就讀時,選修了一門課專門探討路易斯的著作,所以我能夠用切身經驗證明他的文字威力(不過他的科幻太空三部曲寫得不如納尼亞系列,不太可能拍成電影)。柯林斯回憶起他對耶穌是上帝道成肉身這一論點的最初反應,即耶穌以人的身分來到世間,為償還人的罪,使我們都能重生(比如在體育盛事中都能看到海報上寫著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他說:「在我相信上帝之前,這種邏輯簡直就是荒唐。現在,釘十字架和復活,成了上帝和我之間巨大鴻溝的有力解決方案,耶穌基督降生為人,成為這道鴻溝的橋梁。」同樣地,信念一旦形成,自然可以找到支持的理由。
不過,在柯林斯改信之前,他所受的科學和理性訓練,使他一直對信仰存疑。「我心裡屬於科學家的那一部分,一直拒絕走向基督教信仰,不管那有多吸引人,因為聖經裡關於基督的那些文字有可能只是神話,或者更糟,是騙局。」只要解釋先於信念,懷疑之心就能占上風。可是一旦你對信念的可能性敞開胸懷,解釋就自然到位了。他曾接受《時代》(Time)雜誌採訪,與著名的無神論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進行紙上辯論,道金斯挑戰柯林斯認為上帝是在宇宙之外的說法,並稱這種說法是「所有迴避說辭的父母」。柯林斯回應道:
我確實反對將自然界以外的一切都排除在對話中的這種假設,這對於我們會自問的問題――像「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們死後會怎麼樣?」――而言,是一種乏善可陳的觀點。如果你拒絕承認這種觀點的適切性,在檢視自然界之後,自然會得到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是零,因為這不是能用證據來說服的。但是,如果你對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你就能看出宇宙中有許多層面與此結論相符。
先有解釋後有信念的次序即將顛倒。柯林斯正處於懷抱信仰、一躍而下的懸崖邊。對此,丹麥神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表示,這對於繞過「相信一個人既可以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上帝」這一悖論是必要的。路易斯為柯林斯提供了能夠飛越神學峽谷的投石器。在《純粹的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一書中,路易斯提出了著名的「騙子、瘋子或上帝」論點:
一個凡人若說出耶穌說的那些話,他就絕不可能是個偉大的道德導師。這人要麼是個瘋子——就跟一個人說自己是水波蛋一樣瘋狂——要麼就是地獄的惡魔。你得自己做決定,選擇相信這位耶穌是昔在今在的上帝的兒子,或者相信此人是瘋子,又或是一個更加可怕的人。你可以把他當傻子,叫他閉嘴,你可以對他吐口水,把他當惡魔殺死;或者你可以跪伏在他腳邊,稱他為主、為上帝。
關於基督神性正反兩面的思想論辯,在柯林斯的靈性探索過程中始終困擾著他,然而有一天下午在與大自然交會時,這些論辯全部潰不成軍:
路易斯是對的,我必須做出選擇。從我決定相信可能有上帝的那一刻起,已經過了一年,現在我受到召喚要有所承擔。在一個美麗的秋日,我第一次到密西西比河以西旅行,在喀斯開山脈上健行,上帝造物的威嚴和美麗,完全壓倒了我的抵抗力。我拐過一個彎,一道美得不可思議,足有數百英尺高的冰封瀑布映入眼簾,我知道探索已經結束了。隔天早上,太陽升起時我跪在沾滿露水的草地上,向耶穌基督臣服。
***
就在我想進一步瞭解這個歷程時,恰好趕上了一次時機――那次正逢柯林斯要長途駕車拜訪親友,獨自在車上,不會受到身為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的事務所擾。2他非常坦率地從是什麼導致冰封瀑布的頓悟,開始談起自己的信仰和心路歷程。柯林斯之前是名住院醫生,每週工作一百個小時。「我工作過度、睡眠不足,還想努力當好丈夫和好爸爸,所以真的沒有時間深入反思。如果說山裡的那一刻真有什麼特別的話,那就是我拋開所有干擾,讓自己去思考這些深刻的問題。」在這種預備好的狀態下,柯林斯解釋道:「我轉過小路的轉彎處,看到冰封的瀑布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與其說是上帝給的神蹟預兆,不如說是一種召喚我做出決定的感覺。我甚至記得當時自己想著,如果這時有一隻禿鷹從頭上飛過,那就太酷了,不過當然是沒有。但我確實體驗到一種平靜的感覺,準備好在正確的地方做出決定。我就是有一種『我在這裡,我做到了』的平靜感覺。」
柯林斯經歷了「大約一年的蜜月期」,「感受到極大的喜悅和寬慰,並與很多人談論了自己的轉變」,然而這段期間過去之後,懷疑開始爬上心頭,讓他不禁懷疑「這一切都是幻覺」。在一個懷疑格外洶湧的星期天,柯林斯「走到祭壇前,在巨大的痛苦中跪了好一會兒,用無聲的祈禱呼求幫助」。就在這時,他感覺到一隻手放到他的肩膀上。「我回頭一看,是一個那天剛加入教會的教友。他問我怎麼了。我告訴了他,他帶我去吃午飯,我們聊過之後成了好朋友。原來他是一位物理學家,和我有著相似的歷程,他幫助我看見懷疑是信仰之旅的一部分。」在得到同為科學家友人的寬慰後,柯林斯「得以回顧並重建自己最初是如何獲得信仰的,得出『我的宗教信仰是真實的,而不是偽造的』的結論。」
他也是科學家的這一點有幫助嗎?
當然有!和許多人談論過信仰後,我發現我比大多數人更偏重以理性探討信仰,所以能與其他科學家分享我的疑惑這一點非常有幫助。
心中存疑不影響你的信仰嗎?
沒有,懷疑讓人有機會持續成長。
你如何區分「上帝存在,且懷疑是信仰正常的一部分」,以及「上帝不存在,且懷疑是合理且適當」這兩種立場?
以信仰的光譜來說,一端是絕對相信上帝存在,另一端是根本沒有上帝。我們都活在光譜的兩端之間,我比較靠近相信的那一端,但絕不是已經到了端點。我也知道活在光譜另一邊是什麼樣子,因為我二十幾歲時就是那樣。如果從純粹理性的觀點來看,兩個極端都站不住腳,不過如同我在書中敘述的種種理由,我的結論是:相信的那一邊還是比不信的那一邊要來得理智。
***
《上帝的語言》是試圖消弭科學與宗教之間鴻溝的竭誠之作,我在與神創論者辯論時,經常引用書中的句子,因為柯林斯——在其宗教陣營中具有相當科學地位的這位人士——十分清楚地解釋了為什麼智慧設計創造論根本是胡扯。他寫的關於人類演化遺傳證據的章節,是迄今為止關於該主題最具說服力的總結,裡面的內容很值得在這裡摘要一下,因為當中完全展現了柯林斯在事實面前的正直,並提出了當涉及到有關自然的終極問題時,他(和我們所有人)都繞不開的一個難題。
柯林斯首先描述了DNA中的「古代重複因子」(ancient repetitive elements,AREs)。AREs源自「跳躍基因」(jumping genes),這些通常沒有任何功能的基因能夠自行複製,並插入到基因組的其他位置。「達爾文的理論預測,在基因組中不影響功能的突變(即位於『垃圾DNA』中的突變)將隨著時間的推移穩定積累,」柯林斯解釋道,「然而,基因編碼區的突變率應該會較低,因為這類突變大多數是有害的,只有極少數能提供選擇優勢,並在演化過程中保留下來。而我們觀察到的情況也正是如此。」事實上,哺乳動物基因組中到處都有AREs,人類基因組中約有45%是由AREs所組成。如果比對人類和小鼠基因組的片段,會發現相同的基因中有許多AREs都位於同一位置。柯林斯以一段犀利的評論做為總結:「除非有人情願認為上帝將這些沒頭沒尾的AREs精準地放在這些位置,是為了迷惑和誤導我們,否則人類和老鼠有共同祖先的這個結論,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科學如此擅長解釋自然,讓我們不需要為DNA這類了不起的產物援引神靈的力量,那麼柯林斯為什麼相信有上帝呢?確實,為什麼會有科學家或理性的人相信上帝呢?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分別在理智層面和情感層面。從理智上來說,柯林斯用自然法則解釋世界上的一切,這點與其他科學家的作法完全一致,只不過有兩個例外(引述康德詩意的描述):群星蒼穹在我之上,道德法則存我心中。3在這個自然法則的宇宙起源和道德的演化起源這兩個領域交會之處,柯林斯站到了深淵的崎嶇邊緣,他沒有更進一步地逼近科學極限,而是憑著信仰一躍而下。為什麼?
預測一個人宗教信仰的首要指標,就是父母和家庭的宗教氛圍。不過對柯林斯來說,這一點並不適用。柯林斯的父母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生,也是世俗的自由思想家,他們在家自行教育四個兒子(柯林斯是最小的)直到六年級,對於他們的宗教思想保持既不鼓勵也不阻止的態度。除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家庭動力之外,同儕團體和老師也對塑造一個人的信仰有著強大的作用。在柯林斯的中學時代——他終於進了公立學校——他遇到一位極富魅力的化學老師,並因此認定科學就是他的天職。柯林斯認為宗教懷疑論本來就是科學思想的一部分,於是默認了不可知論(agnosticism);但他並不是經過仔細分析論據和證據才這麼想,而比較像是「隨順『我不想知道』的路線」。在讀過愛因斯坦的傳記和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對亞伯拉罕人格神的駁斥後,「我的想法更加強化了,亦即沒有一個有思想的科學家,能夠在認真考慮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時,不犯下某種知性自殺的錯誤。於是我逐漸從不可知論轉向無神論。任何人在我面前提到精神信仰,我都會樂於與他辯上一辯,還把這類信仰觀點視為感情用事和過時的迷信。」4
柯林斯在信仰光譜偏懷疑的那一側建造起知性大廈,但在他作為醫學生和住院醫生的期間,這座精神大廈逐漸受到情感經驗的侵蝕――病患受到的痛苦折磨讓他心中感到煎熬,信仰在病患身上展現的作用則令他驚奇。「我常和這些善良的北卡羅萊納州人在病床邊談話,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在精神層面的經歷。我親眼目睹許多人因為信仰而擁有內心最深刻的平靜,不管是此生或來生,儘管大多數人都是無端受到病痛折磨。所以我認為,如果信仰是一種心理拐杖,那一定是非常神奇的拐杖。如果信仰不過是出於文化傳統的虛飾,那麼這些人為何不對上帝感到憤怒,要親朋好友別再說什麼慈愛和仁慈的超自然力量呢?」
好問題,就像一名患有嚴重且無法治癒心絞痛的女子也問過他另一個好問題:他對上帝有什麼看法?在那一刻,柯林斯的體貼敏感壓過了他的懷疑論調:「我結結巴巴地說『我不確定』,一邊感覺臉都漲紅了。她那明顯詫異的表情,讓我強烈意識到我逃避了整整二十六年的難題:我從沒有認真思索過關於信仰的正反論述。」
柯林斯的家庭背景以及所受的教養和教育,使他成為宗教的懷疑論者。科學訓練再加上與其他心存懷疑的科學家為伍,更強化了他的這種立場。現在一次情緒體驗促使他正視這個問題,並從不同觀點重新檢視宗教信仰的證據和論點。「突然之間,我的論點顯得格外薄弱,有種腳下的冰面正在碎裂的感覺,」他回憶道,「這種體悟真的會讓人心生恐懼,畢竟,如果我的無神論立場再也站不住腳,對那些我不願被審視的行為,我是不是就必須負起責任了?我是不是得對自己以外的人負責?這個問題緊迫到我避無可避。」
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個理智上的臨界點,一次情緒觸動就足以扭轉整個走向——柯林斯開始閱讀路易斯影響深遠的著作,路易斯本人也曾在迷失後被尋回。現在信仰之門微微敞開了一道縫隙,路易斯引起柯林斯的共鳴,引領他不可抗拒地在情感上做好預備,直到冰封的瀑布徹底關上懷疑之門。「我在萬丈深淵前顫抖地站立了好久,終於,我看明白了逃無可逃,只能縱身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