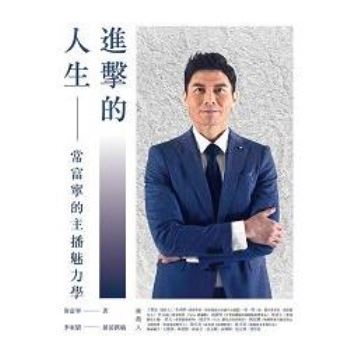1-03
總覺得爸爸一直在盯著我
爸爸來台之後進入軍隊,在海軍艦上服役,卻沒多久就退伍。在我大約二十歲的時候他才告訴我,那時因為一次擦槍走火,把他一個眼睛弄瞎了。
我不曉得這是否對他的內心造成了一些傷害,已經孤身一人在異鄉,又失去了一半的視力。在家裡,他總是顯得木訥,不太說話,但同時也扮演著威嚴的角色,很多事情都是他說的算。我更是從小被他打到大。他打我打得兇,常拿出棍子,叫我趴著就直接騎在我身上打我的屁股。屁股烏青紅腫是常有的事,或許因為這樣,我們兩個一直保持著距離。因為我也遺傳到他的硬脾氣,不容易屈服。
小時候我和妹妹都不知道他有隻義眼,很好奇為何他總是戴著有顏色的眼鏡,把眼睛部位遮住。記得小學一、二年級左右,我常偷看爸爸睡午覺。我總覺得很奇怪,爸爸明明在睡午覺,卻睜著一隻眼睛,彷彿知道我來了。
因為這樣,我總覺得爸爸一直在盯著我,不論我在做什麼,總也感覺得到他監控的視線。
爸爸對我的人生影響至大。我人生當中很多決定不是自己做的,而是爸爸。他就像是我這艘船的舵手,甚至比我更執著在掌舵這件事上。但他是個怎樣的人呢?
我認為他是個「把自己放得很小的人」。很多因素讓他成為這樣的人,但我沒辦法參與到他的過去,很多事情只能自己猜想拼湊。
我爸念過私塾,但我覺得他應該沒有念過高中就來台灣了。而我媽則是在屏東唸完了高中,兩個人學歷的差距,讓我爸覺得自己學歷很不完整,可能就是因為這樣,他總是把自己放得很小,默默地努力。就我小時候的觀察,我爸總想著「自己能夠為公司(中影)貢獻什麼?」後來調派到中廣,想的依然還是「能夠為中廣做些什麼?」我最常聽他對我和妹妹的教訓就是:「要謙虛,要與人為善。」
我到現在從來不曾問過爸爸,沒受太多教育與失去一隻眼睛,是否導致他在對我的管教上,必須透過打罵與不斷的干涉來塑造威嚴,以掩飾他的自卑。我想我應該永遠不會問他這個問題。
有一件事情是我非常佩服他的,我今天能成為一個在國際間暢行無阻、英文講得還算溜的人,爸爸居功厥偉。前面提過,爸爸在大陸唸的是私塾,私塾是不教英文的,但爸爸英文卻講得不錯。這件事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就先擱著吧。另外講兩件對他印象深刻的事。第一個是打麻將,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爸爸從來不理牌的,一般人拿到牌總要先理個老半天,但他即使不理牌還是能揮灑自如,那時左鄰右舍跟公司同事都常來家裡打麻將,爸爸贏錢的機率還滿高的。另一個印象深刻的就是喝酒。他常被同事說是海量、千杯不醉,而且都是喝高粱的。附帶一提,我小時候喝的第一口酒也是高粱,但只是用筷子沾一點來嘗嘗味道而已。
爸爸樹立起一個權威的形象,讓我們知道他說的話是不能違背的。
念國小的時候,星期天是可以出去玩,一般小學生最高興的時候,但卻反而是我最痛苦的時候。早上一起來,吃完早餐,爸爸就叫我練毛筆,練完毛筆可能已經接近中午了,他就接著出一個作文題目讓我寫。通常寫了個開頭就去吃午餐,吃完繼續寫。這時爸爸去睡午覺,等他睡醒我大概也寫完了,我就把作文給他看。這還沒結束,他不是看過而已,還要我訂正,告訴我哪裡寫得不好,哪裡應該要怎麼寫才好。全部訂正完才准我出去玩,每次全部訂正完的時候都三點半快四點了,然後還規定我五點前就得回家。
所以我的星期天根本沒玩到,被爸爸督促得很緊。不過如果沒有他這樣督促,我不可能自動自發去鍛鍊自己的表達能力,也不會想把字寫得好看。
即使我骨架愈拔愈高,在青年時期便已超越爸爸的身高,我卻始終覺得他是個巨大且令我敬畏的存在。我尊敬他,我怕他,但有時候又想要挑戰他。有時候覺得自己翅膀硬了,自己可以決定一些事了,但爸爸總是以一種不希望我在人生路上受到挫折的感覺,為我決定好很多事情。他並不會考慮我是否喜歡,就硬塞給我。
好幾次我試圖反抗他的管教,最後總還是我低頭道歉。其中有一次肢體衝突,讓我到現在都覺得懊悔。
唸師大附中的時候,師大的大三、大四學生都會來試教。這些年輕老師其實只跟我們差三四歲,很容易跟我們打成一片。那時有位教國文的許舜華老師,我們全班都很喜歡她,她總是笑臉迎人,每次上課都覺得如沐春風,沒有壓力。許老師家住鹿港,有一年暑假,我準備去鹿港找許老師。但那天我爸爸怎樣都不讓我去,我們兩個就在大門口對峙。我高中時已經長得比爸爸高了,我們推過來推過去,那時媽媽就夾在中間,不曉得該幫誰,很難做人。我們家那時候住在五樓,我甚至出言威脅爸爸,不讓我去就從這裡跳下去。媽媽很急,她既不希望爸爸這樣發脾氣,畢竟都是高中生了,自己搭公路局去鹿港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一邊與爸爸爭執,一邊也看著媽媽很急的表情。後來我還是奪門而出,去搭上往鹿港的車去找老師。在車上,我眼淚不住地流著,不是因為跟爸爸的這場爭執,而是回想到媽媽的肢體語言與表情,媽媽夾在中間,一邊護著我又一邊安撫爸爸,表情裡透露著無比難堪,這讓我覺得好難過。我一直質問我自己難道我做錯了嗎?我只是要來鹿港找老師,為什麼最後卻讓媽媽這麼難過呢?
讀到這邊的您,不曉得您的人生是否總能由自己來操盤?在我念實踐家專的時候,李明依那支廣告:「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紅遍大街小巷,新人類紛紛主張自我。對我來說,從來沒有這種事。那麼你問我,我會怨我父親嗎?
比如說,如果他沒有幫我報名維也納求學團……
比如說,如果他沒有幫我投國泰航空的履歷……
比如說,如果他沒有幫我投ESPN的履歷……
時間無法重來。如果我堅持繼續走原本的路,也可能遇到「此路不通」的告示,因為未來的事沒人知道。
我一點也不會怨他,反而還很感謝他。他幫我安排的所有人生,我不敢說我都做得很好,但每次我都想盡辦法完成任務。可能有些時候我的成績是他所樂見的,可能有些時候他也覺得不夠好。我還是很謝謝他為我作的一切,沒有他作的這些,也沒有現在的我。現在我作出一點小小的成績,或許他心中也有點寬慰。
即使婚後,我帶著太太回家探望兩老,爸爸在飯桌上仍會當著我太太的面數落我哪裡做得不好啦,哪裡不夠周到之類的,甚至會繼續檢討我播報球賽的表現,讓我覺得他是我最嚴厲的觀眾。
爸爸彷彿不斷想要提醒我還不夠好,要我謙虛,把自己放小。也許我在他心目中從來就拿不到一百分,但我覺得都沒關係,我謝謝他,而且我真的盡力了。進ESPN,在新加坡當了幾年主播,有一年回台灣,爸爸告訴我:「我真是後悔把你送到新加坡去工作。」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結婚的事,因為我不在身邊,他無法督促我決定婚姻這件人生大事。我拖到過了四十歲,到了這兩年才結婚,對他來說一定是件相當遺憾的事情。他的遺憾在於,我結婚的時候他剩下的一隻眼睛也只有不到0.1的視力,幾乎跟失明一樣。所以他沒辦法親眼看到這一切,只能夠用聽覺去感受,聽大家來跟他恭喜。登記結婚的時候,他也沒辦法坐在桌子前面看著我們去完成這些,只能待在一旁。
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個好兒子,我沒有給父母好的生活,雖然他們現在有房子可以住,三餐吃得飽,但相對於爸爸媽媽對我所付出的,恐怕仍差得有點遠。
2-06
飯店不待,寧願待酒店
念實踐家專時,嚴長壽先生曾來學校演講過一兩次,對他留下一點印象,知道他是國內相當有遠見的企業家。後來我在維也納讀旅館學校,念有關於餐飲管理和旅遊業管理。有一次參加「柏林國際旅展」,在台灣的小攤位,又遇到嚴先生,在異國遇到台灣人,覺得非常親切,再加上那時自己年少氣盛,有點「憨膽」,就跑去問他:「如果要從事旅館這個行業,究竟是多讀一點書學理論、知識比較重要,還是實務的經驗與技術比較有用呢?」
他很和善也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一些,內容大約是說:「不管是知識或是技術,其實都很重要。」他這麼說,讓我覺得書沒念很多也沒關係,有實際操作的經驗可能比較有用。聊了一會之後我就跟他說:「等我回到台灣,希望有機會可以到亞都工作。」嚴先生也爽快允諾:「好啊,如果你願意學習一些實務的話,你來找我啊。」
那時在維也納雖然很充實,生活也很開心,但之所以沒把書念完的最大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學的東西,之前在實踐就已經學過了。只不過語言不太一樣,深淺不太一樣,那時我就質疑,為何我還要花時間去學這種重覆的東西。
當時的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也比較單純,認為只要實地去操作就好了,在飯店這個工作上,我知道如何整理床鋪,知道如何準備早餐,這樣就可以了,足夠了。可是我忽略了,專業知識其實對任何人來講都很重要。今天我們為何會稱一個人為專業,不只是因為他實際操作的經驗豐富,也包括他擁有非常專業的知識。今天面對相同的問題,我會告訴他:「書本上的知識與實際操作之間,你得好好地去相互印證。也許中間會有相衝突的地方,但這就是對判斷力的挑戰。到底是要照著書上講的一五一十去做,還是你要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依據每個當下的客觀條件去做變通。在每個印證的過程中,自我的專業能力也將隨之成長」
回台灣之後,確定不再回維也納了,我就跑去亞都應徵。不過當然像我這種小咖的人來應徵,是不會麻煩到他的,面試我的是總經理職位的人。我想那時爸爸有請朋友幫忙疏通,讓我能夠以實習經理的身分開始在亞都學習。這段實習生涯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我漸漸發現跟想像有點落差。
那時在飯店一樓咖啡廳負責早餐跟午餐,穿著西裝,打個領帶,從基本工資開始領起。當時我觀察咖啡廳的女性總經理,每天從早上七、八點就來了,然後一直工作到中午,下午過了餐期之後可能稍微不忙,她就回家休息一下,晚上再來。我發現她必須把每天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在這個工作上,看著她這樣,我也問我自己:「這是我將來想要一直做下去的事嗎?」
那時我還年輕,覺得這似乎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模式,我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工作。剛好也發生了一件事,有個朋友到亞都來吃飯,他看到我,驚訝地問:「欸?你怎麼在這邊工作?」因為我在實踐的時候就當模特兒、拍戲,接很多外面的工作,我認為在別人的眼中,我應該是「那樣」的人才對。被他這麼一問,突然有種莫名的羞恥心,我就只能回他:「對啊,因為我出國念書了一段時間,都不在國內,回來之後就來這邊工作了。」他也沒說什麼,只告訴我說有什麼戲要開拍了,問我有沒有興趣。就這樣,我又動搖了,沒多久自己偷偷辭職。不用說,我爸非常生氣,覺得我又再度糟蹋了他一番苦心,只做了兩個月左右,拍拍屁股就走了。爸爸就是對自己的小孩期望很高,然後覺得我們做的不是他想要的時候,他就會擅自拿橡皮擦把它擦掉,把他要的答案寫上去。當時的我,掙扎在聽話與追求自我之間,總是難以安定。演戲當然不是一個能固定領到酬勞的工作,選擇這個工作意味著有可能落得三餐不繼,所以我必須做很多工作來延長我追逐夢想的時間。當時女朋友也有夢想,對學服裝設計的人來說,去巴黎朝聖是個很大的目標,於是有一段時間我們倆都做晚上的,因為薪水比較好,她在好樂迪,我則去了酒店。
我當時其實最想應徵的是「少爺」,因為可以拿很多小費。看報紙求職欄看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一家在徵少爺,我就興高采烈跑去應徵。進去以後,那個應徵我的領班坐在椅子上,第一句話就跟我說:「你太高了,不行!」我覺得莫名其妙,問他為什麼不行,他說:「你蹲下來會擋到客人唱歌。」聽到他這麼說我有點沮喪,心想長得高又不是我的錯。
沒想到,隔天我又接到那位領班的電話,他說:「我們這邊現在缺一個洗碗的,可以分小費,你要不要來?」我想說就去吧,因為也沒其他工作。去了之後,每天都彎著腰洗碗,洗得真的很累,杯子實在太多,客人一用過就得洗,洗到腰直不起來。洗了兩天我就跟領班講說:「對不起,這個工作真的不適合我,我的腰會挺不起來。」他說:「這樣子啊,我們這邊剛好有另位一個職位也需要人,你要不要試看看?不用站,坐著就好。」我問他那是什麼?他說:「控台。」控台是什麼?我當然莫宰羊。但是我知道坐著比站著好。
酒店這麼大,小姐多達上百個,要怎麼管理呢?如何曉得編號五十一的小姐現在在哪一桌服務客人?三十六號小姐在哪個包廂?雖然有媽媽桑協助管理,但酒店那麼大,媽媽桑也很難全盤掌握小姐。這時候就是控台的工作了。我們的小房間有整個酒店空間的示意圖以及小姐的名牌,比如說有人通報:「一號小姐進了A1。」我們就把一號小姐的牌子掛在「A1」上,依此類推。所以當媽媽桑想知道她的哪個小姐現在在哪裡,就會直接來問我們控台。坐在控台裡的感覺跟在劇場的燈控音控室有點像,讓我覺得自已是讓酒店正常運作的關鍵。當然控台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你每天一定能看到所有的小姐,因為她們得來我們這邊打卡上班。有時候小姐還會來巴結我,因為她們有時候時間沒抓好遲到,需要我幫她們打卡。媽媽桑也要來交關。所以做了一兩個月控台,覺得很新鮮,沒想到酒店裡有這樣的工作。我從原本想要當少爺,變成洗碗洗杯子,最後在控台玩得很開心。
後來錢存好了,我就帶女朋友去巴黎,然後去維也納把東西收拾帶走,我覺得算是完成那時一個屬於我們的小小心願。回國之後生活依舊有一搭沒一搭,在忠孝東路的T.G.I. FRIDAY’S打工,一邊打工一邊拍戲,還參與了兩齣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上演的舞台劇。
總覺得爸爸一直在盯著我
爸爸來台之後進入軍隊,在海軍艦上服役,卻沒多久就退伍。在我大約二十歲的時候他才告訴我,那時因為一次擦槍走火,把他一個眼睛弄瞎了。
我不曉得這是否對他的內心造成了一些傷害,已經孤身一人在異鄉,又失去了一半的視力。在家裡,他總是顯得木訥,不太說話,但同時也扮演著威嚴的角色,很多事情都是他說的算。我更是從小被他打到大。他打我打得兇,常拿出棍子,叫我趴著就直接騎在我身上打我的屁股。屁股烏青紅腫是常有的事,或許因為這樣,我們兩個一直保持著距離。因為我也遺傳到他的硬脾氣,不容易屈服。
小時候我和妹妹都不知道他有隻義眼,很好奇為何他總是戴著有顏色的眼鏡,把眼睛部位遮住。記得小學一、二年級左右,我常偷看爸爸睡午覺。我總覺得很奇怪,爸爸明明在睡午覺,卻睜著一隻眼睛,彷彿知道我來了。
因為這樣,我總覺得爸爸一直在盯著我,不論我在做什麼,總也感覺得到他監控的視線。
爸爸對我的人生影響至大。我人生當中很多決定不是自己做的,而是爸爸。他就像是我這艘船的舵手,甚至比我更執著在掌舵這件事上。但他是個怎樣的人呢?
我認為他是個「把自己放得很小的人」。很多因素讓他成為這樣的人,但我沒辦法參與到他的過去,很多事情只能自己猜想拼湊。
我爸念過私塾,但我覺得他應該沒有念過高中就來台灣了。而我媽則是在屏東唸完了高中,兩個人學歷的差距,讓我爸覺得自己學歷很不完整,可能就是因為這樣,他總是把自己放得很小,默默地努力。就我小時候的觀察,我爸總想著「自己能夠為公司(中影)貢獻什麼?」後來調派到中廣,想的依然還是「能夠為中廣做些什麼?」我最常聽他對我和妹妹的教訓就是:「要謙虛,要與人為善。」
我到現在從來不曾問過爸爸,沒受太多教育與失去一隻眼睛,是否導致他在對我的管教上,必須透過打罵與不斷的干涉來塑造威嚴,以掩飾他的自卑。我想我應該永遠不會問他這個問題。
有一件事情是我非常佩服他的,我今天能成為一個在國際間暢行無阻、英文講得還算溜的人,爸爸居功厥偉。前面提過,爸爸在大陸唸的是私塾,私塾是不教英文的,但爸爸英文卻講得不錯。這件事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就先擱著吧。另外講兩件對他印象深刻的事。第一個是打麻將,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爸爸從來不理牌的,一般人拿到牌總要先理個老半天,但他即使不理牌還是能揮灑自如,那時左鄰右舍跟公司同事都常來家裡打麻將,爸爸贏錢的機率還滿高的。另一個印象深刻的就是喝酒。他常被同事說是海量、千杯不醉,而且都是喝高粱的。附帶一提,我小時候喝的第一口酒也是高粱,但只是用筷子沾一點來嘗嘗味道而已。
爸爸樹立起一個權威的形象,讓我們知道他說的話是不能違背的。
念國小的時候,星期天是可以出去玩,一般小學生最高興的時候,但卻反而是我最痛苦的時候。早上一起來,吃完早餐,爸爸就叫我練毛筆,練完毛筆可能已經接近中午了,他就接著出一個作文題目讓我寫。通常寫了個開頭就去吃午餐,吃完繼續寫。這時爸爸去睡午覺,等他睡醒我大概也寫完了,我就把作文給他看。這還沒結束,他不是看過而已,還要我訂正,告訴我哪裡寫得不好,哪裡應該要怎麼寫才好。全部訂正完才准我出去玩,每次全部訂正完的時候都三點半快四點了,然後還規定我五點前就得回家。
所以我的星期天根本沒玩到,被爸爸督促得很緊。不過如果沒有他這樣督促,我不可能自動自發去鍛鍊自己的表達能力,也不會想把字寫得好看。
即使我骨架愈拔愈高,在青年時期便已超越爸爸的身高,我卻始終覺得他是個巨大且令我敬畏的存在。我尊敬他,我怕他,但有時候又想要挑戰他。有時候覺得自己翅膀硬了,自己可以決定一些事了,但爸爸總是以一種不希望我在人生路上受到挫折的感覺,為我決定好很多事情。他並不會考慮我是否喜歡,就硬塞給我。
好幾次我試圖反抗他的管教,最後總還是我低頭道歉。其中有一次肢體衝突,讓我到現在都覺得懊悔。
唸師大附中的時候,師大的大三、大四學生都會來試教。這些年輕老師其實只跟我們差三四歲,很容易跟我們打成一片。那時有位教國文的許舜華老師,我們全班都很喜歡她,她總是笑臉迎人,每次上課都覺得如沐春風,沒有壓力。許老師家住鹿港,有一年暑假,我準備去鹿港找許老師。但那天我爸爸怎樣都不讓我去,我們兩個就在大門口對峙。我高中時已經長得比爸爸高了,我們推過來推過去,那時媽媽就夾在中間,不曉得該幫誰,很難做人。我們家那時候住在五樓,我甚至出言威脅爸爸,不讓我去就從這裡跳下去。媽媽很急,她既不希望爸爸這樣發脾氣,畢竟都是高中生了,自己搭公路局去鹿港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一邊與爸爸爭執,一邊也看著媽媽很急的表情。後來我還是奪門而出,去搭上往鹿港的車去找老師。在車上,我眼淚不住地流著,不是因為跟爸爸的這場爭執,而是回想到媽媽的肢體語言與表情,媽媽夾在中間,一邊護著我又一邊安撫爸爸,表情裡透露著無比難堪,這讓我覺得好難過。我一直質問我自己難道我做錯了嗎?我只是要來鹿港找老師,為什麼最後卻讓媽媽這麼難過呢?
讀到這邊的您,不曉得您的人生是否總能由自己來操盤?在我念實踐家專的時候,李明依那支廣告:「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紅遍大街小巷,新人類紛紛主張自我。對我來說,從來沒有這種事。那麼你問我,我會怨我父親嗎?
比如說,如果他沒有幫我報名維也納求學團……
比如說,如果他沒有幫我投國泰航空的履歷……
比如說,如果他沒有幫我投ESPN的履歷……
時間無法重來。如果我堅持繼續走原本的路,也可能遇到「此路不通」的告示,因為未來的事沒人知道。
我一點也不會怨他,反而還很感謝他。他幫我安排的所有人生,我不敢說我都做得很好,但每次我都想盡辦法完成任務。可能有些時候我的成績是他所樂見的,可能有些時候他也覺得不夠好。我還是很謝謝他為我作的一切,沒有他作的這些,也沒有現在的我。現在我作出一點小小的成績,或許他心中也有點寬慰。
即使婚後,我帶著太太回家探望兩老,爸爸在飯桌上仍會當著我太太的面數落我哪裡做得不好啦,哪裡不夠周到之類的,甚至會繼續檢討我播報球賽的表現,讓我覺得他是我最嚴厲的觀眾。
爸爸彷彿不斷想要提醒我還不夠好,要我謙虛,把自己放小。也許我在他心目中從來就拿不到一百分,但我覺得都沒關係,我謝謝他,而且我真的盡力了。進ESPN,在新加坡當了幾年主播,有一年回台灣,爸爸告訴我:「我真是後悔把你送到新加坡去工作。」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結婚的事,因為我不在身邊,他無法督促我決定婚姻這件人生大事。我拖到過了四十歲,到了這兩年才結婚,對他來說一定是件相當遺憾的事情。他的遺憾在於,我結婚的時候他剩下的一隻眼睛也只有不到0.1的視力,幾乎跟失明一樣。所以他沒辦法親眼看到這一切,只能夠用聽覺去感受,聽大家來跟他恭喜。登記結婚的時候,他也沒辦法坐在桌子前面看著我們去完成這些,只能待在一旁。
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個好兒子,我沒有給父母好的生活,雖然他們現在有房子可以住,三餐吃得飽,但相對於爸爸媽媽對我所付出的,恐怕仍差得有點遠。
2-06
飯店不待,寧願待酒店
念實踐家專時,嚴長壽先生曾來學校演講過一兩次,對他留下一點印象,知道他是國內相當有遠見的企業家。後來我在維也納讀旅館學校,念有關於餐飲管理和旅遊業管理。有一次參加「柏林國際旅展」,在台灣的小攤位,又遇到嚴先生,在異國遇到台灣人,覺得非常親切,再加上那時自己年少氣盛,有點「憨膽」,就跑去問他:「如果要從事旅館這個行業,究竟是多讀一點書學理論、知識比較重要,還是實務的經驗與技術比較有用呢?」
他很和善也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一些,內容大約是說:「不管是知識或是技術,其實都很重要。」他這麼說,讓我覺得書沒念很多也沒關係,有實際操作的經驗可能比較有用。聊了一會之後我就跟他說:「等我回到台灣,希望有機會可以到亞都工作。」嚴先生也爽快允諾:「好啊,如果你願意學習一些實務的話,你來找我啊。」
那時在維也納雖然很充實,生活也很開心,但之所以沒把書念完的最大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學的東西,之前在實踐就已經學過了。只不過語言不太一樣,深淺不太一樣,那時我就質疑,為何我還要花時間去學這種重覆的東西。
當時的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也比較單純,認為只要實地去操作就好了,在飯店這個工作上,我知道如何整理床鋪,知道如何準備早餐,這樣就可以了,足夠了。可是我忽略了,專業知識其實對任何人來講都很重要。今天我們為何會稱一個人為專業,不只是因為他實際操作的經驗豐富,也包括他擁有非常專業的知識。今天面對相同的問題,我會告訴他:「書本上的知識與實際操作之間,你得好好地去相互印證。也許中間會有相衝突的地方,但這就是對判斷力的挑戰。到底是要照著書上講的一五一十去做,還是你要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依據每個當下的客觀條件去做變通。在每個印證的過程中,自我的專業能力也將隨之成長」
回台灣之後,確定不再回維也納了,我就跑去亞都應徵。不過當然像我這種小咖的人來應徵,是不會麻煩到他的,面試我的是總經理職位的人。我想那時爸爸有請朋友幫忙疏通,讓我能夠以實習經理的身分開始在亞都學習。這段實習生涯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我漸漸發現跟想像有點落差。
那時在飯店一樓咖啡廳負責早餐跟午餐,穿著西裝,打個領帶,從基本工資開始領起。當時我觀察咖啡廳的女性總經理,每天從早上七、八點就來了,然後一直工作到中午,下午過了餐期之後可能稍微不忙,她就回家休息一下,晚上再來。我發現她必須把每天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在這個工作上,看著她這樣,我也問我自己:「這是我將來想要一直做下去的事嗎?」
那時我還年輕,覺得這似乎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模式,我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工作。剛好也發生了一件事,有個朋友到亞都來吃飯,他看到我,驚訝地問:「欸?你怎麼在這邊工作?」因為我在實踐的時候就當模特兒、拍戲,接很多外面的工作,我認為在別人的眼中,我應該是「那樣」的人才對。被他這麼一問,突然有種莫名的羞恥心,我就只能回他:「對啊,因為我出國念書了一段時間,都不在國內,回來之後就來這邊工作了。」他也沒說什麼,只告訴我說有什麼戲要開拍了,問我有沒有興趣。就這樣,我又動搖了,沒多久自己偷偷辭職。不用說,我爸非常生氣,覺得我又再度糟蹋了他一番苦心,只做了兩個月左右,拍拍屁股就走了。爸爸就是對自己的小孩期望很高,然後覺得我們做的不是他想要的時候,他就會擅自拿橡皮擦把它擦掉,把他要的答案寫上去。當時的我,掙扎在聽話與追求自我之間,總是難以安定。演戲當然不是一個能固定領到酬勞的工作,選擇這個工作意味著有可能落得三餐不繼,所以我必須做很多工作來延長我追逐夢想的時間。當時女朋友也有夢想,對學服裝設計的人來說,去巴黎朝聖是個很大的目標,於是有一段時間我們倆都做晚上的,因為薪水比較好,她在好樂迪,我則去了酒店。
我當時其實最想應徵的是「少爺」,因為可以拿很多小費。看報紙求職欄看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一家在徵少爺,我就興高采烈跑去應徵。進去以後,那個應徵我的領班坐在椅子上,第一句話就跟我說:「你太高了,不行!」我覺得莫名其妙,問他為什麼不行,他說:「你蹲下來會擋到客人唱歌。」聽到他這麼說我有點沮喪,心想長得高又不是我的錯。
沒想到,隔天我又接到那位領班的電話,他說:「我們這邊現在缺一個洗碗的,可以分小費,你要不要來?」我想說就去吧,因為也沒其他工作。去了之後,每天都彎著腰洗碗,洗得真的很累,杯子實在太多,客人一用過就得洗,洗到腰直不起來。洗了兩天我就跟領班講說:「對不起,這個工作真的不適合我,我的腰會挺不起來。」他說:「這樣子啊,我們這邊剛好有另位一個職位也需要人,你要不要試看看?不用站,坐著就好。」我問他那是什麼?他說:「控台。」控台是什麼?我當然莫宰羊。但是我知道坐著比站著好。
酒店這麼大,小姐多達上百個,要怎麼管理呢?如何曉得編號五十一的小姐現在在哪一桌服務客人?三十六號小姐在哪個包廂?雖然有媽媽桑協助管理,但酒店那麼大,媽媽桑也很難全盤掌握小姐。這時候就是控台的工作了。我們的小房間有整個酒店空間的示意圖以及小姐的名牌,比如說有人通報:「一號小姐進了A1。」我們就把一號小姐的牌子掛在「A1」上,依此類推。所以當媽媽桑想知道她的哪個小姐現在在哪裡,就會直接來問我們控台。坐在控台裡的感覺跟在劇場的燈控音控室有點像,讓我覺得自已是讓酒店正常運作的關鍵。當然控台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你每天一定能看到所有的小姐,因為她們得來我們這邊打卡上班。有時候小姐還會來巴結我,因為她們有時候時間沒抓好遲到,需要我幫她們打卡。媽媽桑也要來交關。所以做了一兩個月控台,覺得很新鮮,沒想到酒店裡有這樣的工作。我從原本想要當少爺,變成洗碗洗杯子,最後在控台玩得很開心。
後來錢存好了,我就帶女朋友去巴黎,然後去維也納把東西收拾帶走,我覺得算是完成那時一個屬於我們的小小心願。回國之後生活依舊有一搭沒一搭,在忠孝東路的T.G.I. FRIDAY’S打工,一邊打工一邊拍戲,還參與了兩齣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上演的舞台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