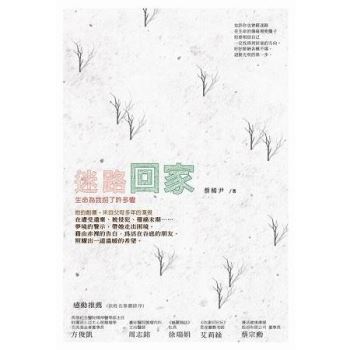1-1逃避很可恥,但也許不得已
☉ 迷宮拼圖第一站:面對
親情本來是一道有形的牆,自靈魂降生到脫離母體子宮,剪斷臍帶,打破第一道牆面,嬰孩成了一個獨立的人,也建立起無形的家庭關係,於是有了父親、母親、兄弟姊妹。
親情從來無從選擇,而且不代表情感的自動延伸,它需要不斷地嘗試和學習。但是,很多人忘了怎麼開始?為何繼續?如何面對?
當我開始築起牆面,選擇逃避一切血緣上的意義,其中有著千千萬萬的迫不得已……
▲失落的親情,只有沉默
活著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件事呢?我看著父親,思考這類無以名狀的問題,試圖從破碎的親情中,看清生命的本質。
「稀尹,妳爸進醫院,跟媽媽回去!」混亂的一天,從媽媽出現在教室門外開始。母親只簡單說了這句話,然後站在門口等我出來,我急忙把所有東西掃進書包,奔到媽媽身邊,媽媽瞧我一眼也不瞧,就邁開大步,我還得小跑步才跟得上。
親情是什麼?在前往醫院的車上,我看著有點熟悉又陌生的母親,還真不知道。母親穿著一件長袖T恤、黑長褲、黑外套,映著暗沈的臉色;她嘴唇緊抿著,雙手環抱胸前,死死瞪著前方,眼神透出來的絕望,像是無底洞一般,把我也跟著拉下去。
我背著書包,肩膀挺直、手放在膝蓋上,心裡滿是問號,一句話也不敢說,和母親之間只有沈默。
也許沈默是最好的存在吧,在母親消失這麼久以後。
若是連這些都沒有,那還真是什麼都不剩。
懂事以來,父母只是個名詞,只有在爭吵的時候,恐懼令人正視他們的存在。
「要走就走啊!永遠都不要回來!回來我打死你!」
「我再也不會回來!」
躲在牆角的我,直勾勾地看著父母親冷戰、對峙,像兩隻被困住的野獸,把挫敗鬱悶化成激烈的言語,將怒恨摔在地上。這些在眼前血淋淋上演的戲碼,不是八點檔,而是生活中的劇情。在我幼小心中所不解的是,到底是怎麼樣的深仇大恨,讓原本因相愛而結合的兩人,反目成仇?
若是如此,這世界還有愛嗎,或者,這就是愛?
▲不斷遷徙,成為愛的遊牧民族
「說!爸媽離婚,你們要跟誰住!」這不是問句,而是極具破壞力的攻擊。
爭吵的最後,問題永遠回到我與哥哥身上,好像孩子才是始作俑者、混亂的根源。
弱小的膝蓋在崩裂的親情之前,逼得我只能俯首,祈求著脆裂的愛,能夠在一覺醒來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龐大的壓力形成最深的恐懼,每晚在夢裡化成厲鬼或惡魔驚嚇著我,孤立無援的我,無能為力。
有人說,愛的反面是恨。
但是年紀小的我已經知道,愛的對立面是──忽略。
比起母親,父親卑微消極的形象、情感的忽視,是更加沈重的攻擊。記憶中的他,幾乎不說話。婚姻失敗之後,他最常做的是一個人坐在餐桌前默默喝酒,暈黃的燈光下,人影顯得更加單薄萎靡;有時一出門就消失,直到隔天早上,才看見他在房裡睡著。父親永遠都說很忙很忙,即使不知道做了什麼事情。
一開始的他是不是就是這樣,我不知道,只是懂事以來,一天之中和父親說話的機會,指頭數得出來。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父親是善良的,只是小時候的我,不懂。不懂屬於他的逃避,把喝酒、忙碌當成保護傘,卻只是保護了他自己,把周遭的人推入更深的旋渦之中。
為了逃避母親,他將孩子當成籌碼,拒絕她的探視權,也讓我徹底失去母愛;為了逃避現實中失敗的婚姻,他怪罪一切,用消極代替溝通,把孩子送往親戚家,眼不見為淨,似乎才有辦法稍解挫敗。因為如此,我從大伯、姑姑、外公外婆家裡全住上一輪,搬家、轉學成了家常便飯。
不斷遷徙的我,和誰都無法建立美好的關係,成了愛的遊牧民族,勇敢被拋在界外。
▲被遺棄的孩子,從此迷路
小時候不懂,善良的人心也是偏的,永遠只能關注一個孩子,即使明知另一個也需要愛,但他給不起。
哥哥虛長我幾歲,從小體弱多病、又有氣喘,稍微打個噴嚏,立刻就能引起眾人的關注。
「兒子,你怎麼了?帶你去看醫生。」這句話,父親只會跟哥哥說,然而當我生病時,永遠是一個人。
「妹妹,妳怎麼一個人自來看醫生?爸爸媽媽呢?」
護士阿姨,我該怎麼告訴你,爸爸媽媽是哥哥的,不是我的?
誰在乎寄人籬下?沒有
誰在乎分離的孤獨?沒有
既然如此,面對這一切,小小年紀我只能流淚、流淚、再流淚,最後學會漠然。
看良久,像在憑弔不曾存在的關心。當時心想,怎麼樣都無所謂了,看著躺在病床上的他,竟然沒有一絲不捨的感覺。
當時,唯一的情緒就是恨,我恨媽媽,認定爸爸會自殺、我會被欺負,都是她的錯!
「妳走,妳走,我們不想看見妳──」離家的媽媽掩著嘴走進來想要探望,我狠下心把他趕出病房。
因為不付出,就不會受傷。
孤單,只能自己消解。 沒有父母,似乎也能長大。
那麼,遺棄就不算什麼呵!
很後來才明白,父親是疼我的,只是他不懂表達,不能控制地將他與母親的爭執憤怒,轉移到孩子身上,然後相較之下又疼愛哥哥多一些,甚至到了溺愛的地步。即使哥哥升上中學,交到壞朋友,走上岔路,學會同樣消極且不負責任的態度,竟和父親如出一轍!「為什麼無止盡的寵溺、放任,卻又要在他惹事後,幫忙擦屁股?而我呢?你有想過我嗎?」長大後的我,曾哭著質問他。
「因為哥哥沒有辦法像妳這樣不會闖禍啊!」這樣的回應,令我啞口無言。
父親教養的無奈、婚姻失敗的無力,他不願說,我也不想理解,因為大人的自私,造成一個家庭的悲劇,以及多少個從此迷路的孩子……
下意識地,我並不想觸碰那些曾受疼愛的記憶,只想將一切掩埋,然後遺忘。
唯有如此,生活才輕鬆得多。
▲情感與死亡的最後拉扯
「好像是喝農藥啊,想要丟下小孩走了……」
親戚們在走廊上圍起小圈圈,小聲談論著,害怕一旦提高音量,真相就會崩解。
☉ 迷宮拼圖第一站:面對
親情本來是一道有形的牆,自靈魂降生到脫離母體子宮,剪斷臍帶,打破第一道牆面,嬰孩成了一個獨立的人,也建立起無形的家庭關係,於是有了父親、母親、兄弟姊妹。
親情從來無從選擇,而且不代表情感的自動延伸,它需要不斷地嘗試和學習。但是,很多人忘了怎麼開始?為何繼續?如何面對?
當我開始築起牆面,選擇逃避一切血緣上的意義,其中有著千千萬萬的迫不得已……
▲失落的親情,只有沉默
活著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件事呢?我看著父親,思考這類無以名狀的問題,試圖從破碎的親情中,看清生命的本質。
「稀尹,妳爸進醫院,跟媽媽回去!」混亂的一天,從媽媽出現在教室門外開始。母親只簡單說了這句話,然後站在門口等我出來,我急忙把所有東西掃進書包,奔到媽媽身邊,媽媽瞧我一眼也不瞧,就邁開大步,我還得小跑步才跟得上。
親情是什麼?在前往醫院的車上,我看著有點熟悉又陌生的母親,還真不知道。母親穿著一件長袖T恤、黑長褲、黑外套,映著暗沈的臉色;她嘴唇緊抿著,雙手環抱胸前,死死瞪著前方,眼神透出來的絕望,像是無底洞一般,把我也跟著拉下去。
我背著書包,肩膀挺直、手放在膝蓋上,心裡滿是問號,一句話也不敢說,和母親之間只有沈默。
也許沈默是最好的存在吧,在母親消失這麼久以後。
若是連這些都沒有,那還真是什麼都不剩。
懂事以來,父母只是個名詞,只有在爭吵的時候,恐懼令人正視他們的存在。
「要走就走啊!永遠都不要回來!回來我打死你!」
「我再也不會回來!」
躲在牆角的我,直勾勾地看著父母親冷戰、對峙,像兩隻被困住的野獸,把挫敗鬱悶化成激烈的言語,將怒恨摔在地上。這些在眼前血淋淋上演的戲碼,不是八點檔,而是生活中的劇情。在我幼小心中所不解的是,到底是怎麼樣的深仇大恨,讓原本因相愛而結合的兩人,反目成仇?
若是如此,這世界還有愛嗎,或者,這就是愛?
▲不斷遷徙,成為愛的遊牧民族
「說!爸媽離婚,你們要跟誰住!」這不是問句,而是極具破壞力的攻擊。
爭吵的最後,問題永遠回到我與哥哥身上,好像孩子才是始作俑者、混亂的根源。
弱小的膝蓋在崩裂的親情之前,逼得我只能俯首,祈求著脆裂的愛,能夠在一覺醒來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龐大的壓力形成最深的恐懼,每晚在夢裡化成厲鬼或惡魔驚嚇著我,孤立無援的我,無能為力。
有人說,愛的反面是恨。
但是年紀小的我已經知道,愛的對立面是──忽略。
比起母親,父親卑微消極的形象、情感的忽視,是更加沈重的攻擊。記憶中的他,幾乎不說話。婚姻失敗之後,他最常做的是一個人坐在餐桌前默默喝酒,暈黃的燈光下,人影顯得更加單薄萎靡;有時一出門就消失,直到隔天早上,才看見他在房裡睡著。父親永遠都說很忙很忙,即使不知道做了什麼事情。
一開始的他是不是就是這樣,我不知道,只是懂事以來,一天之中和父親說話的機會,指頭數得出來。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父親是善良的,只是小時候的我,不懂。不懂屬於他的逃避,把喝酒、忙碌當成保護傘,卻只是保護了他自己,把周遭的人推入更深的旋渦之中。
為了逃避母親,他將孩子當成籌碼,拒絕她的探視權,也讓我徹底失去母愛;為了逃避現實中失敗的婚姻,他怪罪一切,用消極代替溝通,把孩子送往親戚家,眼不見為淨,似乎才有辦法稍解挫敗。因為如此,我從大伯、姑姑、外公外婆家裡全住上一輪,搬家、轉學成了家常便飯。
不斷遷徙的我,和誰都無法建立美好的關係,成了愛的遊牧民族,勇敢被拋在界外。
▲被遺棄的孩子,從此迷路
小時候不懂,善良的人心也是偏的,永遠只能關注一個孩子,即使明知另一個也需要愛,但他給不起。
哥哥虛長我幾歲,從小體弱多病、又有氣喘,稍微打個噴嚏,立刻就能引起眾人的關注。
「兒子,你怎麼了?帶你去看醫生。」這句話,父親只會跟哥哥說,然而當我生病時,永遠是一個人。
「妹妹,妳怎麼一個人自來看醫生?爸爸媽媽呢?」
護士阿姨,我該怎麼告訴你,爸爸媽媽是哥哥的,不是我的?
誰在乎寄人籬下?沒有
誰在乎分離的孤獨?沒有
既然如此,面對這一切,小小年紀我只能流淚、流淚、再流淚,最後學會漠然。
看良久,像在憑弔不曾存在的關心。當時心想,怎麼樣都無所謂了,看著躺在病床上的他,竟然沒有一絲不捨的感覺。
當時,唯一的情緒就是恨,我恨媽媽,認定爸爸會自殺、我會被欺負,都是她的錯!
「妳走,妳走,我們不想看見妳──」離家的媽媽掩著嘴走進來想要探望,我狠下心把他趕出病房。
因為不付出,就不會受傷。
孤單,只能自己消解。 沒有父母,似乎也能長大。
那麼,遺棄就不算什麼呵!
很後來才明白,父親是疼我的,只是他不懂表達,不能控制地將他與母親的爭執憤怒,轉移到孩子身上,然後相較之下又疼愛哥哥多一些,甚至到了溺愛的地步。即使哥哥升上中學,交到壞朋友,走上岔路,學會同樣消極且不負責任的態度,竟和父親如出一轍!「為什麼無止盡的寵溺、放任,卻又要在他惹事後,幫忙擦屁股?而我呢?你有想過我嗎?」長大後的我,曾哭著質問他。
「因為哥哥沒有辦法像妳這樣不會闖禍啊!」這樣的回應,令我啞口無言。
父親教養的無奈、婚姻失敗的無力,他不願說,我也不想理解,因為大人的自私,造成一個家庭的悲劇,以及多少個從此迷路的孩子……
下意識地,我並不想觸碰那些曾受疼愛的記憶,只想將一切掩埋,然後遺忘。
唯有如此,生活才輕鬆得多。
▲情感與死亡的最後拉扯
「好像是喝農藥啊,想要丟下小孩走了……」
親戚們在走廊上圍起小圈圈,小聲談論著,害怕一旦提高音量,真相就會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