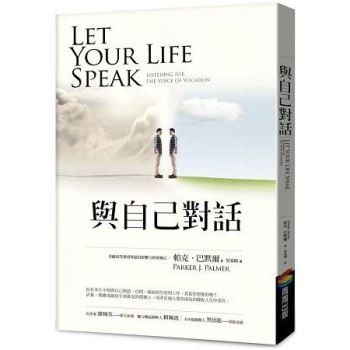在我擔任攀朵山的院長任期內,有一個機會送上門來,要我當某個小型教育機構的校長。我去參觀了校園,跟理事會成員、教職員,還有學生談過;他們跟我說,只要我點頭,這個工作非我莫屬。
當時我對志業一事困惱不已,相當確定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依貴格會的慣例,找了六位信得過的會友,藉由「透明審議」的方式來幫助我釐清志業所在。過程中,團體成員不會給你任何建議,三個鐘頭從頭到尾不停問你問題,質樸開放的問題,幫助你找到自己的內在真理。(當然,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召集大家的真正意圖哪是要釐清什麼,只不過是要誇耀人家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其實已經是要接受了。)
一開始的問題很容易,至少對我這樣一個愛做夢的人來說並不難:你對這個學校有什麼願景?它在這個大的社會架構下擔負什麼任務?你要如何改變課程內容?你該怎麼處理決策過程?碰到衝突時該怎麼辦?
議程進行到一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聽起來很容易,結果卻很難回答:「你最喜歡校長這個工作的哪個部分?」
這個問題的單純讓我從腦袋鬆脫,慢慢降到心坎裡。我還記得我起碼想了有整整一分鐘,才遲疑地緩緩開口說道:「嗯,我不想要因此放棄我的寫作和教學……我不會喜歡其中的政治角力,從來搞不清楚真正的朋友是誰……如果要我因為錢,對我不尊重的人虛情假意,這個我可能也不喜歡……我不喜歡……」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以委婉而堅定的口吻打斷我的話:「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嗎?我問的是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不太耐煩,「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歸納我的答案。」好像有點賭氣,又繼續老實地嘟囔:「我不想要因為這個工作放棄我的暑假……我不想要成天穿西裝打領帶……我不想要……」
提問者再次把我拉回原始的問題。這次我被迫說出我唯一一個誠實的答案,來自我內心深處的真正想法,從我嘴裡說出來時,就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這個嘛,」我的聲音輕得不得了,「我猜我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被貼在牆上,底下還會冠上『校長』這個頭銜。」
在座的貴格會友各個經驗老道,一眼洞知我的答案雖然好笑,但我的道德精神已經在崩潰邊緣!他們沒有笑出來,反倒陷入嚴肅的靜默——時間這麼久,讓我坐立難安、滿身大汗,內心痛苦地呻吟。
最後我的提問者打破沉默,又問了一個問題,所有人彷彿大夢初醒——我更是立時回神。「帕克,」他說,「你能不能想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讓你的照片可以掛在牆上?」
在那個當下一切昭然若揭,就算我自己也頓時明暸,我想要當上校長的欲望是出自我的自尊,不是生命循環下的結果——太清楚了。「透明審議」一結束,我就打電話給那所學校,要他們別再把我列入考慮。要是我接下這份工作,對自己不見得好,對那所學校更是災難。
生命生態的理論(也就是極限理論)碰到這類的狀況再好用不過:我的性格讓我不適於做任何領導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誠實面對我所認識的自己,而我要是做了不該我的天命的事,將來的我可能形同行屍走肉,比死掉還難受。
可是,如果我想要的並不是照片可以掛在牆上,而是滿足人性需求呢?那麼極限理論又該怎麼解釋?如果我的就職出發點為善,非圖一己私利,這個理論又會起什麼作用?也許我想成為讓學生獲益良多的老師,或是協助人們找尋自我的心理諮詢師,或是伸張正義、追求平權的運動份子?很不幸,這個理論在這些情況下的效果,跟在我那個校長夢的作用一樣強而有力。有些事情是我「應該」做,或是「應該」表現的,可是再怎麼樣我就是達不到。
如果我硬要做什麼高尚的事,行跟我自己是誰無關的神聖舉措,別人看我可能會覺得挺好,我自己短時間也覺得不錯,不過我這種超越極限的行為終將遺留後果。我會扭曲自己,扭曲別人,扭曲我跟別人的關係,最後造成損傷——一開始就別給自己立下這麼「良善」的目標,可能還好一點。當我一意嘗試非我本性或非我與世界聯繫之事,這條道路便會在我身後關閉。
當時我對志業一事困惱不已,相當確定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我依貴格會的慣例,找了六位信得過的會友,藉由「透明審議」的方式來幫助我釐清志業所在。過程中,團體成員不會給你任何建議,三個鐘頭從頭到尾不停問你問題,質樸開放的問題,幫助你找到自己的內在真理。(當然,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召集大家的真正意圖哪是要釐清什麼,只不過是要誇耀人家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其實已經是要接受了。)
一開始的問題很容易,至少對我這樣一個愛做夢的人來說並不難:你對這個學校有什麼願景?它在這個大的社會架構下擔負什麼任務?你要如何改變課程內容?你該怎麼處理決策過程?碰到衝突時該怎麼辦?
議程進行到一半,有人問了一個問題,聽起來很容易,結果卻很難回答:「你最喜歡校長這個工作的哪個部分?」
這個問題的單純讓我從腦袋鬆脫,慢慢降到心坎裡。我還記得我起碼想了有整整一分鐘,才遲疑地緩緩開口說道:「嗯,我不想要因此放棄我的寫作和教學……我不會喜歡其中的政治角力,從來搞不清楚真正的朋友是誰……如果要我因為錢,對我不尊重的人虛情假意,這個我可能也不喜歡……我不喜歡……」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以委婉而堅定的口吻打斷我的話:「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嗎?我問的是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不太耐煩,「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歸納我的答案。」好像有點賭氣,又繼續老實地嘟囔:「我不想要因為這個工作放棄我的暑假……我不想要成天穿西裝打領帶……我不想要……」
提問者再次把我拉回原始的問題。這次我被迫說出我唯一一個誠實的答案,來自我內心深處的真正想法,從我嘴裡說出來時,就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這個嘛,」我的聲音輕得不得了,「我猜我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被貼在牆上,底下還會冠上『校長』這個頭銜。」
在座的貴格會友各個經驗老道,一眼洞知我的答案雖然好笑,但我的道德精神已經在崩潰邊緣!他們沒有笑出來,反倒陷入嚴肅的靜默——時間這麼久,讓我坐立難安、滿身大汗,內心痛苦地呻吟。
最後我的提問者打破沉默,又問了一個問題,所有人彷彿大夢初醒——我更是立時回神。「帕克,」他說,「你能不能想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讓你的照片可以掛在牆上?」
在那個當下一切昭然若揭,就算我自己也頓時明暸,我想要當上校長的欲望是出自我的自尊,不是生命循環下的結果——太清楚了。「透明審議」一結束,我就打電話給那所學校,要他們別再把我列入考慮。要是我接下這份工作,對自己不見得好,對那所學校更是災難。
生命生態的理論(也就是極限理論)碰到這類的狀況再好用不過:我的性格讓我不適於做任何領導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誠實面對我所認識的自己,而我要是做了不該我的天命的事,將來的我可能形同行屍走肉,比死掉還難受。
可是,如果我想要的並不是照片可以掛在牆上,而是滿足人性需求呢?那麼極限理論又該怎麼解釋?如果我的就職出發點為善,非圖一己私利,這個理論又會起什麼作用?也許我想成為讓學生獲益良多的老師,或是協助人們找尋自我的心理諮詢師,或是伸張正義、追求平權的運動份子?很不幸,這個理論在這些情況下的效果,跟在我那個校長夢的作用一樣強而有力。有些事情是我「應該」做,或是「應該」表現的,可是再怎麼樣我就是達不到。
如果我硬要做什麼高尚的事,行跟我自己是誰無關的神聖舉措,別人看我可能會覺得挺好,我自己短時間也覺得不錯,不過我這種超越極限的行為終將遺留後果。我會扭曲自己,扭曲別人,扭曲我跟別人的關係,最後造成損傷——一開始就別給自己立下這麼「良善」的目標,可能還好一點。當我一意嘗試非我本性或非我與世界聯繫之事,這條道路便會在我身後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