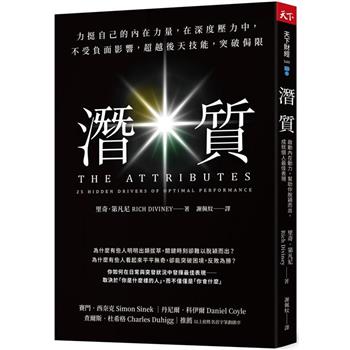你為了這趟中國行存了好幾年的錢,旅行中特別空出兩三天,安插巴士遊覽農村行程。途中的風景好得沒話說,但遊覽車只在觀光客稀少的偏遠村落短暫停留。到了一個特別小的村落,導遊說你們有二十分鐘的時間下車欣賞壯闊山谷籠罩在暮色中的美景。你脫隊踏上繞著一座小山丘蜿蜒而上的小徑,想獨自一人好好欣賞。你沉浸在壯觀的景色中,渾然忘我,也沒注意時間,回過神時看錶才發現已經過了半小時。
你飛快跑下山坡卻為時已晚。遊覽車早就沿著一條黃土小路開走,離你很遠不說,就算司機發現你不見,要在小路上掉頭回轉也很危險。你什麼都沒帶,因為怕弄丟所以你把手機、現金、護照都放在車上。放眼望去只見五、六間小屋,沒有車輛,也沒有電線桿。有位老婦人好奇地打量你,你向她求助,但她甚至聽不懂你說的話。你不會中文,村裡也沒人會英文。假如你沒記錯行程,下一站應該還要三小時的車程,但眼看再兩個小時就要天黑了。
你該怎麼辦?
再來看看以下場景:你帶全家人到紐約玩。孩子們第一次來紐約就愛上這裡。你們去看了自由女神像和時代廣場,現在要搭地鐵去自然歷史博物館。問題是你走錯了月台,這班車要開往市區。你雖然成功阻止你的兩個小孩上車,但另一個五歲大的孩子太過興奮,根本沒聽到你的呼喚,直接穿過人群獨自上了車。車門關上,列車開走,載著你的小孩消失在隧道裡。
該如何是好?
再來一個:新的一年過了三個月,目前為止一切順利,你的新年新希望按照計畫進行,有些長程目標有了進展。然而,冬盡春來之際,全球爆發一種大流行病。整個國家彷彿在一夕之間停擺,各州州長下令全民居家防疫。小孩停課,你不確定自己還有沒有工作,商店紛紛關門,衛生紙和乾洗手液到處缺貨。大家對病毒仍然一知半解,所以你也不知道該不該害怕。你或許能恢復健康,但年邁的父母親呢?更糟的是,你不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幾個禮拜?幾個月?還是情況將永遠改變?
你對這樣的局面有所準備嗎?
當然沒有。但以上三種情況有個共同點:每個都把你拋向未知的深淵,丟進陌生險惡的境地。你的恐慌隨著每次心跳加深,最初的困惑也可能化為恐懼。這種突發狀況無法事先演練,也無法靠學習技能就化險為夷。你學語言的速度很快是嗎?但也不可能天黑之前就學會陌生語言。你很會在大城市裡闖蕩?但你的五歲大小孩又不是你。難道你早已為逐漸停擺的經濟,或是隔離防疫變成新常態做好準備?有誰真的做好準備呢?
儘管如此,你還是必須採取行動。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你如何應對取決於「你是什麼樣的人」,而不是你「會什麼」。
你的技能不一定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你這個人的潛質(attributes)。
何謂潛質?
潛質深植於我們的內在神經迴路中,在後台不停運轉,左右著我們的行為、反應和表現。你可以把它們想成是手機應用程式背後的程式語言。只要點擊一個圖示,一個應用程式就會打開,或許是電子信箱、遊戲,或是天氣預報。整個過程簡單明瞭,前因(點擊)後果(打開)清楚可預期。對一般人來說,大多時候這樣的認知就已足夠:點擊這個圖示,就會發生某些特定的事;點擊那個圖示,就會發生另一件事。運用某項技能,就會得到某種結果。
然而,大多數人從沒想過的是,一行行數不清的程式碼,才是決定手機上的應用程式如何運作的幕後功臣。iPhone應用程式平均每個就有五萬行程式碼。不妨將這些程式碼視為潛質的綜合體。每個應用程式的程式碼組合都不同,但通常我們並不需要知道這些組合。你若是想知道去海邊的路,只要知道點擊哪個應用程式可以導航即可,並不需要知道怎麼寫程式。你的手機主頁井然有序,應用程式一目瞭然,你也知道點下哪一個會啟動什麼功能。
但那些圖示其實沒做任何事,真正驅動功能的不是你看到的東西(打開應用程式的圖示),而是你看不見的程式碼。
程式碼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潛質很重要。
潛質也不該與人格特質混為一談。人格乃是由日積月累的行為模式建立而成,是你之所以是你的各種外在表現的總和,包括你的才能、習慣、情緒、觀點,以及──沒錯,就是潛質。許許多多因素都會影響你的人格,從基因、教養到環境都是。潛質只是這些眾多基本因素之一。
但重要的是要記住,潛質永遠在後台不停運轉。唯有遭遇挑戰性高的情況,尤其是充滿不確定性、迫使你憑直覺行事的情況,潛質才會顯露而出。
潛質雖然深植於每個人的神經迴路中,卻非永久不變,而是可以微調及修改的。我們無法操控他人的潛質,卻可以學會辨識他人的潛質,這點非常有用。若是想要理解自己或他人的表現,第一步就是要了解潛質。
履歷完美不等於表現完美
我學習潛質的過程吃盡了苦頭,一方面要完成工作目標,一方面又要承受來自上級的壓力。
二○一○年,我負責訓練地表最精銳的特種作戰部隊。我們的指揮部從其他特種部隊選了一些人,這些人早已證明自己的過人才能和堅定意志。某個星期五下午,我坐在一張小桌子前,對面是其中一名人選,一整天訓練下來早已精疲力盡,身上的汗甚至還未乾。此人是隸屬於海軍特戰隊的海豹部隊成員,已經服役八年,經驗豐富且完成過無數任務,紀錄中滿是上級的讚賞和推薦。此外,他也很熱心指導經驗尚淺的年輕隊員,每次升遷一定少不了他,而且往往很快就得到升遷。
表面看來,他完美無缺。但九個月的訓練進行到第三週,我們就知道他無法過關。
他上的選拔培訓班剛結束為期一週的近身格鬥訓練(簡稱CQC)。你應該在電影或電視上看過那種畫面:一支特警隊或一隊士兵衝進一棟建築物,高舉槍管左右揮舞,目光隨著槍口四下掃視,每隔幾秒就有其中一人大喊「清空!」。只不過好萊塢的版本比實際情況吵雜和馬虎。在實際狀況下,近身格鬥訓練是由一連串複雜的行動組成,必須在多變、高壓的環境下當場拿捏確切的順序和恰當的時機,只要出錯就可能賠上性命。帶頭的人只專注在盯著門和等待第二人的信號,或許是一個字或一個手勢。接著他破門而入,向左或向右轉,視線掃過牆壁及九十度角切過房間中央。第二人則往反方向前進,跟帶頭的人一人一邊,並同樣用目光掃視。第三人和第四人持續變換方向,尋找房裡是否有需要消滅的壞人或不需消滅的好人。這一切都在幾秒內發生。
坐我對面的候選人一開始表現優異,但過了大約一週就開始失常。小失誤演變成大過失,他的自信也受到打擊。他知道自己逐漸落後,所以拚了命要趕上。他熬夜演練各種狀況,磨練技巧,請教官給他建議,但全都沒用。全世界最訓練有素的戰士,而且還是專為這支特戰隊招募的人選,無論如何就是跟不上。
那個星期五下午我坐在桌前,心情沮喪。此人的從軍紀錄以及他得到的所有表揚和推薦都攤在我面前,我又翻閱了一次。檔案裡的一切都說他是這個單位的完美人選,但近身格鬥訓練的結果卻告訴我們他不是。
我該怎麼跟他說?說他至少不是唯一過不了關的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也被刷掉了?行不通的。措辭再委婉,「你不夠好」對任何人的自尊都是一大打擊,更何況是他這種水準的人。
除此之外,我也得向長官交代。來參加特種作戰部隊選拔的人流失率很高,但這是故意為之的。舉例來說,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選無法完成海豹部隊的基礎訓練。然而,我們這次招募的是已證明自己是頂尖特種作戰員的人。當這些人只有半數通過訓練時,上級指揮官想知道原因也可以理解。若我們無法給上級一個比「他們沒達到標準」更好的答案,他們遲早會開始質疑這個計畫本身,即使我們團隊成員都知道這個計畫不但完備,而且證明有效已經長達數十年。事實上,這些質疑早已出現。在我正式接下培訓任務之前,我的指揮官就要我深入調查,看能否更清楚闡述我們進行的工作流程,以便更能確切說明我們的人選為何成功或失敗。
然而,在二○一○年的那一天,我還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只能告訴這位經驗豐富、功勳卓著、能力一流的海豹部隊成員:「很抱歉,你沒有過關。」
他也跟我一樣沮喪。
「知道怎麼做」vs.「可以做到」
為了找到更好的方式解釋何以這麼多看似合格的人選都過不了關,我認為有必要檢視這一切的源頭。這就要回溯到起點,也就是一九四三年。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將近兩年才會結束,但歐洲戰線的勝利需要同盟國軍隊攻佔陸地,這已成了定局。派遣有限的傘兵前往敵營或許可行,也真的這麼做了,但若想擊敗軸心國軍隊必定要動員好幾萬大軍和準備大量物資才行。要贏得這場戰爭,勢必得展開大規模的水陸兩棲入侵。
同盟國在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就看清了這點。一九一五年爆發的加里波利之戰(The Gallipoli Campaign),原本計畫兩棲登陸後再發動地面攻擊,佔領主要補給線,期望為結束這場戰爭拉開序幕,沒想到卻是一大災難。鄂圖曼軍隊在海峽中布滿水雷和障礙,在首次進攻時,包括兩艘潛水艇在內的許多船艦遭擊沉或被毀。這場戰役持續了八個月,在協約國撤軍前已奪走五十萬條人命。
將近三十年後,同盟國的戰略規劃者並沒有忘記加里波利之戰的教訓。嘗試過一連串危險的登陸行動後,美國海軍指揮官意識到,在大規模入侵之前,必須先由滲透小隊打頭陣。他們的任務是勘查海岸,找到並摧毀障礙,並引導登陸部隊上岸。基本上,諾曼第登陸這個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海上登陸行動之所以成功,靠的就是一小群志願者,甘冒生命危險收集情報和開路。
當時,奉命招兵買馬的是海軍中校德雷普‧考夫曼(Draper Kaufmann)。一年多前,他設計了美國海軍拆彈訓練課程,一開始的學員(海軍工程隊、海軍陸戰隊、陸軍戰鬥工程師)很多都已經有爆破經驗。然而,考夫曼帶領的海軍作戰爆破隊(NCDU)只能穿著短褲、蛙鞋和面罩游進戒備森嚴的敵軍海岸,唯一的武裝是潛水刀和他們能帶的炸藥。這些人必須屏住呼吸潛到十五公尺深的海底,把炸藥綁在障礙物上,找到並記錄水雷的位置,也要留意周遭環境以便轉成可供同盟國軍隊參考的地圖。有時他們還得偷偷上岸確認和破壞敵人的陣地,身上只有可用來自衛的刀,要是被發現,肯定不是被殺就是被俘。
但考夫曼很清楚,光是很會游泳、能偷偷游到對岸,這樣還不夠格進入他的團隊。他需要的是能隨機應變的人。有辦法像環境一樣快速適應、伸縮自如的人,能夠留意周圍環境的各種變化,與團隊一起合作,很快學會新事物,即使面臨深不可測的壓力。
換句話說,考夫曼知道自己要找的不是知道怎麼做的人,而是可以做到的人。
「知道怎麼做」和「可以做到」之間的差距很大。潛水、製圖、爆破等等技能只要一學就會。考夫曼要找的是具有某些天生潛質的人,那些潛質深深融入一個人的核心,永難磨滅。
這些小組必須盡快成立,所以考夫曼沒有時間慢慢篩選和訓練隊員。因此,他沒有藉由幾個月的培訓和操練找出他需要的適應力、區隔化和復原力等等潛質。他靈機一動,打算用他想得到最累人的一週來展開訓練。所有人選都要接受高強度的體能活動、團隊挑戰、作戰模擬和解決問題的訓練。持續五天不間斷,整個禮拜只能睡三到四小時──不是每晚,而是一整週。考夫曼在第一週不考試也不評估大家的表現。假定沒有人因為受傷就退出,也沒有人被迫退出甄選,候選人能否通過完全取決於自己。究竟要留下來?還是放棄?
很多人選擇放棄。事實上,大多數人在第二天就放棄了,流失率約為九成。然而,這對考夫曼來說並不重要,讓大多數人知難而退基本上就是他的目的。留下來的少數人才是考夫曼(和同盟軍)需要的人。他知道這些堅持到底的人真正上場時能夠發揮所長,儘管實際情況一定會超出預期,周詳的計畫可能變得無比複雜,他們也能隨機應變。無論考夫曼本人是否意識到這點,第一週訓練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很大程度把技能移出考量範圍,使每個人隱而不見的潛質顯露無遺。留下來的人擁有克服萬難完成任務所需的潛質,無論情況惡化得多麼徹底都不例外。
成功者的潛質清單
考夫曼令人痛苦的頭一週集訓有個貼切的別稱叫「地獄週」。後來這支海軍作戰爆破隊變成水下爆破隊(UDT),最後又改名為陸海空三棲特戰隊,也就是俗稱的海豹部隊(SEAL),所需的技能隨之改變,訓練和篩選過程也變得更冗長複雜。然而,從未改變的是目標。現代的海豹部隊訓練(亦即「基礎水下爆破/海豹訓練課程」其實就是一種篩選方法。前後為期六個月,「地獄週」從原來的第一週改到第五週,但基本目標仍然不變:候選人是否具備海軍所要尋找的潛質?
這正是我在二○一○年重新思考的問題。在解釋經驗豐富的特種作戰人員何以會被淘汰時,我和同事都專注在評估技能,卻反而劃地自限。我們用錯了度量衡。確實,候選人無法正確或有效地展現技能,表面上看來或許就是失敗。但我們知道考夫曼的直覺判斷是對的,技能經由教導就能學會。重點在於候選人為什麼會失敗。我們的訓練跟考夫曼的地獄週一樣,把候選人操練到原形畢露,讓他們的核心潛質顯露無遺。這種訓練凸顯了我們評估人選的方式,也就是以他們的天生潛質做為基準。
一旦理解這點,我們便開始自問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潛質?我們把人分成不同小組,從中得出多份優秀作戰員所需潛質的清單,同時不忘提醒自己切勿把「技能」和「潛質」混為一談,因為這種錯誤經常發生。換句話說,「射擊精準」或「破門技術一流」之類的表現不列入考慮。接著,我們比對所有清單,將之濃縮成一份完整的列表。
最後,我們確立了一份包含三十六種潛質的清單,從此改變了我們理解自己的訓練過程及解釋結果的方式。現在我們可以對自己和候選人清楚說明,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以及尋找的理由。這使我們對候選人、上級和自己解釋淘汰原因時,能夠更有效率也更有建設性。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這張潛質清單向候選人說明,他們哪些潛質較多、哪些潛質較少,以及最重要的──這些潛質如何轉化成他們的實際表現。
這也產生一個正面的附加效應。一旦把技能與潛質區分開來,我們也能盡早發現黑馬,亦即那些或許「技術並非最高超,卻擁有我們尋找的所有潛質」的人。這些人往往就是我們淘汰掉的人,因為當他們在我們眼前展露潛質時,我們卻看不到。而我們之所以看不到,原因就在於沒有用正確的眼光去看。
把焦點轉向潛質之後,一切都跟過去大不相同。當然,技能永遠有其重要性。但一旦釐清是什麼影響我們的技能,也就是我們視而不見的潛質是什麼,我們就能更清楚說明自己的篩選標準,並用具體且有建設性的語言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人入選、有些人落選。最重要的是,盡可能建立一支最優秀的特種作戰部隊。
軍事訓練,尤其是菁英作戰部隊的訓練,是區分潛質和技能的最佳試煉場,而與特戰隊合作給了我觀察及理解其中差異的難得機會。但同樣的原則在平民生活與在軍事世界中一樣適用。想知道自己為什麼就是無法決定事情的輕重緩急並集中注意力嗎?為什麼每當情況改變你就開始緊張?為什麼你無法鎖定目標,然後堅持到底?潛質是理解這一切的起點。無論在何時何地,當人需要團結合作時,認清和理解自己及他人的潛質,都是表現能否達到最佳水準的關鍵。
你飛快跑下山坡卻為時已晚。遊覽車早就沿著一條黃土小路開走,離你很遠不說,就算司機發現你不見,要在小路上掉頭回轉也很危險。你什麼都沒帶,因為怕弄丟所以你把手機、現金、護照都放在車上。放眼望去只見五、六間小屋,沒有車輛,也沒有電線桿。有位老婦人好奇地打量你,你向她求助,但她甚至聽不懂你說的話。你不會中文,村裡也沒人會英文。假如你沒記錯行程,下一站應該還要三小時的車程,但眼看再兩個小時就要天黑了。
你該怎麼辦?
再來看看以下場景:你帶全家人到紐約玩。孩子們第一次來紐約就愛上這裡。你們去看了自由女神像和時代廣場,現在要搭地鐵去自然歷史博物館。問題是你走錯了月台,這班車要開往市區。你雖然成功阻止你的兩個小孩上車,但另一個五歲大的孩子太過興奮,根本沒聽到你的呼喚,直接穿過人群獨自上了車。車門關上,列車開走,載著你的小孩消失在隧道裡。
該如何是好?
再來一個:新的一年過了三個月,目前為止一切順利,你的新年新希望按照計畫進行,有些長程目標有了進展。然而,冬盡春來之際,全球爆發一種大流行病。整個國家彷彿在一夕之間停擺,各州州長下令全民居家防疫。小孩停課,你不確定自己還有沒有工作,商店紛紛關門,衛生紙和乾洗手液到處缺貨。大家對病毒仍然一知半解,所以你也不知道該不該害怕。你或許能恢復健康,但年邁的父母親呢?更糟的是,你不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幾個禮拜?幾個月?還是情況將永遠改變?
你對這樣的局面有所準備嗎?
當然沒有。但以上三種情況有個共同點:每個都把你拋向未知的深淵,丟進陌生險惡的境地。你的恐慌隨著每次心跳加深,最初的困惑也可能化為恐懼。這種突發狀況無法事先演練,也無法靠學習技能就化險為夷。你學語言的速度很快是嗎?但也不可能天黑之前就學會陌生語言。你很會在大城市裡闖蕩?但你的五歲大小孩又不是你。難道你早已為逐漸停擺的經濟,或是隔離防疫變成新常態做好準備?有誰真的做好準備呢?
儘管如此,你還是必須採取行動。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你如何應對取決於「你是什麼樣的人」,而不是你「會什麼」。
你的技能不一定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你這個人的潛質(attributes)。
何謂潛質?
潛質深植於我們的內在神經迴路中,在後台不停運轉,左右著我們的行為、反應和表現。你可以把它們想成是手機應用程式背後的程式語言。只要點擊一個圖示,一個應用程式就會打開,或許是電子信箱、遊戲,或是天氣預報。整個過程簡單明瞭,前因(點擊)後果(打開)清楚可預期。對一般人來說,大多時候這樣的認知就已足夠:點擊這個圖示,就會發生某些特定的事;點擊那個圖示,就會發生另一件事。運用某項技能,就會得到某種結果。
然而,大多數人從沒想過的是,一行行數不清的程式碼,才是決定手機上的應用程式如何運作的幕後功臣。iPhone應用程式平均每個就有五萬行程式碼。不妨將這些程式碼視為潛質的綜合體。每個應用程式的程式碼組合都不同,但通常我們並不需要知道這些組合。你若是想知道去海邊的路,只要知道點擊哪個應用程式可以導航即可,並不需要知道怎麼寫程式。你的手機主頁井然有序,應用程式一目瞭然,你也知道點下哪一個會啟動什麼功能。
但那些圖示其實沒做任何事,真正驅動功能的不是你看到的東西(打開應用程式的圖示),而是你看不見的程式碼。
程式碼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潛質很重要。
潛質也不該與人格特質混為一談。人格乃是由日積月累的行為模式建立而成,是你之所以是你的各種外在表現的總和,包括你的才能、習慣、情緒、觀點,以及──沒錯,就是潛質。許許多多因素都會影響你的人格,從基因、教養到環境都是。潛質只是這些眾多基本因素之一。
但重要的是要記住,潛質永遠在後台不停運轉。唯有遭遇挑戰性高的情況,尤其是充滿不確定性、迫使你憑直覺行事的情況,潛質才會顯露而出。
潛質雖然深植於每個人的神經迴路中,卻非永久不變,而是可以微調及修改的。我們無法操控他人的潛質,卻可以學會辨識他人的潛質,這點非常有用。若是想要理解自己或他人的表現,第一步就是要了解潛質。
履歷完美不等於表現完美
我學習潛質的過程吃盡了苦頭,一方面要完成工作目標,一方面又要承受來自上級的壓力。
二○一○年,我負責訓練地表最精銳的特種作戰部隊。我們的指揮部從其他特種部隊選了一些人,這些人早已證明自己的過人才能和堅定意志。某個星期五下午,我坐在一張小桌子前,對面是其中一名人選,一整天訓練下來早已精疲力盡,身上的汗甚至還未乾。此人是隸屬於海軍特戰隊的海豹部隊成員,已經服役八年,經驗豐富且完成過無數任務,紀錄中滿是上級的讚賞和推薦。此外,他也很熱心指導經驗尚淺的年輕隊員,每次升遷一定少不了他,而且往往很快就得到升遷。
表面看來,他完美無缺。但九個月的訓練進行到第三週,我們就知道他無法過關。
他上的選拔培訓班剛結束為期一週的近身格鬥訓練(簡稱CQC)。你應該在電影或電視上看過那種畫面:一支特警隊或一隊士兵衝進一棟建築物,高舉槍管左右揮舞,目光隨著槍口四下掃視,每隔幾秒就有其中一人大喊「清空!」。只不過好萊塢的版本比實際情況吵雜和馬虎。在實際狀況下,近身格鬥訓練是由一連串複雜的行動組成,必須在多變、高壓的環境下當場拿捏確切的順序和恰當的時機,只要出錯就可能賠上性命。帶頭的人只專注在盯著門和等待第二人的信號,或許是一個字或一個手勢。接著他破門而入,向左或向右轉,視線掃過牆壁及九十度角切過房間中央。第二人則往反方向前進,跟帶頭的人一人一邊,並同樣用目光掃視。第三人和第四人持續變換方向,尋找房裡是否有需要消滅的壞人或不需消滅的好人。這一切都在幾秒內發生。
坐我對面的候選人一開始表現優異,但過了大約一週就開始失常。小失誤演變成大過失,他的自信也受到打擊。他知道自己逐漸落後,所以拚了命要趕上。他熬夜演練各種狀況,磨練技巧,請教官給他建議,但全都沒用。全世界最訓練有素的戰士,而且還是專為這支特戰隊招募的人選,無論如何就是跟不上。
那個星期五下午我坐在桌前,心情沮喪。此人的從軍紀錄以及他得到的所有表揚和推薦都攤在我面前,我又翻閱了一次。檔案裡的一切都說他是這個單位的完美人選,但近身格鬥訓練的結果卻告訴我們他不是。
我該怎麼跟他說?說他至少不是唯一過不了關的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也被刷掉了?行不通的。措辭再委婉,「你不夠好」對任何人的自尊都是一大打擊,更何況是他這種水準的人。
除此之外,我也得向長官交代。來參加特種作戰部隊選拔的人流失率很高,但這是故意為之的。舉例來說,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選無法完成海豹部隊的基礎訓練。然而,我們這次招募的是已證明自己是頂尖特種作戰員的人。當這些人只有半數通過訓練時,上級指揮官想知道原因也可以理解。若我們無法給上級一個比「他們沒達到標準」更好的答案,他們遲早會開始質疑這個計畫本身,即使我們團隊成員都知道這個計畫不但完備,而且證明有效已經長達數十年。事實上,這些質疑早已出現。在我正式接下培訓任務之前,我的指揮官就要我深入調查,看能否更清楚闡述我們進行的工作流程,以便更能確切說明我們的人選為何成功或失敗。
然而,在二○一○年的那一天,我還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只能告訴這位經驗豐富、功勳卓著、能力一流的海豹部隊成員:「很抱歉,你沒有過關。」
他也跟我一樣沮喪。
「知道怎麼做」vs.「可以做到」
為了找到更好的方式解釋何以這麼多看似合格的人選都過不了關,我認為有必要檢視這一切的源頭。這就要回溯到起點,也就是一九四三年。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將近兩年才會結束,但歐洲戰線的勝利需要同盟國軍隊攻佔陸地,這已成了定局。派遣有限的傘兵前往敵營或許可行,也真的這麼做了,但若想擊敗軸心國軍隊必定要動員好幾萬大軍和準備大量物資才行。要贏得這場戰爭,勢必得展開大規模的水陸兩棲入侵。
同盟國在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就看清了這點。一九一五年爆發的加里波利之戰(The Gallipoli Campaign),原本計畫兩棲登陸後再發動地面攻擊,佔領主要補給線,期望為結束這場戰爭拉開序幕,沒想到卻是一大災難。鄂圖曼軍隊在海峽中布滿水雷和障礙,在首次進攻時,包括兩艘潛水艇在內的許多船艦遭擊沉或被毀。這場戰役持續了八個月,在協約國撤軍前已奪走五十萬條人命。
將近三十年後,同盟國的戰略規劃者並沒有忘記加里波利之戰的教訓。嘗試過一連串危險的登陸行動後,美國海軍指揮官意識到,在大規模入侵之前,必須先由滲透小隊打頭陣。他們的任務是勘查海岸,找到並摧毀障礙,並引導登陸部隊上岸。基本上,諾曼第登陸這個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海上登陸行動之所以成功,靠的就是一小群志願者,甘冒生命危險收集情報和開路。
當時,奉命招兵買馬的是海軍中校德雷普‧考夫曼(Draper Kaufmann)。一年多前,他設計了美國海軍拆彈訓練課程,一開始的學員(海軍工程隊、海軍陸戰隊、陸軍戰鬥工程師)很多都已經有爆破經驗。然而,考夫曼帶領的海軍作戰爆破隊(NCDU)只能穿著短褲、蛙鞋和面罩游進戒備森嚴的敵軍海岸,唯一的武裝是潛水刀和他們能帶的炸藥。這些人必須屏住呼吸潛到十五公尺深的海底,把炸藥綁在障礙物上,找到並記錄水雷的位置,也要留意周遭環境以便轉成可供同盟國軍隊參考的地圖。有時他們還得偷偷上岸確認和破壞敵人的陣地,身上只有可用來自衛的刀,要是被發現,肯定不是被殺就是被俘。
但考夫曼很清楚,光是很會游泳、能偷偷游到對岸,這樣還不夠格進入他的團隊。他需要的是能隨機應變的人。有辦法像環境一樣快速適應、伸縮自如的人,能夠留意周圍環境的各種變化,與團隊一起合作,很快學會新事物,即使面臨深不可測的壓力。
換句話說,考夫曼知道自己要找的不是知道怎麼做的人,而是可以做到的人。
「知道怎麼做」和「可以做到」之間的差距很大。潛水、製圖、爆破等等技能只要一學就會。考夫曼要找的是具有某些天生潛質的人,那些潛質深深融入一個人的核心,永難磨滅。
這些小組必須盡快成立,所以考夫曼沒有時間慢慢篩選和訓練隊員。因此,他沒有藉由幾個月的培訓和操練找出他需要的適應力、區隔化和復原力等等潛質。他靈機一動,打算用他想得到最累人的一週來展開訓練。所有人選都要接受高強度的體能活動、團隊挑戰、作戰模擬和解決問題的訓練。持續五天不間斷,整個禮拜只能睡三到四小時──不是每晚,而是一整週。考夫曼在第一週不考試也不評估大家的表現。假定沒有人因為受傷就退出,也沒有人被迫退出甄選,候選人能否通過完全取決於自己。究竟要留下來?還是放棄?
很多人選擇放棄。事實上,大多數人在第二天就放棄了,流失率約為九成。然而,這對考夫曼來說並不重要,讓大多數人知難而退基本上就是他的目的。留下來的少數人才是考夫曼(和同盟軍)需要的人。他知道這些堅持到底的人真正上場時能夠發揮所長,儘管實際情況一定會超出預期,周詳的計畫可能變得無比複雜,他們也能隨機應變。無論考夫曼本人是否意識到這點,第一週訓練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很大程度把技能移出考量範圍,使每個人隱而不見的潛質顯露無遺。留下來的人擁有克服萬難完成任務所需的潛質,無論情況惡化得多麼徹底都不例外。
成功者的潛質清單
考夫曼令人痛苦的頭一週集訓有個貼切的別稱叫「地獄週」。後來這支海軍作戰爆破隊變成水下爆破隊(UDT),最後又改名為陸海空三棲特戰隊,也就是俗稱的海豹部隊(SEAL),所需的技能隨之改變,訓練和篩選過程也變得更冗長複雜。然而,從未改變的是目標。現代的海豹部隊訓練(亦即「基礎水下爆破/海豹訓練課程」其實就是一種篩選方法。前後為期六個月,「地獄週」從原來的第一週改到第五週,但基本目標仍然不變:候選人是否具備海軍所要尋找的潛質?
這正是我在二○一○年重新思考的問題。在解釋經驗豐富的特種作戰人員何以會被淘汰時,我和同事都專注在評估技能,卻反而劃地自限。我們用錯了度量衡。確實,候選人無法正確或有效地展現技能,表面上看來或許就是失敗。但我們知道考夫曼的直覺判斷是對的,技能經由教導就能學會。重點在於候選人為什麼會失敗。我們的訓練跟考夫曼的地獄週一樣,把候選人操練到原形畢露,讓他們的核心潛質顯露無遺。這種訓練凸顯了我們評估人選的方式,也就是以他們的天生潛質做為基準。
一旦理解這點,我們便開始自問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潛質?我們把人分成不同小組,從中得出多份優秀作戰員所需潛質的清單,同時不忘提醒自己切勿把「技能」和「潛質」混為一談,因為這種錯誤經常發生。換句話說,「射擊精準」或「破門技術一流」之類的表現不列入考慮。接著,我們比對所有清單,將之濃縮成一份完整的列表。
最後,我們確立了一份包含三十六種潛質的清單,從此改變了我們理解自己的訓練過程及解釋結果的方式。現在我們可以對自己和候選人清楚說明,我們究竟在尋找什麼,以及尋找的理由。這使我們對候選人、上級和自己解釋淘汰原因時,能夠更有效率也更有建設性。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這張潛質清單向候選人說明,他們哪些潛質較多、哪些潛質較少,以及最重要的──這些潛質如何轉化成他們的實際表現。
這也產生一個正面的附加效應。一旦把技能與潛質區分開來,我們也能盡早發現黑馬,亦即那些或許「技術並非最高超,卻擁有我們尋找的所有潛質」的人。這些人往往就是我們淘汰掉的人,因為當他們在我們眼前展露潛質時,我們卻看不到。而我們之所以看不到,原因就在於沒有用正確的眼光去看。
把焦點轉向潛質之後,一切都跟過去大不相同。當然,技能永遠有其重要性。但一旦釐清是什麼影響我們的技能,也就是我們視而不見的潛質是什麼,我們就能更清楚說明自己的篩選標準,並用具體且有建設性的語言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人入選、有些人落選。最重要的是,盡可能建立一支最優秀的特種作戰部隊。
軍事訓練,尤其是菁英作戰部隊的訓練,是區分潛質和技能的最佳試煉場,而與特戰隊合作給了我觀察及理解其中差異的難得機會。但同樣的原則在平民生活與在軍事世界中一樣適用。想知道自己為什麼就是無法決定事情的輕重緩急並集中注意力嗎?為什麼每當情況改變你就開始緊張?為什麼你無法鎖定目標,然後堅持到底?潛質是理解這一切的起點。無論在何時何地,當人需要團結合作時,認清和理解自己及他人的潛質,都是表現能否達到最佳水準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