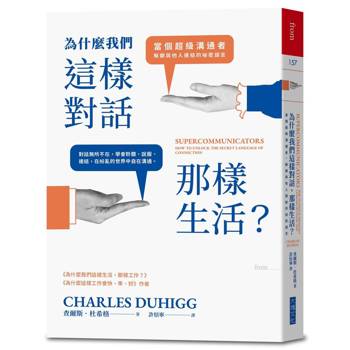【內文試閱一】
三種類型的對話
概述
對話是我們共同呼吸的空氣。我們在一天之中和家人、朋友、陌生人、同事說話,有時還跟寵物說話。我們透過簡訊、電子郵件、網路文章與社群媒體溝通。我們用鍵盤和語音轉成文字發聲,偶爾還提筆寫信。咕噥、微笑、鬼臉、嘆氣,也不時成為表達工具。
然而,不是所有的對話都是平等的。碰上有意義的討論時,我們會感到十分開心,有如撥雲見日。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曾說:「不論是婚姻或友誼,最終所有友伴關係的黏著劑是對話。」
然而,若是重要的對話進展不順利,將導致心情低落、垂頭喪氣,覺得錯過機會。我們心情複雜地離開,悶悶不樂,不確定有任何人聽懂我們剛才講的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
下一章會解釋,人類的大腦演化成渴望連結。然而,我們必須理解,溝通是如何產生作用,才有可能持續與他人同頻──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連結的前提是雙方參與同一種對話。
超級溝通者不是生下來就具備特殊能力──但他們比別人更認真思考對話是如何開展、對話為什麼成功或失敗。此外,他們意識到每場對話都帶來接近無限的選擇機會,人們將因此更貼近彼此,或是漸行漸遠。當我們學會辨識那些機會,將開始以新的方式開口與聆聽。
【內文試閱二】
第1章 匹配原則──為何招不到間諜
吉姆.勞勒(Jim Lawler)要是對自己誠實,他會承認自己毫無吸收間諜的能力。事實上,他度過的多數夜晚都在煩惱,這輩子做過的各種工作中,找人當間諜是他唯一喜歡的,但看來他就要被炒魷魚了。勞勒在兩年前得到這份工作,進入美國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Agency, CIA)當招募員。
時間回到一九八二年,當時勞勒三十歲。他在加入CIA前,畢業於德州大學法學院,成績平平,接著輾轉於一連串無聊透頂的工作。有一天,不確定人生要幹什麼的他,打電話給在校園碰到的CIA獵頭雇員。接下來,他接受面試、測謊,又在數個城市參加了十幾場面試,接著是一系列的考試。考題感覺上是在找碴,專問一些勞勒不知道的事情(勞勒真的想不通,到底有誰會背下一九六○年代的橄欖球世界冠軍?)。
勞勒終究闖進了最後一關的面試,但感覺不太可能會錄取。他的考試表現介於差勁和平庸之間。此外,他沒有海外生活的經驗,不會說外語,沒有軍隊的經驗,也沒有特殊技能。不過,面試官注意到勞勒為了參加這次面試,千里迢迢自費飛到華盛頓特區,而且堅持完成每一場考試,即便大部分問題的答案,他顯然毫無頭緒。勞勒以令人欽佩的正面精神回應每一次的挫敗,甚至有過度樂觀之嫌。
面試官問勞勒,他到底為什麼這麼想加入CIA?
勞勒回答:「我這輩子一直想做重要的事。」他想要報效母國,「把民主帶給渴望自由的國家。」話一說出口,勞勒自己都知道很好笑。有誰會在面試時談什麼渴望?所以勞勒停下來,深呼吸,說出當下能想到最誠實的答案:「我感到人生很空虛。」勞勒告訴面試官:「我想參與有意義的事。」
一星期後,CIA打電話通知他錄取了。勞勒立刻接受,到培里營(Camp Peary)報到──培里營俗稱「農場」(the Farm),是CIA在維吉尼亞州的訓練場地。勞勒在那裡學習開鎖、傳遞情報與跟蹤監視。
不過,農場課程最出乎意料的一面是CIA極其重視對話技巧。勞勒在受訓期間得知,在CIA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溝通。外勤人員的任務不是潛伏在暗處,也不是在停車場竊竊私語,而是在派對上找人聊天,在大使館交朋友,和外交官打成一片,希望有一天能悄悄得知關鍵情報。溝通萬分重要,CIA訓練法的摘要開門見山地指示:「找出辦法連結。」上頭寫著:「CIA招募員的目標是讓間諜人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招募員是少數真正懂他的人,甚至是世上唯一的知己。」
勞勒從間諜學校高分結業,派駐歐洲。他的任務是結交外國官員,和大使館人員培養友誼,並開發各式各樣的人脈。或許有人會願意敞開心扉和他聊一聊—他的上司希望能因此開啟討論的管道,讓全球事務變得更可控一些。•••
勞勒在海外的頭幾個月過得慘兮兮。他盡了最大的努力融入當地生活,參加必須穿著禮服的晚宴,還在大使館附近的酒吧灌酒,但不管怎麼做都沒用。有一次,勞勒在滑完雪的社交活動中,認識一名中國代表團的職員,沒事就相邀吃午餐和喝雞尾酒。勞勒最後鼓起勇氣問這位新朋友,或許他願意賺點零用錢,只要傳遞在大使館聽到的小道消息就可以了。然而,那個人告訴勞勒,自己的家族財力雄厚,謝謝他的邀請,但上頭一般會處決幹這種事的人,所以還是算了吧。
還有一次,一名蘇聯領事館的接待人員看起來可能答應,直到上司把勞勒拉到一旁解釋,那其實是蘇聯情報機構KGB的人。她也在試圖吸收他。
最後,終於出現能拯救勞勒事業的機會:CIA的同事提到,在某中東國家外交部工作的年輕女性茉莉(Yasmin),最近會來到他們這裡。同事解釋,茉莉是來休假的,住在移居歐洲的哥哥家。幾天後,勞勒設法在餐廳「不小心撞到」茉莉。勞勒自稱是石油商人,兩人聊起天。茉莉好像有點寂寞,提到哥哥總是很忙,永遠沒空陪她觀光。
勞勒邀請茉莉隔天共進午餐,詢問她的生活。她喜歡她的工作嗎?住在近期剛發生保守革命的國家難不難?茉莉坦承她痛恨上台的宗教激進分子,渴望移居國外,住在巴黎或紐約,但這種事要有錢才能辦到。光是這次的短期停留,就花掉她好幾個月的積蓄。
勞勒感到這是個機會。他告訴茉莉,他的石油公司正好需要顧問。那是一份兼差工作,可以和茉莉在外交部的正職同時做,但他還是會提供簽約獎金。「我們點了香檳慶祝,茉莉差點喜極而泣,她好開心。」勞勒告訴我。
午餐過後,勞勒衝回辦公室找上司。他終於網羅到第一名間諜!「結果長官告訴我:『恭喜。總部會欣喜若狂。現在你需要告訴她,你是CIA探員,你想取得她的政府的資訊。』」勞勒覺得這樣不大好,如果誠實以告,茉莉大概再也不會理他了。
然而,長官解釋不明講是替CIA工作,對她並不公平。萬一哪天茉莉被政府抓到,她會入獄,甚至被處死。她需要瞭解風險所在。
勞勒於是繼續和茉莉見面,試著找到正確時機,說出自己真正的後台。隨著兩人相處的時間愈來愈多,茉莉講話愈來愈沒防備。她告訴勞勒,她恥於自己的政府關閉報社,禁止自由言論。此外,她也厭惡官僚下令讓女性在大學研究某些主題變成違法行為,還強迫女性在公共場所佩戴頭巾。茉莉說她最初在政府單位找工作時,從沒想到情況會惡化至此。
勞勒認為這是好兆頭。某天晚餐時,他解釋自己其實不是什麼石油商人,而是美國的情報人員。勞勒告訴茉莉,她想要的東西跟美國一樣:他們都想推翻她的國家的神權政治,打擊神權領袖的勢力,終止對女性的壓迫。勞勒說對不起,他對自己的身分說謊了,但工作機會是真的。她願不願意考慮替美國的中情局工作?
「我邊說邊看到茉莉的眼睛愈瞪愈大。她抓緊桌布,瘋狂搖頭,喃喃自語著:『不,不,不。』等我講到一個段落,她便開始哭。我知道我搞砸了。」勞勒告訴我:「她說政府會為了這種事殺人,她不可能協助我。」任憑勞勒說破了嘴,茉莉依然不肯考慮他的提議,「她只想快點遠離我。」
勞勒向上級報告壞消息。「我的上司說:『我已經告訴每個人你招募到她了!我告訴了處長,還告訴了站長,他們又回報給華盛頓特區了。然後你現在要我告訴他們,你沒搞定?』」
接下來該怎麼辦,勞勒毫無頭緒。「不論我提議給多少錢,提供多少承諾,茉莉都不肯冒可能害死自己的風險。」勞勒告訴我。唯一可能繼續推動這件事的辦法,就是說服茉莉相信他。他懂她,會保護她。然而,要如何辦到?「他們在農場教我,要想招到人,得讓對方相信你在乎他們。也就是說,你得真正在乎他們。換句話說,你得以某種方式連結,但我根本不曉得如何才能辦到。」
•••
我們如何與另一個人建立真正的連結?如何透過對話,鼓勵某個人去做有風險的事、踏上冒險旅程、接受某份工作,或是出門約會?
讓我們把難度降低一點:假設你試著和上司打好關係,或是想認識某位新朋友:你要如何讓他們放下戒心?如何證明你在認真聽他們說話?
過去數十年間,隨著研究人類行為與大腦的新方法紛紛出爐,這一類的問題促使研究人員幾乎檢視了溝通的每一個面向。科學家仔細觀察我們的大腦如何吸收資訊,最後發現,透過言論跟他人連結的影響力與複雜度,遠超過以往的想像。我們如何溝通──說話與聆聽時不知不覺做出的決定、問的問題、暴露的軟肋,甚至是語氣,全部會影響我們將信任誰、誰能說服我們,以及我們會找誰當朋友。
除了這方面的全新認識,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研究也顯示,每場對話的核心是潛在的神經同步(neurological synchronization),也就是從每個人的呼吸速度到起雞皮疙瘩,大腦與身體會趨於一致──我們通常不會發現這件事,但這會影響我們如何說話、聆聽與思考。有的人持續未能與他人同步,即便和走得近的朋友聊天也辦不到。有些人似乎毫不費力就能與任何人同步──這樣的人姑且稱作超級溝通者(supercommunicator)吧。大部分的人則落在光譜的中間。然而,如果我們理解對話的機制,就能學著以更有意義的方式連結。
不過,道理懂歸懂,勞勒還是感到茫然,看不出如何和茉莉建立連結。「我知道頂多還有一次跟她說話的機會。」勞勒告訴我:「我得想辦法突破。」
大腦的連結時刻
波.席佛斯(Beau Sievers)在二○一二年加入達特茅斯社會系統實驗室(Dartmouth SocialSystems Lab),一身打扮就像幾年前還在擔任樂手的時期。他有時會頂著金色爆炸頭,套著某次爵士節的破爛T恤,一醒來就衝向實驗室。校警不確定剛跑過去的人到底是博士候選人,還是戕害大學生的大麻販子。
席佛斯繞了一大圈,才進入常春藤名校。他大學原本讀的是音樂學院,研究擊鼓與音樂製作,幾乎不問世事。然而沒多久,他就在想,不論再怎麼瘋狂練習,也很難成為萬中選一的幸運兒,「只靠打鼓養活自己。」他因此開始探索其他職涯。席佛斯向來對人們如何溝通極感興趣,尤其喜愛舞台上不時發生的無聲音樂對話。他和其他樂手即興演出時,有時候突然間所有人彷彿融為一體,共用一個大腦。表演者,以及聽眾、調音師,甚至是酒保,突然間就同步了。席佛斯有時也會在深夜聊得很愉快,或是在約會很成功時,出現相同的感受。他因此上了幾堂心理學的課,最後申請到魏特利博士(Thalia Wheatley)的博士班。魏特利博士是最頂尖的神經科學家之一,專門研究人類如何相互連結。
魏特利在期刊《社會與人格心理學指南》(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中寫道:「為什麼人會和某些人『一見如故』,跟其他人卻不會,這是科學上未解的重大謎題。」魏特利解釋,和某個人聊得來的感覺會很美好的部分原因,在於人腦演化成渴望那種連結。想要連結的欲望,促使人們組成社群、保護後代、尋求新朋友與盟友。這是我們這個物種得以生存的原因。「人類擁有罕見的能力。」魏特利寫道:「有辦法在重重阻礙下依舊彼此連結。」
無數的其他研究人員,也對我們如何形成連結深感興趣。席佛斯閱讀科學期刊後發現,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學者在二○一二年,研究過吉他手演奏音樂家沙伊德勒(C. G. Scheidler)D大調奏鳴曲時的大腦。當吉他手各自彈奏,專注於自己的樂譜,他們的神經活動看起來不太一樣。然而,等進入二重奏,顱內的電脈衝會開始同步。在研究人員眼中,這有如吉他手的大腦合而為一。此外,那個連結通常會流過他們的身體:吉他手往往開始以相同的速率呼吸,眼睛同時瞪大,心臟也出現相似的跳動模式。就連他們皮膚上的電脈衝通常也會同步。接下來,等他們不再彈奏同一個段落──譜子開始不一樣,或是轉為獨奏,「腦間的同步化就完全消失。」科學家寫道。
席佛斯發現其他研究也顯示,當人們一起哼歌、肩並肩在桌上敲打手指、合作解謎,或是為彼此講故事,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普林斯頓的研究人員進行測試神經活動的實驗。十二名受試者聆聽一名年輕女性講述在畢業舞會當天,一則峰迴路轉的故事。研究人員同時觀測說話者與聆聽者的大腦,發現聽話者的大腦開始與敘事者同步,直到所有人感受到相同的壓力、不安、開心、幽默等情緒,就好像大家在一起說故事。此外,有的聆聽者與說話者特別同步;大腦看起來跟她幾乎一模一樣。事後被問到時,那些步調特別相近的受試者,更能清楚分辨故事中的人物並回憶小細節。人們的大腦愈是同步,愈能理解說話內容。研究人員在二○一○年的《國家科學院院刊》(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寫道:「說者與聽者的神經耦合(speaker-listener neural coupling)程度,能夠預測溝通的成功度。」
(未完)
三種類型的對話
概述
對話是我們共同呼吸的空氣。我們在一天之中和家人、朋友、陌生人、同事說話,有時還跟寵物說話。我們透過簡訊、電子郵件、網路文章與社群媒體溝通。我們用鍵盤和語音轉成文字發聲,偶爾還提筆寫信。咕噥、微笑、鬼臉、嘆氣,也不時成為表達工具。
然而,不是所有的對話都是平等的。碰上有意義的討論時,我們會感到十分開心,有如撥雲見日。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曾說:「不論是婚姻或友誼,最終所有友伴關係的黏著劑是對話。」
然而,若是重要的對話進展不順利,將導致心情低落、垂頭喪氣,覺得錯過機會。我們心情複雜地離開,悶悶不樂,不確定有任何人聽懂我們剛才講的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
下一章會解釋,人類的大腦演化成渴望連結。然而,我們必須理解,溝通是如何產生作用,才有可能持續與他人同頻──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連結的前提是雙方參與同一種對話。
超級溝通者不是生下來就具備特殊能力──但他們比別人更認真思考對話是如何開展、對話為什麼成功或失敗。此外,他們意識到每場對話都帶來接近無限的選擇機會,人們將因此更貼近彼此,或是漸行漸遠。當我們學會辨識那些機會,將開始以新的方式開口與聆聽。
【內文試閱二】
第1章 匹配原則──為何招不到間諜
吉姆.勞勒(Jim Lawler)要是對自己誠實,他會承認自己毫無吸收間諜的能力。事實上,他度過的多數夜晚都在煩惱,這輩子做過的各種工作中,找人當間諜是他唯一喜歡的,但看來他就要被炒魷魚了。勞勒在兩年前得到這份工作,進入美國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Agency, CIA)當招募員。
時間回到一九八二年,當時勞勒三十歲。他在加入CIA前,畢業於德州大學法學院,成績平平,接著輾轉於一連串無聊透頂的工作。有一天,不確定人生要幹什麼的他,打電話給在校園碰到的CIA獵頭雇員。接下來,他接受面試、測謊,又在數個城市參加了十幾場面試,接著是一系列的考試。考題感覺上是在找碴,專問一些勞勒不知道的事情(勞勒真的想不通,到底有誰會背下一九六○年代的橄欖球世界冠軍?)。
勞勒終究闖進了最後一關的面試,但感覺不太可能會錄取。他的考試表現介於差勁和平庸之間。此外,他沒有海外生活的經驗,不會說外語,沒有軍隊的經驗,也沒有特殊技能。不過,面試官注意到勞勒為了參加這次面試,千里迢迢自費飛到華盛頓特區,而且堅持完成每一場考試,即便大部分問題的答案,他顯然毫無頭緒。勞勒以令人欽佩的正面精神回應每一次的挫敗,甚至有過度樂觀之嫌。
面試官問勞勒,他到底為什麼這麼想加入CIA?
勞勒回答:「我這輩子一直想做重要的事。」他想要報效母國,「把民主帶給渴望自由的國家。」話一說出口,勞勒自己都知道很好笑。有誰會在面試時談什麼渴望?所以勞勒停下來,深呼吸,說出當下能想到最誠實的答案:「我感到人生很空虛。」勞勒告訴面試官:「我想參與有意義的事。」
一星期後,CIA打電話通知他錄取了。勞勒立刻接受,到培里營(Camp Peary)報到──培里營俗稱「農場」(the Farm),是CIA在維吉尼亞州的訓練場地。勞勒在那裡學習開鎖、傳遞情報與跟蹤監視。
不過,農場課程最出乎意料的一面是CIA極其重視對話技巧。勞勒在受訓期間得知,在CIA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溝通。外勤人員的任務不是潛伏在暗處,也不是在停車場竊竊私語,而是在派對上找人聊天,在大使館交朋友,和外交官打成一片,希望有一天能悄悄得知關鍵情報。溝通萬分重要,CIA訓練法的摘要開門見山地指示:「找出辦法連結。」上頭寫著:「CIA招募員的目標是讓間諜人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招募員是少數真正懂他的人,甚至是世上唯一的知己。」
勞勒從間諜學校高分結業,派駐歐洲。他的任務是結交外國官員,和大使館人員培養友誼,並開發各式各樣的人脈。或許有人會願意敞開心扉和他聊一聊—他的上司希望能因此開啟討論的管道,讓全球事務變得更可控一些。•••
勞勒在海外的頭幾個月過得慘兮兮。他盡了最大的努力融入當地生活,參加必須穿著禮服的晚宴,還在大使館附近的酒吧灌酒,但不管怎麼做都沒用。有一次,勞勒在滑完雪的社交活動中,認識一名中國代表團的職員,沒事就相邀吃午餐和喝雞尾酒。勞勒最後鼓起勇氣問這位新朋友,或許他願意賺點零用錢,只要傳遞在大使館聽到的小道消息就可以了。然而,那個人告訴勞勒,自己的家族財力雄厚,謝謝他的邀請,但上頭一般會處決幹這種事的人,所以還是算了吧。
還有一次,一名蘇聯領事館的接待人員看起來可能答應,直到上司把勞勒拉到一旁解釋,那其實是蘇聯情報機構KGB的人。她也在試圖吸收他。
最後,終於出現能拯救勞勒事業的機會:CIA的同事提到,在某中東國家外交部工作的年輕女性茉莉(Yasmin),最近會來到他們這裡。同事解釋,茉莉是來休假的,住在移居歐洲的哥哥家。幾天後,勞勒設法在餐廳「不小心撞到」茉莉。勞勒自稱是石油商人,兩人聊起天。茉莉好像有點寂寞,提到哥哥總是很忙,永遠沒空陪她觀光。
勞勒邀請茉莉隔天共進午餐,詢問她的生活。她喜歡她的工作嗎?住在近期剛發生保守革命的國家難不難?茉莉坦承她痛恨上台的宗教激進分子,渴望移居國外,住在巴黎或紐約,但這種事要有錢才能辦到。光是這次的短期停留,就花掉她好幾個月的積蓄。
勞勒感到這是個機會。他告訴茉莉,他的石油公司正好需要顧問。那是一份兼差工作,可以和茉莉在外交部的正職同時做,但他還是會提供簽約獎金。「我們點了香檳慶祝,茉莉差點喜極而泣,她好開心。」勞勒告訴我。
午餐過後,勞勒衝回辦公室找上司。他終於網羅到第一名間諜!「結果長官告訴我:『恭喜。總部會欣喜若狂。現在你需要告訴她,你是CIA探員,你想取得她的政府的資訊。』」勞勒覺得這樣不大好,如果誠實以告,茉莉大概再也不會理他了。
然而,長官解釋不明講是替CIA工作,對她並不公平。萬一哪天茉莉被政府抓到,她會入獄,甚至被處死。她需要瞭解風險所在。
勞勒於是繼續和茉莉見面,試著找到正確時機,說出自己真正的後台。隨著兩人相處的時間愈來愈多,茉莉講話愈來愈沒防備。她告訴勞勒,她恥於自己的政府關閉報社,禁止自由言論。此外,她也厭惡官僚下令讓女性在大學研究某些主題變成違法行為,還強迫女性在公共場所佩戴頭巾。茉莉說她最初在政府單位找工作時,從沒想到情況會惡化至此。
勞勒認為這是好兆頭。某天晚餐時,他解釋自己其實不是什麼石油商人,而是美國的情報人員。勞勒告訴茉莉,她想要的東西跟美國一樣:他們都想推翻她的國家的神權政治,打擊神權領袖的勢力,終止對女性的壓迫。勞勒說對不起,他對自己的身分說謊了,但工作機會是真的。她願不願意考慮替美國的中情局工作?
「我邊說邊看到茉莉的眼睛愈瞪愈大。她抓緊桌布,瘋狂搖頭,喃喃自語著:『不,不,不。』等我講到一個段落,她便開始哭。我知道我搞砸了。」勞勒告訴我:「她說政府會為了這種事殺人,她不可能協助我。」任憑勞勒說破了嘴,茉莉依然不肯考慮他的提議,「她只想快點遠離我。」
勞勒向上級報告壞消息。「我的上司說:『我已經告訴每個人你招募到她了!我告訴了處長,還告訴了站長,他們又回報給華盛頓特區了。然後你現在要我告訴他們,你沒搞定?』」
接下來該怎麼辦,勞勒毫無頭緒。「不論我提議給多少錢,提供多少承諾,茉莉都不肯冒可能害死自己的風險。」勞勒告訴我。唯一可能繼續推動這件事的辦法,就是說服茉莉相信他。他懂她,會保護她。然而,要如何辦到?「他們在農場教我,要想招到人,得讓對方相信你在乎他們。也就是說,你得真正在乎他們。換句話說,你得以某種方式連結,但我根本不曉得如何才能辦到。」
•••
我們如何與另一個人建立真正的連結?如何透過對話,鼓勵某個人去做有風險的事、踏上冒險旅程、接受某份工作,或是出門約會?
讓我們把難度降低一點:假設你試著和上司打好關係,或是想認識某位新朋友:你要如何讓他們放下戒心?如何證明你在認真聽他們說話?
過去數十年間,隨著研究人類行為與大腦的新方法紛紛出爐,這一類的問題促使研究人員幾乎檢視了溝通的每一個面向。科學家仔細觀察我們的大腦如何吸收資訊,最後發現,透過言論跟他人連結的影響力與複雜度,遠超過以往的想像。我們如何溝通──說話與聆聽時不知不覺做出的決定、問的問題、暴露的軟肋,甚至是語氣,全部會影響我們將信任誰、誰能說服我們,以及我們會找誰當朋友。
除了這方面的全新認識,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研究也顯示,每場對話的核心是潛在的神經同步(neurological synchronization),也就是從每個人的呼吸速度到起雞皮疙瘩,大腦與身體會趨於一致──我們通常不會發現這件事,但這會影響我們如何說話、聆聽與思考。有的人持續未能與他人同步,即便和走得近的朋友聊天也辦不到。有些人似乎毫不費力就能與任何人同步──這樣的人姑且稱作超級溝通者(supercommunicator)吧。大部分的人則落在光譜的中間。然而,如果我們理解對話的機制,就能學著以更有意義的方式連結。
不過,道理懂歸懂,勞勒還是感到茫然,看不出如何和茉莉建立連結。「我知道頂多還有一次跟她說話的機會。」勞勒告訴我:「我得想辦法突破。」
大腦的連結時刻
波.席佛斯(Beau Sievers)在二○一二年加入達特茅斯社會系統實驗室(Dartmouth SocialSystems Lab),一身打扮就像幾年前還在擔任樂手的時期。他有時會頂著金色爆炸頭,套著某次爵士節的破爛T恤,一醒來就衝向實驗室。校警不確定剛跑過去的人到底是博士候選人,還是戕害大學生的大麻販子。
席佛斯繞了一大圈,才進入常春藤名校。他大學原本讀的是音樂學院,研究擊鼓與音樂製作,幾乎不問世事。然而沒多久,他就在想,不論再怎麼瘋狂練習,也很難成為萬中選一的幸運兒,「只靠打鼓養活自己。」他因此開始探索其他職涯。席佛斯向來對人們如何溝通極感興趣,尤其喜愛舞台上不時發生的無聲音樂對話。他和其他樂手即興演出時,有時候突然間所有人彷彿融為一體,共用一個大腦。表演者,以及聽眾、調音師,甚至是酒保,突然間就同步了。席佛斯有時也會在深夜聊得很愉快,或是在約會很成功時,出現相同的感受。他因此上了幾堂心理學的課,最後申請到魏特利博士(Thalia Wheatley)的博士班。魏特利博士是最頂尖的神經科學家之一,專門研究人類如何相互連結。
魏特利在期刊《社會與人格心理學指南》(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中寫道:「為什麼人會和某些人『一見如故』,跟其他人卻不會,這是科學上未解的重大謎題。」魏特利解釋,和某個人聊得來的感覺會很美好的部分原因,在於人腦演化成渴望那種連結。想要連結的欲望,促使人們組成社群、保護後代、尋求新朋友與盟友。這是我們這個物種得以生存的原因。「人類擁有罕見的能力。」魏特利寫道:「有辦法在重重阻礙下依舊彼此連結。」
無數的其他研究人員,也對我們如何形成連結深感興趣。席佛斯閱讀科學期刊後發現,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學者在二○一二年,研究過吉他手演奏音樂家沙伊德勒(C. G. Scheidler)D大調奏鳴曲時的大腦。當吉他手各自彈奏,專注於自己的樂譜,他們的神經活動看起來不太一樣。然而,等進入二重奏,顱內的電脈衝會開始同步。在研究人員眼中,這有如吉他手的大腦合而為一。此外,那個連結通常會流過他們的身體:吉他手往往開始以相同的速率呼吸,眼睛同時瞪大,心臟也出現相似的跳動模式。就連他們皮膚上的電脈衝通常也會同步。接下來,等他們不再彈奏同一個段落──譜子開始不一樣,或是轉為獨奏,「腦間的同步化就完全消失。」科學家寫道。
席佛斯發現其他研究也顯示,當人們一起哼歌、肩並肩在桌上敲打手指、合作解謎,或是為彼此講故事,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普林斯頓的研究人員進行測試神經活動的實驗。十二名受試者聆聽一名年輕女性講述在畢業舞會當天,一則峰迴路轉的故事。研究人員同時觀測說話者與聆聽者的大腦,發現聽話者的大腦開始與敘事者同步,直到所有人感受到相同的壓力、不安、開心、幽默等情緒,就好像大家在一起說故事。此外,有的聆聽者與說話者特別同步;大腦看起來跟她幾乎一模一樣。事後被問到時,那些步調特別相近的受試者,更能清楚分辨故事中的人物並回憶小細節。人們的大腦愈是同步,愈能理解說話內容。研究人員在二○一○年的《國家科學院院刊》(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寫道:「說者與聽者的神經耦合(speaker-listener neural coupling)程度,能夠預測溝通的成功度。」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