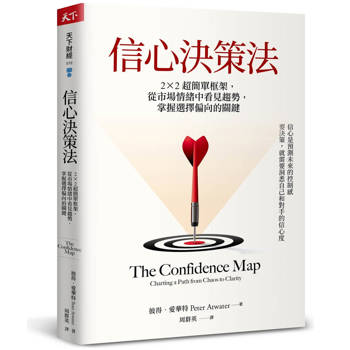每個工作日下午股市收盤後,財經媒體記者投入工作,尋找當天的重要新聞故事,採訪專業投資人。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寫出清晰、有說服力的故事,解釋為什麼股市會上漲、下跌或只是盤整。
大選之夜投票剛結束後,政治記者也會做一樣的事情。他們整合選民資訊、投票率和熱門議題,來解釋當晚的勝利與失敗。
當大事發生,我們都想知道原因。新聞報導以及我們分享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原因。記者把看似隨機且令人不安的事件,組織成有邏輯的時間線。他們判斷是哪些決定因素,導致了特定結果。
逆向回溯一系列行動和先前事件時,我們很容易確認哪些是決定因素。對於過去和已經發生的事情,因果之間的關係很容易梳理。
但是在思考未來時,情況就變得很有挑戰性。我們不僅難以準確預測未來,而且似乎對那些事後很容易發現的決定性因素視而不見。
然而,如果有一個框架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預測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而無須等待後見之明呢?如果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前出現的決定因素,將影響我們的未來偏好、決定和行動呢?
這個框架就是本書的主題。你看,我相信的確有一個決定性因素,在支撐我們所做和將要做的重要選擇。那就是:
信心。
重新定義信心
大多數人想到信心時,真正談的其實是自尊(self-esteem),也就是我們對自己的感覺。自尊的重點是自己的內在,關於這個主題有很多心靈成長書籍,可以幫助我們更懂得欣賞自己的能力。但那不是這本書的主題。
這本書也不是要談「信心表演」(confidence theater),那只是信心的表象(appearance),卻主導了企業界甚至更廣泛的文化。講到「信心」,聽眾很快就會想到「詹皇」詹姆斯(LeBron James)、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碧昂絲(Beyoncé)等無數名人,他們公開的言行,反映出我們的文化如何看待與信心相關的特質。我們認為,充滿信心與獲得成功的意義,就是要像他們那樣言行。
信心表演吸引了人們很多關注,但就像我們不斷在體育、政治、商業領域,或許還有在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看到的,信心和成功並不總是一致。有時候,自信是我們在獲得很高的成就時,不得不戴上的一張面具,但同時內心卻在和「冒牌者症候群」奮戰。也有另一些人,認為自己必須「弄假直到成真」,他們戴上信心滿懷的假面,相信總有一天它會內化成為真正的自己。諷刺的是,在無情的社群媒體,和不斷取得更大成功的壓力之間,許多渴望或已經站上巔峰的人,感覺暴露無遺又脆弱不堪。對這些人來說,「充滿信心」是他們最不可能用來形容自己的詞。
然而,這本書談的是信心本身——是真正的信心。我將要深入探討我們生活裡的一個重要面向,然而它的定義是我們常常無法用言語來具體描述的。此外,這個議題還包括,為什麼有沒有信心,對於我們的感受、我們思考的內容和方式,以及我們的行為,如此重要。這本書要談的,是信心在我們的決策裡扮演的角色。
真正的信心,與高自尊和出色的成就完全不一樣,也和我們如何讓自己看起來很成功不一樣。真正的信心,是我們內在自然的晴雨表,反映了我們的感受:對於即將發生什麼事情,以及對於我們認為自己能夠多成功地處理這些事情。我們對未來的感覺,和我們對想像中未來準備度的感覺,兩者綜合起來就是信心。就像新冠疫情以及近來的地緣政治事件所示,我們可以擁有如搖滾明星般的強大自尊,但同時信心卻被動搖。
雖然我們談到信心時,使用的是現在時態,例如「我有信心」,但我們談的其實都是未來。我們是在預測某個結果,然後判斷成功實現那個結果的可能性。例如,「我現在有信心,因為我相信我明天可以加入棒球隊。」信心在本質上具有前瞻性,那是我們對自身期待的總結評估。我們可能會試著活在當下,但我們此時此刻的感受,與我們想像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大有關係。簡言之,當我們認為自己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情,並且已經為此做好準備時,我們會覺得有信心——因為我們能看到成功就在眼前。
這個道理看起來似乎很簡單,而且再清楚不過,但其實有幾個重要的細微之處值得探討。
首先,信心是一種感覺。信心也許和我們的五感無關,但我們會本能地把它歸類成「感知」(perception)的一種。我們的信心水準如果發生變化,會帶來接近感官的反應:我們會在胃部感覺到它,會從喉嚨的深處嚐到它的味道。
其次,我們用來確定信心水準的評估流程,目前還不是很精準。雖然我們可以像陪審團一樣蒐集證據,但我們也會決定哪些事實才要認真考慮,而且這些決定常常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衡量自己的信心水準時,不會有檢察官或辯護律師,強迫我們思考正反兩方的論點。昨天練球時,我們可能每一顆球都打中了,但是如果腦海裡回想的都是上週比賽被三振的慘狀,那麼昨天打得多好還重要嗎?我們呈現和評估事實的過程,是高度主觀和個人化的。其他人可能會鼓勵我們保持信心,但最後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是否要保持信心。
我們評估的過程,也有自我反映和自我強化的現象。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評估信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信心水準。我們愈有信心,就會愈樂觀,也愈不願意去尋找或相信相反的論點。於是,我們會把自己的觀點,局限在能夠證實自己信念的證據上。
相反,當信心不足時,我們就會想太多。我們會認為,如果一件事出錯,其他事情也可能出錯。於是,我們開始找問題,想像出一長串其他可能出錯的方式。我們審視事情的仔細程度,和我們的信心水準成反比。
我們的信心水準也會起起伏伏。我們沒有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信心。當我們說自己對某件事有信心時,我們無法把這種感覺轉換成華氏度數,或用芮氏地震規模來精確測量。我們只能用個人的尺度,而且,就像股市的牛市和熊市一樣,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信心是非常主觀的東西。
大選之夜投票剛結束後,政治記者也會做一樣的事情。他們整合選民資訊、投票率和熱門議題,來解釋當晚的勝利與失敗。
當大事發生,我們都想知道原因。新聞報導以及我們分享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原因。記者把看似隨機且令人不安的事件,組織成有邏輯的時間線。他們判斷是哪些決定因素,導致了特定結果。
逆向回溯一系列行動和先前事件時,我們很容易確認哪些是決定因素。對於過去和已經發生的事情,因果之間的關係很容易梳理。
但是在思考未來時,情況就變得很有挑戰性。我們不僅難以準確預測未來,而且似乎對那些事後很容易發現的決定性因素視而不見。
然而,如果有一個框架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預測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而無須等待後見之明呢?如果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前出現的決定因素,將影響我們的未來偏好、決定和行動呢?
這個框架就是本書的主題。你看,我相信的確有一個決定性因素,在支撐我們所做和將要做的重要選擇。那就是:
信心。
重新定義信心
大多數人想到信心時,真正談的其實是自尊(self-esteem),也就是我們對自己的感覺。自尊的重點是自己的內在,關於這個主題有很多心靈成長書籍,可以幫助我們更懂得欣賞自己的能力。但那不是這本書的主題。
這本書也不是要談「信心表演」(confidence theater),那只是信心的表象(appearance),卻主導了企業界甚至更廣泛的文化。講到「信心」,聽眾很快就會想到「詹皇」詹姆斯(LeBron James)、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碧昂絲(Beyoncé)等無數名人,他們公開的言行,反映出我們的文化如何看待與信心相關的特質。我們認為,充滿信心與獲得成功的意義,就是要像他們那樣言行。
信心表演吸引了人們很多關注,但就像我們不斷在體育、政治、商業領域,或許還有在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看到的,信心和成功並不總是一致。有時候,自信是我們在獲得很高的成就時,不得不戴上的一張面具,但同時內心卻在和「冒牌者症候群」奮戰。也有另一些人,認為自己必須「弄假直到成真」,他們戴上信心滿懷的假面,相信總有一天它會內化成為真正的自己。諷刺的是,在無情的社群媒體,和不斷取得更大成功的壓力之間,許多渴望或已經站上巔峰的人,感覺暴露無遺又脆弱不堪。對這些人來說,「充滿信心」是他們最不可能用來形容自己的詞。
然而,這本書談的是信心本身——是真正的信心。我將要深入探討我們生活裡的一個重要面向,然而它的定義是我們常常無法用言語來具體描述的。此外,這個議題還包括,為什麼有沒有信心,對於我們的感受、我們思考的內容和方式,以及我們的行為,如此重要。這本書要談的,是信心在我們的決策裡扮演的角色。
真正的信心,與高自尊和出色的成就完全不一樣,也和我們如何讓自己看起來很成功不一樣。真正的信心,是我們內在自然的晴雨表,反映了我們的感受:對於即將發生什麼事情,以及對於我們認為自己能夠多成功地處理這些事情。我們對未來的感覺,和我們對想像中未來準備度的感覺,兩者綜合起來就是信心。就像新冠疫情以及近來的地緣政治事件所示,我們可以擁有如搖滾明星般的強大自尊,但同時信心卻被動搖。
雖然我們談到信心時,使用的是現在時態,例如「我有信心」,但我們談的其實都是未來。我們是在預測某個結果,然後判斷成功實現那個結果的可能性。例如,「我現在有信心,因為我相信我明天可以加入棒球隊。」信心在本質上具有前瞻性,那是我們對自身期待的總結評估。我們可能會試著活在當下,但我們此時此刻的感受,與我們想像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大有關係。簡言之,當我們認為自己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情,並且已經為此做好準備時,我們會覺得有信心——因為我們能看到成功就在眼前。
這個道理看起來似乎很簡單,而且再清楚不過,但其實有幾個重要的細微之處值得探討。
首先,信心是一種感覺。信心也許和我們的五感無關,但我們會本能地把它歸類成「感知」(perception)的一種。我們的信心水準如果發生變化,會帶來接近感官的反應:我們會在胃部感覺到它,會從喉嚨的深處嚐到它的味道。
其次,我們用來確定信心水準的評估流程,目前還不是很精準。雖然我們可以像陪審團一樣蒐集證據,但我們也會決定哪些事實才要認真考慮,而且這些決定常常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衡量自己的信心水準時,不會有檢察官或辯護律師,強迫我們思考正反兩方的論點。昨天練球時,我們可能每一顆球都打中了,但是如果腦海裡回想的都是上週比賽被三振的慘狀,那麼昨天打得多好還重要嗎?我們呈現和評估事實的過程,是高度主觀和個人化的。其他人可能會鼓勵我們保持信心,但最後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是否要保持信心。
我們評估的過程,也有自我反映和自我強化的現象。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評估信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信心水準。我們愈有信心,就會愈樂觀,也愈不願意去尋找或相信相反的論點。於是,我們會把自己的觀點,局限在能夠證實自己信念的證據上。
相反,當信心不足時,我們就會想太多。我們會認為,如果一件事出錯,其他事情也可能出錯。於是,我們開始找問題,想像出一長串其他可能出錯的方式。我們審視事情的仔細程度,和我們的信心水準成反比。
我們的信心水準也會起起伏伏。我們沒有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信心。當我們說自己對某件事有信心時,我們無法把這種感覺轉換成華氏度數,或用芮氏地震規模來精確測量。我們只能用個人的尺度,而且,就像股市的牛市和熊市一樣,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信心是非常主觀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