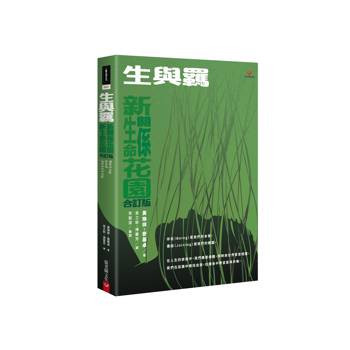【內文試閱】
多年來,我們投入一起自我探索的計畫。在七○年代的探索精神中,我們一致同意要一起探索什麼是真正的親密。我們所謂的「親密」(intimacy)是指彼此深入了解對方,互相坦露自己;這個字的拉丁文來源是 intimus,意指「內部」。打從一開始,我們就像兩個有興趣探索的科學家,盡其所能投入這個研究。我們的基本規則很簡單,但很嚴格,就是互相同意向對方打開內心世
界,意思就是其中一人可以詢問:「你正在想什麼?」另一人同意就自己當時所知,盡可能地回答。但我們有一項保留條款,可以回答「我選擇不告訴你」。當煥祥嚴守口風,不讓基卓事先知道生日禮物是什麼的時候,就幽默地顯明這個條款的重要了;因為嚴格要求說出一切,就會破壞拿到禮物時的驚喜。所以誠實地坦露自己也包括可以坦率地有所保留。
同樣地,我們同意盡可能自發地互相分享自己的感受、知覺和評斷,所以不需要提出詢問,各人的責任就是願意提供這些資訊,好讓對方能加入自己的世界。一開始,基卓並不擅於此道,他做好心理準備,願意提供純然的事實,可是他不了解煥祥要的是細節!於是,我們開始分辨真實卻冷冰冰的摘要報告和具體的坦露有何不同,我們想要分享,為的是更深入經驗:包括每一刻的思緒、感受、知覺和印象。身為訓練精良的科學家,我們需要使勁掙扎,努力進到更深處,進入活生生的個人存在層面。我們從報告的客觀世界轉進不同的領域,需要發展自己的語言和溝通方式,才能分享生活中感受到的經驗。
我們在這項計畫中磨合、發展出「溝通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基本規則雖然簡單,卻非常嚴格,我們會在本書與其他地方加以探討。欺騙是親密的敵人,基卓發現自己是個騙子,他並非刻意如此,而是因為一輩子都嘗試以最適當的表現贏得別人的鍾愛和肯定。我們過去並沒有練習自我坦露,而是遵循欺騙、隱瞞、大事化小、轉移話題的方式;換句話說,我們發現自己採用的是社會既定的各種方式,卻妨礙坦誠的溝通。「溝通模式」幫助我們以耐心通過這道障礙。
我們從一開始就抱持一項重要的態度:沒有真理,也沒有客觀的真實。我們各有自己的經驗,這個經驗受自己過往時光、既有成見的汙染,除此之外沒有「真理」。所以我們可以不從對錯的角度分享自己的觀點,這有助於我們在關係的發展中,不以指責的方式對待彼此,各人完全為自己負責。由於沒有人是對或錯,我們就只是分享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任何情況中都不需要決定誰是「正確」的。所以,我們避免了大多數人身陷其中的規範結構。
一開始,我們各有自己的婚姻,兩人是社交關係,都對心理方面有學術興趣。我們發現共處的時光非常刺激、興奮。基卓學完針灸從英國返回後,在煥祥隔壁開業,兩人共用一間候診室。我們每天見面討論看病人的經驗(沒錯,他們在那個時代被稱為「病人」,我們當時尚未跳脫治療師和病人的醫學模式),討論自己如何處理病人、什麼方式對病人最有效。當然,我們是以心理學的角度處理病人,都相信人只有改變態度和生活方式才能改變人生,即使病人的問題是身體上的不適,我們最大的興趣仍然在於他們如何與自己的世界建立關係。探索的媒介往往是我們與他們之間建立的關係,許多人都敞開地分享生活中的親密與痛苦,也就是在治療關係中向我們敞開。
討論病人的臨床問題時,我們的興趣都在於如何與病人有更深的接觸;我們和他們的接觸愈有意義,他們就愈能得到扎實的收穫,進而處理生活的問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愈了解他們,他們就愈了解自己,能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自己的生活,進而促進療癒。所以,我們想知道,有什麼東西會妨礙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他們。
其中一個障礙就是我們被訓練出來的專業距離。病人向我們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問題是被接受的,但我們卻被教導要與他們保持客觀的距離,這種方式顯然使我們無法全然投入治療。於是在時代精神的影響下,我們決定嘗試敞開自己,更以「人」的方式陪伴案主(當我們敞開自己願意分享時,「病人」就成為「人」而不是「物」,所以現在改稱「案主」而不是「病人」)。可是我們發現自己會有防衛,以自己的偏見限制案主,還有認為事情「應該」如何的僵化態度,而不是單純地欣賞他們。
我們在一起討論「案主」的晨間會議中,開始注意自己身為人的限制如何局限了我們與他們的關係,我們想要找出自己的心牆和防衛,克服我們與人保持距離的習性,好讓療癒的過程更深化。我們決定在這種精神下,探索自己如何設下障礙,與對方保持距離。簡言之,我們決定看看彼此能親近到什麼程 度,並解決每一個妨礙親近的心理防衛作用。
我們開始談論自己的感受以及對彼此的感受,這才發現我們多麼不敢也不擅於把感受化為言詞。我們能自在地在餐廳搶著付帳,或互相讚美對方,作為關心、喜歡對方的表現,卻很難直接說:「我喜歡你這一點。」更困難的是直接說出負面的話,但負面部分是必然會浮現的。我們過於客氣,無法說:「我不喜歡你這一點。」我們了解要使親密愈來愈深入,就必須說出正面和負面的感受。付諸實行後,我們的晨間會議出現重大的突破,沒多久就不再多談案主的情形,而愈來愈常討論對彼此和對自己的感受。這個歷程需要耗費更多時間,我們為了這個「歷程」,開始提早一小時到辦公室,然後是一個半小時,接著是兩小時。每天工作結束時,也會討論當天的想法和感受,以保持密切聯繫。每天晚上又再花一小時打電話分享。我們愈熟悉彼此,就愈了解自己,以及兩人共有的歷程。每當我們在晨間會議有什麼新的發現,接著就會驚訝地看見同樣的問題出現在當天許多案主身上,好像我們必須先面對自己的問題和自身的關係問題,才看得見別人身上的相同問題。於是我們開始建立理論:專業人員只能陪伴案主走到專業人員本身準備好要去的地方。
案主非常著迷,可能也有一點吃驚,他們開始把會談中學習的人際技巧應用到家人和朋友身上。我們發現他們提早抵達診所,和我們的祕書聊天(她也參與這種方式的人際溝通),案主間開始互相談話,在候診室發展友誼!由於我們的案主包括非常不同類型的人,因此產生一些有趣的動力。煥祥的案主大部分是青少年,他們要處理的是人生方向和親子、學校問題;基卓的案主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們為了西方醫學無法處理的慢性疼痛和特殊疾病而接受針灸治療。候診室成了這兩群人的熔爐,他們真心欣賞彼此,從相互的關係中學習。矮小的老太太帶餅乾給小太保吃;我們一直不確定年輕人帶了什麼玩意兒回報老人家!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發現這些人對彼此愈來愈感興趣,對「醫生」反而漸漸失去興趣。他們甚至互邀對方在自己的約診時間前來,在會談中愈來愈對自己負責。一天的工作結束時,辦公室常常聚集了好幾個人,他們是在會談後自動留下來的。於是我們有了團體溝通的歷程,案主的問題則日漸改善!
接下來我們開始到鄉間帶領短期的住宿體驗學習團體,這些工作全部用團體方式進行。我們在候診室和辦公室的經驗中,已看見團體工作的效果。大家在團體中的收穫使我們感到振奮,如此豐碩的成果遠超過個別諮商的有限工作。團體歷程有助於避免卡爾.華特克(Carl Whitaker)針對個別心理治療所說的「情緒相姦」(emotional incest)。我們開始夢想擁有一座農場或鄉間場所,成為大型的候診室,讓眾人同聚一處、彼此相會、互相了解、幫助對方得到療癒。
接下來,我們開始同住一處,除了專業的工作時間,還能共享私人時光。當時,我們各自和妻子分居,兩人的兒子都和母親同住,所以我們都是自由 的,於是兩個單身漢決定同住。處理家務時,我們讓每一件事都成為學習的機會,沒有任何事是微不足道而不需要探索的。禪的傳統中,每一分鐘都是永恆,每一個小動作都包含整個宇宙。我們會為最微小的細節討論、檢視、爭辯,學習觀察共同洗碗時的優美和拙劣之處。一起用餐時,看我們如何在食物的選擇與料理中分擔工作,可說是充滿了美感。如果基卓為煥祥拿了一個他不需要的湯匙,就會因為缺乏「當下的同在」而產生一長串討論與探索。
簡言之,我們學習要在當下彼此同在,並在發現失去當下的同在時,願意承認。我們變得對彼此非常敏銳,失去這種敏感度時就加以承認。
雖然經歷這種實驗的是兩個男人,但我們把自己看成兩個想測定愛的狀態要素的人,一起探索親密關係。我們在共同生活、探索的過程中發現關係中的許多要素,也了解這些原則適用於任何關係。我們的課程教導大家認識這些要素,是任何長期或短期關係都會發生的共通歷程和議題,因此,人們可以與不認識的人在週末工作坊一起處理短期關係的相處模式。同樣地,共度多年時光的人就像剛開始互動的人一樣,也有相同的議題需要處理。
關係的性質也不重要。只要任何兩個人願意承諾對彼此誠實、好奇,就可以產生深入的親密關係。這個原則不但對同性與異性的伴侶非常重要,也適用於朋友、親子、手足與同事。
多年來,我們投入一起自我探索的計畫。在七○年代的探索精神中,我們一致同意要一起探索什麼是真正的親密。我們所謂的「親密」(intimacy)是指彼此深入了解對方,互相坦露自己;這個字的拉丁文來源是 intimus,意指「內部」。打從一開始,我們就像兩個有興趣探索的科學家,盡其所能投入這個研究。我們的基本規則很簡單,但很嚴格,就是互相同意向對方打開內心世
界,意思就是其中一人可以詢問:「你正在想什麼?」另一人同意就自己當時所知,盡可能地回答。但我們有一項保留條款,可以回答「我選擇不告訴你」。當煥祥嚴守口風,不讓基卓事先知道生日禮物是什麼的時候,就幽默地顯明這個條款的重要了;因為嚴格要求說出一切,就會破壞拿到禮物時的驚喜。所以誠實地坦露自己也包括可以坦率地有所保留。
同樣地,我們同意盡可能自發地互相分享自己的感受、知覺和評斷,所以不需要提出詢問,各人的責任就是願意提供這些資訊,好讓對方能加入自己的世界。一開始,基卓並不擅於此道,他做好心理準備,願意提供純然的事實,可是他不了解煥祥要的是細節!於是,我們開始分辨真實卻冷冰冰的摘要報告和具體的坦露有何不同,我們想要分享,為的是更深入經驗:包括每一刻的思緒、感受、知覺和印象。身為訓練精良的科學家,我們需要使勁掙扎,努力進到更深處,進入活生生的個人存在層面。我們從報告的客觀世界轉進不同的領域,需要發展自己的語言和溝通方式,才能分享生活中感受到的經驗。
我們在這項計畫中磨合、發展出「溝通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基本規則雖然簡單,卻非常嚴格,我們會在本書與其他地方加以探討。欺騙是親密的敵人,基卓發現自己是個騙子,他並非刻意如此,而是因為一輩子都嘗試以最適當的表現贏得別人的鍾愛和肯定。我們過去並沒有練習自我坦露,而是遵循欺騙、隱瞞、大事化小、轉移話題的方式;換句話說,我們發現自己採用的是社會既定的各種方式,卻妨礙坦誠的溝通。「溝通模式」幫助我們以耐心通過這道障礙。
我們從一開始就抱持一項重要的態度:沒有真理,也沒有客觀的真實。我們各有自己的經驗,這個經驗受自己過往時光、既有成見的汙染,除此之外沒有「真理」。所以我們可以不從對錯的角度分享自己的觀點,這有助於我們在關係的發展中,不以指責的方式對待彼此,各人完全為自己負責。由於沒有人是對或錯,我們就只是分享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任何情況中都不需要決定誰是「正確」的。所以,我們避免了大多數人身陷其中的規範結構。
一開始,我們各有自己的婚姻,兩人是社交關係,都對心理方面有學術興趣。我們發現共處的時光非常刺激、興奮。基卓學完針灸從英國返回後,在煥祥隔壁開業,兩人共用一間候診室。我們每天見面討論看病人的經驗(沒錯,他們在那個時代被稱為「病人」,我們當時尚未跳脫治療師和病人的醫學模式),討論自己如何處理病人、什麼方式對病人最有效。當然,我們是以心理學的角度處理病人,都相信人只有改變態度和生活方式才能改變人生,即使病人的問題是身體上的不適,我們最大的興趣仍然在於他們如何與自己的世界建立關係。探索的媒介往往是我們與他們之間建立的關係,許多人都敞開地分享生活中的親密與痛苦,也就是在治療關係中向我們敞開。
討論病人的臨床問題時,我們的興趣都在於如何與病人有更深的接觸;我們和他們的接觸愈有意義,他們就愈能得到扎實的收穫,進而處理生活的問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愈了解他們,他們就愈了解自己,能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自己的生活,進而促進療癒。所以,我們想知道,有什麼東西會妨礙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他們。
其中一個障礙就是我們被訓練出來的專業距離。病人向我們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問題是被接受的,但我們卻被教導要與他們保持客觀的距離,這種方式顯然使我們無法全然投入治療。於是在時代精神的影響下,我們決定嘗試敞開自己,更以「人」的方式陪伴案主(當我們敞開自己願意分享時,「病人」就成為「人」而不是「物」,所以現在改稱「案主」而不是「病人」)。可是我們發現自己會有防衛,以自己的偏見限制案主,還有認為事情「應該」如何的僵化態度,而不是單純地欣賞他們。
我們在一起討論「案主」的晨間會議中,開始注意自己身為人的限制如何局限了我們與他們的關係,我們想要找出自己的心牆和防衛,克服我們與人保持距離的習性,好讓療癒的過程更深化。我們決定在這種精神下,探索自己如何設下障礙,與對方保持距離。簡言之,我們決定看看彼此能親近到什麼程 度,並解決每一個妨礙親近的心理防衛作用。
我們開始談論自己的感受以及對彼此的感受,這才發現我們多麼不敢也不擅於把感受化為言詞。我們能自在地在餐廳搶著付帳,或互相讚美對方,作為關心、喜歡對方的表現,卻很難直接說:「我喜歡你這一點。」更困難的是直接說出負面的話,但負面部分是必然會浮現的。我們過於客氣,無法說:「我不喜歡你這一點。」我們了解要使親密愈來愈深入,就必須說出正面和負面的感受。付諸實行後,我們的晨間會議出現重大的突破,沒多久就不再多談案主的情形,而愈來愈常討論對彼此和對自己的感受。這個歷程需要耗費更多時間,我們為了這個「歷程」,開始提早一小時到辦公室,然後是一個半小時,接著是兩小時。每天工作結束時,也會討論當天的想法和感受,以保持密切聯繫。每天晚上又再花一小時打電話分享。我們愈熟悉彼此,就愈了解自己,以及兩人共有的歷程。每當我們在晨間會議有什麼新的發現,接著就會驚訝地看見同樣的問題出現在當天許多案主身上,好像我們必須先面對自己的問題和自身的關係問題,才看得見別人身上的相同問題。於是我們開始建立理論:專業人員只能陪伴案主走到專業人員本身準備好要去的地方。
案主非常著迷,可能也有一點吃驚,他們開始把會談中學習的人際技巧應用到家人和朋友身上。我們發現他們提早抵達診所,和我們的祕書聊天(她也參與這種方式的人際溝通),案主間開始互相談話,在候診室發展友誼!由於我們的案主包括非常不同類型的人,因此產生一些有趣的動力。煥祥的案主大部分是青少年,他們要處理的是人生方向和親子、學校問題;基卓的案主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們為了西方醫學無法處理的慢性疼痛和特殊疾病而接受針灸治療。候診室成了這兩群人的熔爐,他們真心欣賞彼此,從相互的關係中學習。矮小的老太太帶餅乾給小太保吃;我們一直不確定年輕人帶了什麼玩意兒回報老人家!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發現這些人對彼此愈來愈感興趣,對「醫生」反而漸漸失去興趣。他們甚至互邀對方在自己的約診時間前來,在會談中愈來愈對自己負責。一天的工作結束時,辦公室常常聚集了好幾個人,他們是在會談後自動留下來的。於是我們有了團體溝通的歷程,案主的問題則日漸改善!
接下來我們開始到鄉間帶領短期的住宿體驗學習團體,這些工作全部用團體方式進行。我們在候診室和辦公室的經驗中,已看見團體工作的效果。大家在團體中的收穫使我們感到振奮,如此豐碩的成果遠超過個別諮商的有限工作。團體歷程有助於避免卡爾.華特克(Carl Whitaker)針對個別心理治療所說的「情緒相姦」(emotional incest)。我們開始夢想擁有一座農場或鄉間場所,成為大型的候診室,讓眾人同聚一處、彼此相會、互相了解、幫助對方得到療癒。
接下來,我們開始同住一處,除了專業的工作時間,還能共享私人時光。當時,我們各自和妻子分居,兩人的兒子都和母親同住,所以我們都是自由 的,於是兩個單身漢決定同住。處理家務時,我們讓每一件事都成為學習的機會,沒有任何事是微不足道而不需要探索的。禪的傳統中,每一分鐘都是永恆,每一個小動作都包含整個宇宙。我們會為最微小的細節討論、檢視、爭辯,學習觀察共同洗碗時的優美和拙劣之處。一起用餐時,看我們如何在食物的選擇與料理中分擔工作,可說是充滿了美感。如果基卓為煥祥拿了一個他不需要的湯匙,就會因為缺乏「當下的同在」而產生一長串討論與探索。
簡言之,我們學習要在當下彼此同在,並在發現失去當下的同在時,願意承認。我們變得對彼此非常敏銳,失去這種敏感度時就加以承認。
雖然經歷這種實驗的是兩個男人,但我們把自己看成兩個想測定愛的狀態要素的人,一起探索親密關係。我們在共同生活、探索的過程中發現關係中的許多要素,也了解這些原則適用於任何關係。我們的課程教導大家認識這些要素,是任何長期或短期關係都會發生的共通歷程和議題,因此,人們可以與不認識的人在週末工作坊一起處理短期關係的相處模式。同樣地,共度多年時光的人就像剛開始互動的人一樣,也有相同的議題需要處理。
關係的性質也不重要。只要任何兩個人願意承諾對彼此誠實、好奇,就可以產生深入的親密關係。這個原則不但對同性與異性的伴侶非常重要,也適用於朋友、親子、手足與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