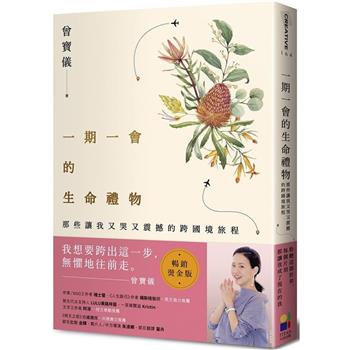【楔子】我想要跨出這一步,無懼地往前走
從沒想過,七年後的我,又站在阿姆斯特丹這座橋上。
一面看著橋下緩緩流過的水,一面看著七年前的自己。
二○一一年的我帶著爺爺去世的傷痛,宛如行屍走肉般行走於阿姆斯特丹的街頭。迎面而來的人們臉上總帶著愉悅,但我的心卻空空的。走著走著,我來到這座橋,被突如其來的悲傷淹沒,毫無防禦能力。
從那時候開始,我花了好多年時間思索生與死的議題。
七年後,二○一八年,我又為了生死議題來到同一個地方,但目的不同。
七年前是為了忘卻死亡的陰影,七年後則是為了直視死亡。
站在橋上,我再次想起爺爺。
我感謝他,感謝他的去世所帶給我的學習、體悟與成長,感謝他幫助我建立了信念,也由於這信念,它帶著我重回舊地,去記錄他人的故事。
這一路上,他未曾遠離。
站在橋上,看著七年前的自己,我多麼希望時空能重疊。
我想對七年前的自己說:
妳得到了一份意義十分深遠的禮物,不要逃避它。
打開它,好好地檢視它,欣然地接受它,並且感謝它。
它真的太棒了。
〈一份特別的工作邀約〉
二○一七年十月,騰訊新聞的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做個原定名稱叫《Tough Job》的節目(後來定名為《明天之前》),去體驗這世界最困難的工作。比方說捕鯨船的船員、西班牙鬥牛士,或是後來採訪成行的執行安樂死的死亡醫生、美國民兵……等等。
接到這個邀約,我心裡是很樂意、也很高興的。一是我認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二是沒想到先前我為了興趣而做的準備:學英文(我的上一本著作《50堂最療癒人心的說話練習》中敘述了原由),正好能派上用場。
簡單地說,由於主持東方衛視與Discovery頻道合作的《越野千里》節目,深覺我的口語英文實在不夠用,於是從二○一七年一月開始,我找了一位英文家教上英文課。剛開始上課時,我心中毫無負擔地跟英文家教用英文聊天,沒想到半年之後,有個需要全程用英文與受訪者與國外工作團隊溝通的工作找上我。
騰訊新聞的朋友說:節目預計從二○一八年春季開拍。我心想:還有大半年可以做準備嘛,儘管知道這工作並不容易,但我樂觀地認為「一定沒問題!」便欣然接下這項工作邀約……沒想到隨著開拍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給自己的壓力也一天比一天沉重,甚至焦慮到快要爆炸!
還記得,當合作拍板定案後,製作單位要我先選一、兩個主題做開拍前的準備。
我的首選是安樂死,這是由於爺爺過世之後,我花了很長時間在思考關於生死的問題。
當我去正視安樂死這主題時,是否能印證我這些時間的思考與學習有所成長?我到底走到何種境界與階段了?心中抱著期待與想望,知道機不可失,因此我毫不猶豫便先選了「死亡醫生」這個主題。
那麼第二個主題呢?除了前面提到的死亡醫生、美國民兵,或是捕鯨船與鬥牛士,其實當時還有一個選項叫做:墮胎船。由於我對性平議題很有興趣,加上我的英文家教剛好也很關注這類議題,於是我選了墮胎船為第二個主題,不過,後來這主題由於某些敏感因素而被排除掉了。
開拍前的準備有哪些?除了閱讀大量從網路上搜集來的新聞、個人背景等資料,受訪者所有的影片、書籍、身邊的相關人物,甚至是所有相同主題的影片,不管有沒有中文或英文字幕……一個都不能落下。我得做足功課,才能與製作單位討論採訪對象與主題的取捨。
〈聽見我的哭聲〉
《明天之前》這系列紀錄片的緣起,在於騰訊新聞想要做出具有國際觀的節目,他們想試著與國外的製作單位合作,看看在共事的撞擊下能產生何種火花,因此找上了曾經得過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的英國團隊GM,在確認雙方的合作共識後,再來徵詢我的主持意願。
騰訊這個對於做出好節目戰戰兢兢且頗具視野的製作團隊,早在二○一三年這團隊還在中央電視台時,我就與他們合作過一個叫《客從何處來》的尋根節目。
當時接到《客從何處來》的邀約我其實裹足不前。所謂尋根就是尋我父系與母系家族的根,這在我家族是件大事,得要與家人商量才行,並非我一人就能作主,我猶豫了好一段時間。
直到我意識到,節目其實是要用我個人的家庭史,去看整個宏觀的大歷史。
大歷史中有些無法言說的部分,若用個人家族的角度來談,或許能將歷史的全貌用一片片切面拼貼起來。
而在宏觀歷史的同時,也能回過頭來看我們當下的處境。有史為鑑,我們該如何面對現下的人生?又或者是,我們的社會是否能跟上世界的腳步,世界已經走到哪裡?世界到底在想什麼?如果有些議題能被討論,那麼所謂價值觀是否都並非牢不可破?
為了這些心中的重重疑問,我與這個製作團隊一同走上尋根之路。
「根」不能亂尋,製作團隊花了很多時間在我的父系與母系家族中找尋對象以及調查。歷史要回溯到多久之前?哪些親族仍健在?
我父系這條線,製作單位花了很多時間搜尋資料,可是最後找不下去只好停擺。而我母系這條線,外公是民國三十八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那段百萬人大遷徙的成員之一,家鄉在江蘇的他,有些故事能探尋,因此節目便以母系這條線為主。
外公祖上曾在清朝出過秀才,他繼承祖先的福蔭,成了家中以及村子裡少數能讀書、會識字的人,也因此十多歲時他在南京中央印製廠謀得一職,並且被廠長賞識而將他帶在身邊,國民政府撤退時,廠長便帶著外公一起逃難來台灣。
由於這段歷史,一開始節目安排我先去南京。得知原來當時外公有指腹為婚的對象(他們叫「娃娃親」),並且安排我們見面。不禁想,若外公未撤退來台灣,或許寶媽就不會出生,也就沒有我的存在了。
接著又去到了國民政府撤退的下關車站。外公是從下關車站坐火車去廣州,再從廣州輾轉來台灣。節目找了一位歷史學家在車站廢棄的月台上,講解外公逃難的路線,再拿當時月台的照片給我看。
當歷史學家講解到一半時,我心裡突然湧起一股強烈的情緒,我彷彿能感受到當時那些逃難者的心情,又彷彿聽到了當時月台的聲音,那種人聲雜沓、兵荒馬亂,好像聽到了逃難者心中沒有說出口的再見,以及永遠無法釋懷的遺憾。
我知道,有些再見,是再也不見。
由於節目正在錄影,在那當下我忍住即將潰決的情緒,一待學者說完,我便獨自往月台的最遠處走去。
我一邊走、一邊讓眼淚傾洩而出,盡情釋放情緒。沒料到的是,麥克風還別在我身上,導演聽到了我的哭泣聲,並且不斷捕捉我漸行漸遠的背影。
這段長達十多分鐘的真情流露,後來被收錄到節目中。
最後則去到外公的故鄉,江蘇北方的淮安。
節目安排我去拜訪外公的老家,見到了外公的弟妹,我喚她叫四外婆。儘管她的兒子在老家旁蓋了間大房子,其他子孫在當地也都是有影響力的人物,但四外婆依然守著那窄小的老房子,屋內只有一個電鍋、一只熱水瓶與老舊的收音機。
四外婆的鄉音我一個字也聽不懂,全程要由她兒子重述。她談到由於外公來台灣,他的特殊身分,讓整個家族遇上了危機,獨自保護一家老小的她在文革時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她當時靠著乞討養活我的外曾祖父、外曾祖母等一家老小,再加上還得獨自應付上門來找麻煩、不懷好意的盜賊與批鬥人士。
看著佝僂的四外婆雲淡風輕說著這些往事,我的眼前卻出現她當時沿街乞討的畫面,一個弱小的年輕女子,她瘦小的肩膀背負起一大家子的生計……我的眼淚再度止不住地往下掉,心中湧起對於她的愧疚。我顫抖著說:「對不起……」
四外婆拍拍我,說道:「妳不必在意,回去也不要跟家人說這些事。只要你們都過得好好的,就好了。」
當時我只能以大哭來回報四外婆的恩情。
我那曾經是秀才的祖先,讓家族成為地方的仕紳,受人敬重,但沒想到這留給子孫的庇蔭,會在戰亂時代讓家族成為盜匪覬覦的對象;但也因為仕紳背景,外公成為村子裡少數有教育基礎的年輕人,讓他逃難在外時,能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工作機會與賞識,於是他得到輾轉來台的機會。
外公來到台灣,帶給後代的我們新的開始與祝福,至於對遺留在家鄉的家人來說,這反而讓他們成為被批鬥的目標。
曾經的榮華,可能會帶來未知的危機;當下的苦難,卻又可能成為下一代的祝福。
《客從何處來》這個節目,透過一個個小家族的切面來看大時代的歷史,真正印證了禍福相倚與命運的弔詭—福蔭可能成為詛咒,危難也可能是機會。
由於這一趟尋根之旅,讓製作團隊見到了我的同理與共感能力,他們認為我跟其他主持人比起來「很特別」。
接下來,我與這個團隊又接連合作了《聽我說》(二○一六—二○一七年)與《回家的禮物》(二○一七—二○一九年),透過這兩個節目他們看到我的另一個可能性:面對陌生人的訪談能力。
而這多年累積下來的合作默契,讓他們在企劃《明天之前》這跨國大製作時,自然而然將我納入主持人選,並再次向我提出邀約,最後還說:「紀錄片共四集節目,妳就全包了吧。」
對於這項難得的挑戰,我躍躍欲試。
〈準備再準備〉
當我接到騰訊的主持邀請時,我心中很清楚:這個機會,在我生命中可能只會出現一次!我不能讓它溜走。這個節目,有可能成為我事業的代表作,我必須要完成它。我也知道,當我完成它時,我必定能脫胎換骨,人生再邁開更大一步。
更別說有人願意出資讓我思考我有興趣的議題,能與國外的優秀製作團隊合作,還能與每個議題相關的頂尖人士以及最有爭議的人面對面……種種誘因讓我知道:無論未來有多辛苦,都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難道當時我心中沒有一絲害怕?當然有。但我告訴自己:害怕不足以成為擋在我面前的石頭。絕對不可以。
我想要跨出這一步,無懼地往前走。
除了前面提到出發前需要大量閱覽資料、做足功課,對我來說,最擔心的就是「英文能力」。
出發前半年那段準備期,由於不停消化外文資料,腦袋不停進行Q&A的沙盤推演,大腦幾乎整天都在高速運轉,使得我的睡眠品質很差,有時連作夢都在說英文。
每個議題都是專業範疇,有許多專有名詞需要學習,除了要會讀它們,還得要用得正確,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考驗,比方說安樂死「Euthanasia」、永生「Immortality」……這些字,我反覆唸了千百次記住它們,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而在受訪對象一個個確認之後,我發現自己必須一坐下來,就要能跟一個陌生人聊他這輩子最傷痛、或是他已經研究了一輩子的事,這是另外一個困難點。
例如安樂死這個議題,幾乎每個受訪者的心中都有很深的傷,而我必須在沒有時間寒暄、互相熟悉的情況下,在短短一、兩個小時中切入受訪者的內心,這對我、對受訪者來說都是很大的壓力。
〈全程英文採訪的壓力〉
除此之外,還有口音這個關卡。
受訪者來自不同地區,澳洲、英國、愛爾蘭、美國東西岸、美墨邊境、英屬澤西島……更有受訪者是戴著呼吸器說英文、口音含糊不清的!再加上一起工作的英國團隊,導演是來自紐約的倫敦人,兩位攝影師中一位是有維京血統的北歐人、一位是敘利亞人,收音師是義大利人,整個工作團隊儼然是個小型聯合國。
製作單位投入了這麼多資源,我絕對不能搞砸,更不想丟亞洲人的臉,可想而知我想把英文說好的壓力有多大了。
這時我得要感謝老天爺給了我一個禮物:我的英文老師Joy。
當時我已與她上了半年多的課。Joy是多明尼加裔美國人,十多歲時從多明尼加共和國搬到美國亞歷桑那州鳳凰城讀高中與大學,二十多歲便來台灣工作,直到如今。
身為移民的她,對於生死、移民以及女性議題也十分有興趣,與我志趣相投。當她知道我接的新工作要討論這些主題,二話不說地願意助我一臂之力,更為我補充許多視野與背景(如美國非法移民與永生議題),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我真是太幸運了!
我與英文老師會先分頭看由紀錄片工作人員收集來的資料,再找時間一起腦力激盪。
當我們見面時,會以英文聊天的方式各自表達讀了資料後帶給自己的衝擊。我可能得用十句話來陳述一件事,但老師用兩句話就能充分說明,由此我便能得知用哪些英文字詞來表達會更恰當。
而討論的最後,我與老師會決定應該要問哪些問題:一個大問題之下圍繞著哪些小問題?問題的先後順序?要從個人經歷開始問還是從議題開始問?從哪個角度切入問題?……與英文老師這番沙盤推演,對於我日後的正式訪談,幫助極大。
〈出發前,我到底是誰?〉
離出發拍攝日二○一八年四月一天天逼近。
三月,我特地飛去北京與騰訊的團隊開會,臨出發前,北京、倫敦以及台北的我,三方再一起開了長達三、四小時的視訊會議。
此時一個個新的問題在我心中浮現:我在這個團隊中的定位是什麼?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記者還是主持人?是一名觀察者?一個好奇的民眾?我到底是誰?……
出發前,這些疑問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答。
以往在工作時,我總是會看著自己的表現,而這次,我意識到了另一雙看著我的眼睛:工作團隊對我的評價。
在不能丟臉、時刻意識到他人眼光的壓力下,我踏上這趟未先磨合的旅程,飛往阿姆斯特丹。
我決定帶著未知出發,不預設答案。
出發前,我也告訴自己:不要用個人的價值觀去評判別人的人生。
而這趟旅程的終末,原本也不該預設只能有一個解答。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