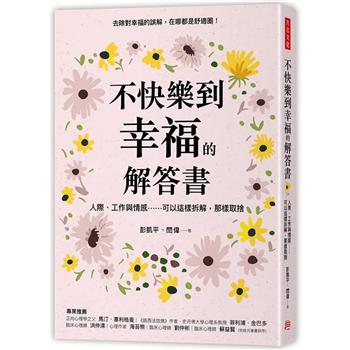正確的幸福,這樣比
康乃爾大學知名心理學家湯瑪仕.吉洛維奇(Gilovich Thomas)曾和兩位學生做了一項研究: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評價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各項比賽中,奪牌選手在透過終點時和在臺上受獎時的情緒表現,並給選手的表情打分數,滿分為10分,表情越開心分數越高。
結果發現,在比賽結果宣佈時,銀牌選手的平均分數只有4.8分,而銅牌選手的分數卻高達7.1分。在頒獎典禮上,銅牌選手的快樂表情有所收斂,但仍有5.7分,而銀牌選手則變得更不開心,表情變成了4.3分。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銅牌選手與銀牌選手的開心程度存在顯著差異。
▍為什麼銅牌比銀牌更快樂?
按照正常的理解,人們的開心程度應該與其成績有對應關係。如果我們表現得好、成績優異,我們會很開心;反之則不開心。依此邏輯,銀牌選手應該比銅牌選手開心才對,畢竟他的成績只是在一人之下,卻在眾人之上。
根據吉洛維奇的研究,產生這種意外結果的主要原因是這兩種人的反事實思考不一樣。所有人都在用反事實思考進行思考。反事實思考是個體基於與現實相反的條件或可能性進行推理的一種思考過程,或者是對事實的一種替換想像。人們通常是在心理上對已經發生過的事進行否定,進而建構一種假設的可能性,即「如果怎麼樣,就會怎麼樣」。
銀牌選手的反事實思考肯定是向上比較,因為對於銀牌選手而言,獎牌已經到手,他只要再努力一下,就一定可以獲得金牌,所以,向上比較的反事實思考很自然。銅牌選手則更可能有向下比較的反事實思考,因為他差一點就可能是第四名,得不到獎牌,因此,向下比較的反事實思考則更為自然。比較的方向不同,人的情緒受到的影響也就不同。
十幾年後,我的好朋友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大衛.松本教授(David Matsumoto)和美國《世界柔道雜誌》(The World of Judo Magazine)的編輯鮑伯.威林罕(Bob Willingham)對2004年在雅典奧運上獲得柔道金牌、銀牌和銅牌選手的臉部表情進行了電腦分析,分析結果再次驗證了吉洛維奇教授的發現。更有趣的是,銀牌選手不但表現得不開心,甚至還流露出悲傷、輕蔑和冷漠等負面的情緒。當然,這些銀牌選手在頒獎臺上還是會露出笑臉,只不過他們的微笑大部分是偽裝的、禮貌性的。
再舉一個中國游泳選手傅園慧的案例。在2016年的里約奧運上,傅園慧在發現自己奪得100公尺仰式銅牌後開心地說:「啊?第三啊?噢,那我覺得還是不錯的。」而當她在2017年的游泳世錦賽上獲得50公尺仰式銀牌後,她難過得眼淚都流了出來。由此可見,銀牌選手確實不如銅牌選手開心。
▍我就是會忍不住在意
上述研究生動地說明:一個人的成就、獲得和收益到底有多大,與其幸福程度不完全相關,而是和他的認識、判斷密切相關。當我們向上比較時,很難感受到自己已經獲得的成就,而當我們向下比較時,反而會知足常樂。這就意味著,真正影響人生的幸福和快樂的,是我們的預期和比較。
生活中,我們經常有與別人比較的衝動,我們感覺的好壞往往取決於比較的結果。當其他人聰明、靈活、成績好的時候,我們就顯得愚昧、笨拙、成績差。當你剛剛為了20萬元的年終獎金興高采烈,卻發現你的同事比你多拿兩萬元時,你可能就會變得不開心。
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那麼我們為什麼會有意無意地跟別人進行比較呢?
在進化史上,遠古人類為了規避風險、活得更久並成功繁衍,最重要的生存條件之一就是從屬於某一集體。他們透過不斷將自己和部族裡的其他人進行比較,保護自己不被集體排斥:我這樣做是否合適?我是否達到了別人的預期?我的貢獻夠大嗎?別人喜歡我嗎……直到今天,人類大腦依然沿用過往的模式,透過跟其他人比較來向自己發出受歡迎或被排斥的訊號。195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里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社會比較理論,他認為,自我認識的不確定性是人們進行社會比較的主要原因。每個人都有瞭解自我、評價自我的衝動,但在缺乏客觀標準的情況下,我們會把他人當作比較的尺度,在比較中獲得意義。另外,我們進行社會比較的對象不一定是那些比我們優越很多的人,往往還是自己身邊的人。也就是說,雖然某富豪可能會給自己定下一年賺1億的「小目標」,但我們不會和他比,但如果自己身邊的某個朋友比自己每個月多賺1萬元,我們便會感到不開心。
我們是如何進行社會比較的呢?社會比較可以細分為向上比較、平行比較和向下比較。向上比較,顧名思義,指的是在一個特定的指標上把自己與比自己強的人做比較,我們一般說的「比較」指的便是向上比較。在財富、成績、聲望上和那些比我們強的人比較,往往會傷害我們的自尊心,但也不排除對有些人來說,向上比較是激勵他們奮發向上、愈戰愈勇的動力。向下比較則是選擇不如自己的個體進行逆向比較,這樣通常會讓自己感覺更好。
由此會產生兩種效應,一種是對比效應。在現實中很多人有這樣的體會,當我們在職場上看到競爭者衣著光鮮、信心滿滿、侃侃而談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產生自卑情緒,降低對自己的評價。反之,當我們面對一個唯唯諾諾、不善言辭的競爭者時,我們便會不自覺地增強信心,提高對自己的評價。另外一種是同化效應。對於一些有上進心、有抱負的人,當向他們展示更加優秀的個體榜樣時,他們會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技能水準和能力做出更高的評價。
社會比較存在什麼樣的問題?現在我們知道,主要有三個問題。
第一,這樣的比較往往不準確。我們並不清楚別人的成功、幸福和財富狀況,因此很多時候我們的判斷是不準確的。例如:請判斷一個出了車禍被撞斷腿的人,與一個買彩券中了500萬元大獎的人,三個月後誰更幸福?多數人憑直覺會認為中了彩券的人肯定更幸福,但實際上心理學研究發現,二者在事件發生的三個月後,幸福指數並沒有太大差別。因為人有非常嚴重的適應傾向。一個人中了大獎,剛開始固然會很開心,但是很快他就會陷入財務的煩惱,要面對繳稅、朋友找他借錢、投資可能失敗等問題。特別是毫無心理準備的中獎者因為突然中獎而產生的壓力,反而比未中獎者的更大。研究發現,除非是至親亡故,否則一般來說,人類所有的不幸遭遇,包括挫折和失敗給人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三個月後都有可能消失。
第二,我們在比較時有很多非理性的習慣。例如:你是否願意和股神巴菲特交換生命?因為巴菲特是億萬富翁,很多人容易被這樣的光環吸引,便不假思索地答應。但他們忘了,巴菲特已經是一個年逾九旬的老人,而自己的生命還如此年輕,這樣的交換並不值得。這種比較容易受鮮明形象影響的習慣性思考偏差,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教授稱為代表性思考偏誤。也就是說,我們往往會被對方有代表性的特徵迷惑,使我們比較的不是真實的整體結果。
第三,比較會對人的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在很多國家,富裕的人透過把自己跟那些較窮的人進行比較而獲得滿足感。但是我們發現,中產階級和窮人往往更願意與比自己收入更高、事業更成功、社會地位更優越的人進行比較,換句話說,我們傾向和社會等級比自己高的人進行比較。
身處的地區貧富差距越大,人們越容易感到不滿足。我們很容易和住在附近,比我們過得好的人進行社會比較,這會讓我們的自尊心和幸福感都受到傷害。想像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人人房子都是40坪的社區,但你的房子有50坪,那你顯然會比同樣住在50坪的房子裡,但周圍的房子都是60坪的人更快樂一些。
此外,媒體對富人生活方式的宣揚或者看到別人炫富,都會加深我們的相對貧窮感,從而降低我們對生活的滿足感和幸福感。
▍如何比較才正確?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然而社會生活充滿各式各樣的比較,即使我們自己不去比,我們周圍的人、親朋好友,也經常會下意識地拿我們和其他人對比,所以才會出現「別人家的孩子」、「別人家的老公」這樣的詞彙。
既然社會比較難以避免,你可以試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做出改變。第一, 根據比較的目的,調整比較的方向。
為了提升自我的滿足感和幸福感,我們可以選擇向下比較,也可以避免比較。也就是說,當我們認為自己在特定領域的能力和表現比較差的時候,便最好不要在這個領域進行向上的社會比較。
如果比較的目的是給自己增加行動的力量,那麼向上比較可以讓我們產生積極的能量,從而提升得更快,進步得更明顯。透過讓自己相信自己是精英或者上層的一部分,強調自己和比較對象的相似性,我們便能感覺舒適、快樂和被接受。有研究發現,雖然癌症患者一般喜歡下行比較,但他們也希望獲得比自己幸運的其他康復者的資訊,從而讓自己產生希望。
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節食的人也經常進行向上的社會比較。在冰箱上貼一張比自己瘦的人的照片,不僅能提醒自己留意體重,還能使自己有一個奮鬥的目標、行動的靈感。所以向下的社會比較可以讓我們感覺更好,而向上的社會比較則能激勵我們努力行動。
康乃爾大學知名心理學家湯瑪仕.吉洛維奇(Gilovich Thomas)曾和兩位學生做了一項研究: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評價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各項比賽中,奪牌選手在透過終點時和在臺上受獎時的情緒表現,並給選手的表情打分數,滿分為10分,表情越開心分數越高。
結果發現,在比賽結果宣佈時,銀牌選手的平均分數只有4.8分,而銅牌選手的分數卻高達7.1分。在頒獎典禮上,銅牌選手的快樂表情有所收斂,但仍有5.7分,而銀牌選手則變得更不開心,表情變成了4.3分。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銅牌選手與銀牌選手的開心程度存在顯著差異。
▍為什麼銅牌比銀牌更快樂?
按照正常的理解,人們的開心程度應該與其成績有對應關係。如果我們表現得好、成績優異,我們會很開心;反之則不開心。依此邏輯,銀牌選手應該比銅牌選手開心才對,畢竟他的成績只是在一人之下,卻在眾人之上。
根據吉洛維奇的研究,產生這種意外結果的主要原因是這兩種人的反事實思考不一樣。所有人都在用反事實思考進行思考。反事實思考是個體基於與現實相反的條件或可能性進行推理的一種思考過程,或者是對事實的一種替換想像。人們通常是在心理上對已經發生過的事進行否定,進而建構一種假設的可能性,即「如果怎麼樣,就會怎麼樣」。
銀牌選手的反事實思考肯定是向上比較,因為對於銀牌選手而言,獎牌已經到手,他只要再努力一下,就一定可以獲得金牌,所以,向上比較的反事實思考很自然。銅牌選手則更可能有向下比較的反事實思考,因為他差一點就可能是第四名,得不到獎牌,因此,向下比較的反事實思考則更為自然。比較的方向不同,人的情緒受到的影響也就不同。
十幾年後,我的好朋友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大衛.松本教授(David Matsumoto)和美國《世界柔道雜誌》(The World of Judo Magazine)的編輯鮑伯.威林罕(Bob Willingham)對2004年在雅典奧運上獲得柔道金牌、銀牌和銅牌選手的臉部表情進行了電腦分析,分析結果再次驗證了吉洛維奇教授的發現。更有趣的是,銀牌選手不但表現得不開心,甚至還流露出悲傷、輕蔑和冷漠等負面的情緒。當然,這些銀牌選手在頒獎臺上還是會露出笑臉,只不過他們的微笑大部分是偽裝的、禮貌性的。
再舉一個中國游泳選手傅園慧的案例。在2016年的里約奧運上,傅園慧在發現自己奪得100公尺仰式銅牌後開心地說:「啊?第三啊?噢,那我覺得還是不錯的。」而當她在2017年的游泳世錦賽上獲得50公尺仰式銀牌後,她難過得眼淚都流了出來。由此可見,銀牌選手確實不如銅牌選手開心。
▍我就是會忍不住在意
上述研究生動地說明:一個人的成就、獲得和收益到底有多大,與其幸福程度不完全相關,而是和他的認識、判斷密切相關。當我們向上比較時,很難感受到自己已經獲得的成就,而當我們向下比較時,反而會知足常樂。這就意味著,真正影響人生的幸福和快樂的,是我們的預期和比較。
生活中,我們經常有與別人比較的衝動,我們感覺的好壞往往取決於比較的結果。當其他人聰明、靈活、成績好的時候,我們就顯得愚昧、笨拙、成績差。當你剛剛為了20萬元的年終獎金興高采烈,卻發現你的同事比你多拿兩萬元時,你可能就會變得不開心。
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那麼我們為什麼會有意無意地跟別人進行比較呢?
在進化史上,遠古人類為了規避風險、活得更久並成功繁衍,最重要的生存條件之一就是從屬於某一集體。他們透過不斷將自己和部族裡的其他人進行比較,保護自己不被集體排斥:我這樣做是否合適?我是否達到了別人的預期?我的貢獻夠大嗎?別人喜歡我嗎……直到今天,人類大腦依然沿用過往的模式,透過跟其他人比較來向自己發出受歡迎或被排斥的訊號。195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里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社會比較理論,他認為,自我認識的不確定性是人們進行社會比較的主要原因。每個人都有瞭解自我、評價自我的衝動,但在缺乏客觀標準的情況下,我們會把他人當作比較的尺度,在比較中獲得意義。另外,我們進行社會比較的對象不一定是那些比我們優越很多的人,往往還是自己身邊的人。也就是說,雖然某富豪可能會給自己定下一年賺1億的「小目標」,但我們不會和他比,但如果自己身邊的某個朋友比自己每個月多賺1萬元,我們便會感到不開心。
我們是如何進行社會比較的呢?社會比較可以細分為向上比較、平行比較和向下比較。向上比較,顧名思義,指的是在一個特定的指標上把自己與比自己強的人做比較,我們一般說的「比較」指的便是向上比較。在財富、成績、聲望上和那些比我們強的人比較,往往會傷害我們的自尊心,但也不排除對有些人來說,向上比較是激勵他們奮發向上、愈戰愈勇的動力。向下比較則是選擇不如自己的個體進行逆向比較,這樣通常會讓自己感覺更好。
由此會產生兩種效應,一種是對比效應。在現實中很多人有這樣的體會,當我們在職場上看到競爭者衣著光鮮、信心滿滿、侃侃而談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產生自卑情緒,降低對自己的評價。反之,當我們面對一個唯唯諾諾、不善言辭的競爭者時,我們便會不自覺地增強信心,提高對自己的評價。另外一種是同化效應。對於一些有上進心、有抱負的人,當向他們展示更加優秀的個體榜樣時,他們會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技能水準和能力做出更高的評價。
社會比較存在什麼樣的問題?現在我們知道,主要有三個問題。
第一,這樣的比較往往不準確。我們並不清楚別人的成功、幸福和財富狀況,因此很多時候我們的判斷是不準確的。例如:請判斷一個出了車禍被撞斷腿的人,與一個買彩券中了500萬元大獎的人,三個月後誰更幸福?多數人憑直覺會認為中了彩券的人肯定更幸福,但實際上心理學研究發現,二者在事件發生的三個月後,幸福指數並沒有太大差別。因為人有非常嚴重的適應傾向。一個人中了大獎,剛開始固然會很開心,但是很快他就會陷入財務的煩惱,要面對繳稅、朋友找他借錢、投資可能失敗等問題。特別是毫無心理準備的中獎者因為突然中獎而產生的壓力,反而比未中獎者的更大。研究發現,除非是至親亡故,否則一般來說,人類所有的不幸遭遇,包括挫折和失敗給人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三個月後都有可能消失。
第二,我們在比較時有很多非理性的習慣。例如:你是否願意和股神巴菲特交換生命?因為巴菲特是億萬富翁,很多人容易被這樣的光環吸引,便不假思索地答應。但他們忘了,巴菲特已經是一個年逾九旬的老人,而自己的生命還如此年輕,這樣的交換並不值得。這種比較容易受鮮明形象影響的習慣性思考偏差,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教授稱為代表性思考偏誤。也就是說,我們往往會被對方有代表性的特徵迷惑,使我們比較的不是真實的整體結果。
第三,比較會對人的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在很多國家,富裕的人透過把自己跟那些較窮的人進行比較而獲得滿足感。但是我們發現,中產階級和窮人往往更願意與比自己收入更高、事業更成功、社會地位更優越的人進行比較,換句話說,我們傾向和社會等級比自己高的人進行比較。
身處的地區貧富差距越大,人們越容易感到不滿足。我們很容易和住在附近,比我們過得好的人進行社會比較,這會讓我們的自尊心和幸福感都受到傷害。想像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人人房子都是40坪的社區,但你的房子有50坪,那你顯然會比同樣住在50坪的房子裡,但周圍的房子都是60坪的人更快樂一些。
此外,媒體對富人生活方式的宣揚或者看到別人炫富,都會加深我們的相對貧窮感,從而降低我們對生活的滿足感和幸福感。
▍如何比較才正確?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然而社會生活充滿各式各樣的比較,即使我們自己不去比,我們周圍的人、親朋好友,也經常會下意識地拿我們和其他人對比,所以才會出現「別人家的孩子」、「別人家的老公」這樣的詞彙。
既然社會比較難以避免,你可以試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做出改變。第一, 根據比較的目的,調整比較的方向。
為了提升自我的滿足感和幸福感,我們可以選擇向下比較,也可以避免比較。也就是說,當我們認為自己在特定領域的能力和表現比較差的時候,便最好不要在這個領域進行向上的社會比較。
如果比較的目的是給自己增加行動的力量,那麼向上比較可以讓我們產生積極的能量,從而提升得更快,進步得更明顯。透過讓自己相信自己是精英或者上層的一部分,強調自己和比較對象的相似性,我們便能感覺舒適、快樂和被接受。有研究發現,雖然癌症患者一般喜歡下行比較,但他們也希望獲得比自己幸運的其他康復者的資訊,從而讓自己產生希望。
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節食的人也經常進行向上的社會比較。在冰箱上貼一張比自己瘦的人的照片,不僅能提醒自己留意體重,還能使自己有一個奮鬥的目標、行動的靈感。所以向下的社會比較可以讓我們感覺更好,而向上的社會比較則能激勵我們努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