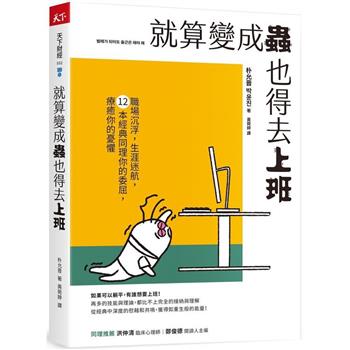工作陷入重複與麻木,怎麼活出你想要的樣子(摘錄自第四章)
讀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
人是應該選擇月亮,還是六便士?
隨著我在公司工作的年資漸長,我感到自己逐漸失去活力與色彩,面對愈來愈多事會感到無趣,對於工作的熱情也在消逝,我不再願意表達自己的情感或看法。更令人沮喪的是,這種沒有色彩的狀態不僅發生在職場,甚至出現在工作之外的生活。我甚至開始質疑自己是否原本就是這樣的人。什麼是我曾經最熱愛的東西?那些讓我心跳加速、臉頰紅熱、眼睛閃閃發亮的東西究竟去了哪裡?
英國作家毛姆有本小說《月亮與六便士》,當中描繪了為夢想而活的人,以及畏於現實而活的人。月亮代表夢想,六便士代表現實。小說中懷抱不同追求的人彼此無法互相理解,他們就像兩個無法共存的世界。
可是,夢想與現實當真無法共存嗎?我們應該追逐夢想,抑或屈從現實?難道我們就必須犧牲並放棄夢想,與現實妥協嗎?為什麼我們會自願放棄自己曾經熱愛的事物?
寫在臉上的溫順,不是發自內心
孫次長一直都是一個極其老實且平凡的人。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堅守崗位。在工作上沒出過大錯,但也沒有亮眼的表現。他忠實地遵循上司的指示,對年輕同事友善。雖然經常需要適應內外部變化,但他也都能順利完成交辦的任務。每當公司聚餐時,他永遠選同樣的食物,但如果說這是他的偏好又不太精準,反而更像是在完成「任務」。他就像是一個「標準化」的上班族,每家公司似乎都會有一位像孫次長這樣的人。
在家裡,他是個好丈夫和父親。晚餐後,洗碗是孫次長的工作。週末,他會主動去洗衣服和打掃,許多人會認為家事是妻子的工作,丈夫若願意在週末「幫忙」做家事,那就太完美了。但從孫次長臉上完全看不到「幫忙」的痕跡,他認為這就是他的「分內事」。對於孩子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只要孩子提出來,他就會盡可能去滿足他們的所有要求。因此,雖然媽媽陪伴孩子的時間比較多,但孩子還是更喜歡爸爸。
每當獨自一人時,他會沉浸在閱讀中。想知道他是否在家,只要看看書房就知道。如果要帶狗狗出門散步,他會在家庭群組聊天室裡留下散步路線和預計時間。孫次長的生活從表面上來看,幾乎無從挑剔,穩定的工作、美滿的家庭,周遭的人對他的評價也是一致的好評,但他自己的感受呢?
倦怠、厭惡、煩躁、乏味、無聊、單調……以上這些詞彙都符合孫次長對目前生活的評價─了無新意。也許他更像是家庭的背景,而不是家裡的一分子。
他每天搭同一條路線的電車上下班,就連遇到的乘客也都千篇一律,就算閉著眼也能往返家裡和公司,工作上也是,每天日復一日地重複做著相同的事,很安全,但毫無挑戰可言。
很難想像,在大學時期孫次長留著一頭長捲髮,總是戴著黑色太陽眼鏡、穿著破爛的牛仔褲、戴著耳環,還貼著紋身貼紙,是風靡全校的硬搖滾樂團主唱,甚至可以輕而易舉地唱出死腔、黑腔。
但現在,孫次長已成為一位毫無個性的證券交易員,每天穿著燙得整齊的西裝、不會出任何差錯的髮型、和令人安心的低沉嗓音。距離那段美好的青春歲月已經過了11年。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這是有原因的,他在公司總會感到窒息,而這樣的表現就是他從職場生活學到的生存之道。
孫次長每天上班時,都會經過企業創辦人的銅像,他總是會不自覺地停下腳步,提醒自己:「希望自己不要變成如同銅像一樣冰冷。」但誰也不了他真正的想法。他已經太習慣在職場上掩飾自己真實的想法,甚至認為這是成為社會人士的必備條件。他也很難在公司裡交到真心的朋友,甚至不太想跟其他人交談,在公司裡他只說必要的話,然後閉上嘴微笑,大家也喜歡這樣的他,甚至覺得他這樣很有禮貌、安靜而且溫柔。
其實,孫次長也曾經試著真誠地與同事交流,但他試過幾次之後,發現即使拿出真心,真心就像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硬幣一樣滾來滾去,這根本不是它該存在的地方。於是,他學會用沉默與微笑防禦,並不斷地自我說服「我是來賺錢的,不是來聯誼的,適當交際就好」,如今,他已經成為寡言的化身,他幾乎不分享關於自己的想法、觀點或過去,當然也沒有人知道埋藏在他內心裡的搖滾夢。
就算穿上了筆挺的西裝,換上了渾厚的嗓音,他還是對搖滾念念不忘,但每當內心響起「好想唱歌」又會有另一個聲音硬生生地打斷自己「那算什麼,你現在還有比唱歌更重要的事要做!上班、賺錢養家才是你現在該努力的事」。
這種生活還要過多久?雖然可以預期總有一天會結束,但就目前來看似乎沒有盡頭。他肩負養家活口的責任,是整個家的主要經濟來源,年邁的雙親每天往返醫院,妻子嫁給他之後就成為家庭主婦,就算孩子大了,她也沒有打算投入職場。
說穿了,他毫無選擇,也無從改變起。這11年下來,讓他愈來愈疲憊、倦怠,甚至反而對這種穩定、美好的生活感到窒息。
「我存在的價值到底是什麼?」孫次長幾乎每天睡前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但他愈來愈答不上來。
孫次長也是閱讀俱樂部的一員,但他參加的理由正如同他的工作或家庭生活一般,就是因為大家都參加了許多社團,所以他選了一個不討厭、也沒那麼負擔的活動。
這個月閱讀俱樂部選定共讀的書是《月亮與六便士》。孫次長就像處理公務一樣,收到通知後,在下班的途中買了這本書,雖然不見得會想讀這本書,但他心想:「至少也要做做樣子」,出乎意料的是,俱樂部這個月指定孫次長作為導讀人,他聽到的當下相當納悶,「為什麼是我?」但也不好意思拒絕。為了準備導讀不得不翻開這本書,「至少要知道內容大概在講什麼」他心裡本來盤算著只要翻翻就好。但看過故事後,他發現自己和小書的主角經歷很類似,這本小說的主角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能專心地畫畫,他也是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在40歲時毅然決然放棄高薪工作,轉而去追尋自己真正的夢想。這讓他不自覺得被故事吸引,一抓到時間就拿起書來翻,忍不住想知道接下來故事的發展。
孫次長的妻子對於他比平常更認真閱讀感到訝異,因此好奇地問他在看什麼書?孫次長簡單地說明了這個故事的大綱,沒想到妻子卻不太開心的回覆,「也太沒營養了。追求個人夢想有必要做到這種地步嗎?」
是啊,有必要放下一切去追尋嗎?
孫次長心理也有相同的困惑,但他下意識地為主角史崔蘭辯護,妻子聽到他還為主角辯護,愈聽愈生氣,進而提高音量質疑他:「所以你也認同他的做法,為了追尋夢想拋妻棄子是正確的囉?」
孫次長頓時語塞,臉上一陣尷尬,但他的聲音聽不出任何情緒,彷彿就在講一件無關己要的事:「要做出這麼重大的決定,必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思考吧。也許真的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呼喚他去做這件事,就像在書裡面作者的形容,那是『受到惡魔突如其來的攻擊』,主角似乎受到惡魔困擾,感覺就要被撕成碎片,那股難以言喻的衝動,的確很適合用『惡魔』來比喻。」
妻子聽到他的說明,頓時覺得安心了不少,畢竟「惡魔」和「禁忌」在某種程度上是很接近的形容詞,都是應該近而遠之的事物。
孫次長看著妻子的表情趨於和緩,暗自慶幸安然度過了一場可能釀成家庭危機的對話,但他又看向被隨意擱置在角落的電吉他,他彷彿感受到「惡魔」的侵擾,不斷產生想要拿起來刷幾首歌的衝動,幾乎無法抑制,這真是太危險了,他平常把這股慾望掩飾的很好,連枕邊人都沒有發現他內心渴望充滿激情的生活,但開始讀這本書之後,愈來愈難掩飾這份悸動,他決定把吉他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本書真是太危險了。」孫次長讀著讀著,愈來愈意識到這件事,同時他也意識到他的生命中,沒有什麼能讓他像看到這本書一樣,有重新活過來的感覺。就像《聖經》中夏娃被蛇所誘惑,聽從蛇的話去摘下果實,明明知道不能做為什麼還是會被吸引,甚至不斷想起呢?因為那太美好、太令人嚮往和─讓人感覺真正地活著。
孫次長不知不覺看了一整夜,直到魚肚翻白他也沒有發現,只是一頁接著一頁地翻著,渴慕著結局。
低頭撿拾滿地的六便士,卻不見頭頂的月亮
《月亮與六便士》這本書,以主角史崔蘭為核心,他是一位過著優渥生活的證券經紀人,家有賢妻又有子女。但在中年40歲的時候,突然回應內心的呼喚,拋妻棄子,捨棄原本優渥的生活,先是兩手空空奔赴巴黎,後來又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與土著一起生活。無論是否能實現理想與熱情,他只知道他要不停地畫,就算最後被眾人唾罵、窮困潦倒、病痛纏身……。
這本書有一句很經典的台詞「一般人都不是他們想要做的那種人,而是他們不得不做的那種人。」史崔蘭的故事完整地體現了這句話。旁人都不理解史崔蘭為什麼不惜放棄穩定生活、美滿的家庭也要畫畫,他只是平靜的說:
「我從未說過我一定要畫畫。但如果不畫些什麼,我就無法生存。對於掉進水中的人,問題不在於他游得標不標準、姿勢正不正確,而是不管怎樣就是要游回岸上,否則就會溺斃。」
「游得好不好不是重點,畫畫是為了生存」看到這句話時,孫次長想起自己在證券公司的工作,每天忽視內心不斷發出的生存渴望,只是麻木地工作,努力滿足主管的要求,回家再滿足家人的需求。
這無疑是一種自殺行為。孫次長這才驚覺,自己都對自己做了什麼。
在這個故事裡,史崔蘭毫不介意別人如何批評他的話,他就只是不停地畫畫,不停地創作,為了更接近他的夢想,他忽視了現實生活所需的一切,就算畫到窮途潦倒,他仍然緊抓著畫筆。
真的有人可以做到這種程度嗎?完全忽視體制,不管他人的眼光?這樣不會太自私了嗎?
孫次長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人活著真的能只追求對自己有意義的事物嗎?但他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告訴他若人只想到自己,只追尋對自己有意義的事物,勢必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這個社會就是團體生活,人無法離群索居,自私自利的人最終必然受到懲罰。
當孫次長還在思索關於自私這個問題時,他看到故事中提到史崔蘭對良知的闡述:
「我認為良知本來是心的守衛,是為了讓人類社會能順利運作、互惠互助發展出來的道德守則,但後來良知變成了每個人內心的道德警察,他監督著我們循規守法。良知也是潛伏在一個人自我意識中心堡壘的暗探。」
這樣形容良知似乎太過偏激,但這描述又莫名的精準,只是為什麼人們願意接受良知的約束,不斷進行自我審查呢?故事中小說家以敘述者的角色繼續分析:
「由於常人總是過於強烈地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同,過於害怕輿論的非議,結果自己引狼入室,把敵人放進了自己的大門。而這個暗探就時刻監視著敵人,始終警惕地捍衛主人的利益,隨時摧毀任何剛冒出頭的想要脫離群體的念頭。良知會迫使每一個人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
他人的肯定與讚美,有比實踐自我價值重要嗎?孫次長又陷入了沉思。如果照著良知的指示去做,就能過上幸福快樂的人生了嗎?
孫次長回頭檢視自己的處境,終其一生幾乎都遵循著良知的指引過日子,他認真工作、用心經營家庭、不遺餘力地奉養父母,但「幸福快樂」卻離他很遠。
如果我們認真地把良知的審核標準一條一條拿出來檢視,就會發現最核心的價值,就是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如果調換了順序,就會變成他人眼中的「混蛋」。
小說中的年輕作家從第三者的角度,探討到底為什麼我們需要遵循良知的指引,若過著不違背良知的生活,就會過得幸福快樂嗎?如果像史崔蘭這樣以個人追求為優先,就會變得不幸嗎?在故事裡,小說家把遵循良知這件事,用以下的情境比喻:
「恰如宮廷弄臣百般頌揚扛在肩上的國王權杖一樣,他為自己有敏銳的良知而感到自豪。這時,對於不承認良知力量的人,他會用嚴厲得不能更嚴厲的言辭來責駡這些人,懲罰以自己利益為優先的人,彷彿這些人是十惡不赦的罪人,因為他現在已成為社會的一員,清楚地知道這些人是沒有力量對抗自己的。」
雖然我們活在不同的時代,但對於上述的場景,我相信每個人尤其是出了社會的成人,一定更能感同身受。
孫次長看到這一段時,不禁想起以前在學校上公民道德課的場景,每個人都需要回答「正確答案」,那個正確答案的標準就是「以眾人的利益為優先」,通常選擇題給出的錯誤選項都顯而易見,只是要強調獨特性、以個人利益為前提,就一定是錯的答案。但這彷彿在灌輸每個人:「有想法、有創意、積極熱情的展現自己,就是犯罪」。
因此當孫次長看到史崔蘭一次一次為了「畫畫」下的決定,愈來愈遠離「良知建議」的行動,他備感衝擊:「原來,就算不依循良知,也能活得幸福快樂。」孫次長回頭看了看自己的處境,他覺得國家彷彿是一台大型的機器,發出轟隆隆的噪音,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遵循「正軌」活到現在,甚至明明可以免役,還是乖乖地去當完兵,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甚至會動用勢力讓孩子不用當兵。自己不這麼做的原因,也只是擔心他人的眼光對自己投以無聲地指責罷了。
孫次長突然覺得,自己對這個世界無比陌生。
當你終於抬起頭,去追尋月亮
在受到啟發後,史崔蘭認識到「幸福」的真諦。他了解自己若無法作畫,就算能延續生命也不代表「活著」,某種程度上,自己不得不繼續畫下去。
雖然在外人眼裡,史崔蘭為了「畫畫」放棄了許多人眼中艷羨的一切,甚至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但對他來說這些選項都只是為了「求生」。
就在史崔蘭終於能一心做畫的時候,支持他的年輕作家卻開始擔憂,史崔蘭很難在充滿階級、惡評且市儈的藝術界存活下來。因此他總在史崔蘭作畫的時候,設法從旁給予建議,使他畫出更容易受到市場接受的作品,但他發現史崔蘭只是埋頭作畫,沒有因為他的建議動搖過。
年輕作家:「我以為你會需要別人的建議,畢竟你不熟悉藝術市場。」
史崔蘭:「你怎麼會覺得我拋下了一切就為了畫畫,還會擔心如何融入市場呢?」
史崔蘭的回應中,傳達出他對年輕作家的想法充滿無法估量的鄙視。
孫次長對這段對話感到無比震撼。居然是史崔蘭鄙視年輕作家給的建議,而年輕作家也沒有加以反駁─這太不尋常了!難道遵循世間的規範過活,反而是一件令人鄙視的行為?
孫次長之所以會感到如此衝擊,正因為他一路走來,都遵循著好公民、好員工、好爸爸、好兒子、好丈夫的標準,以此自我約束。這讓他重新去思考這些標準從何而來?這似乎是沒有選擇的餘地,自他出生在大韓民國,從小接受的教育、父母師長的叮嚀與同儕之間的彼此約束,都是從這個標準出發,每個韓國人都是在這套標準底下長大的,要學韓語、韓國文字、孝順父母、尊重長者、對國家忠誠、為南北韓統一努力、為進步的社會盡心盡力等。
孫次長依循這套標準長大,升學、當兵、退伍、進入職場,在工作穩定後娶妻生子;他也依循著這套標準,繼續教導他的孩子,他閉著眼睛就能想像,孩子會經歷和他一樣的旅程。他認為依循這套標準並沒有錯,國家照顧人民,人民要報效國家,因此對於書中史崔蘭的鄙視特別不滿。但他冷靜後慢慢發現,這理論看似公平,但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活著?自己真的有因此獲得對等的回報嗎?他這才驚覺,為什麼年輕作家沒有反駁史崔蘭,孫次長也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讀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
人是應該選擇月亮,還是六便士?
隨著我在公司工作的年資漸長,我感到自己逐漸失去活力與色彩,面對愈來愈多事會感到無趣,對於工作的熱情也在消逝,我不再願意表達自己的情感或看法。更令人沮喪的是,這種沒有色彩的狀態不僅發生在職場,甚至出現在工作之外的生活。我甚至開始質疑自己是否原本就是這樣的人。什麼是我曾經最熱愛的東西?那些讓我心跳加速、臉頰紅熱、眼睛閃閃發亮的東西究竟去了哪裡?
英國作家毛姆有本小說《月亮與六便士》,當中描繪了為夢想而活的人,以及畏於現實而活的人。月亮代表夢想,六便士代表現實。小說中懷抱不同追求的人彼此無法互相理解,他們就像兩個無法共存的世界。
可是,夢想與現實當真無法共存嗎?我們應該追逐夢想,抑或屈從現實?難道我們就必須犧牲並放棄夢想,與現實妥協嗎?為什麼我們會自願放棄自己曾經熱愛的事物?
寫在臉上的溫順,不是發自內心
孫次長一直都是一個極其老實且平凡的人。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堅守崗位。在工作上沒出過大錯,但也沒有亮眼的表現。他忠實地遵循上司的指示,對年輕同事友善。雖然經常需要適應內外部變化,但他也都能順利完成交辦的任務。每當公司聚餐時,他永遠選同樣的食物,但如果說這是他的偏好又不太精準,反而更像是在完成「任務」。他就像是一個「標準化」的上班族,每家公司似乎都會有一位像孫次長這樣的人。
在家裡,他是個好丈夫和父親。晚餐後,洗碗是孫次長的工作。週末,他會主動去洗衣服和打掃,許多人會認為家事是妻子的工作,丈夫若願意在週末「幫忙」做家事,那就太完美了。但從孫次長臉上完全看不到「幫忙」的痕跡,他認為這就是他的「分內事」。對於孩子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只要孩子提出來,他就會盡可能去滿足他們的所有要求。因此,雖然媽媽陪伴孩子的時間比較多,但孩子還是更喜歡爸爸。
每當獨自一人時,他會沉浸在閱讀中。想知道他是否在家,只要看看書房就知道。如果要帶狗狗出門散步,他會在家庭群組聊天室裡留下散步路線和預計時間。孫次長的生活從表面上來看,幾乎無從挑剔,穩定的工作、美滿的家庭,周遭的人對他的評價也是一致的好評,但他自己的感受呢?
倦怠、厭惡、煩躁、乏味、無聊、單調……以上這些詞彙都符合孫次長對目前生活的評價─了無新意。也許他更像是家庭的背景,而不是家裡的一分子。
他每天搭同一條路線的電車上下班,就連遇到的乘客也都千篇一律,就算閉著眼也能往返家裡和公司,工作上也是,每天日復一日地重複做著相同的事,很安全,但毫無挑戰可言。
很難想像,在大學時期孫次長留著一頭長捲髮,總是戴著黑色太陽眼鏡、穿著破爛的牛仔褲、戴著耳環,還貼著紋身貼紙,是風靡全校的硬搖滾樂團主唱,甚至可以輕而易舉地唱出死腔、黑腔。
但現在,孫次長已成為一位毫無個性的證券交易員,每天穿著燙得整齊的西裝、不會出任何差錯的髮型、和令人安心的低沉嗓音。距離那段美好的青春歲月已經過了11年。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這是有原因的,他在公司總會感到窒息,而這樣的表現就是他從職場生活學到的生存之道。
孫次長每天上班時,都會經過企業創辦人的銅像,他總是會不自覺地停下腳步,提醒自己:「希望自己不要變成如同銅像一樣冰冷。」但誰也不了他真正的想法。他已經太習慣在職場上掩飾自己真實的想法,甚至認為這是成為社會人士的必備條件。他也很難在公司裡交到真心的朋友,甚至不太想跟其他人交談,在公司裡他只說必要的話,然後閉上嘴微笑,大家也喜歡這樣的他,甚至覺得他這樣很有禮貌、安靜而且溫柔。
其實,孫次長也曾經試著真誠地與同事交流,但他試過幾次之後,發現即使拿出真心,真心就像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硬幣一樣滾來滾去,這根本不是它該存在的地方。於是,他學會用沉默與微笑防禦,並不斷地自我說服「我是來賺錢的,不是來聯誼的,適當交際就好」,如今,他已經成為寡言的化身,他幾乎不分享關於自己的想法、觀點或過去,當然也沒有人知道埋藏在他內心裡的搖滾夢。
就算穿上了筆挺的西裝,換上了渾厚的嗓音,他還是對搖滾念念不忘,但每當內心響起「好想唱歌」又會有另一個聲音硬生生地打斷自己「那算什麼,你現在還有比唱歌更重要的事要做!上班、賺錢養家才是你現在該努力的事」。
這種生活還要過多久?雖然可以預期總有一天會結束,但就目前來看似乎沒有盡頭。他肩負養家活口的責任,是整個家的主要經濟來源,年邁的雙親每天往返醫院,妻子嫁給他之後就成為家庭主婦,就算孩子大了,她也沒有打算投入職場。
說穿了,他毫無選擇,也無從改變起。這11年下來,讓他愈來愈疲憊、倦怠,甚至反而對這種穩定、美好的生活感到窒息。
「我存在的價值到底是什麼?」孫次長幾乎每天睡前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但他愈來愈答不上來。
孫次長也是閱讀俱樂部的一員,但他參加的理由正如同他的工作或家庭生活一般,就是因為大家都參加了許多社團,所以他選了一個不討厭、也沒那麼負擔的活動。
這個月閱讀俱樂部選定共讀的書是《月亮與六便士》。孫次長就像處理公務一樣,收到通知後,在下班的途中買了這本書,雖然不見得會想讀這本書,但他心想:「至少也要做做樣子」,出乎意料的是,俱樂部這個月指定孫次長作為導讀人,他聽到的當下相當納悶,「為什麼是我?」但也不好意思拒絕。為了準備導讀不得不翻開這本書,「至少要知道內容大概在講什麼」他心裡本來盤算著只要翻翻就好。但看過故事後,他發現自己和小書的主角經歷很類似,這本小說的主角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能專心地畫畫,他也是在一家證券公司工作,在40歲時毅然決然放棄高薪工作,轉而去追尋自己真正的夢想。這讓他不自覺得被故事吸引,一抓到時間就拿起書來翻,忍不住想知道接下來故事的發展。
孫次長的妻子對於他比平常更認真閱讀感到訝異,因此好奇地問他在看什麼書?孫次長簡單地說明了這個故事的大綱,沒想到妻子卻不太開心的回覆,「也太沒營養了。追求個人夢想有必要做到這種地步嗎?」
是啊,有必要放下一切去追尋嗎?
孫次長心理也有相同的困惑,但他下意識地為主角史崔蘭辯護,妻子聽到他還為主角辯護,愈聽愈生氣,進而提高音量質疑他:「所以你也認同他的做法,為了追尋夢想拋妻棄子是正確的囉?」
孫次長頓時語塞,臉上一陣尷尬,但他的聲音聽不出任何情緒,彷彿就在講一件無關己要的事:「要做出這麼重大的決定,必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思考吧。也許真的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呼喚他去做這件事,就像在書裡面作者的形容,那是『受到惡魔突如其來的攻擊』,主角似乎受到惡魔困擾,感覺就要被撕成碎片,那股難以言喻的衝動,的確很適合用『惡魔』來比喻。」
妻子聽到他的說明,頓時覺得安心了不少,畢竟「惡魔」和「禁忌」在某種程度上是很接近的形容詞,都是應該近而遠之的事物。
孫次長看著妻子的表情趨於和緩,暗自慶幸安然度過了一場可能釀成家庭危機的對話,但他又看向被隨意擱置在角落的電吉他,他彷彿感受到「惡魔」的侵擾,不斷產生想要拿起來刷幾首歌的衝動,幾乎無法抑制,這真是太危險了,他平常把這股慾望掩飾的很好,連枕邊人都沒有發現他內心渴望充滿激情的生活,但開始讀這本書之後,愈來愈難掩飾這份悸動,他決定把吉他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本書真是太危險了。」孫次長讀著讀著,愈來愈意識到這件事,同時他也意識到他的生命中,沒有什麼能讓他像看到這本書一樣,有重新活過來的感覺。就像《聖經》中夏娃被蛇所誘惑,聽從蛇的話去摘下果實,明明知道不能做為什麼還是會被吸引,甚至不斷想起呢?因為那太美好、太令人嚮往和─讓人感覺真正地活著。
孫次長不知不覺看了一整夜,直到魚肚翻白他也沒有發現,只是一頁接著一頁地翻著,渴慕著結局。
低頭撿拾滿地的六便士,卻不見頭頂的月亮
《月亮與六便士》這本書,以主角史崔蘭為核心,他是一位過著優渥生活的證券經紀人,家有賢妻又有子女。但在中年40歲的時候,突然回應內心的呼喚,拋妻棄子,捨棄原本優渥的生活,先是兩手空空奔赴巴黎,後來又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與土著一起生活。無論是否能實現理想與熱情,他只知道他要不停地畫,就算最後被眾人唾罵、窮困潦倒、病痛纏身……。
這本書有一句很經典的台詞「一般人都不是他們想要做的那種人,而是他們不得不做的那種人。」史崔蘭的故事完整地體現了這句話。旁人都不理解史崔蘭為什麼不惜放棄穩定生活、美滿的家庭也要畫畫,他只是平靜的說:
「我從未說過我一定要畫畫。但如果不畫些什麼,我就無法生存。對於掉進水中的人,問題不在於他游得標不標準、姿勢正不正確,而是不管怎樣就是要游回岸上,否則就會溺斃。」
「游得好不好不是重點,畫畫是為了生存」看到這句話時,孫次長想起自己在證券公司的工作,每天忽視內心不斷發出的生存渴望,只是麻木地工作,努力滿足主管的要求,回家再滿足家人的需求。
這無疑是一種自殺行為。孫次長這才驚覺,自己都對自己做了什麼。
在這個故事裡,史崔蘭毫不介意別人如何批評他的話,他就只是不停地畫畫,不停地創作,為了更接近他的夢想,他忽視了現實生活所需的一切,就算畫到窮途潦倒,他仍然緊抓著畫筆。
真的有人可以做到這種程度嗎?完全忽視體制,不管他人的眼光?這樣不會太自私了嗎?
孫次長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人活著真的能只追求對自己有意義的事物嗎?但他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告訴他若人只想到自己,只追尋對自己有意義的事物,勢必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這個社會就是團體生活,人無法離群索居,自私自利的人最終必然受到懲罰。
當孫次長還在思索關於自私這個問題時,他看到故事中提到史崔蘭對良知的闡述:
「我認為良知本來是心的守衛,是為了讓人類社會能順利運作、互惠互助發展出來的道德守則,但後來良知變成了每個人內心的道德警察,他監督著我們循規守法。良知也是潛伏在一個人自我意識中心堡壘的暗探。」
這樣形容良知似乎太過偏激,但這描述又莫名的精準,只是為什麼人們願意接受良知的約束,不斷進行自我審查呢?故事中小說家以敘述者的角色繼續分析:
「由於常人總是過於強烈地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同,過於害怕輿論的非議,結果自己引狼入室,把敵人放進了自己的大門。而這個暗探就時刻監視著敵人,始終警惕地捍衛主人的利益,隨時摧毀任何剛冒出頭的想要脫離群體的念頭。良知會迫使每一個人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
他人的肯定與讚美,有比實踐自我價值重要嗎?孫次長又陷入了沉思。如果照著良知的指示去做,就能過上幸福快樂的人生了嗎?
孫次長回頭檢視自己的處境,終其一生幾乎都遵循著良知的指引過日子,他認真工作、用心經營家庭、不遺餘力地奉養父母,但「幸福快樂」卻離他很遠。
如果我們認真地把良知的審核標準一條一條拿出來檢視,就會發現最核心的價值,就是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如果調換了順序,就會變成他人眼中的「混蛋」。
小說中的年輕作家從第三者的角度,探討到底為什麼我們需要遵循良知的指引,若過著不違背良知的生活,就會過得幸福快樂嗎?如果像史崔蘭這樣以個人追求為優先,就會變得不幸嗎?在故事裡,小說家把遵循良知這件事,用以下的情境比喻:
「恰如宮廷弄臣百般頌揚扛在肩上的國王權杖一樣,他為自己有敏銳的良知而感到自豪。這時,對於不承認良知力量的人,他會用嚴厲得不能更嚴厲的言辭來責駡這些人,懲罰以自己利益為優先的人,彷彿這些人是十惡不赦的罪人,因為他現在已成為社會的一員,清楚地知道這些人是沒有力量對抗自己的。」
雖然我們活在不同的時代,但對於上述的場景,我相信每個人尤其是出了社會的成人,一定更能感同身受。
孫次長看到這一段時,不禁想起以前在學校上公民道德課的場景,每個人都需要回答「正確答案」,那個正確答案的標準就是「以眾人的利益為優先」,通常選擇題給出的錯誤選項都顯而易見,只是要強調獨特性、以個人利益為前提,就一定是錯的答案。但這彷彿在灌輸每個人:「有想法、有創意、積極熱情的展現自己,就是犯罪」。
因此當孫次長看到史崔蘭一次一次為了「畫畫」下的決定,愈來愈遠離「良知建議」的行動,他備感衝擊:「原來,就算不依循良知,也能活得幸福快樂。」孫次長回頭看了看自己的處境,他覺得國家彷彿是一台大型的機器,發出轟隆隆的噪音,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遵循「正軌」活到現在,甚至明明可以免役,還是乖乖地去當完兵,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甚至會動用勢力讓孩子不用當兵。自己不這麼做的原因,也只是擔心他人的眼光對自己投以無聲地指責罷了。
孫次長突然覺得,自己對這個世界無比陌生。
當你終於抬起頭,去追尋月亮
在受到啟發後,史崔蘭認識到「幸福」的真諦。他了解自己若無法作畫,就算能延續生命也不代表「活著」,某種程度上,自己不得不繼續畫下去。
雖然在外人眼裡,史崔蘭為了「畫畫」放棄了許多人眼中艷羨的一切,甚至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但對他來說這些選項都只是為了「求生」。
就在史崔蘭終於能一心做畫的時候,支持他的年輕作家卻開始擔憂,史崔蘭很難在充滿階級、惡評且市儈的藝術界存活下來。因此他總在史崔蘭作畫的時候,設法從旁給予建議,使他畫出更容易受到市場接受的作品,但他發現史崔蘭只是埋頭作畫,沒有因為他的建議動搖過。
年輕作家:「我以為你會需要別人的建議,畢竟你不熟悉藝術市場。」
史崔蘭:「你怎麼會覺得我拋下了一切就為了畫畫,還會擔心如何融入市場呢?」
史崔蘭的回應中,傳達出他對年輕作家的想法充滿無法估量的鄙視。
孫次長對這段對話感到無比震撼。居然是史崔蘭鄙視年輕作家給的建議,而年輕作家也沒有加以反駁─這太不尋常了!難道遵循世間的規範過活,反而是一件令人鄙視的行為?
孫次長之所以會感到如此衝擊,正因為他一路走來,都遵循著好公民、好員工、好爸爸、好兒子、好丈夫的標準,以此自我約束。這讓他重新去思考這些標準從何而來?這似乎是沒有選擇的餘地,自他出生在大韓民國,從小接受的教育、父母師長的叮嚀與同儕之間的彼此約束,都是從這個標準出發,每個韓國人都是在這套標準底下長大的,要學韓語、韓國文字、孝順父母、尊重長者、對國家忠誠、為南北韓統一努力、為進步的社會盡心盡力等。
孫次長依循這套標準長大,升學、當兵、退伍、進入職場,在工作穩定後娶妻生子;他也依循著這套標準,繼續教導他的孩子,他閉著眼睛就能想像,孩子會經歷和他一樣的旅程。他認為依循這套標準並沒有錯,國家照顧人民,人民要報效國家,因此對於書中史崔蘭的鄙視特別不滿。但他冷靜後慢慢發現,這理論看似公平,但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活著?自己真的有因此獲得對等的回報嗎?他這才驚覺,為什麼年輕作家沒有反駁史崔蘭,孫次長也找不到反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