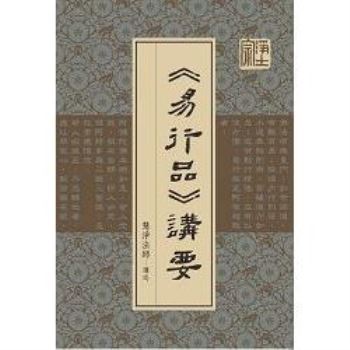序
一、前言
(一)《入楞伽經》懸記之文
龍樹菩薩被大乘佛教尊為八宗共祖,然其本意,唯在淨土宗,不在別宗。此若熟思其《易行品》與《十二禮偈》,便可頷首;尤其「楞伽懸記」之聖讖,更是不容置疑。《入楞伽經》卷九釋尊懸記之文說: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二)《易行品》別冊刊行
《易行品》為龍樹菩薩所撰述《十住毘婆沙論》(daśa bhūmi vibhāśa śāstra)之第九品,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翻譯,收錄於《大正藏》第二十六冊。
古來對《十住論》並不看重,但卻特別重視其中之《易行品》。在古印度時,《易行品》已從《十住論》中抽出別冊刊行。梁朝天監年中(五○二~五一九)僧佑法師所著《出三藏記集》卷四有「《初發意菩薩行易行法》一卷,出《十住論‧易行品》」的記載。可知在我國六朝時代亦將《易行品》別冊刊行,則此《品》之受重視可見一斑。
(三)易行道之內容
眾生根機萬差,故往不退轉地之法亦有多途,龍樹菩薩於此《易行品》中,將所有一切至不退轉地之法門大判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二門。難行道是全靠自力,此即是指淨土宗之外各宗各派所有法門;而易行道則是全靠他力(此他力單指彌陀願力而言),不假自力。如人溺水,頭出頭沒,掙扎痛苦,既不會游泳,也無方便可到彼岸;忽蒙彌陀大悲願力,救度於願船中,乘此願船,安穩自在。此人既不用也沒錢付船票,同時也不用幫忙駕駛,安全快捷到彼岸。此即《易行品》「彌陀章」中所言之彌陀「本願稱名,現生不退」。龍樹菩薩於此「彌陀章」言「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故龍樹菩薩將此「本願稱名」譬喻為「乘船」的法門,而其他一切難行道法門喻為「步行」。「乘船」乃是顯示自己儘管有力量,在此也無用武之地,也置於無用之地;何況就是因為毫無力量,才會墮落,才蒙救度。
《易行品》作為淨土宗尊崇的第一部祖典,對於淨土宗的教理建設,是根本性、基礎性、標準性、權威性的。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修學淨土法門,有否依《易行品》,其淨土教理必有差異,可謂依《易行品》則是純正的淨土宗,不依《易行品》則非純正的淨土宗,足見其地位之重要。
此品文字不長,故凡有志於淨土之行者,應該閱讀,知其要義。
一、前言
(一)《入楞伽經》懸記之文
龍樹菩薩被大乘佛教尊為八宗共祖,然其本意,唯在淨土宗,不在別宗。此若熟思其《易行品》與《十二禮偈》,便可頷首;尤其「楞伽懸記」之聖讖,更是不容置疑。《入楞伽經》卷九釋尊懸記之文說: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二)《易行品》別冊刊行
《易行品》為龍樹菩薩所撰述《十住毘婆沙論》(daśa bhūmi vibhāśa śāstra)之第九品,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翻譯,收錄於《大正藏》第二十六冊。
古來對《十住論》並不看重,但卻特別重視其中之《易行品》。在古印度時,《易行品》已從《十住論》中抽出別冊刊行。梁朝天監年中(五○二~五一九)僧佑法師所著《出三藏記集》卷四有「《初發意菩薩行易行法》一卷,出《十住論‧易行品》」的記載。可知在我國六朝時代亦將《易行品》別冊刊行,則此《品》之受重視可見一斑。
(三)易行道之內容
眾生根機萬差,故往不退轉地之法亦有多途,龍樹菩薩於此《易行品》中,將所有一切至不退轉地之法門大判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二門。難行道是全靠自力,此即是指淨土宗之外各宗各派所有法門;而易行道則是全靠他力(此他力單指彌陀願力而言),不假自力。如人溺水,頭出頭沒,掙扎痛苦,既不會游泳,也無方便可到彼岸;忽蒙彌陀大悲願力,救度於願船中,乘此願船,安穩自在。此人既不用也沒錢付船票,同時也不用幫忙駕駛,安全快捷到彼岸。此即《易行品》「彌陀章」中所言之彌陀「本願稱名,現生不退」。龍樹菩薩於此「彌陀章」言「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故龍樹菩薩將此「本願稱名」譬喻為「乘船」的法門,而其他一切難行道法門喻為「步行」。「乘船」乃是顯示自己儘管有力量,在此也無用武之地,也置於無用之地;何況就是因為毫無力量,才會墮落,才蒙救度。
《易行品》作為淨土宗尊崇的第一部祖典,對於淨土宗的教理建設,是根本性、基礎性、標準性、權威性的。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修學淨土法門,有否依《易行品》,其淨土教理必有差異,可謂依《易行品》則是純正的淨土宗,不依《易行品》則非純正的淨土宗,足見其地位之重要。
此品文字不長,故凡有志於淨土之行者,應該閱讀,知其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