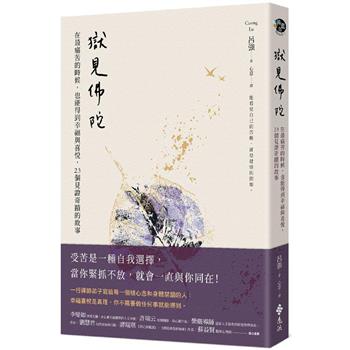24.看見自己的憤怒
我在獄中遇過很多成功人士,漢斯就是其中一位。他第一次參與我們的靜坐冥想小組時大約五十歲,靜坐結束後,他突然一臉驕傲地告訴我:「強,我這輩子從沒生氣過。」
我說:「我不覺得這是真的,我想你只是不曾看見自己的怒氣。」
他聽了很震驚,然後就嚎啕大哭了起來。我讓他繼續哭著,其他的受刑人也都靜靜陪在一旁。漢斯曾經是個龐大家族企業的CEO,也是整個企業管理層中唯一一位不是家族成員的經理人。他很有才華而且極受人們推崇,生活中的一切看起來似乎進行得很順利,不論發生什麼狀況他也都表現得很平靜。
然而有一天,他回到家後便開始毆打女友,女友邊叫邊哭,被他追得滿屋子跑,他就這麼持續傷害她約十分鐘之久。
「你為什麼要傷害我呢?」她問道。然而漢斯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走進警察局自首說:「我差點殺了我女友。」
他告訴我:「我還是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於是,我引導他進行靜坐冥想以及自我觀察,好找尋他的憤怒。然而,他拒絕相信自己有任何怒氣存在。
就在某次的靜坐冥想時段結束之際,他上前擁抱了一位受刑人夥伴,並在他肩上哭了起來。三周後,當我再見到他時,他變得不一樣了。
他跟我回報說:「我碰觸到自己的怒氣了。」這對他來說是重大的發現,因為,藉由正視自己的怒氣,他看見了自己不願接納的某部分人生,而在那瞬間幸福快樂也就綻放了。他開始協助教導其他無法閱讀的受刑人夥伴,也分享了自己對人生的建議。能看到這種轉變實在是太美好了。
他告訴我:「我辛苦打拚了三十年,就是為了建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的事業,而最終一切都付諸流水。看見自己的憤怒,讓我發現到自己內在還有很多部分是我不了解的。雖然失去了一切,但是我找回了自己。出獄後,因為前科紀錄的關係不會有人想雇用我,也許我會成為打掃廁所或做類似工作的人,但我感到幸福快樂。」
「這不代表我將不再受苦,不同的是,如今的我可以看見自己的痛苦。過去的我就是因為看不見自己的痛苦,也看不見自己的憤怒,所以一切才會變得失控瘋狂。也許我很天真,但我覺得現在一切都會安然無恙,因為我已看見自己的苦難,也找到了深刻的幸福喜悅。」34.真正的安全感
艾德是個安靜的男人,我們初見面時他也沒說什麼。就如同其他和我相處的受刑人,他的成長過程也是欠缺關照。我給他愛以及全然的關注,並看見他開始感到有安全感。
孤寂可能是受刑人所面臨最大的痛苦,因為他們必須與家人、朋友分離。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分離感早在他們受到監禁前就產生了。艾德告訴我:「我母親有購物癖。她買的東西堆滿家裡,多到我們連居住的空間都沒有了。」他的痛苦與母親的購物癖無關──他痛苦是因為那股孤寂感。
透過靜坐冥想,艾德得以觸碰自己過去的經歷,感受到自己的怨恨,也感受到了母親的脆弱。隨著我的引導,他寫了封情書給自己的母親,感激她過去雖然也不好過, 卻還是為他付出許多。
經由我們共同的努力,我看著艾德從青少年轉變成一個成年人。以某部分來說,這是做得到的,我看見一個掙扎著找到自己的想法與遠景的成年人。為了自由以及自我的完滿,我們必須為自己著想。
當我看著艾德時,我看見了他的家人、他的祖先,以及這整個社會。艾德入獄不只是因為他做錯事,以某方面來說,是整個社會要為他的行為負責。我們需要運用我們的洞察力,而不是只稱呼艾德的名字「艾德」,他不是孤單的,他代表著我們全部人。
大眾慣於視彼此為「帶有名字的獨立個體」,但是,一旦放下自己的名字、放下自我期盼時,我們就變得單純了。艾德的本性是獨一無二,同時,他也屬於更宏偉事物的一部分,即使法庭判定他有罪,但是在我的心中,他不但是我的一部分,也是全人類的一部分。我只能在看見這個狀態時,才會有辦法幫助艾德。如果沒有把他視為我們的一部分,我也會以艾德所犯的過錯進行批判,然而,這樣的觀點反應出的其實是我個人的侷限。
將認為是邪惡的人關進監獄後,我們往往便覺得自己安全了。然而,我們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罪犯,如果我們不認識這個「自己」,那麼我們還是不安全,因為,像前面提過的漢斯,就是對那個不知打哪來的黑暗情緒摸不著頭緒。除非我們能了解自己,否則,我們也會成為自己孤寂與無知的囚徒。唯有清明的洞察力,且毫不隱藏的自我,才能夠帶給我們真正的安全感。
40.憂鬱症是一種真理
佛教把帶有慾望的幸福,以及不帶有慾望的幸福,區分開來看。前者不是真幸福,因為我們的慾望無窮,總是想要更多,永遠不會得到滿足。佛陀把這種狀態比做狗啃食著一根沒有肉的骨頭,光是啃食骨頭永遠無法滿足狗的飢餓感。在靜坐冥想小組裡,這些受刑人第一次遇見不帶慾望的幸福喜悅感。當你有幸觸及到那種幸福感時,會停止向外找尋,你會知道那就是真正的幸福喜悅。傾聽,有助於他們體驗這種幸福,並成為他們人生的新路標。
許多受刑人容易患上憂鬱症,他們需要不同的能量讓自己往前邁進。我不認為憂鬱症是一種疾病,就佛法來看,憂鬱症是第一真理的一部分,是苦難的體現。苦難是一種真理,不是疾病,這是一個必須被看見和感受到的事實。
只有在不知苦難存在的情況下,苦難才會具有危險性。當我們因憂鬱症而受苦時,那兒存在著我們不願去感受的痛處,也存在著我們還沒學會去面對的苦痛。我們認為自己不夠強大,無法面對它,然而,這是大大地低估了自己。
我們認為憂鬱症是個人問題,然而它也是社會問題。許多囚犯都是獨行俠,也是承載著苦痛的孤獨者,若對自我有這種觀感就會導致憂鬱症的產生。我們要怎麼讓他們知道自己不孤單呢?許多受刑人的家人都讓他們失望,沒人探訪他們,也沒人想念或關心他們。他們會因此感到沮喪也不足為奇。由於這種水平的連結斷開了,因此他們需要的是垂直的連結,垂直的連結來自靜默,也才是真正幸福的源泉。憂鬱症的療癒始於與人產生連結,我曾見過憂鬱症患者與垂直連結完好的人坐在一塊,雖然只有幾分鐘,但他們曾一度從憂鬱症中解脫。
43.惡人和佛陀之間沒有差別(節錄)
在佛教中,真愛、使雙方幸福的愛被稱為「喜」(mudita)。「喜」帶來歡樂、笑聲和滿足感,我們對生命感到滿足。
受刑人經常對許多事物都感到不滿意,包括監獄供應的食物。在荷蘭的監獄裡,他們每天都會收到一個能微波加熱的塑膠便當盒。受刑人告訴我這些食物平淡無味,而且沒有任何營養可言。
當我們學習靜坐冥想時,食物會嘗起來更美味。吉伯特對此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他願意試試。我教他飲食冥想,並建議他吃飯時關掉電視。有些囚犯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與電視為伍,即使睡著了電視還是開著。電視為他們帶來撫慰,以及與生活保持連結的感覺,然而我認為情況恰恰相反。對我來說,電視幫助他們與自己的情感脫節,這樣就不需要與生命有所連結。
吉伯特開始吃飯不看電視,這本身就是個重要的轉變,因為他專注於食用自己的餐點。在進食前,他先練習有意識地呼吸,然後再坐直、專注地進食。這是一個儀式,他很驚訝自己竟然頗喜歡這儀式。
如果我們不懂得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就可能會毀了它。受刑人常將思慮放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卻忘記去回顧自己仍擁有的一切。他們大多都擁有健康,在牢中也努力地保持健康,做了很多體能鍛鍊,如今還願意進行靈性練習。透過呼吸,他們回歸於自身,並開始欣賞所擁有的一切。
他們擁有食物,吉伯特會坐下來,看著他的餐盒,慢慢嘗一口。我建議他咀嚼三十次後再吞嚥,他做到了,而且發現食物確實有些味道了。我相信他不但嘗到了食物的滋味,也嘗到了生活的滋味。他品嘗到滿足感後,生活開始起了變化:他變得更為安靜、更懂得感恩生命。
受刑人常常認為自己只有在出獄後才會開心,而我認為,如果他們現在就對生活不滿意,即使出獄也不會對生活感到滿意。我們總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滿足感。愛上生活是有可能的,這種愛,只有在心滿意足時才可能產生。當我們不滿足時,便無法認清自己的痛苦,也不會知道幸福喜悅為何物。透過鼓勵一個人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感到滿足,我們就能幫助他發現平和。
吉伯特開始會花二十分鐘的時間把飯吃完,過去用不到五分鐘,他就把飯給吞完了。我教了整個靜坐冥想小組如何進行飲食冥想法後,很多人都反應食物變美味了。食物對受刑人來說很重要,而帶有意識地進行飲食,卻是他們從沒想過的一種藝術。他們常在焦慮不安的狀態下進食,我們也低估了好好吃飯所能發揮的力量。我要求他們每天在三餐中至少進行一次飲食冥想,有些人也已養成習慣,並餐餐進行。吉伯特試過一次飲食冥想後,便不再扔掉自己的便當了。
有了喜,我們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以及我們是怎麼樣的人都會感到滿足。當我們感到不滿足時,就會影響我們的睡眠。一些轉介到我們小組的囚犯常有失眠的問題,不過,只要在睡前進行十分鐘的靜坐冥想就能幫助他們睡得更好,冥想時,他們處在當下與自己的苦痛同在。他們為自己而存在,對一切滿足,也帶著深沉的滿足感平等接納幸福喜悅與苦痛。
我在獄中遇過很多成功人士,漢斯就是其中一位。他第一次參與我們的靜坐冥想小組時大約五十歲,靜坐結束後,他突然一臉驕傲地告訴我:「強,我這輩子從沒生氣過。」
我說:「我不覺得這是真的,我想你只是不曾看見自己的怒氣。」
他聽了很震驚,然後就嚎啕大哭了起來。我讓他繼續哭著,其他的受刑人也都靜靜陪在一旁。漢斯曾經是個龐大家族企業的CEO,也是整個企業管理層中唯一一位不是家族成員的經理人。他很有才華而且極受人們推崇,生活中的一切看起來似乎進行得很順利,不論發生什麼狀況他也都表現得很平靜。
然而有一天,他回到家後便開始毆打女友,女友邊叫邊哭,被他追得滿屋子跑,他就這麼持續傷害她約十分鐘之久。
「你為什麼要傷害我呢?」她問道。然而漢斯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走進警察局自首說:「我差點殺了我女友。」
他告訴我:「我還是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於是,我引導他進行靜坐冥想以及自我觀察,好找尋他的憤怒。然而,他拒絕相信自己有任何怒氣存在。
就在某次的靜坐冥想時段結束之際,他上前擁抱了一位受刑人夥伴,並在他肩上哭了起來。三周後,當我再見到他時,他變得不一樣了。
他跟我回報說:「我碰觸到自己的怒氣了。」這對他來說是重大的發現,因為,藉由正視自己的怒氣,他看見了自己不願接納的某部分人生,而在那瞬間幸福快樂也就綻放了。他開始協助教導其他無法閱讀的受刑人夥伴,也分享了自己對人生的建議。能看到這種轉變實在是太美好了。
他告訴我:「我辛苦打拚了三十年,就是為了建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的事業,而最終一切都付諸流水。看見自己的憤怒,讓我發現到自己內在還有很多部分是我不了解的。雖然失去了一切,但是我找回了自己。出獄後,因為前科紀錄的關係不會有人想雇用我,也許我會成為打掃廁所或做類似工作的人,但我感到幸福快樂。」
「這不代表我將不再受苦,不同的是,如今的我可以看見自己的痛苦。過去的我就是因為看不見自己的痛苦,也看不見自己的憤怒,所以一切才會變得失控瘋狂。也許我很天真,但我覺得現在一切都會安然無恙,因為我已看見自己的苦難,也找到了深刻的幸福喜悅。」34.真正的安全感
艾德是個安靜的男人,我們初見面時他也沒說什麼。就如同其他和我相處的受刑人,他的成長過程也是欠缺關照。我給他愛以及全然的關注,並看見他開始感到有安全感。
孤寂可能是受刑人所面臨最大的痛苦,因為他們必須與家人、朋友分離。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分離感早在他們受到監禁前就產生了。艾德告訴我:「我母親有購物癖。她買的東西堆滿家裡,多到我們連居住的空間都沒有了。」他的痛苦與母親的購物癖無關──他痛苦是因為那股孤寂感。
透過靜坐冥想,艾德得以觸碰自己過去的經歷,感受到自己的怨恨,也感受到了母親的脆弱。隨著我的引導,他寫了封情書給自己的母親,感激她過去雖然也不好過, 卻還是為他付出許多。
經由我們共同的努力,我看著艾德從青少年轉變成一個成年人。以某部分來說,這是做得到的,我看見一個掙扎著找到自己的想法與遠景的成年人。為了自由以及自我的完滿,我們必須為自己著想。
當我看著艾德時,我看見了他的家人、他的祖先,以及這整個社會。艾德入獄不只是因為他做錯事,以某方面來說,是整個社會要為他的行為負責。我們需要運用我們的洞察力,而不是只稱呼艾德的名字「艾德」,他不是孤單的,他代表著我們全部人。
大眾慣於視彼此為「帶有名字的獨立個體」,但是,一旦放下自己的名字、放下自我期盼時,我們就變得單純了。艾德的本性是獨一無二,同時,他也屬於更宏偉事物的一部分,即使法庭判定他有罪,但是在我的心中,他不但是我的一部分,也是全人類的一部分。我只能在看見這個狀態時,才會有辦法幫助艾德。如果沒有把他視為我們的一部分,我也會以艾德所犯的過錯進行批判,然而,這樣的觀點反應出的其實是我個人的侷限。
將認為是邪惡的人關進監獄後,我們往往便覺得自己安全了。然而,我們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罪犯,如果我們不認識這個「自己」,那麼我們還是不安全,因為,像前面提過的漢斯,就是對那個不知打哪來的黑暗情緒摸不著頭緒。除非我們能了解自己,否則,我們也會成為自己孤寂與無知的囚徒。唯有清明的洞察力,且毫不隱藏的自我,才能夠帶給我們真正的安全感。
40.憂鬱症是一種真理
佛教把帶有慾望的幸福,以及不帶有慾望的幸福,區分開來看。前者不是真幸福,因為我們的慾望無窮,總是想要更多,永遠不會得到滿足。佛陀把這種狀態比做狗啃食著一根沒有肉的骨頭,光是啃食骨頭永遠無法滿足狗的飢餓感。在靜坐冥想小組裡,這些受刑人第一次遇見不帶慾望的幸福喜悅感。當你有幸觸及到那種幸福感時,會停止向外找尋,你會知道那就是真正的幸福喜悅。傾聽,有助於他們體驗這種幸福,並成為他們人生的新路標。
許多受刑人容易患上憂鬱症,他們需要不同的能量讓自己往前邁進。我不認為憂鬱症是一種疾病,就佛法來看,憂鬱症是第一真理的一部分,是苦難的體現。苦難是一種真理,不是疾病,這是一個必須被看見和感受到的事實。
只有在不知苦難存在的情況下,苦難才會具有危險性。當我們因憂鬱症而受苦時,那兒存在著我們不願去感受的痛處,也存在著我們還沒學會去面對的苦痛。我們認為自己不夠強大,無法面對它,然而,這是大大地低估了自己。
我們認為憂鬱症是個人問題,然而它也是社會問題。許多囚犯都是獨行俠,也是承載著苦痛的孤獨者,若對自我有這種觀感就會導致憂鬱症的產生。我們要怎麼讓他們知道自己不孤單呢?許多受刑人的家人都讓他們失望,沒人探訪他們,也沒人想念或關心他們。他們會因此感到沮喪也不足為奇。由於這種水平的連結斷開了,因此他們需要的是垂直的連結,垂直的連結來自靜默,也才是真正幸福的源泉。憂鬱症的療癒始於與人產生連結,我曾見過憂鬱症患者與垂直連結完好的人坐在一塊,雖然只有幾分鐘,但他們曾一度從憂鬱症中解脫。
43.惡人和佛陀之間沒有差別(節錄)
在佛教中,真愛、使雙方幸福的愛被稱為「喜」(mudita)。「喜」帶來歡樂、笑聲和滿足感,我們對生命感到滿足。
受刑人經常對許多事物都感到不滿意,包括監獄供應的食物。在荷蘭的監獄裡,他們每天都會收到一個能微波加熱的塑膠便當盒。受刑人告訴我這些食物平淡無味,而且沒有任何營養可言。
當我們學習靜坐冥想時,食物會嘗起來更美味。吉伯特對此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他願意試試。我教他飲食冥想,並建議他吃飯時關掉電視。有些囚犯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與電視為伍,即使睡著了電視還是開著。電視為他們帶來撫慰,以及與生活保持連結的感覺,然而我認為情況恰恰相反。對我來說,電視幫助他們與自己的情感脫節,這樣就不需要與生命有所連結。
吉伯特開始吃飯不看電視,這本身就是個重要的轉變,因為他專注於食用自己的餐點。在進食前,他先練習有意識地呼吸,然後再坐直、專注地進食。這是一個儀式,他很驚訝自己竟然頗喜歡這儀式。
如果我們不懂得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就可能會毀了它。受刑人常將思慮放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卻忘記去回顧自己仍擁有的一切。他們大多都擁有健康,在牢中也努力地保持健康,做了很多體能鍛鍊,如今還願意進行靈性練習。透過呼吸,他們回歸於自身,並開始欣賞所擁有的一切。
他們擁有食物,吉伯特會坐下來,看著他的餐盒,慢慢嘗一口。我建議他咀嚼三十次後再吞嚥,他做到了,而且發現食物確實有些味道了。我相信他不但嘗到了食物的滋味,也嘗到了生活的滋味。他品嘗到滿足感後,生活開始起了變化:他變得更為安靜、更懂得感恩生命。
受刑人常常認為自己只有在出獄後才會開心,而我認為,如果他們現在就對生活不滿意,即使出獄也不會對生活感到滿意。我們總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滿足感。愛上生活是有可能的,這種愛,只有在心滿意足時才可能產生。當我們不滿足時,便無法認清自己的痛苦,也不會知道幸福喜悅為何物。透過鼓勵一個人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感到滿足,我們就能幫助他發現平和。
吉伯特開始會花二十分鐘的時間把飯吃完,過去用不到五分鐘,他就把飯給吞完了。我教了整個靜坐冥想小組如何進行飲食冥想法後,很多人都反應食物變美味了。食物對受刑人來說很重要,而帶有意識地進行飲食,卻是他們從沒想過的一種藝術。他們常在焦慮不安的狀態下進食,我們也低估了好好吃飯所能發揮的力量。我要求他們每天在三餐中至少進行一次飲食冥想,有些人也已養成習慣,並餐餐進行。吉伯特試過一次飲食冥想後,便不再扔掉自己的便當了。
有了喜,我們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以及我們是怎麼樣的人都會感到滿足。當我們感到不滿足時,就會影響我們的睡眠。一些轉介到我們小組的囚犯常有失眠的問題,不過,只要在睡前進行十分鐘的靜坐冥想就能幫助他們睡得更好,冥想時,他們處在當下與自己的苦痛同在。他們為自己而存在,對一切滿足,也帶著深沉的滿足感平等接納幸福喜悅與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