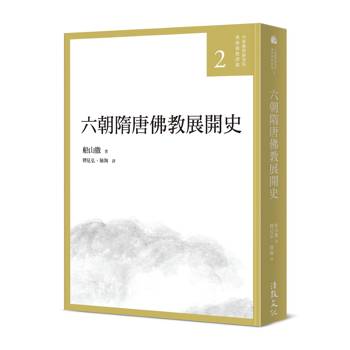〔前言〕
本書是從筆者西元二○○○年以後不定期撰寫的論文中選出十二篇,依照彼此的關聯性編排而成的一部論文集。
筆者的研究經歷與一般常規略有不同,這也影響了筆者的視角及方法論。筆者憧憬高中時代讀過的福永光司譯《莊子內篇》的世界,入學於遠離家鄉的京都大學。幾經周折,最後筆者主要的研習對象不是中國思想,而是印度佛教,而且是以完全沒有漢譯可以參照的七世紀法稱和八世紀後半期蓮華戒的經量部、瑜伽行派思想為主題,完成了佛教學的碩士課程。然而,在那之後,或許該說是機緣巧合吧,筆者攻讀研究生院博士課程一年半後就輟學了,並在校內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部擔任中國佛教研究助手長達十年。通過這段時間的工作經歷,得以深入學習中國學的基礎知識以及風格鮮明的漢譯佛典的閱讀方法。之後,筆者調離該研究所,在九州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講座(譯案:日本大學的講座相當於臺灣的系所,船山教授曾任九州大學助教授,相當臺灣的副教授)獲得從事於印度西藏佛教研究的機會,但不久後又回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因此再度回歸中國學的世界。那是西元二○○○年四月一日的事。從那以後,在該研究所度過了十九年,直到現在。筆者這樣的背景,養成在閱讀漢語佛典的同時,也不斷關注它們與印度之關連性的習慣。
筆者目前研究的課題是,將漢文化圈在六朝時代,特別是從南朝中後期到盛唐(西元約四世紀末到八世紀前半期)所展開的各種佛教現象作為總體來掌握。在此過程中,將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聯繫起來,並有意識地緊扣佛教文化從印度原封不動傳到中國的一面,以及在中國發生變革的一面。這個視角至今沒有改變,今後可能也會持續下去。
關於書名
本書特別從教理解釋學、修行體系、信仰等三方面來處理以南朝宋(劉宋,四二○~七九)、齊(南齊,四七九~五○二)、梁(五○二~五七)三個王朝為中心的整個六朝時期以及隋唐時期的佛教。雖未明確規定時間下限,但以唐代智昇《開元釋教錄》所成的開元十八年(七三○)作為暫時的分界點,以其前的時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這個時期在漫長的中國佛教史中,是所謂的漢譯佛典相繼問世之時,著名的漢譯者鳩摩羅什(約三五○~四○九)、曇無讖(三八五~四三三)、真諦(四九九~五六九)、玄奘(六○○╱六○二~六四)、義淨(六三五~七一三)以及其他諸多翻譯家,陸續產生新的漢譯經典的輝煌時代(關於佛典漢譯史的概略與特色,敬請參考本書末「文獻與略號」所示的船山,二○一三a)。本書的課題就時代而言,單純以《六朝隋唐佛教史》為題也許是直截了當的,但筆者特意加上「展開」二字為《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實有其用意,故於以下略加說明。
從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開始,中國佛教延續至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在此漫長時間內,自六朝時期到盛唐中期編纂《開元釋教錄》為止的這段期間(約西元二二○年到七三○年),從宏觀的角度,可算是中國佛教的早期或前期階段。因此,六朝隋唐的佛教史與其稱之為「展開史」或「發展史」,不如說是「引進史」。至少對於六朝佛教而言,這樣的說法更為貼切。然而,作為一個從印度佛教起步,後來又將視野擴展到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者,筆者深感中國佛教史不應被視為完全獨立於印度之外的單獨佛教史。確實,雖然時期上比較早,但伴隨著印度佛教傳入的同時,六朝隋唐佛教史在與印度不同的中國文化圈中,鮮明地展現出漢語及基於漢語思考模式的具體風貌。從這個意義上講,六朝隋唐佛教史是一個不斷努力於適應漢文化中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史,其中蘊含了印度佛教沒有的新趨勢以及中國獨有的創新和活力。因此,筆者認為六朝隋唐佛教史應被視為是在中國這一新文化中不斷往前變遷的躍動時期。這也是《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一書名中包含「展開」一詞的原因所在。
各篇各章概要
本書如篇名所示,由三個主軸構成。
第一篇名為「佛典解釋的基礎」,若從唐朝玄奘到玄宗治下之開元年間佛教的黃金時代來看,南朝的四個王朝(宋、齊、梁、陳)是形成中國佛教獨特發展的基礎時代,本篇將特別探討南朝,尤其是梁代佛教的教理學特徵。
第一篇分為五章。第一章〈梁代的學術佛教〉指出唐代佛教所呈現的中國特色,其原型大多源自梁代。具體地說,從五世紀下半葉的劉宋後半到梁代,新的漢譯事業數量減少了(船山二○一三a,三十六~三十八頁、二四二~二四五頁)。因此,對現有漢譯的佛典進行重新整理。結果,梁代佛教影響隋唐時期的中國特色,包括音義書、科段分類等中國特有的注釋形態,以及以「體」和「用」作為對立概念的中國式邏輯,還有將佛書統稱為「眾經」,以及收藏佛書的場所如「經藏」、「經臺」、「般若臺」等稱呼,這些梁代所形成的特色,奠定了隋唐佛教的基礎。總的來說,本章討論了梁代佛教如何成為後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基石。
第二章〈體用思想的起源〉,探討了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至關重要的「體」和「用」兩個獨特語法形成的早期歷史。結論是,體用對舉並非起源於儒學或老莊思想,而很可能起源於西元五○○年左右在佛教界掀起廣泛討論的,基於神不滅論之「如來藏」學說的闡述文脈中。
第三章〈「如是我聞」和「如是我聞一時」──經典解釋的基礎性反思〉,探討了佛教經典開頭常見的定型句「如是我聞」的解釋。以往的研究僅考慮印度梵語文獻,並認為在漢語文獻中找不到「如是我聞一時」這樣的表述,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本章則通過探討六朝佛教史中出現過將「如是我聞一時」視為一個完整句子的解釋法,試圖對中國佛教經典的解釋史進行根本性的檢討與重新評價。
第四章〈梁代智藏的《成實論大義記》〉,指出該書是梁前半期出現的一種新形式的漢譯經論解釋方法,它並不是對鳩摩羅什譯《成實論》的逐字注釋,而是對整個《成實論》所涉及的術語和概念進行整理的注解書。此外,本章還盡可能全面地收錄了《成實論大義記》的佚文(後代引用的片段),以便提供更完整的資料。
以上的四章主要為以梁代為主的論考,相對於這幾章,第五章〈真諦三藏的活動與著作〉則綜合考察了真諦三藏於梁末至陳初期間在推廣新教理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自古以來,真諦一直以作為譯經僧而聞名,然而除了翻譯經典之外,真諦還將自己對經典論書的注釋教授給弟子,而與其他漢譯者有所不同。本章從這一觀點出發,整理了印度僧人真諦使用漢語所進行的注釋內容,並探討了他的注釋作品的意義。
其次,第二篇「敘述修行的文獻、體系的修行論以及修行成果」是以第一篇佛教經典教理解釋為基礎,探討了身體修行與相關的僧尼傳記,以及由修行所帶來的宗教體驗等相關文獻。
第二篇共分為四章。前兩章將概述印度的佛教戒律在中國佛教史上被接受的情況。首先,第一章〈隋唐以前的戒律接受史(概觀)〉,將佛教戒律的兩個面向合併起來進行通史性研究。第一個面向是《律》(vinaya)的漢譯史。自初期佛教以來,不論大、小乘所有的佛教出家人都應該遵守的。《律》是出家教團應遵守的生活規則,它的漢譯集中在五世紀前半葉。第二個面向是大乘佛教徒應遵守的大乘特有的生活規則,即菩薩戒。菩薩戒是作為大乘理想形象的菩薩每天所該遵守的德目,在大乘中被視為是比《律》更高階的生活規則。此菩薩戒稍晚於《律》,以一種在《律》基礎上添加新資訊的形式,從五世紀中期到後半期為中國人所知。透過以上兩個面向,本章通史性地論述五至六世紀戒律資訊的傳播與展開。第二章〈大乘的菩薩戒(概觀)〉,專注於第一章所涉及的第二個面向即「菩薩戒」,進行更深入的概說,其中包括了與印度佛教的關係和與菩薩戒這一特殊戒律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第三章〈梁代僧祐的《薩婆多師資傳》〉,以代表梁初的學僧僧祐失傳的著作《薩婆多師資傳》為研究對象。《薩婆多師資傳》不是漢譯,而是僧祐用漢語撰寫的文獻,作為第一章提到的第一個面向的中國編纂文獻,具有深遠的意義。本章將對該書的內容進行解說,並輯錄戒律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佚文片段。
第四章〈隋唐以前的破戒與異端〉,不是從正面闡述戒律的意義,而是從反面,即違反戒律來烘托出戒律的意義。六朝時期的佛教徒—實際上當說包括之後的整個中國佛教—主要是奉行大乘佛教的信徒。因此,雖然有些行為或現象違反了傳統小乘《律》,但在大乘教理中卻被肯定。本章將介紹殺生、性關係等破戒行為以及與實踐菩薩行相關的逸事。
本書最後主軸的第三篇「修行與信仰」,目的在探討「修行」,亦即是以前一篇考察過的戒律為基礎的修行,特別是與菩薩的「修行」有關的諸多樣貌,以及形成此修行基礎的「信仰」之實際情況。
第一章〈聖者觀的兩個系統〉,探討了貫穿於六朝隋唐時期的大乘聖者的定義、實例以及其背後的修行體系。經過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六朝隋唐佛教的聖者,是指那些能夠超越凡夫的大乘修行者,具體來說就是初地及初地以上的菩薩。而且,對於能否達到這種至高境界的觀點上,存在著兩種思潮。一種思潮認為有很多的聖者存在於世上,另一種嚴格的思潮則認為能夠成為聖者的人實際上極為罕見,只有極少的例外修行者可以達成。筆者證實了這兩種思潮同時存在,並深切關注了它們在思想史上的意義。第二章〈異香—聖者的氣味〉與前一章第十節「『異香,滿室』—聖的現前」中所處理的內容相同,但加入了前一章節中未涉及的中國禪宗聖者的傳說,並以綜合性的、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現這些內容。第三章〈捨身思想—極端的佛教行為〉則著重在探討「捨身」一詞的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指為了他人或佛法而犧牲自己身體的行為之意,另一種情況是指將自己的所有物或財產喜捨於寺院之意,以此作為捨棄自我的象徵。後一種情況中所意味的「捨身」,六朝時期,在以梁武帝為首的在家佛教信徒中時常可見。這是一種非常極端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布施行為,本章中將通過許多事例來加以闡述。同時,本章還將探討捨身行為是否等同自殺等相關議題,提供讀者更深入的思考。
本書是從筆者西元二○○○年以後不定期撰寫的論文中選出十二篇,依照彼此的關聯性編排而成的一部論文集。
筆者的研究經歷與一般常規略有不同,這也影響了筆者的視角及方法論。筆者憧憬高中時代讀過的福永光司譯《莊子內篇》的世界,入學於遠離家鄉的京都大學。幾經周折,最後筆者主要的研習對象不是中國思想,而是印度佛教,而且是以完全沒有漢譯可以參照的七世紀法稱和八世紀後半期蓮華戒的經量部、瑜伽行派思想為主題,完成了佛教學的碩士課程。然而,在那之後,或許該說是機緣巧合吧,筆者攻讀研究生院博士課程一年半後就輟學了,並在校內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部擔任中國佛教研究助手長達十年。通過這段時間的工作經歷,得以深入學習中國學的基礎知識以及風格鮮明的漢譯佛典的閱讀方法。之後,筆者調離該研究所,在九州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講座(譯案:日本大學的講座相當於臺灣的系所,船山教授曾任九州大學助教授,相當臺灣的副教授)獲得從事於印度西藏佛教研究的機會,但不久後又回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因此再度回歸中國學的世界。那是西元二○○○年四月一日的事。從那以後,在該研究所度過了十九年,直到現在。筆者這樣的背景,養成在閱讀漢語佛典的同時,也不斷關注它們與印度之關連性的習慣。
筆者目前研究的課題是,將漢文化圈在六朝時代,特別是從南朝中後期到盛唐(西元約四世紀末到八世紀前半期)所展開的各種佛教現象作為總體來掌握。在此過程中,將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聯繫起來,並有意識地緊扣佛教文化從印度原封不動傳到中國的一面,以及在中國發生變革的一面。這個視角至今沒有改變,今後可能也會持續下去。
關於書名
本書特別從教理解釋學、修行體系、信仰等三方面來處理以南朝宋(劉宋,四二○~七九)、齊(南齊,四七九~五○二)、梁(五○二~五七)三個王朝為中心的整個六朝時期以及隋唐時期的佛教。雖未明確規定時間下限,但以唐代智昇《開元釋教錄》所成的開元十八年(七三○)作為暫時的分界點,以其前的時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這個時期在漫長的中國佛教史中,是所謂的漢譯佛典相繼問世之時,著名的漢譯者鳩摩羅什(約三五○~四○九)、曇無讖(三八五~四三三)、真諦(四九九~五六九)、玄奘(六○○╱六○二~六四)、義淨(六三五~七一三)以及其他諸多翻譯家,陸續產生新的漢譯經典的輝煌時代(關於佛典漢譯史的概略與特色,敬請參考本書末「文獻與略號」所示的船山,二○一三a)。本書的課題就時代而言,單純以《六朝隋唐佛教史》為題也許是直截了當的,但筆者特意加上「展開」二字為《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實有其用意,故於以下略加說明。
從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開始,中國佛教延續至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在此漫長時間內,自六朝時期到盛唐中期編纂《開元釋教錄》為止的這段期間(約西元二二○年到七三○年),從宏觀的角度,可算是中國佛教的早期或前期階段。因此,六朝隋唐的佛教史與其稱之為「展開史」或「發展史」,不如說是「引進史」。至少對於六朝佛教而言,這樣的說法更為貼切。然而,作為一個從印度佛教起步,後來又將視野擴展到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者,筆者深感中國佛教史不應被視為完全獨立於印度之外的單獨佛教史。確實,雖然時期上比較早,但伴隨著印度佛教傳入的同時,六朝隋唐佛教史在與印度不同的中國文化圈中,鮮明地展現出漢語及基於漢語思考模式的具體風貌。從這個意義上講,六朝隋唐佛教史是一個不斷努力於適應漢文化中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史,其中蘊含了印度佛教沒有的新趨勢以及中國獨有的創新和活力。因此,筆者認為六朝隋唐佛教史應被視為是在中國這一新文化中不斷往前變遷的躍動時期。這也是《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一書名中包含「展開」一詞的原因所在。
各篇各章概要
本書如篇名所示,由三個主軸構成。
第一篇名為「佛典解釋的基礎」,若從唐朝玄奘到玄宗治下之開元年間佛教的黃金時代來看,南朝的四個王朝(宋、齊、梁、陳)是形成中國佛教獨特發展的基礎時代,本篇將特別探討南朝,尤其是梁代佛教的教理學特徵。
第一篇分為五章。第一章〈梁代的學術佛教〉指出唐代佛教所呈現的中國特色,其原型大多源自梁代。具體地說,從五世紀下半葉的劉宋後半到梁代,新的漢譯事業數量減少了(船山二○一三a,三十六~三十八頁、二四二~二四五頁)。因此,對現有漢譯的佛典進行重新整理。結果,梁代佛教影響隋唐時期的中國特色,包括音義書、科段分類等中國特有的注釋形態,以及以「體」和「用」作為對立概念的中國式邏輯,還有將佛書統稱為「眾經」,以及收藏佛書的場所如「經藏」、「經臺」、「般若臺」等稱呼,這些梁代所形成的特色,奠定了隋唐佛教的基礎。總的來說,本章討論了梁代佛教如何成為後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基石。
第二章〈體用思想的起源〉,探討了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至關重要的「體」和「用」兩個獨特語法形成的早期歷史。結論是,體用對舉並非起源於儒學或老莊思想,而很可能起源於西元五○○年左右在佛教界掀起廣泛討論的,基於神不滅論之「如來藏」學說的闡述文脈中。
第三章〈「如是我聞」和「如是我聞一時」──經典解釋的基礎性反思〉,探討了佛教經典開頭常見的定型句「如是我聞」的解釋。以往的研究僅考慮印度梵語文獻,並認為在漢語文獻中找不到「如是我聞一時」這樣的表述,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本章則通過探討六朝佛教史中出現過將「如是我聞一時」視為一個完整句子的解釋法,試圖對中國佛教經典的解釋史進行根本性的檢討與重新評價。
第四章〈梁代智藏的《成實論大義記》〉,指出該書是梁前半期出現的一種新形式的漢譯經論解釋方法,它並不是對鳩摩羅什譯《成實論》的逐字注釋,而是對整個《成實論》所涉及的術語和概念進行整理的注解書。此外,本章還盡可能全面地收錄了《成實論大義記》的佚文(後代引用的片段),以便提供更完整的資料。
以上的四章主要為以梁代為主的論考,相對於這幾章,第五章〈真諦三藏的活動與著作〉則綜合考察了真諦三藏於梁末至陳初期間在推廣新教理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自古以來,真諦一直以作為譯經僧而聞名,然而除了翻譯經典之外,真諦還將自己對經典論書的注釋教授給弟子,而與其他漢譯者有所不同。本章從這一觀點出發,整理了印度僧人真諦使用漢語所進行的注釋內容,並探討了他的注釋作品的意義。
其次,第二篇「敘述修行的文獻、體系的修行論以及修行成果」是以第一篇佛教經典教理解釋為基礎,探討了身體修行與相關的僧尼傳記,以及由修行所帶來的宗教體驗等相關文獻。
第二篇共分為四章。前兩章將概述印度的佛教戒律在中國佛教史上被接受的情況。首先,第一章〈隋唐以前的戒律接受史(概觀)〉,將佛教戒律的兩個面向合併起來進行通史性研究。第一個面向是《律》(vinaya)的漢譯史。自初期佛教以來,不論大、小乘所有的佛教出家人都應該遵守的。《律》是出家教團應遵守的生活規則,它的漢譯集中在五世紀前半葉。第二個面向是大乘佛教徒應遵守的大乘特有的生活規則,即菩薩戒。菩薩戒是作為大乘理想形象的菩薩每天所該遵守的德目,在大乘中被視為是比《律》更高階的生活規則。此菩薩戒稍晚於《律》,以一種在《律》基礎上添加新資訊的形式,從五世紀中期到後半期為中國人所知。透過以上兩個面向,本章通史性地論述五至六世紀戒律資訊的傳播與展開。第二章〈大乘的菩薩戒(概觀)〉,專注於第一章所涉及的第二個面向即「菩薩戒」,進行更深入的概說,其中包括了與印度佛教的關係和與菩薩戒這一特殊戒律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第三章〈梁代僧祐的《薩婆多師資傳》〉,以代表梁初的學僧僧祐失傳的著作《薩婆多師資傳》為研究對象。《薩婆多師資傳》不是漢譯,而是僧祐用漢語撰寫的文獻,作為第一章提到的第一個面向的中國編纂文獻,具有深遠的意義。本章將對該書的內容進行解說,並輯錄戒律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佚文片段。
第四章〈隋唐以前的破戒與異端〉,不是從正面闡述戒律的意義,而是從反面,即違反戒律來烘托出戒律的意義。六朝時期的佛教徒—實際上當說包括之後的整個中國佛教—主要是奉行大乘佛教的信徒。因此,雖然有些行為或現象違反了傳統小乘《律》,但在大乘教理中卻被肯定。本章將介紹殺生、性關係等破戒行為以及與實踐菩薩行相關的逸事。
本書最後主軸的第三篇「修行與信仰」,目的在探討「修行」,亦即是以前一篇考察過的戒律為基礎的修行,特別是與菩薩的「修行」有關的諸多樣貌,以及形成此修行基礎的「信仰」之實際情況。
第一章〈聖者觀的兩個系統〉,探討了貫穿於六朝隋唐時期的大乘聖者的定義、實例以及其背後的修行體系。經過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六朝隋唐佛教的聖者,是指那些能夠超越凡夫的大乘修行者,具體來說就是初地及初地以上的菩薩。而且,對於能否達到這種至高境界的觀點上,存在著兩種思潮。一種思潮認為有很多的聖者存在於世上,另一種嚴格的思潮則認為能夠成為聖者的人實際上極為罕見,只有極少的例外修行者可以達成。筆者證實了這兩種思潮同時存在,並深切關注了它們在思想史上的意義。第二章〈異香—聖者的氣味〉與前一章第十節「『異香,滿室』—聖的現前」中所處理的內容相同,但加入了前一章節中未涉及的中國禪宗聖者的傳說,並以綜合性的、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現這些內容。第三章〈捨身思想—極端的佛教行為〉則著重在探討「捨身」一詞的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指為了他人或佛法而犧牲自己身體的行為之意,另一種情況是指將自己的所有物或財產喜捨於寺院之意,以此作為捨棄自我的象徵。後一種情況中所意味的「捨身」,六朝時期,在以梁武帝為首的在家佛教信徒中時常可見。這是一種非常極端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布施行為,本章中將通過許多事例來加以闡述。同時,本章還將探討捨身行為是否等同自殺等相關議題,提供讀者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