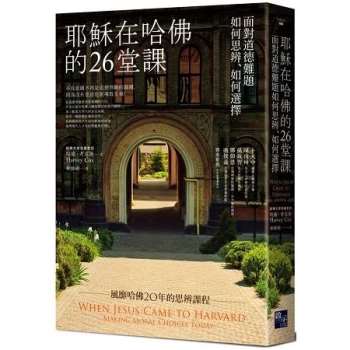前言
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我發現自己陷入這些混亂潮流之中。當時哈佛大學剛在大學必修學分中增設道德判斷課程,同事請我開一門關於耶穌的課。學校當局之所以有此決定,原因是教職員認為哈佛不能再忽視這股日益嚴重的窘境:我們為何愈來愈常聽到內線交易、司法黑幕、醫生注重利潤甚於病患、科學家捏造資料的事情? 更糟的是,為何某些元兇還是哈佛校友? 為何這麼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做出壞事? 我們灌輸給學生的教育是否少了什麼?
我們明白,哈佛已訓練他們可以精確運用人文與科學素養。他們知道美國內戰的肇因,也能寫出流暢的化學實驗摘要;但是我們發現,哈佛根本沒教導他們如何以負責的道德態度運用專業學養。他們漸漸成為專業人才,但在價值觀方面卻是新手。因此校方決定,此後每個學生畢業前,都得修過至少一堂的道德判斷課程。這只是一小步,我們試圖治療的病症不只危害學生,還影響整個社會。當時教職員委員會便請我增設一堂課,教學內容就以道德典範與基督的教義為主。
我卻沒他們那麼有信心。我不確定道德觀可以在課堂上教授,而且我懷疑這應該由宗教機構或家長教導兒童,而非由老師教導青少年。此外我還有其他疑慮:道德判斷、道德信念與道德勇氣之間有何關係? 例如理論上而言,學生會不會一邊培養出超高的道德判斷技巧,一邊照樣考試作弊? 我們培養出的新一批校友,會不會只是表面上口若懸河地討論道德議題,心裡卻不甚相信呢? 這種所謂的詭辯法,不就是雅典青年教育中最令蘇格拉底惱火的一點嗎? 道德勇氣又要怎麼教呢? 課堂上要如何培養這種膽量?
我的顧慮還有:為了提供廣泛選擇給學生,道德判斷的課程還有好幾門。在設計似乎毫無共通點的各種選修課時,校方會不會一時疏忽而重複他們極力想避免的自助餐式道德觀呢?「我想想,我到底比較喜歡康德強調義務的課,還是彌爾的實用主義? 選亞里斯多德,還是阿奎那?」這種多樣性的選擇,提供了模稜兩可的道德相對主義,難道這不就是校方想挑戰的問題嗎?
我在咖啡廳向同事提出這些看法,他們都已經開了道德判斷的相關課程,也努力安撫我。他們說,我們只能希望教導學生清楚思考道德問題。同事認為,只要我們透過選擇幫助他們開口討論,闡述道德立據,學生就能在這方面有所精進,如同他們在實驗室磨練觀察本領、在樂團或合唱團培養音樂素養、在體育場鍛鍊運動技巧……但是這不足以說服我。我認為如果沒有一些共同基礎,道德論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學生可能會發現,自己在道德模糊的環境中更無所適從。
我還預見另一個問題。我們的學生可能信仰各種宗教,也可能沒有信仰,對許多道德問題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校方建議我介紹耶穌的道德看法,對象不只是接受基督宗教教義(例如道成肉身、死而復生)的學生,還包括不是基督徒的同學。我說我的確可以試試看,但是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經行之有年。許多人認為,除非相信耶穌的教義,否則耶穌的道德訓誨便毫無意義,而這些人的確不是無的放矢。耶穌的確將佈道內容個人化,甚至以自己當作所要傳達之啟示的主角。
另一派人馬的看法則是,有千百萬人不相信基督宗教教義,卻同樣從耶穌的道德典範或佈道得到啟發;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甘地。我認為自己可以在課堂上介紹上述兩種意見,卻還無法確定是否要開課。不過,我想得愈多,就愈認為希望濃厚,最後儘管態度仍有保留,我還是同意了校方的請求。
我很慶幸自己答應了。打從一開課就知道,這不是普通課程。第一學期便有許多學生選修,幾年後,竟然每年都有七、八百名學生。沒多久之後,連來訪學者、後博士班的科學研究人員、在職外交官、都市計畫人員、記者……也紛紛加入。無論哈佛內外,只要是認定本校講究教育與宗教分家的人,都很意外這堂課的人數竟然急速增加。課程名字有「耶穌」又有「道德」,怎麼會有這麼多學生選修呢? 吃驚的人顯然錯估這一代學生的意願,也誤判時代趨勢。
我在大學部開的第一堂課是「耶穌與道德生活」,學生多半介於十七歲至二十二歲。以前我的學生多半是研究生,因此起初我相當憂心。我希望上課題材與他們的生活有關聯,但是節奏迅速的青少年文化對我而言既陌生又可怕。我聽過的歌不是他們喜愛的音樂,而是學生的父母輩在聽的。他們看的電影正是我敬謝不敏的作品,我最喜歡的近代樂團是披頭四。我不確定自己談論耶穌的方法,他們的世界究竟能不能理解。
然而課程一開始,我就拋開疑慮,期待上課,尤其是討論會,我的學生都非常喜愛。校方的確要求他們選修道德判斷的課程,但是他們根本稱不上行為不端。他們很聰明、健談、努力,而且非常執意要做「正確的事情」。他們身上沒有常見的道德危機特徵,然而我看得出他們相當困惑。
人類文化學、哲學、心理學、歷史與社會學的課,讓許多人以為道德觀「沒有必然性」,會因時代、社會、個人而有所不同。我們有何資格質疑南海島民不拘形式的性愛風俗? 或是批評奈斯基里克的愛斯基摩人鼓勵長者漫步到雪地上等死的風俗? 我們怎能評斷羅馬百夫長摧毀耶路撒冷,或是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征服者燒毀特諾克蒂特蘭? 我們怎能挑剔同學的「私生活」,如果他們並未打擾到我們,或是導致我們違背良心,就算嗑藥或性生活放蕩又如何? 上科學課程時,老師都鼓勵學生專心觀察,不要質疑實驗數據。然而他們在實驗室也會很快察覺某些學者的觀念—亦即從事研究的人無須擔心手邊實驗在未來的用途是否有害──這種想法雖然普遍,有時卻只能心照不宣。簡而言之,他們接受的教育雖然傑出,卻與道德完全無關。
總之,學生本身對此有強烈的缺憾感。「我知道不該去勢,但是我無法說出個所以然。」某個典型的大四學生到荒涼的訓練團大樓參加討論時,便有此感想。這些學生跟愈來愈多的現代人一樣,發現道德相對主義在基本意義上有些不妥。他們厭惡某些科技對大自然的破壞,看膩政客的虛假與媒體的謊言。他們明白,廣告不過是精心計算過的手段。然而在和別人開口討論真正的道德抉擇時,他們卻尷尬詞窮。只不過想找個道德詞彙表達意見,就讓他們口吃又不安,最後往往放棄,有時只能搖頭說:「一切都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出發。」但是他們知道某些事情「絕對不應該」──例如虐待兒童,無論你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一樣。他們痛恨別人拿自己的道德標準硬套在他們身上,多數人也不願意強迫別人遵從自己的守則。「給自己與他人生存空間」是他們的金科玉律。簡而言之,他們就是我所謂的「善意卻又不安」的相對主義者。
然而,這種善意相對主義的走向也讓學生侷促不安。去勢還是簡單的話題,班上當然沒有一個人贊成。如果是更貼近我們自身的問題呢? 許多人崇拜比爾.蓋茲,但是根據報導,他個人的財產(當時是四百六十億美元)多過美國收入金字塔底端百分之四十家庭的總和;有些人認為不對勁,其他人則不覺得有什麼不可以:難道這不是他自己努力賺來的嗎?
他們爭論了一會便放棄。他們不但無法取得共識,就連討論這種問題也讓他們為難,難道說一句「我就是覺得不對」就可以了嗎? 他們應該勸朋友墮胎(或是別墮胎)嗎? 我們哪有資格數說巴西人能不能摧毀自己的雨林、巴基斯坦人該不該測試核子武器? 恐怖主義與刑求是絕對不行,還是在某些時刻可以通融呢?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切都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出發」,我們又該如何做出一國的決策?
有些學生聽過,只要自問「耶穌會怎麼做?」就能解決所有道德難題。多數人則發現,這個方法並非次次有效,因為耶穌是二十個世紀以前的人,而且當時的生活環境相當不同,耶穌可不必面對學生得處理的惱人問題。他們明白,分隔耶穌與我們之間的歲月就是一大障礙。然而他們在課堂上學到,耶穌是拉比,他並非只是提出答案。相反地,他示範如何做出道德抉擇,學生自己也可以採用。耶穌以神祕的說法與尖銳的比喻要求人們運用想像力,他們發現只要照辦,耶穌所要傳達的啟示的確對我們有所助益。關鍵只在於,我們如何將他的方法與思想翻譯成現代語彙。
近年有大量文獻論述「尋找歷史上的耶穌」,但是這可不是本書的目的,甚至可以說正好相反:這本書的意義是「尋找現代耶穌」,目的就是向二十一世紀介紹一名兩千年前的男子對我們的道德意義。這本書的宗旨,就是這麼直截了當。以下的章節就介紹四部福音書如何記載耶穌的生平,從耶誕故事到復活節記載都兼而有之。本書的焦點在於耶穌本人說過的故事,以及關於他生平的故事。本書會提到學生如何根據這些故事,仔細思考他們所必須面對的道德抉擇,然而他們就跟多數人一樣,有時也會困惑、懷疑、害怕,但是永遠都保持著濃厚的好奇心。書中描述學生各有不同而且往往令人意外的反應,如何促使我自己想得更寬廣、更深刻。此外,本書也記載我們如何按照這些久遠的故事,處理各種現代才有的抉擇。
這些決定都是學生已經碰到,或是知道自己即將面對的問題—隨著人生進入各種階段,我們都會碰上這些問題。
我希望本書可以跨出哈佛校園,激發更多人共同探索;因此各年齡層、各宗教或無宗教背景的讀者都能從這本書走出去,一起加入這趟迫切的探尋之旅。讀者並不需要比我的學生更了解宗教或《聖經》,然而只要是不滿道德基要主義或各行其道的相對論的讀者,本書都歡迎大家一起用嶄新角度觀察第一世紀的拉比,他來自羅馬帝國的偏遠轄區加利利。有人形容他的生平在歷史上最有道德影響力,然而這股影響力的實際功能往往很難判斷。儘管眾人都真正了解所有宗教經文、字句虔誠的保險桿貼紙、耶穌的教義與信條,但本書更大的前提是,這位加利利人對我們的時代仍舊有強而有力、甚至是不容分說的道德意義。
第22章
理智、情感與酷刑
我們對酷刑問題的道德敏感度,如今可能也面臨類似的窘境。儘管自古以來從未消失,人們曾經一度以為酷刑是黑暗時代的遺跡,如今卻因為二十世紀的獨裁者而大剌剌地回到大眾眼前。希特勒的黨羽引進更新、更現代的手法,墨索里尼強餵敵方俘虜喝蓖麻油,史達林將囚犯關在沒有窗戶的牢房,房裡就堆著糞便,拉丁美洲軍事政府則用電擊凌虐囚犯以免留下清楚疤痕。儘管有個推動廢除酷刑的國際組織在法國簽署成立,世人在二○○四年還是心驚膽跳地看到美軍刑求伊拉克囚犯的照片。
酷刑顯然又成為道德考量的議題之一,因此,我很意外聽到有人說艾倫.德蕭威茲教授在新書中公開提倡刑求。畢竟他曾經參與我們的模擬演出,極力為拿撒勒的耶穌辯護,反對他遭凌辱處死。德蕭威茲怎麼說得出這種話? 不會前後矛盾嗎?後來證明,一切純屬謠傳。德蕭威茲的內容其實是,既然自古以來都有酷刑,將來顯然也不會絕跡(而且如今還自稱是根除恐怖主義的手段),那就應該嚴格限制,謹慎規劃。
刑求應該公開進行,經由法律規定,否則只在牢房或暗室進行,便能規避所有責任義務。他引用定時炸彈的舊例加以申論,他說倘若執法人員逮捕某人,而對方的資訊可以預防恐怖炸彈攻擊學校或醫院,避免五千名無辜民眾喪命。如果執法人員只有兩小時打聽重要資訊、拯救眾人,但是囚犯卻不肯透露(要是這顆「定時炸彈」還是核子彈或生化武器,當然又更急迫),這時你該怎麼做?
定時炸彈的故事,是德蕭威茲在課堂上常引用的範例之一,我跟他與已故的史帝芬.傑.顧德(Stephen Jay Gould)一起教授那堂課。德蕭威茲說這些範例是「法學院的假想」,我則認為這些例子證明,故事可以用來教授道德判斷。然而我也常心生懷疑,因為這些假設往往太緊密、太離奇,也就不夠真實。
德蕭威茲本人的解釋是,既然嫌犯知道炸彈藏匿地點,幾乎世上所有警察都會訴諸肢體或心理打壓,以拯救無辜性命。沒錯,否則就枉顧道德責任。然而他又補充(其實這才是論證的精髓,許多人卻聽而不聞),為了避免刑求手法太離譜,也為了避免毫無節制地施以刑求,警方應該申請只准進行一次的「刑求授權書」,才能採取行動,而且手段必須遵照法律規定。這張授權書必須由法官核發,功用類似搜索狀。這張授權書也會規定,可以採取哪些刑求手段。許多讀者只著眼於他所說的某句話(比如他建議在囚犯指甲下插入消毒過的鋼針),卻忽略他論證的全面意義。
我在共同授課的課堂上提出不同意見,結果我很快就發現,討論這個爆炸性話題很難維持理智。我提醒同學,我們有個「聯合國反刑求公約」,而且參議院在一九九四年也批准承認,所以美國境內也有相關的明文法規。然而合法性與道德觀可不一樣,德蕭威茲的提議之目的,便是立法規定高壓訊問。
然而,每個論證都有一個同樣具說服力的反論證,即便睿智的道德思想家瑪莎.努斯鮑姆也說:「任何明智又有操守的人都不會否認,有些假想狀況的確應該(對某個特定人士)採用刑求。」但是大家也知道,遭受刑求的人可能會胡說八道以求逃過凌虐。倘若定時炸彈已經啟動,等到可以驗證供詞真假的時候,一切早就為時晚矣。
此外,還有另一種「滑坡效應」的理論。倘若某些刑求藉由授權書通過法律規定,肯定會廣泛運用在其他案例或是變相行使。法國在這方面就有歷史教訓:儘管該國立法規定刑求手法是為了鎮壓阿爾及利亞叛軍,最後卻運用在整個司法體系,結果一敗塗地,讓法國不但失去阿爾及利亞,刑求手段也導致阿爾及利亞憎恨這個前殖民國數十年之久。以色列以前也准許肢體凌虐,最後也決定立法禁止,然而即便贊成禁止刑求的人也承認,有時候的確可以藉由刑求避免某些恐怖炸彈攻擊。問題關鍵就在於,社會願意犧牲多少人權來換取多大程度的安全。因為這些論證太令人困惑,我們在課堂上的這場辯論也就無法達到結論。
課堂上,支持刑求的主張也時強時弱,因為學生會針對問題的不同層面表示意見。我們在下課前表決德蕭威茲的提議,得票率幾乎是一比一。贊成者採用經典的實用主義邏輯,他們認為這是簡單的數學問題:折磨一人總好過犧牲上千人的性命。然而我還是不甚滿意。我重新引述先前所說的話,也就是請他國代為操刀,結果幾乎所有學生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反對。我又請問他們,如果刑求授權書的法律果真正式上路,誰願意動手將針頭插入嫌犯指甲內? 結果只有幾個人舉手。對那些贊成推動法令卻不肯自己動手的學生,我請他們陳述自己行為的正當性,而且要從道德角度而不是法律角度論述,結果是一片沉默。
我接著又提出另一個問題:假設嫌犯不願意吐實,但是你抓到他的兩名子女—分別是四歲與七歲,你們願意威脅刑求兒童逼供嗎? 畢竟這只是數學問題,兩名孩童暫時的痛苦與五千人的性命怎麼能相提並論? 但是,班上還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傷害兒童。
這類問題很難以理性方法辯論、決定,即便我們在討論時刻意「明理」,助益也不太大。我之所以被迫有這層體驗,是因為那天下課之後,有個學生幾乎是衝到教室前方,憤怒地指著我說:「你將感情因素放進原本應是理性的討論之中。你希望訴諸學生的情感,而非我們的理智!」
這名學生顯然非常激動,而且他的控訴方式也不乏感情因素,但是我還是盡可能理智地回答。我表示他說得對,我的確蓄意加入「情感因素」,因為我認為有其必要。但是,我不接受他所說的情感與理智不該並行。倘若思考推論不帶任何情感,這場討論就沒有活力,單調乏味;反過來說,不加任何理智的情感,就只是歇斯底里或意氣用事。
這名學生顯然是激進的唯理主義者,他並不同意我的說法,態度也相當激動,因為他雙頰漲紅、聲調高亢。他堅決認定學術殿堂不該感情用事,所以我在這場辯論當中的表現並不光明磊落。我微笑地告訴他,我們必須接受別人的不同意見,便向他伸出右手。他稍微猶豫,然後迅速握手,勉強擠出一個微笑。
當我在回家途中想到這件事時,便很感激這個學生勇於提出意見。即便題目是刑求,有些課堂的學生一定只是哈欠連連,不斷看錶。這位先生卻是教授最想要的學生,他不只心裡嘀咕我有違學術殿堂的不成文基本守則,還願意當面告訴我。他也幫助我明白兩個問題:一是這場討論為何如此困難,一是我問學生是否願意親自刑求罪犯或其子女,他們何以立刻改變立場。我相信,在逼供人眼中,他們必須先認為嫌犯只是畜牲。犯人必須先成為敵人、危險嫌犯、非日爾曼人、恐怖份子、不能稱為人的動物。唯有如此,多數人(有些人可能是例外)才能蓄意對他們施加難以忍受的痛苦。
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我發現自己陷入這些混亂潮流之中。當時哈佛大學剛在大學必修學分中增設道德判斷課程,同事請我開一門關於耶穌的課。學校當局之所以有此決定,原因是教職員認為哈佛不能再忽視這股日益嚴重的窘境:我們為何愈來愈常聽到內線交易、司法黑幕、醫生注重利潤甚於病患、科學家捏造資料的事情? 更糟的是,為何某些元兇還是哈佛校友? 為何這麼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做出壞事? 我們灌輸給學生的教育是否少了什麼?
我們明白,哈佛已訓練他們可以精確運用人文與科學素養。他們知道美國內戰的肇因,也能寫出流暢的化學實驗摘要;但是我們發現,哈佛根本沒教導他們如何以負責的道德態度運用專業學養。他們漸漸成為專業人才,但在價值觀方面卻是新手。因此校方決定,此後每個學生畢業前,都得修過至少一堂的道德判斷課程。這只是一小步,我們試圖治療的病症不只危害學生,還影響整個社會。當時教職員委員會便請我增設一堂課,教學內容就以道德典範與基督的教義為主。
我卻沒他們那麼有信心。我不確定道德觀可以在課堂上教授,而且我懷疑這應該由宗教機構或家長教導兒童,而非由老師教導青少年。此外我還有其他疑慮:道德判斷、道德信念與道德勇氣之間有何關係? 例如理論上而言,學生會不會一邊培養出超高的道德判斷技巧,一邊照樣考試作弊? 我們培養出的新一批校友,會不會只是表面上口若懸河地討論道德議題,心裡卻不甚相信呢? 這種所謂的詭辯法,不就是雅典青年教育中最令蘇格拉底惱火的一點嗎? 道德勇氣又要怎麼教呢? 課堂上要如何培養這種膽量?
我的顧慮還有:為了提供廣泛選擇給學生,道德判斷的課程還有好幾門。在設計似乎毫無共通點的各種選修課時,校方會不會一時疏忽而重複他們極力想避免的自助餐式道德觀呢?「我想想,我到底比較喜歡康德強調義務的課,還是彌爾的實用主義? 選亞里斯多德,還是阿奎那?」這種多樣性的選擇,提供了模稜兩可的道德相對主義,難道這不就是校方想挑戰的問題嗎?
我在咖啡廳向同事提出這些看法,他們都已經開了道德判斷的相關課程,也努力安撫我。他們說,我們只能希望教導學生清楚思考道德問題。同事認為,只要我們透過選擇幫助他們開口討論,闡述道德立據,學生就能在這方面有所精進,如同他們在實驗室磨練觀察本領、在樂團或合唱團培養音樂素養、在體育場鍛鍊運動技巧……但是這不足以說服我。我認為如果沒有一些共同基礎,道德論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學生可能會發現,自己在道德模糊的環境中更無所適從。
我還預見另一個問題。我們的學生可能信仰各種宗教,也可能沒有信仰,對許多道德問題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校方建議我介紹耶穌的道德看法,對象不只是接受基督宗教教義(例如道成肉身、死而復生)的學生,還包括不是基督徒的同學。我說我的確可以試試看,但是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經行之有年。許多人認為,除非相信耶穌的教義,否則耶穌的道德訓誨便毫無意義,而這些人的確不是無的放矢。耶穌的確將佈道內容個人化,甚至以自己當作所要傳達之啟示的主角。
另一派人馬的看法則是,有千百萬人不相信基督宗教教義,卻同樣從耶穌的道德典範或佈道得到啟發;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甘地。我認為自己可以在課堂上介紹上述兩種意見,卻還無法確定是否要開課。不過,我想得愈多,就愈認為希望濃厚,最後儘管態度仍有保留,我還是同意了校方的請求。
我很慶幸自己答應了。打從一開課就知道,這不是普通課程。第一學期便有許多學生選修,幾年後,竟然每年都有七、八百名學生。沒多久之後,連來訪學者、後博士班的科學研究人員、在職外交官、都市計畫人員、記者……也紛紛加入。無論哈佛內外,只要是認定本校講究教育與宗教分家的人,都很意外這堂課的人數竟然急速增加。課程名字有「耶穌」又有「道德」,怎麼會有這麼多學生選修呢? 吃驚的人顯然錯估這一代學生的意願,也誤判時代趨勢。
我在大學部開的第一堂課是「耶穌與道德生活」,學生多半介於十七歲至二十二歲。以前我的學生多半是研究生,因此起初我相當憂心。我希望上課題材與他們的生活有關聯,但是節奏迅速的青少年文化對我而言既陌生又可怕。我聽過的歌不是他們喜愛的音樂,而是學生的父母輩在聽的。他們看的電影正是我敬謝不敏的作品,我最喜歡的近代樂團是披頭四。我不確定自己談論耶穌的方法,他們的世界究竟能不能理解。
然而課程一開始,我就拋開疑慮,期待上課,尤其是討論會,我的學生都非常喜愛。校方的確要求他們選修道德判斷的課程,但是他們根本稱不上行為不端。他們很聰明、健談、努力,而且非常執意要做「正確的事情」。他們身上沒有常見的道德危機特徵,然而我看得出他們相當困惑。
人類文化學、哲學、心理學、歷史與社會學的課,讓許多人以為道德觀「沒有必然性」,會因時代、社會、個人而有所不同。我們有何資格質疑南海島民不拘形式的性愛風俗? 或是批評奈斯基里克的愛斯基摩人鼓勵長者漫步到雪地上等死的風俗? 我們怎能評斷羅馬百夫長摧毀耶路撒冷,或是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征服者燒毀特諾克蒂特蘭? 我們怎能挑剔同學的「私生活」,如果他們並未打擾到我們,或是導致我們違背良心,就算嗑藥或性生活放蕩又如何? 上科學課程時,老師都鼓勵學生專心觀察,不要質疑實驗數據。然而他們在實驗室也會很快察覺某些學者的觀念—亦即從事研究的人無須擔心手邊實驗在未來的用途是否有害──這種想法雖然普遍,有時卻只能心照不宣。簡而言之,他們接受的教育雖然傑出,卻與道德完全無關。
總之,學生本身對此有強烈的缺憾感。「我知道不該去勢,但是我無法說出個所以然。」某個典型的大四學生到荒涼的訓練團大樓參加討論時,便有此感想。這些學生跟愈來愈多的現代人一樣,發現道德相對主義在基本意義上有些不妥。他們厭惡某些科技對大自然的破壞,看膩政客的虛假與媒體的謊言。他們明白,廣告不過是精心計算過的手段。然而在和別人開口討論真正的道德抉擇時,他們卻尷尬詞窮。只不過想找個道德詞彙表達意見,就讓他們口吃又不安,最後往往放棄,有時只能搖頭說:「一切都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出發。」但是他們知道某些事情「絕對不應該」──例如虐待兒童,無論你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一樣。他們痛恨別人拿自己的道德標準硬套在他們身上,多數人也不願意強迫別人遵從自己的守則。「給自己與他人生存空間」是他們的金科玉律。簡而言之,他們就是我所謂的「善意卻又不安」的相對主義者。
然而,這種善意相對主義的走向也讓學生侷促不安。去勢還是簡單的話題,班上當然沒有一個人贊成。如果是更貼近我們自身的問題呢? 許多人崇拜比爾.蓋茲,但是根據報導,他個人的財產(當時是四百六十億美元)多過美國收入金字塔底端百分之四十家庭的總和;有些人認為不對勁,其他人則不覺得有什麼不可以:難道這不是他自己努力賺來的嗎?
他們爭論了一會便放棄。他們不但無法取得共識,就連討論這種問題也讓他們為難,難道說一句「我就是覺得不對」就可以了嗎? 他們應該勸朋友墮胎(或是別墮胎)嗎? 我們哪有資格數說巴西人能不能摧毀自己的雨林、巴基斯坦人該不該測試核子武器? 恐怖主義與刑求是絕對不行,還是在某些時刻可以通融呢?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切都得看你從哪個角度出發」,我們又該如何做出一國的決策?
有些學生聽過,只要自問「耶穌會怎麼做?」就能解決所有道德難題。多數人則發現,這個方法並非次次有效,因為耶穌是二十個世紀以前的人,而且當時的生活環境相當不同,耶穌可不必面對學生得處理的惱人問題。他們明白,分隔耶穌與我們之間的歲月就是一大障礙。然而他們在課堂上學到,耶穌是拉比,他並非只是提出答案。相反地,他示範如何做出道德抉擇,學生自己也可以採用。耶穌以神祕的說法與尖銳的比喻要求人們運用想像力,他們發現只要照辦,耶穌所要傳達的啟示的確對我們有所助益。關鍵只在於,我們如何將他的方法與思想翻譯成現代語彙。
近年有大量文獻論述「尋找歷史上的耶穌」,但是這可不是本書的目的,甚至可以說正好相反:這本書的意義是「尋找現代耶穌」,目的就是向二十一世紀介紹一名兩千年前的男子對我們的道德意義。這本書的宗旨,就是這麼直截了當。以下的章節就介紹四部福音書如何記載耶穌的生平,從耶誕故事到復活節記載都兼而有之。本書的焦點在於耶穌本人說過的故事,以及關於他生平的故事。本書會提到學生如何根據這些故事,仔細思考他們所必須面對的道德抉擇,然而他們就跟多數人一樣,有時也會困惑、懷疑、害怕,但是永遠都保持著濃厚的好奇心。書中描述學生各有不同而且往往令人意外的反應,如何促使我自己想得更寬廣、更深刻。此外,本書也記載我們如何按照這些久遠的故事,處理各種現代才有的抉擇。
這些決定都是學生已經碰到,或是知道自己即將面對的問題—隨著人生進入各種階段,我們都會碰上這些問題。
我希望本書可以跨出哈佛校園,激發更多人共同探索;因此各年齡層、各宗教或無宗教背景的讀者都能從這本書走出去,一起加入這趟迫切的探尋之旅。讀者並不需要比我的學生更了解宗教或《聖經》,然而只要是不滿道德基要主義或各行其道的相對論的讀者,本書都歡迎大家一起用嶄新角度觀察第一世紀的拉比,他來自羅馬帝國的偏遠轄區加利利。有人形容他的生平在歷史上最有道德影響力,然而這股影響力的實際功能往往很難判斷。儘管眾人都真正了解所有宗教經文、字句虔誠的保險桿貼紙、耶穌的教義與信條,但本書更大的前提是,這位加利利人對我們的時代仍舊有強而有力、甚至是不容分說的道德意義。
第22章
理智、情感與酷刑
我們對酷刑問題的道德敏感度,如今可能也面臨類似的窘境。儘管自古以來從未消失,人們曾經一度以為酷刑是黑暗時代的遺跡,如今卻因為二十世紀的獨裁者而大剌剌地回到大眾眼前。希特勒的黨羽引進更新、更現代的手法,墨索里尼強餵敵方俘虜喝蓖麻油,史達林將囚犯關在沒有窗戶的牢房,房裡就堆著糞便,拉丁美洲軍事政府則用電擊凌虐囚犯以免留下清楚疤痕。儘管有個推動廢除酷刑的國際組織在法國簽署成立,世人在二○○四年還是心驚膽跳地看到美軍刑求伊拉克囚犯的照片。
酷刑顯然又成為道德考量的議題之一,因此,我很意外聽到有人說艾倫.德蕭威茲教授在新書中公開提倡刑求。畢竟他曾經參與我們的模擬演出,極力為拿撒勒的耶穌辯護,反對他遭凌辱處死。德蕭威茲怎麼說得出這種話? 不會前後矛盾嗎?後來證明,一切純屬謠傳。德蕭威茲的內容其實是,既然自古以來都有酷刑,將來顯然也不會絕跡(而且如今還自稱是根除恐怖主義的手段),那就應該嚴格限制,謹慎規劃。
刑求應該公開進行,經由法律規定,否則只在牢房或暗室進行,便能規避所有責任義務。他引用定時炸彈的舊例加以申論,他說倘若執法人員逮捕某人,而對方的資訊可以預防恐怖炸彈攻擊學校或醫院,避免五千名無辜民眾喪命。如果執法人員只有兩小時打聽重要資訊、拯救眾人,但是囚犯卻不肯透露(要是這顆「定時炸彈」還是核子彈或生化武器,當然又更急迫),這時你該怎麼做?
定時炸彈的故事,是德蕭威茲在課堂上常引用的範例之一,我跟他與已故的史帝芬.傑.顧德(Stephen Jay Gould)一起教授那堂課。德蕭威茲說這些範例是「法學院的假想」,我則認為這些例子證明,故事可以用來教授道德判斷。然而我也常心生懷疑,因為這些假設往往太緊密、太離奇,也就不夠真實。
德蕭威茲本人的解釋是,既然嫌犯知道炸彈藏匿地點,幾乎世上所有警察都會訴諸肢體或心理打壓,以拯救無辜性命。沒錯,否則就枉顧道德責任。然而他又補充(其實這才是論證的精髓,許多人卻聽而不聞),為了避免刑求手法太離譜,也為了避免毫無節制地施以刑求,警方應該申請只准進行一次的「刑求授權書」,才能採取行動,而且手段必須遵照法律規定。這張授權書必須由法官核發,功用類似搜索狀。這張授權書也會規定,可以採取哪些刑求手段。許多讀者只著眼於他所說的某句話(比如他建議在囚犯指甲下插入消毒過的鋼針),卻忽略他論證的全面意義。
我在共同授課的課堂上提出不同意見,結果我很快就發現,討論這個爆炸性話題很難維持理智。我提醒同學,我們有個「聯合國反刑求公約」,而且參議院在一九九四年也批准承認,所以美國境內也有相關的明文法規。然而合法性與道德觀可不一樣,德蕭威茲的提議之目的,便是立法規定高壓訊問。
然而,每個論證都有一個同樣具說服力的反論證,即便睿智的道德思想家瑪莎.努斯鮑姆也說:「任何明智又有操守的人都不會否認,有些假想狀況的確應該(對某個特定人士)採用刑求。」但是大家也知道,遭受刑求的人可能會胡說八道以求逃過凌虐。倘若定時炸彈已經啟動,等到可以驗證供詞真假的時候,一切早就為時晚矣。
此外,還有另一種「滑坡效應」的理論。倘若某些刑求藉由授權書通過法律規定,肯定會廣泛運用在其他案例或是變相行使。法國在這方面就有歷史教訓:儘管該國立法規定刑求手法是為了鎮壓阿爾及利亞叛軍,最後卻運用在整個司法體系,結果一敗塗地,讓法國不但失去阿爾及利亞,刑求手段也導致阿爾及利亞憎恨這個前殖民國數十年之久。以色列以前也准許肢體凌虐,最後也決定立法禁止,然而即便贊成禁止刑求的人也承認,有時候的確可以藉由刑求避免某些恐怖炸彈攻擊。問題關鍵就在於,社會願意犧牲多少人權來換取多大程度的安全。因為這些論證太令人困惑,我們在課堂上的這場辯論也就無法達到結論。
課堂上,支持刑求的主張也時強時弱,因為學生會針對問題的不同層面表示意見。我們在下課前表決德蕭威茲的提議,得票率幾乎是一比一。贊成者採用經典的實用主義邏輯,他們認為這是簡單的數學問題:折磨一人總好過犧牲上千人的性命。然而我還是不甚滿意。我重新引述先前所說的話,也就是請他國代為操刀,結果幾乎所有學生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反對。我又請問他們,如果刑求授權書的法律果真正式上路,誰願意動手將針頭插入嫌犯指甲內? 結果只有幾個人舉手。對那些贊成推動法令卻不肯自己動手的學生,我請他們陳述自己行為的正當性,而且要從道德角度而不是法律角度論述,結果是一片沉默。
我接著又提出另一個問題:假設嫌犯不願意吐實,但是你抓到他的兩名子女—分別是四歲與七歲,你們願意威脅刑求兒童逼供嗎? 畢竟這只是數學問題,兩名孩童暫時的痛苦與五千人的性命怎麼能相提並論? 但是,班上還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傷害兒童。
這類問題很難以理性方法辯論、決定,即便我們在討論時刻意「明理」,助益也不太大。我之所以被迫有這層體驗,是因為那天下課之後,有個學生幾乎是衝到教室前方,憤怒地指著我說:「你將感情因素放進原本應是理性的討論之中。你希望訴諸學生的情感,而非我們的理智!」
這名學生顯然非常激動,而且他的控訴方式也不乏感情因素,但是我還是盡可能理智地回答。我表示他說得對,我的確蓄意加入「情感因素」,因為我認為有其必要。但是,我不接受他所說的情感與理智不該並行。倘若思考推論不帶任何情感,這場討論就沒有活力,單調乏味;反過來說,不加任何理智的情感,就只是歇斯底里或意氣用事。
這名學生顯然是激進的唯理主義者,他並不同意我的說法,態度也相當激動,因為他雙頰漲紅、聲調高亢。他堅決認定學術殿堂不該感情用事,所以我在這場辯論當中的表現並不光明磊落。我微笑地告訴他,我們必須接受別人的不同意見,便向他伸出右手。他稍微猶豫,然後迅速握手,勉強擠出一個微笑。
當我在回家途中想到這件事時,便很感激這個學生勇於提出意見。即便題目是刑求,有些課堂的學生一定只是哈欠連連,不斷看錶。這位先生卻是教授最想要的學生,他不只心裡嘀咕我有違學術殿堂的不成文基本守則,還願意當面告訴我。他也幫助我明白兩個問題:一是這場討論為何如此困難,一是我問學生是否願意親自刑求罪犯或其子女,他們何以立刻改變立場。我相信,在逼供人眼中,他們必須先認為嫌犯只是畜牲。犯人必須先成為敵人、危險嫌犯、非日爾曼人、恐怖份子、不能稱為人的動物。唯有如此,多數人(有些人可能是例外)才能蓄意對他們施加難以忍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