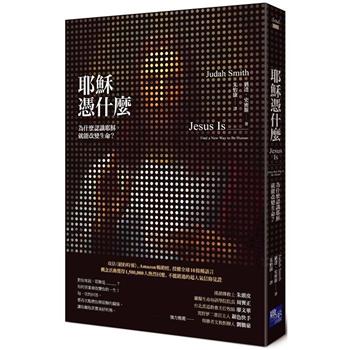兩種罪人
耶穌改變的稅吏不只撒該一個,還有馬太。馬太是耶穌的門徒之一,對耶穌傳道三年半裡的重大事件,他寫的福音書裡著墨不少。
馬太與耶穌第一次相遇的情形,顯示耶穌將罪人分為兩類—只有兩類。聖經裡這樣寫道:
耶穌離開那裏再往前走,看見了一個收稅的,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耶穌對他說:「來跟從我!」馬太就起來,跟從了他。
耶穌在馬太家裏吃飯的時候,許多稅棍和壞人也來了,跟耶穌和他的門徒一起吃飯。有些法利賽人看見了,就對耶穌的門徒說:「為甚麼你們的老師跟稅棍和壞人一起吃飯呢?」
耶穌聽見了這話就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聖經說:『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牲祭。』你們去研究這句話的意思吧! 因為我來的目的不是要召好人,而是要召壞人。」
馬太和撒該一樣也是稅吏,走到哪裡都惹人嫌,每個人都怕他也排擠他—直到他遇到耶穌。馬太絕不會忘了那一天,有個人不知何故根本不在意他的職業,願意把他當成有血有肉的人。
在耶穌對馬太說的話裡,他將一切世人分為兩類:以為自己正直的人,還有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
就這麼簡單。沒有指標量尺,沒有評分標準,也沒有相對的好或主觀的標籤。我們不是假裝自己不需要他,便是承認自己需要他。
我們的共同點是都需要幫助,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承認。我們常常妄自尊大,瞧不起那些做壞事的人,卻忘了自己也需要幫助──就跟那些「壞人」一樣。
我們一定要拋棄自己的評分標準,改用上主的分類框架,因為我們那套標準只會扭曲人與人的互動。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別人在量表上的位置,以為自己知道他們是否準備好認識耶穌、將自己獻給神—這是很大的誤會。
也有很多人以為,接受神的恩典的最大阻礙並不是罪,而是善事做得不夠。
沒錯,有些人問題不小,但也有些人不太容易發現自己有問題:那些住在兩層透天厝、草坪修得整齊、車子洗得乾淨、對伴侶忠實、努力工作、按時繳帳單、從不逃稅的理性中立模範公民,怎麼會覺得自己有問題呢? 他們看看自己的長處、瞧瞧他人的短處,很難不自鳴得意:我實在是個奉公守法的好人,道德清白、行為規矩,我怎麼會需要神的幫助呢?
我們那膚淺的評分系統也問題重重,讓人永難獲得真正的自由。要承認自己跟隔壁的毒蟲一樣糟,的確需要勇氣與謙卑,而許多人確實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人,也不可能誠實面對神,這樣的人只會繼續遮掩缺陷、炫耀善行,到頭來什麼也沒改變。
「嗨,我恨你。」
耶穌與撒該、馬太這樣的罪人交朋友,最難以接受的是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是當時的靈性領袖,精通猶太律法—也就是成千上百條將十誡應用於生活的規定,鉅細靡遺,從怎麼洗手到如何綁東西到駱駝身上,無所不包。
聖經裡的法利賽人總是在指指點點,到處說這樣做錯了、那個人犯罪等等。譴責別人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事業就是奚落受創的靈魂。
法利賽人極為重視律法,卻不太認識神的愛。他們好論斷而無憐憫之心,施懲罰而無慈愛,批判而不試圖了解。
法利賽人敵視罪惡,但最後卻變成憎惡罪人。
最不可取的部分或許是:他們認為高高凌駕於罪人之上便能成聖。換句話說,他們衡量自己有多優秀的標準,其實是被他們排擠的人有多壞。
猶太宗教領袖之所以難以了解耶穌,原因也正在於此。他們等待著彌賽亞、等待著救主,而且他們認為這位救主應該和自己一樣—他應該穿著華麗出眾的袍子,遠遠高於小老百姓之上;他應該趾高氣昂地招搖過市,而閒雜人等應該恭敬讓道。
簡言之,法利賽人認為神若到來,應該會跟他們一樣。可是他們錯了。
耶穌大大方方地去尋找罪人,而且和他們交朋友,一點也不在乎這可能有損他的名聲。耶穌沒有藉著貶抑別人來彰顯自己。他是完美的神,可是他以行動表示:連最糟的罪人他也不譴責。
諷刺的是,耶穌批評得最嚴厲的人就是法利賽人。耶穌看穿他們的偽善,而且不假辭色地公開訓斥,法利賽人因此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最後,大聲嘶吼要將耶穌釘十字架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些宗教領袖。他們煽動群眾,迫使羅馬當局處死耶穌。
殺了耶穌的不是惡名昭彰的罪人,而是「虔信宗教」的人。
我心中的法利賽人
不過,也不必對法利賽人太過憤慨,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個蠢蠢欲動的法利賽人。
我也一樣。每次我克服一種壞習慣,總迫不及待地轉頭批評還沒改過來的人。
我發現義憤比謙卑或同情更常出現,在心裡痛斥別人的壞行為,比面對自己的問題舒坦得多。
我們隨時都能看出別人有問題。但請稍微想想:我們眼中的那些惡人,實在不太可能認為自己很壞。因為他們一旦開始覺得有罪惡感,只要從那條聖潔的食物鏈往下看,立刻就能找到比他們更糟的人,然後大感快慰,再次肯定自己其實還算不錯。
因此我得捫心自問:我到底以為自己在食物鏈的哪一層呢? 同樣地,誰又在我上面低頭看我,以我的是非來證明自己高人一等? 光是想到這裡,就讓我渾身不自在,但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確實切中要點。
簡單說來,我是這樣在看待別人:我立下適合我生活標準的規矩,然後用它們來評判你。如果你遵守我的規矩,你是好人;要是你違背規矩,你是壞人;如果你的規矩居然比我還嚴、還多──你太小心拘謹了,應該放鬆一點。
這種分類方式真方便,但也真扭曲。
如果我們對罪惡的定義是「做壞事」,我想每個人都同意罪惡確實存在,畢竟人類做過不少壞事。即使我們對「壞事」的定義未必一致,但都會同意強暴是錯的,種族屠殺是邪惡,種族歧視則令人作嘔。
問題是,我們不會把自己跟強暴犯、殺人犯歸在同一類。他們犯了罪,我們只是沒那麼完美而已。
面對自己做的壞事時,我們的反應往往跟「國家地理頻道」裡的動物一樣:迎戰或脫逃。我們可能疾言厲色地開始反擊,伸出手指一一點出其他人的名字,也可能開始尋找託詞逃避,感嘆宇宙正邪力量之不可思議,然後話鋒一轉,暢談愛與寬容、建立美好世界等等。但我們心知肚明這只是煙幕彈,只是用來引開別人的注意,讓他們別發現我們的道德缺陷而已。
我無意指責任何人,但自由得從誠實開始。光是把自己當好人、別人當壞人,並不能給自己任何好處。就讓我們承認自己需要幫助吧! 每一個人都不例外。
好消息是,耶穌所宣揚的那位神,不是以我們的行為來評判我們,而是以祂的愛來衡量我們。
既然如此,當我們看到那些被譴責、被敵視的罪人時,為什麼又老是要振振有詞地大談法律或規定呢? 對於新聞裡那些言行古怪的傢伙,還有阻街女郎、竊盜犯、殺人犯、強暴犯,為什麼我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哀矜而勿喜,而是拿出法律大加撻伐呢?
我有想到一個原因,但我實在不願承認。我想,我會這麼急著用規則評判他人,是因為這些規則能把我和那些「壞人」區隔開來。
如果我離這些罪人遠遠的,我就不必分擔他們的痛苦。我不必與他們感同身受、不必愛他們,更不必讓自己為他們心碎。我不必介入,不必幫助他們重回正途、找回人生。我的心原本應該為同情而淌血,但只要我離他們遠遠地,我就能繼續漠不關心,就能繼續嚴厲地譴責他們。然而,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若不是神的恩典,犯下那些罪的「壞人」很可能就是我。
更進一步說:如果我離罪人遠遠地,我就能享受旁觀他們受罰的樂趣。他們越是重刑加身,我就越有施虐的快感,畢竟他們是自找的嘛!
請別誤會,我並不主張拋棄社會公論,而是希望能改變動輒論斷他人的陋習。如果我離罪人遠遠地,或許可以保障自己的名聲不受他們拖累,安安穩穩地繼續待在「高人一等俱樂部」,在那裡彼此奉承、相互吹噓,偶爾嘆息幾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至於純樸社會該有多「古」,我們根本不在乎),有時義憤填膺,再罵罵政府庸碌無能──我們來做一定比他們做得更好!
最重要的是,我和壞人離得越遠,自我感覺就越良好。因為跟他們相比之下,我實在好太多了。
我想再強調一次:請別誤會,我無意指控規則冷血無情,冷血無情的其實是我們運用規則的方式。為了保護孩子們,我會給他們立規矩;同樣地,社會為保障人民安全就必須制訂法律。我完全尊重權威、秩序、公義與執法者。
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規則、法律並不能證明靈性,它們充其量只能證明罪惡,它們頂多只能告誡人人都有可能做錯事、提醒我們需要幫助。
頁數 5/5
法利賽人的問題在於拘泥律法小節,卻遺忘了律法最重要的精神:愛神與愛人。他們以為小心謹慎就能討神歡喜,所以一看到人做錯事便怒火攻心。耶穌想告訴他們的就是這種想法極其荒謬,人犯罪時,神生起的是憐憫之心,並非勃然大怒。自以為是的人再怎麼謹言慎行,對神都無意義,因為這樣的人根本沒把心思放在神身上。
耶穌總是憐憫最不值得同情的人,給予最絕望的人希望,讓最惡劣的罪人獲得恩典。老實說,我也同樣屬於這一類的人。
在內心深處,我焦慮地看見自己仍在與壞念頭搏鬥。我對孩子沒耐心,對妻子言行粗魯,常因惡意或自我中心做出決定,忘卻了愛。事實上,我比你好或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該承認自己需要耶穌。
我不該自以為優越排斥他人,也不應依自己的標準隨意論斷或譴責別人,我該牢牢記住的是:我仍迫切需要耶穌的恩典。
耶穌與最惡劣的罪人為友,所以他與我為友。
耶穌改變的稅吏不只撒該一個,還有馬太。馬太是耶穌的門徒之一,對耶穌傳道三年半裡的重大事件,他寫的福音書裡著墨不少。
馬太與耶穌第一次相遇的情形,顯示耶穌將罪人分為兩類—只有兩類。聖經裡這樣寫道:
耶穌離開那裏再往前走,看見了一個收稅的,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耶穌對他說:「來跟從我!」馬太就起來,跟從了他。
耶穌在馬太家裏吃飯的時候,許多稅棍和壞人也來了,跟耶穌和他的門徒一起吃飯。有些法利賽人看見了,就對耶穌的門徒說:「為甚麼你們的老師跟稅棍和壞人一起吃飯呢?」
耶穌聽見了這話就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聖經說:『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牲祭。』你們去研究這句話的意思吧! 因為我來的目的不是要召好人,而是要召壞人。」
馬太和撒該一樣也是稅吏,走到哪裡都惹人嫌,每個人都怕他也排擠他—直到他遇到耶穌。馬太絕不會忘了那一天,有個人不知何故根本不在意他的職業,願意把他當成有血有肉的人。
在耶穌對馬太說的話裡,他將一切世人分為兩類:以為自己正直的人,還有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
就這麼簡單。沒有指標量尺,沒有評分標準,也沒有相對的好或主觀的標籤。我們不是假裝自己不需要他,便是承認自己需要他。
我們的共同點是都需要幫助,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承認。我們常常妄自尊大,瞧不起那些做壞事的人,卻忘了自己也需要幫助──就跟那些「壞人」一樣。
我們一定要拋棄自己的評分標準,改用上主的分類框架,因為我們那套標準只會扭曲人與人的互動。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別人在量表上的位置,以為自己知道他們是否準備好認識耶穌、將自己獻給神—這是很大的誤會。
也有很多人以為,接受神的恩典的最大阻礙並不是罪,而是善事做得不夠。
沒錯,有些人問題不小,但也有些人不太容易發現自己有問題:那些住在兩層透天厝、草坪修得整齊、車子洗得乾淨、對伴侶忠實、努力工作、按時繳帳單、從不逃稅的理性中立模範公民,怎麼會覺得自己有問題呢? 他們看看自己的長處、瞧瞧他人的短處,很難不自鳴得意:我實在是個奉公守法的好人,道德清白、行為規矩,我怎麼會需要神的幫助呢?
我們那膚淺的評分系統也問題重重,讓人永難獲得真正的自由。要承認自己跟隔壁的毒蟲一樣糟,的確需要勇氣與謙卑,而許多人確實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人,也不可能誠實面對神,這樣的人只會繼續遮掩缺陷、炫耀善行,到頭來什麼也沒改變。
「嗨,我恨你。」
耶穌與撒該、馬太這樣的罪人交朋友,最難以接受的是法利賽人。法利賽人是當時的靈性領袖,精通猶太律法—也就是成千上百條將十誡應用於生活的規定,鉅細靡遺,從怎麼洗手到如何綁東西到駱駝身上,無所不包。
聖經裡的法利賽人總是在指指點點,到處說這樣做錯了、那個人犯罪等等。譴責別人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事業就是奚落受創的靈魂。
法利賽人極為重視律法,卻不太認識神的愛。他們好論斷而無憐憫之心,施懲罰而無慈愛,批判而不試圖了解。
法利賽人敵視罪惡,但最後卻變成憎惡罪人。
最不可取的部分或許是:他們認為高高凌駕於罪人之上便能成聖。換句話說,他們衡量自己有多優秀的標準,其實是被他們排擠的人有多壞。
猶太宗教領袖之所以難以了解耶穌,原因也正在於此。他們等待著彌賽亞、等待著救主,而且他們認為這位救主應該和自己一樣—他應該穿著華麗出眾的袍子,遠遠高於小老百姓之上;他應該趾高氣昂地招搖過市,而閒雜人等應該恭敬讓道。
簡言之,法利賽人認為神若到來,應該會跟他們一樣。可是他們錯了。
耶穌大大方方地去尋找罪人,而且和他們交朋友,一點也不在乎這可能有損他的名聲。耶穌沒有藉著貶抑別人來彰顯自己。他是完美的神,可是他以行動表示:連最糟的罪人他也不譴責。
諷刺的是,耶穌批評得最嚴厲的人就是法利賽人。耶穌看穿他們的偽善,而且不假辭色地公開訓斥,法利賽人因此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最後,大聲嘶吼要將耶穌釘十字架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些宗教領袖。他們煽動群眾,迫使羅馬當局處死耶穌。
殺了耶穌的不是惡名昭彰的罪人,而是「虔信宗教」的人。
我心中的法利賽人
不過,也不必對法利賽人太過憤慨,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個蠢蠢欲動的法利賽人。
我也一樣。每次我克服一種壞習慣,總迫不及待地轉頭批評還沒改過來的人。
我發現義憤比謙卑或同情更常出現,在心裡痛斥別人的壞行為,比面對自己的問題舒坦得多。
我們隨時都能看出別人有問題。但請稍微想想:我們眼中的那些惡人,實在不太可能認為自己很壞。因為他們一旦開始覺得有罪惡感,只要從那條聖潔的食物鏈往下看,立刻就能找到比他們更糟的人,然後大感快慰,再次肯定自己其實還算不錯。
因此我得捫心自問:我到底以為自己在食物鏈的哪一層呢? 同樣地,誰又在我上面低頭看我,以我的是非來證明自己高人一等? 光是想到這裡,就讓我渾身不自在,但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確實切中要點。
簡單說來,我是這樣在看待別人:我立下適合我生活標準的規矩,然後用它們來評判你。如果你遵守我的規矩,你是好人;要是你違背規矩,你是壞人;如果你的規矩居然比我還嚴、還多──你太小心拘謹了,應該放鬆一點。
這種分類方式真方便,但也真扭曲。
如果我們對罪惡的定義是「做壞事」,我想每個人都同意罪惡確實存在,畢竟人類做過不少壞事。即使我們對「壞事」的定義未必一致,但都會同意強暴是錯的,種族屠殺是邪惡,種族歧視則令人作嘔。
問題是,我們不會把自己跟強暴犯、殺人犯歸在同一類。他們犯了罪,我們只是沒那麼完美而已。
面對自己做的壞事時,我們的反應往往跟「國家地理頻道」裡的動物一樣:迎戰或脫逃。我們可能疾言厲色地開始反擊,伸出手指一一點出其他人的名字,也可能開始尋找託詞逃避,感嘆宇宙正邪力量之不可思議,然後話鋒一轉,暢談愛與寬容、建立美好世界等等。但我們心知肚明這只是煙幕彈,只是用來引開別人的注意,讓他們別發現我們的道德缺陷而已。
我無意指責任何人,但自由得從誠實開始。光是把自己當好人、別人當壞人,並不能給自己任何好處。就讓我們承認自己需要幫助吧! 每一個人都不例外。
好消息是,耶穌所宣揚的那位神,不是以我們的行為來評判我們,而是以祂的愛來衡量我們。
既然如此,當我們看到那些被譴責、被敵視的罪人時,為什麼又老是要振振有詞地大談法律或規定呢? 對於新聞裡那些言行古怪的傢伙,還有阻街女郎、竊盜犯、殺人犯、強暴犯,為什麼我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哀矜而勿喜,而是拿出法律大加撻伐呢?
我有想到一個原因,但我實在不願承認。我想,我會這麼急著用規則評判他人,是因為這些規則能把我和那些「壞人」區隔開來。
如果我離這些罪人遠遠的,我就不必分擔他們的痛苦。我不必與他們感同身受、不必愛他們,更不必讓自己為他們心碎。我不必介入,不必幫助他們重回正途、找回人生。我的心原本應該為同情而淌血,但只要我離他們遠遠地,我就能繼續漠不關心,就能繼續嚴厲地譴責他們。然而,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若不是神的恩典,犯下那些罪的「壞人」很可能就是我。
更進一步說:如果我離罪人遠遠地,我就能享受旁觀他們受罰的樂趣。他們越是重刑加身,我就越有施虐的快感,畢竟他們是自找的嘛!
請別誤會,我並不主張拋棄社會公論,而是希望能改變動輒論斷他人的陋習。如果我離罪人遠遠地,或許可以保障自己的名聲不受他們拖累,安安穩穩地繼續待在「高人一等俱樂部」,在那裡彼此奉承、相互吹噓,偶爾嘆息幾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至於純樸社會該有多「古」,我們根本不在乎),有時義憤填膺,再罵罵政府庸碌無能──我們來做一定比他們做得更好!
最重要的是,我和壞人離得越遠,自我感覺就越良好。因為跟他們相比之下,我實在好太多了。
我想再強調一次:請別誤會,我無意指控規則冷血無情,冷血無情的其實是我們運用規則的方式。為了保護孩子們,我會給他們立規矩;同樣地,社會為保障人民安全就必須制訂法律。我完全尊重權威、秩序、公義與執法者。
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規則、法律並不能證明靈性,它們充其量只能證明罪惡,它們頂多只能告誡人人都有可能做錯事、提醒我們需要幫助。
頁數 5/5
法利賽人的問題在於拘泥律法小節,卻遺忘了律法最重要的精神:愛神與愛人。他們以為小心謹慎就能討神歡喜,所以一看到人做錯事便怒火攻心。耶穌想告訴他們的就是這種想法極其荒謬,人犯罪時,神生起的是憐憫之心,並非勃然大怒。自以為是的人再怎麼謹言慎行,對神都無意義,因為這樣的人根本沒把心思放在神身上。
耶穌總是憐憫最不值得同情的人,給予最絕望的人希望,讓最惡劣的罪人獲得恩典。老實說,我也同樣屬於這一類的人。
在內心深處,我焦慮地看見自己仍在與壞念頭搏鬥。我對孩子沒耐心,對妻子言行粗魯,常因惡意或自我中心做出決定,忘卻了愛。事實上,我比你好或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該承認自己需要耶穌。
我不該自以為優越排斥他人,也不應依自己的標準隨意論斷或譴責別人,我該牢牢記住的是:我仍迫切需要耶穌的恩典。
耶穌與最惡劣的罪人為友,所以他與我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