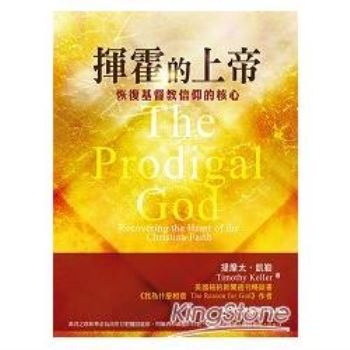第二篇
兩個失喪的兒子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失喪的小兒子
若是將主耶穌所說「浪子的比喻」的標題,改為「兩個失喪兒子的比喻」,可能最為切題。它的劇情有兩幕:第一幕是「失喪的小兒子」,第二幕則是「失喪的大兒子」。
第一幕始於一個簡短卻令人震驚的要求。小兒子來到父親的面前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當時,在場的會眾聽到這樣的要求,必定相當錯愕,並不是小兒子不能期待「分家產」,而是分家產這件事,只能在父親亡故之後,才得以進行。當時的習俗是:父親過世後,長子可以分到其他子女所得之雙倍的遺產,亦即一個父親若有兩個兒子,長子可以分三分之二的產業,次子則分得三分之一。
但是,故事裡的小兒子卻在父親仍在世時,就開口要求分家產,這真是大逆不道之舉!父親還在世就提出這樣的要求,就等同於公開希望父親現在就死去之意。說穿了,小兒子一心只想要得到父親的產業,並且打從心底不在乎父親這個人。他和父親的關係維繫,只剩下企圖分得財產的目的,而此時此刻,他也厭倦了這樣的關係,不想再等待了。於是他說:「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吧!」
接下來,父親的反應卻比小兒子的要求還令人震驚。在當時,那是一個極度父權主義的社會,人們十分看重敬老尊賢的禮儀,特別對於自己年長的父母,更是萬般敬重。在傳統的中東社會,對於這樣不肖逆子的處置,一定先是一頓毒打,再將其逐出家門;然而,這位父親並沒有這樣做,他只是「單單把產業分給他們」。為了要瞭解這裡所表達的意涵,我們要注意到「產業」,這個字的希臘原文是用 bios,意思是生命,而希臘原文卻沒有使用另一個更可以表達財物的字眼,這是為什麼呢?
這位父親的財富大部分應該都是不動產,為了給小兒子三分之一的產業,他必須賣掉相當多的土地持份。我們這些習慣都會生活、機動性高的現代人,很難理解在那時代土地與人們之間的緊密關聯。羅傑斯與漢默斯坦(Rodgers and Hammerstein)的著名音樂劇「奧克拉荷馬(Oklahoma!)」中有一句話說:「噢!我們知道我們屬於這片地土,我們所屬的地土是宏偉的!」留意這句話,不是土地屬於他們,而是他們屬於土地。這說明了以前人們的身份地位,是與他們的所在地域、他們的土地緊緊相連,失去土地就好像失去個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在現代社會中,我們都聽過有些有權有勢、事業成功的總裁們,男女皆有,為了親自照顧受傷或需要陪伴的孩子,便毅然決然地放棄所有事業。以上這兩個比喻雖非完全相似,但這位父親所做的,也正是這樣的事。
仔細思想,這個小兒子的要求,其實是要父親撕裂自己的生命,而父親因為深愛兒子的緣故,也如實照辦了。在當時的中東地區,圍繞在主耶穌身旁的聽眾,應該從未聽過有任何一位父親會以愛來回應,但是,這位父親卻強忍著被藐視羞辱、被拒絕的傷痛。通常,當我們去愛人卻遭拒時,我們會生氣、想報復、會想盡辦法減少對那人付出的愛,以求不再繼續痛苦,但是這位父親卻仍然持續地愛著兒子,並概括承受所有痛苦的煎熬。
小兒子的計劃
現在來到第一幕的第二景。
小兒子去了「遠方」,過著毫無節制的生活,浪費了所有貲財,最終,當他窮困潦倒到只能與豬同住在污泥中時,他才「醒悟過來」,開始為自己籌劃未來。首先,他告訴自己,要回到父家那裡,承認自己的錯誤,因他心裡明白自己早已喪失了「兒子」的身分與資格。第二,他想懇求他的父親:「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
這是一個具體且明確的請求。當時的「僕人」是住在主人的莊園中工作,而「雇工」則是住在附近村莊,靠著技能工作賺錢。許多解經家認為,小兒子原本打算以「雇工身份」度過下半餘生。小兒子使父家蒙羞,辱及整個家族社會,對地方鄰里而言,他也正如他父親所說的一樣,早已是「死的」。猶太拉比教導,一個人若觸犯社會的規範,光憑口頭道歉於事無補,必須要有所償還。小兒子原本想說:「父親,我知道我沒有資格再回到這個家。但是如果您允許我跟著您的雇工當學徒,我可以學習技能並賺錢,至少可以向您償還我的債務。」小兒子在豬圈裡反覆演練著台詞,當他覺得自己已經預備好時,便收拾行囊踏上回鄉歸程。
我們來到第一幕的第三景,也是最後一景,非常戲劇化,小兒子終於快到家了。他的父親看見了他,飛奔急跑,直接奔向他!按照規矩,有地位的中東父親是不奔跑的,孩子們會奔跑、婦女們會奔跑、少年人會奔跑,但家族的大家長、社會中有威嚴的士紳、擁有大片家產的地主,是絕對不奔跑的。但是這個父親卻為了他深愛的兒子,做出有失體統之舉:「他拎起長袍、露出雙腿,像孩子似的向前狂奔,奔向他的兒子,真情流露,緊緊的抱住他,親吻他。」
父親這突如其來之舉,讓小兒子驚嚇不已。他驚慌失措地企圖要按照原訂計劃,進行贖罪告白,此時,他的父親卻打斷了他正想說的話,父親不僅不理會他所要說的,吩咐僕人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上!」這位父親到底要表達什麼呢?
所謂家裡上好的袍子,應該就是父親自己的袍子,這無疑表明是要讓小兒子恢復兒子的地位。父親的動作彷彿是說:「我不需要等到你償還你的債務,也不需要你卑躬屈膝乞求,你不需想盡辦法才能回到家中,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回家。我要用我的地位及榮耀來遮蓋你一切的赤裸、貧窮及缺乏」。
接著,父親立刻吩咐僕人們預備盛宴慶祝,宰肥牛犢作為主菜。在當時,一般三餐飲食中是沒有肉類的,肉是奢侈佳餚的表徵,只有特殊節慶宴會才得以預備。而在肉類中,又屬肥牛犢為最稀有的珍饈,唯有全村一同歡慶,極為重要盛大或宴席場合才得入菜上桌。因此,消息很快地傳開,這裡即將有一場佳餚滿席、歌舞同樂的盛宴要舉行,為要慶祝小兒子重新歸回家庭與社會中。
這故事真是十分戲劇化!在第二幕,父親尚未開始去處理大兒子那更複雜充滿苦毒的屬靈狀況時,第一幕卻以令人震驚的信息挑戰了大兒子的思維模式:上帝的愛和饒恕,能赦免並挽回一切的罪孽及過犯,不論你是誰或做了什麼,不論你是否曾故意壓迫人,或甚至殺過人,或如何地糟蹋虐待自己。小兒子始終知道他父家「口糧有餘」、「恩典豐沛」。沒有任何的罪惡是父親的愛無法饒恕和遮蓋的,沒有任何的罪可以與他的恩典相匹配。
第一幕展現了神恩典的奢侈與揮霍性。主耶穌指出父親帶著愛奔向兒子,不僅僅是在兒子想要重新來過,確實回心轉意之前,甚至是在他說出悔改贖罪告白之前。沒有任何事物,即使是誠心的悔恨,能使我們配得神的恩惠。因為父親的愛與接納是白白恩典,完全不需要你付上任何代價的。
即使父親的愛是如此美好,第一幕還是不能獨立存在。許多解經家,只單獨專注於第一幕時,時常會認為這個比喻的結論與傳統基督教教義相違背。「看吧!」他們說:「這裡沒有提到罪的贖價,好像不需要一個救贖者在十字架上擔負罪債,這位神是博愛,祂無條件完全接納所有人。」
如果主耶穌要傳達的信息真是這樣,故事停在這裡就夠了,但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顯然主耶穌的信息並非到此為止。第一幕告訴我們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得來的,第二幕則是要闡明這個恩典是付上極昂貴的代價,而這個故事也將進入真正的高潮。
失落的大兒子
當大兒子聽到僕人說自己的弟弟回來,又蒙父親恢復他的地位時,他憤怒至極。現在輪到大兒子要來羞辱父親了。
他拒絕參加這場可能是父親有生以來最盛大、最公開的饗宴。他停留在屋外,公然挑戰父親的行為,這行徑迫使父親必須親自出來向他說話;一個莊園的擁有者、又是宴會的主人,這舉動絕對是讓他顏面盡失。父親開始誠懇地勸服大兒子,但是大兒子仍然拒絕參加盛宴。
為什麼大兒子會感到如此憤怒?他特別針對此盛宴的花費,感到忿忿不平。他說:「你從沒為了我殺一隻羊羔辦宴席,你竟然為了他殺肥牛犢宴客?」其實肥牛犢只是一個象徵,因為父親所付上的代價遠超過肥牛犢的價值。父親讓小兒子回到家中,小兒子再度取得產業繼承權,他可再次得到剩下的家產的三分之一,對大兒子來說,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他忍不住說:「我工作得精疲力盡、銖積寸累,才賺得我所擁有的,但我的弟弟什麼都沒做,他只配被趕出家門,而你卻如此慷慨豐富厚待他!這公平嗎?天理何在?」這是為什麼大兒子要提到自己的紀錄:「我從來沒有違背過你!所以我有權利!」他說:「你應該先與我商量!你沒有資格一意孤行做出如此不公平的決定。」
大兒子的忿怒促使他更加重地侮辱父親。他拒絕用當時文化—特別在公開場合裡,下屬對長輩該有的尊敬稱呼,大兒子並沒有說「尊貴的父親」,而是說「看!」這等於是說「你看你!」在一個視尊敬及順從長輩為極重要的文化裡,這樣的行徑簡直是難以想像!這就如同於我們現今社會中,兒子撰寫曝露家醜的回憶錄,摧毀自己父親的名聲及事業一樣,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最後,在故事的結局,這個父親究竟要如何回應大兒子的公然忤逆呢?在父子對立、劍拔弩張的情況下,父親通常會選擇當場斷絕父子關係。然而,這父親卻以出奇的溫柔回應:「我兒!」他說:「雖然你公然侮辱我,我仍然想要你來參加宴會。我不僅不會與你的弟弟斷絕關係,更不會與你斷絕關係,我鼓勵你吞忍壓抑你的驕傲,進來享受筵席,但這需要你自己親自做決定,你願意嗎?」這真是一個出乎意料之外、充滿恩典與戲劇化的請求。
聽眾們坐立不安,引頸期盼,亟欲想知道這家庭會重新合一並相愛嗎?兩兄弟會盡釋前嫌嗎?大兒子會因這溫柔的邀請而心軟,而與父親和好嗎?
當這些臆測正在我們的意念中閃過,故事卻嘎然而止!為什麼主耶穌不把故事說完,直接告訴我們結局呢?因為這故事的主要對象是那些法利賽人,就是所謂的大兒子們!主耶穌在請求祂的仇敵們回應祂的信息,這信息是什麼呢?當我們愈明白理解主耶穌要傳達的核心信息時,這答案將出現在本書後面章節。簡言之,主耶穌正在重新定義一切我們自以為與上帝連結的方式。祂親自要重新定義什麼是罪、失喪的意義、以及何謂得救的真諦。
兩個失喪的兒子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失喪的小兒子
若是將主耶穌所說「浪子的比喻」的標題,改為「兩個失喪兒子的比喻」,可能最為切題。它的劇情有兩幕:第一幕是「失喪的小兒子」,第二幕則是「失喪的大兒子」。
第一幕始於一個簡短卻令人震驚的要求。小兒子來到父親的面前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當時,在場的會眾聽到這樣的要求,必定相當錯愕,並不是小兒子不能期待「分家產」,而是分家產這件事,只能在父親亡故之後,才得以進行。當時的習俗是:父親過世後,長子可以分到其他子女所得之雙倍的遺產,亦即一個父親若有兩個兒子,長子可以分三分之二的產業,次子則分得三分之一。
但是,故事裡的小兒子卻在父親仍在世時,就開口要求分家產,這真是大逆不道之舉!父親還在世就提出這樣的要求,就等同於公開希望父親現在就死去之意。說穿了,小兒子一心只想要得到父親的產業,並且打從心底不在乎父親這個人。他和父親的關係維繫,只剩下企圖分得財產的目的,而此時此刻,他也厭倦了這樣的關係,不想再等待了。於是他說:「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吧!」
接下來,父親的反應卻比小兒子的要求還令人震驚。在當時,那是一個極度父權主義的社會,人們十分看重敬老尊賢的禮儀,特別對於自己年長的父母,更是萬般敬重。在傳統的中東社會,對於這樣不肖逆子的處置,一定先是一頓毒打,再將其逐出家門;然而,這位父親並沒有這樣做,他只是「單單把產業分給他們」。為了要瞭解這裡所表達的意涵,我們要注意到「產業」,這個字的希臘原文是用 bios,意思是生命,而希臘原文卻沒有使用另一個更可以表達財物的字眼,這是為什麼呢?
這位父親的財富大部分應該都是不動產,為了給小兒子三分之一的產業,他必須賣掉相當多的土地持份。我們這些習慣都會生活、機動性高的現代人,很難理解在那時代土地與人們之間的緊密關聯。羅傑斯與漢默斯坦(Rodgers and Hammerstein)的著名音樂劇「奧克拉荷馬(Oklahoma!)」中有一句話說:「噢!我們知道我們屬於這片地土,我們所屬的地土是宏偉的!」留意這句話,不是土地屬於他們,而是他們屬於土地。這說明了以前人們的身份地位,是與他們的所在地域、他們的土地緊緊相連,失去土地就好像失去個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在現代社會中,我們都聽過有些有權有勢、事業成功的總裁們,男女皆有,為了親自照顧受傷或需要陪伴的孩子,便毅然決然地放棄所有事業。以上這兩個比喻雖非完全相似,但這位父親所做的,也正是這樣的事。
仔細思想,這個小兒子的要求,其實是要父親撕裂自己的生命,而父親因為深愛兒子的緣故,也如實照辦了。在當時的中東地區,圍繞在主耶穌身旁的聽眾,應該從未聽過有任何一位父親會以愛來回應,但是,這位父親卻強忍著被藐視羞辱、被拒絕的傷痛。通常,當我們去愛人卻遭拒時,我們會生氣、想報復、會想盡辦法減少對那人付出的愛,以求不再繼續痛苦,但是這位父親卻仍然持續地愛著兒子,並概括承受所有痛苦的煎熬。
小兒子的計劃
現在來到第一幕的第二景。
小兒子去了「遠方」,過著毫無節制的生活,浪費了所有貲財,最終,當他窮困潦倒到只能與豬同住在污泥中時,他才「醒悟過來」,開始為自己籌劃未來。首先,他告訴自己,要回到父家那裡,承認自己的錯誤,因他心裡明白自己早已喪失了「兒子」的身分與資格。第二,他想懇求他的父親:「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
這是一個具體且明確的請求。當時的「僕人」是住在主人的莊園中工作,而「雇工」則是住在附近村莊,靠著技能工作賺錢。許多解經家認為,小兒子原本打算以「雇工身份」度過下半餘生。小兒子使父家蒙羞,辱及整個家族社會,對地方鄰里而言,他也正如他父親所說的一樣,早已是「死的」。猶太拉比教導,一個人若觸犯社會的規範,光憑口頭道歉於事無補,必須要有所償還。小兒子原本想說:「父親,我知道我沒有資格再回到這個家。但是如果您允許我跟著您的雇工當學徒,我可以學習技能並賺錢,至少可以向您償還我的債務。」小兒子在豬圈裡反覆演練著台詞,當他覺得自己已經預備好時,便收拾行囊踏上回鄉歸程。
我們來到第一幕的第三景,也是最後一景,非常戲劇化,小兒子終於快到家了。他的父親看見了他,飛奔急跑,直接奔向他!按照規矩,有地位的中東父親是不奔跑的,孩子們會奔跑、婦女們會奔跑、少年人會奔跑,但家族的大家長、社會中有威嚴的士紳、擁有大片家產的地主,是絕對不奔跑的。但是這個父親卻為了他深愛的兒子,做出有失體統之舉:「他拎起長袍、露出雙腿,像孩子似的向前狂奔,奔向他的兒子,真情流露,緊緊的抱住他,親吻他。」
父親這突如其來之舉,讓小兒子驚嚇不已。他驚慌失措地企圖要按照原訂計劃,進行贖罪告白,此時,他的父親卻打斷了他正想說的話,父親不僅不理會他所要說的,吩咐僕人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上!」這位父親到底要表達什麼呢?
所謂家裡上好的袍子,應該就是父親自己的袍子,這無疑表明是要讓小兒子恢復兒子的地位。父親的動作彷彿是說:「我不需要等到你償還你的債務,也不需要你卑躬屈膝乞求,你不需想盡辦法才能回到家中,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回家。我要用我的地位及榮耀來遮蓋你一切的赤裸、貧窮及缺乏」。
接著,父親立刻吩咐僕人們預備盛宴慶祝,宰肥牛犢作為主菜。在當時,一般三餐飲食中是沒有肉類的,肉是奢侈佳餚的表徵,只有特殊節慶宴會才得以預備。而在肉類中,又屬肥牛犢為最稀有的珍饈,唯有全村一同歡慶,極為重要盛大或宴席場合才得入菜上桌。因此,消息很快地傳開,這裡即將有一場佳餚滿席、歌舞同樂的盛宴要舉行,為要慶祝小兒子重新歸回家庭與社會中。
這故事真是十分戲劇化!在第二幕,父親尚未開始去處理大兒子那更複雜充滿苦毒的屬靈狀況時,第一幕卻以令人震驚的信息挑戰了大兒子的思維模式:上帝的愛和饒恕,能赦免並挽回一切的罪孽及過犯,不論你是誰或做了什麼,不論你是否曾故意壓迫人,或甚至殺過人,或如何地糟蹋虐待自己。小兒子始終知道他父家「口糧有餘」、「恩典豐沛」。沒有任何的罪惡是父親的愛無法饒恕和遮蓋的,沒有任何的罪可以與他的恩典相匹配。
第一幕展現了神恩典的奢侈與揮霍性。主耶穌指出父親帶著愛奔向兒子,不僅僅是在兒子想要重新來過,確實回心轉意之前,甚至是在他說出悔改贖罪告白之前。沒有任何事物,即使是誠心的悔恨,能使我們配得神的恩惠。因為父親的愛與接納是白白恩典,完全不需要你付上任何代價的。
即使父親的愛是如此美好,第一幕還是不能獨立存在。許多解經家,只單獨專注於第一幕時,時常會認為這個比喻的結論與傳統基督教教義相違背。「看吧!」他們說:「這裡沒有提到罪的贖價,好像不需要一個救贖者在十字架上擔負罪債,這位神是博愛,祂無條件完全接納所有人。」
如果主耶穌要傳達的信息真是這樣,故事停在這裡就夠了,但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顯然主耶穌的信息並非到此為止。第一幕告訴我們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得來的,第二幕則是要闡明這個恩典是付上極昂貴的代價,而這個故事也將進入真正的高潮。
失落的大兒子
當大兒子聽到僕人說自己的弟弟回來,又蒙父親恢復他的地位時,他憤怒至極。現在輪到大兒子要來羞辱父親了。
他拒絕參加這場可能是父親有生以來最盛大、最公開的饗宴。他停留在屋外,公然挑戰父親的行為,這行徑迫使父親必須親自出來向他說話;一個莊園的擁有者、又是宴會的主人,這舉動絕對是讓他顏面盡失。父親開始誠懇地勸服大兒子,但是大兒子仍然拒絕參加盛宴。
為什麼大兒子會感到如此憤怒?他特別針對此盛宴的花費,感到忿忿不平。他說:「你從沒為了我殺一隻羊羔辦宴席,你竟然為了他殺肥牛犢宴客?」其實肥牛犢只是一個象徵,因為父親所付上的代價遠超過肥牛犢的價值。父親讓小兒子回到家中,小兒子再度取得產業繼承權,他可再次得到剩下的家產的三分之一,對大兒子來說,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他忍不住說:「我工作得精疲力盡、銖積寸累,才賺得我所擁有的,但我的弟弟什麼都沒做,他只配被趕出家門,而你卻如此慷慨豐富厚待他!這公平嗎?天理何在?」這是為什麼大兒子要提到自己的紀錄:「我從來沒有違背過你!所以我有權利!」他說:「你應該先與我商量!你沒有資格一意孤行做出如此不公平的決定。」
大兒子的忿怒促使他更加重地侮辱父親。他拒絕用當時文化—特別在公開場合裡,下屬對長輩該有的尊敬稱呼,大兒子並沒有說「尊貴的父親」,而是說「看!」這等於是說「你看你!」在一個視尊敬及順從長輩為極重要的文化裡,這樣的行徑簡直是難以想像!這就如同於我們現今社會中,兒子撰寫曝露家醜的回憶錄,摧毀自己父親的名聲及事業一樣,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最後,在故事的結局,這個父親究竟要如何回應大兒子的公然忤逆呢?在父子對立、劍拔弩張的情況下,父親通常會選擇當場斷絕父子關係。然而,這父親卻以出奇的溫柔回應:「我兒!」他說:「雖然你公然侮辱我,我仍然想要你來參加宴會。我不僅不會與你的弟弟斷絕關係,更不會與你斷絕關係,我鼓勵你吞忍壓抑你的驕傲,進來享受筵席,但這需要你自己親自做決定,你願意嗎?」這真是一個出乎意料之外、充滿恩典與戲劇化的請求。
聽眾們坐立不安,引頸期盼,亟欲想知道這家庭會重新合一並相愛嗎?兩兄弟會盡釋前嫌嗎?大兒子會因這溫柔的邀請而心軟,而與父親和好嗎?
當這些臆測正在我們的意念中閃過,故事卻嘎然而止!為什麼主耶穌不把故事說完,直接告訴我們結局呢?因為這故事的主要對象是那些法利賽人,就是所謂的大兒子們!主耶穌在請求祂的仇敵們回應祂的信息,這信息是什麼呢?當我們愈明白理解主耶穌要傳達的核心信息時,這答案將出現在本書後面章節。簡言之,主耶穌正在重新定義一切我們自以為與上帝連結的方式。祂親自要重新定義什麼是罪、失喪的意義、以及何謂得救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