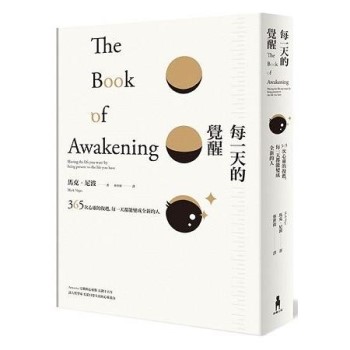一月二十四日 萬事皆奇蹟
有兩種方式過生活。一種是看任何事都不認為是奇蹟。另一種則是:看一切都像是奇蹟。
--愛因斯坦
擔憂是沒有盡頭的。因為我們目光有限,凡視野不能及的事物也是沒有盡頭的。擔憂只是一種賭博,賭著什麼可能發生,什麼可能不會發生。
我有一個朋友在鄉間發生爆胎,車上沒有修車用的千斤頂。於是他開始步行,希望找到願意伸出援手的農夫。天色漸黑,蟋蟀鳴叫漸響,他走在雜草蔓生的道上,心中丟擲著那顆擔憂的骰子:要是農夫不在家怎麼辦?要是他在家卻不讓我使用他的千斤頂呢?他肯不肯借我電話?他會不會被我嚇到?奇怪,我又沒有惡意,他為什麼不讓我用電話!
等到終於敲著農家的門,我那朋友的內心已盤據了所有可能的壞結果。一位友善的老農人應門時,我的朋友對著他怒吼:「好啊,你就留著那爛透的千斤頂自己用吧!」
人生在世,我們勉力於面對「是」,努力不跌入「不是」的黑洞裡,這確實是自古以來的挑戰,一如幾世紀前的蘇菲派詩人迦利布(Ghalib)說的:「天地一切受造之物的每一分子都吟唱著何者為是,何者為不是。聽見了是,你將得到智慧;聽見了不是,你將陷入崩潰。」
靜靜坐著,想著一個讓你擔憂的情境。
放慢吸氣的速度,專注於接受「它是什麼」,試著接納眼前的恩賜與困頓。
均勻吐氣,專注地把「它不是什麼」的想法慢慢釋放掉,試著放下所有還只是想像但尚未成真的結果。
把自己安放在「是」所成就的奇蹟之中。
一月三十日 做一個朝聖者
旅行卻不被改變,是謂游牧民族。
改變卻不旅行,是謂變色蜥蜴。
旅行且被旅行改變,是謂朝聖者。
一開始我們都是朝聖者,想要旅行,也希望被旅行改變。然而,聆聽管弦樂演奏不久,一定會被小提琴或鋼琴的旋律吸引,最後便只欣賞樂團中某一特定樂器。同理,對生命的關注也會脫離軌道,我們經驗著人事時地物,卻沒有領受他們的整體。而有些時候,我們感到孤單又沒有信心,便會刻意改變以求取悅他人或逃避他人,並隱藏真實的內在。
有此觀察,並不是要譴責我們自己,而是要幫助彼此領悟到一件事:追求內外的合一,乃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人性總有疏誤,我們必須不斷讓內在與外在的經驗互相補充,以臻圓滿。
我太了解這些,因我太常在這過程中犯錯。但,我跟你一樣,也把自己視為最深刻意義之下的朝聖者,旅行於一切風俗教條之上,走向那個終於使我們得以領悟的時刻,並且被它改變。那個時刻,不可思議且轉瞬而逝,當我們的眼睛就是我們所看見的,而我們的心就是我們所感受的,那個時刻會讓我們知道,凡是真實的就是神聖的。
集中心神。不帶任何批判,想著一個你不願意被改變的時刻。好好感受那個時刻。
隨著呼吸,想起你為了讓別人高興或者想躲避他人而改變自己的時候。再一次,好好感受那個時刻。
放鬆身體,想著自己向前旅行,並被旅行改變的時刻。感受那個時刻。
不帶任何批判,帶著感激之情接受這全部的時刻。感激自己能生而為人。
二月十四日 一見鍾情
若兩方都深思熟慮,愛則渺渺。有誰愛過而不是一見鍾情?
--克里斯多夫.馬婁(Christopher Marlowe)
一見鍾情的真正力量往往被誤解了。因為我們認定的「一見鍾情」是指初次遇見的時刻便對某人傾心。然而它有更深的意涵,我們必須重新發掘並定義所謂的「第一眼」,那應該是指本質上的初次看見,而非從事相上而言。
畢竟,我們都帶著習慣與規律,將生活視為理所當然。而擁有那「第一眼」,可以開啟每分每秒的新鮮,不受習氣或規則綁縛。那一瞬間,我們透過上帝之眼看、透過心靈之眼看、透過靈魂之眼看,於焉頓悟,感到合一,深受撼動,一切都不再成為阻礙。
每一種關乎性靈的信仰都提到了一見鍾情。是它讓我們清醒,這般的觀看恢復了生存的意義。矛盾的是,這樣的第一眼竟是循環的,我們每天睜眼醒來,覺醒的靈魂都會如何遵循節奏一般地回到這樣的初次相見。當我們能以最原初的眼光觀看事物,讓自己與周遭的生命毫無阻隔,自然會愛上一切。觀看本質,使我們可以敞開胸懷去愛。愛上本質,世界遂成為生機勃勃。所以,一見鍾情是這樣體現的:第一眼,我們發現愛;是因為我們真正看見了,於是被早已存在那裡的愛觸動。
於是,「第一眼」成為了一道門檻,通過它,可以走向存在的壯闊華美。它確切而美妙地發生在人與人的關係裡,當我們真正看見某人,便甜甜墜入他們存在的奇蹟。而這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可能的,當我們一次又一次真正看見自己、看見世界、看見我們心中的上帝。
我可能每天都和同樣一群人一起工作而毫無感覺,但某一天,痛苦把我敞開,也許某道光線剛好劃過某人臉龐,我可能這才第一次發現他們,而生出愛。我可能每天走過同一株柳樹,一季復一季,直到某天雨後的光澤或微風的低拂,我終於看見以往忽略的它,然後對心中那株柳樹生出愛。我也有可能在夜半鏡中看著倒影萬千次,最後終於在自己倦容裡找到那株樹、那道光、那群別人,那個我們覺察的上帝。
事實上,所謂第一眼的重點不在於第一次見面,雖然也可能是在第一次見面時發生這第一眼的領悟,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真正看見。當我們筋疲力竭,終於停止說話、停止表演、停止假裝,如同微風吹盡,水面終於無波,我們也變得清澈,而那顆休憩於萬物的心,將在我們的眼前跳動。
閉上眼,透過呼吸釋放你心所看見的,過去的視野、未來的視野,以及創傷的視野。
隨著每一口緩慢的呼吸,感受到空氣流動來自你最初的視野,你的第一眼。
緩慢呼吸,想像你的心跳承載著一切原初的視野。
當你得到那原始的感受,無論多麼短暫,就在那時睜開雙眼,帶著愛,對你見到的第一個事物鞠躬。
有兩種方式過生活。一種是看任何事都不認為是奇蹟。另一種則是:看一切都像是奇蹟。
--愛因斯坦
擔憂是沒有盡頭的。因為我們目光有限,凡視野不能及的事物也是沒有盡頭的。擔憂只是一種賭博,賭著什麼可能發生,什麼可能不會發生。
我有一個朋友在鄉間發生爆胎,車上沒有修車用的千斤頂。於是他開始步行,希望找到願意伸出援手的農夫。天色漸黑,蟋蟀鳴叫漸響,他走在雜草蔓生的道上,心中丟擲著那顆擔憂的骰子:要是農夫不在家怎麼辦?要是他在家卻不讓我使用他的千斤頂呢?他肯不肯借我電話?他會不會被我嚇到?奇怪,我又沒有惡意,他為什麼不讓我用電話!
等到終於敲著農家的門,我那朋友的內心已盤據了所有可能的壞結果。一位友善的老農人應門時,我的朋友對著他怒吼:「好啊,你就留著那爛透的千斤頂自己用吧!」
人生在世,我們勉力於面對「是」,努力不跌入「不是」的黑洞裡,這確實是自古以來的挑戰,一如幾世紀前的蘇菲派詩人迦利布(Ghalib)說的:「天地一切受造之物的每一分子都吟唱著何者為是,何者為不是。聽見了是,你將得到智慧;聽見了不是,你將陷入崩潰。」
靜靜坐著,想著一個讓你擔憂的情境。
放慢吸氣的速度,專注於接受「它是什麼」,試著接納眼前的恩賜與困頓。
均勻吐氣,專注地把「它不是什麼」的想法慢慢釋放掉,試著放下所有還只是想像但尚未成真的結果。
把自己安放在「是」所成就的奇蹟之中。
一月三十日 做一個朝聖者
旅行卻不被改變,是謂游牧民族。
改變卻不旅行,是謂變色蜥蜴。
旅行且被旅行改變,是謂朝聖者。
一開始我們都是朝聖者,想要旅行,也希望被旅行改變。然而,聆聽管弦樂演奏不久,一定會被小提琴或鋼琴的旋律吸引,最後便只欣賞樂團中某一特定樂器。同理,對生命的關注也會脫離軌道,我們經驗著人事時地物,卻沒有領受他們的整體。而有些時候,我們感到孤單又沒有信心,便會刻意改變以求取悅他人或逃避他人,並隱藏真實的內在。
有此觀察,並不是要譴責我們自己,而是要幫助彼此領悟到一件事:追求內外的合一,乃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人性總有疏誤,我們必須不斷讓內在與外在的經驗互相補充,以臻圓滿。
我太了解這些,因我太常在這過程中犯錯。但,我跟你一樣,也把自己視為最深刻意義之下的朝聖者,旅行於一切風俗教條之上,走向那個終於使我們得以領悟的時刻,並且被它改變。那個時刻,不可思議且轉瞬而逝,當我們的眼睛就是我們所看見的,而我們的心就是我們所感受的,那個時刻會讓我們知道,凡是真實的就是神聖的。
集中心神。不帶任何批判,想著一個你不願意被改變的時刻。好好感受那個時刻。
隨著呼吸,想起你為了讓別人高興或者想躲避他人而改變自己的時候。再一次,好好感受那個時刻。
放鬆身體,想著自己向前旅行,並被旅行改變的時刻。感受那個時刻。
不帶任何批判,帶著感激之情接受這全部的時刻。感激自己能生而為人。
二月十四日 一見鍾情
若兩方都深思熟慮,愛則渺渺。有誰愛過而不是一見鍾情?
--克里斯多夫.馬婁(Christopher Marlowe)
一見鍾情的真正力量往往被誤解了。因為我們認定的「一見鍾情」是指初次遇見的時刻便對某人傾心。然而它有更深的意涵,我們必須重新發掘並定義所謂的「第一眼」,那應該是指本質上的初次看見,而非從事相上而言。
畢竟,我們都帶著習慣與規律,將生活視為理所當然。而擁有那「第一眼」,可以開啟每分每秒的新鮮,不受習氣或規則綁縛。那一瞬間,我們透過上帝之眼看、透過心靈之眼看、透過靈魂之眼看,於焉頓悟,感到合一,深受撼動,一切都不再成為阻礙。
每一種關乎性靈的信仰都提到了一見鍾情。是它讓我們清醒,這般的觀看恢復了生存的意義。矛盾的是,這樣的第一眼竟是循環的,我們每天睜眼醒來,覺醒的靈魂都會如何遵循節奏一般地回到這樣的初次相見。當我們能以最原初的眼光觀看事物,讓自己與周遭的生命毫無阻隔,自然會愛上一切。觀看本質,使我們可以敞開胸懷去愛。愛上本質,世界遂成為生機勃勃。所以,一見鍾情是這樣體現的:第一眼,我們發現愛;是因為我們真正看見了,於是被早已存在那裡的愛觸動。
於是,「第一眼」成為了一道門檻,通過它,可以走向存在的壯闊華美。它確切而美妙地發生在人與人的關係裡,當我們真正看見某人,便甜甜墜入他們存在的奇蹟。而這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可能的,當我們一次又一次真正看見自己、看見世界、看見我們心中的上帝。
我可能每天都和同樣一群人一起工作而毫無感覺,但某一天,痛苦把我敞開,也許某道光線剛好劃過某人臉龐,我可能這才第一次發現他們,而生出愛。我可能每天走過同一株柳樹,一季復一季,直到某天雨後的光澤或微風的低拂,我終於看見以往忽略的它,然後對心中那株柳樹生出愛。我也有可能在夜半鏡中看著倒影萬千次,最後終於在自己倦容裡找到那株樹、那道光、那群別人,那個我們覺察的上帝。
事實上,所謂第一眼的重點不在於第一次見面,雖然也可能是在第一次見面時發生這第一眼的領悟,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真正看見。當我們筋疲力竭,終於停止說話、停止表演、停止假裝,如同微風吹盡,水面終於無波,我們也變得清澈,而那顆休憩於萬物的心,將在我們的眼前跳動。
閉上眼,透過呼吸釋放你心所看見的,過去的視野、未來的視野,以及創傷的視野。
隨著每一口緩慢的呼吸,感受到空氣流動來自你最初的視野,你的第一眼。
緩慢呼吸,想像你的心跳承載著一切原初的視野。
當你得到那原始的感受,無論多麼短暫,就在那時睜開雙眼,帶著愛,對你見到的第一個事物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