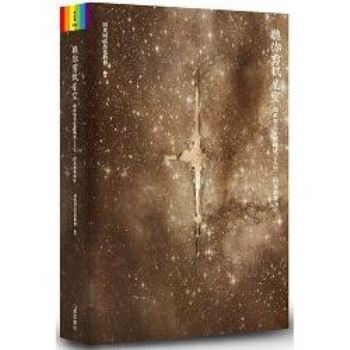仍然在路上
文◎陳煒仁(查令)
小的時候
我的記憶從幼稚園開始。當時剛進入到那所斜坡下的學校,帶著眼淚,我進入到教室當中。連續一個星期,止不住的眼淚,在收到一台模型動力船之後似乎收斂了起來。在船真的能航行在大臉盆的時候,那一天放學前,我看見了那位戴著眼鏡的男孩,比我長一個年級,教室在圖書館的旁邊,有一小群人圍著他,彼此在說話,散發出來的氣息,吸引著我。由於我是半途入學,而那個男孩沒有多久就畢業,並沒有太多可以互動的機會。
我和女同學之間的互動,一直比和男同學好很多,也因此,我常被認為是屬於女生那群的人,只和少數的男同學保持特別好的互動。有一次的打鬧當中,男同學們公開地認為我不屬於男生的群體,並認為我的動作舉止像極了女孩子,幫我取了一個「娘娘腔」的外號。某一次的體育課後,有口渴的男同學在找水喝,我遞出我的水壺,卻得到「我不敢喝你的水,怕變得和你一樣」的回應。在小學高年級時,越加和女同學走得近,和男同學的距離似乎更遠,他們時常會傳著「某某女生喜歡你」,或是已經在交往的消息,是不是有人覺得我刻意地喬裝靠近女生、近水樓台呢?班導師在某一次月考的成績單公佈的那天,看著排名第一的我說:「這是讓陳煒仁揀到的。」我覺得他並不喜歡我,也沒有因為我的學習結果而給適當的讚美或肯定,原因可能在於我不夠像個男生。
轉換到國中的那個暑假,我常常作惡夢。那個年代,學區的國中規定男生要理三分頭。不知道為什麼,我非常地抗拒,直到新生訓練前一天,我才被爸爸壓著去理了頭髮,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便利商店,我感覺羞愧低著頭走進去,風的流動異常的冷。隔天,我被分配到和一位國小同學同班的班級,我不敢和任何人說話,下課時留到教室沒有人了,才覺得可以安心離開。但是,剛走到門口,其他的國小同學們正好走過,高聲呼喊著:「快來看!陳煒仁也剪短頭髮!」除了三分頭,衣服與鞋子都在被嚴格要求的範圍,校長表示這是學校的傳統,多少人因為這樣考上了南一中與省南女。不知道為什麼,老師總是會指定我擔任班上的幹部,並且總是認為我扮演還不錯的角色。這在我某次沒有擔任職務時有了新的認識:沒有班長、幹部與股長的名稱之後,和我說話的人變少了,並且會有人對我做出言語及肢體的侵犯。「身份是一種保護,但成績不是。」在現在解讀起來,似乎是這樣子的。
男女分班的結構裡,嚴格禁止跨越建築物分隔與異性接觸,我和要好的女同學們被分開了,得在男孩圈裡打轉著。偶爾仍有女同學走過窗邊,丟下小東西或是信件,就匆匆離開,這些東西常被班上其他同學當成是娛樂與嘲諷的內容。每個年級都重分班一次,不同的成員組合,反倒是讓我在班上欣賞不同類型的男同學,只是他們似乎不會和我靠近。
有幾個男同學私下傳著我沒有小雞雞的謠言,並且跟著我進到廁所想要驗明正身。一開始,我只覺得無聊,就像是小學時,男生們流行玩著碰觸彼此的小雞雞一樣,我從不參與這樣的活動。有一段時間,有三位同學總約好要一塊來檢驗,一開始只是打鬧著,後來,他們卻認真了起來,其中一位在樓梯口堵住我的去路,後來他在我背上吐了口痰,才讓我進了教室。升上二年級,我竟和這三位同學被編在同一班。開學沒多久的一次下課,我以為他們去買午餐吃,自己去了廁所。他們三人突然地出現,圍住正在如廁的我說,今天終於可以看個清楚。隨即其中一個拉住了我的褲子,另二個伸長了脖子探了個究竟。我不知道他們看見了什麼,兩個人哇的一聲之後,就消失在那個空間。之後,就沒有再來煩過我。現在每每看見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故事,就會想起這段躲藏上廁所不堪的日子。
其實,我後來才辨認出,那三位同學也不同於其他男同學,不僅幾乎貼在一起做每一項活動,也交換著一些常用的東西。後來,他們的態度轉變,向我示好,並邀我參與他們的活動,而且向我道歉。
看見兩兩並肩同行的男生,總會很吸引我的目光:在夏天的傍晚,樹林下。
靠著好運氣,我進入地區最好的高中,告別了慘綠的國中生活與三分頭。一直坐在我旁邊的那位說著怪異華語腔調的屏東男孩,讓我不禁要糾正他的口音;也因為他近乎完美的數學與體育表現,讓我喜歡找他求教、靠近他。騎著單車,補習班、棒球場以及育樂街的小吃店,都是兩個人共同的記憶。暑期輔導時,我們分到不同的班級。那天早上,他在教室門口等我,一起走到小福利社買了紙盒牛奶,再走回教室門口,我們一直說話,在老師出現在走廊盡頭時,我們才分頭才飄進了教室。那天中午,他在樹下等我一起去吃了午餐。隔天,我收到一張三位數定價的進口卡片,以及一隻小白熊布偶。之後的每一天早餐、午餐與放學時,在樹下,都可以看見他。
後來才知道,我們共同參加的那個社團,儼然是個性別友善的自然聚集體,不愧是一個追求實踐愛的群體。參與的成員,在後來陸續聯絡與彼此坦誠,竟都不是異性戀。「聚集」的過程,是自然發生的,那時我還不懂什麼G-Dar,「同性戀」其實仍很不清楚也不常用的名詞。
有人曾告訴過我:「你和隔壁班的某位同學很像,但是他更嚴重。」在運動場結束了棒球的活動之後,走向車棚路上,我看見那位「更嚴重」的同學,坐在另一位男同學單車的後座上,說著話從校門前經過。「他都會扭動屁股,然後很多人喜歡他。」可是我沒有這樣的習慣啊!「若你是女生,我就會來追你。」一年級的時候,某位同學在下課之後,站在扶梯上大聲告訴我,之後就轉身離開。
那年聯考,我們的成績都很糟。被家人安排到不同的補習班去,而我們在下課之後仍一起吃點東西才各自回家。有一天,我騎著單車在補習班樓下等著,看著他走向我,說他的家人打電話來,要我們不要再碰面,而補習班也不會再對我開門。在那一段時間裡,除了無趣的冷氣房之外,我時常被內在的情緒擄掠,不停地與之爭鬥。騎著單車繞到他的補習班,望著樓梯上下的人,卻都沒有見到他。偶爾,接到他的電話,會平靜一些,但是在掛上電話之後又會掉到漩渦中。這一年,許佑生和葛瑞舉辨了婚禮,我在電視上看見了,告訴他:「在一起是兩個人的決定,不是嗎?」「不,是兩個家族的事,我家不會准的。」
第二次參與的聯考,自然組的他先完成,選社會組的我慢一天才考完。他在考完那天,帶了一份熱仙草按了我家的電鈴,要我隔天的考試加油。他是偷溜出來的,很快就又離開了,我知道這是很大的心意。等待放榜的那幾天,我竟硬著頭皮到了他屏東的家裡,卻感受到和原本很熟悉的他的家人們之間的距離。特別是他的媽媽,在言語當中總有讓我覺得刺耳的用詞。放榜時,我幸運地錄取了北部國立大學熱門的科系,他卻考得不太理想。幾天後,他轉告家人請我離開的消息,我從他的眼神中讀出複雜的情緒。
帶著行李,我們坐在海堤上。海風不停地吹著,他問我要不要喝點什麼打破了沉靜,我告訴他我很生氣也很難過。搭上火車之後,靠著電話仍能有些維繫:我打過去的電話一定找不到他,只能等他在無人之時的主動聯絡。上了大學,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斷斷續續地聯絡著遠距離的互動關係,後來,我想他有其他的追求者,就淡了。
離鄉與追尋
在這位於木柵山邊的大學就讀,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靠著搭公車過生活的我,乾脆就盡量不出門了。那時在校園的風雨走廊,都會看見地下的性別社團偷渡在其他社團的佈告欄上面的活動宣傳,我總在沒有人的時刻駐足,看著泛黃的影印紙與許久沒有更新的內容與郵政信箱,但我從沒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可能因為我實在太不主動,害怕「曝光」,也聽聞「他們很亂」,我從沒有機會認識傳說中系上的「四朵花」學弟,以及一個正在形成的同志社群。
我開始在圖書館裡找相關書籍,也好奇在某間24小時營業的書店的神秘的「性別研究」書櫃裡,到底放了什麼書呢?每次走到那區域,都要多留意一下身邊有沒有「特別的人」與認識的人,非得等到四下無人了才敢走近。有一天夜裡,朋友帶我去「朝聖」,告訴我雜誌區是大家彼此打量的地方,性別研究其實都是兩性關係與身體保健,沒啥有趣的,而且看我模樣保證我可以「平安去平安回來。」我也曾按著書上寫的去「新公園」做考查,當然什麼也沒有看見。BBS與剛流行起來的網際網路與網頁當中「%」與「@」的暗號,是能找到「朋友」的另一個管道。在這樣的互動關係當中,我發現自己好孤單,需要被人聆聽以及解答心中種種疑問,這些「網友」幾乎都只存留在NetTerm的黑底畫面上。我還記得幾位曾見過面的朋友,大多數是同學校的他系同學,我大概太需要他們了,這壓力導致他們大多無法與我持續互動下去,但是我同時間也從不同人的留言裡發現,其實不只我一個孤單。系上的學姊可能很早就發覺我的情況,並會主動發些訊息與邀約,好讓我有喘氣的機會。
暑假,我搭上往台南的復興號。鄰座一位女生跟我交換了許多閱讀的經驗,並向我介紹聖經與她所認識的上主。開學後,搭上237公車到這間信義宗教會參與一個學期的活動,我確實在那裡感受到團契的生活。包括出車禍住院的期間,實際的探訪與真實可見的關懷行動,使我覺得這意外來得正是時候。後來我停止去那教會,可能是那股使人窒息的「愛」,把我推出了圈圈之外。某種生命的樣態、信仰的模版與價值觀點,一步步地包圍我的生命,被侵犯的感覺常常在參與聚會的過程裡蔓延。大家說這是「信仰」,而我裡頭有不屬上主的「東西」。
大三,我搬出了宿舍,在校門對面租房子,這是我生命轉折的開始:成績開始有起色,修心理與哲學的課程,並且和幾位同學有比較深入的互動。而最開展的是「家人」的關係,我成為租屋處家庭的一份子,承擔一部份的責任與義務,也被疼愛著。我該怎麼表達這個情況呢?就是:回家有飯吃,考試時有人會在祖先牌位前唸唸有詞,變瘦了會有人挾大塊肉在碗裡,生病有人會大罵快去看醫生,幫忙照顧一下小孩的學校功課與去河堤打球,阿公過世那年一起折蓮花,並全程參與了喪葬的過程……「我在台北的家人」是我向爸媽介紹時的用詞。
我和姊姊、姊夫、妹妹與弟弟之間的互動,讓我重新認識自己,我也練習向他們坦露內心的想法,並且從中得到支持,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階段。我想也因為這樣,在現在我能稍微與人互動時,少了一點生硬與多了一些友善。雖然租屋處隔壁就是一間教會,而我非但沒有走過去,也發現原來街坊們並不怎麼喜歡出入其中的人。一直到畢業服役時,爸爸的一場手術讓我又想起信義會的朋友,透過電話的代禱讓我那夜可以安然睡著。這真是一個複雜的情感,在退伍之後仍舊回到信義會聚會,而且很認真地認識這個信仰,也更發現裡頭混雜著許多我弄不清楚的規範與堅持。
基督宗教與同志遊行
2003年,我開始很大量地接觸性別議題與團體。其中一項是參與熱線的助人工作訓練擔任接線志工。志工訓練時,分成數個小組,讓我們認識彼此的生命故事。對我來說,可真是苦了,要將自己的過去再一次地拿出來與眾人分享。但大家冷靜的回應著實讓我覺得失望,自以為是天下最痴情的故事,在身旁的人看來,頂多只有一些些的感動;若要比誰比較「慘」,我可能無法入圍。
因為參與志工訓練,與教會聚會時間有衝突時,我難以言明。我說:去參與了助人的訓練,卻無法坦白地說出受訓的單位,教會的朋友則不斷詢問並覺得不解,有什麼可以比教會的聚會還有更高的優先性?
在接線室裡,一通又一通的電話打來,訴說著他們在家庭裡無法真實地活出自己、與家人對立的張力、在信仰群體裡被當成鬼附身的、不聖潔的、要受到醫治與釋放的人、被迫離開服事位置,甚至在改變性傾向之前不再歡迎他回到團體中來,有些則是完全不敢出櫃,因為他的家人也都在教會裡服事,而且還是長老,擔心會影響他們,可是自己又很喜歡團契裡的哪位可愛的弟兄……教會真的有人願意了解這群人嗎?那年(2003),第一屆台北同志遊行在二二八公園展開,我是其中一位志工,被分配帶領第一個隊伍:同光教會。記得那天在公園裡走著,一位面熟的女生向我走來,是過去同一間教會的朋友。我問她:「你為什麼也在這裡?」然後,我們都笑了。她告訴我後來發生的事,她向小組長及牧師出櫃,但是得到很負面的回應,讓她感受到熱絡互動背後的虛假,再也無法再相信傳道人及這個宗教團體。我突然明白我所感受的那奇怪氛圍,正是「虛假」。那天接下來的震撼是,時任同光教會駐堂牧師的曾恕敏牧師,在遊行前登上了領頭車,帶著在場500名的遊行者一起做了祈禱,在沿路這群教會的肢體唱著我也熟悉的詩歌,「同志也可以是基督徒」的想法深印在我心底。年底,我離開信義會,轉到同光教會。
一間同志教會所帶來的衝擊
我記得第一次到同光教會參加主日禮拜,是已經參與了一段時間的家庭小組之後才去的。第一次去,對於隱身在老舊大樓裡的秘密團體充滿想像。那一天,我坐在第三排的位置,一位看起來是T的姊妹打鼓,一位弟兄彈琴,一位姊妹領唱。我以為坐在我前兩排的是男生,在與「他們」擁抱問好時,「他們」比我更大方。在會後午餐時,才知道「他們」都是姊妹,我大為吃驚。這對於我想像中的LGBT分類,衝擊實在很巨大。更妙的是,我竟然很快地被邀請參與聖誕晚會的演出,反串當時知名的少女團體Sweety;我現在想起來並不特別,看看那群被我誤以為「弟兄」的姊妹,我應該更合適成為「姊妹」的弟兄。那一年,同光教會租借了某大學的場地舉辨聖誕晚會,後來也年年舉辦了好一段時間。後來,我進行一些自認為是了不起的實踐:留起了長髮。我現在才比較明白,其實這就是「酷兒」(Queer)的生命展演實踐(performativity)。在一位HIV的室友啟發與鼓勵下,我開始參與露德協會的志工。同時間,我也在教會裡參與服事。在這間以男、女同志為主要成員的教會裡,並不如想像地對於不同的類屬的人都是友善的。一位跨性別的朋友,在會友普遍缺乏了解以及對於認同邊界被侵犯的焦慮下,經生理女性的小組成員投票,拒絕其出席小組聚會。相似「不被接納」的情況也出現在我所服事的小組成員身上,我深刻地意識到:一個受到歧視的群體,仍會再複製這個歧視的結構,而且充滿正當性:一個明確的「認同」劃分著你該屬哪一類以及應有的行動規範。
由於更有機會聆聽不同的生命故事,我理解到性的實踐在每個人的生活當中都不同。但似乎仍有一個樣版在這個信仰群體裡,套用著大家所拋棄的原生教會的倫理價值:什麼是聖潔?這個疑問似乎一直很難被眾說紛紜的「大道理」給解答,我感受到加諸在這些生命故事上另一種來自「自己人」的壓迫與網羅。
「我可以喜歡誰?」成為我的困擾。「同性戀」只能喜歡相同性別的人嗎?如果不這樣,還是「同性戀」嗎?「雙性戀」的位置在哪裡呢?「跨性別」到底是要喜歡哪種人才「可以」?以「性取向」為身分認同的標籤,困住了我的想法與生活。有一長段時間,我詢問「愛」與「喜歡」的議題:我好像可以喜歡很多人,對不同的人都欣賞也被吸引,但是,什麼是愛呢?原來,愛也很有「限制」。
向媽媽出櫃,是在邀請她來參加教會聖誕晚會的前一晚。在電話中,我支支吾吾,媽媽卻明白地說:「來,你直接講。」當我說完了之後,媽媽並沒有等待我喘過氣來,反問:「你現在才講,我和爸爸在你國小的時候就在討論這件事情了。……你有沒有向爸爸提?」隔天,表姊告訴我:「你一出場,阿嬸就高興地哭了……並且說:「沒錯,這就是他啦!」我還記得媽媽在演出前遞給我,那份從台南帶上來的飯糰、飲料與那番加油鼓勵的話。2008年5月21日,楊雅惠牧師離開了我們。在收到消息之後,仍覺得不真實:一位勇敢面對父權體系的同志教會建立者,用燒炭的方式解束自己的生命,回到上主那裡去服事他。在台中的那場告別式裡,我又再一次感受到「虛假」充斥在每個環節裡,謊言也在那場合裡散佈著。一直跟到了火葬場,這一切卻沒有隨著楊牧師離開,每雙哭紅的眼睛與無法述說的難過情感,從那裡蔓延開來。那天,我下定決心要朝成為傳道人跨出腳步。
文◎陳煒仁(查令)
小的時候
我的記憶從幼稚園開始。當時剛進入到那所斜坡下的學校,帶著眼淚,我進入到教室當中。連續一個星期,止不住的眼淚,在收到一台模型動力船之後似乎收斂了起來。在船真的能航行在大臉盆的時候,那一天放學前,我看見了那位戴著眼鏡的男孩,比我長一個年級,教室在圖書館的旁邊,有一小群人圍著他,彼此在說話,散發出來的氣息,吸引著我。由於我是半途入學,而那個男孩沒有多久就畢業,並沒有太多可以互動的機會。
我和女同學之間的互動,一直比和男同學好很多,也因此,我常被認為是屬於女生那群的人,只和少數的男同學保持特別好的互動。有一次的打鬧當中,男同學們公開地認為我不屬於男生的群體,並認為我的動作舉止像極了女孩子,幫我取了一個「娘娘腔」的外號。某一次的體育課後,有口渴的男同學在找水喝,我遞出我的水壺,卻得到「我不敢喝你的水,怕變得和你一樣」的回應。在小學高年級時,越加和女同學走得近,和男同學的距離似乎更遠,他們時常會傳著「某某女生喜歡你」,或是已經在交往的消息,是不是有人覺得我刻意地喬裝靠近女生、近水樓台呢?班導師在某一次月考的成績單公佈的那天,看著排名第一的我說:「這是讓陳煒仁揀到的。」我覺得他並不喜歡我,也沒有因為我的學習結果而給適當的讚美或肯定,原因可能在於我不夠像個男生。
轉換到國中的那個暑假,我常常作惡夢。那個年代,學區的國中規定男生要理三分頭。不知道為什麼,我非常地抗拒,直到新生訓練前一天,我才被爸爸壓著去理了頭髮,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便利商店,我感覺羞愧低著頭走進去,風的流動異常的冷。隔天,我被分配到和一位國小同學同班的班級,我不敢和任何人說話,下課時留到教室沒有人了,才覺得可以安心離開。但是,剛走到門口,其他的國小同學們正好走過,高聲呼喊著:「快來看!陳煒仁也剪短頭髮!」除了三分頭,衣服與鞋子都在被嚴格要求的範圍,校長表示這是學校的傳統,多少人因為這樣考上了南一中與省南女。不知道為什麼,老師總是會指定我擔任班上的幹部,並且總是認為我扮演還不錯的角色。這在我某次沒有擔任職務時有了新的認識:沒有班長、幹部與股長的名稱之後,和我說話的人變少了,並且會有人對我做出言語及肢體的侵犯。「身份是一種保護,但成績不是。」在現在解讀起來,似乎是這樣子的。
男女分班的結構裡,嚴格禁止跨越建築物分隔與異性接觸,我和要好的女同學們被分開了,得在男孩圈裡打轉著。偶爾仍有女同學走過窗邊,丟下小東西或是信件,就匆匆離開,這些東西常被班上其他同學當成是娛樂與嘲諷的內容。每個年級都重分班一次,不同的成員組合,反倒是讓我在班上欣賞不同類型的男同學,只是他們似乎不會和我靠近。
有幾個男同學私下傳著我沒有小雞雞的謠言,並且跟著我進到廁所想要驗明正身。一開始,我只覺得無聊,就像是小學時,男生們流行玩著碰觸彼此的小雞雞一樣,我從不參與這樣的活動。有一段時間,有三位同學總約好要一塊來檢驗,一開始只是打鬧著,後來,他們卻認真了起來,其中一位在樓梯口堵住我的去路,後來他在我背上吐了口痰,才讓我進了教室。升上二年級,我竟和這三位同學被編在同一班。開學沒多久的一次下課,我以為他們去買午餐吃,自己去了廁所。他們三人突然地出現,圍住正在如廁的我說,今天終於可以看個清楚。隨即其中一個拉住了我的褲子,另二個伸長了脖子探了個究竟。我不知道他們看見了什麼,兩個人哇的一聲之後,就消失在那個空間。之後,就沒有再來煩過我。現在每每看見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故事,就會想起這段躲藏上廁所不堪的日子。
其實,我後來才辨認出,那三位同學也不同於其他男同學,不僅幾乎貼在一起做每一項活動,也交換著一些常用的東西。後來,他們的態度轉變,向我示好,並邀我參與他們的活動,而且向我道歉。
看見兩兩並肩同行的男生,總會很吸引我的目光:在夏天的傍晚,樹林下。
靠著好運氣,我進入地區最好的高中,告別了慘綠的國中生活與三分頭。一直坐在我旁邊的那位說著怪異華語腔調的屏東男孩,讓我不禁要糾正他的口音;也因為他近乎完美的數學與體育表現,讓我喜歡找他求教、靠近他。騎著單車,補習班、棒球場以及育樂街的小吃店,都是兩個人共同的記憶。暑期輔導時,我們分到不同的班級。那天早上,他在教室門口等我,一起走到小福利社買了紙盒牛奶,再走回教室門口,我們一直說話,在老師出現在走廊盡頭時,我們才分頭才飄進了教室。那天中午,他在樹下等我一起去吃了午餐。隔天,我收到一張三位數定價的進口卡片,以及一隻小白熊布偶。之後的每一天早餐、午餐與放學時,在樹下,都可以看見他。
後來才知道,我們共同參加的那個社團,儼然是個性別友善的自然聚集體,不愧是一個追求實踐愛的群體。參與的成員,在後來陸續聯絡與彼此坦誠,竟都不是異性戀。「聚集」的過程,是自然發生的,那時我還不懂什麼G-Dar,「同性戀」其實仍很不清楚也不常用的名詞。
有人曾告訴過我:「你和隔壁班的某位同學很像,但是他更嚴重。」在運動場結束了棒球的活動之後,走向車棚路上,我看見那位「更嚴重」的同學,坐在另一位男同學單車的後座上,說著話從校門前經過。「他都會扭動屁股,然後很多人喜歡他。」可是我沒有這樣的習慣啊!「若你是女生,我就會來追你。」一年級的時候,某位同學在下課之後,站在扶梯上大聲告訴我,之後就轉身離開。
那年聯考,我們的成績都很糟。被家人安排到不同的補習班去,而我們在下課之後仍一起吃點東西才各自回家。有一天,我騎著單車在補習班樓下等著,看著他走向我,說他的家人打電話來,要我們不要再碰面,而補習班也不會再對我開門。在那一段時間裡,除了無趣的冷氣房之外,我時常被內在的情緒擄掠,不停地與之爭鬥。騎著單車繞到他的補習班,望著樓梯上下的人,卻都沒有見到他。偶爾,接到他的電話,會平靜一些,但是在掛上電話之後又會掉到漩渦中。這一年,許佑生和葛瑞舉辨了婚禮,我在電視上看見了,告訴他:「在一起是兩個人的決定,不是嗎?」「不,是兩個家族的事,我家不會准的。」
第二次參與的聯考,自然組的他先完成,選社會組的我慢一天才考完。他在考完那天,帶了一份熱仙草按了我家的電鈴,要我隔天的考試加油。他是偷溜出來的,很快就又離開了,我知道這是很大的心意。等待放榜的那幾天,我竟硬著頭皮到了他屏東的家裡,卻感受到和原本很熟悉的他的家人們之間的距離。特別是他的媽媽,在言語當中總有讓我覺得刺耳的用詞。放榜時,我幸運地錄取了北部國立大學熱門的科系,他卻考得不太理想。幾天後,他轉告家人請我離開的消息,我從他的眼神中讀出複雜的情緒。
帶著行李,我們坐在海堤上。海風不停地吹著,他問我要不要喝點什麼打破了沉靜,我告訴他我很生氣也很難過。搭上火車之後,靠著電話仍能有些維繫:我打過去的電話一定找不到他,只能等他在無人之時的主動聯絡。上了大學,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斷斷續續地聯絡著遠距離的互動關係,後來,我想他有其他的追求者,就淡了。
離鄉與追尋
在這位於木柵山邊的大學就讀,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靠著搭公車過生活的我,乾脆就盡量不出門了。那時在校園的風雨走廊,都會看見地下的性別社團偷渡在其他社團的佈告欄上面的活動宣傳,我總在沒有人的時刻駐足,看著泛黃的影印紙與許久沒有更新的內容與郵政信箱,但我從沒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可能因為我實在太不主動,害怕「曝光」,也聽聞「他們很亂」,我從沒有機會認識傳說中系上的「四朵花」學弟,以及一個正在形成的同志社群。
我開始在圖書館裡找相關書籍,也好奇在某間24小時營業的書店的神秘的「性別研究」書櫃裡,到底放了什麼書呢?每次走到那區域,都要多留意一下身邊有沒有「特別的人」與認識的人,非得等到四下無人了才敢走近。有一天夜裡,朋友帶我去「朝聖」,告訴我雜誌區是大家彼此打量的地方,性別研究其實都是兩性關係與身體保健,沒啥有趣的,而且看我模樣保證我可以「平安去平安回來。」我也曾按著書上寫的去「新公園」做考查,當然什麼也沒有看見。BBS與剛流行起來的網際網路與網頁當中「%」與「@」的暗號,是能找到「朋友」的另一個管道。在這樣的互動關係當中,我發現自己好孤單,需要被人聆聽以及解答心中種種疑問,這些「網友」幾乎都只存留在NetTerm的黑底畫面上。我還記得幾位曾見過面的朋友,大多數是同學校的他系同學,我大概太需要他們了,這壓力導致他們大多無法與我持續互動下去,但是我同時間也從不同人的留言裡發現,其實不只我一個孤單。系上的學姊可能很早就發覺我的情況,並會主動發些訊息與邀約,好讓我有喘氣的機會。
暑假,我搭上往台南的復興號。鄰座一位女生跟我交換了許多閱讀的經驗,並向我介紹聖經與她所認識的上主。開學後,搭上237公車到這間信義宗教會參與一個學期的活動,我確實在那裡感受到團契的生活。包括出車禍住院的期間,實際的探訪與真實可見的關懷行動,使我覺得這意外來得正是時候。後來我停止去那教會,可能是那股使人窒息的「愛」,把我推出了圈圈之外。某種生命的樣態、信仰的模版與價值觀點,一步步地包圍我的生命,被侵犯的感覺常常在參與聚會的過程裡蔓延。大家說這是「信仰」,而我裡頭有不屬上主的「東西」。
大三,我搬出了宿舍,在校門對面租房子,這是我生命轉折的開始:成績開始有起色,修心理與哲學的課程,並且和幾位同學有比較深入的互動。而最開展的是「家人」的關係,我成為租屋處家庭的一份子,承擔一部份的責任與義務,也被疼愛著。我該怎麼表達這個情況呢?就是:回家有飯吃,考試時有人會在祖先牌位前唸唸有詞,變瘦了會有人挾大塊肉在碗裡,生病有人會大罵快去看醫生,幫忙照顧一下小孩的學校功課與去河堤打球,阿公過世那年一起折蓮花,並全程參與了喪葬的過程……「我在台北的家人」是我向爸媽介紹時的用詞。
我和姊姊、姊夫、妹妹與弟弟之間的互動,讓我重新認識自己,我也練習向他們坦露內心的想法,並且從中得到支持,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階段。我想也因為這樣,在現在我能稍微與人互動時,少了一點生硬與多了一些友善。雖然租屋處隔壁就是一間教會,而我非但沒有走過去,也發現原來街坊們並不怎麼喜歡出入其中的人。一直到畢業服役時,爸爸的一場手術讓我又想起信義會的朋友,透過電話的代禱讓我那夜可以安然睡著。這真是一個複雜的情感,在退伍之後仍舊回到信義會聚會,而且很認真地認識這個信仰,也更發現裡頭混雜著許多我弄不清楚的規範與堅持。
基督宗教與同志遊行
2003年,我開始很大量地接觸性別議題與團體。其中一項是參與熱線的助人工作訓練擔任接線志工。志工訓練時,分成數個小組,讓我們認識彼此的生命故事。對我來說,可真是苦了,要將自己的過去再一次地拿出來與眾人分享。但大家冷靜的回應著實讓我覺得失望,自以為是天下最痴情的故事,在身旁的人看來,頂多只有一些些的感動;若要比誰比較「慘」,我可能無法入圍。
因為參與志工訓練,與教會聚會時間有衝突時,我難以言明。我說:去參與了助人的訓練,卻無法坦白地說出受訓的單位,教會的朋友則不斷詢問並覺得不解,有什麼可以比教會的聚會還有更高的優先性?
在接線室裡,一通又一通的電話打來,訴說著他們在家庭裡無法真實地活出自己、與家人對立的張力、在信仰群體裡被當成鬼附身的、不聖潔的、要受到醫治與釋放的人、被迫離開服事位置,甚至在改變性傾向之前不再歡迎他回到團體中來,有些則是完全不敢出櫃,因為他的家人也都在教會裡服事,而且還是長老,擔心會影響他們,可是自己又很喜歡團契裡的哪位可愛的弟兄……教會真的有人願意了解這群人嗎?那年(2003),第一屆台北同志遊行在二二八公園展開,我是其中一位志工,被分配帶領第一個隊伍:同光教會。記得那天在公園裡走著,一位面熟的女生向我走來,是過去同一間教會的朋友。我問她:「你為什麼也在這裡?」然後,我們都笑了。她告訴我後來發生的事,她向小組長及牧師出櫃,但是得到很負面的回應,讓她感受到熱絡互動背後的虛假,再也無法再相信傳道人及這個宗教團體。我突然明白我所感受的那奇怪氛圍,正是「虛假」。那天接下來的震撼是,時任同光教會駐堂牧師的曾恕敏牧師,在遊行前登上了領頭車,帶著在場500名的遊行者一起做了祈禱,在沿路這群教會的肢體唱著我也熟悉的詩歌,「同志也可以是基督徒」的想法深印在我心底。年底,我離開信義會,轉到同光教會。
一間同志教會所帶來的衝擊
我記得第一次到同光教會參加主日禮拜,是已經參與了一段時間的家庭小組之後才去的。第一次去,對於隱身在老舊大樓裡的秘密團體充滿想像。那一天,我坐在第三排的位置,一位看起來是T的姊妹打鼓,一位弟兄彈琴,一位姊妹領唱。我以為坐在我前兩排的是男生,在與「他們」擁抱問好時,「他們」比我更大方。在會後午餐時,才知道「他們」都是姊妹,我大為吃驚。這對於我想像中的LGBT分類,衝擊實在很巨大。更妙的是,我竟然很快地被邀請參與聖誕晚會的演出,反串當時知名的少女團體Sweety;我現在想起來並不特別,看看那群被我誤以為「弟兄」的姊妹,我應該更合適成為「姊妹」的弟兄。那一年,同光教會租借了某大學的場地舉辨聖誕晚會,後來也年年舉辦了好一段時間。後來,我進行一些自認為是了不起的實踐:留起了長髮。我現在才比較明白,其實這就是「酷兒」(Queer)的生命展演實踐(performativity)。在一位HIV的室友啟發與鼓勵下,我開始參與露德協會的志工。同時間,我也在教會裡參與服事。在這間以男、女同志為主要成員的教會裡,並不如想像地對於不同的類屬的人都是友善的。一位跨性別的朋友,在會友普遍缺乏了解以及對於認同邊界被侵犯的焦慮下,經生理女性的小組成員投票,拒絕其出席小組聚會。相似「不被接納」的情況也出現在我所服事的小組成員身上,我深刻地意識到:一個受到歧視的群體,仍會再複製這個歧視的結構,而且充滿正當性:一個明確的「認同」劃分著你該屬哪一類以及應有的行動規範。
由於更有機會聆聽不同的生命故事,我理解到性的實踐在每個人的生活當中都不同。但似乎仍有一個樣版在這個信仰群體裡,套用著大家所拋棄的原生教會的倫理價值:什麼是聖潔?這個疑問似乎一直很難被眾說紛紜的「大道理」給解答,我感受到加諸在這些生命故事上另一種來自「自己人」的壓迫與網羅。
「我可以喜歡誰?」成為我的困擾。「同性戀」只能喜歡相同性別的人嗎?如果不這樣,還是「同性戀」嗎?「雙性戀」的位置在哪裡呢?「跨性別」到底是要喜歡哪種人才「可以」?以「性取向」為身分認同的標籤,困住了我的想法與生活。有一長段時間,我詢問「愛」與「喜歡」的議題:我好像可以喜歡很多人,對不同的人都欣賞也被吸引,但是,什麼是愛呢?原來,愛也很有「限制」。
向媽媽出櫃,是在邀請她來參加教會聖誕晚會的前一晚。在電話中,我支支吾吾,媽媽卻明白地說:「來,你直接講。」當我說完了之後,媽媽並沒有等待我喘過氣來,反問:「你現在才講,我和爸爸在你國小的時候就在討論這件事情了。……你有沒有向爸爸提?」隔天,表姊告訴我:「你一出場,阿嬸就高興地哭了……並且說:「沒錯,這就是他啦!」我還記得媽媽在演出前遞給我,那份從台南帶上來的飯糰、飲料與那番加油鼓勵的話。2008年5月21日,楊雅惠牧師離開了我們。在收到消息之後,仍覺得不真實:一位勇敢面對父權體系的同志教會建立者,用燒炭的方式解束自己的生命,回到上主那裡去服事他。在台中的那場告別式裡,我又再一次感受到「虛假」充斥在每個環節裡,謊言也在那場合裡散佈著。一直跟到了火葬場,這一切卻沒有隨著楊牧師離開,每雙哭紅的眼睛與無法述說的難過情感,從那裡蔓延開來。那天,我下定決心要朝成為傳道人跨出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