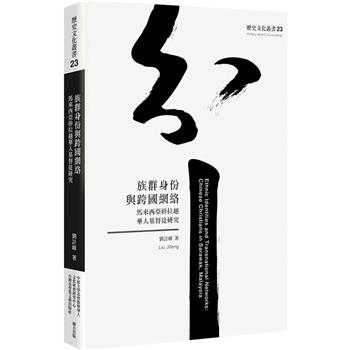詩巫華社,尤其是華人衛理公會,熱衷於族群記憶與歷史敘述。以鄉屬公會為例,福州公會、漳泉公會、海南公會、興化莆仙公會等均編撰、出版了多冊社團成立周年或重大活動的紀念特刊,記錄了各自鄉屬的移民歷史與發展成就。然而,此類歷史工程絕非僅限於舉辦慶典或編撰紀念特刊。本世紀以來,詩巫又興起修建紀念場所的熱潮,幾個頗具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的華人社團與詩巫市議會合作,修建祖籍地文化主題紀念公園和廣場。華人衛理公會亦參與其中,紀念美國傳教士富雅各,積極推動對教會歷史的書寫,強調教會在早期移民與地方發展中的作用。
馬來西亞華人致力於記錄移民歷史與構建族群記憶的事例並不鮮見,尤以祖神崇拜、宗教認同與鄭和記憶等較為典型。近年來,新生代華裔通過流行文化(如華語電影)反思後殖民時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論述,主動回應現實中的族群關係問題。然而,就筆者觀察,如詩巫華人這般熱衷於敘述族群歷史,開展如此密集而持久的重建歷史記憶的工程,實屬罕見。正如下文將要展現的,詩巫華社面臨年輕人流失、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問題,老一輩華人正在思索如何為自己的生命記憶找到載體,將其傳遞給年輕世代。詩巫華人在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打造回憶空間 (spaces of remembrance),讓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的記憶之場 (realms of memory),讓回憶成為日常文化實踐,使之不再局限於節日或慶典等特殊紀念時機。
法國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提出了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強調社會框架 (social framework) 對記憶的形塑與重構作用,將個體記憶置於集體的結構之中。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也預設了記憶的反面—遺忘,即不再擁有社會框架的東西將不可避免地被個人或群體遺忘。對於有共同記憶的同代人來說,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將因代際更迭面臨瓦解。德國的阿斯曼夫婦在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基礎上,從時間維度上進行了深化,開創了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理論。根據記憶的時間跨度,揚‧阿斯曼 (Jan Assmann) 將記憶區分為交往記憶 (communicative memory) 與文化記憶。交往記憶指存在於日常交往中的短時記憶,鮮活地存在於人腦中。它通過群體內的代際傳播得以延續,將不可避免地隨著代際更迭而消亡,因此具有有限的時間跨度。
文化記憶則是超越日常生活領域和個體生命週期的長期記憶,是被固定下來的客觀外在物(如早期文明中的文本、儀式、舞蹈、神話、圖式、繪畫等),經過系統符號化,使之成為記憶的媒介,用於支撐回憶和認同。在交往記憶中,回憶的持久性是有限的(三、四代左右);而在文化記憶中,記憶則被符號化客體固定下來,不會隨著代際更迭而消弭。用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的話說,「如果不想讓時代證人的經驗記憶消失,就必須把它轉化成後世的文化記憶。這樣,鮮活的記憶會讓位於一種由媒介支撐的記憶,這種記憶有賴於像紀念碑、紀念場所、博物館和檔案館等物質的載體」。
與個體主導的交往記憶不同,文化記憶依賴機構化保障,需要專職人員(如歷史學家、檔案館管理員或博物館工作者)負責對文化進行編碼、解碼與傳承。正如本章所要展現的,詩巫華社成立專門的文化機構,推出文物展品,並整理檔案和編撰文本。他們投身於這樣的記憶工程,通過打造全方位的回憶空間,將交往記憶轉化成持久的文化記憶,從而對抗集體記憶的日漸消解。馬來西亞詩巫華社的記憶潮為研究海外華人社會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分析視角,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華人,尤其是華人基督徒,如何通過詮釋移民與發展歷史來塑造族群認同。基於對詩巫華社的個案分析,本章聚焦於當地華人如何將回憶變成日常的實踐,來打造屬於他們的文化記憶。在此基礎上,本章將進一步探討,文化記憶如何形塑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歷史意識,尤其是華人基督徒的族群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