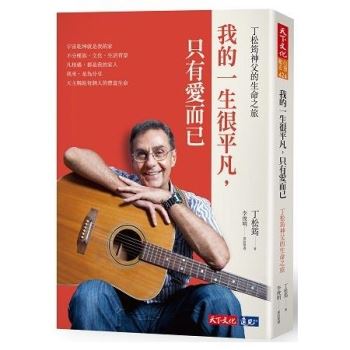雜誌上的史懷哲,勾起我的靈光一現
高中最後一年,我十七歲,決定要當神父。這跟一九五三年贏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史懷哲很有關聯,因為我很嚮往他那服務犧牲的精神。
我當時看了一本雜誌,讀到史懷哲四十多歲離開歐洲,到西非加彭等地貢獻自己的醫療專業、照顧別人,這個故事深深感動了我。雜誌照片裡的他看來似乎過得很開心。我那時突然萌生一個念頭:倘若換成是我,應該也會很開心;如果我可以救人或讓別人得到幸福,世界是否有我,才會有所分別。
那時我還沒想到神職這條路,只是看到史懷哲的服務精神,讓我十分崇拜。
我聽說耶穌會慣常派會士到國外服務,暗暗覺得這是一條十分值得考慮的道路。這種對於到海外服務的嚮往,也許無形中承襲了父親的基因。
小時候除了聽父親講述隨軍隊至遠東的往事,平日他在家裡看書,也總愛挑些探險、航海、飛行的故事來讀,隱約帶著對探索世界的渴望。我想我必定是受到父親的影響,才會對探索未知這麼著迷。
***
五十多年後回想起來,我會下定決心成為神父,轉變發生在某天晚上。
那時我跟幾個好同學一起在音樂廳擔任帶位員,雖然薪水很少,但我做得很起勁。因為打工之便,我常常可以觀賞到洛杉磯、舊金山等大城市來的歌手或合唱團、芭蕾舞團前來表演,讓我吸收不少藝術養分。
快畢業的某天晚上,我們聊起明年到底要做什麼?其中一位同學不假思索便回答,他要去奧思定會修道。
那一剎那,我內心浮現非常強烈的感覺,除了十分羨慕,還甚至有點嫉妒:他怎能如此輕易便做出這麼重大的決定?
我在腦中想過這件事無數次,考慮著我以後不能結婚、要離家很遠、要到異國傳教……這對一個孩子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未來。
但我的同學只是淡淡地說,剛開始的確一切都很令人徬徨,不過一旦做出決定,似乎就豁然開朗,內心也平靜下來,充滿了平安的感覺。
那天晚上,我開著母親的車送他回家後,一個人呆坐在車庫裡,不斷思考這件事。似乎有種看不見的力量,在幫助我得到性靈的啟示。於是我在心中默默對天主許諾:如果祢願意的話,我也願意暫時試試看,投入修道的行列。
開出這種條件式的自我期許,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當晚入睡前,還忍不住自問:這是否只是內心在幻想?沒想到隔天早上醒來,我突然覺得內心很輕鬆,好像解決了一個棘手問題,放下一塊懸而未決的大石。
這奇特的經驗,成為我投入宗教的轉捩點。
活潑善良的瑪姬,第一次心動
總會有人問我,如果還有下輩子,仍會選擇當神父嗎?
我總是回答:「會。」
當神父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我當時在台灣念書時遇到的外國修士,幾乎有一半都還俗了,可見要堅持這條路,相當困難。
其中一個很難度過的關卡,就是我們如何放下對感情的執念。
我的好朋友郎雄,曾在一九八九年主演中視的單元劇「一家之主」,其中我最喜歡的一集,讓人很有共鳴。
戲一開始,有個老太太來教堂敲門,她進門便問:「你不記得我了嗎?」原來,她是郎雄飾演的角色在大陸的未婚妻。兩人原本互許婚約,無奈戰亂暴發而分離。
大難當頭,只能各自分飛,老婦尋覓多年,才終於找到未婚夫下落。可是滄海桑田,人事已非,她滿懷希望攜來布鞋要給愛人,無奈郎雄已成神父,無法再續前緣……
這場內心戲非常感人,結尾跟著老太太遠去的背影,最後鏡頭轉回郎雄關上教堂大門、往回走去的腳上─那雙無緣未婚妻捎來的布鞋。
劇情與對白,雖然只是淡淡的,可是你感覺得到表面下暗湧的情感,與神父內心翻騰的衝突,最後以一絲溫柔為遺憾作結。
老實說,像這樣的人性掙扎,我不但曾經歷過,而且還不只一次。
***
神父也是人,當然也會對別人萌生愛戀的欲望。我初嘗戀愛滋味,是在聖地牙哥就讀高中時,有兩、三年時間,很常跟瑪姬(Margie)在一起。
瑪姬的個性,總是那樣樂觀、積極,非常活潑外向。相形之下,我比較害羞靦腆,也不知道怎麼跟女孩子說話;像是跳舞等社交技巧,都是瑪姬引導我去嘗試。雖然我高中書念得不錯,但會讓男孩子大出鋒頭的棒球、籃球,我總是玩得很差,加上下課後還得打工幫忙家計,因此始終沒有積極去追女朋友。
瑪姬可能很早就看透了世俗標準的膚淺,才能欣賞我身上的一些特質,對於我的害羞內向並不以為意。她能這麼喜歡我,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
本身也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的瑪姬,知道我想當神父後,也沒有特別反對,反而說如果她是男孩,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沒想到隔天早上醒來,我突然覺得內心很輕鬆,好像解決了一個棘手問題,放下一塊懸而未決的大石。
這奇特的經驗,成為我投入宗教的轉捩點。
活潑善良的瑪姬,第一次心動
總會有人問我,如果還有下輩子,仍會選擇當神父嗎?
我總是回答:「會。」
當神父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我當時在台灣念書時遇到的外國修士,幾乎有一半都還俗了,可見要堅持這條路,相當困難。
其中一個很難度過的關卡,就是我們如何放下對感情的執念。
我的好朋友郎雄,曾在一九八九年主演中視的單元劇「一家之主」,其中我最喜歡的一集,讓人很有共鳴。
戲一開始,有個老太太來教堂敲門,她進門便問:「你不記得我了嗎?」原來,她是郎雄飾演的角色在大陸的未婚妻。兩人原本互許婚約,無奈戰亂暴發而分離。
大難當頭,只能各自分飛,老婦尋覓多年,才終於找到未婚夫下落。可是滄海桑田,人事已非,她滿懷希望攜來布鞋要給愛人,無奈郎雄已成神父,無法再續前緣……
這場內心戲非常感人,結尾跟著老太太遠去的背影,最後鏡頭轉回郎雄關上教堂大門、往回走去的腳上─那雙無緣未婚妻捎來的布鞋。
劇情與對白,雖然只是淡淡的,可是你感覺得到表面下暗湧的情感,與神父內心翻騰的衝突,最後以一絲溫柔為遺憾作結。
老實說,像這樣的人性掙扎,我不但曾經歷過,而且還不只一次。
***
神父也是人,當然也會對別人萌生愛戀的欲望。我初嘗戀愛滋味,是在聖地牙哥就讀高中時,有兩、三年時間,很常跟瑪姬(Margie)在一起。
瑪姬的個性,總是那樣樂觀、積極,非常活潑外向。相形之下,我比較害羞靦腆,也不知道怎麼跟女孩子說話;像是跳舞等社交技巧,都是瑪姬引導我去嘗試。雖然我高中書念得不錯,但會讓男孩子大出鋒頭的棒球、籃球,我總是玩得很差,加上下課後還得打工幫忙家計,因此始終沒有積極去追女朋友。
瑪姬可能很早就看透了世俗標準的膚淺,才能欣賞我身上的一些特質,對於我的害羞內向並不以為意。她能這麼喜歡我,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
本身也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的瑪姬,知道我想當神父後,也沒有特別反對,反而說如果她是男孩,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我忍不住開玩笑地想,她會不會太支持了?這麼輕易就放棄我!總之,這是自我調侃的玩笑話。畢業那年暑假,我們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後,就準備各奔前程。
我回想起去到瑪姬工作的醫院找她聊天、散步,臨到說再見那一刻,心裡實在很想擁抱她、親吻她。但是想到自己即將要去修道,心裡就卻步了。
當時的我,並不是逞英雄。不過就是有股神祕的力量,驅使我把這樣的情感牽繫斷開。
初學院兩年,緊接著文學院兩年,再來念三年哲學。這七年的修士生活非常封閉。所有通信往返,都會經過學院導師過濾檢查,因此我跟瑪姬也不敢在信裡寫太多私人感情,她也怕影響我的情緒。
最近,我找到那些塵封已久的信件,細細讀著當年她寫給我的字句。其實裡頭的內容我大多已忘了,但從頭再讀,依然能找回當初那份感動。
善體人意的瑪姬說:「你永遠是我高中生活快樂的基石,不論你選擇什麼職業,都是他們的收穫,我的損失。」(“You shall always be the cornerstone of my high school happiness. In whatever vocation you choose, it is my loss, their gain.”)
如今回想起來,她能這樣成熟地對待這段年少的感情,讓我可以安心放下執著,實在是很美的一件事。
五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感情早已昇華為友誼。我與瑪姬依然保持聯絡,維持好朋友的關係,我心裡一直深深感激著她。她在婚後有了三個孩子,我成為其中一個孩子的教父。
比爾.蘇利文,為我打開旅行新視界
一九六七年,我才二十四歲,修院畢業後我準備前往台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離開北美。在此之前的出國旅行,我只去過墨西哥與加拿大。
為了前往亞洲,六名年紀與我相仿的修士一起前往舊金山,那裡有家商船公司願意讓我們免費搭船前往南韓釜山。
為了趕搭順風船,我們在舊金山足足等了三天。當貨船終於在黑夜穿過金門大橋緩緩出航,四周意外漆黑。我在這樣的寂靜當中,腦海閃過了瑪姬、芭芭拉,還有家人與好朋友的模樣,這是我二十四年生命裡重要的人生縮影。
從舊金山到釜山,船程漂流十八日,只有一天出過太陽。隨著船身不斷破浪前進,我覺得自己好像身處黑洞之中,不知將來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儘管這次旅程帶著淡淡愁緒,但年輕人總是充滿向未來挑戰的冒險精神。我們當中有個修士叫比爾.蘇利文(Bill Sullivan),他對旅行特別有興趣,一手包辦了到台灣的行程規畫。除了帶我們從釜山乘火車到漢城(今首爾),又搭飛機到日本福岡,還多花了點時間,沿路拜訪耶穌會在日本的傳教據點,最後才從東京搭飛機到台灣。
這趟亞洲旅行初體驗,大大打開我的眼界,讓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觀察亞洲人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
我們一行六人,在船上除了用小型攝影機拍攝自己籌劃的電影、打打橋牌,再來就是跟商船上的船員聊天。這些水手好像在全球各地都有女朋友,每天「故意」提醒我們與女孩子交往的事。
已在修院被關了六年的修士,聽到這些故事,眼睛總瞪得很大,心想船員的生活怎如此精采,心裡偷偷羨慕著。他們特別提到,下船第一站釜山,有家酒吧叫 Tiger Bar,裡頭有很多漂亮的韓國女孩,但因為我們是修士,很可惜不能去,還假裝惋惜了一番。
因為我們相處得挺好,船員們提議到釜山後請我們吃飯、餞行。那一晚大夥酒足飯飽,賓主盡歡,後來回程計程車竟然不是返回港邊,而是直直開到 Tiger Bar 門口,這才發現被搞了一回惡作劇!
我們當時那麼年輕,又聽了船員活靈活現的描述,心裡按捺不住好奇,於是相約既然到了傳說中的「老虎酒吧」,那就進去見識一下,喝瓶啤酒就走。
只是沒想到,一進門,精明的媽媽桑立刻精銳盡出,把手下全派到我們身邊團團圍住,陣仗有點嚇人。這些韓國女孩長得非常漂亮,看來天真可愛,說得一口流利英文,一點也不像在情色行業打滾的人物。
我當時還異想天開,幻想眼前和我聊天的這位女孩,說不定是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好女孩,被迫下海工作,才有那樣的氣質。
這樣的幻想並沒有持續很久。我們聊著聊著,「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好女孩」突然表示有點冷,所以我把夾克脫下為她披上。只是不知怎麼搞的,道德感最強的修士突然拿出我們穿著修士服的照片,表明我們想當修士的決心。
「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好女孩」看了,猛然「唰」一聲把夾克撇下,展現自己傲人的身材,希望靠養眼畫面把我們留下。
當然,她的計謀沒有得逞,我們還是乖乖回到船上。可是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相信我們六位年輕修士都一樣。要不是那位最年輕的修士挺身而出,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那樣的毅力離開。
這些奇妙的際遇與考驗告訴我們,要當神父,抵抗誘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難以抗拒的軟弱。
回想起來,旅行時發生的經歷其實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未來我還繼續遇到各種不同的誘惑與考驗。有過前車之鑑,我可以把事情想得更清楚。
高中最後一年,我十七歲,決定要當神父。這跟一九五三年贏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史懷哲很有關聯,因為我很嚮往他那服務犧牲的精神。
我當時看了一本雜誌,讀到史懷哲四十多歲離開歐洲,到西非加彭等地貢獻自己的醫療專業、照顧別人,這個故事深深感動了我。雜誌照片裡的他看來似乎過得很開心。我那時突然萌生一個念頭:倘若換成是我,應該也會很開心;如果我可以救人或讓別人得到幸福,世界是否有我,才會有所分別。
那時我還沒想到神職這條路,只是看到史懷哲的服務精神,讓我十分崇拜。
我聽說耶穌會慣常派會士到國外服務,暗暗覺得這是一條十分值得考慮的道路。這種對於到海外服務的嚮往,也許無形中承襲了父親的基因。
小時候除了聽父親講述隨軍隊至遠東的往事,平日他在家裡看書,也總愛挑些探險、航海、飛行的故事來讀,隱約帶著對探索世界的渴望。我想我必定是受到父親的影響,才會對探索未知這麼著迷。
***
五十多年後回想起來,我會下定決心成為神父,轉變發生在某天晚上。
那時我跟幾個好同學一起在音樂廳擔任帶位員,雖然薪水很少,但我做得很起勁。因為打工之便,我常常可以觀賞到洛杉磯、舊金山等大城市來的歌手或合唱團、芭蕾舞團前來表演,讓我吸收不少藝術養分。
快畢業的某天晚上,我們聊起明年到底要做什麼?其中一位同學不假思索便回答,他要去奧思定會修道。
那一剎那,我內心浮現非常強烈的感覺,除了十分羨慕,還甚至有點嫉妒:他怎能如此輕易便做出這麼重大的決定?
我在腦中想過這件事無數次,考慮著我以後不能結婚、要離家很遠、要到異國傳教……這對一個孩子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未來。
但我的同學只是淡淡地說,剛開始的確一切都很令人徬徨,不過一旦做出決定,似乎就豁然開朗,內心也平靜下來,充滿了平安的感覺。
那天晚上,我開著母親的車送他回家後,一個人呆坐在車庫裡,不斷思考這件事。似乎有種看不見的力量,在幫助我得到性靈的啟示。於是我在心中默默對天主許諾:如果祢願意的話,我也願意暫時試試看,投入修道的行列。
開出這種條件式的自我期許,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當晚入睡前,還忍不住自問:這是否只是內心在幻想?沒想到隔天早上醒來,我突然覺得內心很輕鬆,好像解決了一個棘手問題,放下一塊懸而未決的大石。
這奇特的經驗,成為我投入宗教的轉捩點。
活潑善良的瑪姬,第一次心動
總會有人問我,如果還有下輩子,仍會選擇當神父嗎?
我總是回答:「會。」
當神父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我當時在台灣念書時遇到的外國修士,幾乎有一半都還俗了,可見要堅持這條路,相當困難。
其中一個很難度過的關卡,就是我們如何放下對感情的執念。
我的好朋友郎雄,曾在一九八九年主演中視的單元劇「一家之主」,其中我最喜歡的一集,讓人很有共鳴。
戲一開始,有個老太太來教堂敲門,她進門便問:「你不記得我了嗎?」原來,她是郎雄飾演的角色在大陸的未婚妻。兩人原本互許婚約,無奈戰亂暴發而分離。
大難當頭,只能各自分飛,老婦尋覓多年,才終於找到未婚夫下落。可是滄海桑田,人事已非,她滿懷希望攜來布鞋要給愛人,無奈郎雄已成神父,無法再續前緣……
這場內心戲非常感人,結尾跟著老太太遠去的背影,最後鏡頭轉回郎雄關上教堂大門、往回走去的腳上─那雙無緣未婚妻捎來的布鞋。
劇情與對白,雖然只是淡淡的,可是你感覺得到表面下暗湧的情感,與神父內心翻騰的衝突,最後以一絲溫柔為遺憾作結。
老實說,像這樣的人性掙扎,我不但曾經歷過,而且還不只一次。
***
神父也是人,當然也會對別人萌生愛戀的欲望。我初嘗戀愛滋味,是在聖地牙哥就讀高中時,有兩、三年時間,很常跟瑪姬(Margie)在一起。
瑪姬的個性,總是那樣樂觀、積極,非常活潑外向。相形之下,我比較害羞靦腆,也不知道怎麼跟女孩子說話;像是跳舞等社交技巧,都是瑪姬引導我去嘗試。雖然我高中書念得不錯,但會讓男孩子大出鋒頭的棒球、籃球,我總是玩得很差,加上下課後還得打工幫忙家計,因此始終沒有積極去追女朋友。
瑪姬可能很早就看透了世俗標準的膚淺,才能欣賞我身上的一些特質,對於我的害羞內向並不以為意。她能這麼喜歡我,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
本身也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的瑪姬,知道我想當神父後,也沒有特別反對,反而說如果她是男孩,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沒想到隔天早上醒來,我突然覺得內心很輕鬆,好像解決了一個棘手問題,放下一塊懸而未決的大石。
這奇特的經驗,成為我投入宗教的轉捩點。
活潑善良的瑪姬,第一次心動
總會有人問我,如果還有下輩子,仍會選擇當神父嗎?
我總是回答:「會。」
當神父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我當時在台灣念書時遇到的外國修士,幾乎有一半都還俗了,可見要堅持這條路,相當困難。
其中一個很難度過的關卡,就是我們如何放下對感情的執念。
我的好朋友郎雄,曾在一九八九年主演中視的單元劇「一家之主」,其中我最喜歡的一集,讓人很有共鳴。
戲一開始,有個老太太來教堂敲門,她進門便問:「你不記得我了嗎?」原來,她是郎雄飾演的角色在大陸的未婚妻。兩人原本互許婚約,無奈戰亂暴發而分離。
大難當頭,只能各自分飛,老婦尋覓多年,才終於找到未婚夫下落。可是滄海桑田,人事已非,她滿懷希望攜來布鞋要給愛人,無奈郎雄已成神父,無法再續前緣……
這場內心戲非常感人,結尾跟著老太太遠去的背影,最後鏡頭轉回郎雄關上教堂大門、往回走去的腳上─那雙無緣未婚妻捎來的布鞋。
劇情與對白,雖然只是淡淡的,可是你感覺得到表面下暗湧的情感,與神父內心翻騰的衝突,最後以一絲溫柔為遺憾作結。
老實說,像這樣的人性掙扎,我不但曾經歷過,而且還不只一次。
***
神父也是人,當然也會對別人萌生愛戀的欲望。我初嘗戀愛滋味,是在聖地牙哥就讀高中時,有兩、三年時間,很常跟瑪姬(Margie)在一起。
瑪姬的個性,總是那樣樂觀、積極,非常活潑外向。相形之下,我比較害羞靦腆,也不知道怎麼跟女孩子說話;像是跳舞等社交技巧,都是瑪姬引導我去嘗試。雖然我高中書念得不錯,但會讓男孩子大出鋒頭的棒球、籃球,我總是玩得很差,加上下課後還得打工幫忙家計,因此始終沒有積極去追女朋友。
瑪姬可能很早就看透了世俗標準的膚淺,才能欣賞我身上的一些特質,對於我的害羞內向並不以為意。她能這麼喜歡我,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感謝。
本身也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的瑪姬,知道我想當神父後,也沒有特別反對,反而說如果她是男孩,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我忍不住開玩笑地想,她會不會太支持了?這麼輕易就放棄我!總之,這是自我調侃的玩笑話。畢業那年暑假,我們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後,就準備各奔前程。
我回想起去到瑪姬工作的醫院找她聊天、散步,臨到說再見那一刻,心裡實在很想擁抱她、親吻她。但是想到自己即將要去修道,心裡就卻步了。
當時的我,並不是逞英雄。不過就是有股神祕的力量,驅使我把這樣的情感牽繫斷開。
初學院兩年,緊接著文學院兩年,再來念三年哲學。這七年的修士生活非常封閉。所有通信往返,都會經過學院導師過濾檢查,因此我跟瑪姬也不敢在信裡寫太多私人感情,她也怕影響我的情緒。
最近,我找到那些塵封已久的信件,細細讀著當年她寫給我的字句。其實裡頭的內容我大多已忘了,但從頭再讀,依然能找回當初那份感動。
善體人意的瑪姬說:「你永遠是我高中生活快樂的基石,不論你選擇什麼職業,都是他們的收穫,我的損失。」(“You shall always be the cornerstone of my high school happiness. In whatever vocation you choose, it is my loss, their gain.”)
如今回想起來,她能這樣成熟地對待這段年少的感情,讓我可以安心放下執著,實在是很美的一件事。
五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感情早已昇華為友誼。我與瑪姬依然保持聯絡,維持好朋友的關係,我心裡一直深深感激著她。她在婚後有了三個孩子,我成為其中一個孩子的教父。
比爾.蘇利文,為我打開旅行新視界
一九六七年,我才二十四歲,修院畢業後我準備前往台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離開北美。在此之前的出國旅行,我只去過墨西哥與加拿大。
為了前往亞洲,六名年紀與我相仿的修士一起前往舊金山,那裡有家商船公司願意讓我們免費搭船前往南韓釜山。
為了趕搭順風船,我們在舊金山足足等了三天。當貨船終於在黑夜穿過金門大橋緩緩出航,四周意外漆黑。我在這樣的寂靜當中,腦海閃過了瑪姬、芭芭拉,還有家人與好朋友的模樣,這是我二十四年生命裡重要的人生縮影。
從舊金山到釜山,船程漂流十八日,只有一天出過太陽。隨著船身不斷破浪前進,我覺得自己好像身處黑洞之中,不知將來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儘管這次旅程帶著淡淡愁緒,但年輕人總是充滿向未來挑戰的冒險精神。我們當中有個修士叫比爾.蘇利文(Bill Sullivan),他對旅行特別有興趣,一手包辦了到台灣的行程規畫。除了帶我們從釜山乘火車到漢城(今首爾),又搭飛機到日本福岡,還多花了點時間,沿路拜訪耶穌會在日本的傳教據點,最後才從東京搭飛機到台灣。
這趟亞洲旅行初體驗,大大打開我的眼界,讓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觀察亞洲人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
我們一行六人,在船上除了用小型攝影機拍攝自己籌劃的電影、打打橋牌,再來就是跟商船上的船員聊天。這些水手好像在全球各地都有女朋友,每天「故意」提醒我們與女孩子交往的事。
已在修院被關了六年的修士,聽到這些故事,眼睛總瞪得很大,心想船員的生活怎如此精采,心裡偷偷羨慕著。他們特別提到,下船第一站釜山,有家酒吧叫 Tiger Bar,裡頭有很多漂亮的韓國女孩,但因為我們是修士,很可惜不能去,還假裝惋惜了一番。
因為我們相處得挺好,船員們提議到釜山後請我們吃飯、餞行。那一晚大夥酒足飯飽,賓主盡歡,後來回程計程車竟然不是返回港邊,而是直直開到 Tiger Bar 門口,這才發現被搞了一回惡作劇!
我們當時那麼年輕,又聽了船員活靈活現的描述,心裡按捺不住好奇,於是相約既然到了傳說中的「老虎酒吧」,那就進去見識一下,喝瓶啤酒就走。
只是沒想到,一進門,精明的媽媽桑立刻精銳盡出,把手下全派到我們身邊團團圍住,陣仗有點嚇人。這些韓國女孩長得非常漂亮,看來天真可愛,說得一口流利英文,一點也不像在情色行業打滾的人物。
我當時還異想天開,幻想眼前和我聊天的這位女孩,說不定是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好女孩,被迫下海工作,才有那樣的氣質。
這樣的幻想並沒有持續很久。我們聊著聊著,「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好女孩」突然表示有點冷,所以我把夾克脫下為她披上。只是不知怎麼搞的,道德感最強的修士突然拿出我們穿著修士服的照片,表明我們想當修士的決心。
「天主教學校出身的好女孩」看了,猛然「唰」一聲把夾克撇下,展現自己傲人的身材,希望靠養眼畫面把我們留下。
當然,她的計謀沒有得逞,我們還是乖乖回到船上。可是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相信我們六位年輕修士都一樣。要不是那位最年輕的修士挺身而出,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那樣的毅力離開。
這些奇妙的際遇與考驗告訴我們,要當神父,抵抗誘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難以抗拒的軟弱。
回想起來,旅行時發生的經歷其實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未來我還繼續遇到各種不同的誘惑與考驗。有過前車之鑑,我可以把事情想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