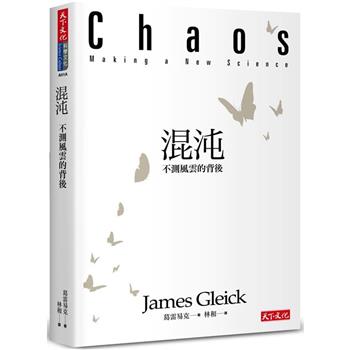勞倫茲沉醉於天氣的樂趣裡,儘管那不算是氣象學者的必要條件,他覺得天氣的變幻賞心悅目,喜歡大氣中川流不息的各類天氣形態,熟悉那些乖乖遵守數學定律,但卻永不重複的擾動和氣旋。當觀察雲朵時,他覺得領悟到了其中某種結構,一度他以為研究天氣的科學像是用螺絲起子拆散魔術盒一樣,現在則懷疑科學能否有一日揭穿魔術?天氣有種特性是不能以平均表達的,麻省劍橋的6月平均溫度是攝氏二十四度,而在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每年下雨的平均天數是十天,這些是統計資料,但重要的是大氣形態隨著時間而變,這也就是勞倫茲從皇家馬克比中想要捕捉到的東西。
他是這個機器世界的主宰,可以隨意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自然定律,經過嘗試與錯誤的一番苦工,他選擇了十二條方程式,方程式顯示出溫度與壓力、或者壓力與風速之間數值的關係,勞倫茲知道自己正在操作牛頓定律,就像時間之神,創造一套世界,使其運行不息。感謝物理定律的決定論,啟動之後即不需要再操心,那些製造模式的人滿懷信心,藉由運動定律來提供數學肯定性的因果關連。一旦掌握法則,也就等於了解宇宙內涵,這是以電腦模擬天氣背後隱藏的哲學基礎。
確實,如果十八世紀的哲學家想像上帝像隱藏在幕後,仁慈而不動聲色的不介入主義者,可以想像勞倫茲就是這類人物。他是一位很絕的氣象學家,有張像新英格蘭鄉下農夫飽經風霜的臉,令人驚奇的明亮眼睛,說不準他是否在笑,而別人總覺得他在開懷大笑。很少談論自己或工作,常常只是傾聽,他往往沉浸在計算狀態或同仁無法思議的夢想中,連他最親近的朋友也覺得大多數時候勞倫茲飄飄神遊太虛幻境。
當勞倫茲還是小男孩時,他就是位天氣迷,看緊了他父母在康乃狄克州西哈特福屋外,懸掛的最高最低溫度計,記錄下每天最高最低溫度,不過他比觀察溫度計花了更多時間在數學謎題的書本上,有時候父親會和他一起解決書本上的謎題,有一次他們碰上特別困難的問題,根本無解,父親告訴他,這也行得通,證明沒有答案亦為解決之道。勞倫茲喜歡如此想,就像他喜歡數學的澄明一樣,當他在1938年於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畢業時,他覺得數學便是他的終身志業了。但是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使得整個情況有些改變,大戰期間,他擔任陸軍航空單位的天氣預報員,戰後勞倫茲決定留在氣象圈子裡,研究氣象理論,多鑽研一些數學,他在諸如大氣環流的正統問題上發表文章,博得響亮名聲,同時他繼續思索預測的問題。
即使對最嚴謹的氣象學家而言,預報還稱不上科學,這是一種熟能生巧的工作,需要一些擁有直覺的技術員,從儀器和雲況中讀出明天天氣,偏向猜測。對於類似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研究中心,氣象學喜歡那些有確實答案的問題,曾經親自提供預報給軍機駕駛員,勞倫茲自然能體會到天氣預報的雜亂潦草,但他對問題懷抱著別具匠心的興趣──一種數學上的興趣。
不僅僅是氣象學家看輕預報,1960年代所有嚴謹的科學家都不信任電腦,這些加足馬力的計算器不像是理論科學需要的工具。所以數值天氣模擬變成進退維谷的問題。但時機逐漸成熟,天氣預報等待一部可以幹粗活兒,重複計算成千上萬次的機器已經整整兩個世紀了,只有電腦能兌現牛頓式的期望:世界沿著前因後果的軌道演進,像是星球奉行的規則,或像日、月食和潮汐般的可靠預測。理論上,電腦應該能讓氣象學家辦到天文學家用鉛筆和計算尺達成的效果,從初始狀況和控制其演變的物理定律,來計算宇宙的未來。描述流體運動的方程式,和描述行星運動的方程式一樣老早為人熟知,對付這座由九大行星、成打衛星和千萬個隕石間重力場形成的太陽系,天文學家並未達到盡善盡美,而且也永遠不會。但天體運動的計算已經準確到使人們忘了那是預測,當一個天文學家說「哈雷彗星在七十六年後將會由這條路徑回來」,這像陳述一項事實,不像是預言,決定型的數值預測刻畫出太空船和火箭的精確路徑,為什麼風和雨卻不能如此?
天氣現象複雜許多倍,但是它卻由相同的定律所控制,也許一部能力強大的電腦,擁有拉普拉斯理想中的卓越智慧,這位十八世紀的哲學兼數學家感染上無可匹敵的牛頓式狂熱,他曾寫過:「這樣一位大智者,可以用相同的方程式,處理宇宙間最大的星體和最小的原子,對它來說,沒有所謂的曖昧,未來和過去都會歷歷如繪,直逼眼前。」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相繼問世後的時日,拉普拉斯的樂觀幾乎像滑稽歌手,但大多數的現代科學仍在追求他的夢想,暗地裡許多二十世紀的科學家,包括生物學、神經學和經濟學家的任務即是去解析其領域至遵循科學規律運行、最簡單的元素,在這許多學門中,都背負著牛頓式決定論的擔子。現代計算的長老們心裡都念著拉普拉斯,自從1950年代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在紐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設計他的第一部機器起,計算和預報的歷史就開始融合在一起。馮諾伊曼體認到天氣模擬會是電腦相當妥貼的目標。
還有一項小小的但書,小到科學家們幾乎都忘了擱在何處?隱藏在他們哲學的角落像一張未付清的帳單,那就是測量絕不可能精確。在牛頓旗幟下踏步前進的科學家們,實際上也搖晃著另一隻旗幟如此說:給我一些系統初始狀態的近似資料和明確的物理定律,就可以計算出系統的近似行為。這項假設座落於科學哲學的核心,就像一位理論學家喜歡告訴他的學生:「西方科學的基本理念就是如此:如果你正在計算地球檯面上的一顆撞球,你就不必去理會另一座星系某星球上樹葉的掉落。很輕微的影響可以被忽略,事物進行總會殊途同歸,任意的小干擾,並不至於膨脹到任意大的後果。」傳統的,信任這種近似和聚集的確有它的道理,修正1910年哈雷彗星位置的小錯誤,只會造成它在1986年來臨時的小誤差,而且百萬年後來臨時誤差仍然會很小。電腦也在同樣的假設下引導太空船航行,近似正確的輸入會獲得近似正確的輸出;經濟預測也根據相同的假設,雖然較少明顯的成功;全球天氣預報的開拓者亦是。
使用他的洪荒級電腦,勞倫茲簡化天氣至一副乾淨的骸骨,一行一行列印出來的風和溫度,似乎大體符合可辨識的地球特色,印證了藏在他心中對天氣的直覺,他覺察到天氣會自我模仿,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似曾相識的類型,氣壓此起彼落,氣流的南北遷移。他發現倘若一條從高降低的線段未曾經歷顛簸,下回就會碰上雙重崎嶇突起,他說:「那是預報員可以用得上的規則。」但是所謂的重複並非那麼精確,而是帶著一點混亂的類型,一種井井有條的無秩序。
讓類型一目瞭然,勞倫茲創造出一種基礎圖表,取代只印出通常的一行數字,他指令機器在字母a前印一定數量的空格,他可以選擇一項變數,比方說是氣流的方向。逐漸的,這些a沿著印表捲筒前進,循著波形線條,前後搖擺,製造出一長系列的山峯與山谷,代表西風穿越大陸南北遷移的方式,其中可辨認的循環代表有秩序的部分,一次又一次發生,但絕不雷同,像一場催眠下的銷魂舞,這座系統慢慢在預測者的凝視下揭露自己的奧祕。
1961年冬季某日,為了檢查一段較長的序列,勞倫茲決定抄捷徑而行,捨棄重新由開頭計算的方式,他改由從中間開始,直接根據先前印出的結果敲進數字,提供給機器當做初始條件,然後離開那些噪音,走下樓小啜一杯咖啡,一小時後當他回來,卻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成果──一些真理為新科學播下的種子。
摘自《混沌》〈蝴蝶效應〉
他是這個機器世界的主宰,可以隨意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自然定律,經過嘗試與錯誤的一番苦工,他選擇了十二條方程式,方程式顯示出溫度與壓力、或者壓力與風速之間數值的關係,勞倫茲知道自己正在操作牛頓定律,就像時間之神,創造一套世界,使其運行不息。感謝物理定律的決定論,啟動之後即不需要再操心,那些製造模式的人滿懷信心,藉由運動定律來提供數學肯定性的因果關連。一旦掌握法則,也就等於了解宇宙內涵,這是以電腦模擬天氣背後隱藏的哲學基礎。
確實,如果十八世紀的哲學家想像上帝像隱藏在幕後,仁慈而不動聲色的不介入主義者,可以想像勞倫茲就是這類人物。他是一位很絕的氣象學家,有張像新英格蘭鄉下農夫飽經風霜的臉,令人驚奇的明亮眼睛,說不準他是否在笑,而別人總覺得他在開懷大笑。很少談論自己或工作,常常只是傾聽,他往往沉浸在計算狀態或同仁無法思議的夢想中,連他最親近的朋友也覺得大多數時候勞倫茲飄飄神遊太虛幻境。
當勞倫茲還是小男孩時,他就是位天氣迷,看緊了他父母在康乃狄克州西哈特福屋外,懸掛的最高最低溫度計,記錄下每天最高最低溫度,不過他比觀察溫度計花了更多時間在數學謎題的書本上,有時候父親會和他一起解決書本上的謎題,有一次他們碰上特別困難的問題,根本無解,父親告訴他,這也行得通,證明沒有答案亦為解決之道。勞倫茲喜歡如此想,就像他喜歡數學的澄明一樣,當他在1938年於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畢業時,他覺得數學便是他的終身志業了。但是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使得整個情況有些改變,大戰期間,他擔任陸軍航空單位的天氣預報員,戰後勞倫茲決定留在氣象圈子裡,研究氣象理論,多鑽研一些數學,他在諸如大氣環流的正統問題上發表文章,博得響亮名聲,同時他繼續思索預測的問題。
即使對最嚴謹的氣象學家而言,預報還稱不上科學,這是一種熟能生巧的工作,需要一些擁有直覺的技術員,從儀器和雲況中讀出明天天氣,偏向猜測。對於類似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研究中心,氣象學喜歡那些有確實答案的問題,曾經親自提供預報給軍機駕駛員,勞倫茲自然能體會到天氣預報的雜亂潦草,但他對問題懷抱著別具匠心的興趣──一種數學上的興趣。
不僅僅是氣象學家看輕預報,1960年代所有嚴謹的科學家都不信任電腦,這些加足馬力的計算器不像是理論科學需要的工具。所以數值天氣模擬變成進退維谷的問題。但時機逐漸成熟,天氣預報等待一部可以幹粗活兒,重複計算成千上萬次的機器已經整整兩個世紀了,只有電腦能兌現牛頓式的期望:世界沿著前因後果的軌道演進,像是星球奉行的規則,或像日、月食和潮汐般的可靠預測。理論上,電腦應該能讓氣象學家辦到天文學家用鉛筆和計算尺達成的效果,從初始狀況和控制其演變的物理定律,來計算宇宙的未來。描述流體運動的方程式,和描述行星運動的方程式一樣老早為人熟知,對付這座由九大行星、成打衛星和千萬個隕石間重力場形成的太陽系,天文學家並未達到盡善盡美,而且也永遠不會。但天體運動的計算已經準確到使人們忘了那是預測,當一個天文學家說「哈雷彗星在七十六年後將會由這條路徑回來」,這像陳述一項事實,不像是預言,決定型的數值預測刻畫出太空船和火箭的精確路徑,為什麼風和雨卻不能如此?
天氣現象複雜許多倍,但是它卻由相同的定律所控制,也許一部能力強大的電腦,擁有拉普拉斯理想中的卓越智慧,這位十八世紀的哲學兼數學家感染上無可匹敵的牛頓式狂熱,他曾寫過:「這樣一位大智者,可以用相同的方程式,處理宇宙間最大的星體和最小的原子,對它來說,沒有所謂的曖昧,未來和過去都會歷歷如繪,直逼眼前。」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相繼問世後的時日,拉普拉斯的樂觀幾乎像滑稽歌手,但大多數的現代科學仍在追求他的夢想,暗地裡許多二十世紀的科學家,包括生物學、神經學和經濟學家的任務即是去解析其領域至遵循科學規律運行、最簡單的元素,在這許多學門中,都背負著牛頓式決定論的擔子。現代計算的長老們心裡都念著拉普拉斯,自從1950年代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在紐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設計他的第一部機器起,計算和預報的歷史就開始融合在一起。馮諾伊曼體認到天氣模擬會是電腦相當妥貼的目標。
還有一項小小的但書,小到科學家們幾乎都忘了擱在何處?隱藏在他們哲學的角落像一張未付清的帳單,那就是測量絕不可能精確。在牛頓旗幟下踏步前進的科學家們,實際上也搖晃著另一隻旗幟如此說:給我一些系統初始狀態的近似資料和明確的物理定律,就可以計算出系統的近似行為。這項假設座落於科學哲學的核心,就像一位理論學家喜歡告訴他的學生:「西方科學的基本理念就是如此:如果你正在計算地球檯面上的一顆撞球,你就不必去理會另一座星系某星球上樹葉的掉落。很輕微的影響可以被忽略,事物進行總會殊途同歸,任意的小干擾,並不至於膨脹到任意大的後果。」傳統的,信任這種近似和聚集的確有它的道理,修正1910年哈雷彗星位置的小錯誤,只會造成它在1986年來臨時的小誤差,而且百萬年後來臨時誤差仍然會很小。電腦也在同樣的假設下引導太空船航行,近似正確的輸入會獲得近似正確的輸出;經濟預測也根據相同的假設,雖然較少明顯的成功;全球天氣預報的開拓者亦是。
使用他的洪荒級電腦,勞倫茲簡化天氣至一副乾淨的骸骨,一行一行列印出來的風和溫度,似乎大體符合可辨識的地球特色,印證了藏在他心中對天氣的直覺,他覺察到天氣會自我模仿,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似曾相識的類型,氣壓此起彼落,氣流的南北遷移。他發現倘若一條從高降低的線段未曾經歷顛簸,下回就會碰上雙重崎嶇突起,他說:「那是預報員可以用得上的規則。」但是所謂的重複並非那麼精確,而是帶著一點混亂的類型,一種井井有條的無秩序。
讓類型一目瞭然,勞倫茲創造出一種基礎圖表,取代只印出通常的一行數字,他指令機器在字母a前印一定數量的空格,他可以選擇一項變數,比方說是氣流的方向。逐漸的,這些a沿著印表捲筒前進,循著波形線條,前後搖擺,製造出一長系列的山峯與山谷,代表西風穿越大陸南北遷移的方式,其中可辨認的循環代表有秩序的部分,一次又一次發生,但絕不雷同,像一場催眠下的銷魂舞,這座系統慢慢在預測者的凝視下揭露自己的奧祕。
1961年冬季某日,為了檢查一段較長的序列,勞倫茲決定抄捷徑而行,捨棄重新由開頭計算的方式,他改由從中間開始,直接根據先前印出的結果敲進數字,提供給機器當做初始條件,然後離開那些噪音,走下樓小啜一杯咖啡,一小時後當他回來,卻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成果──一些真理為新科學播下的種子。
摘自《混沌》〈蝴蝶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