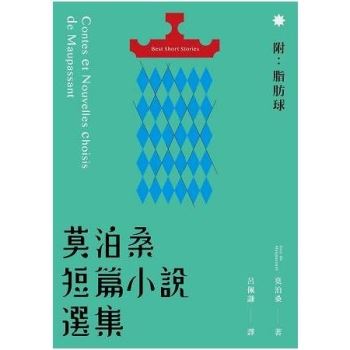獲得勳章了!(節錄)
有些人出生下來,打從開始會說話、會思考,就有一項突出的天性、一個志願,或僅僅有種被喚醒的願望。
薩可耶蒙先生自童年時期始,腦中就只有一個想法──得到勛章。年紀還很小,就會像其他孩子戴軍帽一樣,佩戴著鋅製的榮譽勛位十字勛章。而走在街上,他會挺起別有紅緞帶和金屬星星的胸脯,神氣地把手交給母親牽著。
他書讀得不好,沒通過高中生畢業會考(註1),不曉得該做什麼,但因為有些許財產,所以娶到一個漂亮的女孩。
夫妻倆住在巴黎,生活過得如富裕的上層中產階級,走進與他們同階層的圈子內,並和社交界裡的人保持關係。他們因為認識一位可能會當部長的議員而自豪,此外,他們還是兩名軍團師長的朋友。
但那個自生命初期便進入腦袋的念頭,薩可耶蒙先生始終忘不了,由於無權在禮服上佩戴有顏色的絲帶勛章,他無時無刻不感到痛苦。
在城市大道看見戴勛章的人每每總給他心上一擊。他斜眼看著他們,心中嫉妒加劇。有時,在無聊的漫長午後,他會開始計數著。他對自己說:「來吧,從馬德連納教堂到魯歐特街,看我能找到幾個。」
他慢慢地走,仔細查看行人的衣服,眼睛被訓練得遠遠就能分辨出那個小紅點。當走到路程的盡頭,他總會對這些數字感到驚奇:「八個四級榮譽章、十七個騎士榮譽勛章,竟然這麼多!如此濫發十字章,實在荒謬,且看看回程我會不會找到一樣多。」
他步履緩慢地往回走,遇上擁擠的過路群眾妨礙搜尋,讓他遺漏了人,便覺得惋惜。
他知道哪些地區戴勛章的人最多──皇家宮殿那兒到處都是。歌劇院大道的人數比不上和平街的;相較於城市大道的左側,戴勛章的人更喜歡聚在右側。
這些人似乎也有喜歡去的咖啡店和戲院。每當薩可耶蒙先生瞥見一群白髮蒼蒼的老紳士站在人行道中間,擾亂了交通,心裡便想:「這可都是些獲得四級榮譽章的長官!」他有股想上前致敬的慾望。
得到四級榮譽章的人,與普通的騎士榮譽勛章得主,舉止是有所差別的(這點他經常留意到)─前者的頭部姿態不同,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在官方的認可上擁有更高的尊敬,聲望也更遠播。
時而,薩可耶蒙先生心中也會竄升起一團怒火,所有得到勛章的人都讓他氣憤填膺,他覺得對他們懷有一股社會主義者(註2)式的仇恨。
回到家中,他會因為遇到這麼多戴十字勛章的人而深受刺激,就像饑餓的窮人從販賣食物的大型店鋪前走過那樣,大聲說道:「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有人幫我們趕走這卑鄙醜陋的政府?」
妻子訝異地問他:「你今天怎麼了?」
他回答:「我啊,我是為到處可見的不公義事情而生氣。啊,巴黎公社(註3)的人當初那麼做果真是有道理的!」
但晚餐過後,他又再度出門,前往賣勛章的店鋪流連。他細細查看各式各樣、顏色各異的徽章,真想把它們全都占為己有,然後在公眾典禮場合,在一間滿是賓客與讚嘆者的大禮堂,走在隊伍最前面,胸前閃閃發亮,一排又一排勛章隨著他肋骨的形狀彼此交疊整齊羅列。他手臂下會夾著高頂大禮帽,在一片低聲讚美中、在充滿尊敬的喧譁中,莊嚴地從人前經過,像顆光芒耀眼的明星。
可是,唉,他沒有任何名義可得到任何一種勛章!
他心想:「對一個沒擔任過任何公職的人而言,想獲得榮譽勛位勛章真是太難了。要不我來試試得個文化教育勛章應該也不錯吧?」
他不知道該如何著手,向妻子提起,妻子愣住了:「文化教育勛章?你為這方面做過些什麼啦?」
他發怒了:「你好好聽清楚我要說的!我這不就正在想該怎麼做。你有時候還真笨。」
她微微一笑:「完全正確,你說得沒錯。但你問我,我可不知道!」
他有個主意:「假如你和侯瑟藍議員談談,他或許能給我極好的建議呢?我嘛,你知道,我可不敢直接找他討論這個問題,這太微妙、太難開口了。由你來說,事情就自然多了。」
薩可耶蒙太太照他的要求去做,侯瑟藍先生承諾會對部長說。薩可耶蒙因此不時來纏他,議員最後的回答是必須提出申請,並列舉已有的頭銜。
頭銜?問題來了。他連張高中文憑也沒有。
但他仍投入了工作,他想編一本小冊子,名叫《論人民受教育的權利》。但思想貧乏,沒法完成。
他尋找較簡單的主題,依序涉獵了幾個。首先是「透過視覺來教育兒童」,他想在貧窮的地區為年幼的小孩搭建一些免費劇院。當孩子還小時,父母就帶他們來那裡,讓人們用幻燈片教他們人類所有知識的基本概念。這是名副其實的課程。頭腦藉由觀看來獲取知識,影像牢牢地刻印在記憶裡,科學因此成為看得見的事物。
以這種方式來教授世界史、地理、自然史、生物學、動物學、解剖學等等,還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
他請人印製這本論文,寄給所有議員,一人一本,每位部長各十本,共和國總統五十本,巴黎的報社也各送十本,外省的報社五本。
接著,他探討街上流動圖書館的問題,他希望政府能製造像賣橘子小販用的小車子,車上載滿書籍,派人開到街上巡迴。居民每人繳一毛錢的訂閱費,就有權每月租借十本書。
薩可耶蒙先生寫道──「人民只有為了享樂才會擱下手邊工作。既然他不主動來接受教育,就必須要讓教育去找他等等。」
他的論述沒有得到任何回響。然而他仍舊遞交了申請,得到的答覆是正在登錄中、研究中。他有把握會成功,便等待著。卻沒有任何回音。
於是,他決定自己想辦法找門路。他求見教育部長,結果是部長辦公室的專員接見了他。此人年紀輕輕,舉止已老成持重,甚至頗有權勢,只見他像彈鋼琴般按下一連串白色小按鈕,傳喚門口招待員、候見室的服務生,以及下屬職員。他向求見者確定所申請的事進展順利,建議他繼續這傑出的工作。
薩可耶蒙先生又重新投入了工作。
侯瑟藍議員,現在似乎對薩可耶蒙的事業能否成功相當關心,甚至提供了許多實用的好建議。況且他得過勛章,只不過,大家不太清楚他做了什麼而能得到這份殊榮。
他指點薩可耶蒙可著手研究的新方向,他將他介紹給一些學者組成的協會,這些人專門研究艱深科學問題,為的是想獲得一些榮譽。他甚至還到政府相關部門舉薦薩可耶蒙。
有一天,他到薩可耶蒙家吃午餐(近幾個月來,經常到他家吃飯),緊握住薩可耶蒙的手,低聲說道:「我剛剛為你爭取到一件非常好的差事。歷史工作委員會委派了你一項任務,工作內容是到法國各圖書館做研究。」
聽到消息,薩可耶蒙渾身癱軟,既無法吃也無法喝──八天後,他出發了。
他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研讀目錄、在成堆舊書的頂樓裡搜尋,書上滿布灰塵,他滿懷著對圖書館員的怨恨。
然而有天晚上,他人在盧昂,想回家抱抱一星期沒見的妻子,便搭上九點的火車,預計午夜到家。
他帶有鑰匙,悄悄地走進屋裡,因快樂而微微顫抖,高興能給她來個驚喜。但她把房門鎖住了,真惱人!於是,他隔著門高喊:「簡妮,是我!」
她應該很害怕,因為他聽見她從床上跳起,像做夢一樣自言自語。接著跑到浴室,打開門又重新關上,光著腳在房間來回快跑了好幾趟,碰撞到家具,家具上的玻璃吊飾叮噹作響。終於,她開口問:「真的是你,亞歷山大?」
他答道:「當然是我,開門呀!」
門打開了,妻子撲進他懷裡,口齒含糊:「啊,真是嚇壞我了!好個驚奇!我好高興!」
他像平常一樣條理分明地開始褪去一件件衣物。從椅子上拿起那件他習慣掛在門廳的大衣。但,忽然間,他驚訝地愣住了──大衣的鈕扣眼上繫著一段紅絲帶!
他口吃了:「這......這......這件外套上有勛章!」
妻子一個跳躍,朝他撲來,抓住他手裡衣服:「不......你搞錯了......把衣服給我。」
但他仍一直拉著大衣的袖子不肯放手,慌亂中反覆說著:「咦?......為什麼?你給我個解釋?......這外套是誰的?......既然上頭掛了榮譽勛位勛章,當然不會是我的!」
她發瘋似地努力想把衣服奪過來,說話結結巴巴:「聽著......聽著......把那個給我......我不能告訴你......這是個祕密......聽我說。」
但他生氣了,臉色發白:「我要知道這件外套怎麼會在這裡!它不是我的。」
於是,她朝著他的臉大叫:「怎麼不是,閉嘴,給我發誓......聽著......好吧,你得勛章了!」
他激動得鬆開手上大衣,跌坐在沙發裡:「我得......你是說......我得到......勛章了。」
「是的......這是個祕密,一個大祕密......」(未完待續)
註1:高中生畢業會考(baccalauréat):通過此會考,可獲得一張寫有考試成績等級的證書,代表高中學業的總表現,類似臺灣的高中文憑。法國人相當重視此項考試,有證書的學生才有資格申請大學或同等學校,找工作也較容易。這句話意即,故事中的主角高中沒畢業。
註2:社會主義者(socialiste):主張維護普遍性的公共正義,而非特定少數人的利益。
註3:巴黎公社的成員,主要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及各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曾推行政教分離、工資平等、性別平等,為的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反對國家利益由少數階級所把持。
有些人出生下來,打從開始會說話、會思考,就有一項突出的天性、一個志願,或僅僅有種被喚醒的願望。
薩可耶蒙先生自童年時期始,腦中就只有一個想法──得到勛章。年紀還很小,就會像其他孩子戴軍帽一樣,佩戴著鋅製的榮譽勛位十字勛章。而走在街上,他會挺起別有紅緞帶和金屬星星的胸脯,神氣地把手交給母親牽著。
他書讀得不好,沒通過高中生畢業會考(註1),不曉得該做什麼,但因為有些許財產,所以娶到一個漂亮的女孩。
夫妻倆住在巴黎,生活過得如富裕的上層中產階級,走進與他們同階層的圈子內,並和社交界裡的人保持關係。他們因為認識一位可能會當部長的議員而自豪,此外,他們還是兩名軍團師長的朋友。
但那個自生命初期便進入腦袋的念頭,薩可耶蒙先生始終忘不了,由於無權在禮服上佩戴有顏色的絲帶勛章,他無時無刻不感到痛苦。
在城市大道看見戴勛章的人每每總給他心上一擊。他斜眼看著他們,心中嫉妒加劇。有時,在無聊的漫長午後,他會開始計數著。他對自己說:「來吧,從馬德連納教堂到魯歐特街,看我能找到幾個。」
他慢慢地走,仔細查看行人的衣服,眼睛被訓練得遠遠就能分辨出那個小紅點。當走到路程的盡頭,他總會對這些數字感到驚奇:「八個四級榮譽章、十七個騎士榮譽勛章,竟然這麼多!如此濫發十字章,實在荒謬,且看看回程我會不會找到一樣多。」
他步履緩慢地往回走,遇上擁擠的過路群眾妨礙搜尋,讓他遺漏了人,便覺得惋惜。
他知道哪些地區戴勛章的人最多──皇家宮殿那兒到處都是。歌劇院大道的人數比不上和平街的;相較於城市大道的左側,戴勛章的人更喜歡聚在右側。
這些人似乎也有喜歡去的咖啡店和戲院。每當薩可耶蒙先生瞥見一群白髮蒼蒼的老紳士站在人行道中間,擾亂了交通,心裡便想:「這可都是些獲得四級榮譽章的長官!」他有股想上前致敬的慾望。
得到四級榮譽章的人,與普通的騎士榮譽勛章得主,舉止是有所差別的(這點他經常留意到)─前者的頭部姿態不同,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在官方的認可上擁有更高的尊敬,聲望也更遠播。
時而,薩可耶蒙先生心中也會竄升起一團怒火,所有得到勛章的人都讓他氣憤填膺,他覺得對他們懷有一股社會主義者(註2)式的仇恨。
回到家中,他會因為遇到這麼多戴十字勛章的人而深受刺激,就像饑餓的窮人從販賣食物的大型店鋪前走過那樣,大聲說道:「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有人幫我們趕走這卑鄙醜陋的政府?」
妻子訝異地問他:「你今天怎麼了?」
他回答:「我啊,我是為到處可見的不公義事情而生氣。啊,巴黎公社(註3)的人當初那麼做果真是有道理的!」
但晚餐過後,他又再度出門,前往賣勛章的店鋪流連。他細細查看各式各樣、顏色各異的徽章,真想把它們全都占為己有,然後在公眾典禮場合,在一間滿是賓客與讚嘆者的大禮堂,走在隊伍最前面,胸前閃閃發亮,一排又一排勛章隨著他肋骨的形狀彼此交疊整齊羅列。他手臂下會夾著高頂大禮帽,在一片低聲讚美中、在充滿尊敬的喧譁中,莊嚴地從人前經過,像顆光芒耀眼的明星。
可是,唉,他沒有任何名義可得到任何一種勛章!
他心想:「對一個沒擔任過任何公職的人而言,想獲得榮譽勛位勛章真是太難了。要不我來試試得個文化教育勛章應該也不錯吧?」
他不知道該如何著手,向妻子提起,妻子愣住了:「文化教育勛章?你為這方面做過些什麼啦?」
他發怒了:「你好好聽清楚我要說的!我這不就正在想該怎麼做。你有時候還真笨。」
她微微一笑:「完全正確,你說得沒錯。但你問我,我可不知道!」
他有個主意:「假如你和侯瑟藍議員談談,他或許能給我極好的建議呢?我嘛,你知道,我可不敢直接找他討論這個問題,這太微妙、太難開口了。由你來說,事情就自然多了。」
薩可耶蒙太太照他的要求去做,侯瑟藍先生承諾會對部長說。薩可耶蒙因此不時來纏他,議員最後的回答是必須提出申請,並列舉已有的頭銜。
頭銜?問題來了。他連張高中文憑也沒有。
但他仍投入了工作,他想編一本小冊子,名叫《論人民受教育的權利》。但思想貧乏,沒法完成。
他尋找較簡單的主題,依序涉獵了幾個。首先是「透過視覺來教育兒童」,他想在貧窮的地區為年幼的小孩搭建一些免費劇院。當孩子還小時,父母就帶他們來那裡,讓人們用幻燈片教他們人類所有知識的基本概念。這是名副其實的課程。頭腦藉由觀看來獲取知識,影像牢牢地刻印在記憶裡,科學因此成為看得見的事物。
以這種方式來教授世界史、地理、自然史、生物學、動物學、解剖學等等,還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
他請人印製這本論文,寄給所有議員,一人一本,每位部長各十本,共和國總統五十本,巴黎的報社也各送十本,外省的報社五本。
接著,他探討街上流動圖書館的問題,他希望政府能製造像賣橘子小販用的小車子,車上載滿書籍,派人開到街上巡迴。居民每人繳一毛錢的訂閱費,就有權每月租借十本書。
薩可耶蒙先生寫道──「人民只有為了享樂才會擱下手邊工作。既然他不主動來接受教育,就必須要讓教育去找他等等。」
他的論述沒有得到任何回響。然而他仍舊遞交了申請,得到的答覆是正在登錄中、研究中。他有把握會成功,便等待著。卻沒有任何回音。
於是,他決定自己想辦法找門路。他求見教育部長,結果是部長辦公室的專員接見了他。此人年紀輕輕,舉止已老成持重,甚至頗有權勢,只見他像彈鋼琴般按下一連串白色小按鈕,傳喚門口招待員、候見室的服務生,以及下屬職員。他向求見者確定所申請的事進展順利,建議他繼續這傑出的工作。
薩可耶蒙先生又重新投入了工作。
侯瑟藍議員,現在似乎對薩可耶蒙的事業能否成功相當關心,甚至提供了許多實用的好建議。況且他得過勛章,只不過,大家不太清楚他做了什麼而能得到這份殊榮。
他指點薩可耶蒙可著手研究的新方向,他將他介紹給一些學者組成的協會,這些人專門研究艱深科學問題,為的是想獲得一些榮譽。他甚至還到政府相關部門舉薦薩可耶蒙。
有一天,他到薩可耶蒙家吃午餐(近幾個月來,經常到他家吃飯),緊握住薩可耶蒙的手,低聲說道:「我剛剛為你爭取到一件非常好的差事。歷史工作委員會委派了你一項任務,工作內容是到法國各圖書館做研究。」
聽到消息,薩可耶蒙渾身癱軟,既無法吃也無法喝──八天後,他出發了。
他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研讀目錄、在成堆舊書的頂樓裡搜尋,書上滿布灰塵,他滿懷著對圖書館員的怨恨。
然而有天晚上,他人在盧昂,想回家抱抱一星期沒見的妻子,便搭上九點的火車,預計午夜到家。
他帶有鑰匙,悄悄地走進屋裡,因快樂而微微顫抖,高興能給她來個驚喜。但她把房門鎖住了,真惱人!於是,他隔著門高喊:「簡妮,是我!」
她應該很害怕,因為他聽見她從床上跳起,像做夢一樣自言自語。接著跑到浴室,打開門又重新關上,光著腳在房間來回快跑了好幾趟,碰撞到家具,家具上的玻璃吊飾叮噹作響。終於,她開口問:「真的是你,亞歷山大?」
他答道:「當然是我,開門呀!」
門打開了,妻子撲進他懷裡,口齒含糊:「啊,真是嚇壞我了!好個驚奇!我好高興!」
他像平常一樣條理分明地開始褪去一件件衣物。從椅子上拿起那件他習慣掛在門廳的大衣。但,忽然間,他驚訝地愣住了──大衣的鈕扣眼上繫著一段紅絲帶!
他口吃了:「這......這......這件外套上有勛章!」
妻子一個跳躍,朝他撲來,抓住他手裡衣服:「不......你搞錯了......把衣服給我。」
但他仍一直拉著大衣的袖子不肯放手,慌亂中反覆說著:「咦?......為什麼?你給我個解釋?......這外套是誰的?......既然上頭掛了榮譽勛位勛章,當然不會是我的!」
她發瘋似地努力想把衣服奪過來,說話結結巴巴:「聽著......聽著......把那個給我......我不能告訴你......這是個祕密......聽我說。」
但他生氣了,臉色發白:「我要知道這件外套怎麼會在這裡!它不是我的。」
於是,她朝著他的臉大叫:「怎麼不是,閉嘴,給我發誓......聽著......好吧,你得勛章了!」
他激動得鬆開手上大衣,跌坐在沙發裡:「我得......你是說......我得到......勛章了。」
「是的......這是個祕密,一個大祕密......」(未完待續)
註1:高中生畢業會考(baccalauréat):通過此會考,可獲得一張寫有考試成績等級的證書,代表高中學業的總表現,類似臺灣的高中文憑。法國人相當重視此項考試,有證書的學生才有資格申請大學或同等學校,找工作也較容易。這句話意即,故事中的主角高中沒畢業。
註2:社會主義者(socialiste):主張維護普遍性的公共正義,而非特定少數人的利益。
註3:巴黎公社的成員,主要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及各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曾推行政教分離、工資平等、性別平等,為的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反對國家利益由少數階級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