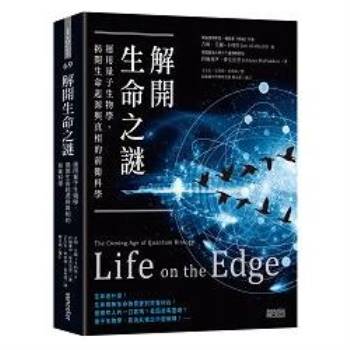生命詭祕的笑
在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裡,柴郡貓會突然消失,只留下牠露齒的笑容,這刺激愛麗絲注意到她「通常看到沒有笑容的貓,但從沒看過沒有貓的笑容」。很多生物學家感到類似的困惑,儘管他們已經知道熱力學怎麼在生物中運作,以及基因如何將形成細胞所需要的每一個步驟編碼,然而生命是什麼這個謎,仍舊對著他們露齒一笑。
我們的問題在於,每個生命細胞裡的生化反應實在太複雜。化學家人工製造出胺基酸或是糖類,幾乎每次總是只能合成單一個產物。他們必須小心控制反應所需的實驗條件,像是不同成分之間的濃度和溫度,來讓目標合成物可以最有效率地進行。這任務並不容易,而且需要小心控制許多不同儀器內部的實驗條件,例如訂做的燒瓶、冷凝器、分離器、過濾裝置和其他精密的化學儀器。但是每個你身體內的生命細胞,卻可以在一個僅有幾百萬分之一微升(註:一微升的水,體積是一立方毫米。)液體的反應室裡,持續不斷合成成千上萬不同的生化物質。所有這種種反應如何同時進行?還有,在這微小的細胞裡要怎麼協調所有這些分子的行為?這些問題是系統生物學(system biology)這個新的科學所關注的,但是我們可以很公正地說,答案仍然是個謎。
另一個生命的謎團是終有一死。化學反應的一個特點則是它們總是可逆的。我們可以寫下一個化學反應的方向:基質 → 產物。但是實際上逆向的反應:產物 → 基質,也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只不過在某一組定好的環境條件下,會導向其中一個方向。但是,總是有可能找到另外一組條件,讓逆向的化學反應發生。例如,化石燃料在空氣中燃燒,基質是碳和氧,而單一的產物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一般認為這是不可逆的反應,但是某些型態的抓碳技術,正嘗試逆轉這個反應過程,藉著外加能量去驅動逆向反應。例如,伊利諾斯大學的瑞奇・馬賽爾(Rich Masel)已經創立了一個公司——二氧化物材料公司(Dioxide Materials),目標是利用電能將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轉變成汽車的燃料。
生命卻不一樣。沒人發現過任何條件能讓反應方向變成:死細胞 → 活細胞。就是這個難題,讓我們的祖先提出靈魂這個想法。我們不再相信細胞擁有某種靈魂,但是當細胞或人死去時,究竟是什麼東西不可逆了?這時也許你會想到:那麼最近所公開的那些人造生物的科技又是什麼?這些科技的實踐者一定掌握了生命之謎的答案吧?最有名的人造生物實踐者應該是基因組序列的先驅克萊格・凡特(Craig Venter),他在2010年引發了科學風暴,他宣稱已經創造出「人造生命」。他的研究成果登上世界各地的頭條,而且點燃人對於逐漸增長的人造生物種族會占領地球的恐懼。但是凡特和他的研究小組所做的,只是去修改一個已經存在的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真的創造出新生命。他們的工作是先合成DNA,並將一種會造成山羊疾病的細菌病原體,稱為「絲狀支原體」(Mycoplasma mycoides)的整個基因碼編入DNA。然後將他們的合成DNA基因組注射到活著的細菌細胞中,並且非常巧妙地控制說服細胞去取代它原來的染色體。
這個研究毋庸置疑是項技術上的精心傑作。細胞的染色體包含180萬個基因的字母,而所有的字母必須以精確的序列串在一起。但是本質上,這些科學家所做的是執行了轉化而已,那些轉化我們本來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做到,我們便轉化食物內的化學物質到我們的肉體。
凡特和他的小組成功合成注射取代細菌自身的染色體,開啓了人工生物全新的領域,這部分我們在最後一章會再談。那可能提供了更有效率的方式,讓我們製造藥品、培育作物或是消滅汙染源。但在這些或是其他類似的實驗中,科學家並沒有創造新的生命。儘管我們有了凡特的成就,生命本質上還是很神祕,並且持續對著我們露齒一笑。諾貝爾物理學得主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堅信:「我做不出來的東西,表示我不懂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懂生命,因為我們還不能製造它。我們可以混合生化物質,可以把它們加熱,可以用光照射它們,甚至可以像瑪麗・雪萊所描寫的科學怪人一樣,用電力賦予它們生命。但是我們唯一可以製造生命的方法,是將生化物質注入已有生命的細胞,或者是吃掉它們,讓它們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為什麼我們仍然不能履行一個幾百萬兆最低階細菌每秒都可以輕鬆完成的工作?這是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埃爾溫・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在七十多年前所思考的問題,而且他那令人吃驚的答案,便是這本書核心的內容。規則一路往下
讓薛丁格感到好奇的問題,是遺傳這個神祕的生命過程。讓薛丁格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法則,讓遺傳忠誠度這麼高?換句話說,一模一樣的基因複製品,如何可以幾乎原封不動從上一代傳給下一代?
薛丁格很清楚,這些精確且可以重複驗證的古典物理與化學的定律事實上是個統計的定律,例如隨機運動的原子和分子是熱力學的核心。這意味著它們只有在平均後的結果才是真實可靠的,因為其中牽涉到非常多粒子的交互作用。回到我們撞球桌的例子,一顆球的運動是完全無法預測的,但是丟了很多球在桌上,而且讓它們隨機碰撞約一個小時,你可以預測幾乎所有的球都會掉進球袋裡。熱力學的運作是這樣的:一群原子的平均行為是可以預測的,但是單一個分子的行為卻不行。薛丁格指出,統計定律(例如熱力學所遵循的),無法精確描述只有少數粒子所組成的系統。
舉例來說,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和雅克・查爾斯(Jacques Charles)在300年前所提出的氣體定律,描述了在氣球裡的氣體體積,如何隨著加熱而膨脹或是冷卻而收縮。這個行為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學法則來描述,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理想氣體定律。一顆氣球遵守這些有條理的定律:你加熱,它會膨脹;你冷卻它,它就會收縮。它遵守著這些定律,儘管事實上它的內部充滿了數兆顆分子,而單一顆分子都像是沒有秩序的撞球,彼此之間有著完全隨機的碰撞運動,並且被氣球壁反彈回來。所以,到底這些沒有秩序的運動是如何產生有秩序的法則?
當氣球被加熱,空氣分子振動更快,這保證它們彼此的碰撞以及與氣球壁的碰撞會更用力。這些額外的力,會造成氣球的彈性表面更多的壓力(就好像它在玻爾茲曼的撞球台時,對可移動的接力棒所做的事),讓氣球膨脹。膨脹的量會和你提供多少熱有關,而且是可以完全由氣體定律來精確預測和描述。重點是單一個物體,像是氣球,嚴格遵守著氣體定律,因為它連續有彈性的表面所產生的規則運動,是由數量龐大的粒子之不規則運動所產生的。這就像薛丁格所說的,規則源自於不規則。
薛丁格認為,應該不是只有氣體定律可以從極大數量的統計性質推算出它的精確性,而是所有古典物理和化學的定律(包含流體力學或是化學反應的定律),都應該基於這個「極大數量的平均」或是「規則源自不規則」的原理。雖然充滿幾兆顆空氣分子普通大小的氣球會遵守氣體定律,但是一個只能有少量空氣分子的微小氣球卻不遵守。這是因為即使在一個穩定的溫度,這些少量的分子在小氣球內偶爾會隨機一起向外運動,導致氣球膨脹。同樣的,氣球分子偶爾會隨機的一起向內運動,導致氣球收縮。因此,一個很小的氣球,其行為是非常不可預測的。
有賴龐大數量才能產生規則性和可預測性,這在其他方面也時常遇到。舉例來說,美國打棒球的人多於加拿大人,但是加拿大玩曲棍球的,多於美國人。在這樣一個統計的「定律」下,我們可以對這兩個國家做出一些預測。例如美國會比加拿大進口更多棒球,而加拿大會比美國進口更多曲棍球。這樣一個統計定律,用在成千上百萬居民的國家,具有可預測的價值;但是曲棍球和棒球在一個小鎮的買賣狀況,例如明尼蘇達或是薩克其萬,它就無法精確預測了。
薛丁格不是只觀察到古典物理的統計定律在微觀尺度上不能成立,他做得更深入:他精確量化這個衰退的情況,計算出偏離這些統計定律的大小,與粒子數目的平方根成反比。所以一個有幾兆(百萬的平方)顆粒子的氣球,只會偏離氣體定律約百萬分之一。但是一個只有幾百顆粒子的氣球會偏離這個有規則的行為約十分之一。雖然這個氣球仍然趨於熱膨冷縮,但是它的行為無法被任何決定論的定律所描述。所有古典物理的統計定律,都受此限制:物體有大量粒子時,它們的描述成立,但是描述由少量粒子所組成的物體的行為時,就會失效。所以任何系統,如果要存在可由古典定律所描述的規則性和可靠性,必須具有非常龐大數量的粒子。
但是生命是如此嗎?它所展現的規則行為,像是遺傳的定律,可以歸類在統計定律嗎?當薛丁格沉思這個問題時,他推論出,這個支撐整個熱力學理論的「規則源自不規則」原理,不能去控制生命——因為有些非常小的生物實在是太小了,以至於不受古典定律掌控。例如,在薛丁格寫《生命是什麼?》這本書時——那時已經知道,生物會遺傳是由基因所控制,雖然基因的性質仍是個謎——他問了個簡單的問題:基因是否足夠大到可由統計的「規則源自不規則」定律來推導它們複製的精確性?他估計,一個基因的大小,不會大於邊長300埃(1埃是0.0000000001公尺)的立方體。這樣的立方體可容納大約一百萬顆原子。這聽起來好像很多,但是開平方後只有一千。所以遺傳的不精確度(或說是「噪音」)大約是千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零點一。假如遺傳是基於古典統計定律,那麼它應該每一千次會產生一次錯誤(也就是偏離定律)。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基因可以忠實地遺傳給下一代,突變的頻率是每10億次少於一次。這個極高的忠誠度說服了薛丁格,讓他相信遺傳的定律無法建立在「規則源自不規則」的這個古典定律之下。他提出,基因更像是原子或是分子,是根據非古典並且奇特的科學法則,也就是他所協力建立的量子力學。
他第一次發表這項理論,是1943年在都柏林三一學院所做的一系列的演講中,而內容在隔年發表在《生命是什麼?》書中。他寫道:「生命有機體似乎是巨觀的系統,它其中一部分的行為非常接近……那些所有系統在溫度接近絕對零度、而且分子的不規則被移除時的行為。」我們之後很快就會發現,在絕對零度時,所有物體遵循的是量子定律,而不是熱力學定律。如同薛丁格所宣稱的,生命是一種量子的現象,使之能在空中飛行、用兩隻或四隻腳走路、在大海裡游泳、從土裡生長,或是閱讀這本書。
隔閡
薛丁格的書發表的幾年後,發現了DNA的雙股螺旋並且迅速帶動了分子生物學,這是一個發展蓬勃而且不涉及量子現象的學科。生物學家已經建立基因選殖(gene cloning)、基因工程、基因指紋分析(genome fingerprinting)、基因組測序(genome sequencing)等學說。大體上來說,他們安於忽略數學上具有挑戰性的量子世界。雖然偶爾會出現生物學結合量子力學的討論,但是大部分科學家都忘了薛丁格大膽的主張:關於生命得用量子力學來解釋的這個想法,許多人甚至還公開攻擊它。許多當時被薛丁格的主張吸引,卻仍持懷疑態度的人,主要都是根深柢固相信,精巧的量子態無法存活在生命有機體中溫暖、潮濕的分子環境。就像我們上一章所討論到的,這是為什麼許多科學家(到現在還是很多),非常懷疑鳥類的羅盤是由量子力學所控制這類想法的主要的原因。你應該還記得我們在第一章討論這個議題時,說到物質裡的量子特性,會被龐大物體裡隨機排列的分子「洗掉」。隨著我們對熱力學的了解,現在可以知道這個消散的來源:它就是像撞球一樣的分子相互碰撞,也是薛丁格所說的「規則源自不規則」的統計定律的來源。散亂的粒子,只有在特殊的環境下可以重新排列去展現它們所隱藏的量子特性,而且通常很短暫。例如,我們已經知道身體裡散亂的自旋氫原子核,如何排列在一起產生一個「相干的」(coherent)核磁共振影像的訊號,這是利用量子自旋的特性——但是只有在外加一個巨大磁鐵製造出非常強大的磁場時能做到。只要磁場一消失,粒子會立刻受分子碰撞而再次變成隨機的排列,而且量子的訊號會變得散亂而且不可偵測。這個小心排列的量子力學系統被隨機的分子運動所瓦解的過程,稱為「退相干」(decoherence),而且它很快就消滅了 巨大無生命物體中神祕的量子效應。
溫度會增加分子碰撞的能量和速度,所以退相干在更高的溫度下會發生得更快。但是不要認為這裡的高溫是指很熱的溫度。事實上,即使是室溫下,退相干幾乎瞬間就發生了。這就是為什麼大家一開始就認定,溫暖的生命體不太可能維持精巧的量子狀態。唯有物體降到接近絕對零度(就是攝氏-273度),這時所有隨機分子運動全部停止,所以避免了退相干的過程,量子力學才得以施展。我們之前引用薛丁格的那段話,意涵也就清楚浮現了。他主張,生命以某種不明原因,讓自己可以去執行那些通常只能在比任何生命物體的溫度低攝氏273度的環境才能執行的工作。約當和薛丁格都認為,生命和無生命物體是不同的,而且繼續閱讀下去你會發現,生命體中所存在數量相當少且高度有規則的粒子,像是那些存在於基因裡或是鳥類羅盤裡的東西,可以對整個有機體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就是約當所說的擴增(amplification)以及薛丁格所說的規則源自規則。我們眼睛的顏色、鼻子的形狀、你性格的表現、你理解力的程度,甚至是你不健康的嗜好,事實上都是由正好46個有高度規則的超級分子:DNA染色體所決定的,而這些超級分子是你從父母那裡遺傳過來的。
在我們所知的宇宙中,沒有任何無生命的巨觀物體具有這種敏感度能處理物質的複雜結構——這是由量子力學而不是古典定律所支配的。薛丁格認為,這就是為什麼生命是如此特殊。2014年,薛丁格發表他的書的70年之後,我們終於可以體會,他對於生命是什麼所提出的非凡的答案中所蘊含的意義。
(摘自本書第二章 生命是什麼?)
在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裡,柴郡貓會突然消失,只留下牠露齒的笑容,這刺激愛麗絲注意到她「通常看到沒有笑容的貓,但從沒看過沒有貓的笑容」。很多生物學家感到類似的困惑,儘管他們已經知道熱力學怎麼在生物中運作,以及基因如何將形成細胞所需要的每一個步驟編碼,然而生命是什麼這個謎,仍舊對著他們露齒一笑。
我們的問題在於,每個生命細胞裡的生化反應實在太複雜。化學家人工製造出胺基酸或是糖類,幾乎每次總是只能合成單一個產物。他們必須小心控制反應所需的實驗條件,像是不同成分之間的濃度和溫度,來讓目標合成物可以最有效率地進行。這任務並不容易,而且需要小心控制許多不同儀器內部的實驗條件,例如訂做的燒瓶、冷凝器、分離器、過濾裝置和其他精密的化學儀器。但是每個你身體內的生命細胞,卻可以在一個僅有幾百萬分之一微升(註:一微升的水,體積是一立方毫米。)液體的反應室裡,持續不斷合成成千上萬不同的生化物質。所有這種種反應如何同時進行?還有,在這微小的細胞裡要怎麼協調所有這些分子的行為?這些問題是系統生物學(system biology)這個新的科學所關注的,但是我們可以很公正地說,答案仍然是個謎。
另一個生命的謎團是終有一死。化學反應的一個特點則是它們總是可逆的。我們可以寫下一個化學反應的方向:基質 → 產物。但是實際上逆向的反應:產物 → 基質,也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只不過在某一組定好的環境條件下,會導向其中一個方向。但是,總是有可能找到另外一組條件,讓逆向的化學反應發生。例如,化石燃料在空氣中燃燒,基質是碳和氧,而單一的產物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一般認為這是不可逆的反應,但是某些型態的抓碳技術,正嘗試逆轉這個反應過程,藉著外加能量去驅動逆向反應。例如,伊利諾斯大學的瑞奇・馬賽爾(Rich Masel)已經創立了一個公司——二氧化物材料公司(Dioxide Materials),目標是利用電能將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轉變成汽車的燃料。
生命卻不一樣。沒人發現過任何條件能讓反應方向變成:死細胞 → 活細胞。就是這個難題,讓我們的祖先提出靈魂這個想法。我們不再相信細胞擁有某種靈魂,但是當細胞或人死去時,究竟是什麼東西不可逆了?這時也許你會想到:那麼最近所公開的那些人造生物的科技又是什麼?這些科技的實踐者一定掌握了生命之謎的答案吧?最有名的人造生物實踐者應該是基因組序列的先驅克萊格・凡特(Craig Venter),他在2010年引發了科學風暴,他宣稱已經創造出「人造生命」。他的研究成果登上世界各地的頭條,而且點燃人對於逐漸增長的人造生物種族會占領地球的恐懼。但是凡特和他的研究小組所做的,只是去修改一個已經存在的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真的創造出新生命。他們的工作是先合成DNA,並將一種會造成山羊疾病的細菌病原體,稱為「絲狀支原體」(Mycoplasma mycoides)的整個基因碼編入DNA。然後將他們的合成DNA基因組注射到活著的細菌細胞中,並且非常巧妙地控制說服細胞去取代它原來的染色體。
這個研究毋庸置疑是項技術上的精心傑作。細胞的染色體包含180萬個基因的字母,而所有的字母必須以精確的序列串在一起。但是本質上,這些科學家所做的是執行了轉化而已,那些轉化我們本來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做到,我們便轉化食物內的化學物質到我們的肉體。
凡特和他的小組成功合成注射取代細菌自身的染色體,開啓了人工生物全新的領域,這部分我們在最後一章會再談。那可能提供了更有效率的方式,讓我們製造藥品、培育作物或是消滅汙染源。但在這些或是其他類似的實驗中,科學家並沒有創造新的生命。儘管我們有了凡特的成就,生命本質上還是很神祕,並且持續對著我們露齒一笑。諾貝爾物理學得主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堅信:「我做不出來的東西,表示我不懂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懂生命,因為我們還不能製造它。我們可以混合生化物質,可以把它們加熱,可以用光照射它們,甚至可以像瑪麗・雪萊所描寫的科學怪人一樣,用電力賦予它們生命。但是我們唯一可以製造生命的方法,是將生化物質注入已有生命的細胞,或者是吃掉它們,讓它們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為什麼我們仍然不能履行一個幾百萬兆最低階細菌每秒都可以輕鬆完成的工作?這是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埃爾溫・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在七十多年前所思考的問題,而且他那令人吃驚的答案,便是這本書核心的內容。規則一路往下
讓薛丁格感到好奇的問題,是遺傳這個神祕的生命過程。讓薛丁格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法則,讓遺傳忠誠度這麼高?換句話說,一模一樣的基因複製品,如何可以幾乎原封不動從上一代傳給下一代?
薛丁格很清楚,這些精確且可以重複驗證的古典物理與化學的定律事實上是個統計的定律,例如隨機運動的原子和分子是熱力學的核心。這意味著它們只有在平均後的結果才是真實可靠的,因為其中牽涉到非常多粒子的交互作用。回到我們撞球桌的例子,一顆球的運動是完全無法預測的,但是丟了很多球在桌上,而且讓它們隨機碰撞約一個小時,你可以預測幾乎所有的球都會掉進球袋裡。熱力學的運作是這樣的:一群原子的平均行為是可以預測的,但是單一個分子的行為卻不行。薛丁格指出,統計定律(例如熱力學所遵循的),無法精確描述只有少數粒子所組成的系統。
舉例來說,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和雅克・查爾斯(Jacques Charles)在300年前所提出的氣體定律,描述了在氣球裡的氣體體積,如何隨著加熱而膨脹或是冷卻而收縮。這個行為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學法則來描述,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理想氣體定律。一顆氣球遵守這些有條理的定律:你加熱,它會膨脹;你冷卻它,它就會收縮。它遵守著這些定律,儘管事實上它的內部充滿了數兆顆分子,而單一顆分子都像是沒有秩序的撞球,彼此之間有著完全隨機的碰撞運動,並且被氣球壁反彈回來。所以,到底這些沒有秩序的運動是如何產生有秩序的法則?
當氣球被加熱,空氣分子振動更快,這保證它們彼此的碰撞以及與氣球壁的碰撞會更用力。這些額外的力,會造成氣球的彈性表面更多的壓力(就好像它在玻爾茲曼的撞球台時,對可移動的接力棒所做的事),讓氣球膨脹。膨脹的量會和你提供多少熱有關,而且是可以完全由氣體定律來精確預測和描述。重點是單一個物體,像是氣球,嚴格遵守著氣體定律,因為它連續有彈性的表面所產生的規則運動,是由數量龐大的粒子之不規則運動所產生的。這就像薛丁格所說的,規則源自於不規則。
薛丁格認為,應該不是只有氣體定律可以從極大數量的統計性質推算出它的精確性,而是所有古典物理和化學的定律(包含流體力學或是化學反應的定律),都應該基於這個「極大數量的平均」或是「規則源自不規則」的原理。雖然充滿幾兆顆空氣分子普通大小的氣球會遵守氣體定律,但是一個只能有少量空氣分子的微小氣球卻不遵守。這是因為即使在一個穩定的溫度,這些少量的分子在小氣球內偶爾會隨機一起向外運動,導致氣球膨脹。同樣的,氣球分子偶爾會隨機的一起向內運動,導致氣球收縮。因此,一個很小的氣球,其行為是非常不可預測的。
有賴龐大數量才能產生規則性和可預測性,這在其他方面也時常遇到。舉例來說,美國打棒球的人多於加拿大人,但是加拿大玩曲棍球的,多於美國人。在這樣一個統計的「定律」下,我們可以對這兩個國家做出一些預測。例如美國會比加拿大進口更多棒球,而加拿大會比美國進口更多曲棍球。這樣一個統計定律,用在成千上百萬居民的國家,具有可預測的價值;但是曲棍球和棒球在一個小鎮的買賣狀況,例如明尼蘇達或是薩克其萬,它就無法精確預測了。
薛丁格不是只觀察到古典物理的統計定律在微觀尺度上不能成立,他做得更深入:他精確量化這個衰退的情況,計算出偏離這些統計定律的大小,與粒子數目的平方根成反比。所以一個有幾兆(百萬的平方)顆粒子的氣球,只會偏離氣體定律約百萬分之一。但是一個只有幾百顆粒子的氣球會偏離這個有規則的行為約十分之一。雖然這個氣球仍然趨於熱膨冷縮,但是它的行為無法被任何決定論的定律所描述。所有古典物理的統計定律,都受此限制:物體有大量粒子時,它們的描述成立,但是描述由少量粒子所組成的物體的行為時,就會失效。所以任何系統,如果要存在可由古典定律所描述的規則性和可靠性,必須具有非常龐大數量的粒子。
但是生命是如此嗎?它所展現的規則行為,像是遺傳的定律,可以歸類在統計定律嗎?當薛丁格沉思這個問題時,他推論出,這個支撐整個熱力學理論的「規則源自不規則」原理,不能去控制生命——因為有些非常小的生物實在是太小了,以至於不受古典定律掌控。例如,在薛丁格寫《生命是什麼?》這本書時——那時已經知道,生物會遺傳是由基因所控制,雖然基因的性質仍是個謎——他問了個簡單的問題:基因是否足夠大到可由統計的「規則源自不規則」定律來推導它們複製的精確性?他估計,一個基因的大小,不會大於邊長300埃(1埃是0.0000000001公尺)的立方體。這樣的立方體可容納大約一百萬顆原子。這聽起來好像很多,但是開平方後只有一千。所以遺傳的不精確度(或說是「噪音」)大約是千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零點一。假如遺傳是基於古典統計定律,那麼它應該每一千次會產生一次錯誤(也就是偏離定律)。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基因可以忠實地遺傳給下一代,突變的頻率是每10億次少於一次。這個極高的忠誠度說服了薛丁格,讓他相信遺傳的定律無法建立在「規則源自不規則」的這個古典定律之下。他提出,基因更像是原子或是分子,是根據非古典並且奇特的科學法則,也就是他所協力建立的量子力學。
他第一次發表這項理論,是1943年在都柏林三一學院所做的一系列的演講中,而內容在隔年發表在《生命是什麼?》書中。他寫道:「生命有機體似乎是巨觀的系統,它其中一部分的行為非常接近……那些所有系統在溫度接近絕對零度、而且分子的不規則被移除時的行為。」我們之後很快就會發現,在絕對零度時,所有物體遵循的是量子定律,而不是熱力學定律。如同薛丁格所宣稱的,生命是一種量子的現象,使之能在空中飛行、用兩隻或四隻腳走路、在大海裡游泳、從土裡生長,或是閱讀這本書。
隔閡
薛丁格的書發表的幾年後,發現了DNA的雙股螺旋並且迅速帶動了分子生物學,這是一個發展蓬勃而且不涉及量子現象的學科。生物學家已經建立基因選殖(gene cloning)、基因工程、基因指紋分析(genome fingerprinting)、基因組測序(genome sequencing)等學說。大體上來說,他們安於忽略數學上具有挑戰性的量子世界。雖然偶爾會出現生物學結合量子力學的討論,但是大部分科學家都忘了薛丁格大膽的主張:關於生命得用量子力學來解釋的這個想法,許多人甚至還公開攻擊它。許多當時被薛丁格的主張吸引,卻仍持懷疑態度的人,主要都是根深柢固相信,精巧的量子態無法存活在生命有機體中溫暖、潮濕的分子環境。就像我們上一章所討論到的,這是為什麼許多科學家(到現在還是很多),非常懷疑鳥類的羅盤是由量子力學所控制這類想法的主要的原因。你應該還記得我們在第一章討論這個議題時,說到物質裡的量子特性,會被龐大物體裡隨機排列的分子「洗掉」。隨著我們對熱力學的了解,現在可以知道這個消散的來源:它就是像撞球一樣的分子相互碰撞,也是薛丁格所說的「規則源自不規則」的統計定律的來源。散亂的粒子,只有在特殊的環境下可以重新排列去展現它們所隱藏的量子特性,而且通常很短暫。例如,我們已經知道身體裡散亂的自旋氫原子核,如何排列在一起產生一個「相干的」(coherent)核磁共振影像的訊號,這是利用量子自旋的特性——但是只有在外加一個巨大磁鐵製造出非常強大的磁場時能做到。只要磁場一消失,粒子會立刻受分子碰撞而再次變成隨機的排列,而且量子的訊號會變得散亂而且不可偵測。這個小心排列的量子力學系統被隨機的分子運動所瓦解的過程,稱為「退相干」(decoherence),而且它很快就消滅了 巨大無生命物體中神祕的量子效應。
溫度會增加分子碰撞的能量和速度,所以退相干在更高的溫度下會發生得更快。但是不要認為這裡的高溫是指很熱的溫度。事實上,即使是室溫下,退相干幾乎瞬間就發生了。這就是為什麼大家一開始就認定,溫暖的生命體不太可能維持精巧的量子狀態。唯有物體降到接近絕對零度(就是攝氏-273度),這時所有隨機分子運動全部停止,所以避免了退相干的過程,量子力學才得以施展。我們之前引用薛丁格的那段話,意涵也就清楚浮現了。他主張,生命以某種不明原因,讓自己可以去執行那些通常只能在比任何生命物體的溫度低攝氏273度的環境才能執行的工作。約當和薛丁格都認為,生命和無生命物體是不同的,而且繼續閱讀下去你會發現,生命體中所存在數量相當少且高度有規則的粒子,像是那些存在於基因裡或是鳥類羅盤裡的東西,可以對整個有機體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就是約當所說的擴增(amplification)以及薛丁格所說的規則源自規則。我們眼睛的顏色、鼻子的形狀、你性格的表現、你理解力的程度,甚至是你不健康的嗜好,事實上都是由正好46個有高度規則的超級分子:DNA染色體所決定的,而這些超級分子是你從父母那裡遺傳過來的。
在我們所知的宇宙中,沒有任何無生命的巨觀物體具有這種敏感度能處理物質的複雜結構——這是由量子力學而不是古典定律所支配的。薛丁格認為,這就是為什麼生命是如此特殊。2014年,薛丁格發表他的書的70年之後,我們終於可以體會,他對於生命是什麼所提出的非凡的答案中所蘊含的意義。
(摘自本書第二章 生命是什麼?)